王堯|“思想”如何成為“文學”的內在構成——對百年文學思想史路徑的思考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32分钟前
一百年與二十年: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專欄
主持人語
21世紀已進入第二個十年,談及這20年的變遷,可以列舉城市化進程高速發展,網絡媒介深度介入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革命性技術不斷迭代更新,等等,而這些無不屬於“器物”的層面。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已不再用思想潮流或思想事件來命名時代,而慣於以“器”為名,指稱我們這個時代的變遷?蔡元培先生在為總結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撰寫《總序》時,將新文化運動比作歐洲的文藝復興,以為新文學、白話文這些“器”的革命實則思想的革命,並高屋建瓴地論斷“為什麼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文學革命同時是思想革命,文學家同時是思想家,這是百年前新文學發端之時的樣貌。10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對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第二個十年同樣做一“總審查”,我們如何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我們是否仍能擲地有聲地説,“文學傳導了思想,文學家同時也是思想家”?100年前的新文化時代,天才成羣結隊而來,今天,締造我們這個時代新文化的天才在哪裏?我們是否準備好了迎接成羣結隊的天才的姿態與土壤?
21世紀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設立“一百年與二十年: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欄目,既是一種回望,也是一種對視,更是一種自省;不僅僅是希望從那種不無歷史侷限性卻影響至今的文學認識論中跳脱出來,站在一百年的歷史視野下重新看待文學是什麼、文學如何發展的問題,而更要在思想已變得稀缺的當下,為日益“內卷化”的文學和文學研究“接枝”(李歐梵語)——不僅是在縱向的古今之間,也在橫向的跨界之間。陳平原先生曾主張將“五四”作為一種“思想操練”,因它是可以“砥礪思想與學問”的“磨刀石”,值得後來者與之不斷保持對話。在一百年與二十年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係,將不僅僅是線性意義、邏輯意義、解釋意義上的,而通過諸如“邀請古人成為我們的當代人”(趙汀陽語)、“查知比對(ChatGPT)的歷史‘比對’”(朱壽桐語)這樣的思想穿越,我們或將由此獲得更豐富的思想的“偶合”和文學的激發,看到思想與思想之間的互相磨礪、彼此點化,從而得以在新的視野下重新發現問題,或讓“問題重新出生”。
文學和文學研究何以跨出近幾十年越來越邊緣化的境地或越來越窄化的路徑,學界亦曾不斷嘗試“接枝”,從“歷史化”到“文化研究”到“社會學視野”,文學不斷與“方法”鏈接,甚至淪為方法的“跑馬場”。而近來學界關於“文學性”的討論則顯示,學者們開始嘗試在文學本身的特性與文學的外部之間探索某種平衡,這是一種立足文學自身的再問題化,也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返景入深林”。“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便是欲將“外部影響”轉化為“內部生成”的一種考察,不僅是在思想史和文學史跨界的意義上展開,更是嘗試建構一種文學思想的整體性,在一種更大的文學觀下,展開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既是學問也是心靈的研究。
主持人——王堯、葉祝弟

“思想”如何成為“文學”的內在構成
——對百年文學思想史路徑的思考
王堯 | 蘇州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王堯教授
**在新文化運動大背景中考察,“新文學”是知識分子尋找思想文化出路的一種形式。**如果,我們將“現代中國”作為一種重要思想,則“現代中國”的“新文學”亦如是,“新文學”因而被視為現代民族國家敍事。新文學很長一段時間被“現代文學”替代,作為另一種新文學的“當代文學”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想象與實踐形式。從“現代文學”到“當代文學”,在思想和語境上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換,這兩種“主義”也成為我們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思想分析框架。在這個大框架中,文學與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交互依存”,形成了複雜斑斕的圖景。
**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置於思想史視野中加以研究,是1980年代以來學界的一種路徑。**一些學者由文學轉向思想史研究,一些文學研究者即便不是專治思想史,思想史作為一種方法也對他們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同樣,思想史研究者也以文學為分析對象。雖然,學科建制劃定了不同研究領域,但在思想史與文學史之間始終存在着無法忽視的“關聯性”。基於思想與文學、思想史與文學史的“關聯性”及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史,我們現在清晰提出“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這一命題,以強化這一跨學科研究。
跨學科:思想史與文學史
不同的視野、方法及其所涉及的領域總有重疊之處,這是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之一。我們討論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首先確認的是,思想史本身便是跨學科的。《思想史期刊》首任主編洛夫喬伊認為,思想史的內容包括哲學史、科學史、宗教史和神學史、藝術史、教育史、社會學史、語言學史、民俗和民族誌史、經濟學和政治學史、文學史和社會史。根據《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中彼得·沃森的介紹,《思想史期刊》第二任主編菲利普·P.維納(Phillip P. Wiener)主編的《思想史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覆蓋了七個核心領域:關於自然的外部秩序的思想,關於人性的思想,文學和美學,關於歷史的思想,經濟、法律、政治思想和制度,宗教與哲學,形式邏輯數學和語言學思想。文學是思想史研究所跨學科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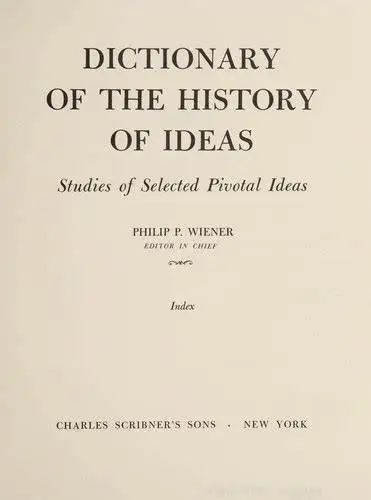
《思想史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維納在《思想史詞典》1973年版的序言中,談到了“思想”是如何對其他學科產生影響的:“藝術家、作家、科學家在創作與研究中,每當其主題超出既定的形式、風格或傳統方法時,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借鑑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思想觀念。藝術語言常常會表現出文學主題、科學發現、經濟發展、政治變化的影響。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是從古代關於自然和人的神話和形而上學觀念中分化出來的,在各自歷史發展中利用了經過檢驗的觀念和實驗方法的交叉孕育而產生的分析結果和實驗方法。這種思想的外向影響促使思想史學家探索人類在不同領域的藝術和科學成就的關鍵線索。在尊重專業領域的完整性和訴求的同時,思想史家通過追蹤思想的主要和次要關注所產生的文化根源和歷史影響,對知識做出了特殊的貢獻。”關於這段文字需要推敲之處是,藝術家、作家的創作與思想的關係遠比維納所説的要複雜得多,借鑑“專業領域之外的思想觀念”並不完全是因為其主題超出了既定的形式、風格或傳統方法;“思想觀念”有跨專業的“共同性”,藝術家、作家有時恰恰是因為在這些“思想觀念”影響下,其創作的主題才超出了既定的形式、風格或傳統方法。
**我們的重點當然不是研究作為思想史一部分的文學,不是把文學史作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但思想史涉及文學的方法和論述也是我們以思想史為視野研究文學的跨學科基礎之一。**在中國學者的思想史著作中,文學也是思想史考察的重要內容,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便收錄了《二十世紀中國(大陸)文藝一瞥》。《思想史詞典》之三“美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中的文學及藝術思想史概念”收錄的關鍵詞有:“文學史裏的寓言”“作為美學原則的模糊性”“18世紀的古今之爭”“藝術與戲劇”“為藝術而藝術”“文學中的巴洛克”“19世紀中葉前關於美的諸多理論”“惡魔學”“文學的演變”“文學的表現主義”“美學史裏的形式”“從文藝復興至1770年的天才”“天才:藝術的個人主義與藝術家們”“音樂天才”“19世紀中葉以後關於美的理論”“淨化”“偶然生成的圖像”“文學中的古典主義”“藝術分類”“喜劇意識”“藝術中的創造性”“文學批評”“哥特式概念”“音樂中的和諧或狂喜”“圖像學”“藝術中的印象派”“反諷”“文學及其同源詞”“文學悖論”“千禧年主義”“摹仿”“母題”“浮士德主題”“關於山林的文學觀念”“音樂作為惡魔的藝術”“音樂作為神聖的藝術”“古代神話”“聖經時代的神話”“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神話”“文學史的分期”“柏拉圖主義中的修辭與文學理論”“從古代至18世紀中葉的詩歌與詩學”“文學、藝術及科學中的現實主義”“柏拉圖之後的修辭學”“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約1780年—約1830年)”“維多利亞時期的情感與感傷主義”“英國文學史的神話(17至18世紀)”“18至19世紀的神話”“19至20世紀的神話”“藝術中的自然主義”“藝術中的新古典主義”“牛頓的《光學》與18世紀的想象力”“文學風格”“外界自然的崇高”“文學中的象徵及象徵主義”“從文藝復興至1770年美學史的品位”“節制及基本美德的準則”“悲劇意識”“詩畫”等。作為思想史詞典,其中的這些可以稱之為文藝學的條目恰恰是以“思想史”概念出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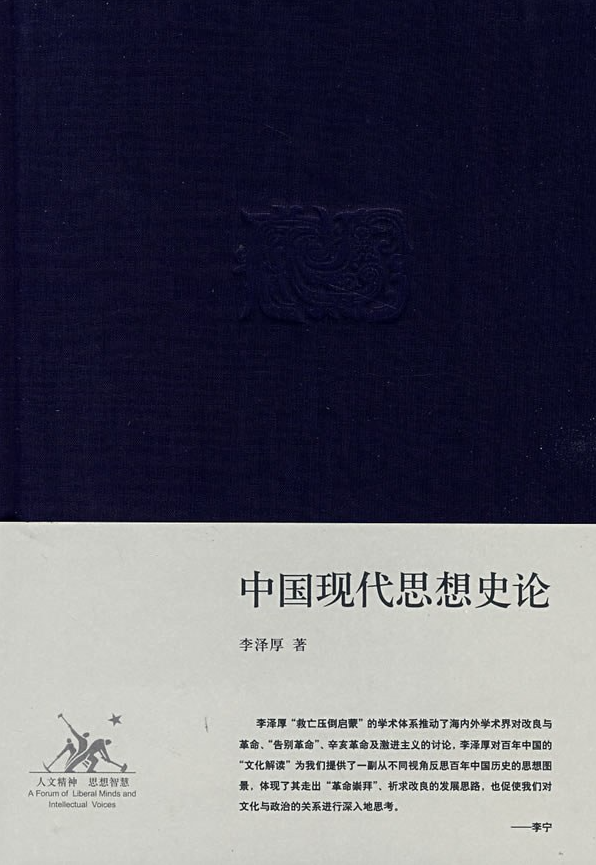
李澤厚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思想史旁及其他學科,特別是其與文學藝術的交叉,是許多學者注意到的現象。在英國學者邁克爾·彼蒂斯看來,“任何對思想史的一般考察,不僅要考慮政治和社會觀念,而且要考慮它們與以下諸多方面的互動,其中包括自然科學、哲學和宗教思想,以及那些與‘文化’史明顯交叉的文學和藝術的發展。只要語詞仍然是我們使用文獻中話語的主要載體”。正是基於這種互動,哲學、文學批評和政治學等領域都出現了代表性的思想史家。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尚未使用“思想史”這一概念,如果換一個角度,陳獨秀、魯迅、胡適等都是跨學科的,文學家的魯迅也是思想家。美國學界在學科的劃分上似乎比英國和歐洲大陸要大而化之:“美國的職業歷史學家在研究思想史方面與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史學家不同,長期以來,那些至今在絕大多數英國和歐洲大陸學界看來仍屬於‘文學史’或‘哲學史’的部分,在美國學界卻被視為歷史研究本身的一個分支。”近幾年來,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史學化”傾向的討論,從更大的學科範圍看,也是視野和方法的差異之爭。
“思想史”視野諸要素
**何為思想史,也許是我們討論思想史視野(方法)的前提。**確實如一些學者所説,“何為思想史”這是一個相當曖昧的問題。英國學者斯蒂芬·柯林尼認為,如果用一句話來定義思想史,我們肯定會有侷限。他從思想史的功能出發對思想史做了這樣的解釋而不是定義:“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分支,思想史的功能在於理解那些共同構成以往思想或反思生活的觀念、主張、信仰、預設、立場以及成見。這種思想生活必然與該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相一致,彼此間並無明確的界線。”這一理解與侯外廬的觀念比較接近,他在《我是怎樣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一文中説:“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會史研究為前提,着重於綜合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包括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同時注意每種思想學説的‘橫通’(歷史時代聯繫)和‘縱通’(思想源流演變)關係。”寬泛地説,觀念、主張、思想、信仰、預設、立場及成見,是思想史的基本內容。我注意到,斯蒂芬·柯林尼上述觀點中包含了“生活”這一概念,如何理解思想史中的“生活”,王汎森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發表了頗有見地的觀點。他認同克羅齊“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職能”的觀點,提出“如果想了解思想在歷史發展中實際的樣態,則不能忽略‘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性’的問題。**所以,一方面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程方式’,另一方面是‘生活是思想的一程方式’”。就文學而言,“生活”是一個更為重要的概念。**借用喬治·艾略特的話説,文學藝術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放大生命體驗、把我們與同伴的接觸延展到我們個人際遇以外的一種模式。”(《德意志生活的自然歷史》,1856)文學源於生活,但思想賦予生活以意義,當生活發生重大變化時,總有一種思想與生活處於親和狀態,也總有一種思想和生活長於緊張狀態。作家的思想視角不同,會發現和理解不一樣的生活,並去建構不同的文學的生活世界。作家的“思想生活”也因此成為關鍵詞。**除了這些要素外,我以為“知識”也應該納入其中。**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的“導論”中談到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分野,同時也強調了知識、學術、思想三者的相互依存:“但是,我必須説明我並不相信離開知識性的學術,思想可以獨立存在,也不相信沒有思想,而學術可以確立知識的秩序。”知識是思想的基礎,作為知識生產的文學研究形成了相關學科的學術史。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則是對作為知識生產的文學和文學研究的一種清理。
**在上述關於思想史的諸要素中,“觀念”尤為引人注目。“觀念”作為一種意識,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在文學研究中,關於理論、思潮流派和作家創作觀的研究都貫穿了“觀念”。當美國學者洛夫喬伊首次使用“觀念史”後,“觀念史”研究便成為“思想史”的一種方法。“觀念史”方法首先主張分離出某些構成複雜信條和理論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觀念單元”。中國學者也呼應了這種“觀念史”研究方法,在文學研究中進行關鍵詞的研究便顯示了這一方法的影響。借用“觀念單元”這一概念,我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實際上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單元,比如:啓蒙、個人、人道主義、形式、審美和純文學;集體、階級、大眾、政治和現實主義等。對不同觀念的認同,構成了不同的思想羣體。以思想來劃分文學羣體,這是我們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形成的學術方法,其慣性一直在延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結構深受這種方法的影響。觀念或觀念單元的劃分,形成了思想史研究中一種主題建構的方法:“就思想史而言,有兩個經常相互交叉的有關該領域的主題的建構得到了許多職業歷史學家的認可,歷史學家用以區分這兩種建構的詞彙至今仍然變動不居,但某些典型的且有時帶有誤導性質的二元對立仍能夠揭示這一區分的某些方面:諸如精英與大眾、學者與民眾、觀念與情感、分析性的與象徵性的,以及理性的與宗教的。”在文學研究中,許多單元觀念也成為文學主題建構的基礎,如我們熟悉的啓蒙/救亡、傳統/現代、中國/西方、文明/愚昧、人文/技術等。

阿瑟·奧肯·洛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
**這種以主題建構思想脈絡的方法,在西方思想史研究中是清晰的。**彼得·沃森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的“前言”中曾經談到思想史研究的一種路徑是強調“大”思想之間的連續性:“例如,在諸如‘進步’‘自然’‘文明’‘個人主義’‘權力’和‘什麼是現代’‘什麼不是現代’等熱門話題上,論著甚多。許多學者,尤其是政治歷史學家和道德哲學家,把貫穿歷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脈絡看作圍繞自由和個人主義兩個主題而推進的道德傳奇。”在討論“自由”和“個人主義”這兩個主題時,彼得·沃森進一步列舉了相關思想家的不同側重,而這些思想家對中國的文學研究者或多或少都產生過影響:“有人把歷史看成一部道德演進的宏大敍事,伊曼努爾·康德就是其中之一。以賽亞·伯林還花了大量筆墨界定和完善不同的‘自由’概念,解釋在不同的政治和思想體制下以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自由是如何被理解的。個人主義的研究近來急劇增加,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它代表了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丹尼爾·丹內特在其近著《自由的進化》中,描述了歷史上個人主義的發展歷程以及自由如何發展,如何造福人類的不同方式。自由本身既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特別能激發思想生成的心理/政治條件。”反顧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自由”和“個人主義”的思想觀念對現代文學史的思想框架影響深刻,而“革命”和“集體主義”同樣深刻影響了當代文學史的論述。這兩種思想脈絡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交替出現,這些知識、觀念、思想和信仰在中國的文學語境中是如何生成的,這些在中國語境中已經具象化的概念、觀點、思想,有沒有形成一條能夠貫穿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脈絡?如果這條脈絡不是單一的,那麼,其思想的網絡又是如何結構的?這些問題都涉及思想與思想語境的關係,因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以思想史為視野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方法和內容就變得十分重要。
方法:語境中的文本
關於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思想史研究》在給“什麼是思想史”欄目加的“編者按”中簡要介紹了西方學界“施特勞斯學派”和“劍橋學派”在思想史方法、文本解釋、學理指向等方面的根本性分歧。“施特勞斯學派”重視對古代經典的重新翻譯和整理,對經典文本予以“注經式”解釋和演繹,在方法論上強調經典文本所承載信息的“顯白”與“隱蔽”,進而要求讀者從文本的字裏行間發現文本本身的“自足性”“連貫性”以及所指涉問題的“永恆性”。“劍橋學派”在方法論上全然反對“施特勞斯學派”,其核心主張是“語境中的觀念”,“觀念”首先指涉的是“文本”,“語境”的內涵則非常複雜。和“施特勞斯學派”不同,“劍橋學派”的文本釋讀方法是:文本在語境中是絕對敞開的,融入語境的文本才能被真正理解,如此才能使思想史家避免陷入“時代誤置”。兩者都重視文本,在這個意義上史學家(包括文學史家)都是文本的闡釋者,區別在於,一者強調文本的“自足性”,一者強調文本的“敞開性”(語境中的文本)。
**觀念史和文本解釋的方法也受到質疑,文學場域和話語理論的出現或許彌補了一些方法的偏頗。**在米歇爾·福柯的影響下,將“觀念史”納入“意義結構”的研究得到長足發展。一些學者主張:“我們不應當將目光侷限在文本或觀念單元上,而應當集中於特定歷史時期總體的社會和政治語彙。由此出發,我們最終能夠將那些重要的文本放在恰當的思想語境之中,將目光轉向這些文本得以產生的意義領域,並進而為這種意義領域作出貢獻。”這種主張和“劍橋學派”的方法是呼應的。回顧這些年的文學研究,雖然未必可以進行嚴格的流派劃分,但大致上也可以分為以文本為中心的研究和語境中的文本研究兩條路徑。這也恰恰説明了在人文學科內部,許多方法是相通的。

米歇爾·福柯
**如果我們接受觀念首先指涉文本這一思想,那麼,和觀念纏繞的文本,就不只是我們通常所説的“文學文本”。**我們所講的文學文本通常是指作為語言系統的作品,在形態上分為小説、詩歌、散文和戲劇等。將文學文本經典化並加以闡釋,構成了文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文學史著作重點論述的部分。我們在這裏不討論以文本為中心的研究得失,即便突出強調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其研究也無法刪除文學文本與思潮、事件、現象的關聯。在思想史研究中,經典文本的闡釋固然是重點,但私人信件、政府檔案、教堂記事簿甚至銷售清單③也被當作文本加以研究。而在文學研究領域,這些年來對副文本、文學制度、出版以及史料中的稿籤、羣眾來信、日記等文本的重視,都表明了文學文本與其他因素的結構關注得到了拓展。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所選擇的文本將更具廣泛性。
**觀念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但它不是抽象的研究對象,它不能不受到社會語境的影響,所以,我也傾向於將文本放在一個恰當的思想語境中加以研究,思想史視野將為我們研究“語境中的文本”拓寬思路和範圍。**就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社會語境”或“思想語境”的影響是深刻的。自新文學以來,關於“純文學”理解的分歧便呈現了“文學”與“社會”的複雜性。這些年來關於文學場域、話語、文學制度、媒介文化、現代化史等領域或方向的研究,在深化文本與世界聯繫的同時,也不斷改變我們關於文學的觀念。在這裏,我們不僅看到文學與語境的相互影響,也看到二者的相互纏繞,其中“語境”的一些因素成為文本的內涵,而文本中的觀念也成為語境的組成部分。將文本置於語境中不僅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思想。如是看待我們的文學研究,就會發現我們缺少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對歷史、現實和正在孕育的未來並無太多的洞見。這是我近年來深刻檢討自我的一個方面。同時,在防止“時代誤置”之餘,我們還要承認文本與語境的關係有“超越時代”的問題,這也是無數經典文本的特徵。
**我們既要研究作為“思想”的“文學思想”,也要研究“文學思想”在什麼樣的思想和思想機制中生成。**以“現實主義”為例,它作為“文學體制”的美學原則一直處於至高無上的狀態,無論是批判現實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等,現實主義因而成為一種思想體制。現實主義已經不只是一種創作方法,它粘貼了許多倡導者的政治和文學思想,特別是在現實主義成為文學制度所規定的最高或者是最重要的創作方法時。我們可能都會注意到,在當代文學史上,關於現實主義的討論都與文學制度的重建有關,尤其是當現實主義從一種曾經的定義中釋放出來時,其討論都與反思這種文學的思想體制有關。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學體制逐漸被重新認識,現代主義的合法化,並不意味着現實主義的弱化。1990年代以後,隨着市場的發育和大眾(大眾作為階級概念淡化)的崛起,許多預設的觀念被顛覆。在精英文化內部循環的“文化轉型”不僅被打開了一個缺口,而且被裹挾到市場潮流中。在這個時候,文化轉型進入了一個有序之前的無序狀態,知識界、思想界的分化才真正成為一種思想的分歧。1980年代文學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後,五四啓蒙文學的觀念成為1980年代甚至更長一段時間文學背後的預設,但其在1990年代以後也遭遇質疑。在這個過程中,所謂文學的邊緣化其實不是文學價值的跌落,而是文學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遷移。我們始終沒有深刻追問的問題是:文學作品的思想和審美出現了什麼問題,又為什麼出現這些問題?這只是我們考察的一個時間點。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不同的階段,我們都可以觀察到觀念抑或思想的沉浮。而在整體上,這就形成了思想的變遷。這些變遷,不僅僅源自思想語境的作用和文學的選擇,也是思想自身的消長。這一過程既有邏輯的、連續的部分,也有非邏輯的、非連續的部分。
**西方思想話語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在中西文化/文明對話的大框架中看待這種影響,我們就不會把這種對話的矛盾、碰撞、衝突簡單視為對立關係。**中華文明的再造,自然包含了對“西方”的批判吸收。如果傳統內部的思想沒有危機和蜕變,也就沒有接受外來影響的內在機制。就像傳統與現代的辯證,中國與西方的辯證,也是我們討論相關問題的方法,從而可讓我們在更大範圍、更深層次上討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思想資源。這裏又隱含了傳統/現代這對關係,特別是在當下“傳統”已經成為流行詞時。我們在中國的思想語境中所説的“現代”,不僅是“西方”的“現代”,也是“現代中國”的“現代”。分析中國的“現代”時,我們已經無法將中國的“傳統”與西方的“現代”簡單剝離開。中國的“現代”生成過程,既可以視為“西方”的“現代”在中國的橫移,也可以當作中國的“傳統”對“西方現代”的再造。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傳統”的創造性轉換時,需要將之置於“中國的現代”與“西方的現代”這樣的思想文化語境中,而不是簡單地進行價值判斷。“當代文學”從未放棄改造“舊傳統”和包括“現代文學”在內的“新傳統”,這種改造首先是“道”的重建,即價值體系的重建,其次才是“器”也就是文學文體和技巧的變化。而“道”的變化遠比“器”的變化要迅速、深刻和複雜,百餘年來小説、詩歌、散文儘管有不少文體創新,但大致是穩定的;反觀文學的“道”,百餘年來風雲激盪。
“思想”與“問題”的對話
**在某種意義上説,跨學科研究的可能性首先不在視野、方法,而是在於超出學科的問題。**正如有學者所説的那樣:“對於被研究的東西,最能讓人接受的表述是‘問題’。那些折磨人的大問題促使思想超越一切精心構建的學科界限。”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思想”與“問題”的對話。我和葉祝弟在討論這個欄目時,曾經設計了若干問題。這些問題是粗糙的,也不甚準確,但大致反映了我們當下在思想史視野下對文學相關問題的“發現”。視野是思想史,問題則在文學史。如果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可以對“文學史”的“思想史”進行清理,那或許可以呈現另一種面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但我們的重點不是把“文學”作為“思想”的代言,不是把“文學史”作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而是把“思想史”作為“文學史”的一種研究方法。**我們討論的重點不只是關注思想影響了文學,而更在於思想如何影響了文學,文學又以怎樣的方式傳達和創造了思想。這裏,思想和文學的關係無法約化,相反,要更多地呈現和揭示兩者之間的複雜性。**在這一點上,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前言”中的表述堪稱經典。
**魯迅先生的《吶喊》《彷徨》《野草》及《故事新編》呈現了經典性的文學的思想方式,以及思想與文學“交互依存”的結構性關係。**這在魯迅先生《吶喊》“自序”中有過精彩深刻的敍述:“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説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但這個“來由”既是非常複雜的“思想生活”,又是“思想生活”轉化為“文學創作”的過程。在魯迅的敍述中,他在質鋪的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枱上給久病的父親買藥;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並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但這個夢被日俄戰爭畫片中的場景擊碎……魯迅意識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此後,“鐵屋”中的“吶喊”也就成了對“新青年”的呼應。在魯迅先生思想與文學“交互依存”的敍述中,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若干關鍵詞:夢、精神、心理、生活、知識、思想、事件、他者、醫學、身體和潮流等,思想之起承轉合與文本生成的複雜關係,在魯迅的敍述中渾然一體。其實,這種特色也體現在他的雜文和小説史研究中,比如,我們熟悉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國小説史略》等。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第七編“《世説新語》與其前後”中説:“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於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惟土屬則流於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與漢之惟俊偉卓為重者,甚不侔矣。蓋其時釋教廣被,頗揚脱俗之風,而老莊之説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為反動,而厭離於世則一致,相距而實相扇,終乃汗漫而為清談。渡江以後,此風彌甚,有違言者,惟一二梟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俱為人間言動,遂脱志怪牢籠也。”這裏,魯迅談漢末至魏晉思想文化和風尚的變遷,同時論及“瑣言第一”的《世説新語》文體之形成。
思潮、學説、觀點、事件、作家、文本、流派及文學教育、出版等雜陳了我們所説的思想,文學文本的生產和傳播也是在這些要素形成的複雜結構中進行的。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常常會讓一些學者擔心會不會因此忽視了文學的本體性。這種擔心並非多餘,所以,我在談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之重點時,強調思想與文學相互依存的關係,強調思想與文學的生成之關聯、文學的思想生產和文學表達思想的方式等。近幾年關於“文學性”的研究逐漸成為一個話題,我也參與了相關討論。如果我們在審美之外不否定文學的認識功能,那麼,思想和情感一樣也是“文學性”的元素之一。斯蒂芬·柯林尼“斷定”一切歷史學家都是文本的闡釋者,其選擇的文本本身就構成了研究的目標。基於此,思想史對文本的闡釋需要借用其他學科的技能:“比如經過專門訓練的文學批評家對形形色色的直白的情感豐富的著作所特有的敏感,以及哲學家探究那種在表面上將提前和結論聯繫起來的推理的分析能力。”技能的借鑑和互通,正是跨學科研究的要義之一,既然思想史研究需要借用文學批評家對“形形色色的直白的情感豐富的著作所特有的敏感”,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會喪失文學批評家的這種特有的敏感。其實,即便不以思想史為視野、方法,文學的本體性也會在研究中丟失。思想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當然包括清理和呈現“外在影響”,但它可能更側重關注“思想”如何成為“文學”的“內在”構成。因而,我們所説的“思想史視野”,是把“外在影響”轉換為“內部生成”的一種考察。
**克羅齊將歷史視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重啓作為歷史的“思想”其實也是對當下生活、思想生活的介入。**列奧·施特勞斯在《政治哲學與歷史》一文中説:“20世紀典型的歷史主義主張,每一代人基於他們的自身經驗以及他們本人對未來的看法,重新闡釋過去。歷史不再是沉思的,也是實踐的;它所從事的對既往的研究,或者從屬於其所期望的未來之指導,或者從當下出發並返回當下;它認為這種研究有着至關重要的哲學意義,期待着從中獲得對政治生活的根本指導。”當我們把“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區分開來時,也就把文學研究區分為歷史的和當下的。思想史研究通常被視為對思想之歷史的研究,但作為“思想”的“歷史”也延續並啓示當下,當下同樣激活着歷史,在這種潛在和顯現的“對話”關係中又將產生新的思想和文學。
**儘管我們強調學科差異,強調研究文學史和思想史的側重,但我們在重視跨學科研究的同時也重視整體性的建構。**維納為《思想史詞典》撰寫的“前言”最後一段話讓我產生共鳴:“這些對思想史相互關係的研究的目的旨在有助於在一個日益專業化和異化的世界中建立人類思想及其文化表現形式的某種統一感。這些數百年來藝術與科學工作累積的成果構成了我們防止知識和文化破產的最佳保險。評估創造我們文化遺產的思想是人類精神未來成長和繁榮的先決條件。”
我們以思想史視野考察中國現當代文學,不是創造和生產一種研究方法,而是運用思想史研究方法,以打開進入文學史的另一條路徑。在這個視野中觀察、發現和闡釋什麼,決定了研究者的創造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