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秋|數字時代的文化記憶危機與建設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3分钟前
編者按
據新京報等媒體消息,當地時間2024年2月19日,德國著名人文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在康斯坦茨逝世,享年85歲。阿斯曼生於1938年7月,曾先後在慕尼黑、海德堡、巴黎和哥廷根學習埃及學及古典考古學。1976年,阿斯曼被正式任命為海德堡大學埃及學教授,並在該校任教至2003年退休,隨後又被任命為康斯坦茨大學文化研究榮譽教授。曾出版著作有《出埃及記:古代世界的革命》《文化記憶:早期繁榮文化中的文字、記憶和政治身份》《摩西的抉擇:一神論的代價》等。作為一位文化學者,揚· 阿斯曼與妻子阿萊達· 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一道提出了文化記憶理論,探討哪些因素有助於形成人類文化與社會中的身份認同和集體意識,對該領域相關研究的推進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本刊亦高度關注相關選題,曾約請劉亞秋、趙靜蓉等學者圍繞“文化記憶”這一問題從不同維度展開深入討論,現將相關文章推出。
數字時代的文化記憶危機與建設
劉亞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8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問題的提出:數字記憶的“無機性”

阿斯曼夫婦
在很大程度上,由計算機語言、文字數字化引發的記憶樣態可稱為記憶的無機性。“無機”與“有機”相對應,在社會學發展早期,很多社會學家都提出過社會的“有機”問題,這類社會學家重視人作為生命體的維度,而且其社會思想的建構也以此為初衷。當然,若簡單將人類社會類比於生物界的“社會”是有很大侷限性的,人類社會畢竟不同於蜂蟻社會,但人類社會賴以建立的生物學基礎是不能被忽視的現實。重視這一生物學基礎給我們最大的啓示是,需要關注人作為生命體的意義和價值,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人的情感和心態問題,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之一。當機器(計算機)被普遍運用於人類社會,隨之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在這一背景下,(與機器互動的)人的心態和情感議題更應該從時代的高度來審視。這也是“有機”概念在今天仍具有價值的原因所在。
在將人類社會的“有機性”着重提出,並作出較為深入討論的社會理論中,滕尼斯的學説是尤其不能忽視的。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中將傳統社會視為“共同體”,工業技術和商業合力構建的現代社會被他稱為“社會”。他認為前者是“有機”的,後者則是相反的。前者更接近生命體的本質意志,後者建立在一種人的抽象化的抉擇意志之上。人的本質意志與抉擇意志相對應,分別是滕尼斯構造“共同體”和“社會”概念的基礎。本質意志是指真實的或自然的統一體,而抉擇意志則是想象的或人造的統一體。前者是有機的,遵循設身處地的生命統一原則;後者則是計算的、任意的自由原則。本質意志包含思維,抉擇意志是思維的產物;本質意志將未來包含在胚胎中,而抉擇意志則將未來描繪在畫面中。**滕尼斯認為,共同體基於本質意志而建造,社會則是抉擇意志的產物。人們可以任意提供社會,卻不能任意提供共同體。**原因在於社會具有人造性,是基於(想象的、計算性的)目的而形成的統一體,是抽象化的;共同體則是自然長成的,有着豐富的社區情境,是具體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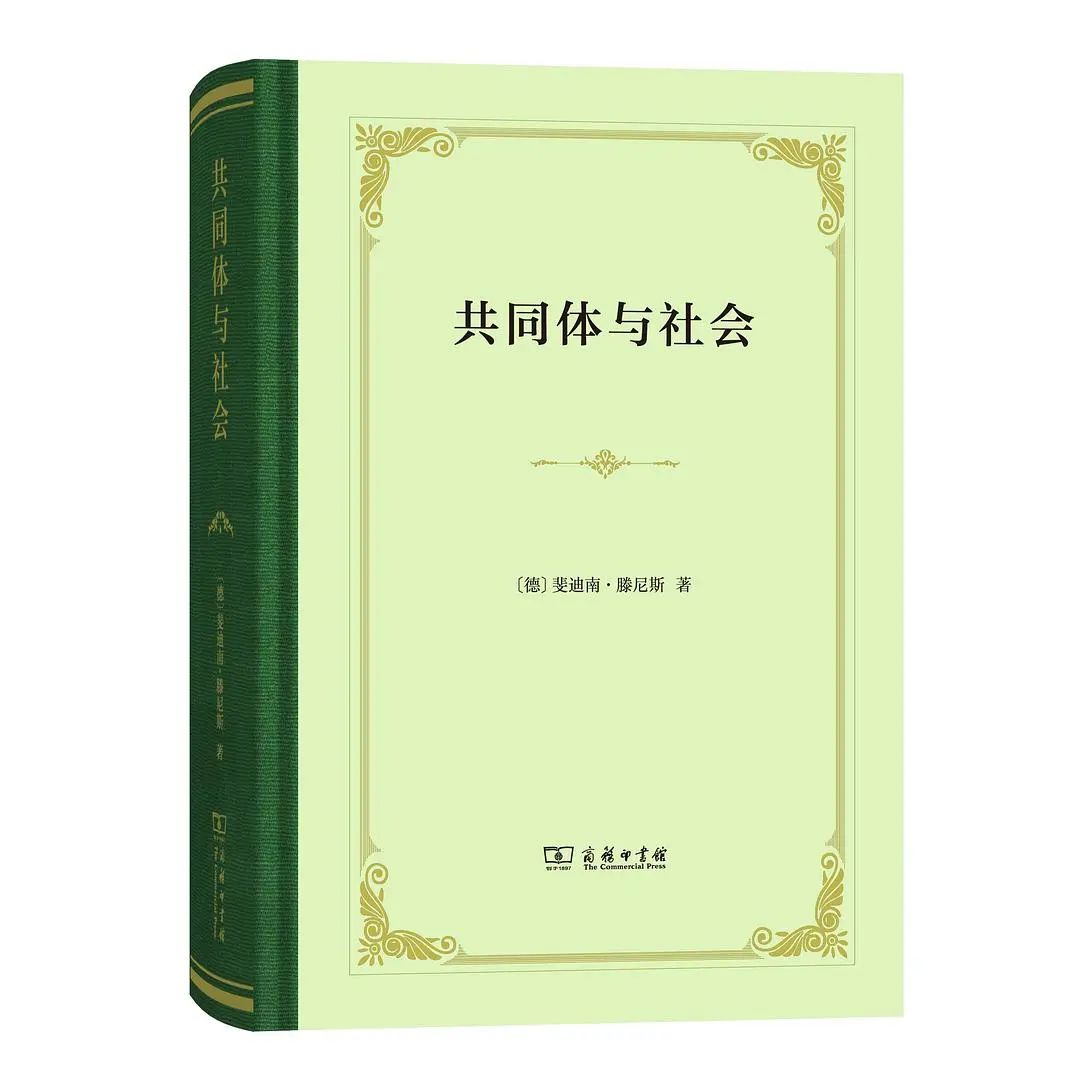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體與社會》
隨着人的理性計算能力的日益增長和商業社會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在工業革命以後又經歷了幾次飛躍,可簡單概括為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再向人工智能社會的轉變。近年來,人工智能議題被密集提出,諸如元宇宙和ChatGPT等概念流行。人類社會似乎進入或即將進入一個新紀元,與之相伴的是人類的新生存處境成為熱點話題。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是一種交織的存在。也可以説,人工智能社會是互聯網社會的一種延伸和深化。互聯網社會廣泛而深入的傳播力和作用力,對社會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如何看待這一過程及其後果?這也是學界熱議的話題。其中記憶視角的介入,可以為我們理解這一變遷過程提供方式方法。
有關數字記憶,目前學界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第一,從數字記憶內部的構成入手,研究數字時代記憶的特點。**例如李紅濤、楊蕊馨從“個體記憶”維度入手,考察數字時代個體的自我和社會認知之間的關係;周海燕強調互聯網實踐中個體的情感實現(emotion achievement)和情感動員問題;姜婷婷、傅詩婷提出數字記憶的構成中尤其要關注人的維度,人作為記憶主體在數字化進程中仍然發揮着關鍵作用。
**第二,考察數字時代記憶的遺忘問題。**人不具備無限記憶的能力,所以需要依靠技術作為大腦以外的記憶載體,但數字時代人們面臨着“遺忘是否被允許”的問題。趙培從貝爾納•斯蒂格勒的記憶工業化角度入手,提出數字記憶不允許遺忘的存在,個體進入了數字全景監獄中;記憶的工業化導致記憶和遺忘的原有平衡被打破,人的遺忘權缺失也導致個體認同出現問題,從而引發時代精神性危機。幾乎所有的技術變革都是雙刃劍,大數據能夠將瑣碎的個人信息迅速匯聚起來,對個體和社會構成潛在危機。袁夢倩強調大數據時代的遺忘權,力圖改變數據主體難以被遺忘的侷限,賦予信息主體對信息進行控制的權利。
**第三,考察文化記憶生產機制及其危機。**有學者從數字時代文化生產的機制角度入手討論時代文化危機,探討短視頻、網絡直播等數字化手段的文化生產與傳統文化的精雕細琢生產方式的本質區別,後者的目的是指引社會道德實踐、形塑倫理秩序,前者則與此日漸背離。阿萊達·阿斯曼從文化記憶角度,提出記憶載體進入電子化時代後,由於人們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中,喪失了深度思考的機會,進而弱化了深度思考能力,從而引發文化記憶危機。
**第四,與文化記憶相關的討論還包括廣義上的數字文化研究。**1995年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出版,提出數字化將決定我們的生存的著名論斷;卡斯特以“信息資本主義精神”來描述數字文化的存在樣式;胡泳提出“眾聲喧譁”是數字文化的一個特徵。楊國斌指出,數字文化引發的文化變遷牽動着社會、政治、經濟等諸多領域,連接着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其中霍斯金斯注意到,數字轉型使人們對於過去的講述出現了新的紀念結構。趙靜蓉認為,從記憶主體到記憶對象、從記憶方式到記憶表徵,互聯網都顛覆了原有的記憶生態,創造出更多的記憶可能性。

**有關數字化生存及其生產的文化記憶,是記憶研究領域的前沿問題。**筆者引入記憶的有機和無機的視角,試圖進一步認識數字時代的文化記憶危機問題。開篇所提記憶的無機性,主要是針對傳統學術研究中“記憶”概念的“有機”意涵而言的。“有機”與人的生命本能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具有社區情境在地化的具體性。在根本上來説,記憶就是人的一種自然能力;如果沒有記憶,那麼人類文明的方方面面也就無從談起。傳統學者基本都是在生命的意義上討論記憶現象,且常將記憶定義為人作為有機體的一種普遍特性。例如,滕尼斯在人的本質意志角度下談論記憶問題,認為記憶是人的心靈性的生命原則。1925年提出“集體記憶”概念的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將記憶放置於個體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中,儘管他強調的是記憶的社會性,但研究的也是以生命為起點的記憶現象。包括1980年代提出“文化記憶”概念的阿斯曼夫婦等,都是基於人作為生命體留下的記憶痕跡角度,去認識人類社會中的記憶現象。
但隨着互聯網社會的興起,這些基於生命體的“有機”記憶,逐漸呈現了一種“無機”的特徵。後者可以看作互聯網社會記憶的一個重要特徵。“無機”在這裏是指這類記憶是由商業和科技聯盟以“人造性”作為主導推進的,它與傳統線下社區情境中的記憶有着很大差異。在嚴格意義上,“無機”並不意味着完全沒有生命的徵象。事實上,一切記憶,無論是傳統的線下記憶,還是信息社會的線上記憶展演,都是人的頭腦(和自然、社會之間交織後)發揮作用的結果。“無機”的記憶中有一個顯著的特徵,這便是人造性以及流動性,後者具有短暫性、表層化特點。這在根本上是人的抽象化的抉擇意志(即計劃性思維導向)的結果,在現實層面更多體現為資本與技術的結盟,筆者將數字記憶的這一特徵統稱為“無機性”。這種無機的記憶帶來的效應是增加了(社會運行的)干擾性。商業和技術在其中的作用變得無比重要,所謂的“人造性”便從這一意義上來講的,吸引眼球是這類記憶生產的最重要訴求。
綜上,從記憶研究的角度,傳統議題多涉及有關個體與社會間關係的“有機”記憶,如弗洛伊德的個人潛意識、哈布瓦赫的記憶社會性、阿斯曼夫婦的文化記憶,等等。從記憶的有機性和無機性角度來看,記憶的有機性首先涉及身體性記憶,這是有機性記憶的第一個意涵。如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提及,腿和胳膊都充滿了沉睡着的記憶,甚至嗅覺和味覺中都沉澱了過往的歲月,這類記憶就是有機的。説它是有機的,還意味着它是有“心理能量”的,這一記憶具有一種“力”。當然,我們也不能説非身體性的、外在於個體的記憶都是無機記憶。這涉及“有機性”記憶的第二個意涵,這便是社會的有機性,也是滕尼斯和涂爾幹的研究議題。從社會有機性的角度,那些構成一個社會可持續運轉的社會底藴和文化底藴,就是保障社會有機性(或社會團結)的基石,是一種“社會力”。筆者認為,對於有機性的判斷除了看它能否產生“社會力”之外,還包括對這一社會力的性質進行檢視。“有機性”多指力的“善”的性質,這與社會的教育功能,如潘光旦的位育理論密切相關,它具有匡定迷亂、指引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意涵。
一言以蔽之,筆者對互聯網記憶的“無機性”的論述,是為了探索重構“有機性”記憶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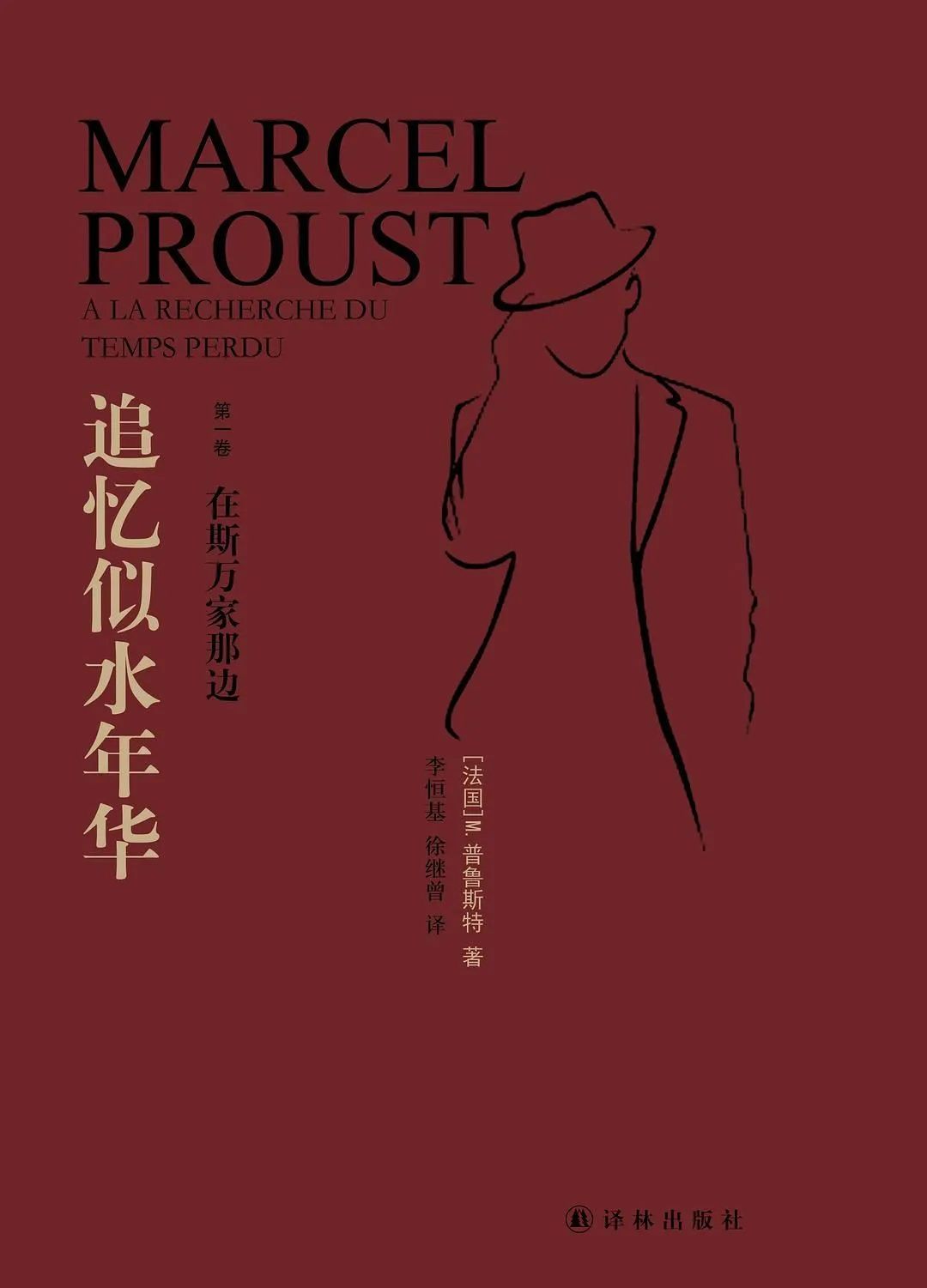
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
數字記憶的基礎機理:記憶的技術性凸顯
從記憶載體的角度看,由計算機語言引發的記憶現象事實上已經引發了傳統文化記憶的危機。廣義上記憶的媒介包括文字、圖像、地點甚至人的身體。它們作為存儲記憶的載體,也會影響記憶的形態和內容。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計算機的記憶存儲行為挑戰了傳統的記憶與遺忘理論。例如面臨海量的信息,個體要塗抹(清除)一時任意而發的記憶似乎變得很難。在這裏,有一個重要的機制由阿萊達·阿斯曼提出,這便是計算機“大腦”把記憶的“技術”給獨立了出來,但代價是犧牲了記憶的“力”的一面。也就是説,既往記憶中那種人之心理能量消失了,這種心理能量便是一種記憶的有機性,它可以生髮善的社會力。

阿萊達·阿斯曼
**“記憶術”的脱域特徵凸顯了數字記憶的“無機”性。**因為記憶的“術”強調“記住”這一機器技術,它是操作性的、冰冷的和機械的。而傳統記憶具有的“力”則是記憶有機性的一個重要體現,它源自人進行回憶的心理動力,關乎身份認同。與生命相關的記憶本身也包括遺忘,甚至相比記憶來説,遺忘更是一種常態。這裏的“力”帶有一種重新回到過去的努力,由於存在這種回憶的力,一些事情變得重要起來。它還意味着記憶與遺忘之間相關交織,其中發揮作用的“認同”本身就是一種粘合的力,以及一種促成社會團結的記憶之力。這一記憶之“力”在兩個層面起作用,在個人層面是一種心理能量;在社會層面,是一種發揮整合作用的社會力。這兩個層面也可以被認為是傳統記憶有機性的具體體現。
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概念就是對這種促成社會團結的“社會力”的一個闡發。他指出,人們從當下情境出發去回憶,也導致了過去被召回的那一刻就發生了變形,因為這時的過去是以當下為取向被修正的。這意味着人們對於過去的追溯和取回,帶有很強的主觀性。這種記憶的“力”是人和社會固有的一種內在的力量。**從這一角度出發,阿萊達·阿斯曼把記憶理解為人類擁有的想象力、創造力之外的第三種精神能力——記憶力。記憶力意味着它不僅是複製、記住,更是一種人的生產能力,以及思考能力和情感能力。**情感能力尤為關鍵,它是人所獨有的。在這個意義上,機器可以存儲信息,但機器無法記憶,它本身不具備整合社會的力量,以及提供一種社會團結的內在的動力,更談不上擁有“心理能量”。因此,機器的記憶是“無機”的。相比人的活的、有情感的記憶,機器所存儲的僅是一個數據“墳墓”;相比人的不穩定的記憶力,它處於靜止狀態。
當然,在互聯網中,一方面是機器在存儲數字記憶;另一方面,由於參與其中的人們不斷留痕,導致數字洪流處於不斷運動和變幻中,這與傳統文字記憶的穩定性構成了鮮明對比。阿萊達·阿斯曼描述了這一狀態:隨着數字時代的到來,不僅印刷術的時代結束了,物質書寫時代也隨之徹底結束了;在新的媒介技術之下,傳統文字因其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長期穩定性受到了數字洪流的衝擊。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第一動力是科學和技術,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隨着科技的快速發展,社會的權威也發生了更替。在無文字時代,記憶載體主要依靠作為生命體的個人,而人所記憶的內容在時間上只能延續80~100年,即一般不超過三代。因此,只有那些對社會有用的東西才能流傳下來。對於重要的社會記憶,人們一般藉助儀式來保存。在無文字社會,老人是有權威的。進入文字時代後,記憶的存儲空間變大,不僅有用的信息被記錄下來,那些暫時沒有實際用處的信息也能被記錄下來,甚至那些被社會孤立的聲音也有了久存於世的機會,這擴大了社會的知識範疇。同時,文字記憶也提升了人的抽象化思維能力。因為在傳統的記憶模式中,所記之物和回憶主體很少被分離開來,就像演出和文本的關係一樣。在發明了文字的社會中,文字作為抽象的符號系統,在記錄中容易將感覺的多樣性轉化為單一性的符號性存在,它提供的是一種抽象編碼。阿萊達·阿斯曼認為,從無文字社會到有文字社會,人類文化的存在方式發生了由具體化到抽象化的轉向,這是文化記憶領域的深刻變革。文本本身是一種物質化的記憶存在形式,而且,這些文本是具有穩定性的;但是,這類載體保留下來的多是精英文化記憶。如同哈布瓦赫所説,在傳統社會中平民是沒有記憶的。
**在文字時代,文本的經典化對文化記憶有重要影響。文字相比於口述而言,是更為穩定的存在,它也因此獲得更大的威嚴。**保羅·利科認為,歷史學家之所以重視檔案,正是因為人們有一種“紙面的迷信”,在歷史中,人們也多把神聖之物都寫在文字中。這是文字的一大特徵,文字的穩定性使其更容易作為社會價值的準繩。費孝通在回憶錄中也提及“敬惜字紙”的重要性,就是“敬惜”寫出或印出的文字,勸導人們在寫字時要下筆謹慎,不要傳播錯誤思想貽害社會。可以説,這是“痕跡崇拜”的積極因素,“文以載道”也帶有這樣的意思。事實上,這就是文字記憶的經典化作用,其對於社會團結的構建、社會秩序的維護,以及人們的身心安放都提供了根基性的價值準繩。這種根基性的價值準繩是經由在地化的社區情境日積月累形成的,但數字記憶的脱域過程也導致具體化社區情境發揮作用的力度被日漸削弱,有機的社會力遭到破壞。
綜上,“無機”作用的機制是,由於過度強調記憶的技術,導致記憶從具體的社區情境中脱域,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喪失掉了記憶發揮作用的社區情境,進而使得記憶作為一種有機性社會力的功能在日漸衰弱。可以説,數字化過度凸顯了記憶作為一種技術存在的特徵,這是數字記憶從有機轉向無機的基本機理。
數字記憶面臨的主要挑戰
在數字時代,我們處於漂浮不定的記憶洪流之中,在這一處境下,人們如何穩固或構建類似經典化(提供穩固價值準繩)時代的文化記憶?在機器存儲記憶的時代,文字不再是穩定的,它轉換為“字節”的跳動。
“字節”是一種計算機語言,是記憶數字化的一個表徵。也可以説,我們進入了一個泛文字的時代。在這裏,不穩固性甚至成為主流。例如,青年亞文化在中國逐漸盛行,近年來B站的崛起就是一個例子。它所表達的文化具有青春的特徵,這類文化是未成熟的,是處於形成中的。在這裏,人們更加追求新鮮的樣式,有創新的衝動,但也製造了迷茫困惑的心態/價值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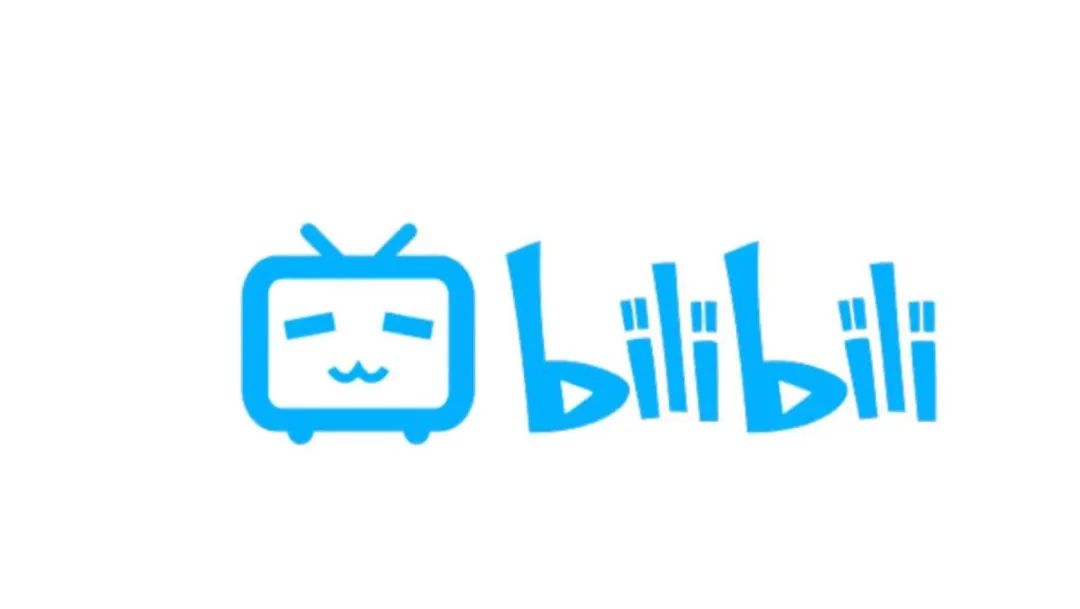
筆者認為,**計算機語言構建的無機性記憶在社會中的主要表徵是記憶的技術凸顯,脱離了具體化的社區情境。在作為有機性社會力、促進社會團結的功能方面,其不僅匱乏,而且強有力地“沖刷”着主流社會的有機性記憶。**以下幾個方面是其沖刷主流社會的主要樣態,這些方面也是數字記憶無機性的具體化表徵。
**第一,轉瞬即逝。**轉瞬即逝是互聯網熱點新聞的一大特徵,例如微信朋友圈的熱帖一般存活時間不超過一週,但其熱度奇高,短時間內在互聯網的作用下情感高速堆積、他人的反應高度在場,最終可以輕易造就一種速度和強度空前的公共制裁形式,甚至導致涉事主體社會性死亡。這對於個體和社會而言,傷害性都極大。這類熱點新聞和回帖在網絡上反響大、發聲多元,但意見淺薄化、快餐化。其主要原因在於這類數字記憶脱離了具體化的社區情境,無機的數字記憶在短時間內藉助流量對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
**第二,眾聲喧譁。**網絡平台提供了數字化的廣闊開放空間,在這裏人人都可以發聲,甚至每個人都有產生廣泛社會影響力的潛質,但這種趨勢利弊共存,最大的弊端是嚴重脱離了人賴以為根基的具體化社區情境,讓人無從判斷真假。比如,製作短視頻背後的個體是一個怎樣的人?無人知曉。但其也提供了向更多人宣講或表演的機會,很多人依靠這種形式積聚人氣,獲得廣泛社會影響力,進而達到盈利的目的。網絡上不乏內容極為低劣的作品,但由於其影響力較大而佔用了大量社會性資源。這些個人制作行為也就不再單純是個體性的行為,而具有了社會性。從構建社會性的角度,其傳遞的價值對公序良俗造成極大的衝擊。因為傳統的社會性價值是經過社區情境嚴格檢視的,由人類社會經驗逐漸累積而成。社會所公認的權威,是由一系列社會品質作為保證的。哈布瓦赫在論述歐洲社會貴族階級傳統的形成與存續時,就指明瞭這一點。但互聯網製造的內容並不遵循這一原則,例如那些短視頻社交平台宣稱的願景是“激發創造,帶來愉悦”,這種“生財”理念勢必帶來缺乏檢視的、輕薄的內容。簡言之,數字記憶的無機性製造了種種幻象魅影,對主流的社會記憶造成巨大沖擊,事實上傷害了社會的有機性。

短視頻社交
**第三,解構主流。**例如鬼畜視頻的雷軍版《Are You OK》,無疑是一種解構,它不是建構,也不是“原創”,事實上僅是一種娛樂文化,通過“隨意為之”的方式給社會增加笑料。這類記憶顯然不同於傳統社會中的主流記憶,後者是為了身份認同,建構人們的意義感。“隨意為之”是數字記憶無機性的一種體現,它不僅忽視和無視具體化社區情境的力量,甚至敵視和破壞這種依靠日積月累才能沉澱下來的可貴的社區情境,社區情境正是人類為了生存下去、賴以為根基的價值和意義力量所在。
**解構具體化的社區情境導致文化的碎片化。**在“每個人都可以做網紅”的“願景”中還藴藏着一種底層的狂歡,這也是主流文化被沖刷的表徵。網紅可以無底線迎合大眾的各種需求,而且至為關鍵的是,以盈利為目的商業手段運作加劇了這一趨勢。平民狂歡造就的網紅模式不乏搞怪成名、意外成名等,被許多人視為“喧囂的泡沫”,存活時間一般都比較短,但其對主流的社會記憶造成極大衝擊。其中,信息碎片化、價值觀多元化的一個消極後果是,無視在地化的社區情境,給社會的價值建設帶來危機,導致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更容易陷入困頓迷茫。像“躺平”“內卷”這些反映社會心態乏力的概念之所以能迅速走紅,都與這一機制有着密切關係。文化碎片化的結果是進一步削弱了社會方面給予個體和社區的安所遂生的力量。
**第四,推波助瀾。**在互聯網時代,藉助互聯網技術,商業邏輯作用於社會的花樣翻新速度比以往時代更快。這裏所謂商業就是滕尼斯所説的無機社會,它是一種人造社會,是在人的抉擇意志推動下的後果,它是人的思維能力的一種體現,表現為計劃性和抽象性,這種發展趨勢愈發掙脱了具體化的社區情境和意義,甚至碾壓、打碎了傳統社區情境中的穩固性力量。在盈利目的驅使下,一些互聯網寫手為了追求高點擊量不惜製造噱頭。例如互聯網軟文大量存在,目的就是吸引眼球、積累人氣,藉此獲得額外的報償以及其他各類社會資源。網絡推手帶有極強的目的性的策劃炒作,甚至可以讓普通人迅速成名,例如“愛豆”現象。愛豆原意是歌手、演員等偶像羣體,現在指一些人即使沒有任何作品,也能通過炒作成為愛豆。這再次印證了數字記憶之無機性的任意妄為特徵。
**第五,表層淺薄。**人類進入機器檢索時代,“死記硬背”的記憶類型似乎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人們對知識性記憶的需求在減少。然而,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多是建立在熟記的記憶類型基礎上,之後才是融會貫通和創造。有學者指出,機器的信息生產機制造了只記錄、不記憶的困境,記憶是內化的、記錄是外在的。前者將對象/物轉化為人的認知、心理的一部分,屬於有機的記憶,可以產生善的社會力;後者將對象/物交付給存儲和檢索技術,這樣查找信息很便利,也很周全,但這類記憶是無機的,而且人在這一過程中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也包括人在深度思考後的判斷力,即什麼才是真正有利於個體和社會的。人類在這方面的能力被鋪天蓋地的信息給擾亂了,思考變得表層化、快餐化。
**可見,數字時代的文化記憶危機,最重要的表現是在“眾聲喧譁”的社會背景下,人的深度思考能力被幹擾,人們找到價值準繩的機會(能力)減少(拉低)。**甚至可以説,我們進入了一個“有文字無教育”的時代,大眾對敍事張力和表達快感的渴望,壓倒了對真實性以及何為人間正道的思考,大眾以數字記憶的無機性為工具快意恩仇,但同時日漸失去了來自社區情境中的安所遂生的力量,即一種有機性社會力的庇護。
事實上,互聯網時代大部分所謂技術與社會互構的“創新”大多具有極度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
性,例如元宇宙概念便是如此。其樣式之“新奇”甚至超出人們的想象,它們很多是在人性複雜性和商業盈利性等各種因素交織下催生出來的“怪物”。“提高某種社會效率”是它的一個基本特徵。商業和技術的“勾結”基本不考慮後果的善惡,我們也難以評估其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到底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綜上所述,**數字記憶的“無機性”對傳統社會的有機性記憶構成挑戰。**一方面是對在地化社區情境的破壞;另一方面是對人的本質意志的削弱,人的本質意志是人作為有機體的基礎構成,在這裏體現為人腦的記憶能力,與之密切相關的是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它受到無機性數字記憶的嚴重衝擊。
文化記憶危機的應對
如同阿萊達·阿斯曼所指出的,文字曾被看作永久痕跡,以及一種過去的、需要解密的現實索引和借鑑,和一種雕刻和持久意義的寫入,但這一古老的隱喻在數字時代將會不知不覺消失。傳統時代的書寫與深度、背景、沉澱和分層等人類社會經驗密切聯繫,但在電子時代,這種關係幾乎站不住腳了,後者變成一種“脱域”的存在。在我們這個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是“表層”,是被計算出來的狀態以及1和0這兩個編碼的開合啓閉。
當然,在嚴格的意義上可以説,古往今來所有寫出來的東西都面臨着“墜入深淵”的可能性。當下,所有發表出來的東西一樣都會面臨這一命運,也包括互聯網上的各種表達形式,如視頻、音頻、文字,等等。“歷史的垃圾箱”在數字時代也將以一種新的形式被打開。無用的、被遺忘的東西都會被迅速推入“深淵”,這個“深淵”也會隨着數字技術存儲容量的增加而不斷擴容。如前所述,朋友圈的新聞熱點一般不超過一週,因為電子媒介在製造新聞熱點的同時,也提供了分散人們注意力的多個焦點。迅速遺忘/拋棄,又迅速提供焦點,是數字時代記憶快餐化的表徵。那麼,**傳統記憶模式還能在這個充滿分散注意力的消遣世界裏停留多久?****顯而易見,互聯網上消遣文化的盛行加速了記憶消失的進程。如此看來,互聯網的痕跡是記憶,還是遺忘?**這讓人頗費思量。商業思維的加入,讓這一過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例如,短視頻具有讓人儘快遺忘的脆弱性。與之密切相關,互聯網時代的文化記憶危機最為致命的是持久性注意力文化被破壞,以及由此導致的人類社會價值準繩身處飄搖不定的危機之中。對於數字記憶引發的文化記憶危機及其應對,筆者主要強調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傳統的文字記錄面臨危機,這波及人類的深度思考能力,這種深度思考能力也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基。人作為生命有機體,在互聯網大潮下日漸鈍化了其賴以生存的深度思考能力。為應對這一危機,亟須在文字使用方面具有相對優勢的知識階層的覺醒和共同努力。
在互聯網語境下,注意力是指民眾對於某一事件的關注時間長度。注意力不夠持久首先影響的是人們的深度思考能力。赫爾德提出,語言起源於思考,而思考又來源於回憶能力。但在互聯網時代盛行的“感知的汪洋大海”和“圖像的縹緲的夢境”,使人的深度思考能力和回憶能力面臨危機。如何保留住思考能力,隨之成為我們時代的議題,這是個體和社會獲得真正發展的內在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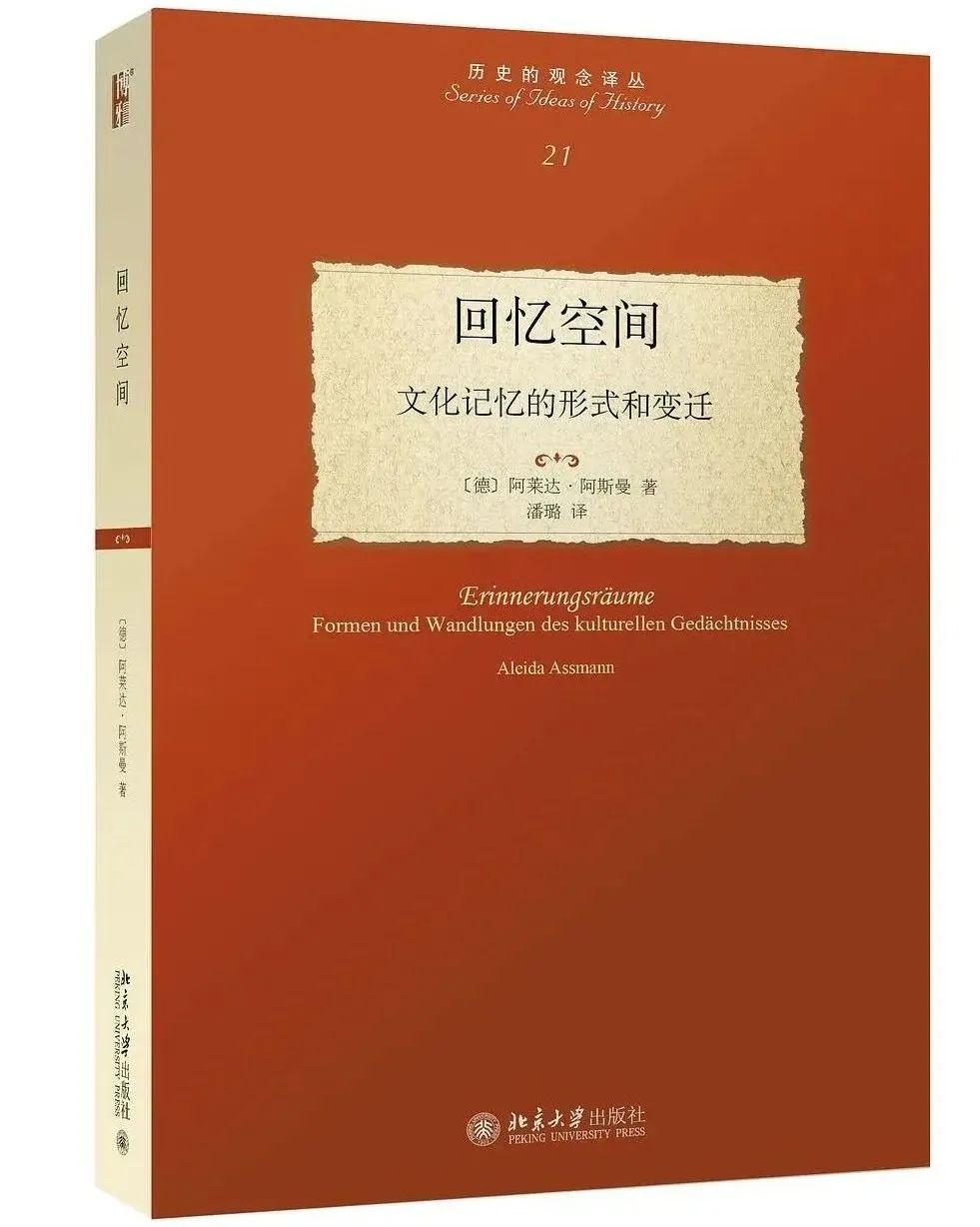
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
深謀遠慮是建立在回憶和思考之上的人之能力。對於個人來説,它是特有的,也是一些人生來就有的基本能力;對於人類社會來説,它是語言和文化產生的源頭。深謀遠慮製造了有文化底藴的回憶空間,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這些既有的人類經驗積累與數字記憶製造的褶皺、空洞和疊層的洪流,還可以相互對抗,或可為毀滅性危機的延遲到來創造契機。這要求與時俱進,適應時代變化,但更要創造一種有利於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文化。
那些穩固的價值有些需要適時調整,但有些則一直以來都是人類社會的航標,是必須要留存的價值,以維持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那麼,知識階層該怎樣做才能保存那些好的價值,並創造新的有益於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呢?
如上所述,**在互聯網引發的文化記憶危機中,人類的深度思考能力顯得尤為重要,也應該得到保護和培育。**對它的保護和培育需要藉助一批人的力量,知識分子在其中可以有所作為,也應該有所擔當。以中國現代化早期的社會思想家潘光旦先生為例,他面對民國社會思潮的思考可以給我們帶來不少啓示。
潘光旦對潮流與時代的關係曾經有一個討論,可以視為對“互聯網時代該如何培育和保持人的深度思考能力”這一問題的積極回應和指引。潮流就是風尚,它們不一定是有價值的。尤其在只普及識字而未普及教育的民國時代,一種思想或一個物件,可以藉助廣而告之的方法,立刻得到大眾的捧場,進而獲得一種聲勢浩大的社會影響力,且這種聲勢還可能歷久不變。但潘光旦指出,在學問界討生活的人,面對這樣的情況,應當知道如何趨避取捨。他認為對待潮流有三種態度和方法,第一種像樹葉落花一樣隨波逐流,第二種像老樹根一樣堅如磐石、不為所動,第三種則像逆流而上的魚。面對各種社會思潮,知識分子應該做一個時代潮流的主動引導者、選擇者,而不能做被動的順應者,至少應當做一個掙扎者。
潘光旦提出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就是把經過社區情境檢視的好的價值傳遞下去。這是他在《學問與潮流》中所談論過的,他自己也是這麼踐行的。面對風起雲湧、思潮變幻的時代,他堅持“為了子孫後代”以及“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準繩,直言批評那些主張取消家庭制度等自由派觀點。可以説,他是“一條逆流而上的魚”,堅持在個人與社會之間構建一種有利於人性與社會性和諧共生的理論。在技術程度日益加深的互聯網時代,知識階層有責任甄選和維護那些值得堅守的價值,從傳遞給下一代和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即便互聯網大潮洶湧澎湃,但只要立場堅定,確立價值準繩也並非難事。
**另一方面,數字記憶的無機性的確破壞了在地化社區情境的力量,干擾了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準繩。**在這方面尤其需要國家和政府的強有力介入,以起到保護社會的作用。國家和政府的作用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應該主要體現為一種規劃力和執行力。尤其在中國社會,只有充分發揮它的力量,才可能更高效地對互聯網之漫無邊際、雜亂無章作出合理的規劃和引導。
**為應對數字記憶的無機性破壞,需要有與之抗衡的對沖力量,筆者強調對根植於社區情境的“有機性”進行保護。**在這方面,政府可以起到維持善的社會力量的作用,即規範商業和市場活動,以及引導科技發展的方向。善的社會力量即有機的“社會力”。例如,“再造附近”就是一種保護社會的設想。“再造附近”是項飆提出的一個概念,與滕尼斯守護“共同體”有異曲同工之意,就是要保護社會的有機性。讓記憶依託於一個在地化的社區情境,從人與社會之和諧共生的具體化情態入手,維護社會的生態。而數字記憶遠離社區情境,甚至牴牾、解構在地化的社區情境,因此它是無機的。人的抉擇意志導致技術和資本在追求利潤/利益的目標下,讓社會日益走向抽象化和計劃性,例如元宇宙設想就有這樣的趨勢,它可以通過技術提供更多的娛樂空間,但它依然解決不了人在時間中的有限性問題。如同趙汀陽指出的,“元宇宙”其實就是一個商業廣告,是資本的劫掠;如果元宇宙真的不幸成為了現實,那麼其引發的社會倫理問題將非常棘手,甚至會成為人類社會的大災難。
需要指出的是,在傳統西方理論中,國家、市場和社會被視為是三足鼎立甚至是三方抗衡的關係,既有研究也往往從這一視角切入。例如在“再造附近”的倡議中,項飆區分了最初500米和最後500米。按照他的理解,最初500米是社會有機性的一股力量,意味着社會的原生態,是“積攢”社會力的場域。**而最後500米,則來自一種自上而下的計劃的力量,在他的討論中,主要來自行政的力量和市場的設計,它會引發一種社會的無機性。**應該説,項飆所分析的這一情況是普遍存在的。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現實中同時存在着國家和社會的協同力量,二者相互促進,可以共同對抗過度化的市場和商業活動對社會的侵蝕。**例如,在中國社會存在着一種“家國一體”的機制。周飛舟認為,在脱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的過程中,國家“順應”社區原有的“生態”和居民的“心態”進行培育、修剪和養護,形成了一種積極推動社會發展的家國一體邏輯。在基層社區治理實踐中,也存在着這樣一種自上而下的黨建引領(動員)和自下而上的社會參與(呼應)之間的合力,二者間的結合點就在於黨建引領(政府部門)藉助了有機的社會性即在地化的社區情境和文化的力量。由此,國家的行動就與基層民眾之間取得了某種利益上的一致性,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並可以在危機時刻完成社會保護的任務。可見,這種社會和國家合作的力量也是普遍存在的。
與之類似,在數字項目的規劃和治理領域也潛藏着這樣的機制,以助推有機的社會力和國家的數字治理之間形成合力,其着力點在於通過規範數字的商業化運作,來保護社會中善的力量和價值,從而維護社會的公序良俗,構築社會的有機團結,進而讓社會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契機,而國家的興盛和長遠發展正建立於這一基礎之上。這一國家保護社會的機制,在數字時代顯得尤為重要。
餘論
我們身處信息的洪流中,不時被變幻的圖像和符號所俘獲並轉移注意力。信息如此頻繁地交織與“轟炸”,損傷了人的記憶和深度思考能力。而有機的記憶本身就是一種值得保護和培育的反思能力,人們在這一基礎上建構社區情境,確立價值的準繩,共同籌劃社會發展以及人類未來的走向。
筆者在涂爾幹的“社會神聖”意義上界定社會的基本價值。互聯網之風潮洶湧在解構秩序與維持秩序之間產生了巨大張力。秩序在這裏並不僅僅是穩定、規訓的代言詞。事實上,在精神層面,它象徵着一種穩定的社會心態。在傳統文化記憶概念中,穩定的社會中都存在着某種類似古埃及的“瑪阿特”一樣的價值,它決定一個社會的正義準繩,並潛在地發揮着穩定社會以及保證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作用。瑪阿特是一種無形宗教,代表普遍與和諧,在宇宙中表現為秩序,在人類社會中體現為正義。
有機的文化記憶中必然藴含着一種引領發展的價值要素,但在眾聲喧譁的時代由於誰都可以發聲,從而使文本的經典化面臨着很大的干擾,導致那些維持穩定的價值觀出現危機,這是時代面臨的困境。當然,文化記憶空間的形態和質量,受制於種種政治和社會的利益,不僅來自技術媒介商業化發展的影響,而且互聯網也受制於整個社會結構的樣態。也就是説,支撐互聯網社會的信息技術模式並非一個封閉的系統,而是開放、多元的,它具有全面性、複雜性與網絡化的特徵。其中,互聯網的“實時”信息傳播給人際交往帶來了時間的極大“壓縮”,甚至發生了時間的消失。在一個沒有時間的心靈環境中,(文化心態)可以同時指向瞬間與永恆。時間/文化變得碎片化,同時虛擬的空間也是一個流動的空間,它放大瞭解構社區情境的力量。伴隨着互聯網這一時空形式的生成過程,整個社會結構也發生着變化。
毋庸置疑,數字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方式、社會情感等都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數字技術重構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關係,精英在文化記憶創造方面的壟斷地位被弱化。在數字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似乎變得很容易,但彼此之間不過是相遇於當下的陌生人,個體轉化為“流浪漢”“觀光客”和陌生人。在這樣的情境下,主流記憶被擾亂或“附近”開始消失,事實上,其背後是一種對於“敬惜字紙”的崇敬感的動搖。
總而言之,我們無法抗拒的現實是,文字記憶已經進入一個“跳動”的不穩定時代。但是,**在新的時代,我們依然擺脱不了作為生物人的具身性,並仍然生活在一個具體化的社區情境之中,仍舊需要一個穩固性的價值支撐,即安所遂生的社區力量。**當下支撐中國社會的一些文化基礎依然堅挺,例如家庭文化,但它也面臨着數字技術助力下的各種思潮的衝擊,如互聯網效應加大了不婚不育等婚戀觀對傳統家庭觀念的沖刷力度,這對於培育健全的子孫後代和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不啻為一種致命傷害。
在數字時代,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處境:數字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影響着各種制度和文化,它創造了財富,同時又引發了貧困;激發了貪婪、創新和希望,同時又強化了苦難,輸入了絕望。不管我們是否有勇氣面對,它都是一個無可逃避的新世界和人類共同的命運。在數字時代,重構記憶的有機性、強調社區情境的力量是應對危機的一個有效途徑。“有機”記憶的強調讓人和社會找回安所遂生的力量,它以人的生命體為起點,並須臾離不開這一初衷;與此同時,它潛藏着一種維護人與在地化社區情境和諧共生的力量,也即努力保存人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