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們的“藥方”,你看得清嗎?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33分钟前
文 | 天書
距“毛星火起訴莫言”事件過去一個多月後,對莫言的爭議和討論仍餘波不斷,月初我寫了一篇《對莫言的批判來得太晚了》,從莫言文學內核上的一些問題,以及當年中國版魔幻現實主義和先鋒文學的成因來討論莫言這一代人的侷限性在哪。
當時限於篇幅,有些問題並沒有展開討論。粗略觀察,這一個多月網絡中反對對莫言進行批評批判的言論,多數都是夾纏不清,屁股大戰,缺乏基本的邏輯,作用無外乎是充當輿論信息污染。
“起訴莫言”從行為效果上看固然是一種鬧劇,不認同這種行為很正常,**但對莫言以及這一代作家的討論批評和批判在文學文化領域中從來都是正當的,只不過過往相關話題並沒有進入大眾視野。**以“反對起訴莫言”的旗號上升到“反對批判莫言”,往往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這種力挺來為另一些東西張目。
今天針對幾種有討論價值的代表性觀點來進行一些辨析和梳理。本文需要結合上一篇《對莫言的批判來得太晚了》一起食用,前文討論過的問題這裏不再贅述。
莫言的“複雜性”
知名編劇汪海林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説到莫言當年發言挺教員導致被孤立,認為不應該簡單給莫言貼標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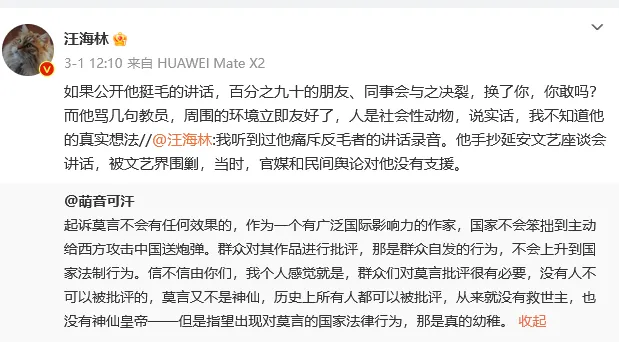
這話是沒錯。不過正因如此,更不能忽略一個人的言論複雜性,畢竟説下面這種話的也是莫言。

上面那條微博説地好,起訴莫言很幼稚,但羣眾們對莫言的批評很有必要。批評莫言也不是為了把他推到敵對面,搞清楚莫言作品中那些問題的內核,認識到當下批判這種內核的意義,比糾結在莫言是挺教員還是罵教員這種表面現象更有實際價值。
我們不談莫言挺教員的言論是不是屬於“連夜繡紅旗”,上幾代人對毛主席的感情本來就是非常複雜的,崇拜他的人未必就理解他的思想,反對痛恨他的人也未必會否認他的高度。認可教員和痛恨“那幾十年”,甚至痛恨社會主義本身也不衝突,同時持有這兩種觀念的大有人在。
另一種觀點也很有迷惑性,認為説莫言的小説裏並不都是醜化中國人民,也寫了日軍和反動派的殘暴。並不都是妖魔化那幾十年,也批判過改開以後。認為批判歷史和現實就是作家的職責。邏輯類似的辯護也經常被用於對閻連科和餘華等人一些作品的質疑中。
這種辯白仍然停留在表面現象。莫言們的作品之所以需要被批判,之所以會被時代淘汰,不是因為他們在作品裏批判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想借作品宣揚什麼。
想搞清莫言們想宣揚什麼,需要一組能揭示中國當代文學困境根源的關鍵詞。
關鍵詞1:批判
以巴爾扎克為代表,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在西方文學中達到了頂峯,也開始衰退。20世紀現代文學的基礎之一就建立在對巴爾扎克式文學的逆反上。在我國,由於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學與左翼運動和社會革命密不可分,加上建國後的文化氛圍,批判現實主義對於大眾來説,長期成為一種文學領域中的“政治正確”,似乎只要是在批判,就有了光環。
然而巴爾扎克之所以是批判現實主義的頂峯,在於他精準還原和揭示了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規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百科全書”。批判現實主義之所以退場,原因之一也是因為20世紀後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已經遠超文學作品的承載能力。
而莫言這類作家,很多人只顧着當社會的“良心”,無論對農村還是城市,他們都欠缺巴爾扎克那樣準確描述和還原問題的能力(最反感莫言的人可能是高密人和山東革命老區人,最反感閻連科的人可能是河南人),如果你拿他們的小説當批判現實主義來看,那你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認知會與現實相去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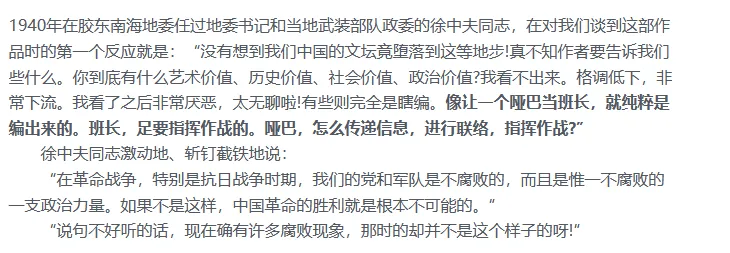
事實上,他們對當代中國文學的價值也並非批判現實,而是在文學技巧和語言本身。雖然批判現實對大眾有光環,但在當代文學圈內也不是主流。如《人世間》這樣為大眾所熟知的作品一般被圈內人認為是為了拿獎的公式化之作。所以,“批判現實”不是當代作家可以拿來拒絕公眾質疑的護身符。
關鍵詞2:苦難
比起批判現實主義,喜歡描寫苦難和醜惡更符合莫言這一代作家的特點。典型的苦難文學作為一個類別,因為文學性和思想性都不高,曾經受到過文化界的批評,不過苦難和醜惡始終作為一種元文本的存在貫穿於當代文學四十年的脈絡中。
同批判現實主義的光環類似,大眾總是認為描寫苦難,揭露苦難是文學的主要價值,但這並不符合文學本身的客觀規律。如果以苦難為最高取向,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就不會是《紅樓夢》了。縱觀世界文學史,成就最高的那批作品也很少有以苦難為主要內核。
即使描寫苦難本身,如果以苦難和醜惡為單一維度,那也説不上是文學的真正價值。正如魯迅評價陀翁所説“他不但拷問潔白,拷問出潔白下面的罪惡,他還要拷問罪惡,終要拷問出罪惡下面的真的潔白。”
當代中國文學中的苦難和醜惡,是鄉土文學內在矛盾的具象體現。
關鍵詞3:鄉土
莫言這一代的主要成就都在鄉土文學領域,以文學史本身來説,這是一種特殊現象。中國文學誕生伊始,雖然詩詞歌賦大量採風於民間,多有描繪農村農民之作,但本質上還是屬於文人士大夫的遊戲。到明清以後小説盛行,描繪市井生活,上層社會,怪力亂神,今古傳奇是主流內容。西方文學軌跡也類似,19世紀近代文學的巔峯作品中,描寫城市生活甚至是中產及以上生活是主流,進入現代後現代潮流之後更不用説。

民國有些作家寫鄉土,但內核和目的性與80年代後的鄉土作家們截然不同。建國早期的農村和鄉土寫作則是屬於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80年代後成名的這代作家與民國作家們有**截然不同的背景。**沒有舊式文學的底藴積累,沒有新文化運動以來對西方文化既吸收又對抗的開闊眼界,沒有見證中國完成革命從舊到新的歷史視野。且這一代因為年輕時的經歷,基礎教育水平普遍比較欠缺,人生觀世界觀早早成型,所以比起那些難以把握的題材,鄉土題材就容易成為文壇敲門磚。
這時期興起的鄉土文學,**混雜了反思文革,傾述傷痕和文化尋根三種訴求。**寫鄉土的未必都是農村出身,但很多都有上山下鄉的經歷,鄉土成了他們傾述傷痕和表達訴求的最好載體。對文壇來説,中國農村長期都是沉默的大多數,再怎麼被誇大失實被妖魔化,都不會引起多大關注。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傳入中國後產生了高密宇宙這樣的變種,這是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創作方式,如果讀者不較真,那就是寫鄉土,寫真實,如果讀者較真,那就是用魔幻手法進行反思批判。只是,高密人看到自己家鄉以那樣的方式獲得國際知名度會感到自豪麼?顯然不會,但這對文壇大咖們的創作產生不了任何影響。
從社會意義上看,莫言一代鄉土文學整個內涵的“批判深度”,都不會超過《鄉土中國》和《叫魂》這類社會學著作的藩籬,在此限度之外的苦難和醜惡寫作就只與作者本身的創作取向和文學表達有關。
如閻連科的《日光流年》,再怎麼樣將司馬藍與三姓村的悲劇融合進建國頭幾十年的各種事件中,對提升小説的“批判深度”也沒有本質作用。閻連科自己接受採訪時就説過“中國文學的發展不力,受制於現實主義”、“真實完全不在於來自生活,而是來自作家的內心。只要心感到真實,一切都是真實的。”

我們上面提到的反對批判莫言的第二種代表性觀點的問題就在於此。按正常人思路理解,寫鄉土問題,寫鄉土社會中的苦難和醜惡,目的應該批判和反思鄉土社會本身,探究鄉土社會的出路。
但莫言和閻連科這些人的書你看了會覺得奇怪。他們有時像在批判鄉土社會,但又經常對改造鄉土社會的實踐深惡痛絕。他們喜歡給社會開藥方,但鄉土社會的藥方最終只有一個,那就是以現代化和工業化對抗鄉土社會的內卷,而他們往往又拒絕這味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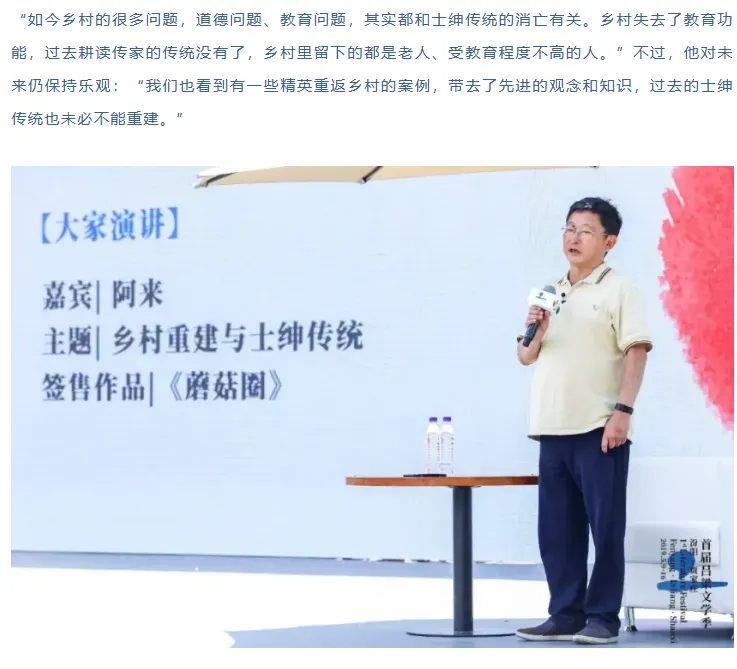

所以,不要看他們作品裏“除了批那幾十年外也批過改開以後,批過侵略者和反動派”,**實際上內核邏輯是一致的,就是“好人觀”和“權力觀”。**不論什麼身份的人都有好人,所以地主也有好人,日軍也有好人。而誰有權力誰就是壞人,所以他們筆下的黨員幹部和軍人總有不堪的形象。
鄉土社會里本來可以有很多好人,但掌握權力的人讓人變成壞人。而新中國頭幾十年政府對鄉土基層的權力達到自古以來最大,所以——按這個邏輯,你就能理解他們作品中所謂批判的本質。
關鍵詞4:權力
中國作家和西方相比,在歷史淵源上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工業革命以前,西方長期都是由封建領主,宗教神權,王朝貴族和強盜蠻子主導的社會。工業革命以後又由資本主義主導,文人作家這一羣體離權力結構有相當的距離。
**中國則不同,**科舉制讓中國從中古開始變成由文人士大夫主導的社會。及至近現代,頂級文人們與中國社會變革和政治動盪一直密不可分。民國時期,左聯成為革命的盟友。建國過程中,文人圈子又成為重要民主力量。這其中很多人都是作家,他們對權力屬於就算沒吃過也見過。
80年代以後的作家們雖然與權力中心絕緣了,**但權力卻成為他們的心魔。**一方面,對自身青年時期經歷的反思,容易讓他們把問題歸結到權力本身。另一方面,中國上千年的文人士大夫傳統又容易讓他們將自身代入其中,質疑自身無法獲得同社會身份相匹配的權力。在他們的邏輯中,顯然這也同權力的來源和結構有關。
對權力的病態性心理在閻連科作品中體現地最為明顯。他自承喜歡通過作品探討“權力對人性的異化”,《日光流年》司馬藍當上村長之後被異化,《受活》中柳縣長想買列寧遺體,搞殘疾人雜技團,“鐵災”“黑災”“紅難”反諷革命,還有那個被韓國拍成同名電影的《為人民服務》(有興趣的可以看下這電影)。揭開文學外衣看本質,閻連科的創作並不真的關心苦難和鄉土出路,關心的是“權力”,對權力的病態反思和扭曲情結則讓他的作品走向一切為了權力而虛構,一切為了權力而誇大,到了《炸裂志》就完全成了過猶不及的爛俗作品。

所以別看閻連科也會説市場經濟時代如何世風日下,他批判市場經濟絕不是認為以前不搞市場經濟就好。以前不行,現在不行,也沒人敢明着説建國以前就行。兜兜轉轉,他們到底想表達什麼?這涉及到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五個關鍵詞。
關鍵詞4.5:贖買
在第五個關鍵詞之前,有必要説下80年代以來作家們的生態位。反對批判莫言的聲音中還有這樣一種話術:莫言這些作家都是體制內作家,作品都獲得過茅盾之類的獎,代表國家肯定他們。你有什麼資格批判人家?
**一個社會中總有反對派的生態,不在內部就在外部。**西方社會通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輪流坐莊,可以讓反對派變成小罵大幫忙的政治遊戲,社會主義國家處理此類問題就顯得被動。蘇聯歷史上因政見問題跑到海外的作家們給社會和民意造成很大沖擊,更何況中國文人羣體在傳統中就是權力的代言人,天然就容易扮演反對派的角色。
我國建國後受蘇聯影響,大幅壓縮了社科在高校中的空間,對文人作家羣體則希望能統一在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的旗幟下。這種嘗試失敗之後,80年代高校恢復社科研究,對於作家羣體不再以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的旗幟為要求,體制內的吸收,名譽和地位的給予更接近於安撫和贖買——先贖買穩定人心,讓他們不至於變成索爾仁尼琴,再慢慢引導,參與文化建設。
這種贖買在人文社科的很多領域都存在,“內部反對派”的存在不代表因為他們是體制內,羣眾就要認可。**恰恰因為贖買本質上是一種妥協,羣眾們更要自覺地對贖買對象擦亮眼睛。**異見文人裏像王小波那樣有節操的是少數,更可能出現的是餘傑這種。
關鍵詞5,基督——基督情結,中國當代文學“不是秘密的秘密”
正如前面所説,如果你以為莫言和閻連科們妖魔化那幾十年,就會一味讚美80年代以後,現實並不滿足這種結論。如果你以為他們批評市場經濟時代世風日下是在懷念從前,那更是絕沒可能。
實際上,莫言們分析中國社會問題的方式未必是依據“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標籤,**實質上更接近“文明”/“野蠻”,“善”/“惡”這種二元標籤,**所以在他們眼裏不是你搞了市場經濟就變文明瞭,還遠遠不夠。
他們劃分文明和野蠻的標準在哪?從基督情結對當代文學龐大的影響中我們可以窺見一二。
基督教文化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伴隨着西學東漸和新文化運動一同發生的。80年代之後,這種影響迅速復燃。從文字最表層我們就可以觀察到這種影響,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吳摩西出延津)、徐則臣《耶路撒冷》、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是三個代際作家羣中最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基督文化內核作為小説的核心意象。如果説這三部作品只是一種文化意象借鑑,那麼以基督教文化內核為元敍事,甚至最後皈依的作家也不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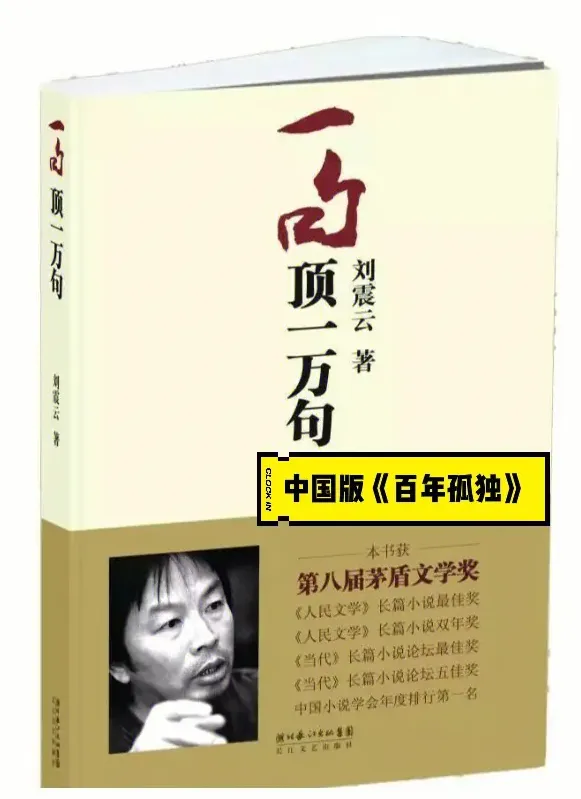
80年代開始基督文化對文學的影響迅速擴大基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一是在傷痕文學之後,劉再復等人提出要對那十年進行**“全民懺悔”**,一時間“懺悔與救贖”成了中國文學的一大母題,而“懺悔與救贖”也正是基督教文化的內核。這股意識在發展到“人文精神大討論”後,**已經遠超文學範疇,**一如史鐵生對基督文化的讚美:
“教堂的穹頂何以建得那般恐嚇威嚴?教堂的音樂何以那般凝重肅穆?大約是為了讓人清醒 ,知道自身的渺小 ,知道生之嚴峻,於是人們才渴望攜起手來,心心相印,互成依靠 。”
二是學習西方搞所謂“現代性反思”,這種反思的成因和上一篇聊莫言文中提到先鋒文學的興起類似。
20世紀前後,西方的思想家們開始了現代性反思,從上帝之死到工具理性批判,再到後來的種種,如果不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反思,人們很容易得出現代社會不如前現代社會的結論。早期資本主義相比封建主義的確扼殺了很多温情脈脈,但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方法不可能是回到前現代。**中國作家們在八九十年代搞現代性反思就是時空錯位了,**完全忽略了現代性反思之後西方社會又經過了各種戰爭,生產力大發展和吸收社會主義思想緩解危機等過程,而我們的現代化才剛剛起步的現實。
鄉土作家對着自己反思了半天一看同期的西方,這不就是基督教裏的天堂嗎?再一尋思,同樣都是搞市場經濟,為什麼人家像天堂我們像土鱉啊,為什麼人家文明我們野蠻啊,總得有個原因吧?再一拍大腿,哎,因為人家是基督信仰社會,可找着根了。(這裏只是不嚴肅的簡略概括現象成因,嚴肅討論以後有機會再進行)
文學評論圈內,對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向來是不諱言的,並且贊同發揚的聲音一直很多。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展開羅列,以後有機會再單獨梳理。我們仍是隻看莫言和閻連科就可窺一斑,這兩位作品中的基督元素和神學內核評論界早有論述。
莫言的《等待摩西》《豐乳肥臀》《餃子歌》,閻連科的《日光流年》,《丁莊夢》,都深度內置了原罪,懺悔和救贖的基督文化內核。只是,這些作家們是覺得全人類都需要懺悔和救贖嗎?看看莫言的《在毀滅中反思》和閻連科的“日軍的一顆糖”,好像也不盡然。總體説來,從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言論看,他們還是更覺得中國人需要懺悔和救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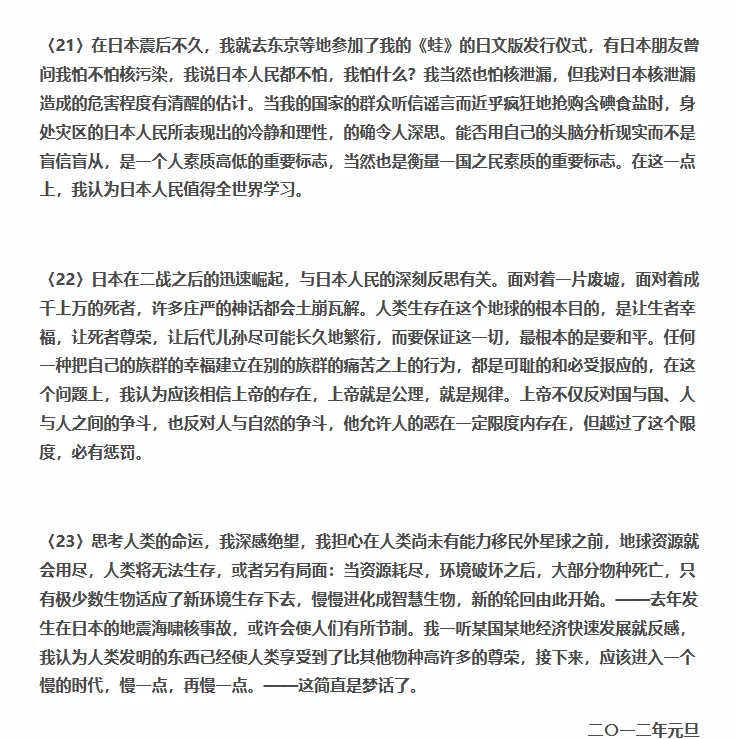
莫言《在毀滅中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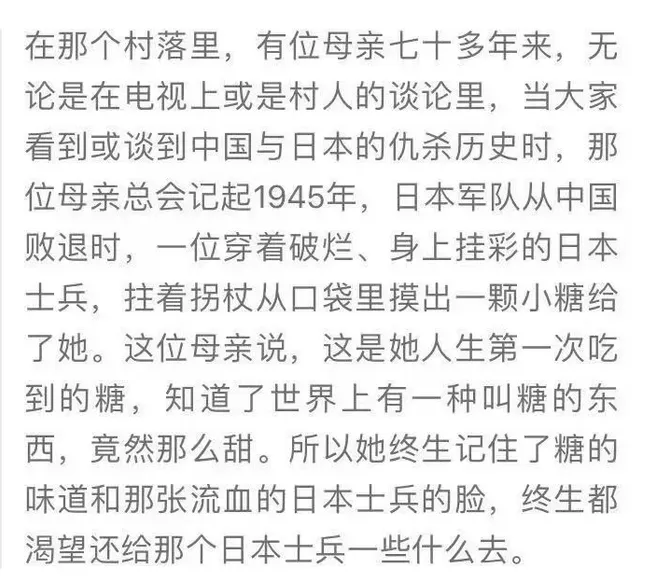
閻連科《比世界更大的村莊》
比內置基督文化內核更進一步,就是北村這種直接受洗,以宣傳基督文化為職責。再極端的就是餘傑,曾經稱聲要寫出最好的華語小説,最後信了基督跑到國外成了叛徒。
**總之,基督文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龐大影響並不是秘密,但卻因為主流文壇與大眾文化的脱節,以及各種評論有意無意地包裝而成為大眾認知中的盲區,並對當今種種話題和爭論產生深遠影響。**這個圈子的風氣確實不容輕視,比如我知道的一位資深圈內人,對東西方思想和文學批判很有造詣,但也因為種種原因受了洗。
僅從文學來説,基督文化作為世界文化中幾大母題之一,在東西方交流碰撞過程中對中國文學和思想產生影響,並使得一批作家以此為內核創作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僅以文學而論無可厚非。
但討論文學現象,不能忽視建國後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的社會大背景,更不能忽視中國的作家們並非單純的作家,也是屬於喜歡開藥方的“文人士大夫”角色,**這就需要普通人對作家的文學作品與士大夫的藥方之間的界限有清醒的認識。**你在文學裏聊基督教我沒意見,認為基督教文化內核是中國當代社會需要的那顆藥那顆糖,那顯然就不是文學的事了。
文學的歸文學,其他的歸其他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説到的,時代的發展就在於新的媒介和內容形態自然而然地斬斷了莫言們在年輕一代中繼續繁殖的渠道。確實對於中國文學來説,80年代以後的鄉土文學是難以迴避的,但這不代表我們就要接受主流文壇長期構造的話語規訓,以文學的名義無腦接受這圈子裏的一切。莫言到近年還在寫《左鐮》這類東西,我們與其幻想這代作家還能有新的突破,不如讓一切自然地更新換代。
我不是高水平文學愛好者,也接受不來圈子內的很多標準和推崇的東西。如果要推薦一本鄉土小説,我會推薦《一句頂一萬句》。這本小説會告訴你剝離苦難和審醜敍事後,鄉土題材如何探尋中國人內心深處的精神癥結。當然也就是如此了,鄉土文學終究沒辦法解答現代後現代的問題。
當你看到如今一些文章和視頻猛誇哪個作家哪本書太有哲理和思考深度時,千萬別輕信,自己看過思考過後再説。莫言這一代作家們不是博爾赫斯更不是荷爾德林,當不了哲學啓蒙者。
沒辦法,文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光環太牢固了,哪怕到現在,像帶貨的董宇輝還會被粉絲安上個知識分子的標籤。

中國傳統文化上習慣文史不分家。到了學術體系現代化的今天,以作家和知識分子自居的羣體就成了這個傳統毛病的最主要保留羣體。讓文學的歸文學,哲學的歸哲學,歷史的歸歷史,科學的歸科學,這樣我們才可能在公共爭論中獲得一點有價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