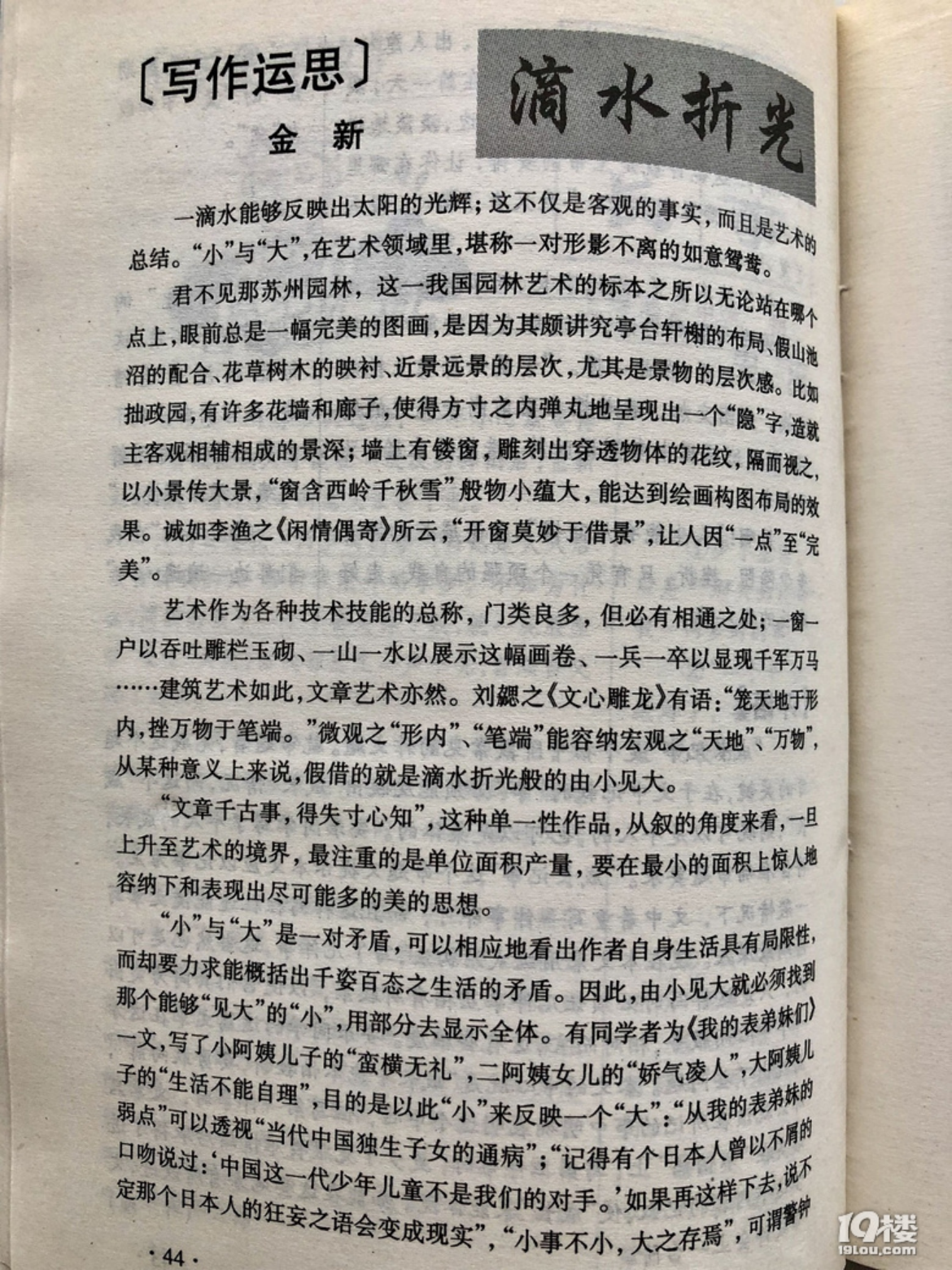金新:由名家“扛鼎”文學評論想到了“滴水折光”_風聞
虎落平阳-7小时前
【虎落平陽按語】今天是世界讀書日,因前幾天《讀寫》雜誌審稿間或通宵達旦而在補覺,亭午時分醒來見有學軍校友發來微信:”金先生昨日就執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之牛耳的洪治綱教授的觀點‘文學創作中沒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筆’所發表的見解令人於文學評論的‘死水’中見‘微瀾’。記得有關‘以小見大’的創作法您20多年前就在某中文刊物上發表過一篇針對中學生閲讀的文章《滴水折光》,洋洋灑灑數千字,不妨發出來讓網民們看看!”看來這位學軍校友知道我在2000年前為全國的中學生寫過百餘篇寫作運思隨筆專欄文章,每篇數千至萬不等,很受歡迎,筆法類似於秦牧的《藝海拾貝》。當年刊發的“寫作運思”文字估計有近百萬,感謝華師大劉陽教授從茫茫刊海中“搶救”出來!
(秦牧《藝海拾貝》封面截圖)
滴水折光
金新
(《滴水折光》第1頁截圖)
一滴水能夠反映出太陽的光輝;這不僅是客觀的事實,而且是藝術的總結。“小”與“大”,在藝術領域裏,堪稱一對形影不離的如意鴛鴦。
君不見那蘇州園林,這一我國園林藝術的標本之所以無論站在哪個點上,眼前總是一幅完美的圖畫,是因為其頗講究亭台軒榭的佈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樹木的映襯、近景遠景的層次,尤其是景物的層次感。比如拙政園,有許多花牆和廊子,使得方寸之內彈丸地呈現出一個“隱”字,造就主客觀相輔相成的景深;牆上有鏤窗,雕刻出穿透物體的花紋,隔而視之,以小景傳大景,“窗含西嶺千秋雪”般物小藴大,能達到繪畫構圖佈局的效果。誠如李漁之《閒情偶寄》所云,“開窗莫妙於借景”,讓人因“一點”至“完美”。
(蘇州園林圖片)
藝術作為各種技術技能的總稱,門類良多,但必有相通之處;一窗一户以吞吐雕欄玉砌、一山一水以展示這幅畫卷、一兵一卒以顯現千軍萬馬……建築藝術如此,文章藝術亦然。劉勰之《文心雕龍》有語:“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微觀之“形內”、“筆端”能容納宏觀之“天地”、“萬物”,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假借的就是滴水折光般的由小見大。
(劉勰《文心雕龍》古本截圖)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種單一性作品,從敍的角度來看,一旦上升至藝術的境界,最注重的是單位面積產量,在最小的面積上驚人地容納下和表現出儘可能多的美的思想。
“小”與“大”是一對矛盾,可以相應地看出作者自身生活具有侷限性,卻要力求能概括出千姿百態之生活的矛盾。因此,由小見大就必須找到那個能夠“見大”的“小”,用部分去顯示全體。有同學者為《我的表弟妹們》一文,寫了小阿姨兒子的“蠻橫無禮”,二阿姨女兒的“嬌氣凌人”,大阿姨兒子的“生活不能自理”,目的是以此“小”來反映一個“大”:“從我的表弟妹的弱點”可以透視“中國獨生子女的通病”;“記得有日本人曾以不屑的口吻説過:‘中國這一代少年兒童不是我們的對手。’如果再這樣下去,説不定那個日本人的狂妄之語會變成現實”,“小事不小,大之存焉”,可謂警鐘長鳴,發人深省。
客觀地講,很難以文學性與非文學性之矛盾關係去界定小中見大;一般情況下,文作者能注意到小與大的辯證關係,文學性具矣。因而只能從濃淡深淺的角度去看待,上例便屬淡者淺者。
濃者深者,或曰高層次的由小見大,那是文章的藝術、藝術的文章了,堪譽滴水折光。
典型化手法的運用。所謂典型化,是一種創造典型的過程,即通過藝術的體驗和分析,把生活中最有意義的東西,即“大”概括出來,並在個別的、具體的、富有美感的形象,即“小”中加以表現。其貫穿於從內容醖釀到形式表現整個創作過程裏,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小説的典型化着重於典型環境中表現人物性格,詩歌是突出詩人的典型感情。前者如《普通勞動者》所塑造的人物林部長(即戰爭年代的林將軍)的獨特的脾氣,後者如《題菊花》“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時開”所寄託的變革現實的叛逆精神。就人物形象的創造説,則有原型基礎上的豐富、改造,如《故鄉》中的閏土、楊二嫂;有不要原型、雜取許多人的拼湊方法,如《祝福》裏的祥林嫂。
典型化就敍而言,主要以創造典型人物深而且廣地反映社會本質。有關典型人物,即個別性與普遍性,抑或個性與共性的統一體人物,在《以簡馭繁)一文內,從“簡”與“繁”的關係的角度,已有略述,在此不再展開。值得一贅的是,典型人物的性格是在典型環境中表現的,何謂典型環境?所謂典型環境,即指文藝作品,特別是敍事性文藝作品中,環繞着人物、促使人物行動,並與整個時代背景辯證地統一在一起,從而反映出時代某些本質規律的環境。如《七根火柴》裏之所以描寫草地上的“鬼天氣”,是因為其乃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縮影,盧進勇性格成熟的關鍵;《祝福》內之所以描繪魯四老爺家的擺設,是因為此係封建統治的縮微,祥林嫂悲劇釀成的根源。
託物寓義手法的運用。託物寓義,顧名思義,即在某一載體上寄以深刻意義。其方法眾多,主要是以物喻人。如《白楊禮讚》:抓住白楊樹的外形特徵,借白楊樹的不平凡的形象,讚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抗戰的北方農民,歌頌他們質樸、堅強、力求上進的精神,抒抒作者對他們的崇敬和讚頌的感情;《香山紅葉》:用凝聚着“北京最濃最濃的秋色”的香紅葉,喻老向導“越到老秋,越紅得可愛”的精神風貌,從而抒發了作者對社會主義新生活,對當家作主的勞動人民的熱愛、讚美之情。
以物喻人一般有兩種方式:直接法,袁鷹的《井岡翠竹》直接將井岡翠竹喻指井岡山人以至億萬羣眾,明寫竹,暗寫人;間接法,楊朔的《荔枝蜜》由物及人,先寫蜜蜂,後寫具有蜜蜂精神的人。特殊則有回龍法,張翅的《春筍》由物而人而物(人),先簡要交代了“我”家鄉盛產竹子的特點和“我”對漫山遍野的春筍的喜愛,隨即轉人對童年時小夥伴們上青竹山尋找春筍、自比春筍等趣事的回憶;然後以“我”這次回家鄉,“去尋找童憶”為由,引出了在一場驟雨中與一位放牛娃相遇的故事;最後以抒情的筆調,把眼前的放牛娃和拔地而起的春筍合二為一,展開想象,給人無窮的回味。
以物喻人與典型化(其實前後是屬種關係)異曲同工,意在由小見大。如《春筍》寫的不僅僅是小之又小的春筍,主要是以春筍比喻少年,以雨後春筍的盎然生機比喻一代少年茁壯成長之大景象;這樣寫,出現在眼前的就不只是一個個性鮮明的放牛娃,而是憑藉雨後春筍聯想到成千上萬個放牛娃,以及具有相同優秀品質之共性的一代少年。
以物喻人,物與人之間風馬牛相及,在於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務必注重其內在聯繫的一維性。錢鍾書《管錐篇·周易正義·歸妹》説;“同此事物,援為比喻,或以褒,或以貶,或示喜,或示惡,詞氣迥異,修詞之學,亟宜指示。”這表明一個現象;喻之多邊。孔雀開屏可謂美極了,且慢比喻,它定會露出不雅的屁眼。“歲寒三友”,儘管松“歲寒知松柏之後凋也”,卻是甚次的木料;雖然竹“修長兮搖曳多姿”,可是“空中多節”;縱然梅“臨霜傲雪”,但是“虯曲棕縛”。正反涇渭分明。由是,正確尋找物之喻之一端,以求與人之精神相合,至關重要。仔細閲讀一下《白楊禮讚》,推敲一下對白楊樹外形的定向描繪,我們當會心一笑!
典型化,對於有的同學來説,也許會有“空中聞天雞”的感覺,偶無意而為之,只是停留在“小處着筆,大處着眼”的原始自發的觀念狀態上,屬低層次的淡者淺者;以物喻人,則是觸手可及的,不妨一學,如何?果真如是,由小見大之本意定能領悟,滴水折光之喻義定可意會:“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