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國外的中國人,有多少後悔了?_風聞
luse-49分钟前
出國移民,在海外留學或工作,曾代表着一種光鮮的人生選擇。
30年前風靡一時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裏,姜文飾演的男主角揹着小提琴,仰望曼哈頓天際線的畫面,讓無數國人心馳神往。進入世界名校,努力紮根海外,逐漸成為中國人自我實現的奮鬥目標。
轉折發生在近兩年。社交平台上的出國熱漸漸褪去,手握綠卡的天之驕子們,好不容易在海外紮根,卻開始後悔當初出國的決定。

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迴流的帖子
有人辭去國內高薪工作,去澳洲幹體力活,發現長期做白領工作的自己,並不適應在工地抬鋼筋水泥;有人全家移民後,因為文化隔閡,找不到能夠談心的朋友,最後選擇獨自回國;還有人羨慕歐洲人的鬆弛與快樂,在荷蘭上班後發覺,國外同樣不乏“狗屁工作”。
國外商超貨架上琳琅滿目的日用品和蔬果,價格動輒是國內的5、6倍;社區醫院下午3點關門,如果生病,小病靠扛,大病看命;走在大街上甚至時不時被當地人喊話“Go back to your country”(滾回你的國家)。
朋友圈分享的九宮格僅僅是真實生活的冰山一角,走出國門的年輕人,開始懷念在國內和朋友熱熱鬧鬧吃火鍋的記憶,以及電話那頭,來自親人的遙遠又熟悉的聲音。
於是,萍飄四方的移民們回頭望,重新走向身後的故土。

“金融理財師,澳洲工地扛水泥”
剛到墨爾本時,李凱在工地上幹小工,將重達100斤的鋼筋水泥扛在身上來回搬運,或者背幾十斤重的工具箱,裏面裝滿鋼釘和釘槍。
負重工作一整天,李凱累懵了,在家躺了三天才緩過勁。
出國前,他很嚮往國外的藍領工作,工資高、地位與白領平等、上手快、不受語言和文化限制。因此,儘管在國內他是金融理財師,落地澳洲後,卻向不少藍領崗位投去簡歷,從中選了這份搬運工作。
李凱1.8米,150斤重,經常泡健身房擼鐵,認為扛東西不是難事,但正如他所言,“‘能扛動’和‘從早扛到晚’是兩碼事”。
澳洲搬運工分小工、中工、大工,新手都從做小工開始,每天工作8小時,每兩個小時之間休息10到15分鐘,永遠包攬最髒最累的活。沒有健身房的動感音樂和跑步機上揮汗如雨的暢快感,真實的工地,只有避無可避的烈日和混着沙土的鹹澀海風。

李凱工作過的工地
有一次,李凱需要順着鐵架爬上三樓,擦掉外牆多餘的油漆。當天風很大,輕薄的鐵架無時無刻不在搖晃。當他往上爬時,手腳跟着劇烈顫動,透過鐵桿往下看,如果自己摔下去,肯定會頭破血流,想到那次的驚險經歷,至今依然令他有些後怕。
在工地上班不久,李凱換到一家台灣老闆開的炸雞店工作,時薪只有22刀。李凱發現,即使在國外,缺乏技術含量的藍領工作也並不高薪。“藍領工資高”的前提條件是“懂技術、有門檻”,他認識一位西澳的電焊工,時薪高達70刀。他算了筆賬,老家西安的平均月工資3500,人家一天就賺到了。
因此他下定決心掌握一門技術——學習開叉車。他報名了關於駕駛叉車的職業教育課程,通過一週的技能培訓拿到證書,在一家快遞工廠做貨品分揀。
開叉車減少了體力的耗損,卻大大增加了李凱的心理壓力。工廠裏來來往往都是人,他一天需要卸數百件貨品,總擔心自己哪天一不小心會砸傷別人。

李凱工作過程中受傷,腰部留下3釐米傷口
來澳洲做藍領工作,不完全是李凱的心血來潮,他有過海外生活經驗。他曾在美國讀本科,學習工商管理。回國後,他換過幾份工作,創業兩次,以失敗告終。家裏人勸他回西安老家考公務員。但李凱不想過“一眼望到頭的生活”,去年跟着女友來到澳洲。
誠然,澳洲有廣闊的沙灘海域,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流光溢彩的歌劇院……但此時的李凱,更想念火鍋、串串還有老家西安的麪食。在老家西安,一碗油潑面只要12塊錢,而在澳洲,吃碗麪都要花好幾倍的錢。
墨爾本的曠野上沒有格子間,卻有大量的露天工地和快遞工廠。出國近一年,李凱終於明白,國外的藍領工作沒那麼快樂,他在社交媒體上勸大家打消來澳洲打工的念頭,“每天習慣坐辦公室的人,過來做苦力活,真的吃不消”。

“高考後全家移民,我卻後悔了”
絕大多數到海外生活的人,無論體驗是好是壞,都是自己主動做出的選擇。君君的故事則有些不同,她遠赴加拿大的開端,是父母準備多年的一場特殊“驚喜”。
高考結束後,當君君正在猶豫該填報什麼院校,母親遞上了一沓資料,稱已經為她申請加拿大的高校,可以直接入讀。
更讓她驚訝的是,父母辦理的是投資移民項目,全家已經預備拿到“楓葉卡”(即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權)。此前父母一直將她矇在鼓裏,是怕她放鬆警惕,對高考掉以輕心。
君君的父母白手起家,全年無休,一直都在為生意奔波。她和弟弟從小被送到外地的寄宿學校,小時候,母親曾給他們念報紙上優秀學子的勵志故事,問君君未來想上什麼大學。

《小敏家》台詞截圖,
父母為孩子留學所作的努力
90年代正值“留學潮”興起,君君隨口説出了“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她從未想過,自己隨口説出的回答,竟讓母親誤以為自己夢想出國,並努力為她實現了這個“夢想”。
對於君君來説,轉變來得太突然了。高考之前,她構思過理想的大學生活,學畫畫、參加街舞和音樂社團,跟寢室舍友一起上課、知無不談。
但在海外上學,和她想象中截然不同。海外大學講究“寬進嚴出”,為了修夠學分順利畢業,很多學生會在圖書館複習一整夜,同一個宿舍的舍友都很少碰面。
文化差異帶來的隔閡無法被忽略,她聽不懂外國同學聊的籃球明星、美劇、當地人才懂的俚語,對方也對自己喜歡的街舞和漫畫一無所知。君君homestay(家庭寄宿)時期住在本地人家裏,只會在吃飯的時候和他們坐在一起,平時幾乎零交流。
人們總以為只有華人愛抱團,其實白人同樣喜歡抱團,君君交到的朋友大多都是華人,“外國人可以聊天,但難以交心,畢竟文化和成長環境太不一樣了”。
大三那年,發生了一件讓君君後悔到國外的事。她選修了一門課“數學經濟學”,期末考試開始不到10分鐘,卻被任課的白人老師冤枉作弊,趕出考場。
老師判定她作弊的理由是,君君考試前上交的筆袋裏,有一張記着數學公式的小紙條。那是君君在複習其他科目時隨手寫下的,公式內容並非這門課所學。最重要的是,考試期間,這張紙條並不在君君身邊,它被連同筆袋一併上交給助教檢查。
君君向老師據理力爭自己沒作弊,甚至表示可以到對方的辦公室重新考試。她想向系主任反映情況,電話卻被老師提前截胡。她只能看着對方給自己蓋上“帶小抄”的帽子,始終沒有機會為自己反駁。

《小敏家》劇照
被判作弊,意味着她會失去課程的分數,面臨延畢,甚至在檔案上留下污點。那段時間君君身處風暴中心,她不禁在想,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白人學生身上,校方也會這樣簡單粗暴地處理嗎?
她開始懷念在國內時的生活,大學畢業後,恰好深圳有個實習機會,她到某影視節組委會實習,國內的溝通方式、文化氛圍、職場環境讓她感到久違的熟悉,對比之下,君君堅定國內的生活更適合自己。
她向父母提出回國永居的想法,卻遭到了反對。徹底回國居住,意味着要放棄在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權,但為了這張楓葉卡,父母不僅花費了大筆資金,還犧牲了國內的生意。君君考慮再三,擱置了這個想法。
直到去年,君君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國際會展策劃的工作,她終於能有理由長期待在國內。這份工作需要經常出差,忙到不能準點吃飯,沒有時間健身。但她欣喜於自己的工作能力正在飛速成長,和同事溝通協作時,彼此之間都有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上海沒有加拿大足以穿透雲層的巍峨冰山,但君君身邊有了志同道合的夥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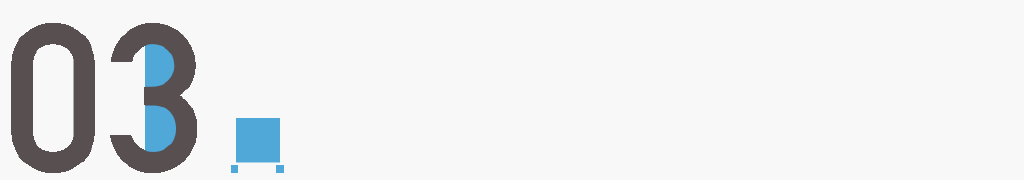
“看胃病拖兩週,醫生的面都見不着”
不同於君君擁有全家移民的機會,蘇州女孩小婭同樣在加拿大求學,卻是高考失利後的無奈選擇。
2013年的夏天,在拿到高考成績單後,小婭決定出國留學,為自己的學歷鍍一層金。
她至今還記得浦東機場T2出關口的磨砂玻璃門,走過那扇門,從未住過校的小婭就要去往另一個國家生活。往後多年,每當她看到揹着書包的少年跟家長,在關口前垂淚相對,擔憂、不捨、搖擺不定的情緒就能被隨時喚醒。

《小別離》劇照,在機場送孩子離開的父母們
到了加拿大,小婭心中飄忽不定的情緒沒有得到安撫,異國生活的麻煩和不便先一步出現。
那段時間,小婭的胃部總是傳來陣陣痛感,伴隨着胃酸上湧,燒灼感襲來。在繁重的課業之間,胃痛持續消耗着她的精力。
小婭預約了住所附近的社區醫院,醫生讓她去查幽門螺桿菌、驗血、驗糞便、吹氣。
這都是治療胃病的常見流程,但在國內時,醫院的各個科室都在同一棟樓裏,所有的檢查流程只需要花半天時間。在海外獨自看病後,小婭才知道,在加拿大,看病是個漫長的過程。診斷歸家庭醫生負責,化驗歸實驗室負責,開藥又要去往其它地點。國內醫院的科室之間,上下樓不過幾步距離,在加拿大卻需要開車來回輾轉。
胃痛是小婭的老毛病,當小婭在加拿大社區醫院檢查完,詢問領取化驗報告時間時,卻被告知實驗室下午3點已經關門了。
她只好忍着疼痛隔天再打電話詢問,得知領取化驗報告的時間,被安排在一週以後。
沒有化驗單,醫生沒法開藥,小婭傻眼了。一週之後,當她好不容易拿到化驗單,又要跟診斷醫生重新預約時間。距離掛號兩週後,小婭終於拿到了治療胃病的藥物,但此時,她的胃早就不疼了。
小病靠熬,大病看命。小婭曾陪伴朋友去過當地醫院的急診,加拿大沒有“線上掛號”系統,臨時看病只能在現場排隊,排隊10到12小時是常態。
在外生病本就是人間疾苦,撐着病體通宵排長龍更是難熬。工作後,有一次,小婭需要做手術,她果斷選擇請假“打飛的”回國內醫院,很快完成了手術。
2020年之前,温哥華每天有4班回國的航班,那時小婭總會攢着假期回來陪伴家人,和朋友相聚,但每當回到温哥華,小婭內心卻變得空落落,“我認識這麼多在海外的人,沒有一個人不想家”。

《小敏家》劇照
她曾猶豫要不要回國,但習慣了海外生活的她,又下不了離開的決心,名校畢業、海外工作、移民身份,每個標籤都光鮮亮眼,讓同齡人羨慕不已。
近些年,父母年齡漸長,每次在電話裏小心翼翼試探着小婭的回國意向。2022年,她想了很久,下定決心辭職,結束了和當地男友的戀情,打包在温哥華近10年的家當,坐上回國的航班。
這一次,她從另一邊推開了那扇讓她又愛又怕的磨砂門,發現那扇門並沒有想象中可怕。
兩年間,小婭陪伴家中老人看過病、送飯、輪流看護。工作之餘,她喜歡陪着家人在家鄉街道溜達幾圈,看着父母漸漸老去,她慶幸自己及時回來,守住了和親人相聚的珍貴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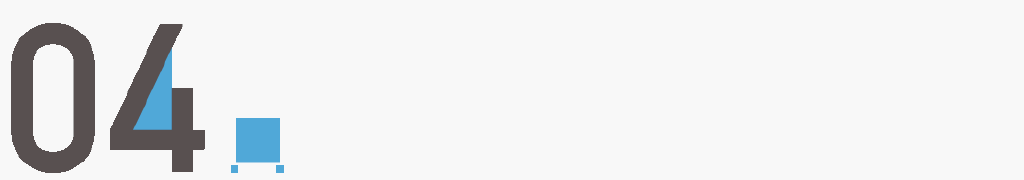
“職場天花板低,遍地都是狗屁工作”
出國前後的想法差異,像是典型的“圍城”困境,走出國門前,人們渴望海外生活的鬆弛與新鮮,走出國門後,卻又留戀國內城市的熟悉和熱鬧。
2016年,吳恙第一次到荷蘭旅遊,正值當地“國王節”,大街上都是塗滿五顏六色油彩、興高采烈的荷蘭人。
吳恙和她的華人朋友走在街上,隔着十幾米,有幾個荷蘭人熱情地向她們招手,甚至走到她們面前,遞過來兩瓶酒,碰杯、祝福,然後散開。

吳恙拍攝的荷蘭國王節盛況
吳恙被這種歡樂的氛圍打動,動了留在荷蘭生活的念頭,朋友問她要不要申請一年工籤,運氣好就能留下來。
吳恙聞言申請了工籤,卻遭到父親的反對。從小到大,吳恙跟父親摩擦不斷,控制慾較強的他不希望女兒留在國外。吳恙沒有顧及父親的反對,揣着僅存的1300多歐,留在了荷蘭。

吳恙搬到荷蘭那天發的朋友圈
熱心的朋友幫她在荷蘭租了一間小卧室,每月房租400多歐,但要“押一付一”。交完房租,吳恙只剩下300多歐,她用在英國買的小電飯鍋,每天給自己燉便宜的西紅柿雞蛋飯,或者拿郫縣豆瓣醬拌飯,就這樣簡單地應付了三個月。
吳恙在當地找到了一份傳媒類實習工作,月薪只有300歐。為了增加收入,下班後她還要到一家日料店做兼職,每天工作到晚上11點,站到雙腿僵直,久久不能緩過來。
幸運的是,吳恙實習轉正,如願留在荷蘭。她和身邊的華人朋友基本上都在華資企業工作,一方面是由於文化接近,本地公司傾向歐盟身份的員工;另一方面企業提供工籤的資質需要申請,因此,華人員工多的企業,更傾向聘用華人。
吳恙所在的傳媒公司負責視頻製作業務,在荷蘭分部只有3名員工。她的職位是“製片人”,由於工作人員太少,聯繫對象、採訪、寫腳本甚至後期剪輯、給外包人員結款等雜務,都要她來承擔。
每到結款時間,外包的攝像和剪輯就會聯繫製片人吳恙,“你們什麼時候打款?”“我都等了多少天了”,有段時間,吳恙一睜開眼就能看到幾十條新的消息通知,卻只能旁敲側擊提醒老闆,“這筆款應該打了,您看能不能明天支付”。
在以鬆弛著稱的荷蘭,吳恙依然需要週末加班,每天重複着“改字幕、摳logo”的瑣碎工作,工作能力很難得到真正的提升。
在荷蘭工作的五年,吳恙感受到一種無窮無盡的消耗感。表面上她工作體面、工資不低,每天從現場跑到機房,能接觸新鮮的人和事物。可吳恙自己知道,大部分時間,她都在處理細碎的外包工作,“小作坊”模式讓每一項工作,都只能蜻蜓點水、略沾皮毛,再深入的學問,自己一竅不通。

吳恙在荷蘭工作後期精神狀態展示
“加班文化”被老闆從國內帶到國外,身邊“996”的朋友比比皆是,到手的年假跟歐洲本地的同事差了十多天,吳恙覺得自己的工作熱情都被耗光了。
她在辭職後才對老闆講出心裏話,“做這份工作期間,我的能量一直在向下走”。
情緒脆弱時,吳恙喜歡外放一位網紅的直播視頻,她羨慕對方的情緒總能那麼飽滿,朋友勸她可以試試向這位主播的公司投遞簡歷。
她在國內求職網站上傳自己的簡歷,除去心儀主播所在的公司外,陸陸續續面試了好幾家互聯網大廠。
國內平台提供的就業機會比荷蘭多,在跟國內HR交流的過程中,吳恙發現自己對工作的好奇和熱情重新迴歸,狀態慢慢變好了。
“相比荷蘭的工作,國內的賽道過於細分,我要想想哪一條更適合自己”。對於吳恙來説,國內崗位龐雜、工作細分,也像是一望無際的曠野,未來的挑戰不比當初出國工作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