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養老院”爆火:“躺到終點”還是“詩與遠方” ?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54分钟前
編者按
據中國新聞網等媒體報道,自2024年春節後,很多咖啡廳、酒吧、民宿、農家樂都打出了“青年養老院”的牌子,一羣二、三十歲的青年人打造一個場所給另一些青年過“養老”生活,成為青年人羣體中一種新的“潮流”。“早上起牀先去吧枱喝杯咖啡,在小院打套八段錦後,就去山上‘禪坐’,下午去捕魚或幫老闆種地.……”以上構成了“青年養老院”的日常。近期,自青年人扎堆入住養老院後,青年人開屬於自己的“養老院”作為新興話題成功破圈,引發輿論熱議。有觀點認為,這是青年人面對社會巨大的競爭壓力和自我的精神壓力,主動逃避和躺平的體現,不值得提倡。也有觀點指出,“暫時養老”是為了重新出發,應該對青年人多一點鼓勵與包容。
事實上,面對當今社會的快速發展和變遷,青年人生活和工作節奏越來越快,利益分化越來越嚴重,以至“佛系”“躺平”等流行話語席捲網絡,類似“青年養老院”的現象屢見不鮮,而如何正確認識和引導這些現象背後的青年社會心態,一直是各界關注的議題。對此,本文指出,躺平是複雜的意義場,不同的人在躺平問題上有不同的心理投射,賦予躺平不同的意義。對某些人來説,躺平是詩與遠方,而對另一些人來説,躺平不過是受挫後的自我解嘲,對於“躺平學”或“躺平族”,應該分情況對待,關鍵是直面躺平背後的社會問題。本公眾號特推出此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合成症候躺平現象分析
汪行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2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躺平如石投湖,一時引起巨大反響,是各種聲音的輻輳。在幾十年高速發展之後,改革紅利正在稀釋,年輕人求職越來越難,職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生活和工作節奏越來越快,利益分化越來越嚴重,少數弱勢人羣生活越來越艱難。在這些情況下,一些人覺得,與其抱怨命運不如改變自己,於是調低自己的慾望,選擇消極退讓的生活態度。還有一些人雖未受上述威脅,但對工業化社會的過度生產、市場經濟催生的過度消費以及全球化時代的過度競爭日益不安,因而也同情和支持躺平。總之,不同的人在躺平問題上有不同的心理投射,賦予躺平不同的意義。因此,筆者把它看作一種合成症候。

一、
首先,在最直接的意義上,躺平意味着閒暇和自由時間,而這是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人被定義為使用工具的動物,勞動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活動,它既是對勞動對象的改造,也是對人自身的改造。就此而言,勞動是人類文明的基礎,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然而,現實中勞動並非都是積極的。馬克思就曾批評黑格爾只看到勞動的積極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方面。不僅如此,馬克思還認為,即使是非強制條件下,勞動的意義也不在於其自身,而在於為閒暇和自由時間創造條件。馬克思在論自由王國和必然王國的著名段落中指出:“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説,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也即真正的自由不是人類理性地認知和改造自然的勞動和生產活動,而是在自由時間中全面發展人的自由個性和能力的活動。在此意義上,自由時間(閒暇)相對於勞動來説具有規範上的優先性。
從這一角度看,作為人類的基本需求,躺平可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加以闡釋。從消極方面説,躺平表達了對閒暇和自由時間的渴望。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曾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懶惰權》,顛覆了勞動光榮、懶惰可恥的正統信條,旗幟鮮明地主張“懶惰權”。拉法格敏鋭地注意到,在資本主義社會,貧困和勞動之間存在着惡性循環,工人越貧窮就越勞動,而越勞動就越是受貧困折磨。與馬爾庫塞反對多餘壓抑相似,拉法格反對出於特殊階段利益強加給工人的多餘勞動。在他看來,一個社會如果合理地加以組織,每天勞動時間可縮至三個小時,到那時,勞動成為閒暇的調劑。從技術和生產能力的發展來説,這樣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關鍵是我們要改變對閒暇的態度並公平地分配享受閒暇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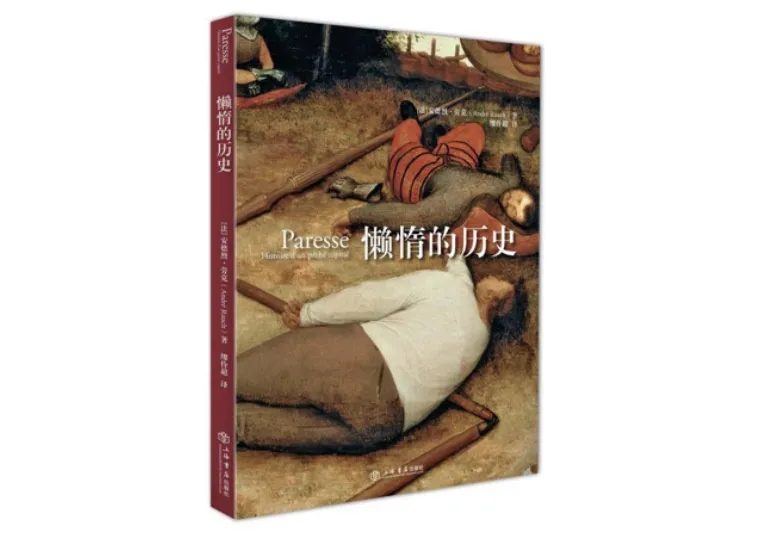
從積極方面説,躺平可以理解為超越了物質需求和功利束縛的自由自願的活動。貝恩德·布倫納在《躺平的藝術》中詩意地説:人生於躺平,死於躺平。在他看來,躺平是一件隨性自然的事情,我們釋放壓力,放鬆自己,從日常繁忙和牽掛中抽離出來。在此意義上,躺平象徵着一個出離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人們可以從事各種以自身為目的的活動,如思考、藝術創作和遊戲。實際上,在人類文化史中,勞動人和遊戲人是兩種相互競爭的人類形象。相對於感性的、物質的勞動,席勒高度讚美遊戲。在他看來,勞動的成果維持着人的生存,但只有遊戲才能使人性得以完滿,“説到底,只有當人是完全意義上的人,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時,他才完全是人”。荷蘭文化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在《遊戲的人》一書中指出,遊戲是在特定時空範圍內進行的一種自願活動或消遣活動,它以自身為目的,伴有緊張感、喜悦感,並與日常生活相區別。他強調,遊戲是人類共有的,是一切文化形式的基本因素。“最初階段的文明是玩出來的;文明並非像嬰兒自己脱離子宮那樣產自遊戲,而是在遊戲中產生併成為遊戲,並且與遊戲永不分離。”當然,遊戲不等於躺平,遊戲有時也是緊張的,但它們都是以閒暇為前提,都要求以自身為目的並擺脱外在功利的束縛。在某種意義上不妨説:遊戲是最高意義上的躺平,而躺平是最低意義上的遊戲。只有當人類有了躺平的條件,才有時間放鬆、遊戲、交往,才有時間發展藝術和文化,並在此過程中增進人與人的團結。就此而言,躺平是任何合理社會的必要因素。在西方文化中,上帝賜福於人類的方式之一就是讓人工作六天後有一天休息。《詩經》也説:“民亦勞止,汔可小息。”在中外文化中,躺平和休息都被承認為人類生活的合理需求。

二、
其次,躺平主義部分地表達了人們對工業化社會的生產主義、消費主義的不滿,表達了調整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以及人與自身關係的積極願望。在躺平問題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部分人之所以同情和支持躺平族,不是緣於與“996”族或“三和大神”處境相同而感同身受,而是以躺平來象徵詩與遠方。
二戰後,西方各種激進思潮的一個共同點是反對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存在主義對大眾社會異化的批判、馬爾庫塞對單面人的批判、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批判、哈貝馬斯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無不藴含着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思想衝動。英格爾哈特注意到,西方社會的公眾價值觀在20世紀下半葉從物質主義向後物質主義轉型。“物質主義類型(materialist)價值觀有一種強烈的維持秩序和經濟所得的傾向。後物質主義類型(post-materialist)價值觀則強調個人的自我表達,以實現一個輕等級、重參與的社會。”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革命是持久和廣泛的,它不僅指向對規訓社會的批判,也指向對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功績社會的批判。
福柯把現代社會視為規訓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典型的權力形式不是統治者的任性或國家暴力,而是工廠、學校、監獄、醫院、軍營等規訓機構及其規訓技術。在規訓社會中,人的欲求和生命受到全面控制,主體失去了意識和行為的自發性,人失去了與周邊環境的熟悉關係,社會成員之間失去了主體間溝通的橋樑。1960年代之前,現代性批判針對的正是這樣的社會。今天,西方正從規訓社會向自我控制的功績社會轉變。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指出,規訓社會以權力對人的外在監視和控制為特徵,功績社會以人的自我強制為特徵,前者是外在地鞭策,後者是內在地激勵。表面上看,在功績社會中,個人對生命和時間有更多的自主權,但是,在高度競爭的社會結構和功績主義的意識形態支配下,每個人為了維持已有的社會地位和消費水平,不得不自我監督、自我驅使、自我加碼,最後掏空自己,陷入厭倦和躺平。可以看出,韓柄哲的倦怠社會論,其診斷和把握到的正是當今許多中產階層和都市羣體的躺平心理。
躺平者並非都想身體上躺平,在社會批判理論視角下,躺平更多的是一種對現代性和現代化進行抵制和反抗的象徵符號。與現代性崇尚的更快、更高、更強不同,今天許多人偏愛“慢生活”、自己動手、與自然親近等。在一些人看來,慢是很重要的價值。盧茨·科普尼克在《慢下來:走向當代美學》中指出,作為一種對運動和時間流逝模式的獨特反思,慢速美學有權堅持自己的要求。當下,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物質生活仍是重要任務。但是,規訓社會、消費社會、倦怠社會和加速社會等帶來的社會問題已進入我們的生活,它們所引發的對現代性和現代化的反思影響着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城市中產階層。這是躺平話題引起眾多共鳴的背景和原因。
三、
最後,躺平反映了當前社會亟待解決的一些突出問題。前文談論的更多是信念價值型躺平。然而,“三和大神”式的打工人以及飽受內卷煎熬的學生、職員、家長等羣體的處境和困難,才是躺平問題受到關注的更切近原因。對這些人而言,躺平不是詩與遠方,而是生活的無助和倦怠,這些被生存需要或內卷困擾者,我們不妨稱之為生活掙扎型躺平者。信念價值型躺平者與生活掙扎型躺平者,都通過躺平表達對現實的不滿,但前者不滿的是世界沒有體現其期待的價值,後者不滿的是自己在現有價值體系和社會安排中受挫。大致來説,前者的躺平是主動的,後者的躺平是被動的。
為什麼被動躺平者要自我標榜“躺平”?眾所周知,在古今中外的主流文化中,躺平者的形象總體上是負面的。如何理解躺平者對躺平的主動認同與社會對其負面評價之間的詭譎關係?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對徵兆人的討論可以給我們以啓發。按照拉康—齊澤克的邏輯,躺平對躺平族來説是其自我同一性——他是自主行動的主體——這一人性外觀的必要徵兆。被動躺平者對躺平能指的依戀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只有那些在生活中無法自如地躺平的人,才會特意強調是自己選擇了躺平。“我選擇躺平”表明,即使無足輕重,我還是一個人,一個意識主體。正如齊澤克所説:“徵兆,作為徵兆合成人的徵兆,從字面上看,是我們惟一的實體,是對我們存在的惟一的實證支撐,是賦予主體以一致性的惟一之處。”躺平之於躺平者正是這樣的徵兆,藉助躺平,躺平者既向他人也向自己表明:無論人生成功與否,我仍然擁有躺平這一剩餘快感。基於對徵兆的這一理解,齊澤克認為,對待徵兆人,不能剝奪其徵兆,或給他們指派一個崇高的符號象徵物。躺平者對待徵兆的正確方式應該是:認同徵兆,避免陷入絕望和完全的自我否定。應該承認,被動躺平無論表現形式如何,都不是個人選擇的,而是由客觀環境造成的。所謂“選擇”無非是他們維持自尊的唯一方式。在此情況下,與其去指責躺平者的錯誤認同,不如關注躺平產生的原因。只有當產生躺平的客觀環境消失後,躺平者的自我幻像才會隨之消失。

總而言之,躺平是複雜的意義場,其中包含着不同的訴求和含義。對某些人來説,躺平是詩與遠方,而對另一些人來説,躺平不過是受挫後的自我解嘲。鑑於躺平族或躺平學含義的多樣性,我們應該對它們區別對待。作為人類的基本需求,休閒和遊戲意義上的躺平具有永恆的意義,並且是社會發展的衡量標準,躺平問題的討論有助於我們深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作為對生產主義、消費主義、加速社會、功績社會的抵制而言,躺平部分地表達了人們對現代性和現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對那些深受內卷之苦的被動躺平者,我們不僅應該予以同情理解,而且要通過社會的發展和完善,消除這種躺平產生的根源。如果以這種方式積極地對待躺平現象,躺平問題就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對它的討論可以推動我們思考什麼是合理生活,對我們的社會經濟結構、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進行反思。直面躺平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有助於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