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都亡了,香港的法官們,幾時才能把頭上的方便麪摘掉呢?_風聞
孤烟暮蝉-时评人-珍惜未来,远离公知1小时前
一、大清亡了要剪辮子,大英亡了為什麼還不摘假髮?
不知道在看這期節目的同志和朋友,有多少和我一樣,時不時就會把以前的港劇港片搬出來回味一下的習慣。如果你們也有這個習慣的話,不知道你們在港劇港片裏看到香港的法律從業者——主要是法官和律師的時候,會不會產生這樣一個疑問:
“這些人難道都是禿頭和地中海嗎?還是説覺得香港室內的空調開得太足怕着涼?不然為什麼這幫人做什麼要在一個終年濕熱的亞熱帶地區戴着一頂卷得跟方便麪一樣的金色假髮呢?總不至於説是覺得這玩意戴着好看吧?不會吧?”

反正我會,我一直都很好奇這個問題,最近一次讓我回想這個問題的,是我這幾天在大公文匯網上看到的一篇評論文章,説是特區政府立法會這陣子就《2024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進行了首次解讀,針對多條條例作出簡單直接的調整修改,並廢除了若干條例中有違香港特區憲制地位的過時條文或提法。

去過香港的同志和朋友都知道,現在香港還有很多地名和路名都是從英語直接音譯過來的,有些甚至乾脆就是和英國王室的息息相關的。其中比較典型的包括: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山、皇后大道、域多利皇后街、英皇道、太子道和公主道等。
而已故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來命名的香港地方更是多達5處:包括伊利沙伯醫院、伊利沙伯中學、伊利沙伯體育館、伊利沙伯醫院路,以及伊利沙伯醫院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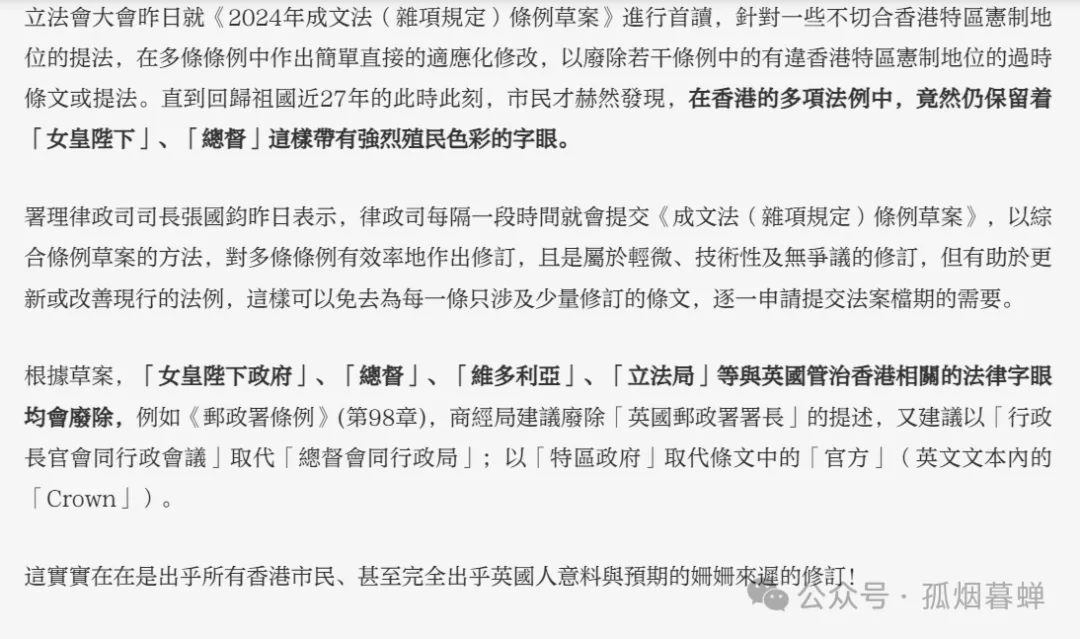
報道提到,以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為例,在其執政的60年間,歷經了工業革命的英國逐漸發展成為殖民地橫跨全球的所謂的“日不落帝國”,由此開啓了英國對外殖民史上的“輝煌巔峯期”。通過船堅炮利,英國殖民者在海外不斷攻城掠地、燒殺搶掠,幾乎掠奪了當時全球一半的財富。
1841年,英國殖民者強行登陸香港,用武力逼迫清政府與之簽署《南京條約》,港島就此被迫割讓給英國長達150多年。1861年1月,英軍再度佔領九龍半島,同年4月,英國人將香港島與九龍半島之間的海港,以當時在位的維多利亞之名,命名為維多利亞港。
除了維多利亞港之外,於1861年建成的伊利近街同樣散發着侵華英國殖民者的惡臭。這條道是英國人伊利近伯爵於1861年到港之後命名的,當年他曾指揮英法聯軍侵我北京,燒燬了圓明園,給中國人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痛與恥辱。
之後,伊利近更是以全權公使的身份,在武力的脅迫下,逼使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全部劃入了英國殖民者的麾下。
還有砵甸乍街。1842年8月,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時,砵甸乍作為英方全權代表,因為英國強佔香港立下了“汗馬功勞”,遂獲委任,成為了英國殖民政府委派到香港的第一任駐港總督。
1843年,維多利亞簽署《香港憲章》,宣佈香港成為英國殖民管治地,並委派砵甸乍為香港第一任總督,同時令其兼任英軍駐港總司令。1858年,港英當局將一條用石塊砌成的街道取名為“砵甸乍街”。
在文章中,大公文匯的評論員用不無悲憤的語氣評論道:
“毫不誇張地説,砵甸乍街的每一塊石板,或許都曾浸潤過港、九、新等地抗英義士的鮮血。而他們的血滴,直到現在也還在若隱若現地滴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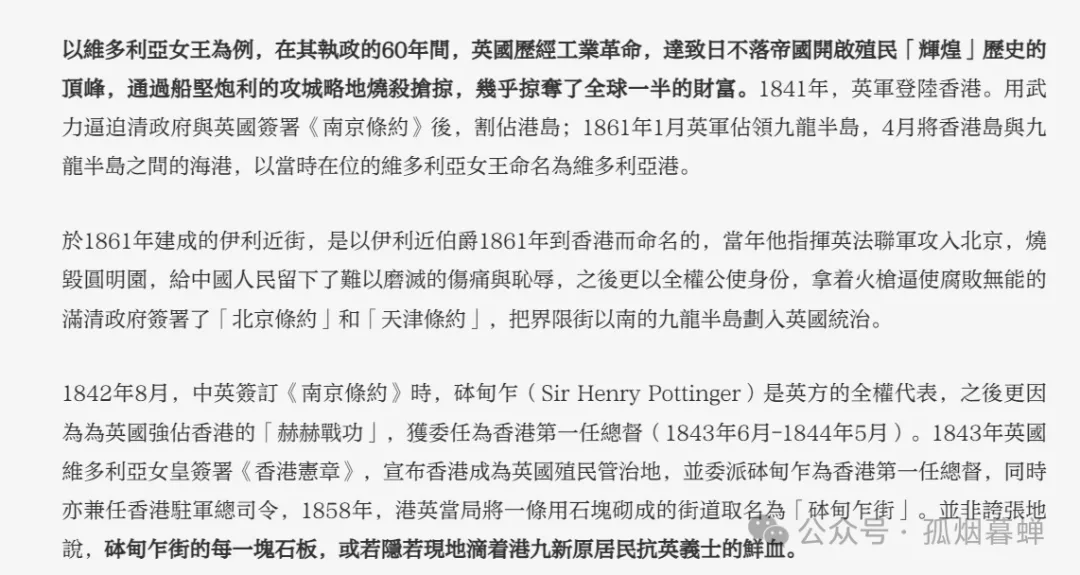
香港市民腳下所走的道路如此,香港法律工作者頭上戴的假髮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和今天香港的很多東西一樣,香港法律工作者頭上戴的那頂金色假髮,也是當初隨英國殖民者的堅船利炮一塊轟進香港的。而英國人戴假髮的習慣,最早則是從法國人那兒學來的。
現在很多研究歐洲假髮發展歷史的學者普遍認為,英國法官戴假髮的這個習俗,起初應該是跟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學的。從17世紀中葉開始,包括梅毒在內的花柳病開始在歐洲的上流階層人士中間廣泛傳播,特別是在當時西方世界的文明中心巴黎,而巴黎又屬法國王室玩得最花,所以包括法國國王在內,這幫人玩着玩着就把自己的頭髮給玩沒了。

為了遮醜,不讓旁人察覺自己是因為得了梅毒而禿的頭,法國的權貴們於是開始紛紛戴起了假髮。而法國人的這一無心插柳之舉,很快就在歐洲的上流社會和中產階級中間掀起了一股跟風潮,很多英國人,包括當時的英國國王查理二世,也開始紛紛學着法國人的打扮,戴起了假髮。

到了 1685 年,齊肩假髮已經逐漸發展成為歐洲宮廷禮服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了一種權勢的象徵。人嘛,都是喜歡趨炎附勢的,在18世紀,因為那時英國上流社會的成員都已經佩戴假髮了,所以這種衣着時尚最終也發展成了當時英國法律工作者們日常工作着裝的一部分。


特別是英國法官和英國的大律師,他們尤其愛戴假髮出庭。在當時一頂品質優良的假髮還是比較貴的,一般的律師未必能戴得起。很多大律師戴假髮就是為了將自己和普通的小律師區分開來。説是這樣能法庭上建立起一種“正式感和尊重感”,但在我看來,英國人整的這出説穿了其實就8個字:豬鼻子插大蒜——裝象。

二、香港法官和律師,心裏默唸的是“Long Live The Queen”呢?還是“人民萬歲”呢?
雖然戴假髮在英國一度十分流行,但到了1820
年代,這一套就不吃香了。在工業革命搞起來之後,英國在國力上已經逐步實現了對法國的反超,於是乎,英國人開始追求具有本國審美特色的衣着品味了。很多英國的上流人士和中產階級開始紛紛摒棄掉假髮這種過時的審美,但是英國的馬車伕、宗教界人士和法律工作者仍然保留了這個習慣。到了1830 年代中期,馬車伕和大主教們也不戴了,就剩下英國的法官和律師還在抱着假髮不放。
雖然英國司法界在此後仍將戴假髮這個習俗奉為圭臬,並且堅持了100多年,但在進入21世紀之後,終於就連英國司法界自己也不再堅持抱守殘缺了。從2007年起,除刑事案件之外,在民事法庭或最高法院出庭時,英國法律工作者不需要再強制戴假髮。戴不戴全憑出庭律師主審案件的法官自行決定。

自那以後,雖然還是會有一些英國律師選擇在民事訴訟中戴假髮出庭,但這種人正變得越來越少。一般來説,通常只有那些倚老賣老的資深大律師才更喜歡這套“祖宗之法”,年輕一代基本上已經不太認這個了。
正如前面提到過的那樣,假髮這東西當初是隨英國殖民者一塊漂洋過海而來的舶來品,過去粵語地區的法律工作者其實是不興這個的。看過《算死草》和《狀王宋世傑》這些老港片的同志和朋友應該還有印象吧?片子裏的陳夢吉和宋世傑在港英當局的法庭上打官司時,腦袋上還都頂着大清的辮子呢,而和他們打口水仗的英國法官、律師呢?都是穿着一席黑色長袍、戴着一頂金色假髮的,他們的衣着與今天的香港法律工作者的並無太大區別。

那為什麼後來香港本土成長起來的法官和法律很多都以戴假髮而非蓄辮子為榮了呢?因為大清亡了唄,後來人都紛紛剪掉了腦勺後頭的辮子,這叫順應時代潮流。那為什麼非得戴假髮呢?因為當時的香港處在英國殖民者的控制下,行使的是英國的司法制度。英國人是一等人,華人是二等人,你要在一等人的條條框框裏玩他們的遊戲,可不就得儘量把自己打扮得跟他們一樣嗎?
可問題是,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就回歸中國了呀,自那以後就再也沒有什麼英國政府遠程遙控的“港英當局”了,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管轄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法律工作者,特別是法官,這些人自那時起就是在靠陸港兩地人民的血汗錢和政府財政在供養着了,這幫人要和主流時尚審美接軌,那也是向北邊的大陸看齊啊。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戴着那頂當年路易十四為了遮掩因為梅毒而禿掉的腦袋瓜子的金色捲毛假髮呢?是因為你們這些司法工作者有尋花問柳的嗜好,也得了掉頭髮的花柳大病了?還是出於其他一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就是沒有哪個香港法律工作者敢説出來的原因呢?

比如,咱們就這麼説吧:諸位香港的法官和律師,你們在法庭上主持你們口口聲聲的那所謂“公平正義”的時候,心裏頭到底默唸的是“Long Live The Queen”(吾皇萬歲)呢?還是“人民萬歲”呢?如果是前者的話,那我只能説香港司法界直到現在也還這幅德性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都説人這種動物啊,相由心生,我看不光是面相,衣着打扮也一樣。
而且,説來搞笑的是,哪怕是香港,其實在2021年也已經廢除了律師在出庭時必須佩戴假髮的硬性規定了——但這個改變不是因為我們大陸這邊向他們施加什麼壓力了,而是因為一個錫克教律師的吐槽,他説他因為宗教緣故要包頭巾,不方便戴假髮。香港司法界是考慮到這一層因素,所以才給律師戴假髮的規定放寬限制的。可即便如此,直到現在也還是有很多香港律師繼續頂着一頭方便麪打官司。
三、為人民服務,才是一個法律工作者永恆的頂級時尚
大公文匯在他們評論香港殘存的英國殖民主義地名的那篇文章裏有一段話,我覺得説得非常好,用來形容如今在香港法律工作者中間仍然風行的佩戴假髮的習慣也挺合適的:
“也許是英國人喜歡寵物狗的緣故,久而久之,就養成了狗的習慣,一隻寵物狗在新到的所經之地,都會揚腿撒泡尿,有時甚至是可憐的點滴尿水,但這都不影響牠宣示屬地管治的強烈目的。這就如同香港的諸多街道公園,狗雖遠去,但是那種陣陣尿騷味,卻着實叫人孰可忍孰不可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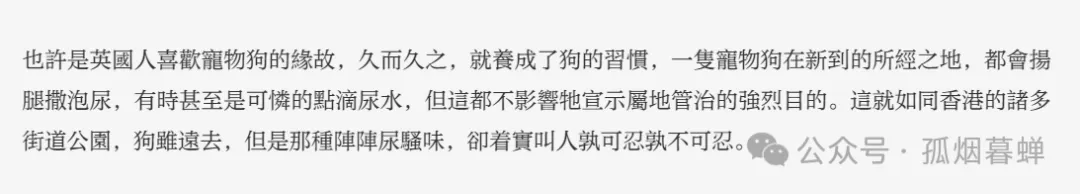
身為一個生在紅旗下、長在春風裏的中國人,恕我直言,香港法官和律師們頭上的那頂假髮是真的醜,又土又殖。我不覺得那玩意現在還能算是什麼“特權的象徵”,開玩笑,伊麗莎白二世連她在英國的一家子都管不住,你們還指望她能保佑你們遠在中國的特權地位和富貴榮華呢?至於時尚什麼的,那就更扯淡了,哪個雙商三觀正常的人會覺得戴這玩意是時尚的?這是法庭又不是漫展,怎麼着?你們該不會當你們在玩Cosplay呢吧?

如果非要將法律和時尚這倆看似九不搭八的東西聯繫起來,我倒是剛好能想到一些應景的例子,但是這些例子和香港那羣頂着方便麪頭的法官律師們無關,全部來自大陸,來自我們黨領導下的、以為人民服務為第一宗旨的、以廣大共產黨員為核心的法律工作者隊伍。
比如溜索下鄉辦案的重慶奉節縣庭長程政清、審判員李明航、舒濤和書記員王威。

比如騎馬巡迴辦案的新疆烏魯木齊縣法官努合馬爾。



比如在隆冬臘月、頂着沒蓋的大雪也要騎馬巡迴辦案的內蒙古通遼市扎魯特旗人民法庭的法官那順。

內蒙古通遼市扎魯特旗巴雅爾吐胡碩人民法庭法官那順在冬季騎馬巡迴辦案
比如在車輛無法通行的雪域高原上,騎着犛牛跋山涉水開展巡迴辦案的新疆塔什庫爾幹縣人民法院法官斯提卡達木。

新疆塔什庫爾幹縣人民法院法官在車輛無法通行的雪域高原上騎犛牛開展巡迴辦案
比如身負碩大的國徽,在鄉野之間長途跋涉,巡迴辦案,送法下鄉的雲南祥雲縣法院副院長白玲和她的同志們。

雲南祥雲縣法院工作人員徒步巡迴辦案
同樣是幹法律工作的,這些大陸法律工作者的收入,大概率連他們那頂着一頭方便麪的香港同行的一個零頭都不到。

但這並不妨礙我覺得他們時尚。不光時尚,而且還很高大。有多高?有巍巍崑崙那麼高,有珠穆朗瑪那麼高。我覺得他們的工作就是在向我們印證這樣一個道理:即便有些地方實在是險峻到就連人性也無法暫時通行了,但是我們的黨性依然可以。
他們全身上下的行頭可能還沒香港法官律師們的那一頭假髮值錢,但是他們身上揹負的國徽,還有胸前的黨章,卻要比所有這些戴着昂貴假髮的香港法官律師,還有他們在英國的“遠親”們的名頭加起來還要耀眼。
什麼是時尚?為人民服務才是最高級的時尚,而且是永不過時的時尚。
醒醒吧,香港司法界的諸位,大英帝國早就亡了,你們還戴着那頭方便麪給誰看呢?《覺醒年代》裏的辜鴻銘説過,頭上的辮子好剪,心裏的辮子難剪。就如今來看,難的豈止是剪一頭辮子啊,要把這腦袋上的假髮給摘下來,恐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咧。

但就是因為難,所以才有必要做。就是因為難,所以才更值得去做。惟其艱難,方顯勇毅,先烈們當年冒着掉腦袋的風險都能把辮子給剪了,我就不信我們今天還摘不掉他們頭上那頂假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