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勇 | 以味不以形: 中華審美文明的標杆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31分钟前
王才勇 |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4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王才勇
**以味喻詩、以味論畫無疑是中華美學敍事的一個傳統。**殊不知,這樣一種基於類比思維的敍事方式恰好標識出了中華審美文明的固有之處,即便到了當代,也值得頌揚,堪稱中華審美文明一張亮麗的名片。
説其固有和亮麗主要是與西方同比。審美無疑是一種感知活動,建基於感官快感。美學敍事主要指向視聽,這是任何文明的常態,但是,以味喻美則非中華莫屬。放眼西方,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便明確拒絕了以味喻美的做法,有言:“美只起於聽覺和視覺所產生的。”“因為我們如果説味和香不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會拿我們做笑柄。”亞里士多德雖然在很多方面批駁了柏拉圖,但是,其論美還是沿襲了視覺中心主義的做法。他在《論靈魂》中講味覺時將味覺與觸覺並列,視之為直接接觸物質的感知活動,以示與視覺和聽覺的區別。狄德羅也認為,美不是全部感官的對象,只有視、聽感官才是“審美感官”。到了黑格爾那裏,情形絲毫未變,正是基於物質性程度的高低他才説道:“藝術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視聽兩個認識性的感覺,至於嗅覺、味覺和觸覺則完全與藝術欣賞無關。”
中國則相反,一開始就用味來喻美。《左傳》論樂之美就明確沿着“聲亦如味”的思路展開,更為著名的是“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將味美與視聽之美相提並論近乎成了先秦諸子的通用做法。《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莊子·盜蹠》)《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嗜焉;耳之於聲,有同聽焉;目之於色,有同美焉。”(《孟子·告子》)《荀子》曰:“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荀子·勸學》),等等。東漢《説文解字》裏著名的表述,“美,甘也,從羊從大”,還是在以味喻美。至於魏晉以後,以味喻詩、以味論畫的興起,更是成了中華美論、詩話、畫論、書論、曲論的一個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重要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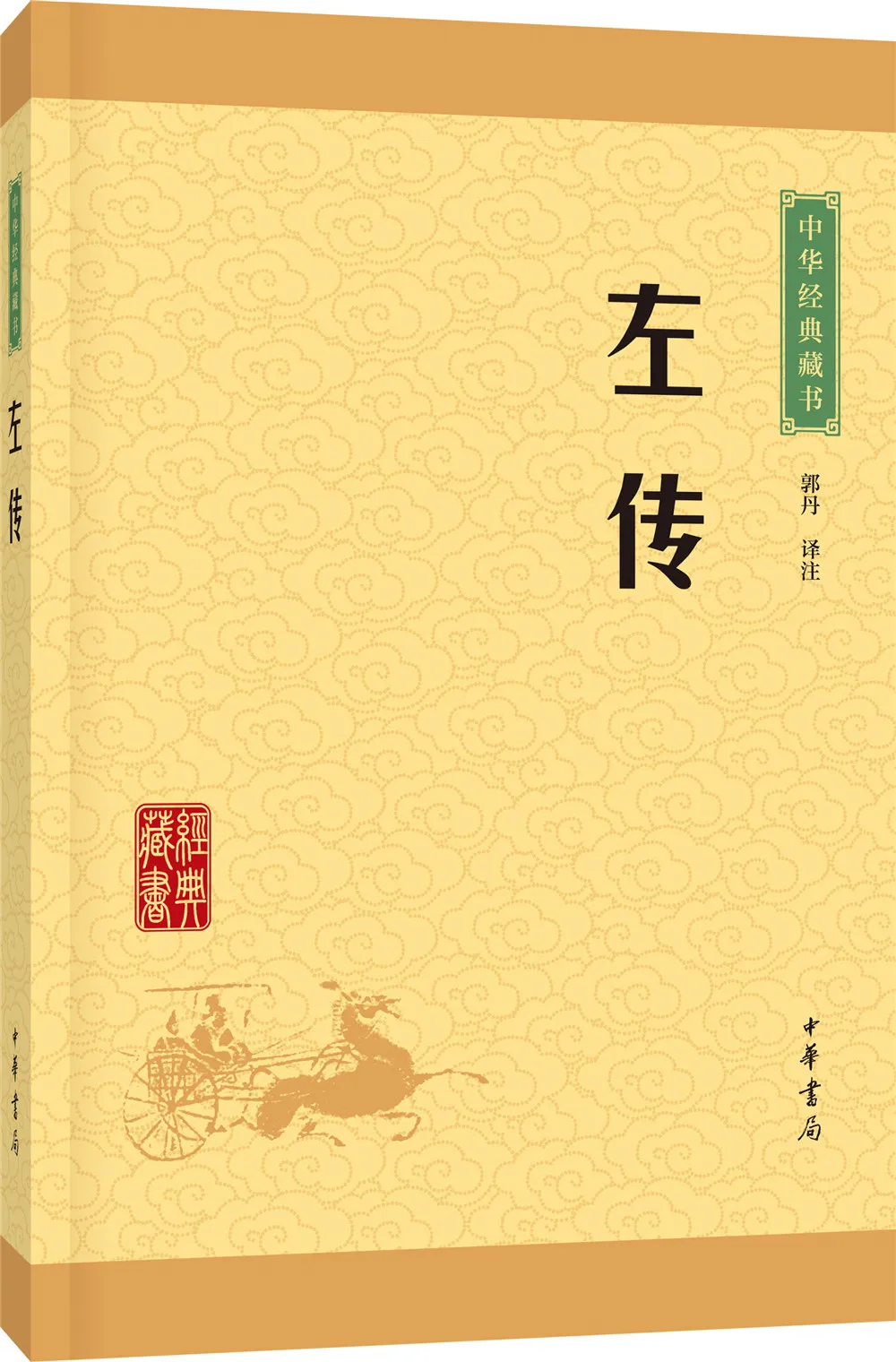
單純從用詞的角度看,taste(味,味覺)一詞在古希臘時還未用於審美。但到了中世紀,尤其是文藝復興以降,情形發生變化,taste一詞開始出現在美學敍事中,比如霍布士、洛克、休謨,包括康德等的相關論述。但它已全然不是味覺感官意義上的用詞,而是在衍生義即口味、趣味意義上來説事,話語大多指向趣味,背景是對個體生命和意義的發現。17—18世紀的歐洲,味成了言説審美差異的一個喻詞。相關美學討論進而關注,口味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本來表明人類共同味覺感知的一個詞,在西方沿用到審美敍事中演變成了一個敍説差異的主詞,進而在研討道德感問題中獲得了重要意義。其美學上的意義就僅指向口味、趣味,衍生義有鑑賞、鑑賞力、審美觀、見解、判斷、看法等。
**與中華美學傳統不同,taste一詞在西方美學討論中完全定格在個體性的主觀趣味上。**對此休謨説得很清楚:“理智傳達真和偽的知識,趣味產生美與醜及善與惡的情感。前者按照事物在自然界中實在的情況去認識事物,不增也不減。後者卻有一種製造的功能,用從內在情感借來的色彩來渲染一切自然事物。在一種意義上形成了一種新的創造。理智是冷靜的超脱的,所以不是行為的動力……趣味由於產生快感或痛感,因而就造成幸福或痛苦,成為行動的動力。”康德的美學分析專注於鑑賞判斷(Geschmacksurteil),其實就是要分析憑主觀趣味或口味(Geschmack)而來的鑑賞判斷,目的在於從如此具有主觀性的趣味判斷中建構出一些普遍性法則,即建構出審美趣味判斷的所在。一般趣味判斷是個人的,不具有普遍可傳達性,唯有審美趣味判斷才具有普遍性。康德的美學分析旨在建構出審美趣味判斷的構成。在康德那裏,taste(德語Geschmack)一詞還是指個人的口味或趣味,審美趣味判斷只是他努力做的區分,旨在區分出受個人趣味左右的一般快感和超越個人趣味的美感。審美趣味判斷,即美感,還是跟味覺(taste,口味、趣味)沒有任何關係。後來克羅齊關注趣味是因為趣味體現了人的身份,可以由此劃分不同階級階層,他將趣味研究變成了品味研究。此間依循的還是趣味的主觀性內涵。
**味覺或品味這樣一種官能感知在中國則完全與美相提並論,並且成為美感要義之所在,對象之所以美是因為有味。**味或味覺在西方美學討論中從未受到關注,而且由於其感物的直接性還不斷被逐出美學敍事的領地,後來即便有出現也完全不是在敍説美是什麼,而是在敍説審美的個體差異,即引發審美差異的主觀原因。可以説,味之於美學敍事在西方是切入味覺的差異方面展開的,回答的是審美何以出現個體差異的問題,在中國是切入味覺的共同方面展開的,回答的是美是什麼的問題。
中西之間之所以出現如此涇渭分明的差異,顯然與不同的審美理想建構有關。歷史長河中,西方主要是從視聽感覺出發去建構自身審美理想的,而且從一開始就將原初意義上的味覺剔除出去;中國則主要從味覺出發,建構出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美學追求,此間並沒有排斥視聽領域的審美享受,只是藉助味覺感知來解密視聽領域的審美快感。
審美理想和美學追求無疑是任何民族審美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由於審美屬於感覺層面事項,審美文明建設大多在於往感官快感中注入一些越過官能快感的精神性內涵。這樣的注入在西方尚智精神引領下,抬高了視覺和聽覺,壓低了觸覺、味覺、嗅覺,其理由是人五種感官中,視聽離物質最遠,最為內藴思維,“嗅覺、味覺和觸覺只涉及單純的物質和它的可直接用感官接觸的性質”,因而,西方一開始就只承認視聽領域的快感為美感,將觸覺、味覺、嗅覺這些官能快感嚴格逐出審美領地。中國在向感官快感注入超越官能快感之精神性內涵過程中着力克服受外物所役,直接否定了單純駐留於外物的感知,故“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而“五味令人口爽”是因為“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道德經·第十二章》)。五味令人在單個物之間“馳騁”,而不是駐守在單一物中,就像騎行狩獵一樣,所以悦心。精神性在中國直接落在了“心”之上,而非“思”。後來的“應目會心”(宗炳《畫山水序》)之説同樣延伸了此義。
**感官活動的直接性決定,但凡感覺,都是對單個物的感,要從中見出精神,必然要超越對單一外物的感。**這種超越在西方一開始就聚焦於五種感官中相對可與具體物質保持些許距離的視覺和聽覺,在中國則走向了直接拋開與單一外物即具體物的接觸,不駐守於單個物之中,而從中走出,馳騁於萬物之間。這樣,沒有了對單個物的感,卻有了對馳騁萬物的感,所以賞心。“聖人為腹不為目” (《道德經·第十二章》)就在弘揚從單一外物走出品味內涵的精神。
視覺較之於味覺、嗅覺和觸覺雖能與對象保持一定距離,但卻帶着對象外顯的全部豐富性。這樣,對單純感知的超越就無法在感這一活動內部發生,只能來自外部,來自感知之外,來自思。思與感是屬於不同界面的東西。西方審美文明建設的核心在視覺中心主義框架下一開始就建基於思,或曰理性,是在保留對象可感豐富性的情況下,由思向感官知覺中注入精神性,這是一種外在注入,不是物自身的內在生成。
所以,西方美學討論中,柏拉圖對理念,亞里士多德對必然律以及後來對想象等問題的關注,都在憑藉思或理性的力量向官能快感中注入精神性內涵。**而中華審美文明從一開始就開闢出了以味喻美的路徑,雖然拒斥了視聽感官的主導,放棄了貼近具體物的感性豐富性,但還是經由味感留在了感知層面。**西方審美的感性機制經由視覺中心主義建基在了物本身的感性豐富性上,超越物的精神性只能由思注入;中華審美的感性機制經由味覺中心主義建基在了對物之變的感知上,超越就在感知本身發生,無須外在注入。西方審美理想是感性(物)+精神(思),中華審美理想是本身內藴精神的感性,或曰感性內藴着精神。前者機械,外發生,後者有機,內生成。
就味覺機制本身而言,味覺大多是在咀嚼時誕生,是在滅掉(克服)單個物時生成。物豐富的外顯性雖然消失,但內藴的味道呈現。中華審美文明在建構感官之精神性過程中剔除了視聽,落在了味覺上,旨在追求一種從單個物走出之後生成的超越性感知,超越物之外顯,進入物之內裏。這是一種不留於固定物而貫通眾物的感知。這顯然與思無關,不是思可以造就,無法由外注入,而只能由感物本身來生成,即所謂體認。中華審美文明以這樣的方式超越了對外物的感。但是,感沒有停止,感依然在,只是由對單一外物的感轉向了對物之生成的感。沒有了物而只有物之生成, 這是一種自我生成而非刻意注入的超越。中華美學敍事中大量出現的以味喻詩、以味論畫的情形清楚表明了對這種審美理想的普遍認可和接受。南宋楊萬里在論江西宗派詩之美時曾寫下名言“以味不以形”(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一句話道出了中華審美理想的獨到之處。
“形”即具體物,“以味不以形”指的當然不是不要形,而是不以形取勝。但凡審美都離不開形,都是對具體對象的感知。可以説,西方視覺中心主義都是以形取勝的,是在看清楚對象基礎上對形進行思而產生美感的。形被看清到什麼程度,思就達到什麼程度,美感也就生成到什麼程度。以味取勝就不能駐留於物,而是要從中走出,將之咀嚼掉,然後品味物內藴的味道。所以,《文賦》和《文心雕龍》以味喻詩時都用
“遺味”來説事,所謂“儒雅彬彬,信有遺味”( 《文心雕龍·史傳》)。**因此,“以味不以形”的首要之務是不駐守於物,要從中走出。因此,中華美學敍事並沒有像西方那樣將形似看得很重,西方看重形似是為了給思提供確鑿的基點,關乎思什麼的問題。而到了中華美學中,聽到的幾乎都是類似“論畫以形似,見於兒童鄰”(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這樣的話語。**無疑,“以味不以形”框架下,重要的不是物本身,而是味,而且,味是在從物中走出後誕生的。所以,中華美學創造中,物不能看得太清,對象細節不能有太多的刻畫,否則,感官會被留住,難以從中走出。中華審美創造強調的比興就是建立在此之上的。鍾嶸是在指出了“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之後才過渡到了“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鍾嶸《詩品序》)的表述。比興就是要從物中出來,進行發揮、衍生。當然,這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想象,不是人為地將一物勾連到另一物上,而是因物而起、循物而生,是物自身在衍生,不是人在物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太多的細節無異於固化了物,有礙於物向他物的過渡和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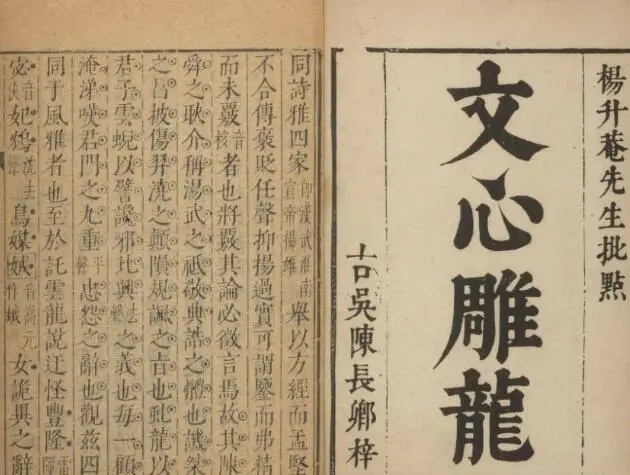
**如此而言,形是否就不重要,乃至無足輕重?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形即感性,沒有了形,審美也就無從發生。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形是否成美或曰基於形產生的快感是否可以稱為美感?**按照西方的追求,形與現實要有匹配度,而萬物皆理,都具有必然性,形與物一致就是要與理(柏拉圖)或必然律(亞里士多德)一致。按照中華審美追求,重要的不在形似與否,而在是否有味。就味覺感知而言,咀嚼產生了味覺,味覺是將物嚼碎後感官馳騁於物之諸要素間產生的。形是否有味就在於是否能令人從中走出。而要做到這一點,形似程度就不能太高,所謂不能太像。一旦太像,就如日常生活一樣,人難以從中走出。畫論説的“筆不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顧陸張吳用筆》),書論説的“計白當黑”(《藝舟雙揖·述書上》)等都是這個道理:形不能與物完全一致。中華美與西方不一樣,從不是基於像,基於模仿,而是基於一定程度的不像,旨在激起從物中走出的“遊萬仞”(陸機《文賦》),進入“畫外之象”。
**那麼,從物中走出,到了“畫外”之後又如何呢?是否像西方那樣由感進入思,由感性進入理性?回答也無疑是否定的。**所謂“畫外”指的只是沒有直接畫出的,目視不見的,而非畫的另一端,或與畫不再相干的那一端,比如思便是感的另一端。“畫外之象”是沒有直接畫出的象,指的還是象,乃更完滿之象。中華審美理想中,“不象”或“不周”之形導致的走出,並非走出形本身,而是由不周之形走向完滿之形。就像味覺體驗中,物由於咀嚼雖然消失,但隨之感受到的是更完滿的物,那就是味。所以,“以味不以形”絕非形不再重要,更不是要拋棄形,而是形必須具備引發味的能力。形是末,味是本。
在西方,審美是感性的,而且必須是進入細節的全部感性,就像視之所見。面對如此固化的感性,意義實現就有待理性,有待思的介入。在中國,審美是感性的,意義實現也還是感性的。“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強調的就是審美不進入思的界面。審美從所感之物走出,並不是從感知界面走出,而是走出感知界面中的固定之物。以味取勝的題旨即在此。從具體物走出,不是落在另一個固定物上,而是不落在任何具體物,不斷地走出,不止地“遊萬仞”,最終走向貫通,走向貫通於所有物的總體。而且,這樣的貫通不是外力作用的結果,而是在感物本身一步一步展開過程中發生的,是由感物行為一步一步所生成。
就一步一步生成,一步一步走向貫通而言,緣起還是在形,恰是特製的形引發了這樣的過程。**為此,中華審美創造發展出了一系列形式創制策略和法則,總體如常言道“似與不似之間”。恰是這種兼而有之,既似又不似,造就了審美感知中既不駐足於具體物又沒有拋離具體物的狀態:不斷從物中走出,進入不盡的流轉本身。**視覺造型中不能太像,不能太有細節,就是為了避免駐足於具體物而無法從中走出,而不能太不像是為了避免滑入虛無,走向抽象;音樂中的調性,節律流轉穿行也是為了達到同樣的效果。這種形式創制的目標只有一個:由具體物出發引發不駐足於任何固定要素的味感。只有貫通才有味感,這是一種對物的總體性感知。
“以味不以形”不僅與西方截然相反,而且也非中華莫屬。它在對物的超越中並沒有越過物,越過感物;在對物的超越中並沒有走向物的另一面,走向思,走向形而上,而是就在感物本身中,拋開了來自物的束縛。假如説,美是感性認識的完善(鮑姆加登),這種完善在西方是位於感性另一端的理性介入的結果,在中國則是在感性內部發生,在感性本身完成的。這是一種不為個體所役,超越個體進入共體的審美文明,一種不為個體所役,而又不走向個體之另一端,不走向否定個體的審美文明。恰是在此意義上,“聖人為腹不為目”(《道德經·第十二章》),這是中華審美文明的一個標杆。
可以説,味是在可見可觸摸對象中感知不可見不可觸摸之物,是物內藴,而非人為介入。現代主義美學表面看也在追尋不可見之物,但那不是可見物內藴的,而是人為介入嫁接建構出的,不是在感物中自然生成的。“以味不以形”作為中華審美文明的標杆絕沒有將中華審美降為日常口舌之好,而是高舉味覺由外入內的品質,正所謂“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國維《人間詞話七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