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子女,開始逃離國際學校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昨天 22:21
南風窗2024年06月14日 13:08:32 來自廣東省10人蔘與2評論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黃澤敏
編輯 | 向由
Kary曾經以為,讓孩子去讀國際學校,就可以逃過“教育的軍備競賽”。
kary和丈夫都是中職畢業。她排斥填鴨式教育,也深知學歷不是人生的全部。於是在2021年,她抱着“快樂學習”的想法,將兒子送進廣東省排名第二的國際學校。
伴隨一大筆資金下注,他們希望並相信,國際教育能提供一個更輕鬆的學習環境,讓孩子自由呼吸、盡情探索,無需擔心那令人喘不過氣的競爭和壓力。
兒子的校園生活確實輕鬆。相較於成績,學校開辦的IB課程體系更注重學生的個性需求和軟性技能培養。每天各種活動,一會兒去插秧,一會兒去動物園探索,下午4點半放學,晚上8點半睡覺。
她知道學生們不是單純地出去“玩”。他們帶着問題探索,活動結束後還會有相應的作業。兒子很有“學霸”範兒,總是做得又快又好。
可是,讓她在意的是,當兒子結束作業開始玩耍,別的孩子轉頭就去上補習班。
“無論是在公立學校還是國際學校,只要想讀名校,沒有一個人可以隨隨便便躺平。”去年夏天,兒子就讀三年級時,kary又帶他逃離了國際學校。
Kary的理念幻滅並非個例。近年來,越來越多家長意識到,國際學校並不是世外桃源。在這場教育馬拉松裏,無論身處何地,都是相似的配方。
“光開心,有啥用?”
若要用一個詞總結女兒就讀國際學校的經歷,夏恬大概會選擇“開心”。一個小時的採訪中,這個詞出現了不下20次。
然而,正是因為“讀得太開心”,夏恬決心把女兒轉到公立學校。
起初,國際學校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她不打算讓女兒擠高考獨木橋,頭頂的升學壓力並不大,學習上似乎不需要太大成就。
結婚後,夏恬隨丈夫去往日本生活。因為丈夫是日本人,加之幼時的文化環境,女兒不擅長中文,她常因此苦惱。恰巧,丈夫工作調動,一家人回到中國。一所雙語國際學校能讓女兒更適應環境,並學習中文。
同時,她無需擔心可能會令“中產返貧”的高昂學費。丈夫的工作單位提供國際學校免學費的福利,一年十幾萬元的學費不在話下,甚至可以一路免費讀完高中。
在主打快樂教育的國際學校裏,“快樂”是許多家長的共識。2020年,夏恬女兒就讀一年級。低年級的課堂設置簡單,下課很早,作業很少。女兒讀得輕鬆快樂,成績卻一塌糊塗。

《交換學校:階級分化》劇照
對於這批成績落後的孩子,老師不會施加太大壓力。本就不擅長中文的女兒,漢字寫得歪七扭八,作業不會寫,老師並不會強行糾正。當成績大幅下滑,她沒有等到老師的聯繫,“老師的狀態就是學生開心就好”。
國際學校特有的鬆弛,投射在夏恬女兒身上,變成純然不上心的學習態度。有時,取得了普遍為“C”的成績評定,女兒依舊笑得一臉燦爛,“沒什麼焦慮,沒什麼想法”。
女兒成績差,老師無動於衷,徒有父母在乾着急。作為經歷過應試教育的中國家長,她發現,自己始終無法忽視內心深處對主科成績的重視。
她期待通過“快樂教育”,培養孩子的個性和技能,亦收穫一個看得過去的主科成績。可女兒似乎什麼都沒學到。
女兒性格活潑,是夏恬眼中“需要盯着”的那類孩子。沒了約束,就像匹脱繮的野馬,自由散漫,“怎麼舒服怎麼來”。她擔心這樣的狀態持續下去,孩子會變得懶惰,沒了向上的動力。
“快樂學習是兩個詞,現在學校只提供快樂,學習部分我沒看到很多。”李昕有相同的看法。
疫情期間,李昕夫婦帶女兒回國。因外籍身份,女兒沒能入讀公立學校,去了北京第一梯隊的國際學校。
“北京公立很難進,反而國際學校、雙語學校,花錢就能進。”國際學校的特性,註定產生了一批順其自然的“佛系”家庭。他們家境富裕,有錢給孩子託底,心思大多不在學習上。

《小捨得》劇照
這無疑加劇了學校生源的差異性。一年級的課程對女兒來説太過簡單,有的學生卻連加減法都沒能掌握。
李昕和丈夫均是清北出身。經歷過題海戰術的這批人,感受過學歷帶來的紅利,深知個人努力的價值。在國際學校,她似乎很難找到同頻的家長。家長們的聚會,她會刻意避開談論孩子們的成績。
“這種氛圍久了,我擔心孩子會不會就自滿了?還有沒有自驅力?”強烈的撕裂感拉扯着她。她可以保證女兒未來的生活“衣食無憂有房有車”,但她不允許女兒甘於此,“在我們家,不努力是不可以的”。
家長們不否認國際學校帶來的眾多好處。如夏恬看到了女兒身上閃耀的個性,開朗自信,富有正義感。可是,面對洶湧的教育洪流,“你光開心,光正義陽光自信,有啥用?”
教師“大換臉”
米朵偏愛國際學校充盈着的“快樂”。可當外教一個個離開,她忍不住思考,國際學校還有什麼優勢?
國際學校曾是米朵心目中的“最優選”。她希望孩子不磨損個性,飛向那片不受應試教育桎梏的藍天。因此,從幼兒園起,兒子便被送進外籍子女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學生在一起學習交流 / 圖源:視覺中國
彼時,那所學校有大量外教,提供跟公立學校不一樣的課程,是她所期盼的鼓勵式教育。在那裏,兒子自信陽光,似乎不需要爬到塔尖,也能閃閃發光。
然而,2020年後,學校開始出現變數。大量外教如潮水般退去,“那兩三年走了十多個”。
原本應有外教負責的英文、體育等課程,只剩下中國面孔。這種震盪,蔓延到學校的管理層,校長也離開了。“上課方式變了,學校理念都變了”,她説。
在國際學校,師資是許多家長眼裏的重要資產。他們認為,一位專業、優秀的外教,能提供更為純正的全英授課環境和多元化的課堂氛圍。“好外教”常被視為提高孩子英語水平的關鍵,直接關係到孩子未來的升學。
根據2022年《國際化教育家庭調研報告》顯示,有15%的家長認為“如果國際化學校沒了外教,不如迴歸體制內”,27%的家長對外教流失表示“很擔心,甚至因為外教問題想換其他國際化學校”。
外教是國際學校吸引米朵的最大亮點。不斷流失的外教,讓她認為國際學校逐漸喪失優勢,“好多課都上不了。”
前幾年,外教招聘市場一度陷入“無序繁榮”。一部分資質不明朗的外教湧入國際學校和培訓機構,“黑外教”成為許多家庭的噩夢。
對此,2020年,教育部制定的《外籍老師聘任和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明確外籍教師需要由教育機構聘任、取得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居留證件,當具備從事教育工作所必需的教育資質和技能證書。
兩年後,教育部工全力推進《外籍教師聘任和管理辦法(試行)》的落地實施。更規範的審核管理之下,資質不全、沒有簽證、存在不良記錄的外教被淘汰。
與此同時,受疫情和政策的雙重影響,外國人來華簽證和許可受到限制,許多外籍教師無法按時回國上課。在部分地區,在華外國人出現了“返鄉”潮。一時間,外教供給端資源稀缺。
夏恬同樣感受到了國際學校頻繁流動的師資。2021年,夏恬女兒升上二年級,學校老師來了個“大換臉”,“語數英的老師全部都走了。”
而快速填補上來的教師教學水平和專業素養參差不齊。當時,班裏來了換了新班主任。在教學過程中,一位學生當眾指出了班主任的錯誤,後者直接甩出一句:關你什麼事,管那麼多。家長們心生不滿。

《小捨得》劇照
北京第一實驗學校校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李希貴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教育首先是關係學,“解決不好師生關係,家校關係就永遠解決不好。”教育關乎老師、家長和孩子三方。
頻繁變動的師資註定會影響固有的人際關係網絡。教師們來了又去,陌生與熟悉反覆出現,好不容易磨合並建立起來的默契和信任,往往在頃刻間化為烏有。
“我們去的學校是(當地)最好最完善的,我們學校老師都走了,別的學校走得更多。”米朵決定離開。
2022年,孩子就讀四年級時轉到公立學校,結束了6年的國際教育。她説,前後選擇離開的家長不在少數,當時班級一共25位學生,“(陸續)走了10人”。
疫情之後,中產家庭重新審視教育的價值。師資是一回事,他們開始考慮,一筆支出能否獲得同等比例的回報。
夏恬女兒班裏的一位學生母親,曾試圖將孩子送到公辦學校的老師那裏補課,卻遭到拒絕。對方一聽到學校名稱,直言底子太差,沒法補。

《小捨得》劇照
“交這麼多錢,還被嫌棄,肯定不行。”就在那一瞬間,她決定轉到公立學校,“不帶猶豫的”。
越來越多家長髮現,“貴”並不代表“好”。kary同樣在乎投出“性價比”。她和丈夫從事抗衰行業,疫情期間收入浮動不大,但也改變了他們的理財理念。
“一開始我們覺得沒關係,兒子出國的錢我都準備好了。疫情以後發現,留學生回來工資也沒多少。”與其將錢投入到不確定的國際教育中,她更傾向於把錢攢在手裏,以更厚實的家底鋪墊對未來的安全感,為兒子提供更多的試錯機會。
教育博弈
曾經,國際學校被視為經濟條件較好家庭的“後花園”。中產子女遠離高考,進入國際學校,按照學校的節奏走,就能輕鬆收穫不錯的洋文憑。kary也一度這麼以為。
待她回過神來,才發現早已捲入無聲的“拼娃”狂潮。擠滿了亞洲面孔的國際學校,從來不缺“卷王”。
在國際學校,完成課程作業是最微不足道的學習“起點”。太多家長爭分奪秒地為孩子“加餐”補習,甚至是短暫的午休時間,也會被高效利用起來。
雙減政策之下,校外大片補習班關停。不過,這難不倒父母。“家長們會動用各種關係,給孩子們在課外有更多學習上的補充。”kary説。
彼時,kary剛生二胎,在郊區上學的兒子只能住宿。她無法像別的家長那樣陪同孩子繼續學習。她擔心孩子會被落下。

kary一家四口 / 圖源:受訪者供圖
儘管國際學校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考試,不以成績劃分學生,沒有明確設立排名,學生們其實不直接存在競爭關係。但這不意味着學生之間沒有優秀和普通的區別。
kary想起,老師曾告訴家長,“如果只是跟着老師的節奏,跟不上就等於差等生,跟得上就等於中等生,跑在老師前面才是優等生。”
天平早已傾斜。優勝劣汰的輪迴中,家長們總希望孩子成為“更優”的那一個。
李昕是這場“較量”中的一道縮影。在國際學校,女兒屬於“尖子生”,英語排名年級前5%,是學校游泳隊一員。校內的EAL(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課程,“每個班只有兩三個孩子晉級”,女兒便是其中一個。
這樣的成績令她滿意。但她認為,國際學校的教學顯然不夠。
為此,李昕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一年級的女兒需要上的輔導班覆蓋英語、奧數、鋼琴和游泳。這是舍取過後的結果。過去,高爾夫、網球、騎馬、滑冰等課程,女兒也都嘗試過。
她毫不吝嗇為女兒的教育進行投資,“學費一年28.8(萬元),補課費一個月七八千(元)。”當然,這筆錢對她而言不算負擔,“佔家庭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如果説我是馬雲這個階級,那我可以説,父母就是孩子的眼界。很明顯大多數中產並不是,更高的世界還得靠孩子自己。”而她能做的,是為孩子爭取更多的資源。
在國際學校讀完K班(幼小銜接)後,如今,女兒就讀一年級。李昕還在等待轉去公辦學校的機會。她奔着頭部公立學校“更好的資源”而去,“二流、三流公立我們就肯定不轉了”。
逃離國際學校後,家長們的目光常投向排名前列的公立學校。例如,kary將兒子轉入了當地排名第一的公立學校。這裏不是填鴨式教育,沒有太多死板的抄寫作業,有負責任的老師,甚至還提供網球、棒球、高爾夫球這類選修課。

kary兒子 / 圖源:受訪者供圖
這是一場更大型的博弈。“如果他小學在國際學校,初中就肯定只能在國際學校,他拼不過公立學生。”kary説。如今,除了校內課程,兒子還額外進行了英語和數學輔導,每年至少3萬元。
選擇國際學校家長們追求的,是能與公立學生相抗衡的實力,以及能夠讓孩子在社會中立於不敗之地的能力。一些時候,公立學校成為“戰勝”國際學校的,更有利的選擇。
無論選擇哪一條路,“十年寒窗苦讀肯定是要的。”夏恬説。
當初就讀國際學校的決定,被她歸咎於想法“不成熟”,導致“浪費一年半時間”。離開國際學校後,她迅速用各種私教補習填滿了女兒的日常。
與同年級學生相比,女兒的成績落下一大截。語文詞彙量不足,數學拓展題不會做,這些都需要額外學習。英語是強項,同樣不能放過,得繼續保持超前學習的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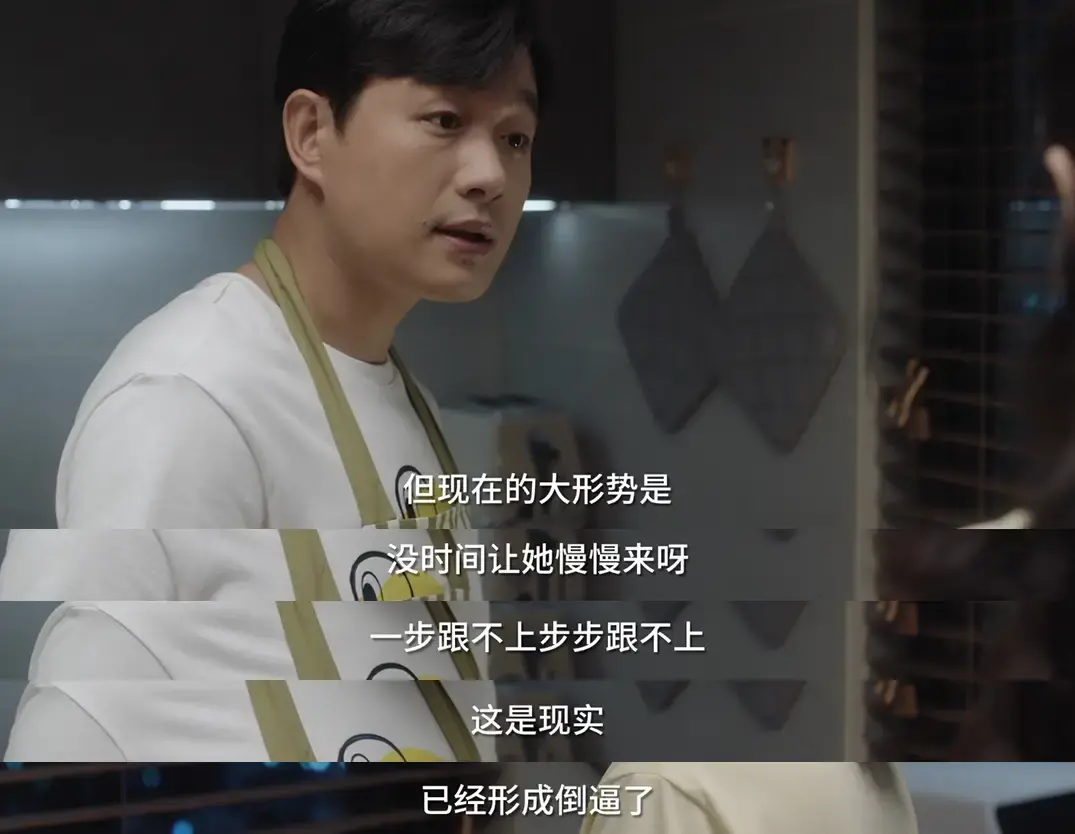
《小捨得》劇照
目前,夏恬女兒轉到公立學校已有三年,正就讀五年級。週一至週五,是雷打不動的一對一私教輔導。一早出門上課,放學後到老師家學習,晚上10點以後回家是常態。
週末,女兒要上的是聲樂課和古箏課,外加兩小時的課程輔導,“把一星期裏沒講完的,或是不會的,再給她拎一拎”。算下來,一年光補課就得大概15萬元。
回到公立學校後,課外輔導通常是家長們的必選。米朵不想雞娃,也不想卷,但“一個班級50人,40多個人都提前學了,怎麼辦?”社會裹挾着她做出選擇。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