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那個“瘋女人”_風聞
毒眸-毒眸官方账号-文娱产业媒体,看透真相,死磕娱乐。1小时前
這兩年,國產劇裏的“瘋女人”越來越多了。《長夜燼明》裏墮落之後的葉冰裳大開殺戒,殺死祖母;《蓮花樓》裏為愛痴狂的角麗譙立志要當天下第一,讓笛飛聲當“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最近兩部熱劇的“瘋女人”更是“瘋”得徹底,《墨雨雲間》裏,脾性古怪的婉寧公主一面縱慾輕狂,一面干涉朝政;《慶餘年2》裏,自視美貌才略無人能敵的李雲睿再次上線,用最温柔的語氣,下最狠絕的命令。

“瘋女人”也不再僅僅是國產劇裏的鑲邊角色,最近熱播的《玫瑰的故事》具體且完整地呈現了一個女人變成“瘋女人”的過程。黃亦玫作為美貌才智上乘、時刻保持體面的都市女性,在戀愛中一點點變得歇斯底里,喝酒發瘋砸爛了男友莊國棟的住所。

《玫瑰的故事》(圖源:微博)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主角還是配角,“瘋”開始成為故事中女性的主要情緒狀態,面對這種人物狀態的激烈變化,觀眾不僅沒有表現出反感與牴觸,反而呈現出格外寬容的接納態度,甚至為“瘋女人”冠上“瘋批美人”的稱號。
這種稱呼變化的背後,其實也是大眾對於“瘋女人”潛在的認知翻覆,而這種社會情緒的變化,反過來進一步影響着創作者對“瘋女人”的敍事挖掘。從早期金庸古龍武俠世界裏,梅超風、石觀音這類純粹的負面反派角色,到如今葉冰裳、李雲睿這類複雜角色,“瘋女人”有了更多的表達空間。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當這類“瘋女人”大量出現時,是否會將女性推向更逼仄的人設陷阱?在回答的這個問題前,更重要的問題呼之欲出,她們的瘋狂到底從而何來?
當女人開始發瘋
世俗意義下,大眾傾向於將“瘋女人”定義為情緒失控的女性,並將其簡單地歸因於女性的脆弱,但在女性主義著作《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書中,對“瘋女人”這類角色有了本質性的思考,即面目猙獰、歇斯底里的女性,她們的“瘋”更多是經受社會性壓迫後,所做出的應激性反應。

《簡愛》中閣樓上的瘋女人伯莎·梅森(圖源:豆瓣)
“瘋女人”的“瘋”並非是一時的情緒外泄,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瘋”更多地來自於她們對規則產生的根本性質疑,並由此進行徹底地反擊。
《長月燼明》裏,受盡嫡庶偏見的葉冰裳大喊“錯的不是我,而是這個世道”;《墨雨雲間》從小就被送去當人質的婉寧公主,受盡折磨之後,心態發生變化,她享受權利帶來的感覺,面對情人沈玉容,她一邊痴愛一邊訓斥,“我就喜歡看你對着我隱忍難言的樣子。”

可以説,“瘋女人”打破了長期以來大眾對女性温順良善的固有認知,正因如此,女性的瘋狂具有一種更特別的震懾性和恐懼感。這種反差帶來了充分的戲劇衝突,同時也反映出值得深思的社會性弊病。
細數過往國產劇的“瘋女人”角色可以發現,古代背景下的“瘋女人”一般佔據多數。《寶蓮燈前傳》的敖寸心,《小魚兒與花無缺》的江玉燕和《美人心計》的聶慎兒,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們並非“天生壞種”,而是在愛情辜負和命運沉淪中,用“瘋狂”進行自我保護。
《楚喬傳》裏的元淳是特徵最鮮明的例子,她在遭遇心上人逃婚、燕北軍侮辱之後,性格大變,原本善良淳樸的價值觀被徹底顛覆,開始變得狠辣果決。在封建體制下的國恨家仇紛爭中,女性往往是最弱勢的羣體,正因如此,女性所經受的戕害更加嚴重,也更加殘酷,於是,成為“瘋女人”是命途多舛的古代女性的必然宿命。

古代背景讓束縛於三從四德的女性處境變得更加容易呈現,但在現代劇中,受限於文明社會的時代背景,“瘋”的呈現幻化成了另一種樣子,以一種更隱秘的方式存在於家庭之中。
《都挺好》裏的蘇明玉拋下重男輕女的家庭,被父母兄弟斥責心狠手辣;《煙火人家》裏的李衣錦掙脱母親的管控,堅定地要跟男友複合,被母親斥責“瘋子”。她們沒有做出格的事情,只是因為背離了家庭的傳統規訓,便被貼上了“瘋”的標籤。

《都挺好》蘇明玉(姚晨 飾)和《煙火人家》李衣錦(馬思純 飾)(圖源:豆瓣)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歡樂頌》裏樊勝美的媽、《安家》裏房似錦的媽,這類窒息的母親,成為了輿論場中爭相討論的“瘋女人”。處於家庭關係中的女性,無論身份如何,都困於時代標準,並因此被冠上“瘋女人”的名號,而她們不過是陳舊的傳統要求與新興女性觀念的夾縫中一羣迷茫的女人。

可以見得,無論什麼時期的女性,其“瘋狂”的背後都是主體性的消失:她們失去了對自己人生的掌控,在“被馴服”與“被絞死”之外,選擇了瘋狂。
為什麼只看得到“瘋女人”
通常而言,“瘋”的起因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天性之下的反叛,一種是壓迫之後的反抗,前者是先天性的病理症狀,後者是後天的社會性壓迫所塑造。不過,在壓迫面前,應當只有階級的區別,而並沒有性別的區隔。
可是,我們一向樂於討論“瘋女人”,卻很少存在“瘋男人”的説法。
《寧安如夢》裏的謝危,《長月燼明》裏的澹台燼,《長相思》的瑲玹,都因為自己的身世飽受折磨,變得殺伐決斷冷漠無情,是世俗定義下的“瘋子”。但是,因為世俗對男性剛硬頑強的要求,他們的“瘋狂”被包裝和美化成為一種英雄主義,他們的瘋狂行徑是野心與能力的體現,進而被美化成霸道總裁的蘇感。
“苦果亦是果”“我想和你長相守有錯嗎?”這類台詞背後的瘋狂,被“瑪麗蘇”包裹成了愛意,也讓男性的瘋狂變得難以察覺。

更進一步地説,男性其實比女性更容易脱離“瘋”的標籤。傳統社會對性別有着不同的完美要求,男性與財權名利綁定,而女性則與貞潔綁定。失權的男性墮落之後,只需要重新開始,證明自己的能力被輕視,便能在父權體制下,一步步重新回到正軌,其本身並沒有脱離這套價值體系。
而女性失節之後的崩潰重建要更為困難,因為失節的女性已經社會性死亡,再難回到社會評價體系中。她們被拋棄在傳統價值體系之外,於是,只能通過“瘋狂”重建一套新的價值體系,與自己和解。在這一過程中,傳統價值體系中處於次要地位的女性,獲得了本位特權,這種地位變化,讓女性復仇往往更具社會意義與現實張力。
從本質而言,“瘋女人”的“發瘋”,更多是在復仇中捍衞自己的主體性地位,並通過“瘋狂”完成一種自我秩序的重建。《長月燼明》裏葉冰裳的真心與良善被踐踏,後來才明白“在這世上,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值得我去愛。”;《千古玦塵》裏的蕪浣自小身份低微,看清女性依附的無用與徒勞,便早早明白,“男人是靠不住的,我們只能靠自己。”

再比如,韓劇《黑暗榮耀》作為典型的女性復仇爽劇,能夠得到東亞範圍的廣泛關注,不僅在於它所營造的爽感,更多是拆解了文東恩、樸妍珍“瘋狂”的緣由,見證了她們在復仇之中完成的第二次社會性成長。文東恩學會讓破碎的自己重新建立親密關係,樸妍珍也為自己的驕縱付出了代價。

《黑暗榮耀》劇照(圖源:豆瓣)
可以見得,“瘋女人”的“瘋”並不一定要情緒極度外放的聲嘶力竭,表現出面目猙獰的樣子,這種“瘋”更多是一種內在性顛覆,對父權體制的挑釁,開闢出獨屬於女性的世界,制訂出新的生存規則。
這種角色內核的先鋒性,與如今輿論場所期盼的、獨立自主的女性精神有本質性的契合,也正因如此,“瘋女人”的定義正在隨着時代發展,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瘋女人”的變化
在國產劇中,“瘋女人”早就存在。
《大宅門》裏的楊九紅,得到白景琦偏愛,從青樓頭牌成為白家二姨太,卻因為窯姐身份處處被宅子排擠,最終發瘋;《情深深雨濛濛》裏的可雲在陸爾豪離開,生下的孩子病死,雙重打擊下,變得瘋顛。除此之外,宮牆之內還有更多的“瘋女人”,皇權與父權的雙重碾軋下,她們不得不用極致的雌競手段獲得生存空間。

可以説,早期影視劇中的“瘋女人”大多都是封建體制下的犧牲品,面對不公只能束手無策,完全以一種“怨婦”的弱者身份存在。
這種沒有反擊能力的瘋狂,雖然真實地呈現了當時時代背景下女性的處境,但是隨着社會思潮的變化,觀眾如今更希望看到具有主動性的反抗女性。《小魚兒與花無缺》的反派江玉燕的翻紅,就暗合了這種期待。
作為掙脱了標準束縛的“瘋女人”,江玉燕在面對自己的慾望時,有着更直接的表達,她為了花無缺不管不顧地索取,孤注一擲地搶奪,“我就是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為了我的野心,我能付出多少。”在這類角色中,觀眾能夠清楚地看到女性角色中鮮明豐富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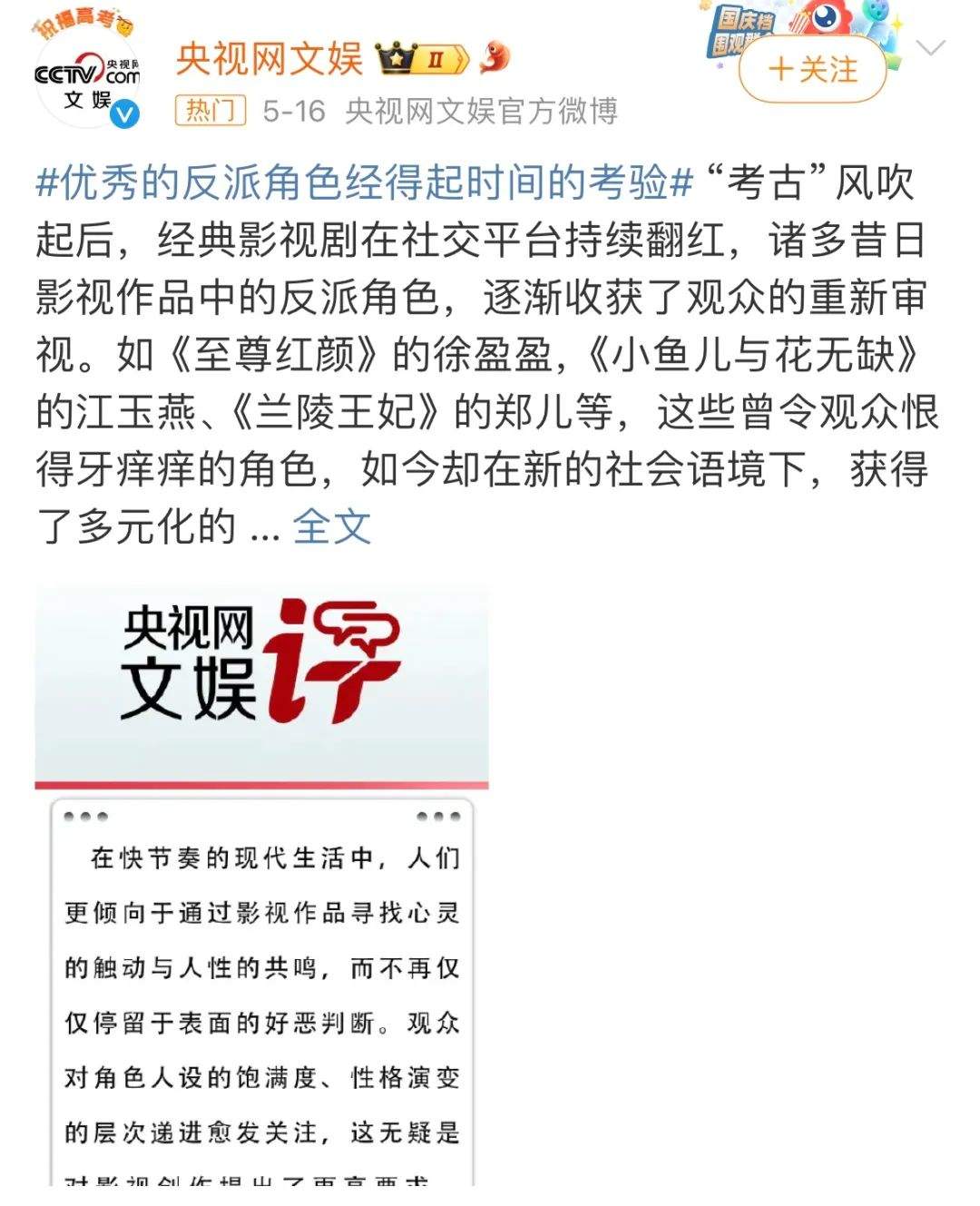
這種社會思潮的變化,進而影響到創作者對女性角色的塑造,創作者開始在“瘋女人”的瘋狂之中,加入女性對於自身的價值索求,和對人性慾望的正視。例如,《蓮花樓》裏的角麗譙,她對武功高強的笛飛聲的愛慕之中有着強烈的權利崇拜,她本想推舉笛飛聲成為天下第一,但因為笛飛聲的退卻,角麗譙決定讓自己走上武林寶座。
 從一開始被動性承受到主動性釋放,“瘋女人”的主體性在國產劇中開始有了更明顯的呈現。
從一開始被動性承受到主動性釋放,“瘋女人”的主體性在國產劇中開始有了更明顯的呈現。
尤其,在新時期的“瘋女人”的世界觀中,情愛不再佔據主要地位,更多是聊以慰藉的次要需求。因為傳統情感關係仍然存在於舊有社會價值體系,一套女性佔據主體性的情感模式仍未建立,於是,為了保證主體性的穩定,“拔情絕愛”便成為“瘋女人”對待感情的通常手段。
可以看出,對於“瘋女人”的價值挖掘和身份建立,某種程度上,也在不斷豐富完整着女性角色,而對於瘋狂賦予更多的敍事維度,實則也在衝破世俗定義下“瘋女人”的負面標籤,以及對於女性慣常的既定身份認知。不過,女性的瘋狂並不能完全等同於女性的野心,畢竟,在父權體制處境下,女性仍舊處於壓迫中,這種社會性困境仍需要更廣闊的敍事空間進行講述。如果一味沉浸在“瘋狂”帶來的戲劇衝突中,那“瘋女人”很快會淪為又一個可供消費的流行標籤人設。
消費也意味着消耗,流行也預示着流逝。突然開始成為熱門人設標籤的“瘋女人”們,固然引起了大眾對於女性處境的討論,和與女性慾望的理解,但其內核及其與社會的關聯性,仍然有進一步挖掘的空間。否則,再強勢凌厲的“瘋女人”,也不過是紙老虎,內裏如果無法重建,便會與過去所流行過的女性角色人設一樣,成為很快被迭代掉的“營銷密碼”、娛樂消費類型角色罷了。
而國產劇裏的女性角色們,也將再失去一次有意義的討論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