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山都的發家史:種子帝國如何影響全球食物體系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昨天 22:22
澎湃新聞
2024年06月18日 12:55:58 來自上海
《種子帝國》(Seed Money: Monsanto’s Past and Our Food Future)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環境歷史學教授巴託·J.埃爾莫爾(Bart J. Elmore)的第二本書,2021年於美國出版。“種子帝國”指的正是如今已被拜耳(Bayer)收購的孟山都公司(Monsanto)。這本詳細回顧了孟山都發家史的書獲得了美國新聞學、環境歷史學以及商業歷史學三個專業領域的五個年度獎項。《種子帝國》實至名歸。以紮實的學術研究為依託,作者埃爾莫爾既從宏觀視角揭示了孟山都對於全球食物體系的影響,又總能在浩如煙海的經驗材料中體會到人物的細膩情感,拆解出不同事件的脈絡和彼此之間的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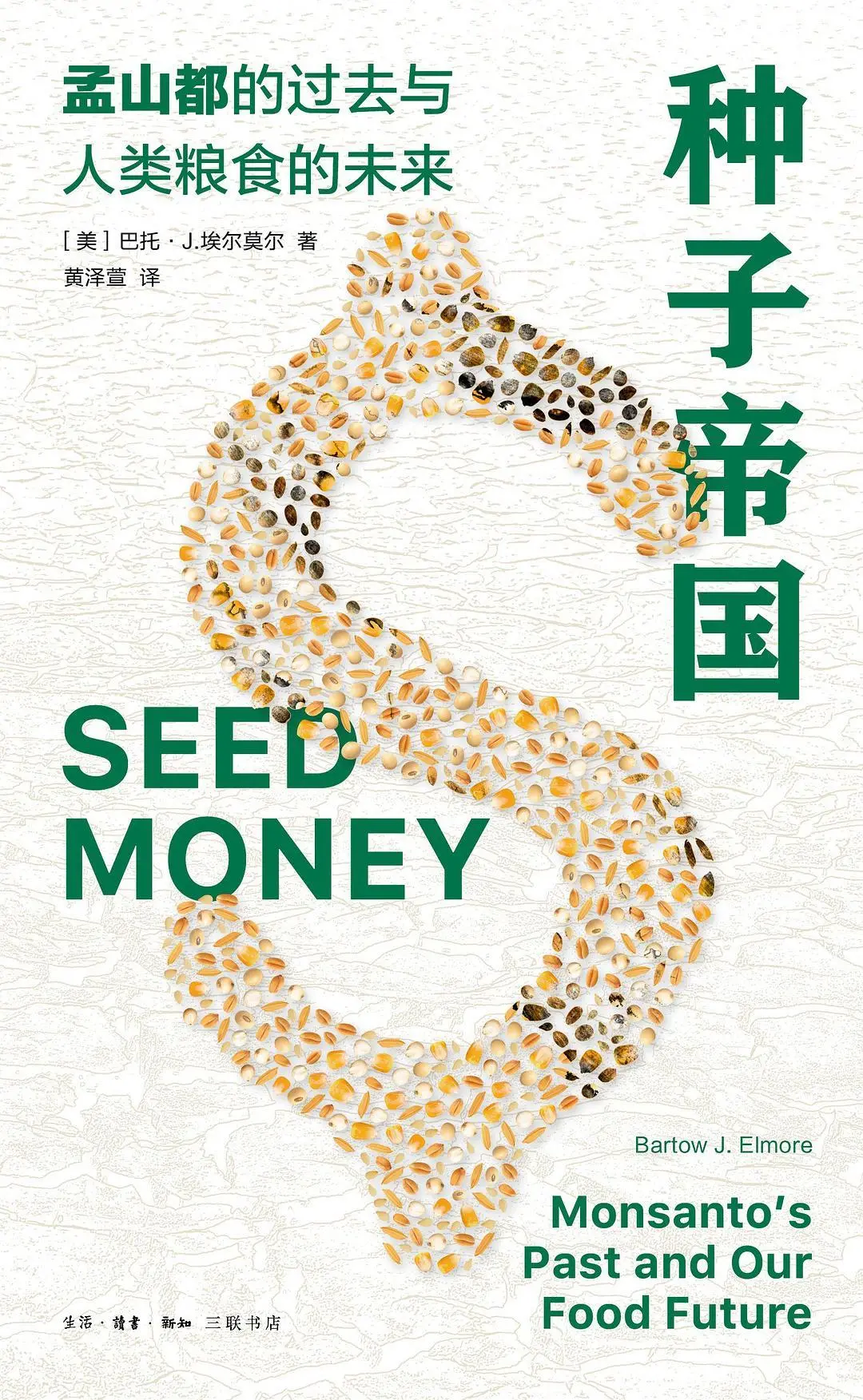
《種子帝國》
該書中譯本題目中的“帝國”二字極為傳神,揭示出孟山都公司發展壯大的過程正是它以化工企業之底色進軍食品加工業、日用品行業、農業生產領域乃至環保行業之後,對這四個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卻通過化工和基因技術相互關聯起來的領域形成實質控制的過程。尤其在食品加工業和農業生產領域,“帝國”的控制威力同時作用於生產端和消費端。在生產端,小生產者的獨立性被無情剔除,他們被塑造為依賴於孟山都的生產過程的一環。在消費端,人們面對的食品雖然品牌眾多、琳琅滿目,但恐怕很多食物的背後都蓋有孟山都參與制造的印章。
然而,這個帝國是人類的福音麼?書中寫道:“由於孟山製造的有毒物質的遺留問題,這家公司一直在美國最令人討厭的公司名單上,一些人把它稱為孟撒旦(Monsatan)。”孟山都生產的化工產品給美國乃至全人類帶來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嚴重污染和破壞,難以預防或治療的惡性疾病,以及因污染、疾病和對孟山都模式的依賴而傾家蕩產的生計模式。
弔詭的是,深受其害的美國人民一直在狀告孟山都,科學家們也一直在揭發孟山都的問題,孟山都卻一直沒有倒台。這些來自民眾、社會的抵抗對孟山都來説,反而成為其砥礪成長的“挫折”。這一邏輯從該書的目錄中就可見一斑。該書分為五個部分,每個部分的標題對應着孟山都不同的發展階段。第四部分的“雜草”比喻那些阻礙孟山都發展的不和諧聲音。比如,上訴討要公道的美國人民,各國環保和農業部門對孟山都產品的質疑等等。然而,第五部分的“豐收”卻暗示了孟山都雖歷經狂風暴雨卻安然無恙的“大團圓”結局。
不過,孟山都的大團圓結局並不意味着人類的糧食生產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種子”“根莖”“植物”“雜草”“豐收”串起了孟山都的發展史,在這一明線之下,我們總能讀出另外兩條交織在一起的線索。首先,孟山都公司的發展歷程正是美國食品加工業和農業發展的縮影,它在國內和國際上的推廣過程正製造了一種關於食品和農業的意識形態。孟山都歷屆總裁的個人特點也表徵了這一意識形態。第二,為應對美國人民的反對之聲,孟山都公司逐步設立了自己成熟的律師團隊、科研團隊、醫療機構、公共關係也即政治遊説團隊、種子糾察團隊和舉報擅自留種的電話熱線。本書清晰地剖析了這些公司部門是如何在本質上也屬於美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的。這些公司部門連同美國的政府部門一道,在鞏固了孟山都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同時,也鞏固了由進步主義、自由買賣、自由選擇權、遵守司法和追求利潤等“部件”組成為一體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美國人民的抗爭雖取得了部分成功,卻總是在美國的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框定的範圍中兜兜轉轉。
根據《種子帝國》的梳理,孟山都的發展歷程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自十九世紀末開始,依靠煤炭、石油等原材料,孟山都以糖精、咖啡因等食品添加劑起步,逐步在日用化學品領域獲得擴張。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切斷了歐洲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運輸,為孟山都從歐洲獲取化工原材料和化工技術製造了障礙,卻也因此“迫使”孟山都的第一代創業者轉而開發美國本土原材料,鍛鍊了自己的化工技術,成功在二戰後完成了相對於歐洲石油化工業的“彎道超車”。二十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是孟山都籌謀轉型的過渡期,日用化學品產業依靠的煤炭、石油是有限的,但孟山都的逐利擴張是不能停的。1970年,除草劑草甘膦誕生,標誌着孟山都進軍農業生產領域。事實上,草甘膦的前身橙劑早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越南戰爭中投入使用,作為武器給越南人民帶去了嚴重的生態災難。但改頭換面了的草甘膦,卻成為美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向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推廣“綠色革命”的主打產品之一。1984年,切斯特菲爾德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的建立標誌着孟山都公司的發展進入到了第二個階段。生物技術和化學工業之間的配合是其第二階段發展的主要動力。孟山都和美國共成長。當孟山都成長為巨型跨國公司的時候,美國也成長為新一代全球霸主。
在《論再生產》中,阿爾都塞揭示了意識形態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在過程上的同一性。在同一過程中,意識形態的生產與再生產紮根於物質性的和實踐性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沒有不借助於意識形態並在意識形態中存在的實踐”,也沒有不紮根於物質實踐,並在物質實踐的過程中生產出來的意識形態。在《種子帝國》這本書裏,我們能讀出意識形態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在過程上生動的同一性來,也能看到意識形態是如何藉助物質實踐而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狀告孟山都的故事總是重複着自己的“原型”結構,下一個官司和前一個官司之間總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相似處不僅包括受害者們的苦痛,還包括了司法流程曠日持久、律師團之間的鬥智鬥勇、孟山都鍥而不捨的政府公關,等等。在一些官司的最後一刻通常會有一個超越了司法範疇的美國政府出場,與孟山都簽訂協議,挽救孟山都於危難。政府為什麼要出場呢?美國不是一個自由、民主、進步的法治國家麼?政府不是不應該干預司法和市場的麼?
上世紀七十年代,孟山都奈特羅工廠的工人及其家屬委託律師考威爾控告奈特羅工廠的生產過程會泄漏有害物質二噁英而危害工人健康。1984年,當孟山都公司的代表律師洛夫在法庭上回應考威爾的時候,他直白地説:
這是一家公司。它的存在就是為了賺錢。所有的企業都是如此。這就是我們的制度,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洛夫的大實話揭示了美國政府支持孟山都的原因:孟山都發展對美國的發展和擴張有利;孟山都如果因某些問題而倒台,會威脅美國政府的利益。這一點在孟山都經歷過的很多難關中都得到了印證。
孟山都的創始人約翰·奎尼就曾有驚無險地渡過了一個難關。支持過《純淨食品與藥品法》的奎尼原本希望該項法案能為孟山都的產品帶來政府許可的廣告效果,增加公眾對其產品的信任。然而,他等來的卻是美國農業部化學局局長哈維·威利依據《純淨食品與藥品法》對可口可樂汽水中的食品添加劑的質疑。孟山都每年為可口可樂提供大量的糖精和咖啡因,這兩項大額訂單支撐着孟山都的發展。面對農業部的猛烈訴訟,法庭上的奎尼如坐針氈。但事情的走向證明奎尼的緊張完全是杞人憂天。
可口可樂和奎尼都不需要證明添加到軟飲料中的咖啡因是無害的,因為首席法官愛德華·桑福德從未允許陪審團討論這個問題。……可口可樂的法律團隊在法官席前主張案件應該被駁回,因為原告從未證明咖啡因是被人為“添加”到可口可樂裏面的。法官桑福德同意這一觀點,最終指示陪審團做出了有利於可口可樂的裁決。在那些指示中,桑福德間接提到了奎尼的證詞。他説:“一種天然食品不能被認定為摻假,比如咖啡。雖然一杯咖啡平均的咖啡因含量遠高於一杯普通的可口可樂……但裏面的咖啡因……是天然和正常進入其配料的基本成分之一。”
桑福德法官、可口可樂的律師團以及孟山都的創始人奎尼一起向我們展示了一場教科書級別的意義接合與拆分遊戲。在被告證明添加到可口可樂裏面的咖啡因是無害的之前,需要先由原告證明咖啡因是被人為“添加”到可口可樂裏面的。而原告沒能證明咖啡因是否被“人為添加”,同時,“人為添加”由被告的證人,也即配料提供商奎尼先生解釋為“天然和正常進入其配料”。於是,添加添加劑的主體被抹去,添加劑自己“天然和正常”地進入了配料後,可口可樂和孟山都皆大歡喜、順利過關。這一案件的裁奪真是特別符合法律程序和法律專業的標準。
這樣的文字遊戲當然一戳就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休斯看透了這個判決的荒謬之處,推翻了初審法官桑福德的裁決,重申了“《純淨食品與藥品法》的全部意義在於‘保護公眾免受有害成分帶來的潛在危險’”這一宗旨。雖然“休斯法官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要求陪審團最終應該討論咖啡因是否真的對人體健康有害。”但是還沒等陪審團討論咖啡因對人體的影響,可口可樂就和政府私下達成了利益交換協議,農業部撤訴,可口可樂減少飲料中的咖啡因含量。
贏得政府的支持是個有效方式,奎尼也開始採用這一方式。面對農業部對糖精的禁令,奎尼和羅斯福總統取得了聯繫,總統慷慨覆信支持了孟山都的糖精,孟山都的律師馬上將這封信公之於眾,用以證明糖精對健康無害,同時將矛頭對準美國政府對食糖的保護性政策。孟山都從三個層面做自我辯護。首先,它指責美國政府保護了糖農,從食糖銷售中獲取高額税收,卻對糖精頒佈限制令,剝奪了個人消費者的選擇權。孟山都用化學工業製造的糖精為消費者帶來了選擇的自由,不應被禁止。第二,根據市場自由競爭的原則,美國政府不應助推食糖行業獲得壟斷地位。第三,糖精對消費者的健康居然有好處:
“這個國家的人民正遭受着食物價值過剩的痛苦,而不是食物價值匱乏的痛苦。”換句話説,糖精對於因補貼和關税而變得暴飲暴食的食品體系來説是一種化學糾正劑。美國人已經吃得很飽了,而化學物質可以幫助他們保持苗條。這是進步時代孟山都給這個世界的信息。
1925年美國農業部終於取消了對糖精的禁令,孟山都的糖精獲得了持續生產。糖精對健康到底有怎樣的負面影響被轉化為“有助於讓人擺脱對糖的依賴”,而自由選擇、自由貿易等進步觀念更是站到了台前為孟山都贏得意識形態戰場上的勝利。
“任何意識形態性的觀念除非它能貫穿到政治和社會力量的領域,貫穿到不同勢力之間利害攸關的鬥爭之中,都不可能產生實質性的效應。”奎尼有關添加劑的證詞之所以能在法庭上發揮作用,並非因為它迷惑性很強。孟山都圍繞糖精建構的支持糖精就是支持健康、自由貿易和自由選擇權這一套話語也並非真理。但它們卻都樹立起來了,發揮了效用。因為它們不僅僅是紙面上的話語表述,而是與特定的社會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孟山都的故事裏,特定的社會力量是走到一起尋求共同利益的可口可樂公司、美國政府,和孟山都公司,他們在雖曠日持久但回報豐厚的司法和政府公關的實踐過程中打造了自由貿易、自由選擇、進步健康的生活的意識形態。即便其中一些個別的——諸如美國農業部這樣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偶然地未能忠於職守地貫徹資本主義謀取暴利的最終目標,整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會予以糾正,讓事情遵循“(企業)它的存在就是為了賺錢……這就是我們的制度,這就是我們的國家。”中所透露出的原則來發展。
翻開《種子帝國》,我們就會發現,頻繁出入法庭對孟山都來説是家常便飯,類似原型結構的故事也還有很多。1970年代,美國分別於1970年和1976年通過並頒佈了《國家環境政策法》《資源保護與恢復法》和《有毒物質控制法》。1980年,紐約州北部一個建於有毒廢棄物傾倒場旁邊的住宅社區發起了草根社會運動,推動美國國會通過了《綜合環境響應、賠償和責任法》(又稱《超級基金法》)。根據這些法律,美國環保署有權追究企業污染者的責任,督促有關公司清理有毒廢棄物。看上去,法律在美國人民的抗爭和推動下日趨完善,然而,現實卻演變為兩個相互關聯的結果。首先,根據法律,既然某塊土地已經被孟山都污染了,那麼在這塊受污染土地上居住、耕作的居民就不可繼續使用這塊土地了,即便這塊土地本就屬於他們。同時,環保署不但沒有勒令孟山都將污染產業停產,反而把清理土地的任務交給孟山都去做。這恰恰是遵守《超級基金法》的做法:由污染企業負責處理污染。於是,既然土地已被污染,土地的主人不可繼續使用土地,必須清理土地,那麼孟山都就可以打着處理污染土地的旗號,低價購入已被污染的土地,繼續做生產污染品的事了。
美國人民的抵抗起到了效果,新法頒佈並被執行,政府部門履行了職責,企業為自己的污染行為付出了代價。但是,社會、政治、法律形成的完美閉環卻為孟山都的持續生產打開了方便大門。孟山都的損失是多花了一筆購買土地的錢,但比起停產整改的損失來説,這點損失不算什麼。受污染毒害的社區居民似乎也解決了問題,通過賣地搬遷到了別處去。然而,污染卻在持續,污染埋下的惡果,終有一天會以更大的量級爆發,影響的範圍也將越來越大。
佈滿全美國的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配合得天衣無縫,促成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繼續。同時,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獲得了再生產,通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進行思考、實踐的主體也一併生成。
1990年代,美國環保署發現美國的蘇打泉鎮處於致病性極高的放射性礦渣的污染中,這些放射性礦渣來源於孟山都工廠的廢料。蘇打泉的居民們頓時不安起來,希望污染問題得到妥善處理。然而,他們的“自由選擇”並不多。居民們可以“減少在地下室的時間……將主要生活區從地下室搬到上層”,但是這個選項治標不治本,受核污染的危險也依然存在。居民們也可以選擇“改建、屏蔽或部分清除”爐渣,孟山都則只負責測試和諮詢的費用,其餘費用需要居民支付,這對於居民們來説不僅是一個經濟負擔,而且治理過程會對仍生活在當地的居民帶來生活上的干擾,事情傳出去之後還會連累當地的房價下跌,進一步損害居民們的經濟利益。居民也可以繼續抗爭,要求孟山都停產,但是居民們並未提出這個訴求,因為孟山都為擁有3000人的蘇打泉鎮提供了大約400個工作崗位。如果孟山都停工,那麼意味着400個居民們就會失業。蘇打泉的部分居民們甚至還提出了站到孟山都一邊,反對環保署的選項,這些居民是包括漢森市長在內的依賴孟山都產業鏈的小企業主。最終,既不想承擔治理成本,也不希望自己的私人財產利益受損的居民們選擇了對自己損害似乎是最小的選項:賣地、拿錢、搬離。環保署盡忠職守地把治理的包袱扔給了孟山都,孟山都以最小的代價迎合了各方利益。
蘇打泉的居民們在“自由選擇”、“民主協商”、“維護私有財產”的意識形態裏完成了這一意識形態主體的再生產,沒有人也沒有機構為公共利益負責,沒有人也沒有機構超越私有財產的範疇去打破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的再生產。
按照類似的劇本,當孟山都向美國農民推銷、兜售除草劑及其配套的轉基因種子的時候,美國鄉土熟人社會中的農業中間商雖然一邊知道自己有負於農民兄弟姐妹們的信任,一邊還是停不下來地為他們推銷孟山都的產品,使美國農民不斷加深對孟山都產品的依賴,因為中間商們可以獲得的佣金實在太誘人了。於是,農民越來越依賴孟山都的除草劑和轉基因種子,越來越沒有其他選擇的時候,孟山都的廣告詞“農民應該享有(控制雜草的)選擇權”就越體現出其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加入孟山都銷售團隊和種子糾察隊的年輕一代可能不會再揹負老一輩中間商那樣的道德包袱了,當他們在孟山都給他們提供的工作崗位上工作的時候,正是他們鞏固“農民須依照和孟山都簽訂的知識產權協議,每年付錢購買孟山都種子,自己留種就是違法”這一觀念的時候,也是他們過上高收入、高消費生活方式的時候。依賴於孟山都產業鏈的漢森市長打心眼裏不想在蘇打泉的污染問題上站到孟山都的對立面上,他愛人於2006年死於因輻射引起的癌症,他自己也患上了癌症。產業是不能丟的,命是可以不要的。弔詭的是,漢森曾認為,反對環保署的進一步干預是“為生存而奮鬥”。在漢森的“為生存而奮鬥”這一語境中再次獲得生命的主體,是被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塑造的、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召喚的主體,即便那個承載主體的肉身已經身患絕症、命不久矣,資本主義的主體卻生生不息。在美國政府以美國納税人的錢,為孟山都製造的橙劑為越南的環境災害埋單的同時,孟山都又用橙劑的升級版產品以“打造孟山都全球合作伙伴”的意識形態打造了夢想以小成本控制雜草獲得農業豐收的越南農民主體。
《種子帝國》以通俗的筆觸揭開這些人物、事件、歷史過程中的層層面紗,為我們呈現了孟山都帝國形成過程中的意識形態運作邏輯。美國人民在美國的法律範疇內對孟山都的鬥爭仍是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範疇內做鬥爭,對美國的國家機器沒有絲毫的損傷,對主體的改造也沒有本質上的影響。這才是種子帝國所埋下的種子的本質,也正是《種子帝國》所揭露的問題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