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虹 鄧建國 | 技術寄生物:數字生存的技術悖逆——兼與陳積銀、孫月琴商榷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昨天 22:18
王曉虹 |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助理研究員
鄧建國(通訊作者)|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5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數字空間取代了地理空間與自然資源,成為數字殖民、數字控制與數字攫取的新對象。**隨着數字技術的突飛猛進,學界對數字技術的關注逐步轉向數字奴役、數字殖民等數字批判領域,越發聚焦於數字技術與人類生存的關係。**2023年11月,陳積銀教授、孫月琴博士在《探索與爭鳴》上發表了《數據資本化與資本數據化:數據資本主義的批判與應對》一文(以下簡稱“陳文”),探究了在數字技術驅動下的數字生產問題。陳文指出,數字技術帶來現實與虛擬的深度交融,虛擬現實的大規模應用構成資本獲取人類數據的新平台,數字技術在對用户的使用進行反饋的過程中不斷形成“數據池”,通過數據餵養實現對人類的數據監控。陳文為我們理解人類的數字化生存及數字技術對人類行為、生產方式的影響提供了理論參考。但筆者認為,若要對人類的數字化生存展開進一步討論,就不能僅侷限於數字技術對人類生產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影響層面。數字技術已滲入整個社會系統並重構了各級場域,數字生存已超越了“數字生產”和“數字消費”維度,業已全面滲入人類所有的實踐維度。據此,筆者引入“數字超級主體”“隱藏人格”“技術寄生物”等理論資源,嘗試描繪一種統攝各級場域的不可逆的、排他的數字權力,這種數字權力為數字奴役提供了可能。
超級主體、技術悖逆與虛擬集權社會
**技術發展不斷脱離人類的發明意圖,以“自我維持”為演進目標,孵育生成“數字超級主體”。**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媒介技術從人類行為中捕獲規律,並將這種規律用於對人類的反制。法國社會人類學家費爾南·德利尼(Fernand Deligny)的實驗表明,在沒有任何外力或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人類行為模式表現出高度規律性。人類行為的規律性為計算測量提供了依據,也為技術悖逆創造了條件。人工智能一經創造,便具有了相對獨立性,它聽命於算法,具備糾正人類決策的強大分析能力。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學習、自主改進、自我修復,甚至產生自主意識,而這種自我進化能力顯著區別於以往一切技術屬性,這意味着此類技術具備了“人格化”特徵。在與“人格化”技術的交互過程中,人類不斷淪為被控制的對象。人類越來越習慣沉浸於由數字技術構建的虛擬環境,不斷交付個體隱私,享受媒介技術帶來的便利生活和奇幻景象。現實經驗逐漸被數字經驗取代,技術與人類之關係逐漸發生“它異”。
**“它異關係”(alterity relations)是唐·伊德在論述人與技術關係時提出的一個十分重要但被學界忽略的概念。**該概念指技術在發展過程中會發生異化,技術具有“準他者性”,具備一定程度的“人性化”,也稱為“人格化”。伊德解釋道,“技術上的‘他者性’是一種‘準他者性’,比單純的物體客體性強,但比動物王國或人類王國中的‘他者性’弱”。伊德構建了“他者”的層次,首先是人類,其次是動物,然後是技術,最後是物體或事物。當技術具有了類似人的人格特質,對人的行為進行回應和控制,並具有一定“自主性”時,這類技術就具備了“準他者性”。

唐·伊德(Don ihde)
**虛擬數字技術的“準他者性”極其激進,徹底顛覆了傳統技術的“非人屬性”。**比如,數字技術打造的虛擬偶像不單獲得了外形上的“人格化”特徵,而且被賦予特定性格和姿態,吸引青少年粉絲瘋狂追捧,甚至為了符合虛擬人物之人設,作為真實肉身的“中之人”還要接受專門的表演訓練。數字偶像通過社交平台分享穿搭和生活獲取品牌合作,藉由強大號召力主導年輕羣體的消費意向。原本作為客體的數字技術變成了另一個“主體”,它不僅成為伊德所説的“與人平等對視的對象”,甚至具備了超越絕大多數人類的超級影響力,成為“俯視、控制人類”的“數字主體”。
**無數個數字主體背後潛伏着強大的“數字超級主體”。**虛擬偶像只是數字技術孵育的一個數字主體,未來數字技術將孵育出越來越多的數字主體,數字主體具有人格化特徵和持續進化能力,將對人類產生深刻影響。人類在不知不覺中投入大量時間、金錢和精力換取與數字主體的持續互動,以標榜一種時髦的、標新立異的生活方式,卻渾然不顧其中隱藏的巨大危機。如果説,伊德描述的技術與人之關係是一個以“轉換”(alter)為標榜的“它異”過程,那麼,數字生存中技術與人之關係則是一個以“反制”為標榜的“悖逆”過程。
數字超級主體擁有強大的數字權力,對人類社會展開全面接管和干預。“數字權力”通過拒絕/允許進入數字場所,實實在在構成人類實踐的前提條件。信息平台將“身份驗證”前置,將之作為“入場資格”,微信登錄、支付寶登錄、抖音登錄等覆蓋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當強權服務規則形成羣體效應時,一種基於技術的利益共謀在數字平台之間悄然形成。如果你拒絕“被畫像”“被監視”,那麼,你將失去通勤、支付、點餐、理財、娛樂、獲取資訊等幾乎所有的“數字便利”,一旦拒絕“數字便利”,就必然遭遇“數字死亡”。萬能數字平台通過種種設置,強行逼迫用户接受其條約,用户若拒絕便會因無法接入社會系統平台而導致“數字死亡”。技術悖逆以一種看似提供選擇權的禮貌方式剝奪了人類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權利。更可怕的是,數字權力取消了回到原本生活方式之可能,我們只需回想一下街頭揚招出租車的痛苦場景,即可明白數字權力是如何通過製造“數字死亡”改變了人類生活。
**“客體主體化”和“主體客體化”經充分轉化後,虛擬集權社會便誕生了。光譜的一端是人類控制的傳統社會,另一端是數字技術控制的人類社會,在這兩端之間存在各種類型的半自治。隨着用户捲入技術程度的不斷加深,最終每個人都將進入光譜的終端——一個虛擬的集權社會。技術發展以脱離人類控制為階段目標,以控制人類為終極目標,最終孵育的虛擬集權社會深深烙印了“悖逆”屬性。這種“悖逆”屬性普遍存在於各領域:工業自動化的最終目標就是創造出能夠獨自應對現實世界並不斷適應環境變化、能夠自我思考和自我決定的機器。媒介技術的最終目標是創造出能夠統攝人類生活,不斷汲取人類之精力、金錢與時間的奇幻世界。無論是工業技術還是媒介技術,技術的“悖逆”屬性不僅是指伊德所説的“人的注意力從自身投射到了技術身上”,而且指技術不斷將我們推離現實世界,由虛擬經驗取代現實體驗,人類從使用技術的主體淪為被技術反制的客體。“它異關係”是伊德提出的四個“人與技術”關係中唯一具有“離身傾向”的關係,因為無法被歸入“廣義具身關係”,難以迎合當下熱門的“具身研究”,並未成為學術熱點。但是,“它異關係”卻是伊德提供的一個極富洞見性的概念,它指明瞭技術發展的最終宿命——與人類的撕裂和對立。**羅森伯格(R. Rosenberger)和韋比克(P. P. Verbeek)同樣指出,“它異關係”解釋了“技術如何既是我們為自己的目的設計和使用的東西,又是如何影響、限制、引導、控制我們的”。可以説,“具身關係”“詮釋關係”“背景關係”指向技術意向性產生的階段性形式,而“它異關係”則指向技術演變的終極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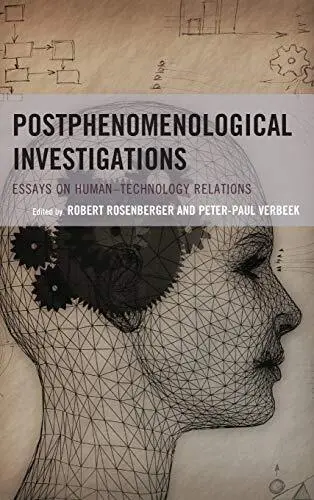
R. Rosenberger and P. P. Verbeek, Post-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ssays on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虛擬集權社會之誕生揭示了媒介技術潛在的發展路徑:從依賴人且易被覺察,到依賴人但不易被發覺,再到逐漸脱離人類,與人類平起平坐,形成與人類對視的“準主體”,最後逐漸掌控人類,成為決定人類生存方式的“超級主體”。技術從“低主體性”不斷走向“高主體性”,從“人—物”層面上升到“人—人”準主觀層面,最後到“物—人”的反制層面。在這一過程中,人類逐漸由主體淪為被技術統攝的客體,最終不得不寄生於技術孵育的虛擬集權社會中。
虛擬自我、超真實情感與現實墮落
數字生存誘發的強烈專注將導致自我意識喪失、時間體驗感扭曲,在此過程中,人們會產生強大“心流”,隔絕周圍現實世界,在數字網絡中迷失自我,達到一種行動與意識的融合狀態**。“心流”使人們沉浸於強烈的“虛擬自我”體驗。“虛擬自我感”是一種將虛擬自我體驗為實際自我的狀態,甚至可能導致人在虛擬環境中反而真實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這種體驗在“第一人稱視角”(POV)的虛擬環境(比如第一人稱視角的遊戲、電影、短視頻等)中表現得更加真實。伴隨虛擬現實技術的加載與升級,自我存在感將會更加強烈,這一過程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實現:一是存在感誘導技術中的“自然映射”會激活用户的真實體驗;二是虛擬空間的“互動控制”所需的警覺性會激活用户的真實心理反應,誘發現實行為可能。
毫無疑問,數字空間的“超真實”已經模糊了現實與虛擬的界線,“數字超真實”超越了現實真實,比真實還真實。伊德指出人類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可能呈現放大或縮小結構,意味着現實世界的體驗可能會被放大。卡斯特提出的“虛擬真實的文化”概念亦強調所謂“真實”永遠基於符號表徵。“情感遊戲刺激”理論(emotionally content stimuli)從實證角度驗證了虛擬技術能夠激起玩家真實的情感反應。觸感手套、列陣式麥克風、Codec Avatars面部捕捉技術、Project Starline全息視頻聊天技術等提供了比現實更加敏鋭的壓力振動,更具凹凸感的紋理,更加逼真的再現音效。加強現實技術放大了知覺體驗,提供了比現實世界更為強烈的感官體驗。真實的情感體驗在數字空間中不僅被積極創造,而且用户很難在虛擬空間將關涉情感的禁忌活動與現實進行區分。

Project Starline全息視頻聊天技術
**那麼,在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中,人類生理和心理是否具有相同的發生機制?這將成為評估“虛擬情感”真實性的關鍵所在。**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兩個平行世界的生理和心理發生機制是一致的,虛擬情感的“真實性”再次深刻展現於此。認知科學認為情緒由“生理層面的生理喚醒,認知層面的主觀體驗,表達層面的外部行為”構成。由於人體鏡像神經系統的存在,通過“觀察”和“想象”兩個知覺思維過程,可以將人類與物質世界交互過程中獲得的知覺經驗模擬呈現於虛擬空間。虛擬技術引發的人體心率、血壓、大腦神經遞質、前額葉血紅蛋白水平等變化的過程與現實世界一致,甚至,現實生活中的人格、情感、身份或刻板印象在虛擬世界中均以類似的方式存在。
**空間存在感、社交存在感伴隨自我存在感,共同促成數字化生存的真實體驗。**就空間存在感而言,在虛擬數字環境中人們會對物體對象產生高度感知。就社交存在感而言,人們會將虛擬社交角色體驗為實際社交角色,對虛擬社交對象產生真實的依戀情感。空間存在感與社交存在感伴隨自我存在感跨越了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孵育了超真實的“虛擬自我”體驗。極致真實的虛擬自我體驗誘發了“夢幻般的狂喜”,現實世界相較之下顯得沉重而粗陋。彼得斯將這種體驗描繪為:“人的感官經歷一種夢幻般的狂喜。在這種狂喜中,我們似乎扔掉了身體,駛離岸邊而進入一個接一個奇妙的場景中,像脱離了肉體的靈魂。”數字技術極力提供現實世界難以滿足的極端體驗如危險、殘酷或變態這類非常誘人但又違法或冒險的極端行為,娛樂至死的誘惑令人嚮往,同時又映射出現實世界的壓抑與乏味。就像電影《頭號玩家》中展現的場景一樣,主人公通過穿戴設備在虛擬世界中任意馳騁,獲得非凡成就和甜蜜戀愛,而現實的落魄與虛擬世界的刻骨銘心形成鮮明對比,現實世界成為可憐肉身的暫棲地,遭到無可避免的揚棄。伴隨虛擬真實全面勝利的是現實世界的無邊墮落。小説《雪崩》中,主人公在元宇宙中的豪宅與現實中的貧困形成鮮明對比。現實的落魄被這樣描繪:“人變得越來越簡單,行為和互動變得標準化和機械化,活動空間可能只需一間小屋子或一張沙發,設備只需一個VR眼鏡和一台接入互聯網的設備。而虛擬化身在虛擬世界則變得越來越多變,越來越豐富。”貧瘠壓抑的現實世界和光彩奪目的虛擬世界形成強烈反差,物質和意識不斷分離、割裂,物質開始被拋棄,意識在數字生存中得以永生。

《對空言説:傳播的觀念史》,約翰·杜翰姆·彼得斯著,鄧建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虛擬性”即將大獲全勝,無論人類願意與否,“虛擬性”已成必然。**虛擬“臨場體驗”(mental transportation)之逼真、“平靜技術”(calm technology)之遁形,阻隔了物理世界的刺激源,極大強化了感官體驗,創造了比物質世界更加逼真的虛擬感知。尼葛洛龐帝因此説:“虛擬現實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實事物一樣逼真,甚至比真實事物還要逼真。”需要警惕的是,現實接觸的重要性被顯著降維,實體交往反而變得次要。未來,“數字超真實”將越來越多地代替現實經驗,成為人類獲取生存經驗的主要方式,而面對這種交換我們往往是疏於防備且樂於妥協的。
隱藏人格、人格失調與技術寄生物
埃裏克·查爾斯·斯坦哈特在《你的數字來生》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你的個人信息、記憶、情緒感受、思維特徵、表達方式和生活習慣全部被打包上傳到計算機中,當你死亡之後,你的數字靈魂仍然存在,它可以代替你接待朋友,與家人溝通互動。人的肉身會死亡,但數字靈魂卻可以永生。這種數字景象固然極端,但是它描繪了一種極可能發生的景象,即在數字生存中人類越來越去肉身化,人類行動總體上將不斷向精神層面坍縮。根據極端“後人類”思想,任何人的存在本質至少在理論上可以被下載到計算機中,並跨越廣闊的時空距離進行傳輸。這即意味着,生物體的“邏輯形式”可以與其“物質基礎”分離,並且“生命力”將是前者的屬性,而非後者。
**在物質向精神的加速坍縮進程中,“人格失調”或將成為潛在的精神風險。**從精神分析學來看,社會中的個體採用多種心理防禦機制以應對社會壓力,而心理防禦機制在數字世界中顯然存在不同的啓用概率。現實社會中,個體高度傾向使用“壓抑”“否認”“潛抑”等“逃避型”心理防禦機制以壓抑本我慾望,但由於虛擬空間的匿名性,“數字替身”傾向於採用“投射”“轉移”等“攻擊型”心理防禦機制,這就將導致“多重人格”的顯現。比如在電影《失控玩家》中,大鬍子粗漢在遊戲中是隻粉色兔子,呆板程序員是暴力炸彈球女郎——現實中被壓抑的人格在虛擬空間噴湧顯現,構成數字替身的“多重人格”傾向。有學者也觀察到虛擬生存中的“離散分身”現象,“分身性是離散的,從屬於多重的感知、身份、行動和交往律,因此具有在跨體系、變維、多分身的生存模式條件下的多重自我”。“離散分身”構成多重人格的不同自我維度,其中“隱藏人格”是人格結構中被壓抑的那部分。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結構由自我、本我和超我組成。“隱藏人格”高度關涉“本我”,“本我”指向人的原始慾望與本能,不為社會所接受,時刻受到社會規範的遏制。“超我”是社會道德和社會良知的道德判斷,是人格結構中的最高管理者。在現實生活中,潛意識層面的“本我”被意識層面的“超我”強力壓制,以塑造符合社會規範的“自我”。數字生活中,原本被“超我”強力壓制的“本我”解除了現實束縛,裹挾着原始慾望的“隱藏人格”便開始充分顯現。

電影《失控玩家》劇照
數字文化鼓勵一種分裂的自我感,人們將自己分裂成多個不兼容的身份,現實中被壓抑的“隱藏人格”的湧現是對主體人格整合能力的一次挑戰,失效的整合可能導致“人格失調”的潛在風險。“弗洛伊德認為人格的正常發展是由本我、自我、超我處於協調和平衡狀態而得以維持,如果三者失調乃至破壞,就會產生神經病,危及人格的發展。”“隱藏人格”的湧現打破了人格結構的穩定。數字生存中湧現的“隱藏人格”將主體分裂為多個“分身”,既然每一種人格都是主體人格的一部分,那麼,人的主體性到底由哪一部分代表?當人格整合失敗時,主體性將陷入徹底分裂,這將導致嚴重的“人格失調”。有學者甚至預言,如果“意識上的主體性任意分裂,神經病或許會成為數字時代的普遍問題”。
這樣就會形成一個主體性悖論:假如一個主體可以變成任意多個主體,也就不存在主體性了。主體性的意義基於唯一性,並且必須具有唯一性。“後人類”主要以信息模式的形式存在,威脅動搖了人文主義價值觀的核心——“一個連貫的、理性的自我,這個自我擁有自主權和自由的權利,以及與信仰啓蒙的自我利益相關聯的代理感”。面臨主體“人格失調”的風險,後人類之主體性岌岌可危,難以避免數字世界與現實世界間的“存在論差距”,跨世界的主體將因此到達意識分裂的臨界點。
**“人格失調”將人矮化,這一矮化過程可藉由斯蒂格勒和勒魯瓦·古蘭的思想獲得進一步解釋。**斯蒂格勒指出,人類記憶主要由“後種系生成記憶”生成,“後種系生成記憶”藉助古蘭提出的“外在化”過程——將人類文明外化為由工具、機器等物質構成的“技術物體”和由語言、文化等虛擬形式構成的“技術體系”——以保存人類記憶。在此過程中,人將身體功能不斷交由技術進行“外在化”,到最後只剩下“知性思維”。“一旦人類成功地外在化大腦的所有運動,從人類直立姿勢開始的大腦運動皮層區域的解放過程就會完成。除此之外,外在化過程就只剩下知性思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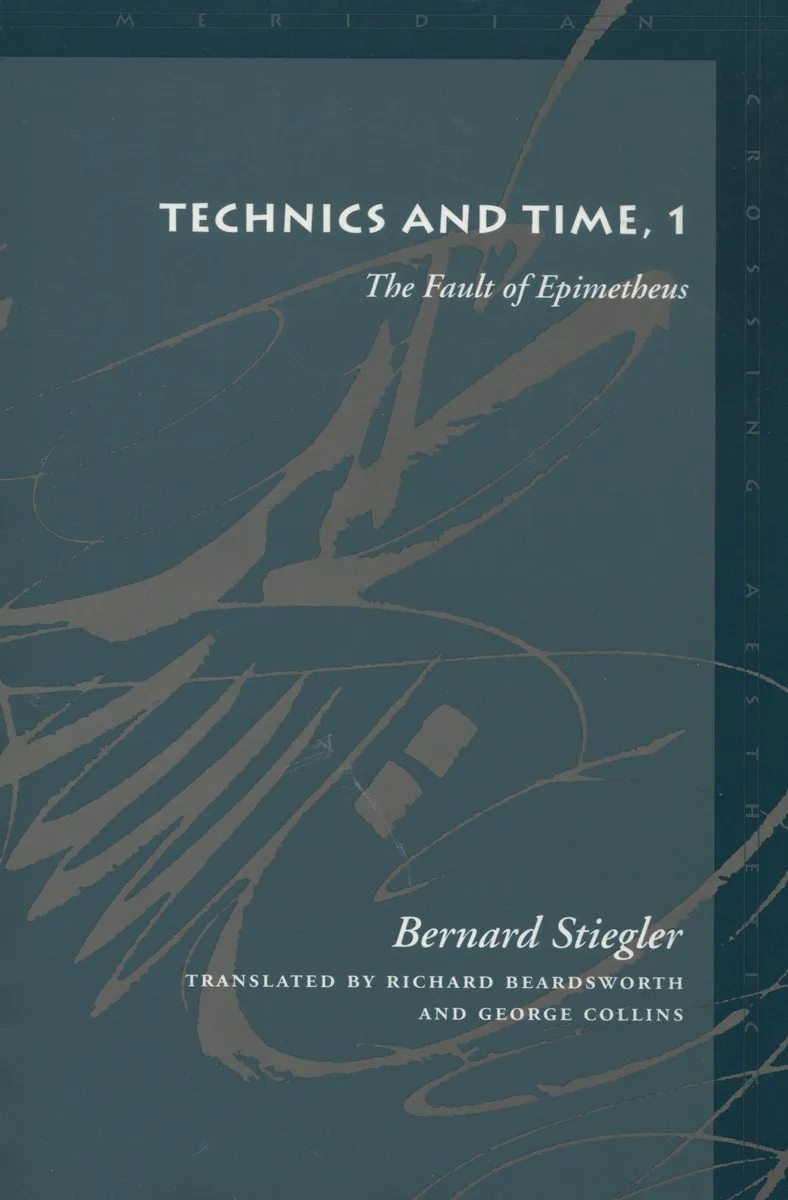
B.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技術個性化”的超速發展打破了它與“心理個性化”“集體個性化”構成的亞穩定平衡態,數字生存的精神坍縮和人格失調症候就是三角穩定結構被打破的後果。**當身體在“外在化”過程中被不斷剔除,到最後人只剩下“知性思維”時,思維就開始脱離身體成為人類存在的主要方式了。數字虛擬技術不斷引發的“外在化”過程催生了“人格失調”症候,最終將“不留給人類任何去做的事”,而當唯一剩下的知性精神被技術不斷扭曲而墮化,人類終將失去自我生存能力,不得不作為“寄生蟲”依附於技術而活。
**技術從“被使用的工具”,到人機複合的“賽博格”,再到“數字超級主體”——技術的演進譜系逐漸脱離了人類的發明意圖。**可以説,依附於人體只是技術暫時的發展階段,擺脱人類獲得完全自主才是技術發展的最終目標。斯蒂格勒將技術這種“自我進化”屬性概括為“技術趨勢”(technical tendency),技術趨勢並不受“發明意圖”的驅使,不受人類組織“構造意圖”的驅使,不受任何“主宰意圖”的驅使。技術以“脱離人類意志”為終極演化目標,隨着技術對人類的架空與反噬,人類終將淪為技術的附庸。
結語
人類原本試圖通過技術革新獲得更大自由,然而技術演進卻越來越脱離人類意圖。隨着數字生存的全面降臨,數字技術之演進譜系越來越展現出“自我維持”的特徵,技術成為宰制人類的力量,技術與人類之關係發生悖逆。數字權力具有不可逆性、排他性和強制性,全面控制着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遠非前述陳文所論之生產與消費場景所能涵括,並且已然取消了人類回到原有生活方式的可能。為了獲取數字便利和避免數字死亡,人類無法避免地全面陷入數字生存,不斷交付個人隱私,持續接受數字餵養,最終降維為無法脱離數字技術的“寄生蟲”。而數字生存越來越去肉身化,人類行動總體上將不斷向精神層面坍縮,精神與身體不斷分離,主體意識遭到分裂。現實世界的重要性被顯著降維,虛擬性成為未來生活的基調,虛擬奴役將成為可能。最終,人與技術之主客體關係將發生徹底悖逆,技術從人類的附屬物衍變為超級“吞噬物”,而人類則從宿主淪為技術的“寄生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