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灣學生的北大回憶_風聞
台北女孩看大陆-台北女孩看大陆官方账号-昨天 22:43
五月中旬,回北大傳播學院參加了畢業十年的返校聚會,不出所料,現場娃兒滿地跑,貌美的室友生了二胎後依舊美貌。唯有我,晃晃悠悠,同學客氣道,“你一點也沒變啊,還是在學校時那樣。”
“嘿嘿嘿嘿當然!”爽死。
當年,同學們畢業時一個個奔進了體制內,那時覺得這幫人的職業選擇真是無聊,現在才知道能穩定苟着就是勝利。原本羨慕着體制內的處長同學,結果陸續有幾位同學説道,“你現在挺厲害啊,聽説都職業作家了?” “你好像挺自由自在的,給自己打工,好羨慕。”
“我倒是希望自己是職業作家呢!書都賣不動,你們還不買一本!”我破防。
由於在校期間老浪跡五道口、上課摸魚恍神,除了仍舊美麗的自家導師之外,完全認不出再返校聚會上出現的幾位老師。倒是一位負責學生行政的老師讓我認出了,啊,當年我來北大面試,接待我們的就是她!
港澳台學生,在北大校園裏常常被認為資質不足、混水摸魚、靠着港澳台聯招進來的,但當年除了我之外,其餘台灣學生倒是都認真刻苦,亦有拿獎學金的。剛進北大,驚喜的不是大陸同學之資質,而是碰到許多來自台灣大學的同學,蹦跳着跟家人報喜,“當年我分數離台大很遠,現在還不是跟台大的當同學!”
我是2012年來的,大陸人或許會憤恨不平,覺得我們這些台灣人撿了大便宜(事實也是如此),但選擇來大陸讀書,在台灣社會是非常小眾的(到今天仍是),在不少台灣中小企業眼中歐洲水碩可能秒殺大陸985。但是北大嘛,在台灣社會屬於“小眾中的極熱門選項”,從2012年至疫情前,台灣人來北大的人數節節上升,據説後來很“卷”,畢業後仍有台灣學弟妹們來問北大的報考秘訣。
畢業後一段時間,每年五月四日,朋友圈總有人發文慶祝,回憶在校時期的青葱歲月,而我總是羞於發這些。有一年,憋不住了,朋友圈發文:“我其實很怕提及母校,因為總覺得自己不配。”
我原以為,只有我這種期末看名次得從最後一排開始倒數看的學渣有這種心情,不料這條朋友圈炸出了一些在我看來很優秀的北大畢業生。果然,出社會的北大人,碰上冷嘲熱諷“你是北大的,怎麼這都不會”是其次,“我的能力與成就,似乎配不上這塊招牌”之自我貶低與質疑,才是心魔。
我沒有在公眾號寫過在北大的一些回憶,那就在畢業十年後,寫寫自己還記得的一些瑣事吧。

畢業十年後回校啦
瑣事一,豬肉燉粉條。
我第一次有“這個地方的政府可以養活十三億人,真是厲害”,就是在北大食堂。
某個食堂的面特別便宜,根據葷素一碗從六七塊錢到十塊錢左右(年代久遠,不正確見諒,反正我常去吃六元七元的面),第一次見到份量時驚了,只能吃下三分之一,一邊吃一邊看旁邊的女同學。
她、吃、完、了!
大陸人好恐怖啊,這食量可以吃掉一個台灣人了。
後來因為永遠吃不完這碗麪,避免浪費,我就很少去吃麪了。我常在食堂要關門之際去打豬肉燉粉條與白飯,那時大媽會把剩下的粉條全給我,沉甸甸一大盒,加上白飯也就七八塊錢,但老吃還是會吃膩。
吃膩的時候,就去吃吉野家,二十多塊。畢業後的一段日子,我非常窮,每每想到那時不吃豬肉燉粉條、跑去吃吉野家,就會在租住的小次卧裏狂罵自己:那時多吃點豬肉燉粉條,不就省下更多錢了?!
直至今天,我在出差時碰到豬肉燉粉條,都會告訴同桌的人,“我在北大都在吃豬肉燉粉條!這是我學生的回憶,是我第一次對東北菜有概念!”
瑣事二,單車。
北大校園很大,清華據説又是北大的兩倍大。為了遊走兩校,入校不久我就買了一輛二手單車,是從另外一位台灣同學那裏“繼承”來的,八十塊。
才騎一天就不見了。
我滿校園找車,四處問“有沒有看到一輛黑色藍色相間的腳踏車”,滿頭大汗、火急火燎,偏偏遇見的學生都泰然處之,“沒有”“不知道”。
又急又氣,北大同學怎麼沒有絲毫人情味!
後來,一位實在看我可憐的同學提點我,“在北大,沒有丟過單車的生活是不完整的。”
瑣事三,空調戰爭
我的貌美河南室友,透過我認識了台灣。在她眼中,這位台灣同胞很奇怪,比如竟然沒看過龍應台。“什麼?你這年紀的台灣人不看龍應台?”
台灣同胞:我們看藤井樹和九把刀。
比如這位台灣同胞在澡堂洗過幾次澡後,就大言不慚地斷言:“大陸女生胸部好小。台灣女生比較大。”
比如這位台灣同胞很愛看鄉村愛情故事,説這是認識大陸的方式。
不久,宿舍內就爆發“兩岸衝突”,因為一台空調。
**我從小的家庭教育就是,開空調的房間必須關好門窗,不然很浪費電。**而作為台北小孩,我們從小住家裏,連讀大學時都無法倖免(誰讓台北這麼多大學),結果我嚴重缺乏與人同住經驗,把家規當絕對正確的標準。
某次我回宿舍,窗户大開,冷氣大開。我瘋狂唸叨,這很浪費電怎麼能這樣開冷氣要關窗不是基本常識嗎~
貌美室友大怒,我對不起你行了吧!你這傢伙!
剛來大陸的台灣菜鳥,是特別容易講出“大陸人都怎樣怎樣”的時期,講電話時不忘跟家人吐槽,“氣死,大陸人怎麼開冷氣不關窗户啊?很浪費欸!”
那兩年是我目前人生中唯一跟人同住一間房間的時期。畢業後因為發展不順,我租住的小次卧沒空調,所以都會跑去隔壁主卧蹭大陸室友的空調,並跟他們説:
“開空調不要關門啦,我從小在家開空調都不關門的。台灣人是這樣的。”
瑣事四:我的美麗導師
野心勃勃、狼性十足、衝勁百分百,這是台灣學生對大陸學生的普遍印象,事實證明確實如此(至少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同學們不光發言踴躍,選導師時更熱衷於選大牌導師,汲汲營營想接項目、一展身手。
而我在選導師時,唯一打聽的就是:哪位老師最不用幹活?
結果,選定導師之後,我的導師竟然接了一個大項目。但有鑑於我實在混水摸魚,她對我呈現放棄狀態,甚至某次問我,“今天去五道口嗎?老師順路送你去?”(那時同學們都知道,我是五道口酒吧的常客)。
我的畢業論文寫得出奇順利,因為那時已經開始在豆瓣連載《台北女孩看大陸》的我,選了一道論文題:**台灣人對大陸的認知轉變。**這題目處於傳播學院老師們的“認知盲區”,他們只能聽我滔滔不絕、胡吹海吹,最後發表“恩,這種題目挺有意義”之評語。
輕鬆通過。
雖然我自詡那篇論文寫得挺認真,但對照那些嚴謹的論文,我始終認為自己是“混”過去的。
畢業後我鮮少回母校,印象中第一次回去,是去送自己的第一本書給老師。
那是2016年了,年代久遠,與老師聊了些什麼已經忘記,只記得她説,“其實你的論文差一票,就能得到優秀論文。”
寫這篇文章時我努力回想當時情景,不確定老師是安慰我、還是我記岔了,但貌似是這件事,讓我從“我是個混畢業的”之自我譴責中稍稍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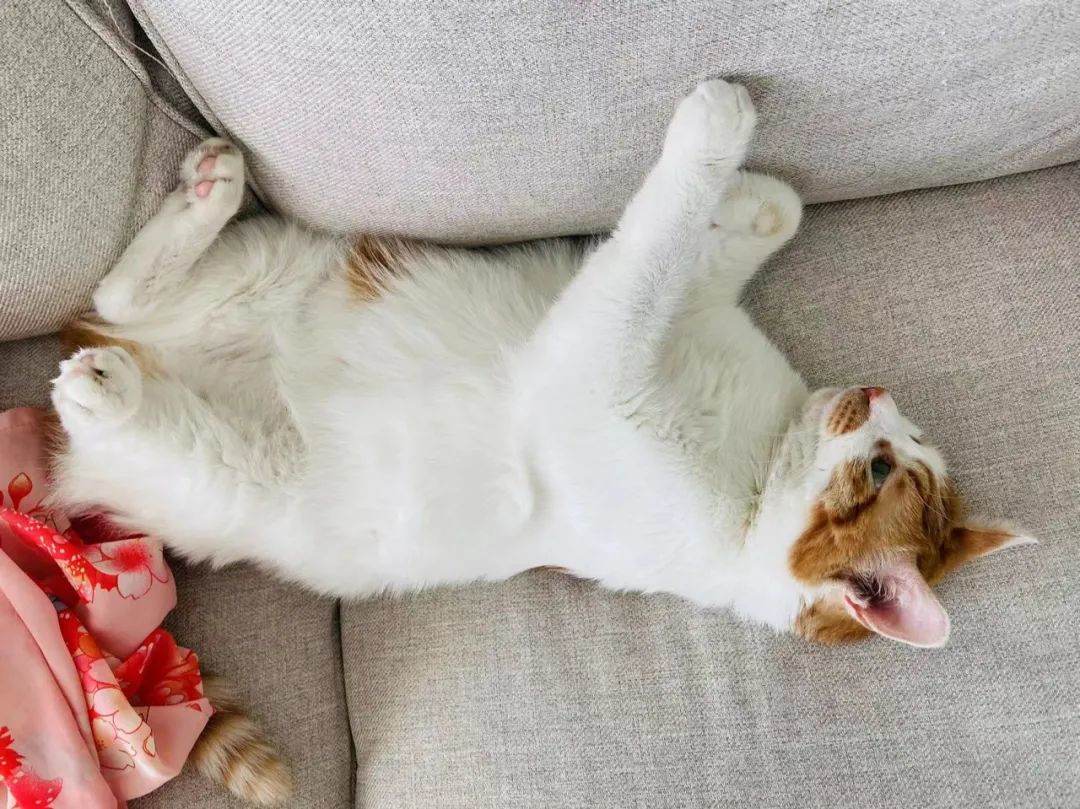
北大的圖書館,我只進去過一次;北大豐富的資源我也沒怎麼用,如果時光倒流,我不會再浪費。
我確實不是個好學生,是個用惠台政策混進去的幸運兒——2012年時,台灣申請北大的人數還是少,趕上時代紅利。
**但北大的經歷、**與那時碰到的同學,是我日後能在大陸生活十多年的根源。那時我們不畏懼與對方交流一切“敏感議題”,意見不同不會立刻譴責或質疑,而是分享彼此的成長過程,討論不同觀念之形成背景。
2015年開始從事媒體,並在出第一本書後與許多涉台人員有所往來,我的溝通方式仍儘可能地延續“北大風格”。這幾年,兩岸情勢變了,我不知道北大的台灣學弟妹,是否還如我們那時一樣?
我與北大多數同學,已經成為“朋友圈”之交,甚至連彼此現況都一無所知。但我無比幸運,在剛來大陸的時候,就體會到了最真誠的交流方式。
也因為這份真誠,往後數年,直至兩岸政治日漸陷入僵局之際,我都碰上了那麼些願意“以真心對真心”的大陸朋友。
朋友問過我,以後我回台灣,換個環境後,會怎麼跟別人説大陸?我笑,好壞都可以説,但不能太誇大,好歹我得顧及一下我的大陸朋友吧!
這是北大給我的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