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佔有慾”的讚歌_風聞
死理性派-死理性派官方账号-“死理性派”是一种信仰,致力于从荒诞中寻找理性,从虚无中看到……46分钟前
文 慧敏 | 玉崽
(此文為雙作者作品,一切讚賞及相關收入由雙作者平分。)
慧敏:
Mona Eltahawy在《女人與女孩的原罪》中提及,蘇珊·宋(Susan Song)曾説:
“誠實坦白地在同一時間擁有數量大於一的親密關係,且所有親密關係人都知情並瞭解此狀況……多重伴侶制的誠實與坦白,代表了無政府主義的自願合作性質與互助性質。多重伴侶制也允許我們自由相愛,這是單一伴侶制的性觀念所不允許的。”
讀到這段話後,我的第一反應是,如果兩人關係都處不好的話,多人關係似乎就更難了。問題是,先嚐試多人關係更簡單,還是先嚐試二人關係更簡單呢?我發現我竟然不敢亂回答。因為這裏涉及的操作細節背後的倫理其實是非常陌生的,陌生意味着需要多動腦,但傳統二人關係對人的認知力的消耗其實也相當可觀。

玉崽:
關於這個話題我想先引用「兩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公眾號的推文:《「脱男緣」就是遠離男人嗎?》裏的內容:
一個人所能付出的愛應該是接近無限的,而當今社會對「絕對專一」的推崇無疑斬斷了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更加劇了關懷和情感的匱乏。
……想要最好的朋友/唯一的愛人」也是人之常情。可是,為了避免異性戀範式對人性和關係的腐蝕,我們依然要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在個人層面,我們應該積極探索新型的情感模式、身體力行地建立平等的親密關係……。而在社會層面,大家也要儘可能地拓寬感情的邊界、建立更多更緊密的紐帶。畢竟,沒有女性聯盟就沒有進一步的行動,而廣泛的同盟要求我們把眼光投向小圈子之外,儘可能地關愛更多女性。當愛不再匱乏、私有,當每個人都能獲得無條件的愛,我們自然也就不會再執着於“偏愛”帶來的保障了。
總第三十七封,公眾號:兩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脱男緣」就是遠離男人嗎?
我暫時還不擁有可以朝夕相處的伴侶或是非伴侶的同居夥伴,也沒有經歷過高質量的親密關係,所以對親密關係的細節一定程度上還依賴於我的想象力。在我看來,或許兩人關係因為所謂的偏愛,所謂的專一而顯得更為匱乏和難以維持,所以我覺得可能“兩人關係都維持不好,多人就更難”這個説法不太充分。
慧敏:
是的,我也是不敢對這方面的問題下定論。目前我的小微信羣也算是我對“多人關係”的實踐,自己當下的現實生活也是三人關係。我發現我的多人關係都是奠基於二人關係基礎之上的,比如,我與A、B相愛(任何可能性的相愛),在感覺條件適合時介紹A與B認識,如果這兩人恰好互相喜歡,就建立三人關係,以此類推慢慢擴大。
更具體地,在介紹兩個朋友互相認識的時候,我會説:“不管你們之間的關係發展成什麼樣子,都不影響我個人對你或對她的感情。”在一些時間裏,會發生那樣的事情:我與某兩人分別相愛,但這兩人暫時互相反感,我們接受這樣的狀況。
在目前我的三人小家庭中,每兩個都是另外一人生命中最親密、最信任的人。網絡羣空間的關係則相對鬆散,我在開始奠定的規則是(1)全女(2)如果有爭議私下解決,不得在公共空間攻擊羣友。目前我的網絡大家庭和線下小家庭的狀態都是讓我自己滿意的。
過大的鬆散式集羣有點兒像不夠好的親戚關係:個體在一些情況下可以感受到被支持,但其實並沒有強烈的歸屬感與安全感,特別是,在手機與電腦全部關閉之後,人還是會感受到強烈的孤獨,即使開着手機,羣空間的文字能給人的情感撫慰也是極其有限的。
真實的多元家庭則有可能給到人實實在在的“愛”的感覺。
在多元多人家庭中,人感到自己的生命與希望不是完全寄託在某一個人身上的,甲與家庭成員乙發生衝突之後,還可以立即請同在一個家庭中的丙幫忙從中調節,這就使“今日衝突今日了結”的可能性也大大上升,另外,就算與乙發生了劇烈衝突以至於三天不説話,如果可以從丙丁那裏獲得支持,這種衝突對個體的衝擊也會相對二人原子家庭來説降低許多,由此,多人家庭確實可以降低個體“討好”任何人的需要。
另外,如果以傳統的原子家庭為目標,人們對伴侶的共情能力、鈔能力、性能力、認知能力等多個方面都會有不低的期待,或者説,因為需要將餘生的所有希望寄託在這一個人身上,人理所應當期待對方“超過九十分”,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是難找的,但如果以多元多人家庭為目標,我們可能只需要“潛在家人”綜合水平達到八十分甚至七十分就好,這樣建立新家庭的難度也會大大降低。
但真正操作的時候,每一次向家庭中納入新的成員,一定是需要全體家庭成員同意的,或者説,要讓某人下班後有強烈的“回家”的願望,一定是因為家裏不存在任何讓自己想要躲避的人,同時存在幾個與自己有極好的二人關係的人,而不是因為這個“家”擁有任何抽象意義上的優點。
這樣的話,“多人關係”最終還是落到了這幾個人的兩兩關係之上,這也是我説“處不好二人關係的人似乎也難處好多人關係”的原因。當然,這個也可以落到個體的具體習慣上:如果可以培養自己“認真表達出自己的感受與欲求”並且“認真傾聽別人的感受與欲求”的習慣,經營好多數關係都是有可能的。
玉崽:
理解萬歲!任何關係傾聽是前提~
我又想到了一段話:
我們對時間的感知其實也是被塑造的。……一位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女性覺得太陽有時走得很快,有時卻又很慢。**她們認為時間只有在自己做事時才會流逝、休息時則會停止,所以就算無所事事也不是在浪費時間。**我們可以想見,在這種未經資本主義形塑過的地區,親密關係也並不會是一場“你有我無”的惡性競爭。掠奪和佔有是父權的底色。……在母系或者説私有化之前的社會,萬事萬物都是地球母親慷慨賜予這個世界的禮物,它們是共有且共生的。那時的我們可能會喜歡一棵樹,但不會非要把她搬回家裏——我只要能與你在地球上同呼吸就好。由此看來,佔有慾並非天性,而是父權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
總第三十七封,公眾號:兩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脱男緣」就是遠離男人嗎?
回到我自己。我現在就一直和自己的佔有慾作鬥爭。當我喜歡一個人,我就很想成為ta的唯一,或者怎麼怎麼樣。但事實上,我自己就喜歡好幾個人,我的腦子知道不該要求我的戀人或者我的朋友需要跟我彙報什麼。但要知道,其實知行合一還蠻難的。如果我不承認自己內心還是有佔有慾的,顯然不真實,只是想説這種冒出來的念頭還蠻困擾的。
慧敏:
我很喜歡你引用的對時間的新觀點。“浪費時間”這個詞組的大前提是對“有價值”的定義。如果我們可以奪回對“價值”的定義權,如果我們可以堅信自己的存在本身有價值,那麼,任何人的任何時間都不該被定性為“被浪費”的。從神經科學的角度,在睡眠或是放空時,我們的大腦也在進行着永無止息的信息處理與自我修復,生物體內部不存在完全“無所事事”的時間。與“創造力”有關的研究也表明,人在“無所事事”時是最有創造力的,而創造力正是我們的世界得以向前發展的重要原因。
看到你將自己內部的某種慾望定義為“佔有慾”,我感到一絲難過。我想,這種定義/定性方式正是“鬥爭”的原因呢。
在我單身的日子裏,我也會對某些人與物產生強烈的佔有慾。但當我真的擁有了足夠相愛的愛人、家人與朋友,當我真的擁有了足夠的安全感與歸屬感,我發現我自然地變得“寬容”且“博愛”起來,我的朋友們都是我的“N分之一”,我也會對所有人説“請不要讓我成為你的唯一,請更多地尋找像我一樣愛你的人吧!”這不是因為我“先天是個聖母”,而是因為當下自己的基本需求獲得了滿足。
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大規模的“獨居”是隻發生在近小几十年的事情,“原子家庭”的歷史也極為短暫。在更為漫長的幾十萬年中,人類一直是結合成大家庭生活的。《妮薩》中講述了一個採集部落在二十世紀中期的存在狀態,雖然已經受到了父權社會的侵蝕,但至少在Marjorie Shostak早期進行觀察研究的時候,這個部落是分散成一個個十至三十多人的小集羣(也可以説是村莊或“大家庭”)生活的,村莊部局一般是一圈房屋蓋在外圍,中間是公共活動空間,兒童在這個公共空間中玩耍,獲得全村人的照料,這是“It takes a village to take care of a child”的極好例證。我想,不僅是照料孩子,即使是我自己,我也是渴望獲得一羣人的關愛的,不管我的伴侶多麼愛我,我都會覺得“還不夠”。
所以我想,與其説玉崽當下的情感是“強烈地想要佔有”,倒不如説,玉崽是看見了自己“強烈地想要與一羣人建立並維繫深度聯結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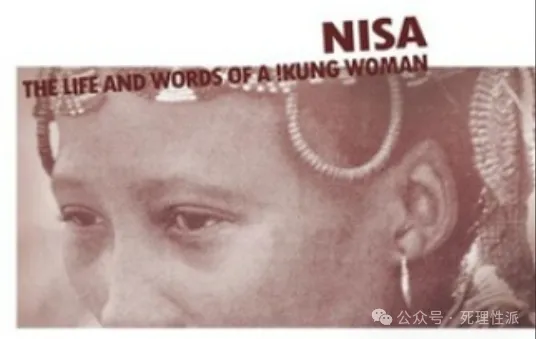
玉崽:
嗯~所以我一直呼籲人本身就是目的,人本身就是價值體現。
關於我為什麼會説自己有“佔有慾”,我想可能是因為接收到的文化,那些詞語讓我分不清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其實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想要的,我想“佔有”的是什麼呢?這個應該是符號學的內容了,表達不清、語言無法跟不上解釋的時候,就出現了語言倒退的感覺。只能用更簡單的詞去代替其他符號。
慧敏寶説自己單身的時候也會這樣,所以還是覺得在當時我們擁有的愛太匱乏了,於是見到想要的才會那麼激動,得到後又不敢放手吧。
你説的對,現在想想,我以前發出信號:我渴望和人真誠的暢談一把。其實就是表達,我想要可以深層思考互動的共同體。在我堅持不下去的時候,見到有那麼幾個人還可以對話。我覺得自己不再是孤立的。
而且,很喜歡你的“還不夠”,我也是這樣的,我不覺得“一輩子只求一人愛我忠於我”就夠了。這太易碎太不現實也太匱乏,所以我還蠻不喜歡關係中的排他性。
慧敏:
不僅是“深層思考互動的共同體”,“生活共同體”也很重要呢。
現在我們是三個人一起生活,大家都覺得做飯是非常頭疼的事情,一週吃一、二次自己做的大餐,其它時候都是在湊合或是點外賣,大家都覺得不是最理想的狀態。聽説每個月兩千塊就可以聘請阿姨每天為我們做一次飯並順帶打掃房間,我想,如果我們可以組建出五、六人的大家庭(幾個小家庭住得很近其實也算一家),就可以湊錢每天吃到體面的午餐與晚餐了!
另外,前陣子周海媚在獨居的房子裏因為暈倒後沒被及時發現,結果遺憾地早早離世,我想,如果是幾個人一起生活,每天有至少五分鐘的互動,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我習慣性地看到“他”字就會腦中亮紅燈。我想,如果是在某些關係中適當排斥符合刻板印象的“順直男”的“他者”,似乎是在操作上有益的,畢竟那樣可以少許多drama。當然,這不是你的原意,你只是下意識用“他”來代指“other”而已。
我不知道引進與“女也”並行的“男也”更有益於公眾在看到“他”時想到“這也有可能是女人”,還是在一切“可男可女”的地方都使用“她”或者“它”更好一些。無論如何,我受夠了“男人=人”的思維定勢。
玉崽:
在你標記“排他性”中的“他”時,我就明白你要説什麼了——“我受夠了‘男人=人’的思維定勢”。我理解你的心情,非常支持你做這方面的努力。只是我的精力更多的放在了“法律公正”層面上,所以大方承認自己確實沒那麼在乎“敍述”上的細節。我認識一些律師,那些案例觸目驚心。一個印象深刻的案子是,有個法官自認為公平正義絕不歧視女性,卻因為偏見而判決女性敗訴。
這帶來的眼淚大多了。所以在我心裏會是“無論如何,我受夠了充滿偏見卻號稱正義的人於無知中讓女人成為祭品”。她們應得的正義也沒有得到,只能在眼淚和屈辱裏成為待享用的祭品,供消遣的娼妓。
關於你説的“生活共同體”:我之前一直幻想可以有個“大家庭”,這裏充滿愛很少有偏見。大家都記得對方喜歡什麼,發自內心的為對方準備浪漫,沒有小心翼翼隱藏自己的故事,哪怕做錯了什麼,也不會有人攥着你的把柄將你審判驅逐,沒有人需要犧牲自己的舒適去維護關係。
周海媚的遭遇讓我想到,我也不喜歡一刀切地講“女權主義者就是要當大女人、就是要當強者的”“靠自己,獨身主義也很酷”“要競爭,成為勝者”。我想,我們沒必要故作瀟灑,整天像唸經似的唸叨着“自立、自立”。上野前輩説:如果自立代表孤立,那麼拋棄親情、拋棄家人卻換來寂寞孤獨的這一形象,當然會讓女性感到恐懼。如果自立只是這樣一種貧瘠的形象,那女性自然會有“即使受點束縛也寧願依靠男人活着”的想法。女性主義者在運動中發現的**“自立”應該是“共立”。人的自立能力只有在集體的支撐下才能被培養起來。身邊有夥伴,才能安心自立。自立絕不是孤立。女性運動鑄就的其實不是"自立",而是“相互支撐”**。只有存在一個個自立的個體,才能彼此依靠;只有知道可以相互支撐,才能安心自立。自立的女性逐漸明白了彼此之間是可以撒撒嬌、可以依靠的。
我曾經想過,我可能會不停迴歸單身,但我希望在大年初一的晚上,能打電話給一些人:“喂,今年,我們一起過吧?”我會暢想開門時的暖光和擁抱,我們就着霧氣忙活起團圓飯,飽餐後圍坐火爐看着電視聊聊天,睡前洗個熱水澡,這幾天是快活的,我不再需要忍受良久的孤寂。
我曾經與一個姐姐聊過之後,觸及了現實最底層的孤獨。
我的孤獨不是説有個人在我身邊這就能緩解的,而是要ta聽得懂我在説什麼。姐姐説,從社會學的一個理論出發的話,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如果你想要交那種非常誠實的朋友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需要你們的經歷差不多,然後還有思想的差不多才有可能。
這樣想着,我幾乎陷入絕望,你説能有幾個人04年出生小學就經歷孤立,後因為實在不解為什麼世界這麼爛去嘗試讀社科又愛上社科的?有幾個人讀了社科就能讀懂社會的一角和人與人之間權力的湧動?有幾個人可以暢談性與愛的?但我在表達的時候,總有人覺得我是文明時代的瘋子。
姐姐説我孤獨是因為太超前,慧敏説我是某個領域的有天賦者,但我在無數次面對黑暗時總哭笑不得,覺得擁有這種天賦好像也不是什麼好事哈哈。只是現在的自洽告訴我,這條路沒錯,我確實在變好。
因為太想要一些關係,所以很坦誠地展現自己,總有人説:你太天真了,ta們會拿着你的弱點攻擊你利用你的。只是我總不由自主的將自己的真實寫出來給大家看。我太想要被人看見了,以至於可以忽視危險,傻瓜似的坦白。
慧敏:
我已經“專業躺平”十四年多,所以經常會在過年前很久就研究邀請朋友一起過年的事情,共處的時間似乎也是越久越好。看到你説“大年初一的晚上”而不是“除夕”,我感到你很特別。你的除夕是更喜歡一個人度過麼?還是説確定與媽媽一起呀?去年除夕我是與伴侶一起度過的,我們先開車去附近的一個古鎮散了一會兒步,看了一陣子陌生小鎮的煙花,之後又回到合肥吃年夜飯,順帶研究了城郊最大的煙花燃放點,在跨年之前半小時趕過去,欣賞了我這輩子見過的最壯觀的煙花盛會。那晚上與愛人相擁着欣賞寬約百米的超大煙花的感受大概也會是永生難忘了。
我之前也以為“經歷差不多”是“思想差不多”的前提,但現在我的兩位家人與好幾位親密的朋友都是在中產有愛的家庭中長大的,具體經歷其實與我有着相當大的差異。我們的最大共性是“高共情”,雖然經歷迥異,但如果願意靜下心來傾聽,“差異”就可以幫助我們擁有極為豐富的人生體驗(替代體驗也是可以像真實體驗那樣影響人的心靈的)。每個人的經歷都有其獨特之處,對於我來説,我身邊擁有“高理解力”的人們中沒有一個是經歷過我幼時的那種貧困的,許多讓我敬仰的女性主義者早期也會至少擁有一個高知家長,“找不到人深刻地交流對貧困的感受”其實也是我三十六歲前感到孤獨的重要原因,但最後讓我接納貧困歷史、與金錢之間達成更為和諧的關係的仍然是一羣沒餓過的人。
所以最終我的總結是,只要一個人善良、高共情、擁有較高的自我接納水平且喜歡你(喜歡聽你説話),就都是有可能讓你感受到不孤獨的。
我也經歷過被人“拿着我的弱點攻擊我利用我”,經歷了所有這些傷害之後,我對“善惡”有了更深刻的感受與理解,並在交友過程中將“善良”放到了至高的位置。我已經擁有了一些可以看見我的人,但我依然像你一樣坦誠地展現自己,我認為這並不是“太想要被人看見”的結果,而是我們一直在“勇敢接納自己、努力愛全世界”的證據。
在《女人與女孩的原罪》中,Mona用一整章的筆墨來論證,我們“應該要求獲得關注的權利”,應該以“身為關注婊”而感到自豪。
如果我們不展現自己的真實,如果所有像我們這樣有能力表達(擁有表達天賦)的女人們不拼了命地聲嘶力竭地説話,幾十億不夠擁有天分的女人們就沒有機會從我們的文字中獲得鼓舞,她們就會被迫誤信男人們的文字,就會像之前的你我一樣認為自己期望被愛、被關懷的正當願望是一種“罪”。
玉崽:
因為現在還年輕,所以除夕會和家人過哈哈,而且因為沒有朋友,所以你説的早早規劃邀請朋友我一時沒有想到,其實也是不確定到底有沒有讓我迫不及待想見面的人。以後就不一定了呢?在這裏工作,也會早早過完節就上崗吧,所以會想在初一這幾天和朋友戀人過過小日子幸福一把呢~
果然還是需要交流,我經歷的太少,看到你説“最後讓我接納貧困歷史、與金錢之間達成更為和諧的關係的仍然是一羣沒餓過的人。”似乎讓我有了更多的想象。
你説“我認為這並不是‘太想要被人看見’的結果,而是我們‘勇敢接納自己、努力愛全世界’的證據。”我很喜歡這句話。我確實有在努力地愛這個世界,這是一生的修行。我曾經也在朋友圈發過:我知道做勇士很累,而且很委屈,我覺得自己還需要很多年去走出對這個世界的厭惡,但沒關係。是的,我覺得沒關係,雖然很委屈,但不得不承認在路上的感覺很好。
你的很多話讓我感動,我突然想到自己曾經有段時間是做着同胞嘴裏的‘支教’工作的,或者説,不挑對象地宣傳女權理論。但我和她們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支教的時候,更多的是幫助女孩自洽。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是會有很多負反饋的,每次因為這種事懷疑自己時,很容易對一句話產生短暫的認同:“人真正能影響的人少之又少,那些被你影響的人,只是片刻的感動。”這説法是錯的,我很肯定這些妹妹已經受我影響了,她們已經學會怎樣去正視自己的傷痛,去回應自己的需求和感情,我不覺得這是片刻的感動。話説回來,支撐我不斷表達的理由也並不高尚,我不只是想要為女權事業做什麼貢獻,自己也需要這份關注。
慧敏:
看到你説自己“並不高尚”,我想到自己曾經因為“事實上非常高尚”而經歷過許多次道德綁架,典型説法包括:
“你是老師,生活得比我們好,給我做個免費諮詢怎麼了?”
“我們都把你當成榜樣、導師的,你怎麼可以期待別人對你像你對對方一樣好呢?你就應該多包容那些不如你的人的!”
“你一直都有在做慈善的,你要守住你的初心,就算別人在什麼地方辜負了你,你也該把你的善良進行到底,不能跟普通人一般見識,不能在利益得失上斤斤計較。”
……
如果放在兩年前,我很可能會被這些話繞進去,會為了自己的integrity/完整性/自洽而在許多地方妥協,但現在,我學會了另一套回覆方式:
“是的,我一直有努力做一個最好的女人,活成更多人的榜樣。在研究了許多女人的故事以及我們社會的運作模式之後,我發現,‘好女人’首先需要奪回的是對‘好’的定義權(裁判權)。可持續發展的人際關係是**‘互惠互利、互相看見、互相承認’**的關係,所以我會首先對別人好,努力看見別人,努力愛人,但是,如果給予足夠多的付出之後發現對方並沒有嘗試理解我、與我達成互惠關係的意願,我就會適可而止,這不僅是為了我個人的可持續發展,也是為了讓對方有機會對‘好的人際關係’有更深刻的感受——我單方面扮演‘男人口中的理想母親’的關係不是健康的人際關係。父權社會下女人最大的弱點就是過度擔責、過度付出,如果我想要活成更多女人的榜樣,就需要更加刻意地強調‘互惠’與雙方的‘對等感’。”
玉崽:
“活成更多女人的榜樣”,這讓我想到曾經一個姐姐和我説的話——“你可以給你身邊的女孩子,一個開開心心做女性主義者的榜樣”。這句話讓我很受用,因為當時已經被各種新聞擊打得站不起來。我喜歡被人評價為“你是一個散發着温潤光澤的女人,一個值得駐足的朋友/愛人。”
説起來在遇見你之前我就渴望和人交流,後來見證你做的這些事後,我是真的感覺到“原來人可以這麼活啊”。原來可以行動,原來自己的需求並不奇怪也不可恥。
慧敏:
是呀,父權制硬性規定了“公”與“私”的區別,將一些個人化的感受與欲求都定性為“不具普遍性”,但每次當我們分享自己的感受,都會激起強烈的共鳴。“奇怪/正常”與“可恥/高尚”都是環境強加給我們、激發我們自我否定的概念。如果我們試着將所有自己感到“羞恥”的事情全部説出來與朋友們分享,我們很有可能從中找到父權社會傷害我們(WOMEN)的法門,而這也是我們打開枷鎖、釋放真實自我及我們內在神聖創造力的法門。
Elise Loehnen和Mona Eltahawy分別從自己的經歷出發講了她們所感受到的“七宗罪”,通過從寫作中獲得的自我接納以及與更多人互動中獲得的來自外界的接納,她們成為了更勇敢、更有力量、更完整的人,同時也鼓舞了無數的讀者。我想,這大概就是“把膿泡戳破並清洗”帶給自己與全世界的好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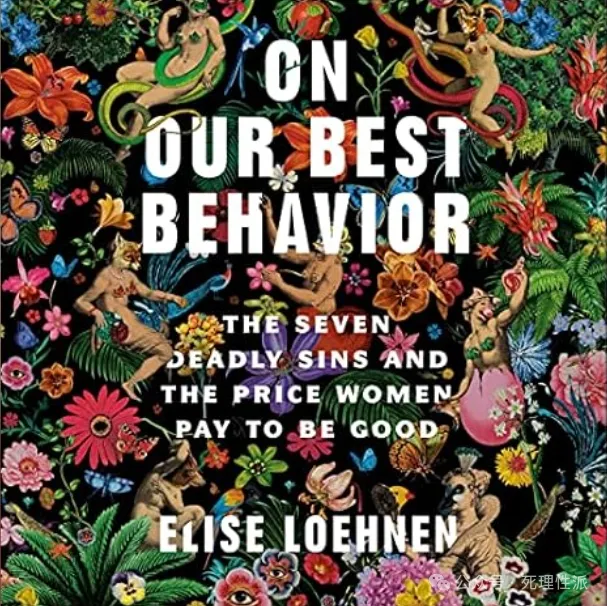
玉崽:
還真沒説錯!我在羣裏打出“缺愛ing”時又被自己尷尬的想撤回,但最終忍住了,我怕羣裏的人覺得“誒,你好奇怪啊,我們又不認識,你跟我們説啥愛不愛的。”
我怕招人煩。但是事情似乎沒有想的那麼糟糕,只是那股羞恥帶來的焦灼真是不好受。但又想着,可我真的很想説自己缺愛啊,説吧説吧,沒事。
我覺得要成為一個完整的人,要費好大的勁兒啊。真給我累壞了。_(-ω-`_)⌒)_
慧敏:
戴着面具生活需要費更大的力氣,試着多多地與人交流自己的一切感受,每天為自己創造一些安全時間,在那些時間裏做個沒心沒肺放飛自我的小孩子就很好了。之前你説的“工作”也是一樣。如果是像正常人一樣給父權企業打工,每年能夠擁有的高質量假期確實屈指可數,但如果可以發揮創造力與親密的女性朋友一起研究出非傳統的創造財富的方式,讓工作成為幸福生活的一個有機組分,那麼,“在年輕時就過上養老的生活”其實是完全可行的——誰敢説老人就缺少創造財富的意願與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