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來 | 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探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31分钟前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人們的生活方式、文明素養及價值體認現代化的特徵日益明顯,社會的倫理道德發展面臨着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如何激活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實現中國傳統倫理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何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築牢倫理之基?這些成為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為此,2023年11月25—26日,江蘇省道德發展智庫、江蘇省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協同創新中心、東南大學道德發展研究院、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共同舉辦“倫理道德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國際會議,就現代化進程中倫理道德發展的新方向、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期約請部分與會學者撰文,以饗讀者。
李萍教授從歷史與實踐的角度闡述了“倫理覺悟”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的啓蒙意義。她認為,“倫理覺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發展具有某種內在的歷史契合性,現代文明的發展必須保持文化自覺,保持文化反省力、批判力,特別是在文明發展的重大轉型時期,這種“覺悟”顯得尤為關鍵。賀來教授強調,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尋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是西方和中國現代化進程都難以迴避的重大倫理挑戰。為此,我們需要對中國傳統倫理體系進行批判性反思,既吸取其有益的資源,又對其侷限性有充分的認識。王淑芹教授認為,道德分歧與社會團結矛盾的凸顯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必須妥善處理道德分歧與社會團結之間的關係,使二者間的張力在相互成就中實現和諧平衡。談際尊研究員提出,權利性道德作為一種“批判性道德”,在試圖衝破傳統道德束縛的同時,也可能帶來道德異化風險。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權利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而不是將之視為社會實踐的道德依據或美好生活的道德合法性基礎。龐俊來教授指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必須立足於文明的價值內核,唯此才能確立中國式現代化的當代文明位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才能獲得精神支撐。濤慕思·博格(Thomas Pogge)教授認為,當前國際關係呈現出對抗性,這不僅加劇了出現暴力災難的潛在風險,而且阻礙了道德上頗為緊迫的各種倡議與改革合作的推出。他呼籲推動國際關係向道德化方向發展,為更深入的改革奠定信任與尊重的基礎。
——主持人 樊浩 葉祝弟 張蕾
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探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
賀來|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社會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5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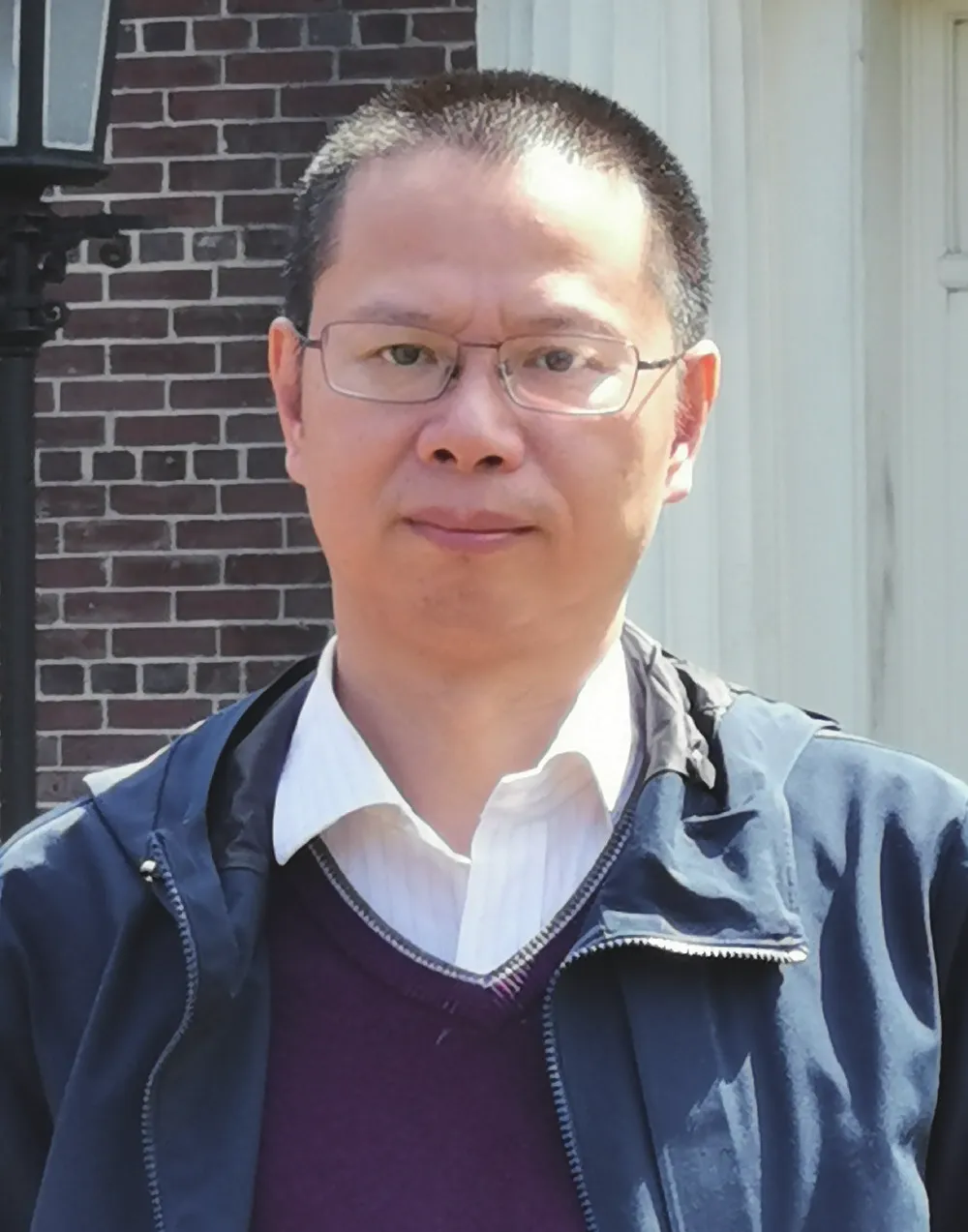
賀來
現代化是人類近幾百年來最為重大的歷史變遷,它開拓了一個傳統社會無法比擬的更廣闊和開放的空間,並對人與人的倫理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尋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是西方和中國現代化進程都難以迴避的重大倫理挑戰之一。
異質化的現代社會“共同生活”何以可能
**人的倫理生活在深層總是受到其生存方式的制約和規定。**馬克思曾指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也就是説,無論是“亞細亞”“古代”,還是“日爾曼”類型的傳統社會,人對共同體的無條件依賴構成了生存方式的根本特質。這一點決定了傳統社會人們的倫理生活必然是以共同體為中心的。然而,現代化的進程不可逆轉地終結了這一生存方式,社會生活的分化和異質化趨勢導致傳統共同體的全面解體,從而使人們的倫理生活面臨全新的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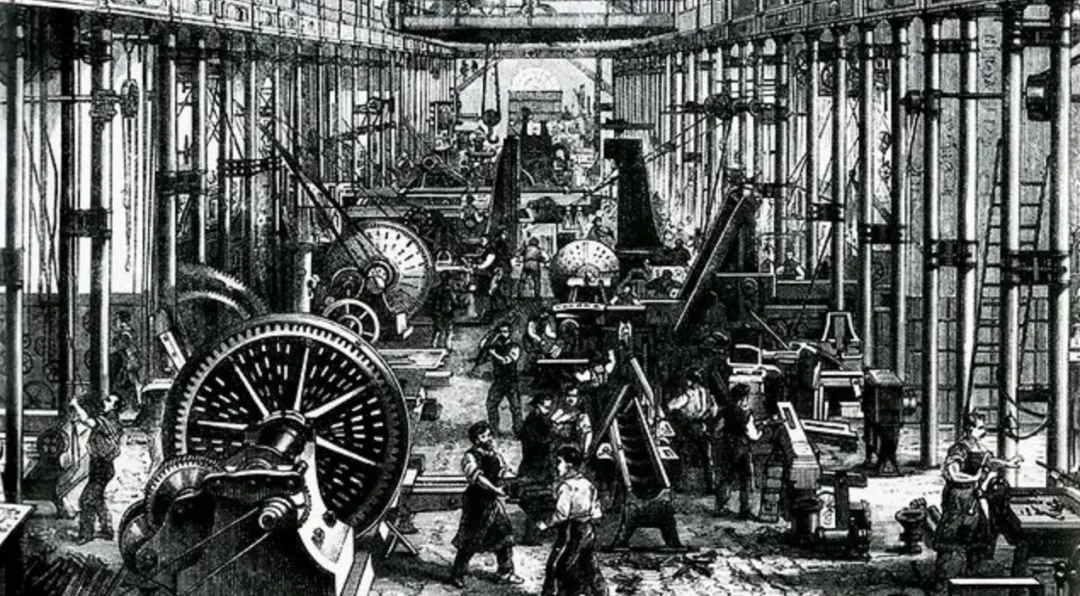
在哲學史上,黑格爾曾從“個人主觀性的自由”的角度深入闡發了現代社會的這種分化和異質化趨勢,以及由此產生的重大倫理後果。黑格爾認為:“一般説來,現代世界是以主觀性的自由為其原則的,這就是説,存在於精神整體中的一切本質的方面,都在發展過程中達到它們的權利的”,正是這種個人“主觀性的自由”,打破了傳統社會以共同體為中心的直接的、非反思的有機整體,導致希臘城邦那種“優美的統一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解體。基於這一自覺認識,黑格爾把如何實現“主觀性”的個體自由與普遍性的“倫理實體”的協調、和解與統一視為“現時代”最為根本的倫理任務,並在其《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等著作中系統闡發了他對現代社會所面臨的這一特殊倫理處境的解讀、反思和回應。
如果説黑格爾是以一種哲學思辨的方式對此進行了探討,那麼,社會理論家對此的闡發則更為直接和具體。滕尼斯、韋伯、涂爾幹等現代社會理論家以理解現代社會相對於傳統社會的重大變遷為己任,雖然他們立論的出發點和思考進路不盡相同,但他們均指出,“分化”和“異質化”構成了現代社會的本質性特徵。滕尼斯以“共同體”,韋伯以“目的論的世界秩序”,涂爾幹以“機械團結”等核心概念概括傳統社會的“未分化性”和“同質性”,並以“社會”“有機團結”“諸神的爭鬥”等概念來描述現代社會“異質化”和“分化”的特質。在這種異質化和分化趨勢形成過程中,“個人主體性”的興起被視為最為核心的因素和力量。如滕尼斯指出,與“共同體”不同,在現代社會,社會的基礎是個人、個人的思想和意志。涂爾幹認為,與“機械團結”不同,“集體意識”的弱化和由社會分工所形成的個體人格是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徵。而在韋伯看來,與“目的論世界秩序”不同,隨着現代社會工具理性佔據主導地位以及“世界的祛魅”,個人而非共同體成為價值的出發點與歸宿。當代另一個社會理論家鮑曼對上述趨向作了簡潔而深刻的提煉:“把社會成員鑄造成個體,這是現代社會的特徵。”
**現代社會的異質化和分化給現代人帶來全新的倫理境遇和倫理課題。**它意味着,人們的倫理生活不再以同質的、未分化的、前現代的共同體為中心,而是要直面現代社會的異質化和分化這一基本現實並回答:在“個人主體”成為新的倫理主體的條件下,人們共同的倫理生活如何成為可能?傳統社會以前現代的共同體為中心,人們共同的倫理生活具有無需質疑的自明性,但是,在現代社會的異質化和分化的背景下,這種自明性已不復存在。當人的身份不再基於“與生俱來”的共同體依賴關係,而是通過個體自覺的選擇和活動實現自我決定,那麼,人們共同的倫理生活如何成為可能?如何在這種異質化和分化的條件下探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
這一倫理課題的複雜性在於,**現代社會的異質化和分化凸顯了傳統社會的倫理生活所不存在的倫理挑戰:以個體化原則為出發點,如何能通向他人,與他人建立一種具有“共同感”的倫理關係?**對此,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們從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揭示。例如,麥金泰爾等哲學家指出,個體化原則必然導致倫理價值上的個體主義興起,從而使社會團結失去所必需的內在精神紐帶;黑格爾等哲學家指出,個體化原則內藴的“對象化邏輯”必將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分裂和對立,進而使倫理共同體面臨解體的危險;托克維爾等思想家指出個體化原則容易助長社會成員對公共利益和公共事物的懷疑和冷漠態度,從而使人們失去對社會團結的願望和信心;等等。
回應這一倫理挑戰,意味着要克服現代社會的異質化和分化所形成的“異質化”與“統一性”、“分歧性”與“一致性”、“特殊性”與“普遍性”、“個人自由”與“倫理秩序”等之間的一系列深層矛盾。**現代社會的異質化和分化,突破了傳統社會封閉、僵化的抽象共同體的專制,尤其它為個人的主體性和獨立開闢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這是現代社會巨大的歷史成就。**現代社會人們的倫理生活對此必須予以積極的保留和肯定,但另一方面,如同前述思想家們所深刻反思並揭示的那樣,如果個人主體性膨脹為實體化的、絕對化的存在,並使現代社會的異質化和分化趨勢喪失了必要的約束和限制,那麼,人們倫理生活共同體就將因此瓦解、崩潰。
以“家”“國”為中心的中國傳統倫理體系的限度
**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尋求人們“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這是每個追求和推動現代化的社會都需面對的倫理課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也不例外。**為此,我們需要對中國傳統倫理體系進行批判性反思,既吸取其有益的資源,同時對其侷限性有充分的自覺。
摒棄抽象的觀念主義立場,從現實生活出發來理解中國傳統倫理體系。可以看到,在這一體系中,“家”以及作為其擴充的“國”具有中心的地位。其中,**“家庭”最為基礎,“家族”是“家庭”倫理在宗法層面的擴大,“國家”則是“家族”宗法倫理在國家治理層面的進一步擴大,這也是被諸多學者所概括並闡發的傳統中國社會組織結構的“家國同構”特徵。**在“家庭”中,父子關係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從父子關係出發,進一步延伸到兄弟、夫妻關係;君臣關係雖然是國家制度層面的臣屬關係,但由於“國”與“家”具有同構性,君臣如同父子,就此而言,君臣關係實質是父子關係在國家層面的映射和放大。以家庭倫理關係為基礎向外類推,形成傳統中國社會最為重要的倫理規範,所謂“三綱五常”“三綱六紀”“五倫八德”即構成這些倫理價值規範的核心內容。在所有這些關係中,父子關係與兄弟關係是最為重要的“兩倫”,其他各倫皆是由這兩倫演化和類推出來的。在此意義上,以自然血緣親族關係為中心並向外擴展,把家庭倫理、家族宗法倫理和國家政治倫理貫通,構成了這一倫理體系的特質。無論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藴含的“外推式”倫理進路,還是“以孝治天下”所代表的倫理綱領,等等,均從不同方面體現了這一特質。

立足於今天現代化的歷史座標反觀上述傳統倫理體系,我們必須承認它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對於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認同、促進社會和諧和民族團結等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今天,它所藴含的諸多倫理價值,經過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轉化,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中仍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反思它在現代社會異質化和分化的新的歷史語境中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中國傳統倫理體系是與中國傳統社會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生活世界緊密關聯在一起的。**林安梧先生曾將這一生活世界的特點概括為“三性”,即土根性、血緣性與道德性,並指出這三者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相互融合、捆綁在一起的,鄉土性社會也是血緣性社會,同時也是道德性社會。費孝通先生則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視角出發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樣的社會是區別於“法理社會”的禮俗社會。雖然學科視角不同,但他們均揭示了中國傳統倫理體系與中國傳統的以血緣共同體和地緣共同體為基礎組成的生活世界之間的內在親和性。
正是基於這一深層根源,中國傳統倫理體系中以“家”和“國”為中心的倫理意義與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從現代性反思的語境出發所討論的“家”和“國”的倫理意義有着顯著的區別。在後者那裏,家庭雖以自然血緣關係為紐帶,但其目的是培養合格的、具有社會公德的公民,家庭最終要走向分化並進入社會,而“市民社會”以“個體的自由”為基本原則,以“個人主觀性”的充分發展為基礎。黑格爾所謂“國家”也非未分化的共同體,而是通過對市民社會的揚棄所實現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相統一的倫理實體。與之不同,**中國傳統倫理體系是以自然血緣為基礎外推而成。**對於這種通過類推所建立的倫理關係,費孝通先生曾以“差序格局”概念為核心進行闡發。所謂“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絡”,因此形成的道德是一種“維繫私人的道德”,“從己向外推以構成的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每根繩子被一種道德要素維持着。社會範疇是從‘己’推出去的,而推的過程裏有着各種路線,最基本的是親屬:親子和同胞……向另一路線推是朋友”,“中國的道德與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所謂“人倫”,“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羣人裏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如同波紋所及的距離是有限的一樣,這種倫理關係往外類推的限度就在於,它隨時隨地以“自己”為中心,只有與“自己”具有血緣親情關係,至少也是“親近”和“熟悉”的人,才能進入自己的倫理關係網絡中。“波紋”的運動距“自己”這一中心越遠,其力量越小,最終消失於無形。
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現代社會形成了一個與傳統社會有着巨大差異的生活世界,其異質化和分化的性質使之根本不同於鄉土性、血緣性以及以此為根據形成的前現代共同體。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大大超出了以親人、熟人等私人關係為軸心的關係網絡,取而代之的是流動的現代性中陌生的個人主體之間極為廣泛的社會交往關係。無法進入這一倫理網絡之中的他人、生人、外人、路人等將被排斥在外,成為“被遺忘者”甚至“被遺棄者”而無法獲得其應有的倫理價值。無論在口頭上多強調“推己及人”“四海之內皆兄弟”,只要維持這種“差序格局”,它對異質性的他人的承認必然是有限度的。
毋庸諱言,中國傳統以“家”和“國”為中心的倫理體系與異質性和分化的現代社會之間的確存在着巨大的衝突。費孝通先生説得頗為中肯:這種倫理秩序在“陌生人面前是無法應用的”。觀察今天人們的現實生活,諸如“小悦悦事件”“老太太摔倒了要不要扶”等爭論,我們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在異質性和分化的現代社會中,上述傳統倫理體系在面對現代社會不存在“私人關係”的他人時所具有的深層侷限性。
“為他人的個人主體性”:在異質化中實現“共同生活”的辯證中介
在異質化的現代社會尋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需要關注兩種抽象的倫理原則並克服其帶來的實踐困境:一是現代化進程中日益凸顯的抽象的個人主體性原則,其無限制的膨脹將導致倫理共同體的瓦解,從而使“共同生活”變得不可能;二是前現代的抽象共同體原則,前述中國傳統中的“家”“國”倫理體系是其體現,它以個人對共同體的依賴和對外在於共同體的他者的排斥為條件,這使得它無法應對異質化的現代生活。面對現代世界以及由此所導致的“異質化”與“統一性”、“分歧性”與“一致性”、“特殊性”與“普遍性”、“個人自由”與“倫理秩序”等之間的矛盾,這二者各自固執於其中的一極,均無法找到推動這一系列矛盾關係辯證和解的現實出路。
為此,我們需要找到調和上述矛盾關係、推動矛盾雙方良性互動的辯證中介。在我們看來,這種辯證中介就是“為他人的個人主體性”的培育和生成。
**“為他人的主體性”是對異質化和分化的現代社會所形成的“個人主體性”的一種改良方案。**它充分意識到,要克服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異質化所造成的新的矛盾,決不能以一種浪漫主義態度退回到未分化的、同質性的傳統共同體。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那樣:“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否則,所確立的所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將以抑制個人主體性的充分伸展為代價,它所確立的只能是一種虛假的、抽象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停留於實體化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個人主體性,如阿多諾所言:這種“主體”“永遠鎖閉在它的自我中”,只能“通過堡壘牆上的瞭望孔來注視夜空”,在這種意義上,這是一種“為己”的、把他人視為“客體”的“個人主體”,從此出發,只能導致人與他者之間的對抗和分裂,從而使得“共同生活”成為不可能。“為他人的主體性”正是基於上述自覺理解,要求在保留現代社會“個人主體性”積極成果的條件下,克服其離心和排他傾向。如果説“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那麼,“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之中,也是可笑的”,只有在“為他人”的開放性之中,“個人主體性”才能避免其陷入“完全空虛”而成為溝通上述矛盾關係的辯證中介。
“為他人的個人主體性”與近代以來的“為己”的、自我中心的“個人主體性”相比,有兩個根本區別。
**第一,它要求在與他人的“共在”中理解“自我”的存在。**按照麥克弗森等人的觀點,現代社會的個體自我實質上是“佔有式個體”,這種佔有性既表現為“自我所有”,也表現為“物的所有”,前者意味着“對自己的支配和控制權”,後者意味着“對物質財產的支配和控制權”,其深層信念是“我佔有故我在”。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這種“佔有性個體”並非建立在人與人的結合之上,而是以人與人相分離為基礎。它不僅不能確證人的真實存在,相反,只有超越和揚棄這種佔有性和隔離性,在與他人的“共在”中,人才能確立自身真實的存在。馬克思從人作為“社會存在物”的角度出發,對此進行了深入的闡述:人的生命表現,“即使不採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現這種直接形式,也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人的個體生活和類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儘管個體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類生活的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方式,而類生活是較為特殊的或者較為普遍的個體生活”。在馬克思看來,個人生活與類生活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二者的分裂所體現的是人的自我異化。揚棄這種自我異化,使得每個人既是“他自己為別人的存在”,同時這個別人的存在,“也是這個別人為他的存在”。這意味着,不是排他性的自我佔有,而是在這種與他人的“共在”中,每個人才確立和獲得其真實的存在。
第二,它強調每一生命個體通過與他人建立能動的創造性關係,生成共同的生活世界並從中獲得存在的意義和生活的幸福感。“為己”的個人主體性之所以堅持“我佔有故我在”,在於它把自我利益和慾望的滿足視為存在的意義和生活幸福的終極根源。這是現代人對個人存在意義和價值的一種片面化和抽象化理解。事實上,人作為社會性的存在,其生存狀況、生命品質和生活前景均深受人與他人之間社會共同生活的影響和制約。因此,只有通過實踐活動,創造一種合理的社會關係,每個人的存在意義和幸福生活才能獲得根本的保障。因此,投身和貢獻於這種社會關係的創造,是個人真實的主體性得以生成的重要內容和標誌。對此,近代以來的不少哲學家已做過深刻的反思和闡發。例如,美國哲學家杜威把現代社會以佔有為目的的個人主義稱為“舊個人主義”,認為其極端膨脹恰恰使個人失去了真正的主體性。他強調:“個性的穩步恢復伴隨着舊的經濟和政治個人主義的廢除——它將解放我們的想象力和幹勁,從而使合作的社會有助於豐富其成員的自由文化”,區別於“舊人本主義”,這種着力於“個性恢復”的個人主義是一種“新的個人主義”,它意在消除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因而可稱為“社會的個人主義”。再如,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通過對近代以來狹隘的“主體性”觀念的反省,強調應把人的“主體”描述為“同中之他”,把與“他者”的相遇視為“主體”的內在構成要素,把對“他人”的責任視為“主體性”的確證與自覺。這種區別於“自我中心主義”的“主體性”,列維納斯稱之為“為他人”的“人本主義”。儘管這些哲學家的出發點和思路有區別,但在強調對他人的開放性和在創造性關係中重塑“個人主體性”的努力上,他們展現出共同的旨趣。
從上述簡要闡發可以看出,“為他人的個人主體性”體現出內在統一的雙重關切:一方面,它對異質化和分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現代個人主體性這一歷史成果充分肯定和珍視;另一方面,它對個人與社會以及與之內在關聯的“異質化”與“統一性”、“分歧性”與“一致性”、“特殊性”與“普遍性”、“個人自由”與“倫理秩序”等之間相輔相成、相互滲透的辯證關係給予注重和伸張。它要拆除個人與他人之間截然分隔的藩籬,溝通上述一系列矛盾關係,推進它們的辯證和解,並強調只有在這種辯證關係中,那種既充滿個性,同時又通過自由的交往、合作和聯合而形成的共同生活才成為可能。
**“為他人的個人主體性”為異質化的現代社會中人們追求“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提供了一種辯證中介。**其出發點雖是“個人主體性”,但着眼點和落腳點在於探求“主體間”良性互動的合理倫理關係。我們相信,通過人們的實踐活動,不斷培育和生成這種新型“主體性”的過程,也將是人們共同生活的倫理之道的創造和呈現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