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會(六):怎樣超越“羞恥感”_風聞
死理性派-死理性派官方账号-“死理性派”是一种信仰,致力于从荒诞中寻找理性,从虚无中看到……55分钟前

文:阿水,慧敏,阿想,玉崽
(本文為多人合作產品,讚賞及一切相關收入由幾位作者平分。)
如果感到“無法自洽”,或許我們不該懷疑自己的行為,而是懷疑當下信奉的那些理論。

玉崽:
説到“羞恥感”,我的經驗格外豐富。寫這一篇的觸發因素是被慧敏説“不自恰”,我先是感到羞恥,驚慌失措,然後嘴硬為自己辯解,最後才安慰自己説“掩蓋沒用,也掩蓋不住,既然説出來了,那就承認,再慢慢調整自己吧”,就想着追問慧敏關於“不自洽”的細節,於是有了之後的交流:
敏:“你在**《與男性戀愛不是‘背刺女性’——怎樣做自洽的女性主義者》**中引用上野的話説‘女性世界的支持已經足夠’,那麼理論上,男性的看法對你是不重要的,但你依舊關心男性的想法,很渴望來自男性的理解與愛,這種渴望是需要接納起來的。”
我:咋説捏,我只能説不知道怎麼緩解這種矛盾,太多男性的做法讓我失望,我當然會不願意去“多瞧”他們,就像你説的“低段位男性我看不上”,在與男性相處時,如果我為他付出了,發現他“不值得”,會有“嘖,又讓男性佔到便宜了”的感覺。比如我希望我爸爸能理解媽媽的付出,但他就是看不見,我覺得憤怒,為媽媽不值。對男性的絕望無法緩解,所以想看看“全女是否才是出路”。但我強烈的想要男人理解女人,因為我想讓女人的付出被看見不被埋沒。這是在意男人嗎?我不知道。就像你,你為前任付出了太多,我非常怨恨他“佔了你那麼多便宜”,我極度怨恨男性也是因為他們得到了太多,我無法做到不功利。我氣極了,無法做到對男性的剝削行為釋懷,裝瀟灑。男性也是父權受害者,男性不全是壞人,但具體的男性就是傷害到了女性,我無法停止憤怒。為了讓自己找到出路,也是為了很多如我一樣的女孩找到出路。有時我強烈的想找到問題的解決辦法,所以才一直去看社科,但超累,效率不高。
敏:你的爸爸大概率一輩子也看不見你與你的媽媽,因為底層的感受與基礎價值觀硬件化的身體的事情,讓老男人發生改變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如果你擁有了非常好的社區,在這個社區中為媽媽創造一個位置(讓媽媽與你做鄰居同時可以擁有好的經濟來源,讓你的一些朋友成為她的密友),那麼,即使不離婚,她也會在社區中獲得許多支持,她會自然地疏遠丈夫,對自己更有信心。
我們不能把“女性社區”理解為“養老社區”。“養老”意味着只消耗而無法創造價值,生命力就是有限的。我們需要可以創造財富的女性社區,讓各種年齡段、擁有不同愛好與特長的人都可以在社區中找到創造財富的方式,感到“這裏真的比別處好”,這個開放式社區不需要排斥男性,只需要讓女人感受到“有他是錦上添花,沒他也沒關係”就夠了。當然,壞人在這樣的社區中會被排斥,他們自己會慢慢離開的。
相關鏈接:“開放式社區”的理論與實踐初探
我:明白的,我想為此努力。我倒是非常願意把自己的所有矛盾展現出來。
敏:這就是“幫助自己的同時幫到別人”啦!我們可以把憤怒的力量轉化為創造力,想辦法幫到更多的女人,讓她們即使戀愛也無需因為恐懼而額外付出,這也是創造。這是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改變世界。
我:我當然想,但總是氣餒,一想到任重道遠,就覺得腿軟了。我並不堅韌,遇到點負反饋就容易累,如果在過程中能慢慢自洽就好了。
敏:負反饋與身體傷害給人的影響是相同的,被捅刀子之後一定會累,這是人性,不是你的問題。每次感到疼痛時就找我或更多女孩説話就好了,女性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關愛自己。
我:嗯嗯,現在我們就是在關愛自己哈哈。想起來我在一開始就和你説過我會立人設,我並沒有自己説的那麼大方,如果有人發現我並沒有多自洽,沒那麼善良,不像一開始那麼支持我喜歡我了,我第一反應是想到“糟糕”然後心理壓力很大,讓我平靜的方法是遠離,但這解決不了問題。怎麼辦呢,我不知道迴避到什麼時候才是終點。
敏:看到有刀子捅過來,立即迴避一下是有必要的,否則我們就會受重傷了。所有人都會這樣。這不是你的問題。這壓根不是問題。善良的人才會説“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善良”。如果支持你的人太少,那麼,任何負反饋都會把你嚇到,但如果支持你的人很多,負反饋的傷害力就有限了,甚至,受傷後獲得的別人的支持會給到你特殊的創作動力。
我:所以説我的愛太匱乏了。就比如現在吧,你們發現我沒那麼自洽,我瞬間驚慌,然後變得好累。寫文的熱情沒那麼多了,誰傷害了我嗎?沒有,但我就是會慌,然後累,迴避。
敏:如果我只愛光鮮好看的你,那我肯定是不愛你。
我:但我沒自信有人會愛不那麼光鮮好看的我,所以只敢展現好看的一面。沒有愛,所以哪怕是假的,也想死死抓住。
敏:你太完美的話,別人會嫉妒你、攻擊你的。人們能發自內心去愛、去付出的對象一定是有缺陷、不完整的人。
我:可我覺得自己的缺陷挺多的,我害怕被人發現所有的不足,然後説“呀,你現在怎麼是這副樣子,我當初真是看錯你了,你真會裝啊。”
敏:如果這些缺陷都展現出來,你的許多關注者大概就會過來與你交朋友了。正是因為你掩藏了自己的需要,別人才會誤以為“玉崽太完美了,她不需要我”。
我:如果這是出路的話,我好像會放鬆一點。
敏:一點一點剝掉自己的鎧甲,把容易受傷的血肉之軀展現給世界,你將因此獲得擁有“鬆弛感”的人生,由此讓更多人看到自己的真實。一切真實的都有價值,特別是你的眼淚。

來自韓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
與慧敏及更多女孩交流後,我的腦子越來越明白自己的不堪不是錯的,就像我不覺得女孩男孩們的脆弱是錯的,但我的身體還是強烈地害怕別人因為我的不堪而攻擊我。我得到的支持太少了,也對別人沒有信心。我當然期待有人接納我,想真實地感受到有人擁抱我的軟弱,拼湊起我的破碎,但又不敢想象細節。每次與你們聊完都會舒服一陣子,我也很珍惜這種安全放鬆的機會,只是緊接着又是洶湧的羞恥,我有點後悔和人這樣哭着談心,覺得狼狽,尷尬。
我在想,對方在和我交流時會不會首先記憶起我哭的模樣,會不會覺得“玉崽真麻煩,真糟糕”。到下一次交流的時候我該怎麼辦?我的出路在哪兒?在寫這篇時我每刻都在想:“要不算了,好難寫下去,我太害怕了。”直面自己的內心真的相當痛苦,眼淚像進入了梅雨季一般無休無止。我會想,我走了這麼遠的路,付出了這麼多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打碎自己再重塑,為什麼還是無法達到內心的富足。

來自韓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
總有人羨慕我年輕,説:“年輕好啊,二十歲思想覺悟就這樣了以後一定前途無量!”。可我完全不覺得自己的二十有多美好。日子每一天都充滿迷惘,身體每一刻都坐立不安,我格外想成為身邊那些比我大十幾二十歲的人,她們不論怎樣都一副遊刃有餘的樣子,眼睛裏的亮光讓我感覺不可思議。
現在我再一次溺水,我説出來了,我想大聲喊:我好難受!我想被支持!但是,真的有人願意救我上岸嗎?此刻我感覺自己最裸露的不是脱光衣服,而是在你面前流下了眼淚——我在赤裸着求擁抱,我想被你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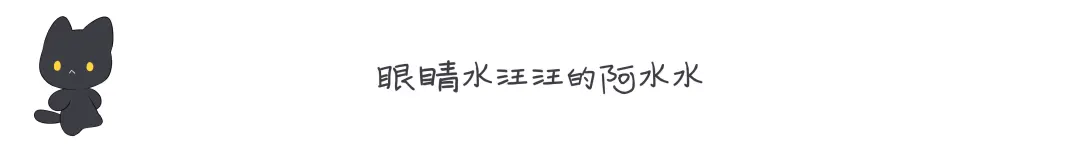
阿水:
我愛任何樣子的你。這不是縱容,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你渴望愛也渴望被愛,甚至為了讓別人愛你而逼迫自己強行奔跑。你的脆弱讓我感受到你的真實,你是需要幫助的,如果你強大到被傷害也無所謂、不被愛也無所謂,我們就沒辦法愛你了:這樣的人太完整了,不需要別人的愛。
這種愛可以説是無條件的,我知道你受了傷會難過會哭,我知道你想要立的人設與自己的真實南轅北轍,我知道你不完美,我愛的就是這樣真實的你;這種愛也可以説是有條件的,你的善良和愛的能力註定了我會愛你,如果這個基礎改變了,可能我們都會離你遠去——但你的善良與你瞳孔的顏色一樣難以更改,這是你生命的底色,所以我永遠都會這樣信任你。
我又想起來前幾天分享給你們的歌《行走的魚》:
人們傳頌勇氣
而我可不可以
愛你哭泣的心
……
別後退 聽我説 人們愛 你的光
我偏愛 你的黑 你的笨 你的錯
用瑕疵 做我們 找彼此 的印記
沒關係 沒關係
你一定愛我不完美的心
你也説和慧敏聊天是一個“安全放鬆的機會”,你願不願意放下防備向信任的人展示真實的你呢?把肌肉放鬆下來,卸下面具,或許會更加舒服呢。小動物的傷口本身就會激發善人的愛意,你也是一樣。如果説,如果真的有人説“玉崽真麻煩,真不堪”,那就遠離ta,ta不是適合你的朋友,至少還有我們在愛你。
我在二十歲的時候很迷茫,現在二十七歲了依然迷茫。很早之前互聯網有一句話“我像趴在窗户前的蒼蠅,前途一片光明,卻找不到出路。”,我感覺我就是那隻蒼蠅。從初中、高中、大學,甚至一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我未來會做什麼工作,是否會結婚,在我父母沒有勞動能力之後怎樣給予支持。我的大腦轉個不停,但是又完全演算不出結果,我不知道答案。我也曾深陷抑鬱,那時雖然知道生活很美好,但我感受不到——感受不到活着的意義。

電影《怦然心動》劇照
我在近幾年的狀態越來越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離開了糟糕的關係——包括友情和愛情。我跟越來越多能給我正反饋的人交往,ta們讓我更自信,也更自洽。你不用去改變什麼,無需強求,愛你的人自然會留在你的身邊,不是因為你多強大多完美,而是因為你是你。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未來的路怎麼走,但我知道今天的路怎麼走,怎麼讓自己開心。如果把握好當下的每一天,就能創造美好的未來了。
不用去羨慕比你大十幾二十歲的人生狀態,二十歲好就好在身體機能處於人生的巔峯,如果在二十歲鍛鍊身體,三十歲就能收穫健康,如果在二十歲用最好的記憶力閲讀大量書籍,三十歲就能收穫相當龐大的知識量,在二十歲交足夠好的朋友,説不定在三十歲就能有一起共度餘生的好閨蜜。在二十歲思考人生,在三十歲把握人生。種下一棵樹最好的時機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

阿想:
此時此刻,我在體味着一些羞恥感。
我的腸胃,我的肌肉,我的感受,我的思想,所有和我相關的都不夠完美,甚至不足以支撐我獨自面對工作和生活。
我不知道我之外的有缺點的普通人會不會在下列情況感覺糟糕:上班時忽然胃痛無法如期交付任務;工作中被強烈的恐懼情緒裹挾,平時簡單的任務也看起來比泰山更可怕,不得不去廁所躲進生與死的漩渦;被焦慮抑鬱狀態控制時,別人怎麼勸導都無法相信活着是有希望、有意義的,諸如此類。
周圍的家人朋友在嘲笑弱者的時候,我常常感到非常受傷,為自己也是一個弱者感到羞恥。可是為何明明自身也不是金字塔中上層的他們,這麼信奉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呢?我不敢告訴他們我感到糟糕,需要陪伴和幫助,因為他們的話可能會讓我更加質疑自己的感受是否合情合理。
慢慢地,我在男友身上也發現了這一點。他是個難得的善良的男生,跟外邊的流浪動物大都可以很快建立友好關係,很招小動物喜歡。可是面對痛苦的我時,他仍舊會指責我是“鑽牛角尖”,後來他説不會再試圖改變我,我感受到的也不是接納,而是失望,他不想見我了,離我越來越遙遠了,每每這樣想,我就會悲傷得無法呼吸。
我曾被許多人指責“鑽牛角尖”。我從小學就開始痛苦地思考人生的意義,那時我真的很想成為哲學家,理解所有這些問題。曾經有許多人説我“鑽牛角尖”、“想太多”,試圖勸説我停止思考失敗後,就慢慢都遠離了我,留我一個人對抗巨大的無意義感。
我孤單了很多年。我的青春期沒有玩耍,沒有遊戲,沒有同伴,家人在心理上遙遠的地方沉默着,無法理解我為什麼活不下去。有時我會做夢,夢見自己是水裏的怪獸和各種非人形象,可能實在不想做人了。
被別人貼上標籤,被孤立,那些扎心的詞與我有關,我因此感到羞恥。
在我當下的這個工作環境裏,大家都忍受着很大的壓力,加班常態化且不容拒絕,帶病工作從大家學習的典範變成了對大多數人的日常要求。正是這種氛圍,讓我感到身體弱是可恥的、需要感到羞愧的,如果要再請病假耽誤工作簡直太丟臉了。
一位與我做着類似工作的男性朋友説,如果他不在崗,領導會讓他同事代他完成工作,於是他隔三差五就會請病假,去醫院以腸炎為名掛個號拿點藥,反正不扣工資。但我就不行,因為工作分工明確,時間節點也很重要,上午請病假去看醫生,晚上就要加班熬夜,搞不定就太可怕了。無法想象自己對領導説“我做不到”的畫面,**無法應對領導從態度到能力各方面的質疑。**他們説,“做不做得完一定是態度問題,做不做得好可能是能力問題”。

電影《奧麗芙·基特里奇》劇照
前面講到的是對自己能力,身體,情緒的羞恥。還有對外貌的羞恥,聊這部分格外讓我感覺不適。昨晚聽到路邊有隻小喵喵淒厲求助,於是花了很長時間尋找它並將它餵飽,回來後太累就沒洗頭,但今天男友要過來給我的喵喵“咕嚕”洗耳朵,夜裏便因為擔心被男友嫌棄頭髮的味道而做了一宿惡夢。印象深刻的一個是頭髮異味被討厭,還有一個是面試前居然頭頂前額一大片頭髮沒了禿頂了。我沒想到自己對禿頂的恐懼這麼嚴重,我爹禿禿的小腦袋可能也以基因形式傳遞給了我麼?還有我對自己真實的蓬鬆易炸毛的頭髮好像也不夠接納,所以她們要在夢裏離我而去警示我麼?
我又聯想到,小時候被一直外出打工難得回次家的我爹説“你怎麼能黑成這樣?你走路為什麼不能站直?”,其實在他説之前我照鏡子時都感到了一些不公平,為什麼我沒有別的女孩子柔軟的頭髮,白皙的皮膚,亮白的牙齒?我最愛的小姨看到我黃黃的牙齒懷疑我沒有刷牙,提醒我要好好刷牙,我好委屈,明明刷牙老認真了好嘛?初中也曾有一個男孩也非常認真地跟我説,你牙齒太黃了,要刷牙才行。每一次聽到這樣的話,對自己的討厭就會加深一些,我想變成隱形的人,至少越小越好,所以會自然地低頭含胸。
我後面遇到了一個諮詢師,她認真地跟我説“你很美,哪怕第一次視頻,你穿着睡衣極度抑鬱的時候,我都覺得你很美。”這些話慢慢拯救了我跟人視頻時面對鏡頭極度的羞恥感。而且喜歡我的朋友可以給我拍出美美的照片,我也可以給朋友拍出美美的照片,這些都讓我相信,在充滿愛的眼睛裏,我是美的。

慧敏:
在讀到阿想這段文字之前,我剛與玉崽有個短小的交流。玉崽説覺得自己這陣子負能量太多,雖然很想一直寫下去,但是很害怕給我們添麻煩,或是讓我們逐漸不喜歡她、疏遠她。當時我對玉崽説:“如果我們的作品只有‘正能量’,其實多數人是無法共情的,略讀幾段就會感到厭煩。你的孤獨與糾結才是千千萬萬有血有肉的凡人正在真實經歷的東西,你展現真實的痛苦,並在互動中慢慢成長,這正是給讀者樹立的最好的榜樣呀——不是因為‘完美’才被愛,而是因為你是人,所以我們相愛,並用這愛把每個人的脆弱接納起來。”
我還想到了二十歲的一段日記,當時我與一個老男人糾纏不清,為自己的“精神不獨立”、“不上進”感到自責,寫道:
突然想到了可憐的父親,對女兒的情況一無所知,只知道苦口婆心的勸“好好學習珍惜青春把這類事情就放在邊上”,我回答得很好,可是一點都沒有做到,非要身邊有個穩定的男人才罷休的樣子。父親對我本無所求的,但是我,也太不肖了。
為什麼感到羞恥的時候會覺得愧對父親呢?事隔十多年仔細回味,我發現,我媽媽是從來沒有攻擊過我“不獨立”的。
**我爹是父權社會向我灌輸羞恥感的中間人。**這大概也是當代女人無法忍受“爹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我想到之前曾經讀過一些論文,説儒教文化是恥感文化,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前者讓人監控自己的行為,只能將自己好的一面展現給世人,壞的一面只要藏好了就行;後者則讓人監控自己的思想,哪怕什麼都沒做,只要有了某個念頭就要開始自我審判。按前者的邏輯,只要自己一直以來的在外人眼中的行為是無可挑剔的,那麼人就可以不用感到羞恥,所以便利的方式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於是有了**“划水文化”);但是按後者的邏輯,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我們需要有所作為**才能贖罪。雖然我同樣不認同罪感文化,但是,“恥感”更大限度地束住了我們的手腳。
內在羞恥感的外在表現便是對面子的執着追求,我們的大樓越來越高,馬路越來越寬,衣着越來越光鮮,內心卻依舊空洞。我們中的許多人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變成了只有面具的軀殼,想要內外兼修的人發現自己似乎永遠也達不到那些高不可攀的標準。

圖片來自互聯網
我們都有過努力維持某種人設的階段,那時候我們在外人看來或者許高冷、或許八面玲瓏步步生風,但自己的感受都是一樣的孤獨而恐懼,因為我們感到自己內外不一,我們害怕別人觸到自己的面具,害怕面具下面的真實暴露到陽光下,害怕失去一切——但是那時的我們究竟擁有什麼呢?
我的救贖來自莎莎和你們這羣好朋友。我們昨天半夜還發生了這樣的對話:

圖片來自互聯網
我:(玩了很久的遊戲才關燈進卧室,之後説:)我好害怕這屋子燒起來……
莎:怎麼了?
我:我明明什麼都沒做,就在那玩枯燥的數獨遊戲,想到那些不愛妻子的丈夫們下班後即使早回家也要在車裏坐半天,我就想,要是你因此説我不夠愛你,我好像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證明自己。而且你還在不遠處做家務、照顧貓咪,老覺得你要開始原地爆炸,説我不體諒你……
莎:然後就越糾結越停不下手裏的遊戲,越玩越害怕,就像懷裏抱了個煤氣罐子一樣……
我:是啊
莎:我是內耗大師,我最懂這個了。
我:那怎麼辦啊?
莎:那就學輝輝虎,被嚇到就來個後空翻(輝輝好幾次探索新事物的時候被小動靜嚇得後空翻,莎莎説的時候模仿了一下,逗得我大笑)
我:(撅嘴)我不會啊
莎:那我給你買個煤氣罐玩具,你抱着玩
我:啊啊啊……
莎:那我下回如果從你旁邊過,就過去親親你、摸摸你吧,告訴你一直玩也沒關係。如果我想要你幫我分擔什麼,我就好好跟你説。
類似的對話在我們家發生過許多次,我一直都在慢慢變好,也可以迅速學會用她對待我的方式對待別人,但是自己內心最深層的感受是很難發生變化的,對於這種**“感受與思維的不夠匹配”,我想,最需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多與人交流吧——越交流越會發現,只要説到最內在的感受,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並沒那麼大,年近四十的我在處理事情時確實比二十歲時更從容、更有底氣,但我永遠有自己的知識盲區,永遠會犯錯,每次碰到任何問題,我身體的反應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一直以來的固有模式,這其實也是身體幫助我們記住過往的方式,是高共情的人們擅長換位思考的重要原因。**
過於強烈的自我懷疑也是我們正在被身邊的某些人打壓的證據(比如親戚、伴侶或同事),豐富而持續的正反饋可以幫助我們逐步減少自我懷疑,越來越堅信自己的身體感受。如果可以對自己樹立起信仰來,我們將終有一天為自己創造出更好的職場與家園,不再需要“一口毒藥一口解藥”,而是真正生活在空氣清新、有毒物質極少的新世界裏。

玉崽:
水水和慧敏的話讓我好安心。最近我開始感到自己是真的被愛着的,我的缺陷也是有人願意接納的。
你們反覆説“胡説八道也沒關係,抓狂也沒關係,你什麼樣子我都能接納你、擁抱你、愛你”,我從中感受到了一種力量,説出自己的傷痛似乎不像以前那樣困難了,面對自己的“奇怪”似乎也更容易了,雖然眼淚還是有點止不住。
我下面的話是在慧敏發出上一段之前打出來的,結果突然發現我接下來想説的是與你們共通的感受,這讓我感覺恍惚,好像是在與自己對話,這種奇妙的感受讓我心跳加速。原來我並不孤獨,原來我的感受竟是千萬人的感受。
我和阿想一樣,曾經也認為情緒動盪、身體孱弱是可恥的。但真正可恥的是資本主義“效率第一”的單一尺度。當人成為“勞動力商品”,原先體現了光輝人性的情緒情感都成了資本眼中的“不穩定因素”。這就是社會對人的異化。現在我常常因為這片土地不允許有gap year,女人懷孕後還要繼續工作七、八個月而感到強烈的憤怒。
“時間就是金錢”這一觀念只有非常短的歷史,卻深深荼毒了幾乎所有人的心靈,催着我們趕緊啓程,哪怕我們身體超負荷,哪怕我們連去哪兒都還沒搞清楚。
消除“恐弱”心理是個艱難的過程。當我慢慢知曉與“慕強恐弱”相關的投射性認同,我開始厭惡“慎獨”文化,練習在“躺平”時安撫自己。
最近羣裏有人説:“如果可以有一天不用思考這麼多問題,大概也是一種足夠幸運的證明吧。那就是説作為弱者的我也可以安心的活着了。作為一個俗人不那麼計較的活着可能也是一種比較美好的平庸吧。”
我很有共鳴,回應她:“最近我也想了很多,時不時抓狂,感覺自己狼狽得要命,不得不去思考自己的所有‘奇怪’,剖析自己的衝突,慢慢理解並接納自己的情緒、慾望與需求。如果做一個脆弱的人也可以安心地活着,這真的太幸運了。我期待‘一事無成’的人生,想要漫無目的地尋找有趣的東西,就這樣慢慢變老。‘穩定的情緒’與‘要健康的體魄’被認為是‘體面人’的標配,但是,如果真的‘修’成了沒有感情的勞動機器,‘我’就不再存在了。”
我或許永遠不會“心安”,我在變得更加敏感,在聽到“不可控”“不可開發””不健康”“不創造價值”“沒有幹勁”等詞彙時開啓自我保護,我想,對外“炸毛”總比對內攻擊(感到羞恥)更好一些。
我有在變好,我要為此刻的自己感到驕傲。

來自韓劇《我們的藍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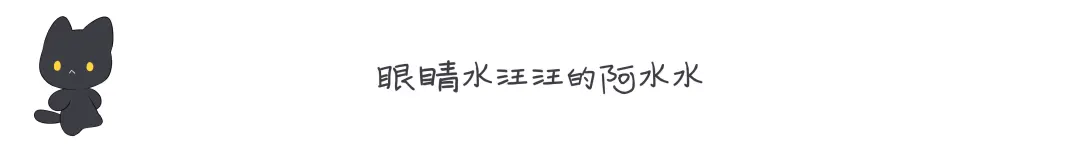
阿水:
最近咱們開始對話式寫作,對象特別積極地想要看我們的作品,在這個時候我就特別特別羞恥,我緊張、激動、害怕,擔心自己是不是寫得不夠好,會不會低於或高出他的預期,把他嚇一跳。他現在要通過文字的方式瞭解我了,我們從來沒有這樣交流過,這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他自己不寫作,這會不會導致我們疏遠?我不知道。
類似地,對很多人講述自己的看法時我會覺得羞恥。我知道我在每個人心中的形象都不一樣,現在要把ta們聚在一起,向一大羣人開誠佈公,好像是在對着公眾解剖自己一樣。舞台中間的我會臉紅,不敢直視觀眾的眼睛,害怕一個出戏就不知道接下來要説什麼了。
另外,我在性高潮時特別有羞恥感。在這個身體失控、心靈敞開的狀態下,我擔心我的表情是否太過猙獰,我的身體反應是否太過誇張。所以我都緊緊地摟着伴侶,要麼把自己埋在他懷裏,要麼把他的臉藏在我肩膀後。
我想我們的這些羞恥感都是來自內在慾望與外界規訓之間的衝突。社會要求我們心智強大、穿好鎧甲、不露軟肋,要求我們**“存天理,滅人慾”**,做聽老師話的好學生、聽父母話的乖子女,工作之後通過服從性測試將我們訓練成為會忍耐、會為公司貢獻的好員工。我們的人生被抽象為讀書、工作、結婚、生子、老死。女人則被賦予更多不合理期待,被要求賢良淑德、相夫教子、白瘦美、既上得了廳堂又下得了廚房、20歲生個娃30歲不能再有性慾(因為男性能力不行了)、老了還要帶孫子孫女…… 恨不得是一個全能的機器。
可我們是人啊,人怎麼可能沒有自己的慾望呢,如果凡事按照社會規訓我們的來,豈不是早就痛苦死了?!社會對你説的這樣那樣,其實就是為了讓你產生羞恥感,讓你產生假象:我這樣是不對的,大家都沒有這樣做。我這樣不夠乖,不夠聽話,會被人討厭的。
可我偏偏不要這樣,我發現,我們去做社會不想讓我們做的事情才會給我們帶來快樂,社會要學生好好學習,我上課最愛發呆胡思亂想,胡思亂想至少讓我在學生時期減少一些痛苦。社會要人社畜一樣的工作,我偏偏準時下班到點就走。就算我瘋狂加班又怎樣呢?只是變成了一個在老闆眼裏聽話、好控制的員工。社會要女性保持貞操,從不宣傳衞生棉條,我就要把棉條推薦給所有女同學,從知道棉條這個東西后再也沒用過衞生巾。社會説25歲是女性最好的生育年紀,**但二十五歲做什麼不是最好呢?**撿垃圾都比別的年齡段的人撿得多。
“羞恥感”是社會規訓我們的工具,想要我們穩定、服從、忍耐、安然接受被奴役的狀態。我們需要保持清醒,多與給自己正反饋的人交往,慢慢將“自信”建立起來。

阿想:
慧敏説的“恥感文化”讓我感觸良多。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小學一、二年級學騎自行車的經歷。當時那個自行車是老式的帶橫樑的自行車,非常高,而我還是個矮小的小不點兒,跟本不可能像大人那樣騎車,只能把右腿從自行車主幹的三角形結構中間伸過去,側着騎車。第一天我試着自己學,毫無進展,第二天爸爸就教了我一陣子,不過是扶了我二、三次,見我沒有成功,他就一直羞辱我,説我“笨死了”、“學了半天還沒學會”,我感到非常羞恥。
如果有什麼事情我不得不做卻沒有做好,就會有強烈的羞恥感,與慧敏一樣,早期爸爸對我的打壓、諷刺是我的重要恥感來源。在跟着他學了半天車之後,我再不想讓他教我學車,而是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悄悄努力練習,逼着自己學會了騎車。

圖片來自互聯網
後面這種感覺就延續到了其它許多事情上,我成了大眾口中的“要強”的人,內心不過是害怕被嘲諷、被排斥罷了。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因為工作感到非常焦慮、抑鬱、低落,朋友説,你是可以放棄這份工作的,你可以去開個花店或者是任何讓自己開心的事情。但是我就無法想象有什麼事情是“我想要的”,或者可以讓我開心的,做什麼都困難重重,我無力應對。
因為害怕追不上別人、害怕被父母所羞辱,**我一直在做着家人覺得很正確的事情。**我因此迷失了自己。
玉崽説的“浪費時間可恥”也對我影響很大。我無法一個人安心地在週末睡大覺,除非有一個人陪着我一起睡,並在我本來後安撫我“又浪費了時間”的慌張與自責。越是這樣越是渴望沒心沒肺的睡眠,因為以結果為導向的風氣讓我對一切都失掉了興趣。就算不討論“反正都要死掉”,僅僅是日常生活的不確定性都會讓我輕易陷入絕望。
我在去年此時漸漸喪失了很多社會功能,不敢停下來休息,直到一位諮詢師問我:“等待沒有意義麼?”我才漸漸發現等待也是有意義的,有時就算放手,事情也是可能解決的。
現在心情糟糕時,我會出去漫無目的散步,自己不同材質的鞋跟落在不同地面上的聲音,路邊的花花草草,天空的雲或者下個不停的雨,都可以陪我度過難熬的時光,偶爾邂逅的貓貓、狗狗、小朋友、幫我一把的小妹妹或是大姐姐也會加深我與世界的聯結。

慧敏:
阿想説那個職位與自己相同的男性在“經常請假”這事情上沒有障礙,阿水現在也可以做到“下班就走”,阿想表面上似乎有更多的不得已,但其實怕的是失去目前的社會支持系統,同時暫時沒有釋放出自己的全部攻擊性——“敵意”是一種信號,如果讓自己更加“瘋”一些、多“原地爆炸”幾次,我們將有可能對“我想要什麼”做出更讓自己感到滿意的回答。
回想二十年前,我最嫉妒的是別的女孩擁有別人的關注與愛,於是我執着地追尋愛與被愛,也曾經被無數人説是“分不清輕重緩急”,但現在回頭,我的慾望事實上引領着我走了一段豐富而美好的旅途。
阿水説“如果都按羞恥感的指引生活”會“太累”,阿想也確實暫時進入了這種極度疲憊的狀態,所以更加期待被關懷、被照料。只要有點兒“陽光”,阿想就能“燦爛”起來,比如去年的旅行讓你感覺很好,最近我們一羣人的交流也可以斷斷續續地給你打氣,雖然這些都遠遠不夠,但你已經在跌跌撞撞地以某種方式“向前走”了。
“結果導向”會讓你失去興趣與動力,但是,如果我們只是一起攙扶着,一起慢慢向前走,就像金草葉在《地球盡頭的温室》中所展現的那樣,不談宏大敍事,不設定宏偉目標,只是交替着邁出左腳、再邁出右腳,累了就大哭一場甚至大睡一覺,最終我們將會發現,我們創造的奇蹟很可能超出現在所有人的預料。
我們傾向於高估自己未來半年的變化,但是低估自己未來十年的變化。
所以短期計劃不如只定成“每天做一件讓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就好,至於未來,微笑着迎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