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Crunch 是如何迷失方向,走到今天這一步的_風聞
航通社-航通社官方账号-微信公号:航通社1小时前
本文首發於航通社,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航通社微信:lifeissohappy 微博:@航通社
過去的好時光有多好,現在就有多壞

文 / 書航 2024.7.16
社長的話
曾任TechCrunch網站編輯的比格斯(John Biggs)在很多年前離職後,一直經營自己的生意。他具體在做什麼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在做那種幫助創業公司的訓練營服務。他在自己的newsletter中寫了一篇批評和哀悼老東家的文章,詳細記述了他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在這十幾年間發生的變化。
比格斯在TC工作時,正是硅谷科技媒體的黃金年代,這種影響即使在他們逐漸沒落後也持續了很長時間。我就是在那個時候入行的,並且在盧剛老師的帶領下,在他當時跟阿靈頓合作引進的“TC中國”項目工作了兩年多。
我們那時仍然用自己的腦力去編譯文章,而不像現在直接喂進AI就好,根本不擔心什麼語法錯誤。如果不是AI,我也不可能在半小時內就搞定從編譯,到念出這段“編者按”,語音轉文字,再改錯字的過程。甚至貼進編輯器發佈的手動過程,現在都顯得比出稿本身繁瑣了。
當時大多數人都堅持在半夜一兩點鐘起來聽蘋果的發佈會,然後和國外同行比拼文字直播的速度。許多像小米手機1這樣的產品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布的,在國內受到了與國外科技媒體同等的待遇。
當時媒體確實默許編輯們靠車馬和禮品來補貼家用,但媒體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遠比現在健康的關係。這篇文章中所敍述的美國科技企業與科技媒體之間關係的變化,同樣適用於國內的情況。
我之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中國科技公司都要去外媒“刷臉”?》,提到
“當今中國科技企業如果真的想出海和樹立全球化的影響,還必須以英文為基準,去國外那些著名的科技媒體上尋求報道,再由國內的科技媒體翻譯回來。”
當時(我一會説具體是哪一年)的情況是:
國外媒體剛剛開始關注國內大型科技公司,報道普遍浮於表面及偏正面;
國內大眾傳媒,甚至財經媒體的科技報道都相對偏少;
國內媒體報道科技新聞主要是安全廠商提供的病毒播報、基於大數據的細分行業報告,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宣傳典型;
根據我本人的觀察,企業願意優先選擇海外媒體,這種“崇洋媚外”是因為他們早知道國內會“出口轉內銷”,不用專門拜訪。
這一年是2016年。現在想來,那正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當事情剛剛才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回頭看都是它最輝煌的時候。
當我們討論這些往事時,事情已經開始逐步發生轉變。至少在新能源汽車和人工智能這兩個領域,國內的一些主要進展會主動被外媒抓取。
但是今年依然還有往《南華早報》身上扎小人的人呢。我感覺,現在仍然對海外科技媒體心存執念的人,都是和我經歷差不多、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
現在更重要的事情都不是這些了,是“活下去”。對於創業公司,或者任何從舊日輝煌中被放逐的個體而言,“活下去”可能就是堅持做自己的事情,不因外界的影響而改變。
上TechCrunch可以成就或毀掉一個初創公司。現在同樣的權力接力棒交到了MKBHD們手上。準確地説,Marques Brownlee 剛剛用這把權杖毀掉了 Humane AI Pin。
希望一個以“小而美”起家的發聲渠道,可以儘可能縮減成本,保持更長時間的本色運營,而這又不應該以燃燒創始人的生命作為代價。
下面是那篇newsletter的翻譯:

T(太)C(蠢)了:初創公司首選的新聞發佈網站,是如何迷失方向的
約翰·比格斯
2024年7月15日
2005年初,律師邁克爾·阿靈頓和企業家基思·特爾創辦了一家名為阿基米德創投的基金。他們當時的想法是投資Web 2.0,即新興的網絡應用世界。通過這個基金,他們創建了兩個產品。一個是名為Edge.io的在線分類廣告服務,旨在模仿Craigslist在網絡上的每個站點。另一個是名為TechCrunch的初創公司追蹤服務,旨在評論每個新興的Web 2.0網站。
當時,媒體行業正在被博客作者顛覆,他們行動迅速,寫出隨意的故事,幾乎擊敗了印刷雜誌。他們摧毀了保密協議機制,建立了第一批“網紅”,催生了傳記式的訪問新聞報道,把真實評論變成了廣告聯盟營銷手段,削弱了廣告收入,並將傳統新聞業推入瞭如今正在全球崩潰的死亡螺旋中。但當時,他們真的很酷。
特爾和阿靈頓在TechCrunch和Edge.io之間分配時間,阿靈頓花費了大部分時間發佈Web 2.0故事,並向他的風投夥伴打探內幕消息。他通過在頁面側邊出售廣告位來賺錢,每月幾千美元,那些贊助商是阿靈頓正在評論的網站。最終,這些贊助商支付了足夠的錢,讓網站擴展到多個主題,包括手機評測網站MobileCrunch和我負責的數碼評測網站CrunchGear。
2006年,我為邁克創建了CrunchGear。此時,TechCrunch已經超越了大部分阿基米德創投的其他部分,讓特爾專注於投資,而阿靈頓則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了TechCrunch上。
為了迎合全球觀眾,他會熬夜到凌晨三四點,寫關於Twitter和Spotify等新服務的獨家新聞,並大聲斥責生物學專業學生馬克·亨德里克森,這位他的“合夥人”被“囚禁”在阿靈頓在帕洛阿爾託的家。當我去面試新員工時,我不得不叫醒邁克,他帶我去開市客買東西,為他當晚的派對做準備。

如果你想了解當時的生活:博主Om Malik因過度工作(和過多的雪茄)而心臟病發作。而阿靈頓自己也對《紐約時報》説他的生活方式很糟糕:
“我還沒死呢,”TechCrunch的創始人和聯合編輯邁克爾·阿靈頓説。這個受歡迎的科技博客已經帶來了數百萬的廣告收入,但代價不小。阿靈頓説,他在過去三年裏體重增加了30磅,患上了嚴重的睡眠障礙,並把自己的家變成了他和四名員工的辦公室。“總有一天,我會崩潰住院,或者會發生別的事。”
“這種狀態是無法持續的,”他説。
TechCrunch是首屈一指的初創公司新聞網站。上首頁 - 即使只是短暫的 - 意味着你的服務會增加1萬名新用户,並接到無數來自硅谷風投的電話。這就是TechCrunch的力量:它可以成就或毀掉一個網站。這賦予了我們這些年輕人過多的權力(最終讓我陷入了嚴重的抑鬱症),因為初創公司創始人需要我們來完成他們的融資。
風投會説,“搞定一個TechCrunch報道,”創始人們會聽從。一對荷蘭企業家帶着咖啡走進邁克的家,進入他的卧室,希望説服他寫關於他們宣傳的東西。傳説有一次,一位憤怒的德國企業家在一個活動上向邁克吐口水,這讓我們對人類產生了深深的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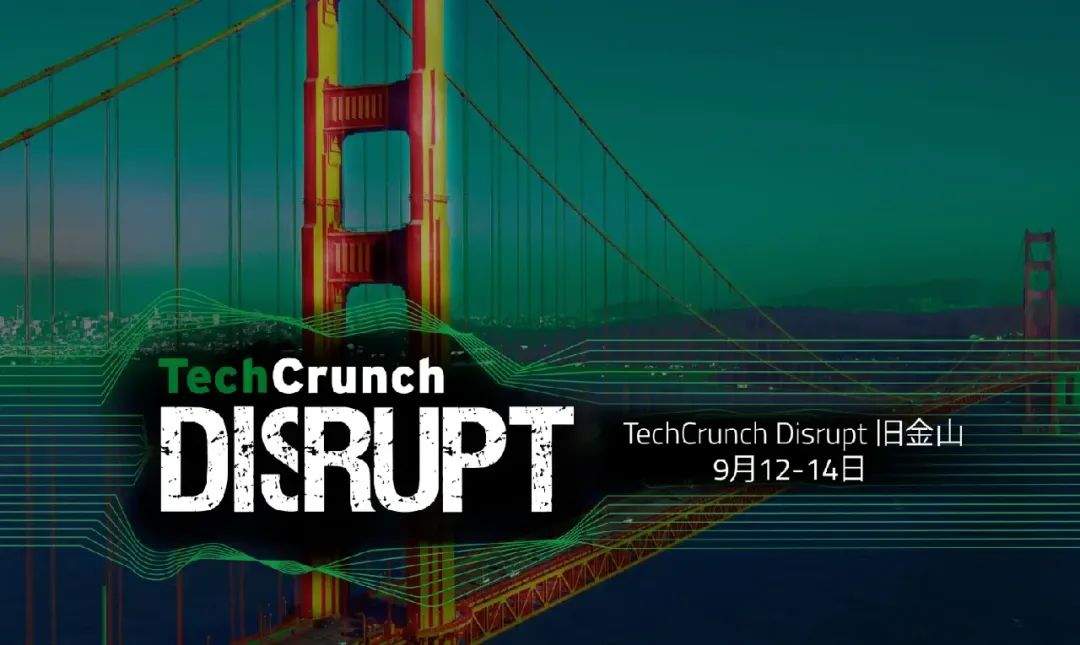
該網站在Web 3.0和移動網絡時代蓬勃發展,並逐漸形成了初創公司新聞與更深入的調查報道的慣例。它催生了全球最好的初創公司活動Disrupt,並基本定義了成千上萬創業者的推銷方式。我個人在全球各地的酒吧和音樂廳舉辦推銷比賽,作為TechCrunch的一個發現機制。那時,在2010年代初期,TechCrunch已經變得自我封閉,並專注於舊金山(硅谷)。
然而,經過(2018年後的)大衰退後,全球初創公司開始產生一些有趣的東西。舊金山的作者們通常忽視這些外地的初創公司,因為他們不認為創新可以發生在“天命之地”之外。我稱自己為東海岸編輯,並表示我的報道範圍是舊金山以外的所有地方。
這是TechCrunch的第一個錯誤。
為了讓Disrupt充滿初創公司,它需要吸引來自硅谷以外的希望者。當然,你可以把扎克伯格從帕洛阿爾託叫來演講,但像巴黎、芝加哥和特拉維夫這樣地方的小公司才是真正的客户。
這些被幾乎所有人忽視的人,覺得他們可以在Disrupt和TechCrunch的頁面上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不知道的是,舊金山的團隊主要關心Uber的下一輪投資,而我和邁克·布徹等人則把TechCrunch的福音帶給渴望被注意到的人。
這種努力變成了一種磨難。我飛到一個城市,到了酒店,吃喝太多,然後在一個活動上被困五小時,喝得更多。我們會和當地的一些初創公司和風投舉行推銷比賽,然後跑到Yount或Dizengoff街,喝着杜松子酒和湯力水,直到深夜。畢竟,我們是“造王者”。
這是TechCrunch的第二個錯誤。
TechCrunch浪費了這種權力。現在由AOL和雅虎(Yahoo)管理的舊金山團隊,專注於初創公司以外的所有事情。流量至關重要,廣告銷售也很重要,所以小眾初創公司文章——過去人人都讀的文章,現在只被公司內部閲讀——失去了價值。
隨着時間的推移,傳統TechCrunch故事的價值減少。像ProductHunt這樣的站點——TechCrunch的老闆們曾考慮收購它——超越了TechCrunch文章的影響力。
公關費用變得昂貴,所以公司採用游擊戰術來增加用户數量和更多現金。風投變得更聰明,創建了自己的推銷比賽和加速器來建立更大的投資組合。造王者不再掌權。此外,主流新聞也在報道初創公司,關注新酷的網站和數碼產品。
順便説一下,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數碼網站現在很糟糕?你可以感謝在我創辦CrunchGear之前替代我的Gizmodo的傢伙布賴恩·藍姆。
藍姆想到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概念,即他應該為每一個他的評論賣出的物品得到報酬,這導致了聯盟營銷,並反過來把數碼評論網站變成了新聞業的糟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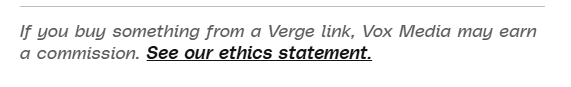
實際上,他的概念——摧毀了Engadget和CrunchGear的網站——直接導致了《紐約》雜誌等媒體寫那些為了SEO優化目的寫的音響和電視機評測,以便他們能從每次銷售中獲得2%的提成。確實令人感到不安。
但TechCrunch始終有一個優勢。阿靈頓對未能兑現承諾的初創公司,常常表現得非常刻薄。他批評Twitter頻繁宕機,基本上是他發明了“在社交媒體上抱怨”來獲得更好服務的這種方法。在CrunchGear,我們嘲笑我們認為糟糕的東西,揭露壞人,並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做了個鬼畜視頻,讓“元首”抱怨一款新的、過度炒作的平板電腦上市延遲。

隨着雅虎高層試圖瞭解如何從TechCrunch的活動部門榨取更多現金,同時關掉了TC的融媒體部門,這一切都消失了。編輯馬修·潘扎裏諾尚且可以出色地隔離高管們,實現自主編輯。但他離開後,他們急忙填補了他的缺位。結果是TechCrunch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錯誤。
經過多年的公司所有權流轉,雅虎最終被賣給了私募股權公司阿波羅,TechCrunch變成了一個温吞水的站點,專注於由昂貴的公關人員特意安排的大筆融資,和被攪拌成糊狀的隨機科技新聞。
目前的編輯結構,由一兩個老TechCrunch成員和由編輯康妮·洛伊佐斯僱傭的大量老編輯控制。曾經自由奔放的編輯策略——作者隨時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幾乎沒有人編輯任何東西——被一個更正式化的系統所取代,這個系統對那些準公關人員來説很熟悉,而任何對舊金山現有“王者”表達憤怒的跡象,都會被嚴厲處理。
這導致了最近在TechCrunch發生的事情。哈傑·坎普斯(Haje Kamps)寫了一篇文章,噴了當前的一位“王”——Scale AI的創始人亞歷山大·王對優績主義的看法。在一篇後來被雪藏的文章中,哈傑認為亞歷山大·王“是個白痴”。

(順便説一下,哈傑有一個副業,為初創公司提供建議。如果在我那時候的TechCrunch這樣搞,他會被解僱,但因為投資人和編輯之間的壁壘已經被磨損到接近為0,所以這事被忽視了。)
亞歷山大·王這麼説是想要挑戰多樣性和政治正確的原則,這在硅谷一直是一個危險的東西,主要是因為硅谷主要由白人主導,對外界要求變革的聲音只是陽奉陰違而已。白人CEO甚至不惜掏遣散費讓“鬧事”的員工離職,這導致他們公司士氣低落,但他們在賺錢,寶貝,所以一切都很好。
因此,從各方面來看,亞歷山大·王的反多樣性發言,就是廢話。哈傑用曾經在舊的TechCrunch中響亮的聲音指出了他的問題。隨之而來的Twitter反彈嚇到了他的上司洛伊佐斯,哈傑被從編輯名單中剔除。
這篇文章隨後不得不加上“編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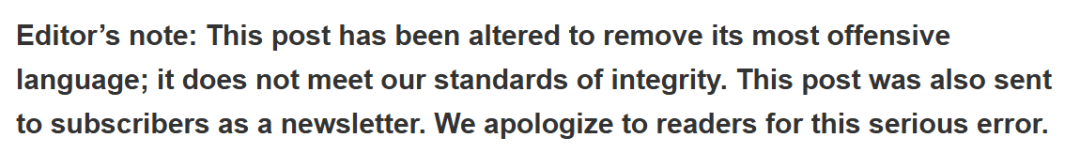
這篇文章已被修改,刪除了其最具攻擊性的語言;它不符合我們的誠信標準。這篇文章也作為時事通訊發送給訂閲者。對於這個嚴重的錯誤,我們向讀者道歉。
而在此之前,另有一些老TC人,包括凱瑟琳·舒、馬特·伯恩斯和達雷爾·艾瑟林頓被裁。這三人單獨負責了TechCrunch全球流量的很大一部分,因為他們一直在寫有趣的東西,並且已經寫了近二十年。
管理層還裁掉了大量的營銷團隊。簡而言之,TechCrunch正在收縮並變得膽怯。
洛伊佐斯必須完成她的收購,而她的新編輯們,主要是前幾年的商業媒體大裁員的倖存者,渴望保住自己的工作。TC依然是一個全球性的網站,但現在的新聞條目是幾小時一更新,而不是以往的幾分鐘,網站的價值跌入谷底。
我在《Keep Going》中經常與風投和初創公司創始人交談,他們都説同樣的話:他們不讀TechCrunch。對他們業務的價值已經消失,目前的帖子列表——從剪映用户協議變化的新聞稿——到閃閃發光的風投訪談——都是垃圾。
我認識的許多人仍在編輯部工作,且是我認為的朋友和知己,我知道並不是每個故事都是垃圾。有時金子仍然閃耀(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文章也太長了,一些有名望的編輯應該注意到這一點)。但最終,TechCrunch不再有影響力了。
這是最悲哀的事情:它本該如此。初創公司並沒有消失。任何創投媒體都可以基本上重建阿靈頓的模式,通過為初創公司做廣告來賺錢;通過揭穿硅谷吹牛者的泡沫找到樂趣;通過告訴人們如何在創業界取得成功來獲得大量內容。
但TechCrunch不會再這樣做了。它被困住了,翻閲來自同樣咄咄逼人的硅谷公關人員的新聞稿,並自認為在做有意義的工作,實際上根本沒有。
如果我掌管TC,我會怎麼做?讓初創公司報道迴歸全球焦點,忽略那些宣傳大公司的小更新的公關人員,成為風投尋找投資機會的地方。這是TechCrunch的原始魔力。通過減少編輯人數,讓TechCrunch恢復一些活力。這樣,他們在再次通過辦會賺錢,並把自己從投資人的重壓下解救出來時,可以獲得額外的報酬。
寫下這些話我並不輕鬆。我知道如果TechCrunch沒有自滿,會成為什麼樣子,這讓我感到憤怒。一個曾經增長、變化並擁抱幾乎所有人的行業,如今收縮成硅谷自負的黑洞,現在掌控着對硅谷的讚美和批評。
TechCrunch不再是一個新聞網站。它是一具屍體。這是它的最終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