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仕培的《負負得正》為什麼沒有“得正”……_風聞
四味毒叔-四味毒叔官方账号-1小时前
文 | 毛浩宇
今年的七夕檔,顯得略微有些冷清。不過,由甯浩監製,温仕培執導,朱一龍、邱天等主演的愛情電影《負負得正》定檔七夕,算是給觀眾帶來些許期待和遐想。
《負負得正》講述了27歲的都市打工仔黃振開(朱一龍 飾)懷疑自己正生活在一部電影裏,任人擺佈,但囿於自己沉默老實的性格,他無法改變現狀。直到搬到新住處後,他遇到了神秘的合租室友李小樂(邱天 飾),她的突然出現和莫名消失讓黃振開的生活蕩起漣漪,在來回搖擺和試探追尋的過程中,他重新拾起愛的勇氣。
不得不承認,温仕培導演自處女作《熱帶往事》起就已經展示出其對風格化視聽的熟練駕馭能力,呼吸感的手持攝影、低照度的燈光、細膩的聲音細節,色彩濃烈,光線渾濁,顆粒飽滿,有着復古膠片套上柔光鏡般的夢幻質感,使得視聽成為一種觀影享受。
但也不可否認,其一貫善於用情緒以及大量文化景觀符號來主導故事,使得敍事邏輯複雜模糊,觀眾理解門檻驟然抬高,而這種創作傾向也再次延續到《負負得正》中。

濫用元電影元素,是純粹的過度自戀
元電影(Metacinema)指的是關於電影的電影。狹義上,元電影包括那些在影片中呈現電影製作過程的電影;廣義上,元電影還可以指那些與傳統電影反其道而行之,不是竭盡所能讓觀眾信以為真,而是主動顯露攝影機、導演等存在,探討影像與創作者或觀眾的關係的電影。
縱觀影史,無論是吉加·維爾托夫的《持攝影機的人》、 比利·懷爾德的《日落大道》、費德里科·費里尼的《八部半》,還是張藝謀的《一秒鐘》、大鵬的《吉祥如意》、魏書鈞的《永安鎮故事集》,無一不借助拍“拍電影”的過程,表現一定的作者性反思。
因此,元電影最突出的特徵表現為媒介自反性,其哲學意義表現為,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觀看者,在元電影面前應當會反思自身正在進行的創作或觀看行為。
正如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所提出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任何一種存在,都只有在認識到自己的存在之後,才能成為一種自為獨立的存在。它彰顯了人的主體性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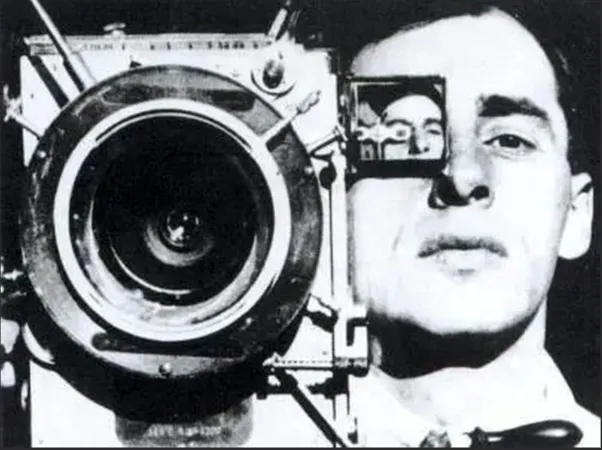
但反觀《負負得正》,卻把元電影元素作為消費符號呈現,使之變得膚淺獵奇的奇觀式表達。
電影一開場就是異世界裏的外星人在拍電影的畫面,背景白得發光,好似潛意識深處,而外星人拍電影這件事也與黃振開的主觀感受相關聯,換句話説,拍電影的外星人是黃振開內心世界的外化。
之後,下班回家,作為社畜的黃振開攤在沙發上,或許是為了爆梗或者碰瓷熱點,這時候導演又安排外星人出場,一邊拍着電影,一邊強行昇華強調“社畜也有被記錄的價值”。當黃振開和李小樂同居,感情逐漸升温之後,外星人又突然冒出來,以旁白的形式指導現場的燈光、音響佈局,場景頓時進入曖昧狀態。
再之後,主觀鏡頭注視之下,外星人驚呼兩人看鏡頭了。影片後半段,黃振開以為李小樂死了,傷心欲絕之際,拍電影的外星人再次出現,追着黃振開拍,黃振開惱羞成怒,對着外星人大打出手。黃振開被抓到異空間,他不滿外星人給自己寫的劇本,和外星人打團戰,艱苦鬥爭之下最終以一敵多獲勝,踩碎了“命運的遙控器”,拒演外星人安排的人生劇本……
拍電影的外星人進進出出,貫穿了全片,其實也只是作為“命運之神”的具體投射,除了能讓觀眾更加直觀地感受到主人公與命運的抗爭之外,別無他用。

幾個憨頭憨腦、嘰嘰喳喳的外星人,變成了觀眾獵奇觀看的消費符號。
實際上,呈現電影中主人公內心狀態的手法有很多,選擇如此濫用元電影的形式,不僅無法為影片增添更多層次的科幻或哲學質感,空洞無物的符號堆砌反倒顯得創作者過於自戀,在自己營造的符號系統裏摸不着頭腦。
與他作的強烈相似,變成了東施效顰
自宣發階段開始,就有觀眾直言本片跟美國導演米歇爾·貢德里的電影《曖曖內含光》類似。
其實,儘管二者都是愛情片,都在探討愛情雙方之間的關係,但《曖曖內含光》中的科幻元素——記憶清除程序起到了重要的推動敍事的作用。
故事講述了主角約爾在失戀之後試圖藉助記憶清除程序讓自己忘掉前女友克萊門汀,在本能思念和傷心遺忘、美好回憶和殘酷現實之間,他經歷了濃烈的情感糾葛,影片以此呈現出愛情本身的偉大。
可《負負得正》中的科幻元素不僅沒能起到推動敍事的作用,反倒給原本浪漫迷離的主體敍事增添了龐雜無聊的搞怪效果,使得影片基調不倫不類。浪漫浪得不純,科幻幻得不粹,結果變成了一種怪異的雜糅。

此外,大多數觀眾都認為影片多處橋段與王家衞作品類似,如《重慶森林》《春光乍泄》等,如片中布宜諾斯艾利斯、兩人多年後在有着燈塔的海灘邊重逢,甚至還有若有若無、時隱時現的孤獨唸白,再輔以高度概念化、哲學化的愛情雞湯,如“什麼是愛?愛是地域,不是自己的地域就是他人的地域”“假的有時候比真的還真”“每個人要經歷很多悲傷和難過,很多離別和重逢,才能理解愛是什麼”等。
特別是李小樂離開三年後的劇情結構,黃振開辭職去了很多地方,見了很多人,在同與李小樂有過交集的他人口中,瞭解到自己所不知道的李小樂的過往。黃振開傷心惋惜之際,又在一個平平無奇的海邊夜晚和李小樂重逢。
如此雷同,如此高度相似,讓人很難不想到對王家衞的復刻和借鑑。
可就算借鑑,本片也沒有展現出王家衞電影裏香港小資產階級的閒適和優雅感,形似而神散,反而變成了過度巧合、過於自我的敍事敗筆,變成了低質量的東施效顰。

致敬應當成為電影畫龍點睛的臨門一腳,而絕非在劇作無力時的東拼西湊。文藝作品應當以創新引領社會話題,做時代的風向標,而非跟在“致敬”背後人云亦云。
當文藝作品充滿了移植和嫁接的痕跡,其生命力不會長久,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也是一種對觀眾審美水準的居高臨下的蔑視:看吧,你們都沒吃過好的吧。不如來吃吃我這鍋大雜燴吧。
行業的低迷和冷落,呼喚真正的創造與創新
今年這個暑期檔有些特殊,剛好撞上了四年一度的奧運會,加上我國奧運健兒捷報頻傳,甚至打破世界紀錄,揚我國威,令國人沸騰,自然是分走了大量觀眾的注意力。
根據網絡平台燈塔專業版的實時數據,截至8月13日16時30分發稿前,2024年暑期檔(6月—8月)檔期總票房(含預售)突破93億元。事實上,根據目前趨勢和新片定檔計劃來看,今年暑期檔票房很有可能產生歷史性倒退,而在客觀的市場遇冷之外,更嚴重的情況是觀眾的主觀退場以及輿論黑手的陰謀。

如影評人譚飛所説,電影輿情出現了“五種陰謀”:身份論、抄襲論、翻舊賬、爛片論、黑粉毒唯。當前,我國電影面對的輿情不再真實客觀,而是充滿了主觀臆斷和惡意煽動,這樣的現象不僅挫傷出品方和製作方的積極性,更破壞了整個電影生態環境。
誠然,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應當包容所有類型的影片,允許多種不同聲音的存在。但在行業面臨如此窘困之際,電影從業者要做的,首先應當是齊心協力,把觀眾從手機熒屏之前重新拉回電影院。

從創作層面來説,就是要降低觀影門檻,在更加通俗易懂的情節基礎上進行多樣的探索。
《負負得正》意識流式的敍事邏輯,以及迷離的人物狀態,必然會將許多在短視頻媒介環境中被“短平快”浸染已久的觀眾拒之門外,從而最終使影片受眾收縮到特定小圈子內,而無法觸及更多其他圈層的受眾,也無法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力。
一個優秀的電影導演最大的優點應當是準確。無論影片涉及何種類型、何種藝術風格,都應當做到自我表達的準確和觀眾審美接受的準確。《負負得正》想要的太多,明確的太少,含混不清的表達,曖昧不語的類型,最終丟失了自我的準確,也就迷失了自己的定位,拋棄了觀眾和市場。
我們鼓勵創新,是要鼓勵那些純粹原創的乃至樹立自身獨特藝術風格的創新,而非充滿大量致敬、爆梗、模仿和借鑑的“創新”。真正的創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話題度,能夠迅速擊中社會痛點,從而成為他人的致敬對象,如去年暑期檔電影《長安三萬裏》中台詞“輕舟已過萬重山”的火爆,便是極佳例證。
近年來,市場上也出現過既有市場也有藝術的作品,如《漫長的季節》《狂飆》《我不是藥神》等,在收穫觀眾喜愛的同時,導演也完成了自身的作者性表達。
商業性和作者性的平衡是每個創作者的追求,也是懸在每個青年創作者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新導演向來都是不缺的,但如何站穩腳跟,持續發力,確實是歷來的難題。在這個問題上,温仕培導演還有諸多成長空間。

我們期望於創作者能在行業舉步維艱之時,內下苦功,能夠真正做到創新創造,在堅持自我表達探索的同時,能夠贏回觀眾,創造良好的市場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