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者的光與影——重温老電視劇《新四軍》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小时前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79週年之際,我又重温了20年前看過的電視連續劇《新四軍》。
這次重看,印象最深的卻是幾位“無名者”。
第11集繁昌保衞戰中,男主角黃江河率領臨時編成的新四軍第13團堅守青平江前線,阻擊日軍兩個精鋭師團的進攻。共同防守青平江的國民黨第三戰區精鋭部隊187師為了借刀殺人,竟然在未通知新四軍的情況下撤出陣地,放日軍繞到新四軍側翼。13團腹背受敵,傷亡慘重,正在與敵殊死搏鬥之際,忽然有戰士看到一位穿着粉紅色小褂的姑娘摟着一個藍布白花的包袱,冒着的敵人炮火,跌跌撞撞地朝陣地上跑來。戰士們將被炮彈炸傷流血不止的姑娘背到戰壕裏,一口一個“小大姐”地呼喚着昏迷過去的姑娘。小大姐微微睜開眼睛,捂着手裏的包袱對黃江河説: “這是我們繁昌老百姓親手做的一面旗子,讓我一定要送到新四軍手裏……終於送到了……我…我終於送到了…”
黃江河憤然道:“他們怎麼能讓一個女人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來呢?”
姑娘用盡最後的力氣解釋着:“還有兩個人,他們在路上犧牲了。鄉親們説……説你們新四軍是最好的……” 話沒説完,小姑娘頭一歪,倒在將她從彈坑裏扛出來的營長鬍富財的肩頭上犧牲了。
話沒説完,小姑娘頭一歪,倒在將她從彈坑裏扛出來的營長鬍富財的肩頭上犧牲了。
黃江河打開染着鮮血的包袱,是一面紅底金字的錦旗,上面繡着:
“獻給 抗日英雄鐵血新四軍 繁昌人民敬獻”
在這面旗幟下,黃江河告訴還活着的全體戰士:
“同志們,這面旗幟是繁昌城的老百姓拼着性命,冒着敵人的炮火給我們送上來的。我們靠着簡陋的裝備,擊退了日寇兩個精鋭師團的輪番進攻。我們為新四軍爭了光,現在全國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們新四軍是不可戰勝的。我們子彈打光了,刀也砍鈍了,我們沒有預備隊了。可是敵人依然在向我們進攻。軍部命令我們再堅守48個小時。我們靠什麼堅守?靠石頭、棍棒、牙齒和我們的生命!只要13團還有一個人存在,就不能讓這面旗幟倒下!”
這位小姑娘就出場了這一次。戰士們無法知道她的姓名,可是這個“無法知道”卻讓她分外高大了——我們聽到黃江河在對戰士們最後的動員中用錦旗的落款稱呼這位小大姐“繁昌城的老百姓”。
還有她犧牲在路上的兩個同伴(應該是小夥子)——我們能夠想像,這是一次“飽和式獻旗”:從織機下繡出錦旗,到一棒又一棒前仆後繼的接力傳送,那些活潑美麗的生命灑盡鮮血交到戰士們手中的,不是她們自己的姓名,而是世界上最堅不可摧的兩個大字——“人民”。
這兩個字確實是威力無窮的。不但新四軍戰士靠着這個信念守住了陣地,而且葉挺軍長怒髮衝冠地趕到187師陣地,處決了擅自撤退的師長,並正告187師的官兵們:
“你們187師在中國軍隊裏裝備最好,待遇最優厚。中國的老百姓用多少血汗錢供養着你們!你們怎麼能做出這樣無恥的勾當?!我現在命令你們立即反攻,恢復陣地!”
在之前的劇情中,葉挺赴任新四軍軍長途中路過國民黨軍防守的長江要塞,守軍士兵們紛紛跑出來一睹威名赫赫的葉挺將軍的風采。有個士兵還對葉挺説:“您真是葉挺將軍嗎?我們老家人都説您是趙子龍再世!”葉挺問:“弟兄們,現在日本鬼子來了,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你們怎麼辦?”士兵們回答:“那還能怎麼辦?用大炮轟他兔崽子,用大刀砍他兔崽子!”這是因為葉挺是當年的北伐名將,在國民黨軍隊中威望也很高。所以今天他當眾處決187師師長,187師其他將領也不敢説半個不字。
而且187師到底還是有不少愛國官兵,對長官丟棄陣地置新四軍於險境也很不滿,經他們心目中的大英雄葉挺一番督勵,終於向敵人側後發動反攻,配合新四軍擊潰了日寇,繁昌城轉危為安。
國民黨的報紙當然將“繁昌大捷”歸功於“國軍”,而那位小大姐用鮮血染紅的錦旗帶來的才是繁昌人民最真實的評價:
“你們新四軍是最好的……”
第17集,日寇向雲嶺的新四軍軍部進攻,葉挺軍長親自到前線指揮戰鬥。在軍部工作的梅青是南洋華僑富商出身,她一邊帶着戰士們出發向前線輸送彈藥,一邊與自己照顧的新四軍託兒所的孩子們告別。副軍長項英碰到了她,勸阻道:“怎麼能讓你一個女同志去前線呢?”
梅青反問:“不是説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就缺少戰火的鍛鍊嗎?”
“誰説的?”
“就是項副軍長你啊。”
項英這才想起來:“哦哦,是我説的,我是説過。”然後又一個個問那些活蹦亂跳的孩子:“你是誰的兒子?”
孩子們爭先恐後地報着父母的姓名。
有個小男孩怯生生地不説話。項英問他是誰的兒子時,他説: “我是新四軍的兒子。”
項英一楞。梅青解釋道:“他的父母上個月都犧牲了。”
項英抱起小男孩,對大家説:
“對。你們都是新四軍的孩子!”
也就在這一集,江南日軍進攻雲嶺的同時,國民黨頑固派也向新四軍江北部隊進攻。新四軍某部在餘秀英(她的原型應該是新四軍第五師副政委、著名女將陳少敏同志)率領下堅守半塔集抗擊頑軍。激戰到彈藥將盡時,一名負傷的戰士抱着一堆手榴彈衝上陣地交給餘秀英,對她説:“首長,這是最後幾顆手榴彈了。”説完,戰士就犧牲了。
餘秀英問旁邊的戰士:“他叫什麼名字?”可大家都不知道。餘秀英説:“記住給他立一塊墓碑,上面就寫:新四軍。” 半塔集戰鬥勝利了,但這位無名戰士的墓碑立了沒有呢?劇中再無任何交待;正如在一年後皖南事變的腥風血雨中,我們也不知道那一位以及那一羣“新四軍的孩子”命運究竟如何。我們只知道他們最喜歡的“梅青阿姨”——那位與黃江河一起被葉挺軍長稱為“新四軍的金童玉女”的姑娘——在突圍戰鬥中為了不被國民黨軍俘虜,跳崖犧牲了。
半塔集戰鬥勝利了,但這位無名戰士的墓碑立了沒有呢?劇中再無任何交待;正如在一年後皖南事變的腥風血雨中,我們也不知道那一位以及那一羣“新四軍的孩子”命運究竟如何。我們只知道他們最喜歡的“梅青阿姨”——那位與黃江河一起被葉挺軍長稱為“新四軍的金童玉女”的姑娘——在突圍戰鬥中為了不被國民黨軍俘虜,跳崖犧牲了。
20年前看這部劇時,我並沒有注意到這些無名者,將他們當作龍套、背景板一掠而過了。
20年後,我感到這部劇的獨特魅力之一,正在於它以速寫式的筆法勾勒了這些無名者的形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這些無名者的形象當然有政治意義,代表了廣大人民羣眾和基層指戰員,可是他們也有着獨特的審美價值。
電視劇《新四軍》的正面人物羣像可以分為四類:
1.毛澤東、周恩來、葉挺、項英、陳毅、劉少奇等領袖人物;
2.黃江河、餘秀英、梅青、謝成龍、胡富財等虛構的但有歷史原型的主配角人物;
3.陳小布、劉小丫等有名有姓、出場不只一次、有較完整的故事線的虛構人物;
4.送錦旗的姑娘、送手榴彈的戰士、託兒所小朋友等無名無姓只出場一次卻有深刻意藴(分別代表着人民、戰士、未來)的人物。
這四類人物讓整個電視劇的人物長廊有了豐富的層次感,而這種層次感給人一種真實感。一個人的生活環境裏的確有這四類人物:一是那些影響力非常巨大但距你很遠幾乎不會直接照面的人物;二是非常出色魅力十足而且就在你身邊的人物;三是那些比較平常但有個性,和你相處過一段時間的人物;四是那些飛鴻踏雪偶然一遇,卻給過你很大幫助或很深印象,但還沒來得及認識就各奔東西的人物。當一部劇將這四類人都呈現出來時,就與實際生活有了同構性,觀眾就比較容易產生代入感了。
尤其是第四類人物,他們沒有來龍去脈,沒有故事線,所有的魅力只綻放在一個場景、一個時間點上。“曇花一現”通常被認為是貶義的,可曇花明明是很美的,而且花期的短暫更增添了人們的不捨、關注與聯想。實際上,往往正是轉瞬即逝的東西更容易讓人們想到永恆:讓我們想起珠峯的千年積雪的,往往就是手心裏轉瞬即化的一片冰晶。“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同一個月亮在我們的想像中可以短暫到極致,也可以持久到極致。
《新四軍》電視劇能夠用一定的筆墨勾勒這些“無名者”,讓我想起了中學時讀過的一篇課文《牛福兄,你在哪裏?》。這是著名作家袁鷹的一篇回憶文章。他1941年在日寇佔領的上海讀高中,很想參加新四軍去抗日。終於他的一個後來參加了新四軍的同學告訴袁鷹會有一個地下交通員“牛福兄”來聯繫他,帶他到蘇北根據地去。過了幾天,袁鷹在家見到了來訪的“牛福兄”,是一個20來歲、瘦長身材、留着平頭、穿着灰布長衫,老練精幹,像個小學教員一樣的人,説話有南通、如皋一帶的口音。袁鷹急切地問他新四軍的情況,牛福兄笑了,説這些以後再聊,要袁鷹先做好出發的準備,下次來接他走。可是下一回再見面時,牛福兄對袁鷹説另有任務這次不能帶他走了,要再等一段時間。但牛福兄再也沒有來。“牛福”當然不是這位交通員的真名,甚至也不是化名,而是“新四軍”的英文“New Fourth Army”的諧音。袁鷹在抗戰勝利後加入了地下黨,從這時起直到解放後,他一直向同志們打聽這位不知姓名的牛福兄。從袁鷹的回憶推斷,這位牛福兄大概是他親自打過交道的第一個一見面就可以完全確認是共產黨的人,就好像無邊黑暗中的人看到的第一縷霞光一樣,而且説要帶他走又爽了約,讓他產生了一定要找到這個人的執念,可能還想問一句:“你當年為什麼不帶我走?”但他一直沒有找到牛福兄,甚至隱約聽説過有一個這樣的交通員,不知姓羅還是姓劉,在執行任務時犧牲了——我個人感到這是牛福兄後來爽約不來的最合理的解釋。可是袁鷹又不相信,因為據説犧牲的那位交通員是上海口音,而不是牛福兄的南通口音。在文章的結尾,袁鷹説他已經不再打聽尋找牛福兄了,因為牛福兄就是所有為人民作貢獻的革命戰士,他一直和我們在一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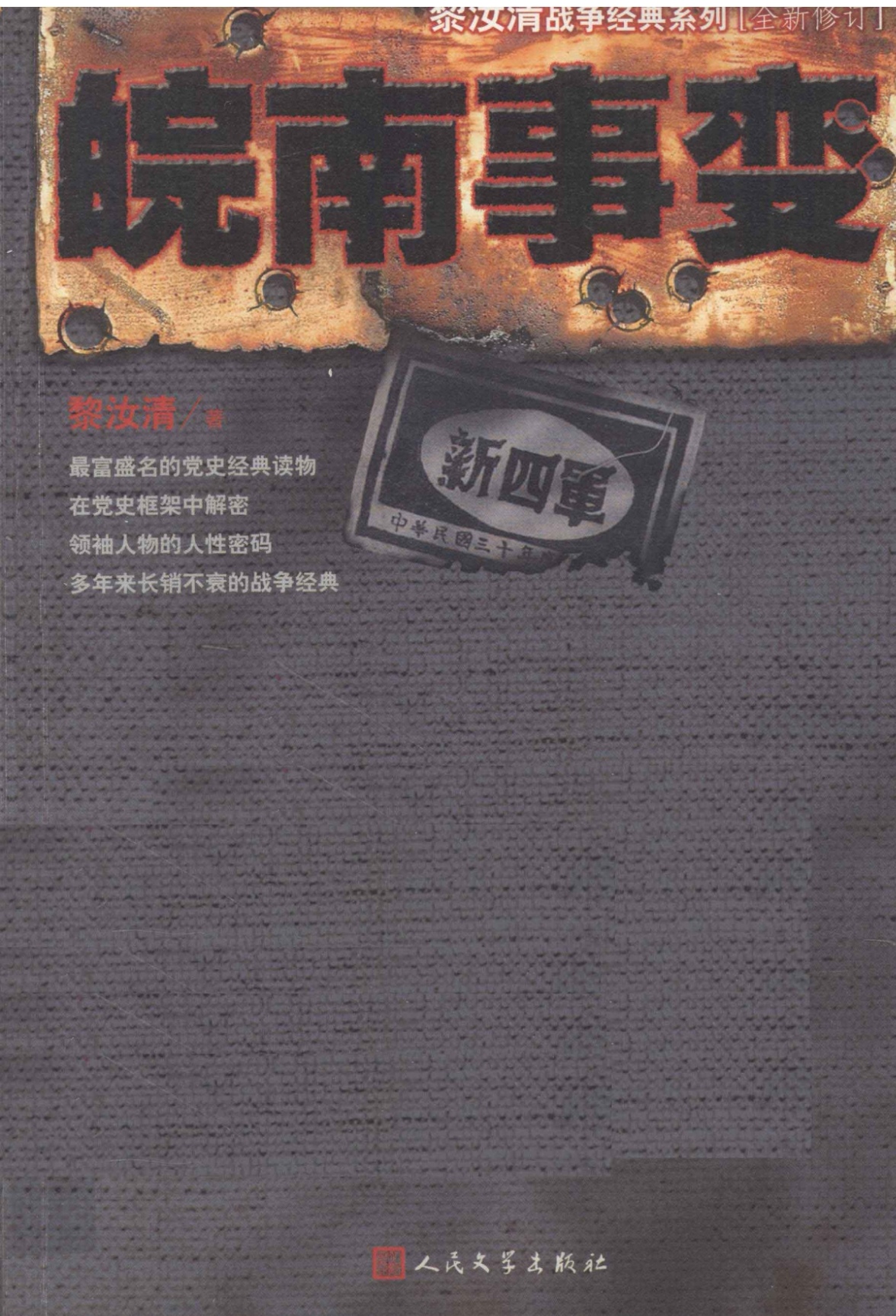 另外,上世紀八十年代黎汝清的小説《皖南事變》中有這樣一個很有意思的情節:
另外,上世紀八十年代黎汝清的小説《皖南事變》中有這樣一個很有意思的情節:
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抗敵報》記者白沙突圍途中被一位農村姑娘所救。頗具文人浪漫氣質的白沙喜歡上了這位美麗善良的姑娘,可是相處的幾天裏他竟沒有好意思問這位姑娘的名字。
白沙不知道的是,這位姑娘其實是皖南的地下黨員,後來還曾奉命向突圍後隱蔽在山洞裏的副軍長項英等人送糧食並傳達中央的指示。有一次項英見她比上次來的時候要憔悴不少,神情也很悒鬱,感動地説:“地方上的同志們辛苦了,你們一定遭了不少難吧?”
姑娘説:“同志,説實話,這袋糧食是從村裏男女老少的口糧裏摳出來的。我們鄉有二十三户人家因為掩護新四軍被敵人抓去坐了牢。我弟弟是新四軍,跑進我們村,我恰好掩護別的同志去了。他就讓保安隊盯上打死了。損失是大,可是鄉親們説新四軍成千上萬地遭了難,俺們還有啥捨不得呢?身家性命都捨得!”
項英肅然起敬:“皖南的父老鄉親們太偉大了!”
姑娘彷彿被“偉大”這個詞刺痛了,含着眼淚説:“同志,你説什麼偉大?為革命,人人都要犧牲,算不上偉大。我是一個農村的小學教師,從來沒想過什麼偉大。老百姓只有平凡,做這些是覺得為人就該這樣,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是偉大……”
項英所不知道也讓一位姑娘無法啓齒的是,為了完成籌糧和掩護新四軍的任務,這位年輕的農村女黨員剛剛忍受了國民黨保安隊長的姦污。她不能拼,也不能死,只能默默地背上生活的十字架。項英是萬萬想不到這位姑娘説的“什麼都捨得”是有這層含義的。
但項英還是被姑娘的話深深打動了。皖南事變我軍損失八千人,與項英不服從中央命令,指揮又發生失誤有很大關係。項英正在給中央寫報告和個人自傳,他在這些文稿中本來極力為自己推卸責任,可是這位普通女黨員的話讓他反省到自己太在意個人的榮辱得失,太對不起犧牲的戰士和為了支持新四軍而受苦受難的鄉親們了。他決心重寫報告,坦然承擔責任,接受任何處分。可惜的是,他永遠來不及寫完了。這天晚上,項英身邊的副官劉厚忠發現項英、周子昆身上攜帶了新四軍的經費,為了謀財,開槍將他們殺害,叛變投敵了。
而那位浪漫的記者白沙呢?後來他和作戰科長林志超等同志突圍到達了蘇北新四軍根據地。三個月後,白沙在鹽城的反掃蕩戰鬥中身負重傷。臨犧牲前,他囑咐護士將一封信轉交林志超,請他設法找到皖南地下黨組織轉交收信人。
而那的信封上寫的是:
“皖南放牛郎山某村姑收”
兩年後林志超也犧牲了,在他的遺物中沒有找到這封信。沒人知道這封信是不是已經轉給了皖南黨組織。更沒人知道這封連收信人地址姓名都不詳的信能否送到。
那位忍辱負重全力保護着新四軍留在皖南的火種的姑娘,又怎能知道這在只是她照料過的許多失散戰士之一的那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心裏掀起了怎樣的波瀾呢?怎能知道這個本來一心去蘇北的小夥子因為她而一度想留在皖南打游擊呢?又怎能知道在蘇北投入反掃蕩戰鬥之前,他曾經託付戰友帶信給連名字也沒問過的心上人呢?
許多東西就是這樣,還沒有來得及開始,就已經結束了。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革命者被戰火一次次撕裂的浪漫。
《新四軍》中的無名戰士與袁鷹筆下的“牛福兄”很有異曲同工之妙;而送錦旗的小大姐與小説《皖南事變》中那位我們始終不知道姓名的姑娘又何其神似。編導們或許正是從這些作品中汲取了靈感。
我還要附帶指出:陳道明曾經怒斥現在的電視劇給八路軍女戰士畫濃妝是迎合了惡趣味。
那麼我們來看一看20年前《新四軍》中演員的妝容: (為新四軍送錦旗犧牲的姑娘)
(為新四軍送錦旗犧牲的姑娘)
 (“我是新四軍的兒子。”)
(“我是新四軍的兒子。”)
 (目送小朋友們離去的項英與梅青)
(目送小朋友們離去的項英與梅青)
 (為送手榴彈犧牲的戰士)
(為送手榴彈犧牲的戰士)
 (率部堅守半塔集的餘秀英)
(率部堅守半塔集的餘秀英)
沒有磨皮,沒有濃妝,沒有髮膠,粗衣敝服,硝煙滿面,黃土滿身——為送錦旗而犧牲的姑娘,你甚至能看到她的臉龐在逐漸失去血色而變得蒼白。
但有人會説這些面孔和身姿不美麗嗎?
《新四軍》在革命歷史題材的電視劇中算比較好的一部了。前面説到對“無名者”的勾勒,是這部劇的魅力之一。
而總的來説,該劇對於新四軍的活動講了抗日鬥爭、統一戰線(不光是對國民黨,也包括改造古無畏那樣的民間抗日武裝)、國共矛盾、葉項矛盾,處理山陽縱隊常山虎事件也涉及了黨和軍隊的組織建設,算是比較全面了,但在政權與根據地建設方面沒有怎麼着墨,不能不説是一個缺憾。
沒有完美的作品,但可以鑑別是否褻瀆。
文中提到的袁鷹的散文《牛福兄,你在哪裏?》出自他的文集《上海:未褪色的夢憶》,還提到了黎汝清的小説《皖南事變》。這兩本書均可一讀。
新四軍題材是座富礦,應該有更多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