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濤 | 走向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學史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昨天 22:35
劉洪濤 |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6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劉洪濤
21世紀以來,歐美國家陸續出版了三部用英語撰寫的世界文學史,它們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Gunilla Lindberg-Wada)教授主編的《文學史:走向全球視野》(Literary History: Towards a Global Perspective, 2006),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德比加尼·甘谷利教授主編的《劍橋世界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2021),哈佛大學達姆羅什教授和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教授共同主編的《文學:世界史》(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 2022)。**這三部世界文學史,雖然體例與風格大不相同,但都力圖摒棄西方中心主義,展現真正的全球視野。**相較於19—20世紀歐美國家出版的諸多世界文學史只有“世界”之名而主體部分實為西方文學史的情況,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稱之為世界文學史書寫的“革命”都不為過。而這種“革命”來自西方內部,其產生的語境、具體表現、意義與後續的影響,就更值得我們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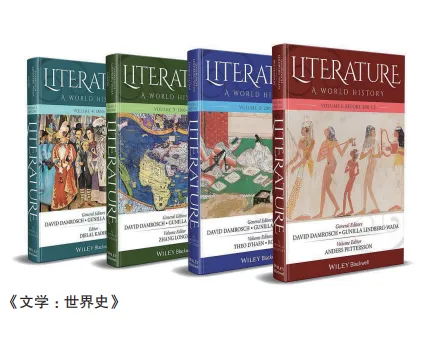
一
三部去西方中心化的世界文學史,雖然出版於21世紀,但其變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是西方學術界對冷戰結束之後加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地緣政治劇變、多元文化觀念日益強勢、世界文學新樣態繁榮興盛做出的回應。1993年,美國比較文學學會發布的伯恩海默報告敏鋭地指出,一直支配着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的歐洲中心主義“已經受到來自多方面的挑戰”,比較文學“正朝着多元文化的、全球的和跨學科的課程方向發展”。1994年,莎拉·拉沃爾(Sarah Lawall)主編的《閲讀世界文學:理論、歷史與實踐》一書出版。拉沃爾在此書的前言中指出,**世界文學課程的使命是“向未來的公民介紹我們自己社會‘外部’的文化體驗……這類課程將非西方文化呈現為‘他者’,我們必須瞭解它,以便使之在更大的背景中有效地發揮作用,並區分我們自己的獨特身份”。**而此書最重要的章節是多位學者對跨文化閲讀世界文學的理論和方法的探索。
對於歷來將世界文學教學的宗旨理解為鞏固美國與歐洲精神與文化聯繫的美國學界來説,這一轉變可謂巨大。同年,考斯(Mary Ann Caws)和普倫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主編的《哈珀·柯林斯世界文學讀本》出版,選入了包括亞洲、非洲、大洋洲在內的來自世界各地的475位作家的作品。1995年,莎拉·拉沃爾主導的《諾頓世界文學名著選》“擴展版”出版,實質性地改變了該書自1956年出版以來,40年只選收歐美名家名著的傳統,在共計6000多頁的篇幅中,收入了2000多頁非西方文學作品。21世紀初出版的“諾頓”“朗文”“貝德福德”三種世界文學作品選集,則以更大的規模、從全球的範圍選收世界文學作品。這類世界文學選本,將來自世界各個地區的作家作品,按照時間線索排列,以重大歷史節點分期分卷,其組織方式和框架,具備了世界文學史的基本特性,是將廣大區域的非西方文學大規模納入世界文學史的初步嘗試。
正是在這種求新求變的時代氛圍中,由瑞典科學研究委員會贊助的“全球語境中的文學與文學史”項目於1996年啓動,一批瑞典比較文學學者和區域國別文學研究專家就此合作,致力於撰寫一部跨越歷史與文化鴻溝,“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具有全球視野”的“真正的”世界文學史。該項目持續到2004年,出版了《跨文化文學史研究》(Studying 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論文集。2006年,由古尼拉·林德伯格-瓦德擔任主編的《文學史:走向全球視野》作為該項目的最終成果出版,英語學界在21世紀的第一部世界文學史誕生。不久,另外兩部世界文學史先後啓動,並幾乎同時出版。這兩部世界文學史同樣表現了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自覺意識。《劍橋世界文學史》的主編甘谷利在導言中指出:在我們看來,世界文學既不受單一市場的束縛,也不受單一的資本主義一體化世界史的束縛,它為研究歷史上無數的文學世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橫向和比較的框架。
21世紀的世界文學史“可以探索世界文學形成的譜系,這些譜系不僅早於歐洲的崛起,而且在批判意義上與歐洲的崛起相輔相成,並對現代世界文學觀念的形成具有明顯的奠基作用”。佩特森(Anders Pettersson)與德漢(Theo D’haen)合作撰寫的《走向非歐洲中心的世界文學史》一文,將其參與編寫的《文學:世界史》定位為一部“非歐洲中心的世界文學史”,其結構安排“反映了嘗試在文學文化之間達成更平等、更少歐洲中心主義的平衡的努力”。
二
三部去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史,也從20世紀末以來出現的世界文學理論熱潮中汲取了資源和營養。其中,法國學者卡薩諾瓦1999年出版的《文學世界共和國》描繪了一個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世界文學體系。卡薩諾瓦認為,這個體系以歐洲為中心,巴黎是其首都,它積累了最多的文學資本,比其他任何國家的文學擁有更多的自主性,是時尚、創新的代表。非歐洲世界的文學生產,也被卡薩諾瓦納入這個世界文學體系中。在她看來,每一個文學文本都處在與其他文本的競爭關係中,非歐洲世界是文學現代性進程中的後來者,在這種競爭關係中處於劣勢,在這個世界文學體系中處於邊緣位置。卡薩諾瓦揭示了近代世界文學發展與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形成之間的關係,有重要的認識價值;但又因其赤裸裸的歐洲中心主義引發了激烈批評,而這種批評又為學者探索新的世界文學生產和流通模式提供了持續的動力。

美國學者莫萊蒂2000年發表的論文《世界文學的猜想》及其他相關著述,同樣“把近代以來的世界文學看成一個不斷進化發展的體系,這個體系有中心,有邊緣,其權力關係是不平等的。文學的進化發展總是從中心向邊緣運動,是一個不斷擴散的過程”。**這種擴散的結果,往往是中心區域的文學影響和改變邊緣區域文學的自主進程,對其產生同化作用。但莫萊蒂認為邊緣區域的文學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它會對中心的形式加以選擇和改造。**莫萊蒂用“波狀”和“樹狀”模型來概括這種文學傳播擴散的規律,還倡導以“遠讀”(distant reading)的視角和數字人文手段對世界文學進行研究。莫萊蒂同樣因為其提出從中心(歐洲)到邊緣(非西方地區)的文學流通邏輯,以及簡化甚至單一化了跨文化文學間相遇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而飽受詬病。但莫萊蒂也打破了歐洲文學自主生成的假設,表明大多數文學都經歷了與其他文化“妥協”、融合的過程。同樣重要的是,莫萊蒂提出了一種理解全球範圍文學生產、流通的新範式,並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
美國學者達姆羅什2003年出版的《什麼是世界文學?》把“世界文學”定義為離開起源地,以源語言或翻譯在世界範圍流通和被閲讀的作品,構建了一個文學全球生產、流通和閲讀的模型,影響巨大。但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論述,同樣受到不少學者的批評,認為其世界文學觀念,及其闡述的世界文學生產、流通和閲讀機制,是以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為依託的,仍然沒有擺脱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雖然如此,相較於前二位,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空間建構,表現出去西方中心化的自覺,對非西方文學是相對友善的。此外,他把世界文學看成多元起源,從民族、國家和區域向全球發展的進程,拓展了世界文學的經典觀念和範圍。
上述三位學者關於世界文學的論述,雖然各有其不足,但都構建出一種世界文學生成和發展的模型,為世界文學史模式的創新,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外,海德格爾發明的“世界中”(worlding)一詞,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新的世界文學建構,由此生成了“世界中文學”(worlding literature)概念。這一概念的價值在於,不再把“世界”看成一個既定的事實,而是看成一個不斷流動、生成的概念,這樣,“文學”和“世界”之間就不再是一種固定的、僵化的搭配,而成了互相成全的關係。還有斯皮瓦克對“星球性”(planetarity)概念的闡發,呼籲用其所包含的自然論、生態論和異質論內涵,抵制包含資本論、技術論、控制論內涵的全球化,由此衍生出與世界文學相對的“星球文學”(planetary literature)概念。這些創新性概念,都對學者們描繪擺脱資本主義全球市場邏輯的新世界文學圖景,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三
三部世界文學史從多方面、多維度,對去西方中心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文學史:走向全球視野》分4卷,前2卷共13章,分別論述了中國、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拜占庭、非洲傳統文學觀念、文類觀念的演變,沒有任何一個案例來自歐洲國家或地區;後2卷共13章,雖然主要聚焦歐洲文學向其他地區的流動和產生的影響,但都是立足非歐洲地區的主體性,凸顯這些地區對歐洲文學的主動選擇和創造性轉化。《劍橋世界文學史》共2卷47章,它沒有按照時間線索、歷史分期來講述文學史,而是以9個專題47個案例統領全書,這些專題和案例聚焦全球範圍內多樣態、多層面的文學流通,其中絕大多數案例也都取自非西方地區。《文學:世界史》按時代分為4卷,按地理區域分為六大板塊:東亞,南亞、東南亞和大洋洲,西亞和中亞,非洲,歐洲,美洲。每卷書在各自的時段內,對這六大地理區域的文學依次交替進行論述。這種結構模式,使得整個西方文學(歐洲、美洲)只佔到總量的三分之一。
三部世界文學史不僅在數量比例上大幅降低了西方文學的份額,還對其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做了降格、弱化處理。安德斯·佩特森與西奧·德漢在合寫的《走向非歐洲中心的世界文學史》一文中,詳細講述了他們如何在《文學:世界史》中做到這一點:主要是不再把歐洲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引領者和現代性之源,而是作為一個“問題”加以反思。編者利用地理區劃的歐洲與文化實體的歐洲之間的張力,來凸顯其“問題”所在。
**具體來説,地理上的歐洲與文化實體的歐洲並不完全重疊。**例如古希臘和古羅馬屬於地中海文化圈,但大部分地理上的歐洲地區卻在這個文化圈之外;羅馬帝國先是分裂為東、西羅馬帝國,然後其西亞和北非部分被伊斯蘭教同化。德漢就此追問:“希臘人真的是 ‘歐洲人’ 嗎? 還是我們只是在回顧歷史時才讓他們成為歐洲人, 並服務於我們自己的特定文化甚至種族偏好或偏見, 就像馬丁·貝尓納在《黑色雅典娜》中所説的那樣?”事實上,作為文化實體的歐洲是在與相鄰的亞洲地區的一系列大規模衝突與融合、在全球的殖民和去殖民進程中被形塑的,包括基督教的引入與傳播、十字軍東征、阿拉伯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先後崛起等。

《文學:世界史》將歐洲作為一個宏觀地理區域,而不是一個文化實體,凸顯了其內部的駁雜性及與地中海地區文化的密切聯繫,表明“歐洲”從一開始就受到與“其他”實體尤其是地中海周邊國家關係的影響。基於此,《文學:世界史》的歐洲部分,把重點放在那些處理歐洲與他者關係的作品上,同時,強調歐洲文學的多元性和外源性,指出其成就往往是域外文學文化衝擊和影響的結果。
**三部世界文學史之去西方中心更具根本性的,是對構成傳統世界文學史基石的一些要素和觀念的摒棄與顛覆。**安德斯·佩特森與西奧·德漢在文中指出,“世界文學史是一種歐洲體裁,它傳統上滲透着歐洲對事物的看法”,這些 “世界文學史通常被設計成西方文學史,穿插其他文學文化,它們通常是由西方學者撰寫,用西方的眼光看世界,依靠西方的概念體系”。僅從歐美國家出產的世界文學史類著述看,這個判斷無疑是正確的。從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文學史——德國卡爾·羅森克蘭茨(Karl Rosenkranz)的《詩的通史手冊》——在1833年出版,直到20世紀末,歐美國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世界文學史類著作,但總體情況莫不如此。具體來説,就是以歐洲文學為中心,以名家傑作作為基本材料和載體,以民族國家作為劃分單位,以單一的時間線貫穿始終,以精神演進或進化論作為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
21世紀以來出版的三部世界文學史顛覆了這一切!其對“文學”的理解,遠遠超出了傳統世界文學史主要由詩歌、小説、戲劇三大文類的西方經典文本構成的狹隘範圍,不僅將全球生態文學、兒童文學、監獄文學、繪本小説、傳記、演説辭、書信、遊記等亞文學文本,以及史學、哲學、心理學等學術性文本納入其中,更將文學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乃至網絡文學和數字世界,都囊括在內。其對“世界”的理解,不再偏於歐洲一隅,反而是將歐洲“邊緣化”,讓廣大的非歐洲地區上升為世界文學史的“主角”。它們也不再以民族國家作為“世界”的基本單位,而將更大的地理區域“洲”作為基本單位,探索洲域內由地理、人種、語言、文化、歷史的相似性和關聯性所形成的文學共同性,以及洲際文學的交流和影響;或者更進一步,並不以人們熟知的地理、文化區域內的文學作為論述重點,而是更關注“世界”的流動性、生成性,致力於挖掘新的、多樣態的世界文學體系與中心、類型與風格、要素與媒介。它們的編者尤其反對把世界文學史寫成朝着某種最高精神或高級形態演進的歷史,反對寫成單一的世界文學體系形成的歷史,反對一切形式的整體性和統一性;對文化文學多元性、差異性的重視,對平等尊嚴的強調,對跨文化比較與對話的推崇,成為其核心價值觀。
最後,三部世界文學史也破除了以單一的時間線貫穿始終的傳統模式。《文學:世界史》雖然有一以貫之的時間線,但這個時間線始終是複數的。《文學史:走向全球視野》以對文學的觀念、文類的觀念、文學的流通與互動這三個問題的討論,支撐起文學史的框架。《劍橋世界文學史》則設置了九個專題:文學譜系,思考世界,跨區域世界,地圖轉換,世界文學與翻譯,詩學、文類、跨媒介,範圍、多邊系統、經典,閲讀與流通模式,世界與星球。後兩部世界文學史中的時間破碎、繁複而多元,沒有整一性,以致有多位學者指其更像是世界文學史論文集。
四
國內比較文學界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正日益走向自覺和深入,這三部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學史,正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鑑。但借鑑不是照單全收,而應該從中國立場、中國語境、中國問題出發,有所取捨和選擇。
20世紀初,美國學者莫爾頓(Richard Green Moulton)在他的《世界文學及其在總體文化中的地位》(1911)一書中強調**,“世界文學”概念有別於“總體文學”,需要引入一個觀察的視角,例如觀察者自身所屬民族國家的視角,而世界文學研究同樣需要一個立場、一個特定的視角。**他説:“我們必須立足於我們自己的立場,並從這一點看向四周,我們必須發揮視角的作用:我們必須從我們的視角來區分什麼是偉大的,什麼是渺小的,什麼是必不可少的,什麼是不那麼重要的。”
中國學者鄭振鐸在《文學的統一觀》(1922)一文中對此提出批評,他認為世界文學以普遍的人性為基礎,具有整體性和統一性;對世界文學的研究,也需要將其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統一的研究,而不被國別、時代等局部因素所分割。莫爾頓與鄭振鐸的觀點相左,蓋因為他們都是站在自身所屬民族的立場上,從自身民族的現實需求出發討論世界文學問題的。**莫爾頓強調英語民族視角,是因為20世紀初葉的美國需要建立起一個從《荷馬史詩》《聖經》到莎士比亞、彌爾頓、歌德的世界文學經典傳統,以此強固自身與歐洲之間文化和精神的血脈聯繫。**鄭振鐸的世界文學觀則反映了五四新文學渴望與域外文學建立廣泛聯結,從“人類性”的高度思考民族文學發展方向的思想。所以,儘管鄭振鐸的世界文學觀受到莫爾頓的很大影響,但他們的立場、問題意識和出發點卻有極大的差異。就像當下,同樣是批判西方中心主義,中國學界與西方學界的立場、出發點,需要解決的問題和追求的目標也不相同。
簡言之,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作為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東方大國,作為擁有源遠流長、輝煌燦爛文學傳統的國家,我們的學者需要將中國文學作為一種顯明的存在、重要的力量,置於世界文學史的時空框架體系中,置於與各區域、洲域文學深廣的聯繫之中。在此前提下,中國學者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學史寫作,才能真正開創新局,走出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