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雲南拾菌子,一場生意一場夢_風聞
刺猬公社-刺猬公社官方账号-1小时前
爆火的雲南採菌遊,和它背後的生意與江湖。
文|啊遊
編|園長
半夜,一場雷雨突襲大理,風從敞開的窗户潛入民宿,我起身關窗,看到閃電把天空劃成碎片,遠處的蒼山時隱時現。
雨勢越來越大,我和朋友不免有些擔心明天的拾菌之旅能否如期進行。那時的我們還不知道,雷雨過後正是採拾野生菌的好時機,經過雨水的滋潤,埋藏在泥土中的野生菌孢子將加速萌發,一夜之間就能生長3至5釐米。
第二天一早,風雨已停,我們坐車前往約定地點,與領隊匯合並領取拾菌工具——每人一個竹籃,一個鐵耙,隨後便從蒼山的一角進入山林。

遊客上山
抵達雲南前,身為北方人的我總是給朋友説“我們要去採蘑菇了”,抵達雲南後,語言習慣被當地人同化,這句話就變成了:“我們要去拾菌(四聲)子了。”
領隊小嶽也並非雲南當地人,他的家鄉是與雲南分處對角線兩端的黑龍江,小時候在東北的大山裏拾菌子,2021年來到大理後,又開始在雲南的山裏拾菌子。
全國的可食用野生菌有一千多種,雲南所在的西南地區就佔了八百多種,除此之外,當地還有大量不可食用的野生菌。
菌子的生長有自己的節奏,一年裏會在6月至9月集中出現,這段時間也因此被人們稱為“菌子季”。而在短暫的菌子季週期裏,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地點,又會催生出不同的野生菌品種。
近兩年的採菌過程中,小嶽捕捉到了當地更為具體的菌子節律:蒼山的7月多喇叭菌,8月多抹布菌、奶漿菌、青頭菌和黃賴頭,9月多青頭菌,9月之後菌子則會越來越少。

我們上山時已是9月初,野生菌數量遠不如7、8月份,想要拾到菌子就更加考驗眼力、體力,大部分時間,我們只能提着籃子,小嶽在前方發現菌子,我們在後面跟着撿。
“那裏有一個大的,看見沒?”小嶽慧眼識菌,很快在路邊發現了一株考夫曼牛肝菌。
這是一種無論長相還是名字都很像麪包的菌子,我迅速跟上,捏住傘柄後用力向上一拔,菌子離開土地,被我小心翼翼地放進竹籃。
鋪設了台階的山路兩旁很難看到菌子的身影,大部分時間需要離開主幹道,深入兩旁的林子裏尋找,避開蜘蛛網,撥開樹下的落葉與松針,有時甚至會路過墳墓。
但菌子的魔力不斷吸引着我們走向山林更深處。
道路越是崎嶇,越有可能發現不常見的菌種,就如同珍寶總是被藏在最隱蔽的地方。
山下的世界已經被拋之腦後,山上變成一處秘境,植物的枝幹隨時會劃過衣服,露珠和汗水打濕了劉海兒,摘菌子時會不自覺地屏息。直到菌子與土地分離的瞬間,潮濕的泥土氣再次湧入鼻腔,耳畔的鳥鳴和蟲鳴使得整片山林喧囂又寧靜。
小嶽邊帶路邊給我們講述菌子的傳説:有的菌子在這個山頭能吃,在另一個山頭可能就有毒;菌子怕人,見到人知道自己要被摘走了,就會不長了……
認菌子是拾菌子的前提。
“我們一般是根據外觀特徵,比如菌蓋顏色和形狀,菌褶的形狀等來辨別菌子的種類。”小嶽傳授給我們一條簡單分辨菌子是否有毒的口訣,“大部分毒蘑菇一般頭戴小帽子(毒孢子),身穿小裙子(菌環),腳上有靴子(菌托)。”
此外,還有一些“上手”的法子。比如説,見手青之所以叫見手青,就是因為用手碰過後菌子的傷口會變青;再比如説,用手劃一下菌子的菌褶,黃汁乳菇這類奶漿菌真的會有汁液滲出。

當遇到在外觀上實在難以分辨的菌子時,比如可食用的大紅菌和毒紅菌,小嶽説他們平時會掰一小塊放嘴裏嚐嚐,辣的就是毒紅菌,吃了會腹瀉,他一再叮囑:“你們可別隨口亂嘗啊。”
一路上,我們遇到了依附在樹幹上生長的美味金耳;傘杆呈青色,被譽為“松針下的綠寶石”的青頭菌;炒不熟吃了會中毒,但最受歡迎的見手青;還有一些顏色鮮豔的大紅菌。
兩三個小時很快過去,竹籃變得沉甸甸。
小嶽誇我們運氣好,昨晚的一場雨又給蒼山帶來了不少菌子,許多剛冒頭的小野生菌一團團依偎在樹根旁。


拾菌團湧入
拾菌之旅結束後,我們轉給領隊當天的費用188元,羣裏的江江詢問道:“下山啦!體驗如何?”江江算是小嶽的老闆,也是我們報名採菌半日營時的對接人。
在來到大理前,江江在深圳做建築設計,因為壓力太大而裸辭。在大理gap的第一年,她嘗試了許多工作,攝影、收銀、直播,最終在接觸了自然教育後,選擇專注這一行業。雲南的野生菌聲名在外,理所當然也是自然教育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開始覺得如果有人能帶你到山上採摘、識別野生菌,順便學習一些有關菌子的知識,會很有意思,也有意義。所以我們在2022年9、10月份開始嘗試帶朋友上山,慢慢在去年形成了完整的商業模式。”
雲南當地拾菌團、採菌項目的商業模式其實並不複雜。一方面,組織者們會在線上的社交網站發佈野生菌相關內容,直接招攬C端消費者;另一方面,有些規模較大的組織者會與B端的旅行平台、旅行團進行合作,提供定製化的採菌遊服務。
據江江觀察,前往雲南採菌的客户基本是一二線城市居民居多,7、8月份主要是帶小孩的家庭暑期出行,9、10月份則是度假的情侶較多。
抖音和小紅書是拾菌團組織者們,爭相運營的兩大平台。藉助網友對於野生菌的好奇,只要堅持發佈與野生菌採摘相關的內容,積攢起粉絲後,流量將很容易落地變現。

雲南楚雄人王開煜,一開始沒想到菌子會火。
從小就喜歡菌子的他,在上一份工作接觸到了農產品銷售,有了一定經驗後,去年夏天開始試着宣傳當地野生菌。王開煜告訴我們:“本來沒想到會有拾菌子這個業務,拍了四五個菌子的短視頻發在抖音、小紅書上,後台開始有人主動私信,問怎麼能去當地摘菌子。”
外省人對於雲南野生菌的痴迷程度的確正在與日俱增。
如今在抖音平台上,搜索“雲南野生菌”會發現相關話題已有35.4億播放,此外還有數十個相關話題的播放量過百萬;在小紅書平台上,關於雲南野生菌的相關筆記也已超2萬篇。
網友們熱衷於講述並傳播一切“吃菌中毒事件”,朋友開始説胡話最後發現是吃菌中毒啦,同事某天突然失聯是吃菌中毒啦,IP為雲南的網友出現怪異行為更是吃菌中毒啦,諸如此類。
也許是毒菌子在網絡世界中撒了一把賽博孢子,魔幻的氛圍裏,無論是“紅傘傘白杆杆,吃完躺闆闆”,還是“先菌子,後小人”的警示語,非但沒能讓人望而卻步,反而讓大眾對於野生菌的獵奇心理逐漸達到頂峯。
好奇心驅使下的消費動力不容小覷。
去年6月到9月,整個菌子季王開煜總共接了幾十個人在楚雄當地拾菌子,而到了今年的雨季,他幾乎每天都要接待3到4人上山,沒有中斷過。“去年拾菌團還不太火,今年宣傳的人很多。楚雄的小縣城願意來的人還相對較少,大理和昆明的拾菌團更多。”

身處大理的江江,見證了今年夏天的拾菌團大爆發。
“今年有太多人進入這個行業了。我們之前常走的一條路線,直到去年9月都還沒有同行,去年10月菌子季結束時也就2個同行。今年那個山頭,一天就能遇到十來個同行,每天得有三四百人在採菌子。”
江江坦誠發言,拾菌團火爆最直觀的原因就是——賺錢。“我們去年聽到的內幕消息,也可能是謠言,有一個同行兩個月賺了16萬。”
山上的野生菌世界是秘境,但身為現代人的我們總要下山,迴歸現實世界。
眼看着又一隊拾菌團,在領隊的帶領下進入蒼山,我們終於從沉迷採菌的恍惚中清醒過來。野生菌,從古至今都是一門極具經濟效益的生意。

被拓寬的野生菌經濟
王開煜的家鄉楚雄被譽為野生菌王國,在他長大的楚雄北部的牟定縣,每個村子裏都有至少一兩户人家從事野生菌收購生意,他家正是其中之一。
每逢雨季,當地居民早上5、6點就會進山採拾菌子,直至中午12點日頭已高才下山。
相鄰的幾個村子會共用一個收購點,村民們揹着竹簍把當日新鮮的野生菌送去收購點賣錢:上等的雞㙡和乾巴菌的收購價每斤能達到八九十元,甚至上百;備受歡迎的見手青每斤能賣七八十元;再往下,白牛肝菌也能賣到每斤三四十元。
“有些村民會專門在菌子季放下手頭的活計,進山採菌,幾個月下來多的話可以賺七八萬。”王開煜説道。
而他的父母,會在收購了村民採摘的野生菌之後,將其運往昆明木水花野生菌批發市場,或是華南野生菌交易市場。在這兩個全國數一數二的野生菌集散中心,七八十元收到的菌子,最高能賣到200元一斤,收入翻倍。
王開煜的印象裏,小時候農村經濟還不發達,野生菌對外交易的渠道只有線下收購,當時外省人對於菌子的熱情也還沒膨脹到如今的地步。野生菌根本不用找,而是直接“撿”,出門幹活的時候順手撿一點,一家人可以大吃一頓。
“看到青頭菌、銅綠菌、小黃菌、羊肝菌、雞油菌、掃把菌之類的,就摘兩棵長長的野草,草的一頭打個結,把菌子一朵朵串起來,拿回家;奶漿菌胡亂咬兩口,當場就吃了。看到鵝蛋菌、變色菌、松毛菌之類的,就當玩具,或者一腳踢飛。”

但如今,行情已經變了,藉助急凍鎖鮮和冷鏈運輸技術,今天剛摘下的野生菌,明天就有可能空運至國內的任何省份。
王開煜也算是“菌二代”,今年緊跟時代潮流在縣城的野生菌市場開了個門頭,一邊收購新鮮精品野生菌,一邊線上直播帶貨。
在菌子季,每天下午兩點王開煜準時開播,一直播到晚上,有時候吃完晚飯也會再直播一會兒。超長時間的直播,主要是展示野生菌從農民手中收購的全過程,“觀眾看見當天新摘的菌子,直接送到我們這裏,會更放心。”
觀眾多的時候有幾十個人,少的時候十幾個人,雖説今年還沒建立起更多的粉絲流量,但由於雲南野生菌單價高,遇到大客户時,一場直播也能收穫幾萬塊的銷售額。
“野生菌在線上渠道主要賣去廣東、北京、上海這類一線城市,廣東的消費者最多,物流走順豐冷鏈,今天發明天就能到。”
愈發忙碌後,王開煜將拾菌團嚮導的工作分了一部分給自己的表哥表姐,他們也正是小時候領着王開煜一起認菌子的夥伴。外地人認菌、拾菌主要依賴專業書籍、拍照對比,詢問當地人或者專家學者,而云南本地人的拾菌本領則是全靠口口相傳。
家鄉村子附近有好幾座連綿的高山,王開煜開發出了5、6條路線,每天帶遊客換着路線採摘。與此同時還在村裏專門找了個小院子,辦理了餐飲許可證,如果遊客想品嚐野生菌,也可以在採摘結束後跟隨嚮導回去處理、加工野生菌。

這是當地人帶團與外地人帶團很不同的一點。“很多同行都不讓客户把菌子帶走,更不建議客户自己吃。但我們是本地人,從小經常食用野生菌,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分得很清楚。”
我又想起先前江江説的:“對於當地人來説,野生菌只分成兩大類,能吃的和不能吃,不能吃的統稱為雜菌,他們不會特意記菌子的名稱。而能吃的菌子,又分成好吃的和不好吃的,説起好吃的菌子當地人才會滔滔不絕。”
王開煜證實了這一點。不同於外地領隊和外地人,痴迷於尋找美麗的“毒蘑菇”,當地人做嚮導時根本不讓遊客採毒菌子,如果偶然遇到了,當地人一般會用棍子把其敲碎、搗爛,避免別人誤食。
“採摘菌子之後,我們還會把被翻開的樹葉、松針恢復為原樣,這樣會把生態保護得好一些,不然被採摘過的地方,明年就不會再有菌子了。”

無言的山脈,會説話的菌子
採摘路線對於拾菌團而言,是最重要的財富。路線是否好走,產菌量是否充足,決定了遊客的採菌體驗,也決定了拾菌團的營收。
但有些路線,已經很難再採到野生菌了。
“你們那天走的路線已經是第三代路線了。”江江告訴我們,2022年她們走通的第一條的採菌路線,在蒼山無為寺附近,這條路線早在去年9月份就已經人滿為患,菌子數量鋭減了,於是她們又尋找了第二條便於攀爬且風景優美的拾菌路線。
然而,今年走進拾菌生意的人太多了。第二條位於大理大學附近的路線,今年6月又被同行擠爆了,江江甚至還遭遇了惡性的同行競爭:“有個‘朋友’第一天報了我們的團,第二天就自己帶客户上山拾菌子去了。”
蒼山無言,但野生菌的數量説明了一切。
江江明顯感受到了這條線路上的菌子量,與去年截然不同:“去年在那邊見到的野生見手青,都是一窩一窩的,今年都是獨苗苗。”
雖然一個野生菌可以散發100萬個孢子,孢子會飛得到處都是從而保證繁衍,但有些地方因為過度採摘,野生菌仍處幼年就被摘走,已經沒有散發孢子的機會了。一些業餘領隊帶的團隊不會保護野生菌的生長環境,也會使得泥土環境變幹,許多孢子無法長出。

拾菌團之間的價格戰也開始打響。在小紅書上,最便宜的拾菌團只要20元一人,行業整體均價從去年的普遍過百元,降至80元左右。江江表示有同行去年還收168元,今年只收60元,不然就要面臨客户的流失。
拾菌這項剛誕生不過兩三年的項目,業態正以最快的速度變得魚龍混雜。有些領隊只是暑假在大理旅居幾個月,看到拾菌能賺錢、好獲客,只要把價格壓低就能在行業裏大賺一筆,很難阻擋這種誘惑。
可這也造成了拾菌體驗的下滑。有遊客告訴我們,滿心期待的雲南採菌之旅讓人大失所望,菌子很少,領隊不負責、林子裏的平地上散落着其他隊伍離開前丟下的菌子,讓人覺得可惜又可氣。
目前對於拾菌團這類旅遊項目,雲南當地尚沒有統一的監督管理方案,全憑組織者的良心自我約束。
此前江江已經申領了旅遊業的相關營業資質,王開煜近期也正在籌備註冊公司、申請執照,他給我們發來了長長的材料清單。
但對於許多隻想賺快錢的人來説,他們並沒有把項目合法化的需求,也沒打算註冊公司,菌子季一結束,他們就會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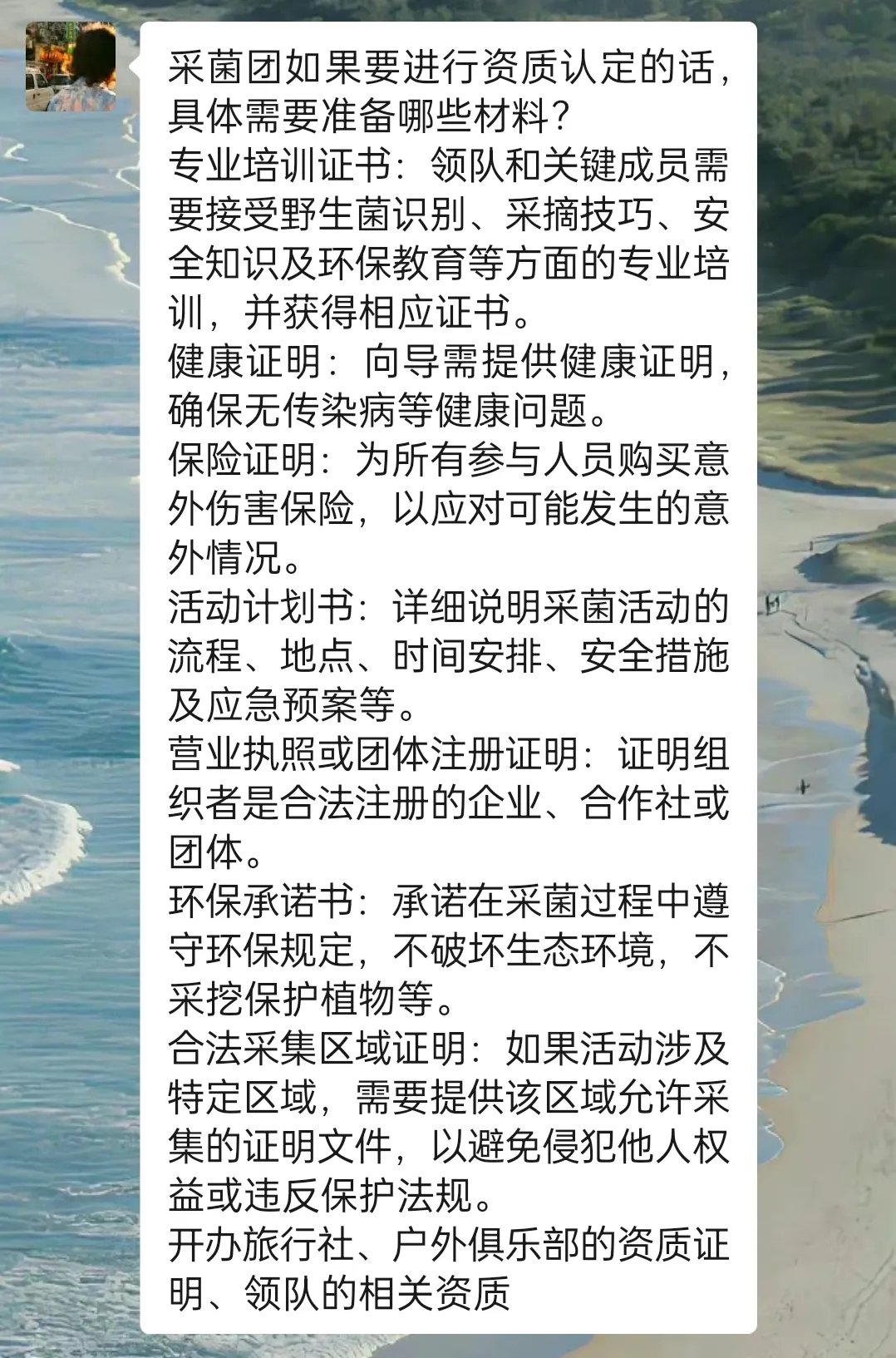
路線被走爛了,成窩的野生菌不見了,當地人喜憂參半,喜的是靠野生菌賺錢、吸引遊客的渠道又多了,憂的是“你們把菌子都摘走了,我們吃什麼啊……”
最先發布新規的是雲南楚雄市政府。今年的8月1日,楚雄的《野生菌保護利用管理辦法》正式施行,這是全國首個野生菌保護管理規範性文件。
主要內容包括:要求使用科學規範的採集方法,如使用木棍、竹片等工具輕輕挖出子實體,避免使用鋤頭等大型工具破壞菌塘,同時,採集時應留足子實體以供自然傳播菌種;禁止採集、出售、收購、運輸未成熟的野生菌(如長度小於5釐米的松茸、牛肝菌等)及過熟的野生菌;此外,還禁止對野生菌和野生菌生長環境施用農藥、化肥等有毒有害物質等等。
具體到某個年份來看,菌子的生長週期決定了這會是一門季節性的生意,但是從十年、二十年、甚至百年來看,野生菌的生態需要保護。
臨近10月,今年的菌子季就要結束。蒼山的採菌隊伍逐漸變少,山脈開始變得冷清,億萬野生菌的孢子和菌絲將在泥土中沉睡,等待來年的下一個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