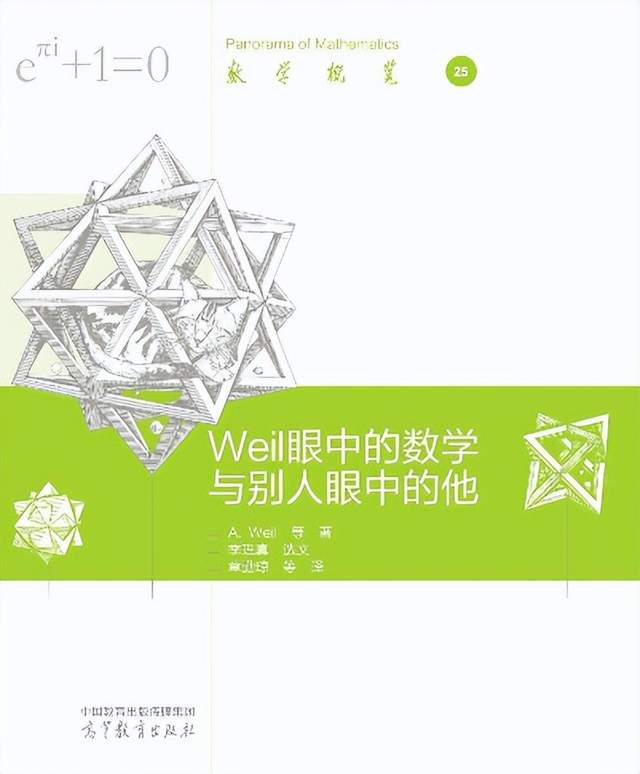韋伊女兒深情回憶父親:他最恐懼的是無聊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5小时前
在女兒記憶中,大數學家André Weil是什麼樣子?一件件生活趣事,她為我們翻開了私藏相冊。
撰文 | Sylvie Weil
翻譯 | 章勤瓊等

距我[1] 父親逝世的日子(1998年8月6日)大概有20年了。但至今,他有時候還會呼喚我:Sylvie,帶我離開這吧。我很無聊(他用的法語並不那麼客氣)。
我相信,按照猶太人的傳統,André有了一個終身的學習夥伴。我曾經問過他這個同伴是誰。“Euler。”他回答,然後笑了笑。所以,當他叫我並告訴我他很無聊時,我會問:“Euler怎麼樣?他也很無聊嗎?”
沒有什麼比感到無聊或浪費時間更讓我的父親恐懼的了。(他的)每一刻都需要被有效或愉快地利用。我至今還保留着父親在我十幾歲時給我的信。他推薦了非凡的節目:晚上閲讀Euripides和Sophocles[2]的作品,週四在盧浮宮遊玩或觀看法國喜劇,週日下午在普萊耶音樂廳聽Beethoven……這些信中呈現出的理想主義讓我愉悦,但也激發出了我可怕的內疚感,因為15歲的時候,我只是想好好享受美好時光。
和André一起就餐總會感到一些壓力,我們需要聊些有趣的話題。吟誦Racine的詩是很受歡迎的,更好的是吟誦Virgil的詩。然而,很難避免被批評,André的反應很可能是:“我可憐的女孩,他們沒有教你正確地重讀拉丁文嗎?”但他的日常安排並不一定都是嚴肅的。他喜歡Satyajit Ray和Kurosawa(黑澤明)的電影,喜歡游泳、滑冰……他可能也會表現得非常誇張。當我和妹妹還是孩子的時候,他給我們讀了“Molière的喜劇”。他非常擅長扮演年輕的女郎,並且發出一種讓我們欣喜若狂的假聲。
大多數時間,我覺得和這樣父親一起長大很特別,他不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數學家之一,而且常以傲慢、諷刺和威嚴聞名於世。博士後會把我和作業一起送到他的辦公室來了解這位偉人的心情,這太可怕了。如果聽到他對我大喊大叫,他們就會離開!
正是André傲慢自大的名聲,讓童年的記憶如此“美妙”:可怕的、傲慢的數學家André Weil在他的睡衣外披了一件雨衣跑進雨裏,在美國西部某個破舊汽車旅館燈光昏暗的院子裏敲着門,絕望地乞討着二十五美分。在我們那間糟糕的房間裏,有兩張吱吱作響的牀,媽媽、姐姐和我正在投幣式電視上看電影,而我們沒有錢投幣了。André的乞求失敗了,我們也不知道電影裏那個失聰的年輕漂亮女主角身上發生了什麼。
2008年,Simone Weil[3]百年誕辰臨近,顯而易見,大量關於她的書籍也即將出版。我一直扮演着“聖女侄女”這種可疑的角色,或者可以説是“遺蹟”,因為完全陌生的人可以隨意接近我、觸摸我,甚至親吻我,就像他們驚歎的那樣——“哦!你長得多像她!”現在是時候寫別人都寫不出的書了。
當然,Simone比André更為人所知。因為更多的人有能力,或者認為他們有能力閲讀哲學、政治或神秘的著作,而不是數學著作!是的,在許多人看來,她是一個聖人!
但是不寫關於André的事情似乎是不公平的。這是一個平衡的問題,尤其是因為我一直把André和Simone看作是一對奇怪的雙胞胎。除了做聖人之外,我的姑媽是我父親的“複製品”,她和我父親長得像雙胞胎。這對我來説是個很可怕的“複製品”,因為我長得很像她。我長得也很像我的父親。[4]
當然,這種相似性影響了我們的關係。André覺得Simone被他們母親的溺愛過分地庇護了,遠離了日常的生活,所以他鼓勵我獨立!有一次,在我12歲的時候,我不得不穿過法國去親戚家度假,這次旅程包括三次火車的換乘。André寫信給三個站長,請求他們看到我後幫助我。在每一個車站,我都確定站長沒有找到我,我是靠自己換乘火車的。回到家後,我告訴了父親。他很高興,説:“我盡了父親的職責,你盡了女兒的職責。”
在我的書中,我想做的不是寫傳記,而是重温,並重建一個“Weil空間”。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再次引用我書中的一章,標題是“Euclid之美”。
我在Simone的一本筆記本上讀到:
“現代數學家的公理系統。他們在找什麼?他們做數學時不理解它的用法。
(問André:當他成功的時候,他會感到快樂嗎?還是審美上的快樂?)”
我讀了這個……突然,不由地感到美妙。上面的括號裏有着一個小家庭的團聚。這個家庭是我的……我想象着在家裏的廚房裏吃午飯,有我祖母的特色泡菜,一瓶雷司令,還可以聽着Simone和André的對話。André像他有時告訴我的那樣,告訴他妹妹,數學不是科學而是藝術嗎?他有告訴她奇蹟般的經歷一個接一個地相互流淌碰撞的思想的快樂比性的快樂更為優越嗎?因為它可以持續幾個小時,甚至幾天,就像他後來寫的那樣。
1938年Bourbaki會議期間拍攝的一張照片顯示我父親興高采烈地高調地按着門鈴。Simone在那兒,非常認真地,俯身看她的筆記本! 這張照片是在我出生之前拍攝的,但那是圍繞着我童年的角色。Bourbaki學派充滿激情、理想主義,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非常無私,他們在文章上的署名為南卡大學(南希芝加哥)Nicolas Bourbaki。
但是,Bourbaki學派的無私和理想主義的激情是不會高調宣傳的!在阿爾卑斯山的一家小旅館裏,有一個臭名昭著的集會,當這些紳士們互相猛烈地尖叫時,旅館老闆給憲兵打電話了,擔心有人會被謀殺。
我必須提到,André的第一個興趣似乎不是數學,而是槌球。這讓他產生或者可能激發了他對幾何學的興趣。我祖母Selma,幽默但自豪地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宣佈了這一轉變,那時André都七歲了。
恐怕André熱情的天性沒有給他太多的阻礙,特別是沒有妨礙他的傳統禮儀。有一次,在普林斯頓的一場音樂會上發生了騷亂,一個坐在André前面的人被擔架抬走了。音樂會重新開始,但人們卻在竊竊私語。我父親憤怒地要求他們安靜下來。一位女士朝他噓了一聲:“那個人死了!你知道嗎?”——“那又怎樣!”André回答説:“臨死時能聽Mozart的音樂並不是最糟糕的事情!”這正是他自己的願望:聽Mozart的音樂死去。遺憾的是,我沒能安排好。
1939年,令人振奮的Bourbaki大會之後的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1939年12月在赫爾辛基,父親被捕的故事眾所周知了。Rolf Nevanlinna的故事版本講述了他是如何拯救André以免被當作蘇聯間諜槍斃的。在被轉移到瑞典、丹麥和英國的各個監獄後,他因沒有服兵役而被監禁在法國。
在我寫書的時候,我在一盒文件中發現了一張小紙。我立刻把它叫作“家庭畫像”。四個簡短的句子,四個手寫體,事實上,對我來説都是那麼熟悉,就像是真人。毫無疑問,第五個人出現在信上的形式是一個巨大而粗糙的深藍色字體——監獄主管。1940年2月,André在魯昂監獄。家人來看他,當班警衞卻拒絕他們進入,不能探視。我能想象我的祖母用一種非常有説服力的氣魄抨擊。衞兵被説服了,他答應可以給我父親一封信。四個人去了咖啡館,監獄對面總有個咖啡館。他們每人寫一個句子。首先是三個藍色的句子,可能是用我母親的鋼筆寫的:Selma,Simone和我的母親Eveline。我外祖父Bernard拒絕使用藍墨水寫字,他的句子是黑色的,有可能是用從咖啡館借來的鋼筆。
一張集體照可能會説謊,因為每個人都會努力裝出愉快的樣子,也許會用微笑來掩飾自己的感情。但這四句話沒有掩飾!雖然很簡潔,但是每一句都是絕對真實的性格,揭示了每個人與André的情感關係。Selma和Eveline在情感表達上是相互競爭的,Simone希望她的哥哥正在寫詩,夢想着美麗的定理。Bernard不像女人們那麼熱情洋溢,只是希望他們很快能再次見到André。從這張紙條上,我可以構建一個完整的Weil家庭場景,好像我去過那裏一樣。
事情後來如何了?幾個月後,André被判入伍,然後被流放到英格蘭。
1994年,我父親獲得了京都獎。我陪他去了日本。日本對我來説是一個神秘的地方,一個被André描述成充滿想象的地方,那時我和妹妹都是小女孩。1955年,在日本待了一段時間後,他帶着對日本的迷戀離開了日本。他教我們如何鞠躬,如何用筷子吃飯,如何用小浴巾。當電話鈴響時,我們會趕忙去接電話,然後回答“喂!”André解釋説:“在日本,永遠不要表現出你的情感。這是不禮貌的,你必須一直微笑。”
我和父親在京都的前兩天晚上,我們離開了他看不上的豪華酒店,去一家酒店女僕推薦的簡陋餐館吃飯。當我們慢慢地走在一條黑暗的小街上時,André在解釋和評論我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時,我覺得我回到了童年時想象中的日本。
André很高興見到了Kurosawa。“我比你有很大的優勢,”他對那位著名的導演説,“我可以喜愛並欣賞你的作品,而你卻無法喜愛並欣賞我的作品。”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刻薄的恭維。他們錯了,André非常真誠。
在東京的最後一個早晨,當我們在等出租車送我們去皇宮時,寂靜令人壓抑的氛圍使André感到厭煩。他轉向Kurosawa:“天皇喜歡你的電影嗎?”在一段短暫的沉默之後,Kurosawa鞠了一小躬,回答道:“陛下是一個偉大的天皇。”
在京都,有無數的儀式。這些需要“表演”,但現在André已經老了。他不想表演或鞠躬,他不再想當日本人了。我負責照顧他。有時我覺得我是一個文樂(Bunraku)木偶演員,他是我的木偶!有時候我希望能給我的老父親買一個漂亮的日本面具,甚至是一個可怕的紅金惡魔面具,因為他不想笑,也不想再作出禮貌的樣子。
最後,他不需要面具。我看了三位京都獎獲得者的官方照片。Kurosawa微微地笑,肥肥的、高高的美國科學家開心地大笑。老矮人André擠在兩個巨人中間,笑到最後。他把手從那堆手上拉開,這是一隻結實的手。他獲得了自由!

註釋
[1] Sylvie Weil 是數學家 André Weil 的女兒,也是哲學家 Simone Weil 的侄女。她的書 At Home with André and Simone Weil 是 20 世紀最有趣的知識分子家庭的親密寫照, 已從法語版翻譯成 多種語言。
[2] Euripides,Aeschylus 和 Sophocles 並稱為希臘三大悲劇大師。
[3] Simone Weil是André 的妹妹, 作者的姑媽。
[4] Simone Weil 的 At Home with André and Simone Weil,Benjamin Ivry 翻譯,原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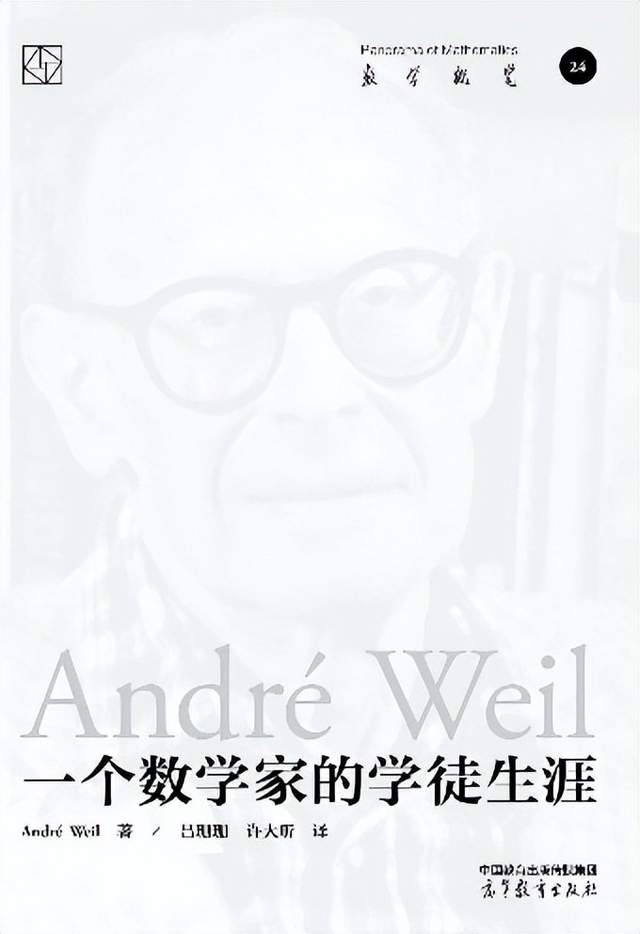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