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場雜誌丨1%有,1%治,1%享_風聞
听桥-57分钟前

繪圖:Stephen Doy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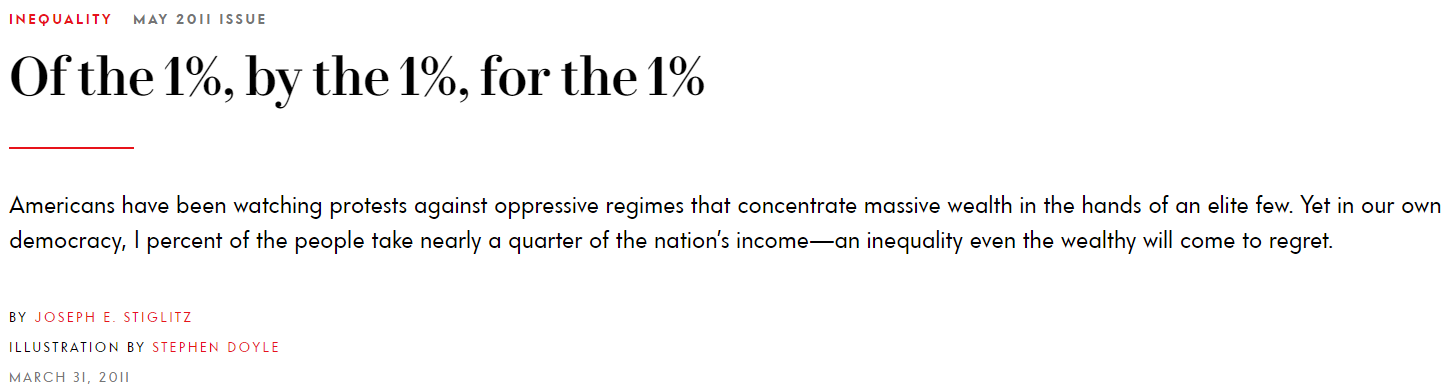
原文截圖
譯按
本文是一篇舊文,原題“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原載美國《名利場》雜誌2011年5月號。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生於1943年2月,是美國經濟學家,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曾在1997年至2000年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總裁。
譯者聽橋,對機器形成的初步譯文有修正,對原文有多分段。斜體字為原文所有。
**名利場雜誌丨1%****有,1%****治,1%**享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假裝顯然已經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沒有發生,是無所助益的。
美國更上層的1% 人羣眼下每年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近四分之一。就財富而非收入而言,最頂層的1%人羣控制着美國財富的40% 。他們的生活有極大改善。二十五年前,相應的數字分別是12% 和33% 。
一種回應可能是讚揚給這些人帶來好運的聰明才智和十足幹勁,並聲稱大潮漲起會抬升所有船隻。這一回應會是錯誤的。過去十年裏,最頂層1%人羣的收入增加了18% ,中產階級的收入卻下降了。對只有高中學歷的男性來説,下降是急劇的:僅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間,就有12% 。
近幾十年裏,所有以及更多增長流向了社會最頂層人羣。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國落後於小布什總統曾嘲笑過的任何一個古老而僵化的歐洲國家。與我們最接近的對手是寡頭眾多的俄羅斯,還有伊朗。巴西這樣拉美的古老不平等中心,近年來尚且一直在努力,相當成功地改善了窮人的困境,縮小了收入差距,美國卻任由不平等加劇。
許久以前,經濟學家就試圖為十九世紀中期看上去令人極度不安的巨大不平等辯護,但當日的不平等相較於我們今天在美國所見,只能是黯然失色。他們拿出的理由被稱為“邊際生產力理論”。簡言之,這一理論將更高的收入與更高的生產力和對社會的更大貢獻聯繫在了一起。富人對該理論一直青眼有加,但其效力的證據始終是薄弱的。
那些幫助釀成了過往三年間經濟衰退的企業高管,為我們的社會以及他們自己的公司的貢獻了巨大負面後果,但繼續領到鉅額獎金。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公司極其尷尬於將這種獎勵稱為“績效獎”,乃至於它們覺得不得不把名稱改為“留任獎金”(哪怕唯一留下的是糟糕的績效)。相較於那些要為造成我們的全球經濟差一點崩潰的金融創新負責的人,那些為我們的社會貢獻了重大積極創新的人士,如理解基因的先驅和信息時代的先驅,只收獲了微不足道的報酬。
有些人琢磨了一下收入不平等,然後聳聳肩。那麼,假如這個人得到了,而那個人失去了呢?他們認為,重要的不是如何分蛋糕,而是蛋糕的大小。這種論調從根本上説是錯誤的。一個像美國這樣,其最大多數民眾年復一年生活狀況惡劣的經濟體,長期而言不太可能運轉良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日漸加劇的不平等,其另一面是機會減少。每當我們削弱機會平等時,就意味着我們沒有以可能的最高效方式利用我們的某種最寶貴資產——人民。其次,導致不平等的許多扭曲 (比如,涉及壟斷權力和服務於特殊利益集團的特惠繳税待遇的扭曲)損害了經濟的效率。這種新的不平等繼續製造了新的扭曲,進一步損害了效率。僅舉一例:我們最有才華的年輕人中,有太多太多人因為見證了天文數字般的回報,所以進入金融業,而不是那些可能形成一個更具創造力的健康經濟的領域。
第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現代經濟需要“集體行動”,即需要政府投資於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美國和全世界都極大獲益於政府資助的研究,那些研究催生了互聯網,帶來了公共衞生等領域的進步。但長期以來,美國在基礎設施(看看我們的高速公路和橋樑、鐵路和機場的狀況)、基礎研究和各級教育方面投入不足。這些領域的投入即將遭到進一步的削減。
沒有一點理當驚詫眾人:那只是當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變得一邊倒時會發生的情況。一個社會在財富方面越是分化,富人就變得越是不願在人們的共同需求上花錢。富人不必依靠政府建設公園、接受教育、提供醫療服務或提供個人安全保障,因為他們可以為自己買到所有這些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變得更加遠離普通人,失去了他們曾經擁有的同情心。他們還擔心強有力的政府:這個政府可以利用其權力調整平衡,拿走他們的部分財富,並將那些財富投入於公共利益當中。最頂層的1% 人羣可能會抱怨我們在美國擁有的那種政府,但事實上他們喜歡這樣的政府: 它太僵化而無法實現重新分配,太分裂而做不成任何事情,只好去減税。
經濟學家不確定如何圓滿解釋美國愈發加劇的不平等。尋常的供求關係變化無疑是一個因素: 節省勞動力的技術減少了對許多“好的”中產階級藍領工作的需求。全球化創造了一個全球性市場,令美國昂貴的非技術工人與海外廉價的非技術工人勢同水火。社會變革也是一個因素:例如,工會的衰落。工會曾經代表美國工人的三分之一,而眼下代表12% 左右。
但我們之所以有太多不平等,一大原因是那1% 的人羣想那樣。最凸顯的例證是税務政策。降低資本利得税率(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資本利得),給了最富有的那些美國人幾乎是免費搭車的機會。壟斷和近乎壟斷,一直是經濟實力的來源,從上世紀初的約翰·洛克菲勒到上世紀末的比爾·蓋茨都是如此。反托拉斯法的拉胯執行,尤其是在共和黨執政期間,已經成了最頂層1% 人羣的天賜良機。今天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金融體系受到操縱,而金融業自身收買和付費的那些規則的變化造成了這一點:這是金融業有史以來的最佳投資之一。政府以接近零的利率借錢給金融機構,並在其它所有措施都失敗時,以優惠條件提供慷慨的救助。監管機構對缺乏透明度和利益衝突視而不見。
當你審視這個國家最頂層1% 人羣控制的財富總量時,你很難不把我們愈發加劇的不平等看作是典型的美國成就:我們開始的時候遠遠落在後面,但眼下我們正在締造世界級的不平等。而且看起來,未來一些年我們將有賴於這一成就,因為成就此番景況的因素正在自我強化。財富催生權力,權力催生更多財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儲蓄貸款醜聞發酵期間,銀行家查爾斯·基廷(Charles Keating)被一個國會委員會問到,他在幾位關鍵的民選官員當中分發的一百五十萬美元,是否真的能買到影響力。按照今天的標準,這場醜聞的規模顯得完全不可思議。“我當然希望如此,”他回答説。最高法院在最近的聯合公民一案中取消了對競選支出的設限,由此莊重載明瞭企業收買政府的權利。今天,個人和政治是完全一致的。
事實上,所有美國參議員,以及眾議院中的絕大多數議員,他們到任時都是最頂層1% 人羣的一員,他們的在任是由最頂層1% 人羣支出的金錢維持的,他們也明白,假如他們妥帖服務最頂層的1%人羣,當他們離任時,他們就將收穫那1%人羣的回報。總的來説,貿易和經濟政策方面的關鍵行政部門決策者也來自最頂層的1% 人羣。當製藥公司因禁止最大的藥品買家即政府的討價還價而收到一份一萬億美元的禮物時,這不應成為驚訝的理由。除非對富人大幅減税,否則國會就不會通過某項税務法案,這不應讓人瞠目結舌。考慮到最頂層1% 人羣的權勢,這就是你會期望的這個體制的運轉方式。
美國的不平等以各種可以想見的方式扭曲了我們的社會。首先,生活方式上的影響是證據充分的:最頂層1%人羣以外的人士越來越多地入不敷出。涓滴經濟學可能是一種虛妄的構想,但涓滴行動是非常真實的。不平等嚴重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最頂層1% 人羣很少服兵役:事實上,“全志願”軍隊沒有足夠的薪水可以吸引他們的兒女,愛國主義也只能到此為止。另外,當國家陷入戰爭時,這一最富有階層不會因為更高的税率而感受到痛苦: 借來的錢將為所有一切買單。根據定義,外交政策關乎國家利益和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由於最頂層的1% 人羣負責發號施令,而且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平衡和剋制之説是不存在的。對我們可以從事的冒險事業,限制是不存在的;公司和承包商只會得到好處。
經濟全球化規則的設計同樣令富人獲益,那些規則鼓勵國家之間的商業競爭,那種競爭降低了企業税,削弱了健康和環境保護,破壞了過去被視為“核心”的勞工權利,其中包括集體談判。想象一下,如果那些規則的設計反過來是為鼓勵各國之間爭取工人的競爭,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政府將在提供經濟保障、對普通工薪階層實施低税政策、良好教育和清潔環境方面展開競爭:這些都是工人關心的問題。但最頂層的1% 人羣不需要關心。
或者,更準確地説,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關心。在最頂層1% 人羣強加給我們社會的所有代價中,或許最大的是: 對我們身份認同感的侵蝕。
在我們的身份認同感中,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區意識極其要緊。長期以來,美國一直為自己是一個公平社會而自豪,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出人頭地的平等機會。但統計數據卻昭示了不同的情況: 一個貧窮的公民,甚至一箇中產階級公民,在美國步入社會頂層的機會比在許多歐洲國家都要小。他們的處境非常不利。正是這種制度不公、缺乏機會之感引爆了中東的衝突: 不斷上漲的糧食價格和不斷加劇且持續存在的青年失業,只是充當了導火索的作用。美國的年輕人失業率約為20% (在某些地區、某些社會人口羣體中,這一數字是兩倍) ; 每六個渴求全職工作的美國人中,就有一人無法如願以償; 每七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領取食品券(大約同樣數量的人受到“食品不安全”問題的侵害)。
——考慮到所有這些,有充分證據可以表明,有什麼東西阻止了被吹噓的“涓滴效應”從頂層的1% 人羣流向其他所有人。所有這些都形成了可以預見的疏離效應:在上次選舉中,二十多歲選民投票率為21% ,與失業率相當。
最近幾周,我們看到有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壓迫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在埃及和突尼斯,政府已被推翻。在利比亞、也門和巴林,抗議活動爆發。該地區其它國家的統治家族在他們帶空調的頂層公寓中緊張地旁觀這一切:他們的國家會是下一個嗎?他們有道理擔心。在這些社會中,極小一部分人口(不到1%)控制着最大一部分財富; 財富是權力的主要決定因素; 這種或那種根深蒂固的腐敗是一種生活方式; 最富有的一羣人往往積極阻撓實施那些會改善普通人生活的政策。
審視街頭大眾的熱情時,一個要問我們自己的問題是: 美國何時會出現這種情況?在一些重要方面,我們自己的國家已經變得像是那些遙遠動盪的國度之一。
托克維爾曾經描述他所觀察到的美國社會諸多奇特稟賦的最主要之處,即他所稱的“正確理解的私利”。“正確理解”是關鍵。每個人都有狹義上的私利: 我現在就想要對我有利的東西!“正確理解”的私利有所不同。這意味着要領會到,留意其他每個人的私利(換句話説,共同的福祉)實際上是個人自身最終福祉的前提。托克維爾沒有暗示這一見解有任何品格高尚或理想主義之處:事實上,他的意思恰恰相反。這是美國實用主義的標誌。那些精明的美國人理解一個基本事實: 照顧別人不只有益於心靈,還有益於生意。
最頂層的1% 人羣擁有最優質的房子、最優質的教育、最優秀的醫生和最優渥的生活方式,但有一樣東西似乎是金錢買不到的: 理解他們的命運與其他99% 人息息相關。縱觀歷史,這是最頂層1%人羣最終確實會學到的東西。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