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 我一氣採訪了5位動畫導演,鑽進了他們的白日夢_風聞
第一导演-第一导演官方账号-导演社群19分钟前
採訪、撰文/法蘭西膠片
四部動畫短片,四個前傳故事,五位新生導演,這是**第一導演(ID:diyidy)**圍繞個人新作的採訪策劃裏一次性觸及作者最多的一回。四部作品均來自騰訊視頻原創動畫短片集“青年導演系列”,又稱“白日夢繫列”。
叫白日夢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都在“造夢”——遠離或者擊碎這沉悶臃腫的現實,重塑一個新世界,或者,找到真正的新世界。為了做好這場白日夢,他們都在年輕時追尋世界最強的創作者,有美影廠,有日漫黃金時代作者,也有好萊塢名作,從中吸取最大的養分,然後進入而立之年,迴歸本土文化,釋放成熟的表達。

他們有的已經在國內知名節展斬獲大獎,有的從漫畫家轉身,換一個載體去呈現人文主義的世界觀,有的用靈活機動的工業流程服務並紮根於中國古文化古哲學,還有的創作者,他並不崇拜萬物理論的幽深,只願製造一個輕盈的避風港,請所有孤獨的人在此棲息。你能感受到在這樣的環境裏,這些創作者仍有蓬勃的書寫動力,仍不放棄對動畫最原始魅力的探尋,因為真的有積累也真的渴望表達,他們產生了明確的影像信仰。
白日夢一定有醒來的時候,因為現實在不斷震動,但醒來時,你多了一份篤定。
01
首獎
《糖果狂想曲》導演應勳:加班回家得知在FIRST影展拿獎,感覺很虛幻
**第一導演:**FIRST獲獎那天,你怎麼沒在西寧?
**應勳:**因為我們當時有個廣告項目在做,剛好有衝突,所以就沒去成。
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剛好加班完回家,突然一個行內的朋友微信發了圖片給我,得獎了。真是突如其來的感覺,挺不真實的。
我其實很早就關注FIRST影展了,印象裏是偏獨立藝術一點,在行業裏挺專業的,所以就更感覺虛幻,本來能入圍就已挺幸運了。
所以這個結果對我挺有鼓勵的,第二天我就在團隊裏組織了一個看片會,大家吃了一頓蛋糕,算是慶祝一下。
像我們這種做定格動畫的,工作週期比較長,每天只有那麼一點點進展,大家都不知道最終出來會是什麼樣。有這麼一個獎,確實對大家激勵也是挺大的,最起碼這次能給更多的人看到。

**第一導演:**話説這次騰訊視頻是怎麼找你合作呢?
應勳:這個故事有點長,我們最早大概在2017、2018年的時候,看到了阿國老師的插畫繪本**《糖》**,特想把那個繪本改編成電影,為了做這個電影,我們做了一個測試片,大概兩三分鐘,沒什麼情節,但是把角色的設定、氛圍基本上做了出來。
後來不知道再怎麼就被平台的製片人看到了,我們也沒上傳過,可能是因為一直在跟不同的公司接觸,圈內關係近的就看到了,剛好他們在策劃“白日夢”的原創動畫短片集項目,就把我們這個短片加了進去。
第一導演:《糖》這個繪本對你的吸引力在什麼地方?
**應勳:**我比較喜歡它的形象,它不是很傳統的國風,但也不很西式,或者説,**它帶一點西方的美術氣質,但還是有挺傳統、挺本土的一種設計。**故事本身簡單,但是能讓我發揮的東西還挺多,可以虛實結合地做。
其實我們現在還是保留了原來故事背景,只是把整個的時間設置成為長片電影的一個前傳。小女孩安妮原本在長片裏是一個十八九歲成年的女孩子,而且她是一個孤兒,用這個背景作為我們自己重新設定的故事,形成了《糖果狂想曲》。**現在除了兔子怪,所有角色都是繪本里面沒有的,**還有很多羣眾路人角色,我們就用公司員工的形象來定,所以街上一個個走的都是我們公司同事。
平台方對我們這個做法沒有太多異議,當時粗剪一出來,他們也經過好幾輪內部的看片,覺得我們做得挺精緻,挺喜歡的,可能就唱歌時的歌詞有一點調整吧,我們的自由度很大,挺感激他們的。
**第一導演:**説到唱歌,你為什麼會想到用音樂劇的類型?
**應勳:**這可能跟我自己有關係,因為我喜歡每個片子都有一點不一樣的東西,能有一種新的嘗試。還有就是,我個人比較看中故事邏輯,邏輯不通的話,這個故事我講不下去,我自己就會找出其中很多漏洞,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但是音樂它本身可以避免你對邏輯太去較真,放在短片上這點會比較討巧。
另外對於音樂類型本身,有兩部片子對我影響挺大的,就是蒂姆·波頓的**《聖誕夜驚魂》和《殭屍新娘》**,算是給我埋下了伏筆。
**第一導演:**包括這個壞兔子的設計,它本身也有點哥特式的偏暗黑系的方向。
**應勳:**是,可能都是有《聖誕夜驚魂》的一些潛意識的關聯。
原來我們在做電影測試片的時候,怪兔子是完全按作者的設計來,它有幾個特點,眼睛很小,顯得很邪惡,牙齒很尖,小細牙,手指是很長的尖爪子。
問題來了,它如果手那麼細長,可能就拿不起來東西;牙齒很尖的話,我們做不到那麼精細;眼睛小,它的表情就不豐富,感覺什麼戲都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幾個地方做了修改,還有一些服裝上的改動,原來它的服裝可能有一些絲線拖得比較長,這會導致我們定格動畫拍攝變慢。

**第一導演:**説到這種製作細節,《糖果狂想曲》裏的糖果都是什麼材質做的,可以放真的糖果進去拍嗎?
應勳:沒有真的糖果,真的糖果容易壞,棚裏又熱,會化,還招蟲子,不是很好用。所以我們做的材料基本都是黏土,軟陶,還有一些樹脂,電影裏父女倆專門做糖的那個鏡頭,那個樹脂還沒定型,每拍一次要把它加熱,變軟,我們為此試了很多材料。
在某些幻想場景中,彩色圈層裏晶瑩剔透,那是有機玻璃和水晶做的,我們自己上的色,這些工藝都會花費很久時間,光測試它們就得花一點時間。稍微有點麻煩的是街道上的車需要亮燈,所以這些模型經常會拖着根電線,拍完以後就要把這根電線給修掉。
**第一導演:**説到車,電影重要情節是車禍與死亡,包括幾個怪物一直有死神的意味,你想表達的是什麼呢,對死亡的一種理解?
**應勳:**可能是吧,我不太擅長歸納這些,但我覺得有這方面的考慮。就像惡魔,我覺得也不是説一定就是邪惡,它可能就是一個本職工作,只不過它的工作原理跟我們的生活是違背的,對我們七情六慾來説是一種頂撞。
我覺得就像那句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規律,它不會看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東西,但是因為我們有豐富的情感,我們人世間才產生這種美妙,才讓惡魔也有點動了心思。
對於死亡,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正視死亡,不要避諱。當然了,我們整體沒那麼沉重,就比較童趣,比較動畫感。

其實當年我之所以投身這個行業,一開始並沒想拍動畫,而是想拍真人短片,但場景要花錢,演員要花錢,設備又很大,那時候沒錢,攝影機,燈光……那怎麼辦?後來就覺得,為什麼不自己搭一些景,做一些小人偶來拍?就試着拍一個定格短片,很粗糙,但很多人看了覺得挺好,慢慢就開始拍定格動畫了。
其實我不是學動畫出身,我的長處,或者説我的喜好點,就是取景,打光,去構建這個空間,至於角色動作交給專業的動畫師來做,術業有專攻。
第一導演:《糖果狂想曲》之後擴展成長片,還跟騰訊視頻合作嗎?
**應勳:**有這個可能性,當然還得看現在電影市場,我們這個週期長,風險也大。
02
拍檔
《山海戮:蜃景篇》導演鄧志巍&吳青松:我們都是自然世界裏能量循環中的一環
第一導演:《山海經》一直對國內動畫導演的創作影響非常大,不知道兩位怎麼看?
**鄧志巍:**其實《山海經》讀起來是非常晦澀的,要找一些資料或批註、翻譯文本配合着讀,光是看文字的話很難想象。
但是在作畫的時候又太具像了,就比如説《山海戮:蜃景篇》參考吳老師的漫畫原作,它裏面的神明有點帶西方神話的體系,這個跟《山海經》的架構也比較接近,就是在那種比較原始的文明剛興起,火種剛開始的時候,人類對這些自然界裏其它的競爭者或者是不可名狀的物理現象的觀察,他把它描繪成具像的想象。
**第一導演:**可是為什麼會有很多蒸汽朋克的元素出現?
**鄧志巍:**吳老師跟我提過,這個山海世界文明已經毀滅了好幾次了,所以這些人的服裝才會又有點蒸汽朋克,又有點漢朝的東西。
**吳青松:**是這樣的,後面的時代興起時,會繼承以前某些文明遺留下來的科技或文化,形成一種混合型的、雜糅的狀態。
其實最開始這個故事的起源是我在2005年的時候,快20年了,不知道是什麼情況,突然某一天,突發奇想,就想到這麼一個有很多很多山的世界,每座山裏有他們守護的神靈,有人類在這裏生活。
然後就想探討一下,因為現在的人類對於自然界是非常強勢的存在,我們按自己的喜好修改這個世界。就想如果人是很弱勢的話,在這個世界上如何與其它更強勢的東西,比如神或者其它生物共存,這會是什麼狀態。
當時畫了一個很粗略的設想,後來就停下來了,因為還要上班。後來大概在2015、2016年的時候,冥冥中天註定的緣分,我突然讀到一本關於《山海經》的書,可能是電商打折的時候買的,還不是《山海經》的原作,是一個白話文的譯版。我看這裏的內容怎麼跟我的世界觀這麼像?
因為《山海經》它其實也就是一個地理志,大概從春秋戰國時期一直到西漢左右時期形成的一部書,哪個地方有一座山,山裏面有什麼神,有什麼奇珍異獸,有什麼特殊的礦產……我當時一下懵了,本來我的故事跟《山海經》沒有關係的,名字也不叫《山海戮》,但是我看到之後就覺得,太有意思了,我就把這個名字給它改了一下,決定把這個事情重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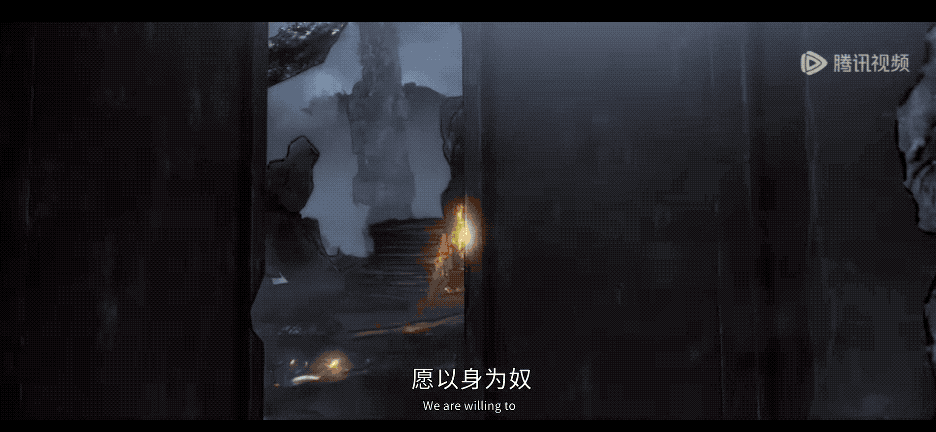
**第一導演:**那鄧導吳導都是怎麼和騰訊視頻建立合作的呢?
**鄧志巍:**首先是平台想做一些不同品類的動畫,因為現在小説、漫畫同質化很嚴重,當然也可能受了海外動畫短片集模式的啓發,想國內也搞一個。
**吳青松:**剛才你叫我吳導的時候,我心裏咯噔一下,我配不配啊?因為我的職業是漫畫家,沒有導演方面的經驗,不然這個東西完全交給我這樣一個什麼都不懂,只看過動畫的人來做的話,有很多東西是沒有辦法把控的,需要有一個成熟的導演來一起合作。
**第一導演:**你們第一次碰面都聊點啥?
**鄧志巍:**一上來認家門,互相介紹一下是哪裏畢業的。
**吳青松:**發現竟是校友!大家就親切了不少,就這麼直奔主題了。
**鄧志巍:**聊劇本,怎麼能在這20分鐘的短片裏讓觀眾認識《山海戮》這個世界?因為這算是個前史,要引出之後長片的角色。
**吳青松:**對,主要是世界觀的體量比較大,你想象一下,你把《指環王1》或者《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壓縮到20分鐘,你要闡述的東西,哪些保留,哪些一定得説出來,這種取捨是挺複雜的。
**第一導演:**很好奇,兩位平時怎麼一起工作?
**吳青松:**大多數時候是靠電話會議,有一些確實覺得必須面談,內容比較多的時候,就跑一下。還好,我在成都,鄧導在重慶,離得也不是很遠,高鐵、開車,幾個小時就解決了。
**鄧志巍:**我們在劇本環節見面的次數比較多,我記得見了三次,主要是這些東西它在吳老師腦子裏面。
**吳青松:**找一個茶館的天台,就開始聊。後來動畫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要大家一起坐下來邊看邊當面討論。
**第一導演:**有沒有彼此爭議比較大的點?
**鄧志巍:**有一點點爭議,我最開始不太理解吳老師對結局的設定,按道理,我們做這類片子,觀眾需要得到正反方的勝利時刻,不然的話觀眾會覺得,你給我鋪墊這麼多,祭祀、神明、舞蹈,結果神最後就走了,這個設定讓我有點擔心,感覺需要斟酌一下。後來我也理解了,神明只是一個生態系統,核心其實還是講人,講國度之間、種族之間、文明之間產生的問題。
**吳青松:**確實作為一個短片來説,最後如果沒有跟主角達成一個巨大的矛盾衝突,並解決這個矛盾衝突,那觀眾會覺得有一點莫名其妙。看了20分鐘,就這?會有這種可能性。
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我的世界觀是如此設定的,《山海戮》裏的這些神其實也叫屍神,它其實是已經死去的神,只是被某種力量重新強拉在一起,像屍體一樣拼湊起來的,成為自然世界裏能量循環當中的一環。
**而人開始以為我要去打敗這個神,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但其實他們最大的敵人是他們自己。**這個想法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因為我們人類沒有思考怎麼讓自己成為自然界的一部分,怎麼去共存。只是説這個短片沒有辦法講到這個層面上,可能會讓大家產生這種疑惑。

**第一導演:**我發現《山海戮》還有一些宿命論的東西,這是怎樣的想法?
**鄧志巍:**年輕的時候會這樣,特別是我30歲以前,不管看片子也好,還是自己做片子也好,這種想法特別多,對於打破常規,或者反抗,有那種潛意識的精神存在。但是年紀大了之後,尤其結婚生子,35歲以後,就變得温和很多了。
其實揭露一些特別激烈的矛盾衝突,當然有必要,但是站在我的角度,我想看看做點單純的東西,會不會也起到一樣的效果。可能從對立面的角度看,我是把頭埋在了沙漠裏,但如果能正面影響到觀眾,讓這些感受好的東西更多一點,也算是一個積極作用。
**第一導演:**把這種情緒或感受,轉化到角色身上時,有沒有什麼個人的創作法門?
**鄧志巍:**有,我一般在人物造型畫完後去做顏色時,會喜歡拍一些生活裏的局部,就比如説水果、花卉,或者是桌面上一些物品的局部,拍出來之後,我感覺這塊顏色情緒是什麼樣的,就把這個顏色分配到我想給的那個角色的性格情緒上。
這樣做顏色的話,在我的工作裏又快又比較統一。因為一般來説,做人物顏色的時候都需要一個主體色,就是整個人第一眼看上去是一個什麼樣的顏色傾向。但如果按照常規動作做了之後,再給身上那些雜七雜八的花紋或圖案做配色就很麻煩,這裏要用什麼對比色,加百分之幾的顏色,加白加黑……比方説我要做一個角色是藍色的設定,我把整個主體塗藍之後,他身上還是有其它小細節,要去確定它們的配色比例,真的很頭疼啊,要花很大的腦筋,很累,就像在做高考數學題,就不是很直觀。
所以我就做這種顏色設定的時候,比如説這個角色他比較開朗,那我可能去拍一些比較好看的水果,比較鮮明的水果攤的局部。它拍出來,人的色彩就是我剛才説的這種很開朗的性格。如果要拍那種很晦澀,或者是情緒很中性的,我就拍一些冰冷酒店的局部,顏色裏面帶一些高級灰。最後用PS把這個拍出來的局部照片標註上,就得到了一個對應角色的情緒。
它們就從生活當中來,就跟道家説的道法自然一樣。
**吳青松:**你這個辦法好,你這是讓大自然幫你調色,我還沒有想到過。
**鄧志巍:**主要是在大自然的光線下,所有東西都是相對和諧的,它不會突然出現很不搭調的,很突兀的配色,它都在一個調子裏。其實我也是偷懶偷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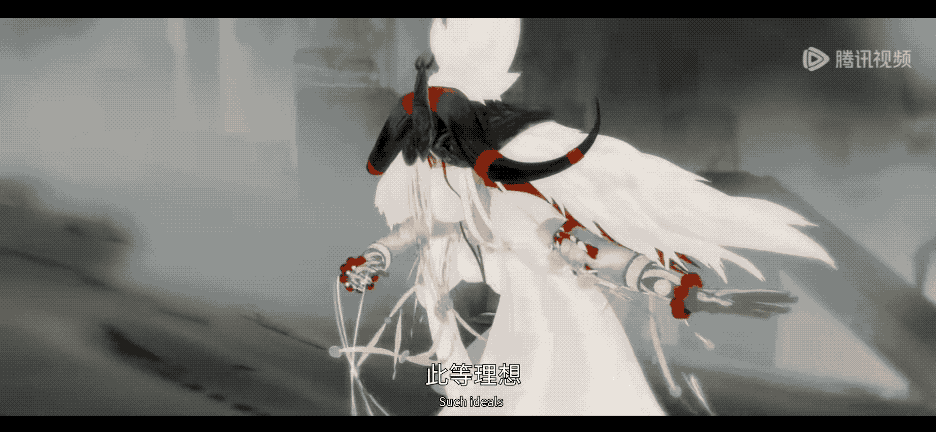
**第一導演:**那這是靜態的人設,涉及到動態的,尤其全片的動作戲,這實現起來有“偷懶”的捷徑嗎?
**鄧志巍:**這次動作戲有一種超級感,一些非人的行為,拋開寫實的武打,我們會提前手繪,畫一套動作,雖然説不是所謂的幀數補齊,但是也是一個流暢的動作展示,讓3D部門對着我們的動作去做,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有些動作戲也不是完全交給畫師,我們畫師是有一定的動作經驗,包括我自己,但是肢體的肌肉反應習慣,我們畫畫的人和習武的人還是不一樣,所以《山海戮》也找了真人電影的武術指導來幫我們設計一些動作,就是《目中無人》的動作團隊。
**第一導演:**説到打鬥,我感覺咱們都是從《少年週刊JUMP》過來的。
鄧志巍:像我這麼大的人,小的時候都是看日漫長大的,從小學的時候就開始在那種租書店裏,5毛錢去租一本,《龍珠》《美少女戰士》《亂馬1/2》這些。就跟現在小孩子玩手機、看短視頻一樣。到了小學六年級升初一的時候,看了《浪客劍心》,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一下,被戳中了,就覺得這個男人有一種魅力。
我突然產生了思考,人到底是怎麼做事情的呢?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精神內核?再加上那個故事背景我覺得很牛,就開始在書上畫小人、臨摹,上到初三開始學美術了。
**吳青松:**我跟鄧導成長時間差不多,我也是看這些日本漫畫長大的。我記得特別深,初一的時候,一個女同學聽説我會畫畫,叫我給她畫一個美少女,我畫得很亂,很土,之後就被嘲笑了。我就下定決心,練了一下,可能還是有一點天賦吧,練得還行,就為了獲得女同學的認可。後來有一年初二從成都回家的路上,要坐很久的長途汽車,在車上過夜,我就跟我旁邊的表姐説,以後我這輩子就畫漫畫!“莫名其妙,你瘋了吧?畫漫畫?”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少年的衝動,可能也是最純真的吧。
結果畢業後去報社工作,漫畫離你遠去,真覺得再也不會去涉足它了。誰知道在2005年的時候,成都做了一個國際動漫展,特別多的小朋友、年輕人去看,報社就成立了一個特別報道組,對這個動漫展進行一個比較深入的、大規模的報道,領導他們知道我以前喜歡這個,就把我放到這個組裏了,弄了一圈之後,銷量不錯,領導一直頭疼沒有年輕人看報紙,原來你們年輕人喜歡這個東西,就在報紙上開闢了一個版面,把我給抽到那個專欄做負責人。
我懵了,讓我做管理?搞得我頭大。但我獲得的好處就是,因為經常去報道這方面的新聞,就跟當時國內一些做漫畫的人建立了聯繫,對這個圈子有一些瞭解。36歲那年,我就辭職了,再不去拼一下,瘋一下,就沒有以後了。
03
迴歸
《字陣訣》導演宋瀏:遊歷西方,魂在江南
**第一導演:**先聊聊最初的創意吧。
宋瀏:我父親是一名園林設計師,也愛寫書法,刻印章,有一次,我看他在抄一個帖,叫《集王羲之聖教序》,你要學王羲之的行書,基本上都會去臨那個帖。
我發現這個帖的背後有很宏大的一個歷史故事,當時有一個僧人叫懷仁,用25年的時間集王羲之的字,做了一個“王羲之體”,相當於人肉打字機,把唐太宗寫給玄奘的序轉成王羲之的字體。
我當時覺得這個故事挺有趣的,想做這樣一個歷史題材,那個時候還很早,大概2019年,能力和資源都有限,做了一個兩分鐘的小樣片。
那這個樣片就被騰訊視頻看到了,平台方希望我把它做一些更商業化的拓展,我就結合自己喜歡的一些東西,比如説志怪的,就中國古代神神怪怪的東西,想出來用書法去降妖伏魔的概念。
我這個片子還有一名哲學顧問,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古代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林丹慧老師,我們一起構想這個世界觀,就提起王羲之當年有一位很厲害的女師父叫衞夫人,衞夫人有一個寫書法的口訣,叫“永字八法”,諸如撇如犀角、折如弩發,而永字八法有個前身就是**《筆陣圖》**。我們就以衞夫人的《筆陣圖》為靈感,給這個短片起名《字陣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這個故事設定裏不是妖怪,像《西遊記》是妖怪修煉成人,我這個是反的,是人因為各種執念,失去了人類的意識,變成了怪物,就相當於他降維或降級了。有的人極度貪婪,可能他就像妖怪一樣,或者有的人在當下的一個時刻特別憤怒,他跟野獸也沒有什麼區別。
林丹慧老師説這在學理上是説得通的,因為中國自古講天人合一,天地本來就有它自然的這種能量在裏面,但是當我們過大的慾望在干預或扭曲這種能量時,那他自己就會發生異變,與天地之氣就不和了,然後就會有所謂的霍亂。
第三點是視覺上的靈感,可能是來源於我比較受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老一輩的中國學派的影響,還有我現在的工作單位是蘇州工藝美院,它是江蘇省的一個大專院校,但它的前身是蘇州美專,這裏開設了中國第一個動畫專業,美影廠的老一輩藝術家都是蘇州美專培養的,我就一直在探索如何用中國的美術視覺講中國故事,就現在市場上大部分的古風的創作都很少用中國古代美術這個視覺系統裏的語言去講故事。比如説這次《字陣訣》的造型,人物的面部,眉弓到鼻樑,頭髮的細節,包括很多衣紋,披風斗篷,以及顏色也比較濃郁,這些都是借鑑敦煌的雕塑,很有一種裝飾性,視覺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我們這次在三渲二上的合作方杭州深零動畫,他們專業能力非常強,實現得很好。
所以,這次《字陣訣》創作靈感就來源於家庭氛圍的影響、跟志同道合的朋友的交流還有我自己的興趣愛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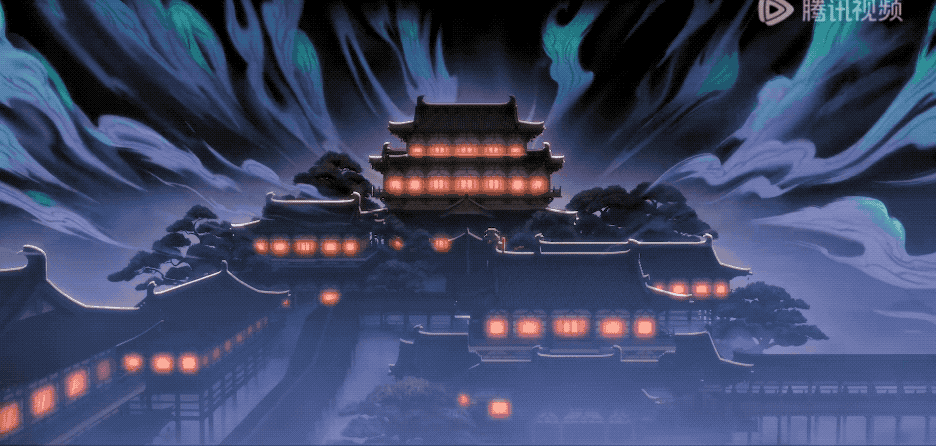
**第一導演:**比較花開銷的場景在哪裏,是後半部分捉妖嗎?
**宋瀏:**打妖怪倒還好,主要是開篇,因為要決定整個片子的風格,包括世界觀,戰鬥的系統,同時把書法的意象結合敦煌舞蹈的形態招式化,招式也是有一層層遞進邏輯的,花了很長時間,做了好多個版本,可能之前有比現在更好的版本,但為了考慮片子的整體性棄用了。
其實這個短片有點像一個先發集或者預告集,當時和平台策劃的時候,就是按照一個IP去打造的,劇本寫了十幾二十幾稿,限於篇幅很多沒展示出來。
其實男主角出自一個叫字修門的門派,這些人從最早的老祖宗,中國寫字的倉頡,皇帝的史官,一代一代傳下來,甚至王羲之也是一個這方面的大師,書聖嘛,他的筆就有點像哈利·波特的魔杖,筆頭用的什麼毛,筆幹又是什麼材質,是竹子的還是烏木的,筆端的裝飾是玳瑁的還是瑪瑙的,一根筆分成三部分,很像魔杖的魔芯、魔尾的概念。
**而筆“開”之後,每一支筆的性能都不一樣,有的攻擊力特別強,有的適合防守。**字修門在故事裏已經沒落了,其實也是映照現在的文化環境吧,練字真的需要挺心平氣和,你哪怕寫草書,速度比較快,和這個快節奏的網絡時代比,也很少人寫字,用它修身養性了。
**第一導演:**話説你是怎麼投身到動畫這一行呢?
宋瀏:我小時候受日漫影響很大,像《灌籃高手》,但有兩部電影,對我改變很大,看的遍數非常的多,可能近百遍吧。一個是夢工廠的動畫電影**《埃及王子》,非常震撼,我當時就突然意識到,哇,怎麼動畫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另一部電影,就是《指環王》第一部**。
後來考研究生就出國去加拿大Sheridan College,但是挺神奇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去了國外之後,反而特別想念中國。我是去了國外之後,才開始看中國古典思想的書,比如説老莊、佛學的,在國內的時候不愛看,現在反過來了。
有一次,我在加拿大旅遊,那個地方叫千島湖,那個場景,正好是夕陽下,我的天哪,跟《指環王》裏的場景一模一樣,神一般的地方,太美了,跟古典油畫巴比松畫派非常像。
但是,我突然就感覺到我跟這個場景融入不進去,是很美,但我覺得我的靈魂不屬於這裏。
後來我有一次回國,那幾年我父母在安徽黃山造一個園林,我就去玩,看到黃山,坐在上面看這個雲海,突然一片雲過去,裏面浮現出了一個怪石,沒幾秒鐘,那個怪石又被雲海蓋住了,特別宏大的若隱若現撲朔迷離的感覺,我就很受震撼,我的靈魂是屬於這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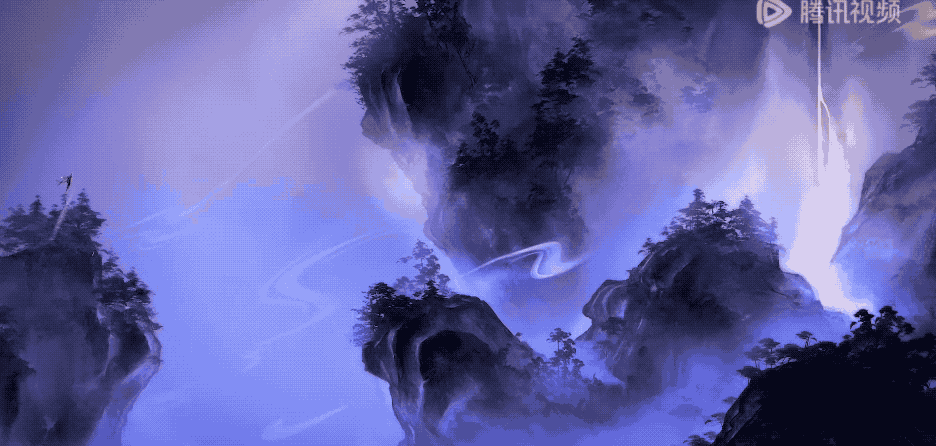
現在對於我來講,西方的那一套內容,保留下來的是一些理論基礎或技術,比如説視聽語言或三維的製作流程,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我當時出國,也是想快速學會整個流程,他們教一年的東西,可能是我們國內學校兩三年的量**,現在你只要給我時間,我是可以一個人做一個三維動畫的,或者説在一個項目流程中,哪個崗位缺人我就可以去哪裏,除了動畫表演我沒參與過,其它流程全都參與了。**當時看到Arc動畫公司裏有一位40多歲的華裔,在這個公司裏面吭哧吭哧做到一個部門總監,但從創作性質上看還是一個工人,我覺得太無聊了,果斷選擇回國。
我稍微再説一個題外話,我現在這條路很難走,説實話,在中國願意做風格化,或者可以做風格化的公司和創作團隊非常少,這次平台能做這套原創動畫短片集,實現過程已經挺難的。
04
築夢
《神弦曲·時光鈴鐺》導演鍾離華蟲:創造一個世界,成為所有人的桃花源
第一導演:《神弦曲·時光鈴鐺》最初的創意是什麼樣?
**鍾離華蟲:**其實最初計劃做一個16集的番劇,劇本寫了大概兩三年,完整的大綱更早的時候就寫完了,一直在找一個機會,因為當時參加了騰訊視頻的青年導演大賽,我的製片就跟平台溝通一下看有沒有可能性。
後來平台開始籌劃這個短片集,我們就根據番劇的前15分鐘內容做了一小段短片故事,相當於一個前傳。為了讓這個短片有一個完整性,我們花了三四個月,改了蠻多版劇本,它和番劇之間可能會有一些交集,實際上也不完全相同。劇本定下後,接着就開始推進製作,但中間又遇上特殊時期,也停了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短片的體量可能不在於時長,而在於我們去尋找一些新的表現形式。因為現在大部分畫二維背景的工作室,可能都是以快速的拼圖,或者共用資源的創作形式,但我們都是以手繪的形式在做,儘量去實現這種觀感和藝術質感。所以這次可能會比普通的二維動畫影片製作週期長,花的精力多一些。

**第一導演:**女主人公有來自你自己的生活經驗嗎?
**鍾離華蟲:**可能有一部分跟我比較像,比如説高中的時候喜歡看世界未解之謎、史前文明這些東西,所以我的某些學生時代的經歷會放到這個人物身上。其實以小女孩做主角,是因為我比較喜歡看宮崎峻,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小女孩。
**第一導演:**這個時光鈴鐺的想法是怎麼形成的?
**鍾離華蟲:**雖然這個題材很常見,但我覺得可以玩的東西還有很多,可以腦洞更大一點。我當時在想時間穿越能不能有比較簡單的方式,你説跳樓、摸電門,感覺沒太大意思,我想要再簡單一點,搞笑一點。
你知道我喜歡畫貓,一般貓脖子上都會掛一個鈴鐺,像哆啦A夢一樣,我就突然有了靈感,用鈴鐺穿越,只要擰它就可以隨便穿越,甚至會有自己跟自己相見的情況發生。
然後,如果這個鈴鐺是唐代的話,需要找一個符合那個年代的好看的器具,把它的元素吸納進去。我就想到了非常好看的金屬香囊,你無論怎麼轉,這個香囊放香的那一塊都會朝上,很有意思。我其實比較喜歡傳統文化的東西,之前上大學到畢業期間,會經常去各省博物館照一些照片,拍裏面的文物,收集很多這樣的資料。

**第一導演:**想問其中哪一部分在實現時技術上比較複雜?
**鍾離華蟲:**進到時間神廟那一段,那一段主要是整體建築是要設計的,而且我希望比較反映出唐代建築的味道,比如説多拱那種梁、柱,需要設計得更合理,更像唐代,包括上面的彩繪,屋頂瓦片的結構,屋脊的形狀,都需要考究。只有這個場景的建築需要很細緻的設計,其它的可以“走過場”,像露天這樣的場景,沒必要做太多的細節。
另外就是這一場戲特效比較多,比如説鈴鐺會有很多光效,時光倒流的效果,從一個破敗到完好的過程變化,而且基本上都是手繪,後期會做一些效果。最難的一個鏡頭就是那棵樹,從一片乾枯的樹葉長到整棵樹,表現那種生命的逝去,那個鏡頭做了好幾版,我都不滿意,還跟周圍其它幾個鏡頭不搭,就是周邊做得比較好,這棵樹反而low了。沒辦法,我就讓美術組逐幀的畫,修改得比較費勁,最後效果還是達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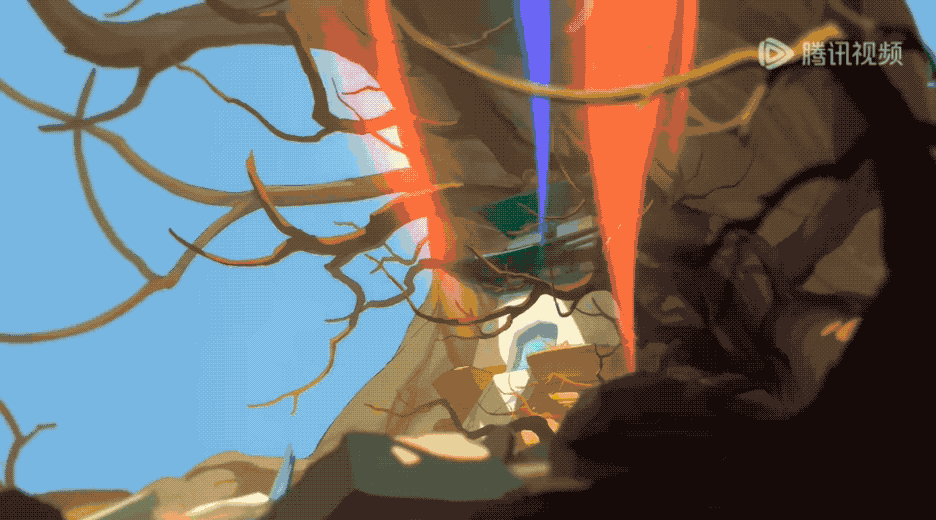
其實我希望主角在動作上,能更寫實一點,更活一點,但如果用默片的辦法,真人表演出來的風格又不太像,就沒有到我想象中的樣子。説實話,還是因為時間與成本有限吧。
**第一導演:**片子整體看下來是一種很明確的樂觀主義的創作,你本身也是這種性格嗎?
**鍾離華蟲:**悲劇的故事,只要好看的我也喜歡。對於藝術創作,創造出的世界大概有兩種,有一種是比如説我的情緒不好,在自我表達上就會把那種負面東西直接展現出來;另外一種,可能現實中遇到挫折,遇到難受的事,但是我創造一個我喜歡的世界,我可以在這裏進行自我逃避,就像一個世外桃源。
我可能更偏向後者,所以我畫的漫畫插畫也好,做的動畫也好,更喜歡塑造一個讓你想進去的世界。只是説我不反感那些悲情或過於自我表達的作品,我甚至也可以把這種情緒加入進我的作品裏,不排斥,我覺得今敏導演就還是蠻樂觀的人。
**第一導演:**你是怎麼篤定要走這條路的?
**鍾離華蟲:**從小就喜歡看動畫,很喜歡八十年代那些老動畫。我高中時上的就是美術班,我家人還是比較支持我的,我喜歡什麼他們就會支持。在學校,下午就去學畫畫,我就想報畫畫班,我家人也支持就去了。至於我的繪畫水平,這麼説吧,我是美術課代表,至少在班裏排名是靠前的。
除了學習繪畫,平常我自己也會畫一點漫畫,就是一些插畫,畫着玩的,有時候上課時就在課本上畫。當時很希望將來有機會從事這個職業,所以大學就報了北京電影學院動畫系,當時這個專業北電是最強的。
來到北電,最大的滿足感就是學到了怎麼做動畫,因為之前是喜歡但是不懂,到大學就能完整地學習動畫製作流程,主要是提升專業性,也參與過一些實踐作業,同時漫畫也會去涉及一些,我確實是愛好比較廣泛,只要是跟動漫相關的我都喜歡參與。
那時候學校有一部動畫電影叫**《歡笑滿屋》,執行導演叫沈友亮**,當時我跟着他們一塊去,相當於實習。
**第一導演:**現在整個行業和你當時大學時已經翻天覆地了,包括AI正在快速介入進來,你本身對它緊張嗎?
**鍾離華蟲:**看你站在什麼角度了,如果你是站在一個藝術家創作的角度,**如果我要做插畫,肯定不會用AI,我會每一筆自己畫出來,但是如果我要做一個商業片,如果它好用,我幹嗎不用呢?**所以我分得很清,不會像很多人要麼特別喜歡,要麼就特別排斥它。
其實我之前就試過,拿AI模型按我的風格訓練過一次,出來的效果非常差,如果有人能把這個訓練好,我可以買過來給自己用,用在商業操作上。AI就是一把雙刃劍,就看你掌握它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導演:**那現在的短視頻在改變人們接受視覺信息的生理習慣,你有擔心過嗎?
**鍾離華蟲:**這個我想過,包括那種電影解説,兩個小時的電影15分鐘給你解説完,小美、小帥啥的。但我現在沒有想到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沒有明確答案。
可能還是需要電影來造夢吧,創造一個現實中你想要進去,但是你還進不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