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會(十):不化妝真能提升生活質量?_風聞
死理性派-死理性派官方账号-“死理性派”是一种信仰,致力于从荒诞中寻找理性,从虚无中看到……48分钟前
文 | 阿水,慧敏,若妍,玉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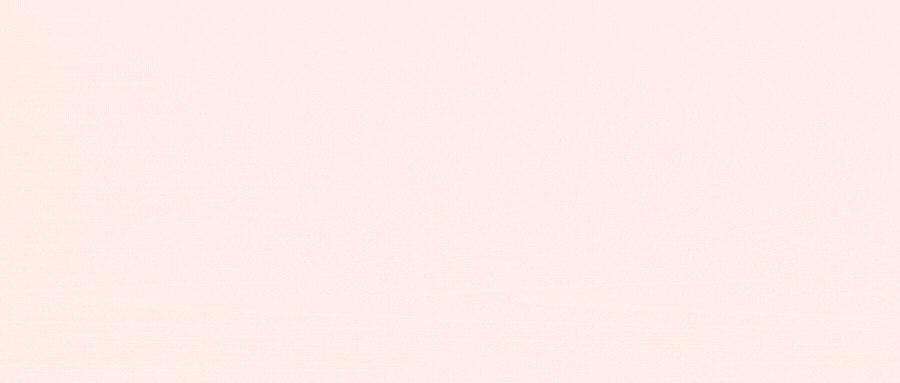

玉崽:
不久前,我跟隨學校的安排,緊湊地執行各種事情,其中就包括拍畢業照,明明離畢業還有好久好久,但我目前的生活已經像身處人生重大轉折點一樣陷入了極度的瑣碎裏。
但瑣碎之餘,我竟然還不忘化妝。
其實平時也並不怎麼化妝,一直都是素面朝天,我的許多同學都開玩笑説我一副“要死不斷氣”的貧血模樣。我也經常哈哈大笑着回應“舒適最重要啦”。只是內心還是會想:哎呀,那我應該更加健康一點的;這個年紀就要朝氣蓬勃的;我需要把更好的一面展現在你面前,我怕自己礙眼,怕影響到別人;同時我又希望自己在外人看起來很厲害,不能讓別人小瞧。
而且,那可是畢業照!一瞬間定格,0.3秒就將你的幾年囊括進一個小格子裏。所以覺得“青春就該有青春的模樣”,我不應該死氣沉沉。於是我起了個大早,跑到學校可以免費化妝的地方,讓一位做志願者的女生在我的臉上一頓操作。
這期間我有好幾次都快要睡着了,沒睡夠是一個原因,那柔軟的毛刷在臉上掃動時舒服的微㾕也有種安眠的效果。女孩温柔的操作也讓我心動,我最後還加了她的微信(算是我那天最大的收穫之一了)。
最終的效果很滿意,我的頭髮也從“細軟塌”捲成了蓬鬆的樣子,突然覺得自己的髮量變多了,我第一次見自己這個模樣,很新奇,也有點陌生。我頂着這樣的髮型走進寢室,所有的室友都在驚呼;我把這樣滿意的“我”發在了大家都在的小羣裏,所有的女孩都湧上來誇我“真漂亮/真好看/真美好”。我被讚美得心花怒放,突然有了“下一次我也要這麼漂亮”的想法。
我很疲憊,那些讚美在一段時間內讓我忘記了勞累,享受到了短暫的快感——人們稱之為“虛榮”。
當天晚上我卸了妝,變回了之前醜小鴨的模樣。
如果沒有發生後續事件的話,我會覺得卸妝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室友們看到了我的臉後大叫:你怎麼把妝卸了,我們還沒有拍照呢!
我們還沒有拍寢室的四人照。

玉崽和室友的拍立得合照
“哎呀,好可惜。”我想尖叫。突然後悔,我想和她們拍很多照片,但好像大家(包括我)都有點不能接受素顏的玉崽。臉上的瑕疵開始變得格外刺眼。我忐忑了一整晚。因為各種原因,我錯過了和大部分人拍照的機會,我感到了自己的缺席。哭着發私信給慧敏:這麼重要的日子,我為什麼要把妝提前卸掉?我應該美美地跟大家玩作一團才是對的。
我又在崩潰,為什麼情緒這麼不穩定?我怎麼又哭了,**我不應該在別人面前哭,我的樣子好狼狽,你們會不會覺得我真沒用。**只是慧敏的問句把我拉回了現實:
“為什麼要化妝呀?你在羣裏發的那些照片,和你平時沒有什麼區別的呀。”
我還沒哭完就又笑着回應:
“那我就是本來就很漂亮的!哈哈。”
心情穩定了一丁點兒之後,我開始追着內心的疑問探究更多。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壓力,我在一個這樣的大環境下,我沒辦法逃離,哪怕逃離了,我該逃去哪兒?
但我最無法面對的,感到極度羞恥和刺眼的是:我感覺自己陷入了雌競中。
我把照片發在羣裏的另一個微妙小心思是,我想讓別人看到我比大家都更漂亮。我突然意識到我似乎在和全校的女生比美。這一天所有的女生都在化妝。鏡頭也讓我感到焦慮。
我到底是怎麼了,有誰告訴我該怎麼辦嗎?我突然好絕望。
我要被審判了嗎?好害怕……我好害怕自己真的在嫉妒那些女孩,好害怕被人發現自己的嫉妒。
這樣的我確實很醜陋……
大家都説我很好,我超好。仔細想想,是我把最好的一面展現給你們,才讓你們覺得我很好。其實我的狀態一直都不好,我想要許多人對我説“你現在還好嗎?你要不要抱抱我,其實你原本脆弱的樣子才是想讓人靠近的樣子,嫉妒只是暫時的,嫉妒沒有錯,好好放鬆吧”。
許多人都高估了我,我發現這樣的結果是我找不到地方哭泣,我最終逃到了另一個人的家裏,在沒有熟人的地方哭了個暢快。我連哭都不敢大聲了,明明以前可以好好哭的。我不敢在大家都開心的日子裏,去做那個“掃興”的人。
我可不可以“無理取鬧”地大哭一場,大聲嚷嚷:
“你們怎麼都這麼好,哪哪都好,我怎麼總是這麼笨拙!我就是嫉妒,為什麼我總是嫉妒你們……”
“為什麼你們都把自己照顧得很好,為什麼好像總是我在需要別人,為什麼別人都不需要我,難道是我太無能了嗎?”
慧敏説:“大家都和你一樣。如果大家都努力在別人面前展現出自己最好的樣子,世界就會一直是一個個孤立的原子。我覺得不化妝的最大好處是,只有展現出最真實的樣子,別人才會在你氣色不好時第一時間發現,然後設法提供幫助,然後彼此才會有更多的互動,感情才會更親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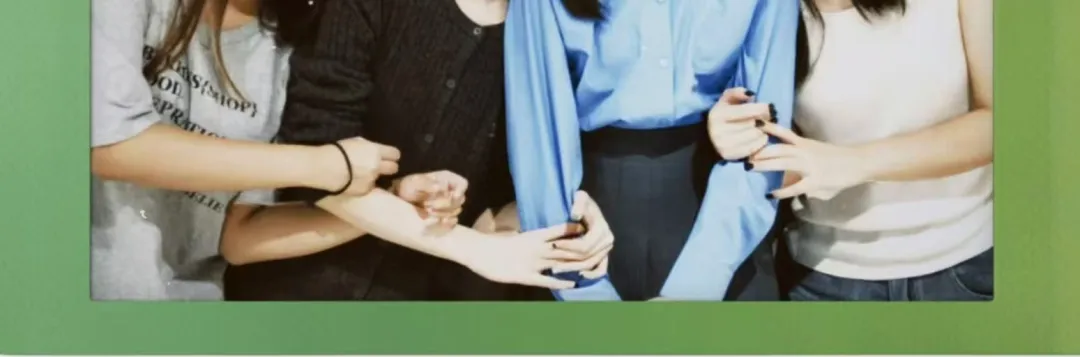
我以為我懂了,但身體並不同步。我需要時間。
而且我感覺到無力,因為只有我不化妝這根本不夠。我感覺自己一直在碰壁,比如之前我又對一個人發出交友邀請,被拒絕了。當我説我很孤獨,別人卻説他不需要朋友,他説他享受孤獨。他在防禦,而我又好討厭別人説“享受孤獨”這類話。我也會因為別人的防禦而防禦,變得沒那麼能共情,覺得他嘴硬的樣子讓我不想靠近。於是對方也會想“我本來也不需要你來靠近”,我們就這樣錯過了。好可惜。剛剛伸出的手上好像落了一記重錘,疼得厲害。
如果大家都展現真實的樣子,讓我看到真實,我也不會嫉妒了吧。也不會有這般的內耗和糾結吧。
我好想要一個能夠坦然説“其實我和你一樣普通”的環境,好想找到一個普通女孩不需要因為“普通”而內耗的環境。我總是首先預設自己的哭泣會迎來冷嘲熱諷,自己的嫉妒會被人攥着一直詬病。所以我一直在裝成熟,裝遊刃有餘。
好笑的是,拙劣的演技首先就沒能騙過自己。

若妍:
跟大學室友曾經聊過化妝的話題,她是喜歡並擅長化妝的,看我不化妝,就有點好奇我的想法是怎樣。我覺得會化妝很厲害,也會觀看美妝博主的視頻,雖然我自己化妝不感興趣也不買美妝產品,就好像有人喜歡運動擅長運動,有人不喜歡也不擅長一樣吧?化妝也是一個道理。作為一項技能,喜歡化妝熟悉化妝,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件事上也是一個人重要的優勢嘛。就我本人的情況來説,其實是因為不喜歡有多餘的東西在身上的感覺,小時候拍藝術照或者上台表演帶妝太久都會不太舒服,也戴不住髮飾、首飾(但是眼鏡這種重要配飾還是要戴的因為不戴會瞎)。
還是大學的時候,跟另一個朋友就化妝這件事甚至發生過爭吵。她平常也是不化妝的人,但那天突然帶妝出門,我就好奇地多問了兩句,沒想到兩個人就這麼吵起來了。她是在為找工作做準備,因為很多工作崗位是需要化妝的。我自己也接到過這樣的電話面試,賣化妝品的絲芙蘭問我有沒有意向,我問你們這個崗位是要帶妝的吧?顯而易見啊,畢竟這個品牌就是賣化妝品的。對面回答説是,我就遺憾退場了。朋友想要進的外企面向女性的崗位,有很多就是要求帶妝的,這也是她開始化妝的原因。我不太能理解,説實話那時候也很不成熟,對工作也還沒啥概念,就提出説,如果不喜歡化妝那就找個不化妝的工作不就得了,只要不是展示性的工作,很多普通工作都是不會硬性要求帶妝的。她説我太幼稚(現在看來是説得很對,只是那時候我不太能理解),這樣白白卡掉需要化妝的工作崗位不是自找麻煩。但我很堅定自己的想法,於是又試圖反駁她。我倆就這樣吵起來了。
這件事過去了也有大概四、五年了,不過現在提起化妝的話題,還是會勾起對這場爭吵的回憶。平時也經常看到對女性的容貌紅利的討論。前幾天還在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如果愛上了一個人,但這個人要求你做改變才會考慮跟你在一起,比如要短頭髮的你留長頭髮(改變外形),或者要不化妝的你開始化妝(改變習慣),你會非常樂意嗎?當時在場的大部分人好像都是默認願意的,因為很“愛”對方嘛,兩個相愛的人在一起,本來就是要為對方改變一些,相互適應咯。不過這題也有另一個解法吧?比如有不喜歡改變的人,不想改變自己的關鍵外形,也不太想改變自己的重要習慣,那是不是可以換個人來愛呢?畢竟有緣的人總是會在一起,那沒有在一起就説明大家沒有緣分,沒有緣分的話,不在一起也沒有什麼好遺憾的啦。
好吧,這個不願意改變的人就是我。
外形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應該是向外界傳達信息的表意的部分吧?想要當甜妹,所以化了甜美的妝容,搭配上Lolita風格的小裙子。要做職場女強人,所以化了港劇裏的職場女主妝,再配一套利落的suit,手裏拿着咖啡,高跟鞋在CBD的路面上釘出聲響來。這樣別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什麼身份的人,能預測出她出門到底是要和姐妹悠閒下午茶還是趕時間去公司。玉崽也分享了她化妝後變漂亮、被誇獎的經歷。更好的外形會受到更多的注目、更加被青睞、更加受喜愛,也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掙到更多錢、過上更好的生活,也就是所謂的外貌紅利吧?花費時間和精力去妝點自己,讓別人得到視覺上的享受,也表達出對重要場合的尊重。當然這也引出另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有人能夠即便在非常重要的場合都不化妝,也沒人指責這是不尊重。

圖片來自互聯網
這種違和感被提出來的時候就好像演了一出《皇帝的新衣》,指出皇帝根本沒穿衣服的小孩被指責怎麼説不合時宜的話。皇帝一貫都是如此,為什麼只有這個小孩這麼沒有眼力見、不會讀空氣、沒向傳統和社會主流屈服而放棄自己的眼睛和思考(寫到這裏,才發現皇帝的新衣原來是這樣一個故事……)?就好像大家都是大石頭下面的螞蟻,但突然有個螞蟻指出來了這件事,並把石頭往上搬了一點,透進來的光晃瞎了其他螞蟻的眼睛,受到指責。或者這塊石頭本來放在這裏好好的,突然有人要把它搬起來看看下面藏着什麼東西——一羣螞蟻,如果石頭不被搬起來,螞蟻和人類相安無事,但石頭被搬起來了,習以為常的被隱藏的那一面突然被光照到,不管螞蟻還是人,習以為常的被打破,不得不面對一直被忽略和隱藏的部分,不得不開始思考石頭究竟意味着什麼,石頭接下來要怎麼辦,螞蟻接下來要怎麼辦,人接下來要怎麼辦。太累了,還不如維持原狀,大家都裝作看不到皇帝赤裸全身的樣子,自欺欺人地把皇帝哄好了算了。
**犧牲。化妝是一種犧牲。**粉塵、假睫毛膠水甲醛超標、美瞳和眼線對眼睛的傷害……就算這些都不論,化妝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也不能不被算為一種犧牲。如果不化妝,當然空下了本來用於化妝的時間、精力、健康。但是拿它們去做什麼呢?為了事業加班爆肝、為了病人通宵手術、為了救人跳下河去,人總要選一個犧牲的方式,來換一點自己覺得值得的東西。(注1)
只要覺得值得就好,無關對錯。
最後還是説回到外形的表意作用,雖然毫無設計感、顏色單調、基本理念是實用性大於一切,但即便是這樣的外形也幫忙釋放了它應該釋放的信號,舒適的、普通的、大眾的、通用的、易得的。很多人就喜歡找這樣的人問路,而非外表光鮮亮麗的人,很多人也更傾向於跟這樣的人搭話,而非精心設計外表的人。穿着這一身普通、大眾的服飾,也可以隱藏在人羣之中,不彰顯太多存在感。這也是一種表意。外表很重要。經常看到那種改造視頻,女朋友改造男朋友居多,之前還有一位男生自我改造變身“聽勸”引發潮流的故事。
目前為止,一直在討論化妝/打扮的話題,但有另一個説法似乎在被推向大眾的過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誤讀。“服美役”的概念被理解為單純的化妝打扮,這完全是對詞語本義的簡單化和概括化。“美役”這個概念本身是從“役”而出,類似於兵役、徭役,被徵召的,具有強迫性的,深層目的是維護現存秩序的穩定。美役類似,是對女性強制性的徵召,提出要求,為了維護現存的性別秩序而存在。脱美役類似於逃兵役,支撐這一行為的動力源泉是不認同,不想維護現存的性別秩序。也許可以叫做逃美役,“脱”這個字,讓人聯想到脱束身衣。還有將女性的長髮稱為蛋白質頭巾的説法。個人觀點認為脱美役比起外表的改變,重點在觀念的轉變上。一個人不打扮,但這個行為可能是在不瞭解美役和脱美役的情況下,僅僅因為別的某些原因而作出的選擇/決定,那麼就不能稱為脱美役。當一個人意識到脱美役的概念,即便仍然打扮自己,但開始反思自己所受到的服美役的影響,思考自己的處境時,才是脱美役的真正開始。
注1:
犧牲一詞的含義比較豐富,原指祭祀用的牲畜,後引申出放棄或損害利益、為堅持信仰/正義而死、花費掉等義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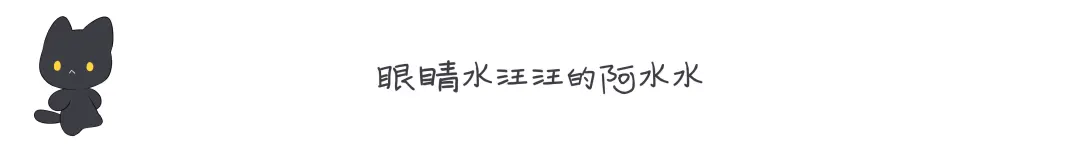
阿水:
受媽媽的影響,從出生到高中這相當長的時間裏,我的生命中沒有“化妝”這個東西,我媽媽不化妝、不護膚,僅有的護膚品是大寶,洗臉用的是香皂。在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從她的針線盒裏發現了一根眉筆,一根口紅,看上去已經相當有年代感,不知道已經放過期了多久,那是她僅有的化妝品。
她一直到現在也是這樣,對護膚、化妝完全沒有興趣,不會花任何錢和時間在美容上,最多就是在超市買7.99的杏仁蜜來抹抹臉。
她從來不給我扎漂亮的小辮子,一直都是簡單的扎個馬尾,有一次大娘去學校看我表演節目,她説別人家的小姑娘都辮了各式各樣的辮子,我媽媽怎麼沒給我也搞一個。她懶得給我梳頭,懶得辮小辮兒,導致我自己也不會扎辮子,上初中的時候就自作主張剪了短髮。
她也從不給我穿裙子,她説裙子活動不方便,對腿也不好。小的時候她買什麼衣服我就穿,到了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就開始鬧着不願意穿那些褲子,有一條胖胖大大的,有很多口袋,走起路來褲子會晃來晃去;有一條是厚厚的棕色條絨褲,我覺得很土氣。印象中是到了高三,我有了一點自己的零花錢,才買了第一條黑色半身裙,那天下午我穿到學校去,同學説看我這樣打扮嚇了一跳,不過還怪好看的。
在我初中的時候,大家已經開始接觸化妝品了,那個時候班裏的女孩會討論BB霜、會畫眉毛、塗塗不明顯的口紅,會用媽媽的護膚品和麪膜,初中畢業的時候已經有相當多的女孩去割了雙眼皮,她們看起來很成熟很漂亮,和我完全不像一個世界的人。那個時候我媽媽哄着我説要給我買金耳墜,金的可以保值,拉我去打耳洞,可是打完耳洞後我痛得睡不着覺,兩邊耳朵都在發炎流膿,在牀上只能平躺,不能側躺,我躺在那裏邊哭邊睡,眼淚順着臉流到受傷的耳朵上,最後又落到枕頭上。沒過幾天我就受不了那個痛,自己把耳墜取了下來,從那以後再沒有打過耳洞。
高中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很多媽媽都會化妝,也不反對自己的孩子化妝。也是高中的時候同學告訴我,護膚品的存在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我從那時候才開始用第一支洗面奶。

一直到上了大學我才有了化妝的概念,大學時候大家都沒什麼事,也普遍在意起自己的外表來,室友們經常坐在那裏照鏡子,對着鏡子研究自己的臉怎麼拾掇才更好看,我也是在那個時候買了第一支粉底液和口紅,現在還記得那是一支天鵝絨粉色口紅,臭臭的,塗上去也很不襯我。我在和當時的男朋友出去玩的時候會化妝,但我的化妝技術很sorry,看上去的美麗程度和不化並沒什麼不同。
到了大三大四的時候看自己化妝怎麼看都不順眼,有可能對着鏡子塗抹一個小時到最後又全部卸掉,影響了本來的好心情,再加上我對化妝實在沒什麼興趣,就不再化妝了。化妝不是簡單的假白配紅唇,要做好實在是太麻煩了,要有足夠的審美能力,要挑適合自己的化妝品,要嫺熟的手法,要提前一小時起牀,帶妝一天後又要卸妝,還要買專門的眼唇卸妝液,要洗刷子粉撲,這一切都既費精力又費時間,有這些時間我更願意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在面試第一份工作的時候我塗了口紅,去了之後發現公司裏大家看起來都灰頭土臉的,化不化妝並不重要,後面的面試我也沒有再化妝了。
小的時候會羨慕那些嘴巴紅紅臉蛋嫩嫩的姐姐,覺得她們光鮮亮麗,現在覺得只要睡得飽、心情好,就能成為元氣十足容光煥發的大美人,我並不再想花時間和金錢在這件事上了。我實在是太懶了,一切需要時間護理的事情都不想做,我可能會花錢種個睫毛,因為種上之後就不用再管了,但如果是貼假睫毛或者畫眼線,就都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我更想拿這個時間去做別的事情。
我現在對化妝的唯一的興趣點就是有時候會看一些“化妝換頭”或者coser化妝的視頻,感嘆擁有這些化妝技能的人真是厲害。我上一次化妝是兩年前生日的時候去換裝館拍了一套自拍生日照,斥巨資(168元)讓化妝的姐姐來幫我做妝造,最後出來的效果讓我感覺其實和不化妝沒什麼區別,並不是説妝後沒什麼變化,而是我還是我,不會因為我的眼睛大了一點、皮膚好了一點而有什麼不同。我不想做假面人,每天都是同一個標準的完美無瑕的樣子,皮膚和五官的狀態會説話,我想每天都能看到真實的自己。我翻看自己狀態好和不好的時候拍的照片,可以看出狀態不好時候面色格外憔悴,狀態好的時候確實是充滿精氣神,心情好就是最好的美容。
我沒有因不化妝被指責過“不尊重、邋遢”,也沒有因化妝被誇獎驚為天人,是否化妝於我而言實在是無足輕重的事情。如果下一次化妝我希望是換頭式改造,想要試試看用不是自己的臉生活一天是什麼樣。

慧敏:
我曾與一位“校花”做過同班同學。現在四十歲的她看起來依然完美:容貌像是停在了二十歲,身材苗條,工作體面,兒女雙全,朋友圈展現的與家人的關係似乎也是和和美美。
她看起來無可挑剔。但是某一天她喝多了酒,一個人在辦公室裏給我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她説她每年都要打兩次瘦臉針,每天半夜還去健身,經常睡眠不足三小時,情感生活也糟得厲害,她用加班迴避自己的伴侶,在心裏還一直懷念初戀,但又為了維持“人設”而不可以與初戀聯繫。所有男性都對她不懷好意,所有女人都對她至少是略有妒忌。
而她困在了自己編織的“完美”外殼裏。
玉崽説自己習慣把最好的一面展現在人前,讓別人看起來很厲害。那位同學也是這樣。沒有任何人敢小瞧她。但是她也沒有一個真正算是“相愛”的人。
現在玉崽説“我很缺閨蜜”時,別人也感到難以置信。而我至今也沒有創造出“住在隔壁的閨蜜”來。(我已經有了兩位特別好的室友,只是仍然會期待更多。知心的好朋友多少都不嫌多。)
在我三十歲以前,所有看起來很完美的女人都讓我害怕。我以為這些人不僅擁有比我更姣好的面容與更嫺熟的化妝技巧,還擁有比我更強的大腦,以及一顆隨時準備傷害別的女人的心——就像宮鬥劇裏演的那樣。
宮鬥劇讓我害怕所有美麗或有智慧的女人。
我生來與“美麗”無緣,但後來我也成了讓人害怕的女人——許多人因為我喜歡研究個體心理學,就以為我有能力看透一切、掌控一切,就把我也當成了宮鬥劇的反派一號。
現在完全信任我的人,幾乎全是不止一次見識過我的狼狽、無助與絕望的人。
後來玉崽説:“我現在知道你想做一個小孩子了。”
我心裏想:“我就是一個小孩子啊。”但這似乎不符合事實。事實是“我像個小孩子”?
但是小孩子和大人的差別是什麼呢?
我覺得好朋友J在我的朋友中是最有童真(單純?天真?)的人,他是我世界中最酷的博物學家,對一切自然科學知識都很好奇,在外面玩時完全不介意把自己弄髒,不怕觸碰任何別人可能覺得“噁心”的東西,我也是這樣,所以跟J一起出門研究花花草草蟲魚鳥獸、一起傻樂的時候很開心。

慧敏和J (已徵得本人同意)
但有童真不等於愚蠢,不等於什麼都不思考。
我只是像孩子一樣在追求最真實的東西。但是,所有孩子都求真麼?為什麼一些孩子後來變得越來越不像孩子了呢?
還是説我打小就與環境格格不入呢?我的特點到底是什麼呢?
玉崽説,你最後的兩句話就是你的特點,沒有幾個人會像你這樣努力地求真。
嗯。確實也沒有幾個人活得像我一樣輕鬆。我的生活並不完美,但我的思考確實幫我化解了許多“徭役”。
我想,化妝對於多數女人來説並不是像運動一樣的“愛好而已”,就好像,當一位奴隸説“我喜歡服侍別人”時,我們不能相信這句話是全部的事實。——如果有選擇,如果不是身為奴隸,這個人更可能説“我喜歡與好朋友互相關懷”。
化妝追求的是“健康的表象”,就像玉崽説的,化妝讓人看起來健康、看起來朝氣蓬勃。
如果女人擁有足夠的選擇,我們本可以追求事實上的健康:好好吃飯,好好睡覺,花很多的時間與好朋友一起開懷大笑。
若妍説化妝是一種犧牲,我想,這不僅僅是個人的犧牲,也是在傷害整個女性羣體:
當一位底層工奴用996甚至007的工作方式來努力為自己掙得一個“體面”時,這人是在捍衞並鞏固一種“內卷”的文化,不僅壓縮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也壓縮了所有夥伴們的生存空間,逼着所有工奴一起將頭壓得更低一些。
當玉崽的所有同學都在化妝時,玉崽發現如果自己不參與,就會遭遇顯性或隱性的人際暴力,而如果參與了,就跟身邊所有同學一起變成了假人——我至今記得十多年前我在一場活動中拍下的一張全員化妝的照片,當時的背景是黑夜,每個人的臉都在閃光燈下顯得煞白,但手與脖子的顏色是完全自然的,就顯得整個畫面非常驚悚。
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無法欣賞真實的女人的呢?
為什麼男性只要洗臉梳頭就可以獲得讚美呢?
為什麼男性犯了重罪仍可以成為“受害者”,可以歸咎於他的母親或妻子,而女人會僅僅因為在親人的葬禮上化了淡妝就可以遭遇網暴呢?
通宵做手術的醫生不過是加了個班而已,好處是可以獲得加班費、升職加薪的機會,還可以確實拯救別人的生命,最終可以更加確信自己的內在價值。但那天玉崽化了一天的妝,除了瞬間的虛榮感之外什麼都沒撈到。多數女人也是一樣:幾乎不會有任何人承認一個“美女”的化妝是“犧牲”,反而會説她是收穫了“外貌紅利”,將她與“既得利益者”混為一談。
我也盯着若妍説的“人總要選擇一個犧牲的方式,來換一點自己覺得值得的東西”想了很久。
我想,對我來説,我現在最大的幸福感來源就是幾位好朋友的愛,而我沒有為這幾位好朋友做過任何犧牲。
理想的“愛”是愛的雙方都從這份情感紐帶中受益。
“人總需要犧牲”的這個邏輯又是哪位奴隸主第一個説出、最終被世上的那麼多人接受的呢?
我又想到了一個看似“跑題”的故事。
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小A是跨性別女人。我愛她就像愛我自己。
她用了很長時間探索自己的真實。
她從幼兒園就説自己“喜歡粉色”,但旁邊人告訴她“男孩應該喜歡藍色”,所以她開始對外聲稱自己“最喜歡藍色”。
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塑造着她的語言與自我認知,也導致她越來越不敢交朋友——如果交朋友意味着説謊,那確實還是一個人更好一些。
她小學時想過“我要是個女孩就好了”,但又聽説女孩子要跟男的戀愛,又覺得很可怕,因為還是跟女孩子戀愛比較好。
“所以我大概是個男孩吧。”
她不再思考性別問題。只是偷偷一個人看那些女孩子喜歡的東西,對外則跟男孩子一起打遊戲,所以看着還挺“正常”的。
當然,男人都沒什麼很親密的朋友,這也使她顯得很“正常”。她還説曾經很想找個女朋友,原因是“這樣就可以正大光明地買可愛的東西了。”(男性太難了!)
她還沒有向我之外的任何人出櫃過,所以還沒有遭受過社會的毒打。(當然,她完完全全理解什麼叫“現實的殘酷”。)
她花了很長的時間思考要不要改變身體,就像一個六指兒思考要不要切除多餘的手指一樣。
但我們都知道,六指兒的第六指完全不是“病”,只是一種“特殊”,這些人甚至可能會在魔方、積木、乃至一切需要靈巧手指的事情上有優勢。(如果沒有歧視,或許也可以成為優秀的鋼琴家?)

在西班牙電影《兩萬種蜜蜂》中,Lucia的姥姥對長錯了身體所以不敢洗澡的小女孩説:“女孩子也要洗乾淨自己的小牛牛呀!”(我當時就感動哭了。)
最後大家都接受了Aitor其實是Lucia這個事實。但是沒有人討論手術,因為還沒到時候,這個話題對小孩子來説太早了。
為什麼許多人認為跨性別者一定要改變身體呢?因為如果一位女人的快感器官長得過大,很容易激起女性的恐懼與男性的雄競心理。如果改變身體,就可以更好地將自己塞進性別二元的社會模板之中,就可以更好地獲得多數人的接納了,就可以自然地跟喜歡的女孩子們抱抱貼貼了。
我承認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或許真的有人純粹因為自己內在的“身體焦慮”而想要改變自己的身體,但現實世界中,我沒見過。
我長得很黑,我曾經把很多錢花在購買“美白”相關的產品或服務上。
但是,我“天生喜歡白皮膚”嗎?
不是。我天生喜歡所有對我友善的人。
如果所有人討論另一個人的時候都在討論這個人的內在氣質與修養,如果我們自己在面對朋友與身邊的人時儘可能展現真實,至少身邊人的容貌焦慮會因為我們的存在而降低一丁點兒。
如果沒有性別刻板印象,如果從來都不存在“男性應該……”與“女性應該……”,還會有性別焦慮麼?
如果所有人都在這世界上擁有至少三個彼此之間完全信任的朋友,或者説,如果一個人完完全全地相信這世界上至少有三個人深深地愛着自己,無論如何都會支持自己,這個人還會有容貌焦慮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