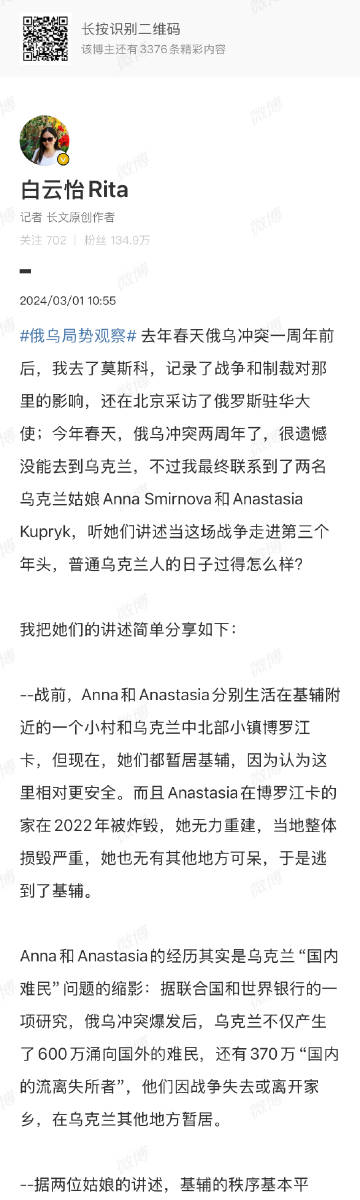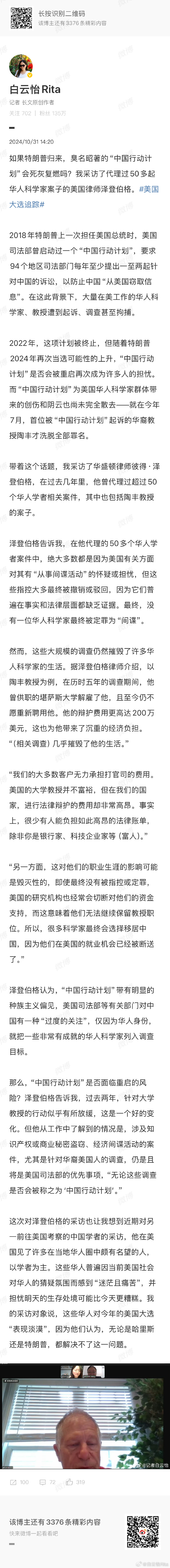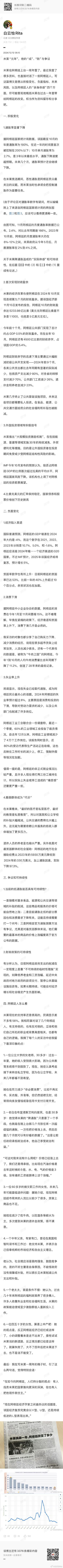採訪本上的2024——那些讓我最難忘的採訪故事_風聞
记者白云怡-环球时报记者-1小时前
今年1月,我採訪了正在北京訪問的原巴以和談巴方代表葉茲德·賽義格,因為我想與一個巴勒斯坦人面對面地對話,瞭解那裏發生的一切。賽義格的家族一直投身於巴勒斯坦獨立建國運動,他的叔叔更曾成為摩薩德的暗殺目標,並被“信件炸彈”奪取數根手指。在那次採訪裏,他所描述的加沙的慘狀讓我至今難忘——“以色列人‘科學地’用一個人維持基本生存需要攝入多少卡路里,‘計算’出一個加沙人需要多少食物的數值,並以此為依據,嚴格控制進入加沙的食物。加沙,就像一個‘開放的大監獄’,這是一個囚禁着225萬人的地方。”
2月,我採訪了兩個烏克蘭姑娘,因為我想知道,當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普通烏克蘭人的日子到底過得怎麼樣。兩位姑娘都因戰火而流離失所,失去摯愛。我最難過的一刻,是聽到一位姑娘説,她連孩子都不敢生,因為在此時生養孩子是一種不負責任,這讓同為女性的我格外難過。“我現在只計劃未來兩三個小時的事情,連全天都不會想。”她説,“我活在當下,因為也許明天不會到來。”
3月,我採訪了日本經濟學家德地立人,因為我想了解,今天的中國經濟和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哪些相同與不同。德地教授告訴我,今天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面對一個共同的挑戰,即阻止通縮。“日本的悲劇是,政府動作太慢、太小、不堅決,其結果是時間拖得太長,成本變得很高,挫傷了國民尤其青年人重振旗鼓的元氣。”還記得他告訴我,“(中國經濟)困難是長期的,但前途仍是光明的。不過,不解決好眼前的挑戰,光明的前途是等不來的。”
從春天,到深秋,我先後採訪了阿根廷的外長、大使,以及許多阿根廷的普通人,因為我好奇,這個我曾經待過三年的、深陷經濟困境的國家,在米萊的“電鋸改革”下,到底會“休克到底”還是涅槃重生。我得到的答案是複雜的:有人告訴我,米萊的改革讓她從吃牛肉變成吃玉米粥,她討厭他;也有人告訴我,他認為社會應該就是弱肉強食、充分競爭的,很支持米萊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現在阿根廷經濟學家之間最熱議的話題是,該國經濟走勢究竟會以V型、U型,還是持續低迷的L型表現出來。”
還有中國人和中國企業的出海故事——我始終覺得,出海,或許是今天中國企業的一個“時代命題”。從到越南設廠的機械製造企業,到墨西哥北部的產業園負責人,在所有的出海故事裏,我總能看到中國人的智慧與堅忍,不過讓我覺得最有趣的採訪,還是一箇中企為非洲提供平價互聯網的故事。這家企業的創始人周先生在肯尼亞當地有一個外號,“Mr Wifi”,因為他結合WiFi技術和城域光纖網,讓內羅畢人用上了每G平均0.07美元的移動互聯網,相比於非洲大陸超過4美元的均價,這無疑是一種顛覆性的改變。
Mr Wifi的講述裏,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這麼一段,“剛到肯尼亞時,我看到當地人在街頭賣西瓜,他們習慣於把一個西瓜切成二十多片來賣,一個人只買一兩片,很少有人買一整個西瓜。我當時就想,也許我們做互聯網服務,也不必像國內那樣包月、包年,而是可以做更多‘小套餐’,比如包周、包日,甚至8小時、2小時、40分鐘。後來證明,這種套餐設計很符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習慣,現在,我們已經有超過120萬用户!”
在美國大選前,我採訪了一位代理過五十多個華人科學家案件的美國律師澤登伯格,因為我想知道,隨着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持續上升,臭名昭著的“中國行動計劃”會不會死灰復燃。澤登伯格告訴我,首位被“中國行動計劃”起訴的華裔教授陶豐儘管洗脱了罪名,但陰雲與創傷仍在,“在五年的調查期間,陶教授曾供職的堪薩斯大學解僱了他,至今仍不願重新聘用他。他的辯護費用更高達200萬美元,為他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這幾乎摧毀了他的生活。”他説,涉及知識產權或商業秘密盜竊、經濟間諜活動的案件,尤其是針對華裔美國人的調查,仍是且將是美國司法部的優先事項,“無論這些調查是否會被稱之為‘中國行動計劃’。”
12月,我採訪了一個在北京的敍利亞人,因為我想多瞭解一點這個國家劇烈政治變化下普通人的所知所感,所思所想。這個阿拉維派的敍利亞人向我講述了敍利亞人過去這些年的日子,“在那裏,一個人活着需要的一些最簡單的東西,比如電、水、食物,都沒法保證。每個人都過的非常辛苦”“我們阿拉維派生來就得當兵,除了當兵,沒有第二種選擇。”對於敍利亞的未來,他有很多期待,儘管這些期待有很多都不可能實現。這份在苦難里長出的天真的夢想,在殘酷現實裏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讓我心酸,卻又不知該如何回答。
於是,我的2024,從對中東的採訪開始,又以中東的故事結束,只是這片土地上的苦難和混亂,仍看不到終結的跡象。
還記得我曾對一個朋友説過,對於自己的職業,我有時喜歡,有時厭惡,正如我不喜社交,卻又想對話不同的人,聽到、看到更多的故事,從不同的側面去管窺這個複雜而龐大的世界。
我的2024年就要過去了,我想,我會很懷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