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凱瑞·布朗:西方準備好接受中國了嗎?
guancha
導讀:2023年9月,英國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中國問題專家凱瑞·布朗(Kerry Brown)出版專著《包含中國的世界: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後的世界政治》(China Incorporated:The Politics of a World Where China is Number One)一書。**該書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西方是否準備好接受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為什麼允許中國“做自己”對西方以及全世界而言是最佳選項。**近日,布朗在訪談中介紹了他的新書,並探討了西方在接納中國上面臨的障礙以及西方為什麼要改變與中國打交道的觀念。布朗認為,共存會讓世界變得比現在更好。本文為採訪內容。
【文/凱瑞·布朗 翻譯/李旭】

圖源: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Q:您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包含中國的世界:中國成為第一後的世界政治》。此書的書名讓我們想起了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當然,日本從未成為過第一。當您選擇這個書名時,您是基於什麼來思考中國未來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尤其是中國也面臨挑戰?
**凱瑞·布朗:**我認為關鍵不在於中國是否真的會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經濟方面)。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計算方式,因此有人説,就購買力平價而言,中國已經是第一了。然而,就經濟的總體規模而言,中國不太可能在短期內趕上。
我更感興趣的是,假設中國真的成功成為了第一,那麼世界其他國家會採取什麼態度。在我看來,過去幾年的一個怪現象在於,人們對中國可能崛起的恐慌情緒不斷升温。這一點尤其令人費解,因為按人均計算,中國很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需要發展。我真的十分困惑,為什麼對許多人來説,世界上出現一個更加富裕、更加繁榮的中國會成為一個如此嚴峻的問題。
我認為,當今中國與西方之間關係緊張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西方(我指的是歐洲、北美及其盟友)對自身制度缺乏信心,而不是擔心中國的情況如何以及中國可能會做些什麼。
我記得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我與倫敦金融城的一些人士交談時,他們對我説,英國不應該害怕中國公司來英國投資或經營,因為他們需要遵守我們的規則以及法規。但如今,這種信心似乎已經消失了。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極力聲稱中國的海外投資都是出於某種邪惡的意圖,旨在影響並改變外部世界。還有一些人聲稱這些活動都具有強烈的政治導向性。
在我的書中,我試圖認真分析這些説法的含義。我發現了兩個特別的問題。其一是為什麼我們喪失了2000年初時對西方制度的信心,其二是為什麼現在的我們會認為自己如此脆弱,以至於中國的投資不再被視為經濟或金融事務,而是被視為承載着更深層、更令人不安的因素。證據何在?
我可以理解,任何一種投資,無論投資方是誰,其目的都是利己的,都是為了給投資者帶來利益。但如果超出一定的範圍,聲稱中國的投資懷揣着更大的野心,似乎就很難讓人真正信服了。這讓我意識到,問題也許並不在於中國在做什麼,而是在於外界是如何回應這些行為的。畢竟,這是一條雙行道,永遠只關注其中的一邊顯然是錯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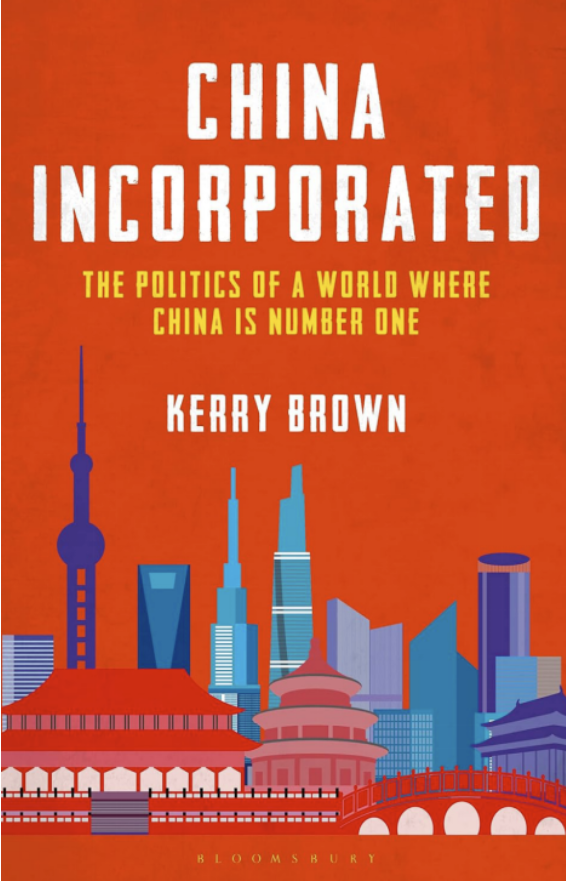
凱瑞·布朗:《包含中國的世界: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後的世界政治》
Q:您已經研究中國幾十年了,不知您是否能告訴讀者,在您看來,中國與西方有何不同?這種不同是否有利於全球的和平與繁榮,還是説中國應該解決這種不同,加入西方俱樂部?
**凱瑞·布朗:**我認為,長期以來歐洲與中國之間的主要問題就是因為雙方存在的差異,這至少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或更早的早期啓蒙運動時期,在這一時期,明清兩代的耶穌會士開始將中國的風土人情與信仰等資料傳回歐洲。如何看待一個基本哲學觀念與世界觀如此不同,歷史發展也與自己相差很大的地方,是先前歐洲人必須回答的核心問題之一。
一開始,這一問題並不帶有什麼傾向性。這不是一個究竟該擁抱中國還是譴責中國的問題,而是該如何理解中國的問題。早期來到中國的觀察者對這個古老的文明感到相當震撼,同時也震驚於中國擁有數千年的文字記載傳統這一事實。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根本不存在這種連續性。
如今,經過幾個世紀的相互接觸與影響,我認為我們應該已經認識到,試圖改變對方,讓對方更加符合我們立場的做法從來都沒有真正奏效過。我們需要做的是找到一個雙方均可接受彼此的狀態。
我認為,至少對歐洲人來説,這是有可能的。我們擁有多元的價值觀。我們想要多樣性,想要一個不同的人都可以和平共處的世界。也許對美國人來説,這有點困難。在研究英國對華關係史時(我的相關著作將於明年出版),我深有感觸,在清末,美國的在華傳教士要比英國的傳教士發揮了更大的作用,而在20世紀初,美國人對於中國沒有按照自己預期的方式進行改革感到非常失望。這種失望情緒在1949年達到了頂峯。
歸根結底,我們需要與不同的理念和平相處,接受彼此的不同,而不是把對方改造為我們希望的樣子。這並不容易,但卻是基於現實的。根據我的經驗,在處理實際問題時,現實主義通常更為有效。
Q:您支持一個多極世界秩序,在其中,西方與中國共享空間,接受中國的不同之處,並與中國合作應對一些共同的挑戰。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似乎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您為什麼認為這是最佳的解決方案?西方接納中國的障礙是什麼?
**凱瑞·布朗:**我認為最好的情況就是人們的心態能發生變化,進而超越目前經常出現的、相當具有侷限性的二元對立局面。幾十年來,英美許多政治家——例如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英國前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ey)——都曾説過,我們不能用一個詞或一個概念來概括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這太複雜了!然而,在當下的大量公開討論中,我們一直都在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來展開辯論,似乎這其中只存在好與壞,而沒有任何介於兩者之間的選項。使用“邪惡”這樣一個帶有道德譴責與摩尼教式信仰的術語來處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好像用前牛頓時代的物理學來描述量子力學一樣!
在新的世界裏,我們需要換一種思維方式,至少作為西方人,我們要接受這樣一個新的現實:不僅是中國人,印度人以及南半球其他地區的人們都在不斷提升自己的繁榮水平,這意味着我們必須接受一個與當下不同的世界秩序來適應這一巨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説,我們還是在用前牛頓時代的外交手段來解決當下量子時代的問題!難怪我們會有如此多的煩惱。
Q: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很難與中國和睦相處,而您卻提出了用一種去道德化或務實的方式來與中國打交道。您的基本觀點是,西方應該與中國合作,完成一些對自身國民有利的事情,而不是專注於改變中國。這一論點讓我們想到了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批評者認為,這一政策並未能給中國帶來好的變化,因此應該廢除這一政策,實行脱鈎/去風險的新方案。您對反對接觸政策的人有什麼看法?
**凱瑞·布朗:**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中國在過去四十年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接觸不是一個錯誤,這一政策的確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的中國甚至與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一次訪問之時都有着巨大的變化。可以説,我們唯一確定的事情就是變化一直都在發生!
如今,中國似乎帶來了很多問題。但正如我之前所説,這些問題往往與外部世界對其的恐慌和誤解有關,而與中國自身正在做的事情無關。
那些認為接觸政策沒有讓中國變好的人實際上只生活在自己的白日夢當中。2020年時,中國就已經解決了極度貧困的問題。在當下這個時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20世紀70年代末完全不同。中國人也正以先前根本無法想象的方式漫遊全世界。現在有近100萬中國人在國外學習。2023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出口國!這些變化怎麼會是壞事呢?

中遠海運騰飛輪停靠碼頭,近4000輛汽車在船邊整齊排列,工人不斷將車開上滾裝船。(圖源:視覺中國)
人們想説的是,中國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但至少在政治上並不是人們所期望的那樣。不過,對我來説,這只是一種短期的、狹隘的看法。正如我在前面所説的那樣,中國一直以來都是與我們不同的國家。中國也總是會給我們帶來驚喜。我相信,未來的中國也不會失去這種特質。中國就是中國!它不是歐洲或美國。中國正在尋求自己的道路。
至於“脱鈎”,我認為在某些領域或許可行,但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挑戰而言,例如全球變暖、人工智能以及大流行病,“脱鈎”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共同努力。這就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因此,儘管媒體和其他平台都在強烈要求中美脱鈎,但實際上,未來很可能是中美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努力合作的時代。這是一個相當簡單的選擇。
要麼我們合作,並有機會阻止極端氣候的發生,很明顯,2023年已經是一個極端氣候頻發的年份了;要麼我們不顧這些迫在眉睫的威脅,繼續相互爭論。我知道我更想要選擇哪條路。我只希望能有足夠多的人同意讓這一切成為現實!
Q:説到“脱鈎/去風險”或“小院高牆”,您如何評價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對中國採取的這種政策?
**凱瑞·布朗:**拜登政府曾試圖對中國採取一系列混合戰術,我認為,隨着脱鈎與雙循環理論的出現,中國也在試圖給出回應。然而,截至2023年末,很明顯,這種方法存在侷限性。

圖截自:《經濟學人》
我認為,現在雙方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即:考慮到代價與風險,相互隔絕比相互合作更有害。從經濟角度看,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於,雙方都已經深深地嵌入到了對方的體系當中並相互融合。因此,在某些領域(如高科技、金融、半導體),劃清界限是可行的,但在其他領域,這樣做則會損害雙方的利益。我們必須記住,中國的中產階級仍然是外部世界的主要市場,他們不斷增長的消費對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而言至關重要。如果不與這一市場打交道,就會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
Q:當中國被西方視為世界上幾乎所有問題的根源時,您會告訴年輕一代的學生關於中國文化、歷史以及這個國家的什麼知識?您認為他們有必要花時間去學習這些知識嗎?
**凱瑞·布朗:**我認為西方國家的學生有必要在這方面向那些中國學生學習。我經常與在英國學習的中國學生打交道。他們相當勤奮,能夠接受不同的思想,也有能力在與他們所熟悉的環境截然不同的地方工作,同時還能保持自己的身份與價值觀,這讓我感到相當驚訝。
這確實很矛盾。一方面,西方有那麼多的批評家糾纏於中國如何試圖影響我們的機構。然而,與此同時,在我們的環境中就存在着大量這樣的人,他們似乎完全可以深入持久地接觸另外一種文化,同時又不會質疑自己的身份與價值觀。
中國學生有着很強的多面性,他們可以跨越不同的體系和信仰,但仍然知道自己究竟是誰。當西方人也能如此接觸中國之時,我想整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加美好。而那些至少帶着開放的心態去中國學習、生活、工作或只是遊歷的人,至少可以在之後體會到更加複雜的現實。而這正是我們亟需的能力。
Q:整個歐洲,特別是英國,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緩解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
**凱瑞·布朗:**借用《孫子兵法》當中的一句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中國的崛起讓我們開始懷疑我們是誰,我們到底信仰什麼。我們對此感到十分不安。但是,我們也絕對能夠應對這一劇變。我堅信,如今圍繞中國的問題不是政治或經濟挑戰,而是一場全球性的文化革命,因為西方國家自近代以來第一次看到一個與他們旗鼓相當、但價值觀卻不一樣的大國。
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這是一個文化挑戰,而非政治挑戰。我們需要通過了解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我們是誰來應對這一挑戰。作為一個崇尚多元與多樣的民族,在未來,中國的存在及其與其他國家的差異和不同,這既是好事,也是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一點,我想我們就能走向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