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青松、馬嶽達、曾維政:烏克蘭危機與西方的中俄關系認知及轉換前景
guancha
【文/萬青松、馬嶽達、曾維政】
2022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危機,被視為近年來最大的“黑天鵝”事件。這場被稱為“21世紀以來歐洲發生的最大規模軍事衝突”,至今已持續近兩年,依然看不見和平的曙光。雖然戰場在烏克蘭,但戰線卻在全世界。持久化的危機進一步演變成大國關係競爭、博弈、調整、演化的催化劑,形成以美國和中俄為代表的新舊兩種力量的較量,朝着競爭與對抗的方向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對中俄的“雙重遏制”步步緊逼,不斷升級。
烏克蘭危機以來,從2022年3月美國國會議員炮製《遏制中俄合謀法案》,4月又拋出《中俄“軸心”法案》,再到5月美西方公開宣佈“必須讓普京失敗”(挫敗普京的同時也意在打擊中國),6月七國集團(G7)領導人峯會發布的聯合公報和隨後北約馬德里峯會通過的《北約2022戰略概念》,以及10月以來拜登政府發佈《新北極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等政策文件,都表達了強化對中俄的捆綁式打壓、極大地壓縮兩國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的意圖。
與政治層面“極限施壓”相伴的是,美西方政策研究界大有借烏克蘭危機配合一些政客進一步唱衰、抹黑、離間中俄關系的平行聲音,且這些聲音在西方輿論的推波助瀾下儼然成為遏制中俄兩國的“急先鋒”。不過,西方政策研究界對烏克蘭危機背景下的中俄關系的認知並非鐵板一塊,在所謂的“主流”之外還有一些值得關注的“逆流”洞見,更有助於理解西方視野下的“新型”中俄關系內涵。本文重點呈現烏克蘭危機以來西方研究界對中俄關系“雙流”(“主流”與“逆流”)認知的三重表現,並探討這些認知的轉換前景。
一、脆弱性與強韌性
西方政策研究界對中俄關系“雙流”認知的第一重表現,可以用“脆弱性”與“強韌性”來概括。
脆弱性(vulnerability)這個概念在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倫理學等領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1]在國際關係領域,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在他們1977年出版的專著《權力與相互依賴》中較早運用了“脆弱性”概念,並將其定義為“行為體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發生變化之後)強加的代價而遭受損失的程度。”[2]這就有別於試圖改變局面而做出變化之前受外部強加代價影響程度的脆弱性,更加突出行為體受到壓力或衝擊這一前提。脆弱性既適用於社會政治關係,也適用於政治經濟關係。
“強韌性”則是美國著名作家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他的著作《反脆弱》中提出的概念,塔勒布認為,面對不確定的環境,特別是存在黑天鵝事件的突發危機環境中,不同事物/系統表現出三種反應:脆弱性—強韌性—反脆弱性。[3]其中,“強韌性”至少包括雙重含義:既是遭遇重創時的抗打擊能力,又是走出逆境的恢復力;既是“百折不撓”的堅韌,又具備“以柔克剛”的靈活。[4]“脆弱性”與“強韌性”顯然與危機有着緊密的關聯,因而也更適合考察烏克蘭危機背景下的中俄關系及其變化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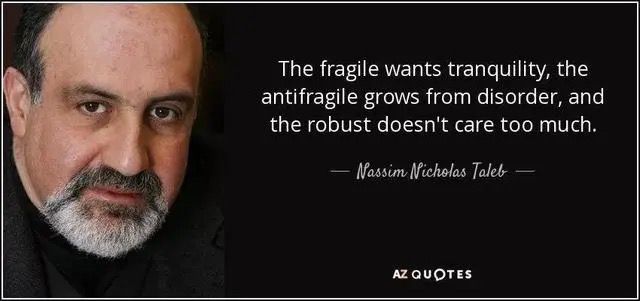
美國著名作家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與他的著作《反脆弱》(圖片來源:網絡)
(一)主流:烏克蘭危機與中俄關系的脆弱性
長期以來,西方中俄關系研究界存在着一種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論調,認為中俄之間的戰略伙伴關係是脆弱的,充滿侷限性。有專家將西方這種“主流”論調稱為“有限論”。[5]在以烏克蘭危機為代表的歐亞地緣政治衝突凸顯的今日,這一老生常談的論調再度在西方政策界、學術圈和輿論場活躍起來,並且斷言中俄關系的未來走向:要麼分道揚鑣,要麼實力虛弱的一方淪為強大一方的附庸。
基於這種二元對立的判斷,此類論調給西方政策界開出的“應對藥方”,往往傾向於主張採取拉攏一方打壓另一方的方式分化、離間中俄關系。具體而言,西方對中俄關系脆弱性的主要認知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中俄關系的脆弱性來自兩國在安全與發展方面相互需求的錯位。西方學者重點強調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中俄在安全和經濟問題上對彼此的需求不相稱,雙邊關係缺乏平等互利的堅實基礎。
歐洲政策分析中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基辛格全球事務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阿林娜·波利亞科娃(Alina Polyakova)指出,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希望獲得中國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強有力支持,這無疑會讓中國在國際上陷入不利地位,因為中國更在意的合作對象是西方發達國家,而俄羅斯目前的國際角色無助於增進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經濟聯繫。[6]
曾任奧巴馬執政時期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成員、美國天主教大學歷史學教授邁克爾·金麥芝(Michael Kimmage)認為,中俄關系受制於雙方矛盾的價值觀和俄羅斯超出中國預期的軍事行動,雙方都不願意為對方做出犧牲,更不用説向同一方向努力了。因此,中俄兩國既不是夥伴關係,更不是同盟關係。[7]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安全研究講師馬辛·卡茲馬斯基(Marcin Kaczmarski)也認為,俄羅斯與中國在綜合國力、特別在經濟潛力方面的不對稱性不斷擴大。過去幾年,俄羅斯大膽而有效的外交政策行動縮小了這種不對稱範圍,但是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的“重大挫敗”損害了軍事強國的形象。隨着衝突遷延和西方制裁加碼,這種不對稱性變成了事實上的結構性因素,將越來越多地決定兩國關係的發展趨勢。[8]
第二,中俄關系的脆弱性來自兩國對彼此威脅的感知。也有西方學者通過刻意放大中俄之間硬實力的巨大差距,借“威脅平衡”等視角來強調兩國關係的脆弱性。
比如,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兩位資深俄羅斯問題專家尤金·魯默(Eugene Rumer)和理查德·索科爾斯基(Richard Sokolsky)提到,美國國家安全界在烏克蘭危機之前普遍認為,俄羅斯忽視“中國威脅”、強化對華合作的戰略是短視且被誤導的;從中長期來看,俄羅斯的真正“威脅”將來自中國而不是西方。因此,美國的政策不應該再強調與俄羅斯的競爭,而是在尋求應對中國“共同威脅”的基礎上與俄羅斯建立夥伴關係。[9]
曾任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歐盟事務主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講席教授查爾斯·庫普錢(Charles A. Kupchan)也認為,烏克蘭危機加深了俄羅斯對中國的戰略和經濟依賴,以及中俄夥伴關係的不對稱性,使得俄羅斯對中國在俄羅斯遠東、北極和中亞日益增長影響力的擔憂增多。[10]
第三,中俄關系的脆弱性還將導致一國對另一國依附更深或“分道揚鑣”。西方專家認為,中俄關系的不對稱性會造成兩國夥伴關係僅侷限於較低水平、特定領域,未來兩國關係要麼破裂疏遠,要麼較弱一方淪為附庸。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俄羅斯與歐亞研究中心主任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認為,在與西方的艱難對抗中,俄羅斯不但喪失了戰略選擇的自主空間,還因經濟、科技和外交等領域遭受制裁而被迫以不利地位向中國的產品、貨幣和技術標準開放,最終可能會淪為一個依附中國的孤立、貧窮、落後的國家。[11]
在里加斯特拉金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脱維亞國際事務研究所新絲綢之路項目負責人烏娜·亞歷山德拉·貝爾津娜-切倫科娃(Una Aleksandra Berzina-Cerenkova)看來,中俄關系高調的官方敍事只能視作動機宣示或未來展望,甚至更多僅着眼於國內宣傳需要。實際上,中國對結盟的謹慎態度未能符合俄羅斯的預期,俄羅斯也一直擔憂自己缺乏對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響力,因此,在高調宣傳下,兩國事實上的疏遠並非不可能。[12]
第四,中俄關系的脆弱性為西方離間兩國關係提供操作空間。
前英國《金融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凱瑟琳·席勒(Kathrin Hille)、前美國外交政策和國防記者卡特里娜·曼森(Katrina Manson)、布魯塞爾分社社長亨利·福伊(Henry Foy)、原北京通訊員克里斯琴·謝潑德(Christian Shepherd)聯合撰文指出,中俄的互信合作僅僅是因為雙方都決心挑戰美國,但中俄並非正式的同盟關係,仍有各自的戰略利益和對國際秩序的不同看法,因此美國有機會尋找中俄關系的弱點,挑撥兩國關係。[13]
美國網絡安全公司CrowdStrike聯合創始人德米特里·阿爾佩羅維奇(Dmitri Alperovitch)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基辛格全球事務中心傑出教授謝爾蓋·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則提醒,俄羅斯應該意識到,中國的目標是實現自己的利益,而非俄羅斯的利益。因此他們認為,西方國家都希望俄羅斯能擺脱對中國的依賴,轉而尋求與西方國家的合作,以實現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成為中國的附庸或乞求者。此外,美國可能會提供某種形式的激勵,以鼓勵俄羅斯在當前的中美戰略競爭中保持中立,而不是與中國結盟。[14]
在這方面提出更大膽的公開建議的是查爾斯·庫普錢,他向拜登政府建言,可以通過離間中國的主要合作伙伴——俄羅斯,來限制其崛起的影響力,具體包括“七步走”:美國放棄以“民主與專制”的框架來構建對外戰略;敦促美國盟友與俄羅斯進行對話;幫助俄羅斯減少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依賴;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擺脱經濟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方面,為俄羅斯提供幫助;主動發起戰略穩定對話;強化與俄羅斯在北極地區的合作;鼓勵和幫助莫斯科遏制中國在發展中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15]
(二)逆流:危機考驗與中俄關系的強韌性
與多數西方學者強調中俄關系脆弱性的“主論調”不同的是,還有一些專家觀察到,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中俄關系的“強韌性”愈發凸顯,尤其關注兩國關係面對危機的抗打擊能力和走出逆境的恢復能力。
一方面,從內部視角理解中俄關系的強韌性,將其與兩國戰略和政策習慣的靈活、彈性或模糊相關聯。
謝爾蓋·拉琴科以保持戰略自主和政策靈活性詮釋中俄關系的韌性,他認為,中俄兩國更傾向於保持各自的戰略自主性,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對方犧牲其核心利益,這種靈活性使得目前的中俄關系比任何軍事聯盟都更持久。在地區事務中,兩國在利益重疊的地方(如中亞)能夠保持一致,同時在利益不重疊的地方(如烏克蘭或南海)保持距離。 [16]
哥倫比亞大學韋瑟黑德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海軍分析中心(CNA)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威什尼克(Elizabeth Wishnick)則將中俄關系“無上限”的提法視為一種具有威懾作用的模糊性策略,能夠給予兩國政策更多靈活的操作空間。她還認為,中俄對於政權安全等國內問題的共同關注,也有助於在分歧問題上達成共識,使中俄夥伴關係依然保持韌性。[17]
此外,烏娜·貝爾津娜-切倫科娃和德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歐盟委員會主席諮詢中心中國問題研究員蒂姆·呂利格(Tim Rühlig)從中國對外政策的“底線思維”出發,認為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中國仍在外交和經濟上給予俄羅斯有限支持,此舉僅是為了避免俄羅斯因陷入內亂和分裂而向中國外溢風險,中國對俄羅斯國內風險因素的擔憂超過了對東歐地緣政治危機的關切,因而願意更加靈活地處理中俄關系。[18]

列車穿過中俄口岸駛入滿洲里國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另一方面,從外部視角理解中俄關系的強韌性,將其與西方競爭,尤其是應對美國的打壓所採取的靈活應對策略相關聯。
瑞典國防研究局亞洲和中東項目研究員克里斯托弗·韋達赫·熊(Christopher Weidacher Hsiung)從觀念建構的視角指出,中俄關系的堅韌性來自美西方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威脅的不斷加劇。這種對共同威脅的認知塑造了中俄的聯合傾向,使得兩國往往會克服潛在的摩擦因素,增強兩國關係的抗風險能力。[19]
美國國家利益中心主席、布什政府高級外交顧問保羅·桑德斯(Paul Saunders)認為,中俄關系立足於互不侵犯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共識,睦鄰友好合作關係極大地釋放了兩國的軍事和外交能力,使雙方可以專注於其他重要戰略方向,因此雙邊關係能夠在外部壓力乃至危機下保持穩定。[20]
甚至在西方政策研究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中俄關系“有限論”的主要代表之一的澳大利亞知名俄羅斯問題專家波波·羅(Bobo Lo)也撰文指出,中俄面對與西方的競爭,彼此成為無可替代的最可靠夥伴,雙邊關係因此具有顯著的韌性,西方國家的分化策略和捆綁打壓只能讓中俄越走越近;為此,他建議西方應關注提升自身競爭力,在國內政治議程和全球治理問題上,繼續發揮軟實力優勢和價值觀吸引力。[21]
二、結盟與去等級化
西方政策研究界對中俄關系“雙流”認知的第二重表現,可以用“結盟”與“去等級化”來概括。結盟(或聯盟)是國際關係最古老的話題之一,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通過集合他們的國力,以增進安全而建立的一種長期的政治與軍事關係。”[22]
不過,隨着時代的變化,對結盟(或聯盟)含義的理解也與時俱進,比如,烏克蘭危機後的2023年5月,美國著名戰略家亨利·基辛格在其百歲生日前與《經濟學人》記者的對話中談道:“我們的聯盟概念不是19世紀的‘聯盟’。我們的理念是建立一個思想平等、美國貢獻巨大的體系,但絕不是完全平等的體系。”[23]很顯然,基辛格對聯盟的理解區別於19世紀的均勢,強調實力優先與等級差異。實際上,西方學界還在爭論聯盟(alliance)與結盟(alignment)的不同內涵。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悉尼大學國際安全高級講師托馬斯·威爾金斯(Thomas S.Wilkins)指出,目前在關於聯盟/結盟的大量文獻中存在重大缺陷。他認為,“聯盟”這個詞通常是本能的和不加反思的使用,而事實上“結盟”一詞是一個更好、更準確的描述詞,他認為當代世界安全環境的特點是多種形式的“結盟”,而不僅僅是聯盟。此外,他還認為“安全共同體”和“戰略伙伴關係”等概念與傳統的“聯盟”模式截然不同,主張對國際關係學科中“結盟”概念進行再分類,呼籲改變對“結盟”和“聯盟”的定義和概念化的思考,以使學科工作向當代國際政治中正在發生的範式轉變。[24]
與結盟相對立的另外一個被越來越多使用的概念是“去等級化”。其中,關於“等級”概念的討論,可以參考美國政治學家戴維·萊克(David Lake)對“國際關係中的等級制”的界定,也即實力較弱的附屬國通過主權讓渡的形式使佔據實力優勢的主導國為其提供一套有價值的政治秩序。[25]換句話説,“去等級化”就是不再以實力對比來固化國家間關係,而是強調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互利共贏。有中國專家也指出,20世紀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等級化國際秩序,21世紀的全球危機則推動國際秩序向去等級化方向轉型。[26]由此可見,結盟與去等級化都反映出國際權力結構的深刻變化,其中也包括大國關係。烏克蘭危機以來,面對西方政策研究中俄“結盟論”的甚囂塵上,“去等級化論”也逐漸積蓄起對中俄關系的解釋力。
(一)主流:結盟與中俄關系
長期以來,西方對“中俄結盟”草木皆兵,用美國戰略思想家布熱津斯基的話説,美國安全面臨的最糟糕情況將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大聯盟”,“俄羅斯和中國一旦在地緣政治壓力下成為同盟,將是西方世界的噩夢……”[27]烏克蘭危機進一步“激活”西方政策研究界的中俄“結盟論”,且呈現出程度不同的表現形式。
一是中俄是不對稱聯盟,且俄羅斯必定扮演“小兄弟”角色。
尤金·魯默和理查德·索科爾斯基指出,與中國建立緊密聯盟來平衡西方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核心,認為兩個“威權國家”之間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互補性,而且美國擁有的全球能力和影響力挑戰了中俄關鍵戰略方向的利益,雙方相互發揮力量倍增器作用,阻止美國將精力集中在其中一方身上。[28]
還有西方學者認為,烏克蘭危機以來,俄羅斯在國際上愈發孤立且對中國的依賴性日益增強,因此未來的中俄關系中,中國的主導地位會逐漸增強,俄羅斯最終會扮演一個“小兄弟”的角色。美國前高級情報官、新美國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兼主任安德烈婭·肯德爾-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也持同樣的看法。她認為,中俄都將美國視為國際上的最大競爭對手,因此兩國有動力加強合作,以對抗美國的影響力和制裁;雖然目前中國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持謹慎態度,不過一旦國際社會的關注度降低,中國可能會更加公開地為俄羅斯提供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29]美國喬治城大學歐亞、俄羅斯和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安傑拉·斯滕特(Angela Stent)也認為,未來中俄關系的不對稱性只增不減,但因兩國彼此需要,俄羅斯也願意扮演“小兄弟”的角色。[30]

2024年1月27日,中俄建交75週年,瀋陽市舉辦俄市奇遇季集市(圖片來源:IC photo)
二是中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針對美國霸權的未正式宣佈的“聯盟”。
多數西方專家認為,中俄關系目前是基於對抗美國的共同戰略,而不是基於真正的友誼或價值觀。兩國關係的密切程度是由與美國領導的“集體西方”之間的對抗所決定的,而不是由兩國自身發展需求所決定。[31]也有部分西方學者從結盟的動因和形式出發,認為中俄結盟是基於對抗美國這一共同對手和打破由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這一相同戰略目標所做出的符合兩國利益的選擇。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俄羅斯事務”項目首任主任西蒙·薩拉吉安(Simon Saradzhyan)指出,中俄處於事實上的互不侵犯條約中,但並未達到相互提供安全支持的聯盟標準,只要中俄都有能力在各自方向單獨威懾美國及其盟友,兩國就不會走向正式結盟。[32]新南威爾士大學政治和國際關係高級講師亞歷山大·科羅廖夫(Alexander Korolev)也強調,中俄結盟是對中美關係和俄美關係同時惡化的自然反應,很大程度上受國際體系因素驅動,兩國都有自己的戰略利益和地緣政治考量,可以提高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可以抵禦西方的干涉和制裁。[33]
三是中俄關系是更加緊密的“軸心同盟”。
烏克蘭危機以來,部分西方專家對中俄結盟的認知更進一步,將其與冷戰陣營對抗的軍事政治聯盟類比。早在烏克蘭危機之前,中俄“軸心”這一生造概念,已經被美國重點智庫、知名專家和部分主流媒體不斷地羅織、拓寬為“(新)威權軸心”、“軸心合作”、“便利軸心”、“網絡軸心”、“文明軸心”等,這樣的看法實際上也體現出超越黨派、政府屆別的延續性認知特徵。
以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NBR)為例,2016年10月,基於兩黨對中俄關系的高度共識,該智庫獲得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的慷慨撥款,專門用於研究美國如何應對中俄戰略合作。國家亞洲研究局與美國多家智庫和大學聯手,發起一個有數十名資深專家參與的為期兩年的研究項目,[34]目的就是找出中俄關系的“離合器”到底在哪裏,什麼原因使中俄志同道合,又有哪些潛在的因素會使中俄反目,最終呈現的報告就將中俄合作定性為“威權軸心”[35]。
有學者指出,參加該項目的絕大多數美國學者都屬建制派,在政見上與時任總統特朗普格格不入,也難以接受特朗普對俄羅斯的一片“痴心”,但在遏制中俄兩國問題上卻是急美國曆屆政府之所急,拜登執政更是為建制派繼續推進打壓和遏制中俄兩國提供了新契機。[36]而烏克蘭危機讓美國政策界對中俄“軸心”合作的程度與未來走向更加擔憂,將其視為“中俄軸心”的試金石。
比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基辛格全球事務中心傑出教授哈爾·布蘭德斯(Hal Brands)認為,雖然中俄兩國並不總是彼此喜歡或互相信任,但他們都在努力打破由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並吸取了冷戰失敗的教訓,在歐亞地區“背靠背”地站在一起對抗美國,以實現在歐亞大陸兩端占主導地位的目標,他們的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冷戰時期的中蘇同盟和二戰時期德日同盟的特徵。他還提到,中俄已經形成了穩定的軸心關係,美國採取讓步和外交等手段離間中俄只會適得其反,因此他主張,必須吸取歷史經驗,推行類似“雙重遏制”戰略的強力手段。然而,美國及其盟友如今雖在經濟、外交和軍事能力方面遠超中俄軸心,但卻無法以低成本來推行雙重遏制戰略。[37]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認為,美國將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一個迅速崛起的系統性對手和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庫的大國正在緊密結盟反對美國。[38]
(二)逆流:去等級化與新型中俄關系
與“結盟論”預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即使是在大國博弈空前激烈的背景下,中俄官方依然堅決否認兩國是結盟關係。2021年10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瓦爾代”年會上表示,俄中沒有建立任何封閉的軍事集團,將來也沒有建立這一集團的目標。第二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高度讚賞普京總統對中俄關系的積極評價,指出“中俄兩國不是盟友,勝似盟友”。雖然這樣的外交話語給人更多想象空間,但在2022年2月4日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中,明確寫入“中俄新型國家間關係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關係模式”[39]。烏克蘭危機以來,兩國也否認結盟。2023年3月,普京總統在接受國家電視台採訪時再次表示,中俄沒有建立軍事聯盟,兩國的軍事技術合作沒有任何秘密,更不會創建一個反北約的全球組織。由此可見,結盟並非中俄關系當下的最佳選項。這一點西方政策研究界的專家也給予了重點關注。

2023年3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稱中俄遵守“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原則(圖片來源:外交部)
1. 中俄關系已經成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
早在2017年,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塞繆爾·查拉普(Samuel Charap)、約翰·德雷南(John Drennan)、皮埃爾·諾埃爾(Pierre Noel)三位研究員就撰文指出,中國和俄羅斯已經學會相互合作和照顧彼此利益,通過兼顧彼此的戰略利益,兩國在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建立了有效的夥伴關係。兩國平等相待,優先考慮“正和”互動,表明中俄之間已經構建起大國關係的新模式。[40]波波·羅也認為中俄遠非基於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的聯盟,而是以現實利益為中心的典型大國關係。在當前國際形勢下,這樣的夥伴關係相對穩定,西方難以分化挑撥中俄關系,因為中俄雙方都無法承受彼此為敵的代價。[41]
與此同時,美國維克森林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助理教授莉娜·貝納卜杜拉(Lina Benabdallah)觀察到,中國大多數時候只是在口頭上支持俄羅斯,而未採取具體的親俄行動,因此“中俄結盟”只是媒體和黨派的政治宣傳手段,未來應該就此類消息加以批判。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俄羅斯戰爭問題高級研究員馬蒂厄·布萊格(Mathieu Boulègue)也明確指出,中俄之間並非結盟關係,而是一種基於利益的務實和機會主義關係。[42]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歐亞項目研究主管羅伯特·漢密爾頓(Robert E. Hamilton)對中俄之間的務實傾向做了更細緻的詮釋,他認為中俄之間既非戰略伙伴關係,亦非“各取所需的軸心”,而是一種取決於具體區域和情境的複雜、動態關係;中俄在利益重疊地區既有合作又有分歧。[43]
中俄關系“不是盟友,勝似盟友”這一頗具中國風格的描述在學術界亦有迴響。有專家認為,中俄遠超結盟性質的關係是建立在雙方對主要國際政治問題以及世界經濟大變局的相似願景的基礎之上的,認為中俄兩國中誰是“大哥”,誰是“小弟”,對於雙方本身來説很重要,但對於全球局勢來説並不重要,因為中俄關系是一個整體現象,並且是國際關係的單獨部分,不涉及承擔義務,不是聯盟但近似聯盟。[44]
2. 中俄意在構建一種去等級化(平等)的戰略伙伴關係。
有學者從中俄合作中強烈的問題導向、務實風格出發,闡述雙邊關係中的平等特徵。謝爾蓋·拉琴科指出,中俄雙方都不太願意接受盟友關係的約束,因為這通常要求雙方承諾互相保護,並就外交政策進行密切磋商,而且這種約束還會導致雙方戰略上的分歧和領導權上的爭執。他認為,中俄關系並沒有形成等級制度,而是以重要戰略問題為基礎,這使得北京和莫斯科都無法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對方,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也可以達成共識,這與中蘇同盟形成鮮明對比。在中俄兩國這種非正式盟友的現實情況下,美國更難“以寡敵眾”。[45]
也有學者將中俄兩國彼此尊重、相互協調的相處模式視為兩國平等關係的基礎。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斯蒂芬·布蘭克(Stephen Blank)指出,與過去不同的是,如今的中俄關系並非等級森嚴,也不要求俄羅斯毫無條件地服從中國的意願,而且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相距甚遠,誰也不指望對方接受同樣的世界觀,所以認為美國可以利用俄羅斯的不滿情緒和對從屬地位的牴觸情緒來挑撥離間的假設是錯誤的。[46]美國海軍分析中心俄羅斯研究項目主任邁克爾·科夫曼(Michael Kofman)也指出,中俄關系不是正式的軍事同盟,俄羅斯也不是中國的附庸,因為北京從未這樣想過,而且經濟實力的不對稱不是決定中俄關系等級的決定性因素,兩國關係是一種協調的、互補的戰略伙伴關係。[47]
此外,還有西方專家的研究指出,中俄追求的去等級化關係在全球層面也得到了積極回應,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中俄項目首席研究員德米特里·努魯拉耶夫(Dmitriy Nurullayev)和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高級研究員米哈埃拉·帕帕(Mihaela Papa)通過對1991至2020年聯合國大會投票狀況的量化分析發現,當中俄立場一致地反對美國時,大多數國家傾向於支持中俄;此外,上合組織、金磚國家、77國集團這類鬆散的非正式聯盟比北約集團在投票時更加團結;這反映出中俄合作立足於推進多極化和革新國際秩序的共同目標,並且得到了可觀的國際支持。[48]
三、存異與求同
西方政策研究界對中俄關系“雙流”認知的第三重表現,可以用“存異”與“求同”來概括。在中文語境中,“求同存異”思想深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無論是《易經》中“厚德載物”、“以同而異”的論述,還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名句,都體現着這種多元包容、追求和諧的觀念。“求同存異”思想在現代被中國共產黨人吸收運用,其核心意指可以理解為“找出共同點,保留不同意見”。這種思想在國內統一戰線事業和新中國外交實踐中大放異彩,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關於“求同而不立異”、“求同而存異”的即席發言是其高光時刻。[49]
“求同存異”思想極大地塑造了中國處理國與國關係的風格和策略,歷久彌新。過去三十多年來,在中蘇關係正常化到中俄建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歷程中,“求同存異”思想越來越被中俄兩國各界接受,構成處理兩國關係的思想理念基礎,對兩國關係的發展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這個成語放在西方語境下卻是先後、主次的“顛倒割裂”,究其根本原因在於:中俄都不是“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的歐美式的二元社會;宗教(或民俗信仰)在長時期中依附於或合作於世俗權力,與歐美大不相同;百年社會主義歷史實踐又使得中俄兩國有着與歐美並不相同的結構稟賦與精神遺產。[50]這些客觀性差異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被西方進一步凸顯為兩國關係的“主流”,尤其是拜登政府執政以來,除了濫施霸凌,還着重以“民主與專制”敍事劃分世界,於是,中俄關系的“求同”就越來越多地被固化為“逆流”。

1955年4月18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萬隆會議,提出並堅持“求同存異”的方針。圖為周總理於萬隆會議(圖片來源:共產黨員網)
(一)主流:中俄關系的“存異”
烏克蘭危機以來,不少西方學者強調中俄在外交政策、地區合作、社會文化方面的諸多“差異”,並且以此判定兩國關係陷入危機或分道揚鑣的必然性。
在外交政策層面,西方學者聚焦中俄在國際舞台上行事風格和策略重心的顯著差異。
有的西方學者着眼於中俄兩國在面對世界變局時總體戰略的差異。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牛津大學榮休教授傅若詩(Rosemary Foot)認為,中俄同時面臨着來自西方的壓力,但兩國處理衝突的方法不同,俄羅斯傾向於對抗性(兼有軟硬手段),而中國更願意避免危機或在危機出現時加以管控,這一定程度上將導致中俄關系疏遠。[51]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史蒂芬·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也總結説,當前世界秩序處在轉折點,中國此刻更希望平靜,而俄羅斯希望製造混亂。[52]
也有西方學者聚焦中俄在具體議題上的策略分歧。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教授史黛西·戈達德(Stacie Goddard)認為,中俄在全球秩序層面擁有對抗美國的共同目標,但在策略工具的選擇上存在分歧,中國更願意通過經濟影響力解決問題;相反,俄羅斯訴諸武力的做法不但在觀念上與中國不同,還可能在實質上削弱中國的經濟工具。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太問題高級編輯林賽·梅斯蘭(Lindsay Maizland)同樣觀察到,不同於俄羅斯對國際秩序的負面和破壞性主張,中國從當前的國際秩序中獲益匪淺,主要尋求改革而非取代,以更好地滿足自身利益;同時,中俄國力發展和經濟影響力的不同軌跡,也導致中國政府內部一些人始終將俄羅斯視為拖後腿的夥伴;此外,中國也極力避免如俄羅斯一樣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採取完全挑釁性的主張,更多采取謹慎和目光長遠的態度。[53]
還有學者關注到中俄外交視野和行動維度的差別。塞繆爾·查拉普在烏克蘭危機前就提到,中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多維化和全球化,而不是僅將俄羅斯作為政策重心。[54]哈爾·布蘭茲也指出,由於中國的國力優勢,中國追求陸地和海洋的複合權力,而俄羅斯侷限於恢復在東歐和中亞的主導地位。[55]
在地區合作層面,西方學者強調中俄在處理地區問題和強化功能性合作方面的差異乃至分歧。
首先,中俄在兩國周邊地區各自開展經濟、外交或安全行動時,特別是在與被另一方看重的第三方互動時容易誘發分歧。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牛津大學歷史學和政治學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強調了中國對北極地區增長的興趣、在中亞日漸形成的經濟主導地位令俄羅斯感到不滿;在中印領土爭端背景下,俄羅斯依然保持與印度密切的軍貿和安全合作也有悖中國的利益。[56]史黛西·戈達德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她還強調了與中國存在海洋爭端的越南也是俄羅斯軍火的重要消費者;這些分歧若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將使中俄關系在未來充滿不確定性。[57]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中國項目”撰稿人和《中俄報告》編輯約瑟夫·韋伯斯特(Joseph Webster)、大西洋理事會歐洲能源安全助理主任帕迪·瑞安(Paddy Ryan)着眼中俄在中亞能源問題上的分歧,指出俄羅斯在衝突爆發以來兩次阻止哈薩克斯坦石油出口,這不僅損害了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的重大經濟利益,也打擊了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
更進一步講,這一分歧突顯出中國其實在保障能源供應、降低能源價格和確保產業鏈供應鏈流動上與西方國家的共同利益更明顯。[58]安德烈婭·肯德爾-泰勒等人也將中亞和北極這些俄羅斯的“腹地”視為中俄區域合作的關鍵分歧點,並且將其與中俄防務安全合作中存在的歷史上的不信任、文化上的不可調和與日益增長的不對稱性相關聯,認為如果不是對抗美國的共同意願,中俄在這些地區和安全領域的合作將難以為繼。他們還進一步提出美國應該利用這些分歧並區別對待中俄,限制兩國合作的範圍和深度,展示與美國和西方合作的可取之處和優勢。[59]
除傳統的經貿、能源和安全這些領域外,中俄網絡空間合作也愈發受到西方學者關注。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新興技術和國家安全研究項目負責人亞當·西格爾(Adam Segal)認為,雖然中俄都基於防範風險考慮推動“網絡主權”的理念,對境外信息加以嚴格管控,反對美國的網絡議程,並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加強合作和協調,但中俄在網絡領域不僅缺乏實質合作,而且仍然彼此保持着戒備和警惕,不太可能分享攻擊性的網絡能力,也沒有在網絡防禦上達成顯著共識。中俄之間在高性能芯片、5G通信等技術上的差距也可能導致長期的緊張和不信任。[60]
在社會文化層面,中俄歷史文化傳統差異持續凸顯的同時,兩國國內當代政治文化的差異也愈發不容忽視。在歷史遺留問題方面,中俄關系中許多負面的歷史遺產依然被一些西方學者關注。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國家歐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史密斯(Nicholas R. Smith)和寧波諾丁漢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特雷西·法倫(Tracey Fallon)將深植於文化和歷史中的國家間友好關係稱作“真誠的國際友誼”,這類友誼能夠顯著增加雙邊關係的穩定性和靈活性。他們的研究認為,雖然俄羅斯是最接近獲得中國真誠友誼的對象國之一,但中俄關系的歷史負面遺產、近期“文明轉向”可能導致的排他性、以及兩國現實權力關係的失衡,都將成為限制因素。[61]
文化方面,在2022年6月美國《外交事務》網站發起的中俄關系專家調研中,有學者指出文化路徑的差異意味着中俄很難真正走近。雖然西方將中俄的政治體制與其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對立,但俄羅斯基本上屬於歐洲文化,目前正在經歷“歐亞化”畸變。但俄羅斯遲早會迴歸歐洲的共同命運,其意識形態中的反西方主義將被拋棄。與此相反,中國是真正的亞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體現,正在努力為躋身21世紀的超級大國而進行全球擴張。[62]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教授威廉·卡拉漢(William A. Callahan)認為,中俄關系中的中國“統一戰線”理念、中俄各自的全球秩序模式和兩國民族復興敍事三類觀念性因素,在中短期內促進了兩國關係發展,但是這三類因素內部存在明顯張力,在雙邊關係層面可能隱藏着放大中俄文化乃至文明差異的風險,在全球層面也不足以支撐起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觀念。[63]
但也有學者強調,在所有影響中俄關系的觀念性因素中,具體的國內政治文化才是決定性因素。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米哈伊爾·特羅伊茨基(Mikhail Troitskiy)認為,中俄兩國的文明或文化差異並非限制兩國務實合作,特別是經濟合作的主要障礙,俄羅斯官僚體系的陳腐作風和惡劣的營商環境才是癥結所在。他認為,只有俄羅斯改變保守和過度“安全化”的政治文化,推進社會生活的法治和多元化,才能激發中俄之間巨大的經濟交往潛力;中俄在當前俄烏衝突背景下經濟往來的增加只是一種“次優狀態”,只有出現可喜的政治過渡,才能真正實現中俄健康蓬勃的相互依存關係,這對美國及其盟友也是有利的。[64]
(二)逆流:中俄關系的“求同”
區別於“存異論”的説法,主張“求同論”的一些西方學者更多地強調中俄兩國的內外“求同”:對內,兩國都深刻地意識到彼此註定是鄰居,因此選擇強化內生合作,補足短板;對外,兩國頂住美西方的壓力,協調處理雙方之間的問題,避免被第三方利用。
1. 中俄傾向於協調處理好雙方之間的分歧與矛盾,避免被第三方利用。謝爾蓋·拉琴科從中俄/中蘇交往的歷史出發,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和有益實踐,強調雙方形成的管理分歧和差異的調節能力。他認為這種調節能力之所以能夠產生,首先是基於中俄所處的複雜國際環境,無論是在冷戰中,還是在當下大國競爭、地緣危機的背景之下,“中俄之間的摩擦很可能會被第三方利用”,超越雙邊範疇影響兩國的全球利益;其次,中俄兩個大國是地緣上“註定的鄰居”,即便不考慮兩國間雖不甚完美但依然可觀的經貿成果,兩國能夠避免敵意和相互威脅已經能極大地減輕兩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成本。這兩方面的成本收益考量其實足以超越兩國間大多數現有分歧。[65]
丹麥外交政策協會研究員、丹麥皇家防務學院副教授莉賽洛特·奧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也從中蘇關係帶給中國的歷史記憶出發,認為冷戰歷史遺產和當代軍事聯盟的負面事例讓中國對“聯盟陷阱”充滿警惕,特別是在中俄關系中,傾向於發展靈活、開放的夥伴關係,既避免了陷入彼此各自的地緣安全議程,又不將自己的夥伴關係完全押注在對方身上。[66]

當地時間2023年9月18日,王毅會見俄外長拉夫羅夫,並聲稱:中俄合作不受第三方干擾 更不被第三方左右(圖片來源:中國外交部)
2. 來自霸權國的直接安全威脅也構成中俄頂住巨大外部壓力、強化“背靠背”戰略協作的動力。美國頂尖智庫蘭德公司發佈的一份研究中俄關系的重磅報告中提出了一種“相對實力理論”,即綜合衡量中美俄三國的軍事、經濟和技術能力,將其與攻擊能力和意圖兩個因素構成的“威脅感”結合在同一個模型內,指出由於力量平衡的趨勢以及美國持續對中俄表現出侵略性意圖的政策,中俄關系加強的趨勢短期內不可阻擋。[67]
旅華德國學者比約恩·亞歷山大·杜本(Björn Alexander Düben)認為,中俄應對相似國內安全風險的需要推進了政策合作,構成雙邊關係的持久增長點。他採用“全方位平衡”理論分析中俄關系趨近的動力,認為兩國在國際體系層面的均勢需要與國內政治中的政權安全考慮,共同推動了中俄關系的走近。[68]史蒂芬·哈德利也提到,從短期來看,中俄關系之所以走近,是因為美國嚴重威脅了兩國的國內安全。[69]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在西方工作或經常發表英文文章的俄羅斯學者也傾向於強調中俄自身發展優勢、兩國深化合作的內生動力,認為中俄應藉此調整和推進雙邊關係。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安德烈·科爾圖諾夫(Andrey Kortunov)認為,雖然中俄雙方在部分國家利益、願望和優先事項上存在重疊,但這種重疊還沒有形成互補發展的內生需求。為此,俄羅斯應該努力推進改革和現代化,提高本國的社會經濟水平,釋放俄羅斯社會的創造潛力。在危機和制裁背景下,俄羅斯應該將困境轉化為加速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動力,成為一個更有價值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指望中國提供不符合經濟理性的幫助。[70]
四、國際危機與西方中俄關系認知的轉換前景
從辯證法的角度看,肯定因素與否定因素的對立統一推動着事物的發展,“危機”也意味着危險與機遇的共存。回顧國際關係史,多數情況下,不同程度的國際危機,是構成新舊國際秩序更替、國際格局演變、大國關係調整的巨大推動力。這一邏輯在中俄關系發展過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演繹和實踐。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外在的自然演進過程。
一方面,從過去三十餘年中俄關系的發展歷程來看,不可否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俄之間緊密的戰略伙伴關係,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在一系列國際危機的推動之下、或至少是在其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比如,1998年亞洲和俄羅斯同時發生的金融危機、1999年科索沃戰爭和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轟炸、對21世紀初恐怖主義襲擊的集體預感、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2020年全球疫情危機、以及當下依然愈演愈烈的烏克蘭危機,都一次又一次地推動着中俄兩國持續接近,並不斷強化兩國戰略伙伴關係。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盧基揚諾夫認為,在重大國際危機背景下,中國傾向於將與俄羅斯的關係視為一種整體現象,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一個獨立因素。[71]
另一方面,烏克蘭危機以來,中俄之間越來越頻繁的交往表明,兩國關係再次經受住了這場巨大危機的新考驗。中俄兩國繼續保持着從元首到事務部門的常態化互動,雙方依然高度評價兩國關係。2022年3月7日,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全國兩會期間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説,不管國際風雲如何險惡,中俄都將保持戰略定力,將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斷推向前進。[72]2022年7月7日,王毅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在印尼巴厘島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時再次強調,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中俄排除干擾,保持正常交往,有序推進各領域合作,展現出兩國關係的強大韌性和戰略定力。[73]2023年3月,正值烏克蘭危機以來中俄兩國面臨極其複雜的外部環境,國家主席習近平再次將俄羅斯作為新任期出訪首站。這絕非偶然,而是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政治決斷,傳遞出的明確信號是:全球變局大背景下必須堅持深化中俄關系不動搖。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會見普京總統時所指出的,中俄互為彼此最大鄰國,同俄羅斯鞏固和發展長期睦鄰友好關係,符合歷史邏輯,是中方的戰略抉擇,不會因一時一事而改變。[74]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與普京總統分別發表署名文章,不約而同地將中俄戰略協作稱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中流砥柱”。迄今,中俄兩國之間的正常經貿合作仍在有序推進,2022年雙邊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1902.71億美元,同比增長29.3%。2023年前11月中俄貿易額為2181.76億美元,同比增長26.7%,提前實現了兩國領導人設立的2000億美元貿易額目標。[75]中俄在區域互聯互通上的合作不斷深化,在其他全球熱點事務上依然保持緊密的戰略協作。

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3日,普京舉行年度記者會 盛讚中俄關系為“史無前例”(圖片來源:IC photo)
基於發展雙邊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主觀和客觀需求,以及兩國不斷深化互利共贏合作的豐富實踐,是否可以認為烏克蘭危機能夠構成西方對中俄關系認知結構轉換的巨大推動力?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認知結構及其轉換作一闡釋。在心理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認知結構的轉換性”[76],是指人類認知系統具有自我調整和適應性的能力,可以根據不同的任務需求和環境條件,調整自身的認知結構和認知策略,以更好地適應外界的變化和需求。無論主權國家及其構成的國際體系多麼複雜難料,歸根結底都是由人構成的,研究分析國際政治現實的理論工具也都可以歸結為人的認知過程,在一定條件下也遵循認知結構轉換的規律。具體到中俄關系而言,邏輯上,當下西方學界的認知可以總結為兩種層面的轉換路徑:一種是宏觀層面的縱向轉換,也即“主流”與“逆流”之間的轉換;另一種是微觀層面的橫向轉換,也即脆弱性與堅韌性、結盟與去等級化、存異與求同三者之間的相互轉換。
理論上而言,這兩種層面的轉換在國際危機的驅動下還會呈現出各種不同的場景組合,在否定之否定規律下,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77]從這個意義上説,西方關於中俄關系認知的“逆流”也確實存在轉變成新“主流”的可能性,也即主張以強韌性、去等級化、求同為內核,構成新型中俄關系的顯著特徵,而不是刻意宣揚兩國關係的脆弱性、結盟、存異,並進一步將其固化為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思維定式。
但考慮到烏克蘭危機的發生恰逢全球轉型的不確定性進入新階段,[78]也即過去的國際體系逐漸坍塌,而新的體系,即使是抽象的“多極體系”,也沒有構建起來,對未來國際體系的想象也不甚清晰,使得世界發展變得越發複雜。在“缺少透明遊戲規則和國際體系構建共同原則的背景下,各方之間的衝突、矛盾會越來越多,國際體系的碎片化趨勢”[79]將會更加強化。而“舊世界已然老去,新世界尚未最終形成”,[80]這既意味着在舊世界向新世界轉換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也意味着包括“主流”與“逆流”在內的不同轉換路徑之間的曲折複雜進程。
雖然西方關於中俄關系的那些所謂“主流”,就學術研究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而言,可能已經與具有新的生命力、代表未來發展趨向的“逆流”相去甚遠,但作為已被固化並進一步被強化的西方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還會繼續成為“‘逆流’而上”難以跨越的一道門檻。
1. 李鶴、張平宇、程葉青:“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評價方法”,《地理科學進展》,2008年第2期,第18-25頁;楊飛、馬超、方華軍:“脆弱性研究進展:從理論研究到綜合實踐”,《生態學報》,2019年第2期;王福玲:“認真對待脆弱性”,中國社會科學網,2021年9月7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396138;《中國大百科全書》也收錄了“脆弱性”術語,界定為經濟學範疇,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 =120436
2.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p.13.
3. [美]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反脆弱》,雨珂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4. 吳晨:“韌性與創新”,《經濟觀察報》,2022年12月5日,第1098期。
5. 於濱:“中俄正常關係的再思考:理論、歷史與未來”,《俄羅斯研究》,2023年第4期。
6.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Foreign Affairs, June 21,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sk-the-experts/2022-06-21/will-china-and-russ ia-stay-aligned
7. 出處同上。
8. Marcin Kaczmarski, “Which Russia-China Relationship Will Emerge After the War?”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May 5, 2022, https://www.ispionline.it/en/p ublication/which-russia-china-relationship-will-emerge-after-war-34895
9. Eugene Rumer, Richard Sokolsky, “Narrative: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3,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 s/87185?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
10. Charles A. Kupchan, “The Right Way to Split China and Russia: Washington Should Help Moscow Leave a Bad Marriage”, Foreign Affairs, August 4,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 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04/right-way-split-china-and-russia
11. Alexander Gabuev, “China’s New Vassal. How the War in Ukraine Turned Moscow Into Beijing’s Junior Partner”, Foreign Affairs, August 9,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 na/chinas-new-vassal
12. Una Aleksandra Berzina-Cerenkova, “Sino-Russian Narratives of Coopera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Baltic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ugust 6, 2020, https://www.fpri.or g/article/2020/08/sino-russian-narratives-of-cooperation-and-what-it-means-for-the-baltics/
13.Kathrin Hille et al., “US urged to exploit cracks in Russia-China relationship”, The Financial Times, July 27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b59bd581-a9f8-4415-9be6-4dff722 e87a9
14. Alpetrovitch, D., Radchenko, S., “Another Russia Is Possible. The Kremlin Will Eventually Tire of Its Reliance on China”, Foreign Affairs, August 29, 2022, https://www.forei gnaffairs.com/russian-federation/another-russia-possible
15. Charles A. Kupchan, “The Right Way to Split China and Russia: Washington Should Help Moscow Leave a Bad Marriage”, Foreign Affairs, August 4,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 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04/right-way-split-china-and-russia
16. Alpetrovitch D, Radchenko S, “Another Russia Is Possible. The Kremlin Will Eventually Tire of Its Reliance on China”, Foreign Affairs, August 29,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 m/russian-federation/another-russia-possible
17. Elizabeth Wishnick, “Still ‘No Limits’? The China-Russia Partnership After Samarkand”, Russia Matters, September 22, 2022,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still-no-limits-chi na-russia-partnership-after-samarkand
18. Una Berzina-Cerenkova, Tim Rühlig, “China’s Complex Relations with Russia: Tracing the Limits of a ‘Limitless Friendship’” Internationale Politik Quarterly, September 12, 2023, https://ip-quarterly.com/en/chinas-complex-relations-russia-tracing-limits-limitless-friendship
19.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20.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21. Bobo Lo,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ssumptions, Myths and Realities”, Russie.Nei.Reports, 2023, No.42,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etudes-de-lifri/russienei reports/sino-russian-partnership-assumptions-myths-and
22. [美]T. N. 杜普伊主編:《國際軍事與防務百科全書》,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編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
23. “A conversation with Henry Kissinger: The transcript of his meeting with our journalists”, The Economist, May 17,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kissinger-transcript
24. 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 –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2, Vol.38, No.1, pp.53-76.
25. [美]戴維·萊克:《國際關係中的等級制》,高婉妮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26. 鄭宇:“21世紀多邊主義的危機與轉型”,《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8期。
27. [美]布熱津斯基:“美對華缺戰略目光 需警惕中俄結盟”,《環球時報》,2017年1月13日;“社評:結夥對抗中俄將是美西方噩夢之旅”,《環球時報》,2021年5月5日。
28. Eugene Rumer, Richard Sokolsky, “Narrative: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3,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 s/87185?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
29.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30. 出處同上。
31. 出處同上。
32. Simon Saradzhyan, “Why Russia’s alliance with China is improbable, but not impossible”, The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Research, September 21, 2020, https://www.frstrategie.org/en/pu blications/recherches-et-documents/why-russia-s-alliance-china-improbable-not-impossible-2020
33.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34. 該項目的核心成員包括:美國前負責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國家亞洲研究局主席、著名的中美關係專家理查德·埃林斯(Richard Ellings),知名“中國通”、曾任國家情報委員會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情報官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長期供職布魯金斯學會負責俄羅斯歐亞項目的資深俄羅斯問題專家安傑拉·斯滕特(Angela Stent),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與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韋茨(Richard Weitz)等。Se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https://www.nbr. org/program/strategic-implications-of-russia-china-relations/
35. Richard J. Ellings and Robert Sutter, Axis of Authoritarians: Implications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8.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axis- of-authoritarians-implications-of-china-russia-cooperation/
36. 於濱:“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5期,第70-108頁。
37. Hal Brands, “The Eurasian Nightmare. Chinese-Russian Conv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Order”,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china/2022-02-25/eurasian-nightmare?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registered_user_welcome&utm_term=email_1&utm_content=20231125
38. “Putin to visit China to deepen ‘no limits’ partnership with Xi”, October 15, 2023, https://w ww.reuters.com/world/putin-visit-china-deepen-no-limits-partnership-with-xi-2023-10-15/
39.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22年2月5日第2版。
40. Samuel Charap, John Drennan, Pierre Noël, “Russia and 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urvival, 2017, Vol.59, No.1, pp.25-42.
41. Bobo Lo,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ssumptions, Myths and Realities”.
42.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43. Robert E. Hamilton, “Stress-Testing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y 25, 2023,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3/05/stress-testing-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44. Lukyanov, F.A, “Between Two Special Operation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3, Vol.21, No.2, pp.5-10.
45. Sergey Radchenko,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on’t Work”, War on the Rocks, August 24, 2021,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8/driving-a-wedge-between-chi na-and-russia-wont-work/
46.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47. Michael Kofman, “The Emperors League: Understanding Sino-Russian Defense Cooperation”, War on the Rocks, August 6,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8/the-emp erors-league-understanding-sino-russian-defense-cooperation/
48. Dmitriy Nurullayev, Mihaela Papa, “Bloc Politics at the UN: How Other States Behav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Russia Disagree”, Global Studies Quarterly, 2023, Vol.3, No.3, pp.1-11.
49. 孫信、李健:“求同存異原則溯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50. 引自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教授承擔的2021年度國家高端智庫重點課題的結項報告(未對外發布)。
51.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52. Stephen J. Hadley, “Stephen Hadley on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vember 14, 2023, https://w 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stephen-hadley-major-challenges-facing-united-states-today
53. Lindsay Maizland, “China and Russia: Exploring Ties Between Two Authoritarian Power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4, 2022,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a-russia- relationship-xi-putin-taiwan-ukraine
54. Samuel Charap, John Drennan & Pierre Noël, “Russia and 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urvival, 2017, Vol.59, No.1, pp.25-42.
55. Hal Brands, “The Eurasian Nightmare. Chinese-Russian Conv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Order”,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5,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china/2022-02-25/eurasian-nightmare?check_logged_in=1&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lo_flows&utm_campaign=registered_user_welcome&utm_term=email_1&utm_content=20231125
56.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57. 出處同上。
58. Joe Webster, Paddy Ryan, “Beijing and Moscow clash over Kazakhstan’s oil”, Eurasianet, Aug 11, 2022, https://eurasianet.org/perspectives-beijing-and-moscow-clash-over-kazakhstans -oil
59. Andrea Kendall-Taylor, David Shullman, Dan McCormick, “Navigating Sino-Russian Defense Cooperation”, War on the Rocks, August 5,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8/ navigating-sino-russian-defense-cooperation/
60. Adam Segal, “Peering Into the Future of Sino-Russian Cyber Security Cooperation”, War on the Rocks, August 10,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8/peering-into-the-future-of- sino-russian-cyber-security-cooperation/
61. Nicholas Ross Smith, Tracey Fallon, “The importance of bona fide friendship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a’s quest for friendships that matter”,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62. “Will China and Russia Stay Aligned? Foreign Affairs Asks the Experts”.
63.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Global Orders: Socialism, Tradition, and Nation 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2023, Vol.59, No.2, pp.1-28.
64. Mikhail Troitskiy, “A Final Reckoning? Sino-Russian Relations Amid Russia’s War on Ukraine”, PONARS, June 9, 202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71445335_A_Fi nal_Reckoning_Sino-Russian_Relations_Amid_Russia’s_War_on_Ukraine
65. Sergey Radchenko,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Won’t Work”.
66. Liselotte Odgaard,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Alliance and Alignment: Entrapment Concerns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sian Affairs, 2023, Vol.54, No.3, pp.432-452.
67. Andrew Radin, Andrew Scobell, Elina Treyger, J. D. Williams, Logan Ma, Howard J. Shatz, Sean M. Zeigler, Eugeniu Han, Clint Reach,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Determining Factors, Future Trajector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21.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3067.html
68. Björn Alexander Düben, “Omnibalancing in China-Russia relations: regime survival and the specter of domestic threats as an impetus for bilateral alignment”, Post-Soviet Affairs, 2023, Vol.39, No.6, pp.462-486.
69. Stephen J. Hadley, Karen Donfried, “Stephen Hadley on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Belfer Center, November 14, 2023,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 tion/stephen-hadley-major-challenges-facing-united-states-today
70. Andrey Kortunov, “Russia Facing China: Little Red Riding Hood or Cinderella?”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September 16, 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 omments/analytics/russia-facing-china-little-red-riding-hood-or-cinderella/
71.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Анти-СВО и е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рофиль. 2023. №.11-12. С.40-42.
72.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回答中外記者提問”,中國政府網,2022年3月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3/08/content_5677795.htm
73. “王毅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2年7月8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207/t20220708_10717115.shtml
74. “習近平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新華網,2023年3月21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3/21/c_1129448868.htm
75. “中俄全方位合作務實高效”,人民網,2024年1月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0108/c1002-40154720.html
76. 關於認知結構的轉換性及其轉換規律的論述參見[瑞士]皮亞傑:《結構主義》,倪連生、王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11頁,第52-67頁。也可參見國內學者相關梳理,陳英和:“皮亞傑學派與現代認知心理學關於兒童認知發展觀點之比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
77. [德]卡爾·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頁。
78. 本文的“全球轉型”主要指:各國內部政治經濟體制轉型;在此背景下的國際秩序的調整;作為內部制度變遷和國際秩序這兩者間連接物的各國對外政策與戰略。這三者經過互動而形成的普遍性趨勢與進程,可被視為是全球轉型的總體態勢。參見馮紹雷:“歐洲對抗與亞洲突圍——全球轉型中的歐亞新博弈”,《俄羅斯研究》,2022年第1期,第84-91頁;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Эпоха полураспада: от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 миропереходу//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9. T.17. №2; Владимир Барановски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динамика систем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7. №3; Barry Buzan,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9. 萬青松:“2021年的俄羅斯外交:再平衡中的新調適”,《俄羅斯研究》,2022年第1期,第164-192頁。
80. 馮紹雷:“舊世界已老去, 新世界尚在構建中”,《文匯報》,2021年1月22日,第8版。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