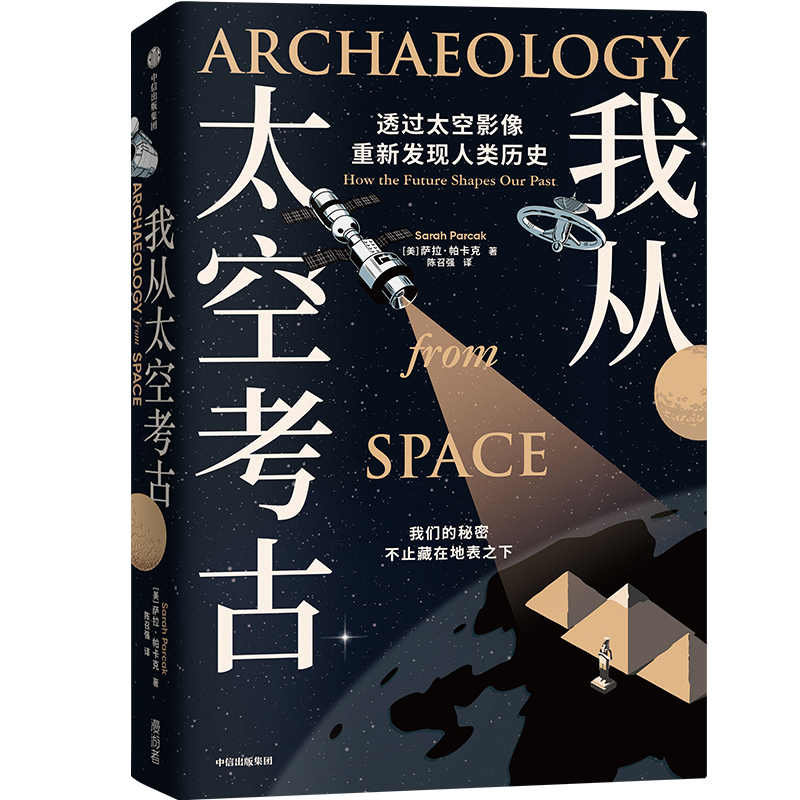薩拉·帕卡克:盜墓賊,我們在看着你
guancha
【文/薩拉·帕卡克】
從古遺址到易貝
如今,古物收藏的歷史已經開啓了新篇章。得益於易貝以及其他類似的網站,一個人只要花上幾百美元,就可以購得一枚聖甲蟲飾物。
在易貝輸入“antiquities”(古物)一詞,就能找到55000條結果。點擊“Egyptian antiquities”(埃及古物),結果減少至5000條。在第一頁的50條結果中,有一半的賣家稱其所售物品為“真品”,不過在我看來,真品可能也就兩三件。有些是相似度非常高的仿品,看起來就像是工匠對着原作打造出來的,只不過在某些細節上搞砸了。專家當然可以甄別出贗品,但大多數持有信用卡的冤大頭一無所知。
在與易貝團隊就該問題進行交流之後,我心中可以説是五味雜陳。我問他們能否把“古物”品類從網站上移除,因為上面出售的任何真品都可能是盜墓賊盜掘所得。他們告訴我:“我們可以這麼做,很容易處理那些人。但你想抓的是那些真正的壞傢伙,所以首先還得搞定他們。”
盜墓的歷史源遠流長。國王圖坦卡蒙的喪葬祭禮人員就監守自盜,將罐子中的油膏據為己有,因為這種濃稠、芬芳的護膚膏不像其他物品一樣刻着國王的名字,因此丟了也無從追查。圖坦卡蒙墓葬的發現者、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及其團隊,就曾看到油膏容器裏留有手勺的痕跡。
每每從被嚴重盜掘的遺址走過時,我依然感到心碎。看着地上散落的人體遺骸、木乃伊裹屍布以及最近才被盜墓賊打碎的陶器,我就知道我們又永久地失去了人類歷史的一部分(見圖11—1)。木乃伊的每一個部位,都來自一個曾經活生生的人。他們曾經跟你我一樣,會呼吸,會笑,心中也充滿愛。如果你的至愛的長眠之地亦遭此褻瀆,你會有何感受?

圖11—1 埃及吉薩附近遭盜掘的墓葬
除了造成明顯的物質破壞之外,盜墓賊還會給現代社會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在當今很多地方,人們依然認同甚至崇尚古代文化。他們信守已有數千年曆史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併為此感到自豪,而種種的盜掘和其他破壞遺址的行為,則會抹去那些不可替代的文化記憶。如果數百處遺址齊齊被盜掘,那就好比那些肆意破壞文化遺產的古汪達爾人將關於該文化的所有圖書館都付之一炬。
其中有一些議題非常貼近我們的生活。在美國西南地區,盜掘活動與當地日趨嚴重的甲基苯丙胺(冰毒)和阿片類藥物的濫用有關。美國的盜墓賊是高度組織化的,而且善於鑽空子。2018年1月,美國政府宣佈停擺,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後,“金屬探測”主題郵件就開始在電子郵件列表服務系統上傳開,內容大致是“夥計們,開幹吧,沒有人值班了,我們一起去盜掘南北戰爭的遺址”。
街區暴動
在“阿拉伯之春”系列事件發生之後,我的職業生涯找到了新的重點。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的來自埃及的直播畫面令人難以接受。如果宇宙中有一個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車水馬龍、永不停歇的中心的話,那麼摘得這一殊榮的一定是位於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每次到那裏,我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按順時針方向看,廣場周圍分別坐落着埃及博物館;深受考古學家偏愛的讓人愉悦的廉價酒店;埃及美國研究中心,這是一家為美國研究團隊提供大力支持的考古機構;尼羅河希爾頓酒店,即如今的麗思卡爾頓酒店,酒店內的美食區曾一度成為埃及古物學家休息日的總部。
2011年1月25日,數十萬人湧入解放廣場,他們舉着旗幟,喊着口號,要求結束總統穆巴拉克長達30年的統治。在隨後的幾天裏,我們一直都守在電腦前。週六醒來時,我們看到了埃及博物館被洗劫的新聞報道。
我忍不住痛哭起來,同時也做了最壞的設想。2004年2月29日,我就是在那座博物館裏向我丈夫求的婚。要知道,這顆星球上最精美的埃及古物,都被收藏在那裏。在令人難以忘懷的畫面中,埃及人圍成人牆,保護着他們的文化心臟。“這裏不是巴格達!”他們大聲喊道,很多人眼裏都噙着淚水。
幾個小時之後傳來新聞:暴徒並沒有給博物館造成大面積的破壞。這是一起漫無目的的打砸搶事件。而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博物館員不辭辛勞,找回了大多數被盜的藏品。
我如釋重負,但這也只持續了短短24小時。接着,網絡上有傳言稱,吉薩和薩卡拉遭到大規模洗劫。我加入了一個數百名考古學家參與的全球郵件系統,互通信息。大家對當時的埃及局勢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毫無幫助的郵件越積越多,指責埃及同行的嗓門也越來越大,控訴他們做得不夠,未能在“革命”時期阻止洗劫活動的發生。但實際上,在那段時間,這些埃及同行都在冒着生命危險,同全國各地的遺址洗劫者做鬥爭。
我隨即寫了一封郵件告訴每一個人,確定洗劫活動是否對遺址造成破壞的唯一方法就是查閲衞星影像,即對遺址遭洗劫前後的衞星影像進行比照。幸運的是,這次收到了比較令人滿意的信息,回信人是時任《國家地理》雜誌總編輯克里斯·約翰斯。
克里斯問我們是否可以從太空測繪洗劫活動。我説可以。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我的同行、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伊麗莎白·斯通就率先使用高分辨率衞星影像記錄伊拉克南部地區的遺址遭洗劫情況。我告訴克里斯,我有2010年的衞星影像數據,可作為洗劫活動發生前的資料使用。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和地球之眼基金會幫助購買了薩卡拉地區的新數據——這些衞星影像是在埃及“革命”暴發僅兩週之後拍攝的。在仔細對比洗劫活動發生前後的兩組數據集時,我發現了種種駭人跡象:在左塞爾金字塔建築綜合體的東北部,存在明顯的推土機車痕,而這無疑是該遺址在近期遭到野蠻盜掘的證據(見圖11—2)。我把相關影像發給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由此也拉開了一個專注於埃及考古和文化遺產的合作項目的序幕。

圖11—2 薩卡拉一帶遺址遭洗劫前後的高分辨率衞星影像對比(資料來源:數字地球公司)
2011年5月,美國古物聯盟邀請我陪同一羣前外交官和政府官員前往埃及考察,其中包括總統喬治·W.布什的一位新聞秘書。我提前準備了一份提交埃及政府的簡報材料,並附上了最新的衞星影像。這些影像是在出發前幾天拍攝的,從中可以看出薩卡拉和代赫舒爾等重要遺址遭到進一步破壞。
我們前往議會大廈,同埃及旅遊、對外關係、文物和外交等部門的負責人舉行會談。走進會議室時,我不知所措了。天花板距離地面約有100英尺,室內華麗的帷幔如同懸垂的瀑布。媒體人員和埃及各部門負責人的隨行人員擠在一旁。我沒有任何外交經驗,以為自己不會被安排在會議桌旁。
我們坐在埃及高級官員的正對面。我先前準備的材料,他們人手一份。美方代表團團長、古物聯盟的負責人德博拉·萊爾在發言中先對與會人員表示了感謝,做了開場白……然後轉向我説,“現在請薩拉談一下她的衞星影像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對埃及文化遺產的意義”。
我做了我唯一知道該如何做的事:當一名埃及古物學者。
在講述埃及一些最知名遺址被盜掘的現狀時,與會人員無一插話。衞星影像資料呈現的結果可謂觸目驚心,事實無可爭辯。他們對發生在自己國家的事情感到擔憂和震驚,心情也越發沉重起來。他們聽着,認真地聽着。
當我儘自己所能,用阿拉伯語向在場的人表示感謝時,我看到他們揚起了眉毛,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我在想我是不是違反了基本的國際外交禮儀。但隨後,埃方隨行人員滿面笑容,紛紛豎起大拇指。一名女士補充説:“你説話就像個土包子,不過我們都聽懂了。”
這場會議改變了我的人生。我當然知道考古和歷史在全球政治中所發揮的作用,但親自參與其中,並塑造兩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另一回事。這讓我跳出象牙塔,進入一個更開闊和更駭人的世界。
故事還在繼續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隨後加大了支持力度,為整個埃及的盜掘趨勢提供研究資金。我聘請了一個團隊來幫助處理相關數據。在一個面積超過70萬平方千米的地區,面對成千上萬處考古遺址的12年的數據,我別無他法,只能組建自己的“復仇者聯盟”。在該項目中,我們主要利用的是谷歌地球的開放數據,因為若採用商業衞星數據,光是購買成本就超過4000萬美元。
在長達6個月的時間裏,我們對2002—2013年的高分辨率衞星影像進行分析,測繪了超過20萬個盜洞。一旦你知道了你要找的是什麼,那麼工作就會變得容易起來:暗色正方形,周圍有一圈土,形狀類似於甜甜圈。這些土是盜墓賊在尋找有利可圖的墓葬豎井時挖出來的,而有些豎井的深度甚至達到10米。盜洞的平均直徑約為1米,這就意味着它們在衞星影像上很容易被識別出來。在分析的數千處遺址中,我們發現有279處遭到了盜掘或破壞,而且證據清晰。在處理數據的過程中,我和我的團隊見證了一段又一段歷史的消失,心頭也越發沉重起來。
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出現在2008年之後的數據中。2002—2008年,遺址遭盜掘事件的發生率一直維持在一個相對固定的水平上。按照我們的預計,2011年之後會大幅上升。但科學總有辦法顛覆那些想當然的、易於得出的結論。在全球經濟出現衰退後,遺址遭盜掘事件在2009年呈急劇增長趨勢。沒錯,2011年是出現了大幅上升,但這個上升趨勢早在2009年就已經拉開了序幕,推動這一進程的不是當地的掌權者,而是全球經濟。
我們對數據做了全面處理,並試圖確定未來的趨勢。我們的結論是,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那麼到2040年埃及的所有遺址都會遭到盜掘。
我們的全球文化遺產面臨着一個嚴峻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只能靠周密、審慎的長期規劃。如果考古學家和其他專家不去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在接下來的20年到25年裏,中東地區的大部分古遺址將會消失殆盡。
希望或絕望
此前,你已經看到了很多關於考古發現和歷史重述的故事。如果你在意未來考古發現的價值,那麼本章的內容會讓你痛心,因為你現在非常清楚地知道這些損失的利害關係了。抱歉擾亂你的心緒,但我依然會這麼做。要知道,面對每一處遺址,我和我的團隊都會問我們已經失去了什麼,以及接下來我們可能還會失去什麼。
有時候光明會出現在隧道的盡頭。參與遭盜掘遺址的測繪工作的同行在出席美國國會和國務院舉行的聽證會時,通過衞星影像展示了恐怖分子和其他國際犯罪分子正在進行的遺址破壞活動。遙感領域的“神奇女俠”、史密森尼學會下設的博物館保護研究所的研究員凱瑟琳·漢森,在此過程中也貢獻了自己的專業力量。由此,美國2015—2016年國會通過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和保全法案》(HR1493)。該法案倡導成立一個文化遺產協調委員會,並對來自敍利亞的考古材料實施進口限制。
2014年,我和6名同行在美國國務院舉行的聽證會上做證,支持對埃及古物實施進口限制。此次聽證會上,我分享了遺址遭盜掘的相關數據,而其他人則談了盜掘活動對特定遺址的影響。在此基礎上,2016年美國與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某個國家簽署了首份雙邊文化遺產保護備忘錄。
2017年秋,一樁非法走私古文物案登上新聞頭條。涉事企業是在美國隨處可見的手工藝品連鎖店好必來,年營業額超過30億美元。為證明《聖經》所載內容的真實性,好必來的所有者格林家族開始收集古物,進而斥資5000萬美元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成立聖經博物館,其展品中包括數以千計的中東物件。
幾年前,格林家族與專門研究非法走私古文物的專家會面,其中就包括德保羅大學的法學家帕蒂·格斯滕布里斯(PattyGerstenblith)。在文化遺產和法律領域,格斯滕布里斯是大神級人物,專門撰寫過該題材的教科書。格林家族原本考慮購買來自伊拉克的滾筒印章,但心中頗多顧慮,因為他們懷疑那些印章可能是在伊拉克戰爭後非法外流的文物。格斯滕布里斯及其同事對此表示認同,建議格林家族放棄購買。傳遞的信息非常明確:購買那些印章可能是違法行為,並會產生嚴重後果。
但格林家族最終還是選擇了購買,並以“屋頂瓦片”的名目進口到美國,隨即被當局查獲。這次人贓並獲的行動,不僅讓外界對聖經博物館的藏品來源的合法性產生了懷疑,而且導致博物館被罰了300萬美元。對億萬富豪來説,這樣一筆罰金在財務上可以説是九牛一毛,但執法人員並未收手,而是繼續展開針對格林家族的調查。截至2018年冬,博物館的另外數百件藏品也受到了嚴格審查。
防止類似案子發生,絕非易事。對執法部門來説,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為古物走私確立“相當理由”,即為指控或逮捕提供合理依據。一旦有了相當理由,檢方將案子提交法庭就會簡單很多。不過,海關和移民部門官員在蒐集證據方面仍面臨巨大障礙。當他們懷疑某個人非法購買古物時,他們必須在排除合理懷疑的前提下,證明古物是盜墓賊盜掘的。此外,他們還必須準確指出盜掘時間。
盜墓賊,我們在看着你
衞星影像等技術不僅可以幫助政府確認某一物品是否為盜掘所得,還可以幫助考古學家找到該物品的確切來源,從而獲得與之相關的寶貴背景。你可能會對此嗤之以鼻,我理解你的懷疑心態。在本書中,我一直都在講衞星可以為考古做什麼以及不能做什麼。沒錯,我們無法從太空將鏡頭拉近來看清每一件物品。即便我們能夠看清,捕捉盜墓賊把木乃伊從地下盜掘出來的瞬間場景也可能比中彩票還難。由於缺乏物品盜掘地的照片證據(盜墓賊通常不會在現場擺拍),我們可能無法支持相當理由的認定。
暫且再相信我一次。如果你可以確定一件物品的來源,那麼其中就有很大的寓意。各國政府會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返還它們的文化遺產,而原住民社區也可能會提出同樣的要求,將物品收回並在當地博物館展出。就一件物品而言,即便我們無法準確掌握它在考古學上的來龍去脈,但只要知道出土它的遺址,我們仍可以從中獲取新的考古知識。最後,證明物品是否為盜掘所得,是檢方起訴前的首要一步,而只有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將那些毀壞全球文化遺產的不法分子繩之以法。相信我,這個夢想一定會實現的。
木乃伊詛咒行動
在《國家地理》關於埃及遺址遭盜掘事件的專題報道中,我收集了特定案例的信息。2014年冬,我和專題作者湯姆·米勒在紐約碰面,決定共同調查相關的犯罪事實。湯姆一頭鬈髮,脾氣火暴。對於我搜集整理的埃及遺址遭盜掘的資料,他已經非常熟悉。不過,他還想了解一下這個產業鏈的下游,即那些被盜的古物流入西方市場後的情況。
在美國聯邦移民海關執法局(ICE)的邀請下,湯姆和我獲得了訪問許可,可實地探訪一個秘密據點。該據點位於布魯克林,是一棟氣勢恢宏的輕質磚砌建築物,牆上裝有假窗,後門配有一個裝卸平台。這是一個儲藏設施,專門用來存放被沒收的藝術品,即紐約富豪名流收集的非法藏品。在安檢口接受了例行檢查之後,我們被帶到樓上,映入眼簾的是形狀、尺寸各異的箱子,從地面一直堆積到天花板,就像《奪寶奇兵》片尾的場景一樣。(是的,我每一層都仔細看過,想找到約櫃形狀的箱子,但運氣不好,一無所獲。)
隨後,和我們聯絡的探員又領着我們到了樓下,進入一間光線明亮的房間,裏面陳列着在木乃伊詛咒行動中查獲的古物。順便説一句,“木乃伊詛咒行動”是官方行動代號,可不是我隨口杜撰的。2009年,美國聯邦移民海關執法局根據可疑的進口單證,對知名的埃及古物收藏者約瑟夫·劉易斯三世的車庫進行了突擊檢查,查獲了一口被切成兩半的由美國郵政系統運送的埃及棺槨。
劉易斯是從一個名叫穆薩·扈利(外號“莫里斯”)的交易商手中買的那口棺槨以及其他文物。特別探員布倫特·伊斯特此前就從扈利那裏查獲了一尊來自伊拉克的雕塑頭像,但他懷疑這只是這個從事骯髒勾當的傢伙的第一次失手而已。在扈利公司的網站“温莎古物”上,伊斯特發現了若干宣稱來自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埃及文物。
扈利最終承認它們來自埃及,也就是説這違反了埃及的《國家失竊財產法案》。按照該法案,埃及的古物是被禁止運送到國外的。在伊斯特開展的突襲行動中,共查獲價值250萬美元的古物。扈利僅被判居家監禁6個月和社區服務以及一年的緩刑。劉易斯辯稱他不知道自己收到的是贓物。在2014年該案再審時,他被撤銷所有指控,但美國國土安全部全部沒收了查扣的若干文物。
湯姆後來告訴我,他真希望當初有人能夠拍下我走進那間存放找回的古物的房間時的表情:震驚、憎惡和完全不可思議。在那一刻,我這名埃及古物學者一句話也説不出來,因為一個古老的幻象飄浮在我的面前,輕飄飄地進入記憶的蒼穹,可以讓我在臨終時重温。紅色、白色、淡黃色、黑色—彷彿一塊完美的調色板被畫在了一口有着2400年曆史的棺槨上,而這是我先前從未見過的。棺槨裝飾還包括一張優美的雕刻面孔,這或許是死者的肖像。
我強忍着淚水,在《國家地理》團隊拍攝專題報道照片時,轉身去看其他非法入境的文物。從中王國時代的船隻模型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木質雕像,再到那些可能與棺槨配套的靈柩,都是美國聯邦移民海關執法局查獲的。隨行探員解釋説,我的考古學家同行已經將那口棺槨上的銘文做了翻譯,具體年代可追溯到後期埃及和托勒密王朝時期之間,或許就是阿爾塔薛西斯三世率軍進攻特比拉時期。
這些棺槨上的銘文讓我想起了一個人的名字:謝塞普–阿蒙–泰耶斯–赫裏特女士(Shesep-Amun-Tayes-Herit)。美國聯邦移民海關執法局知道她的棺槨是被非法走私到美國的,對出土地點卻一無所知。我建議用她來做一個測試案例,看看我們花大量時間搭建的衞星影像數據庫是否有幫助。當年夏天,她就會被運回埃及,所以這項研究值得一試。

謝塞普–阿蒙–泰耶斯–赫裏特的棺槨,可能出土自阿布西爾馬利克遺址(資料來源:麗貝卡·黑爾,美國國家地理創意機構)
窮家難捨
假設這位女士來自某一墓區,而不是崖墓,那麼衞星有可能—只是説有可能—記錄下這一特定的盜掘事件。要知道,早在2500年前,開鑿于山崖或岩層中的墓葬是非常普遍的,而這類墓葬很難被衞星捕捉,所以還是先讓我們祈禱吧。
我首先從數據庫已收錄的279處被盜掘的遺址查起,並依據先前的發掘和調查數據,列出每一處遺址所屬的年代。探員傳來棺槨的放射性碳測年結果,進一步確認所屬年代介於後期埃及和托勒密王朝時期之間,即公元前664—前30年。第一步,在這279處被盜掘的遺址中,看是否存在年代相符的墓區。僅此一步,就將符合條件的遺址數量驟減至33處。
當我轉頭望向那名女士的臉龐時,她的眼睛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她眼角處有微小的閃光點,再仔細看,原來是遺留下來的細碎沙粒。謝天謝地,還好盜墓賊的木料清理功夫太差。沙粒的存在意味着出土地為沙漠地帶,而極佳的保存狀態也表明這個地方較為乾燥。
第二步,依照沙漠邊緣存在墓區的標準,進一步縮減遺址的範圍。此外,我們還設定了另外一個條件,即遺址靠近市中心,因為我們的這位女士代表了最精湛的藝術形式,是由達·芬奇式的高級作坊打造的。在古代,這樣的作坊通常都在大城市。
如此篩選下來,符合上述條件的遺址只有10處。幸運的是,我們掌握了這位女士被運抵美國本土的時間。一般來説,一件文物從出土到走私到國外市場,需要一年乃至更長時間。該批文物是在2009年9月到11月查獲的,因而盜掘活動可能發生在2005年至2009年年初。
衞星影像記錄的遺址遭盜掘事件大都是在2009年及以後,也就是在全球經濟衰退之後發生的。在我們篩選出來的10處遺址中,有5處是在2009年之前被盜掘的。其中,只有一處遺址在2005年至2009年出現了數以千計的盜洞,而它就是阿布西爾馬利克遺址。
在古埃及,家族中往往沿用同樣的名字,而謝塞普–阿蒙–泰耶斯–赫裏特並不是一個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名字。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坦帕藝術博物館,恰好有一口棺槨的主人,跟我們這位女士同名,所屬時期也對得上。這對我們來説無疑是一條關鍵線索。博物館裏的那口木製棺槨同樣色彩豔麗,但藝術性不是很高,出土地點為阿布西爾馬利克遺址。一切似乎太過巧合了。此外,我還發現了一尊來自“薩卡拉地區”的書記員雕塑,而該地區也是阿布西爾馬利克遺址的所在地。這尊雕塑上面刻着謝塞普–阿蒙–泰耶斯–赫裏特,是書記員的母親的名字。
由於長期遭受盜掘活動侵害,阿布西爾馬利克遺址如今已經變得坑坑窪窪,看起來就跟月球表面一樣(見圖11—3)。遺址處可見成千上萬的新舊盜洞,而時至今日,各種盜掘活動依然猖獗。人類遺存散落各地,就和秋天樹下的落葉一樣。有同行曾經拜訪該處遺址,回來後看得出大為震驚。綜合各方面證據來看,這處遺址極有可能就是這位女士的故鄉所在地。

圖11—3 埃及阿布西爾馬利克遺址。注意看該處遺址數以千計的盜洞(資料來源:谷歌地球)
大約2500年前,她長眠於當地的一個豪華墓區,而那時的尼羅河沿岸坐落着一座繁華的城市。從棺槨上描述的頭銜——“阿蒙神的吟唱者”來看,她是在神廟工作的,而這也是一般女性公民所能擔任的最高的職位之一。她的住所很可能是一棟多層樓房,配置相當奢華,而且她深受家人的愛重。他們費心費力,聘請城中的頂級匠師為她打造棺槨並繪製圖案,而在她的隨葬品中,自然也少不了各種雕塑、隨葬俑、珠寶以及所有能想到的華麗服飾。這位女士的家人付給祭司豐厚的報酬,供奉祭拜她。這個家族可能連續幾代人都是這麼做的。如今,她的名字已經被世人銘記。雖然盜墓賊偷走了她的隨葬品,破壞了她的遺骸,但諷刺的是,在他們的“幫助”下,她被載入史冊,並實現了永世不朽的夢想。
杯水車薪
找到棺槨可能的出土地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一旦考古學家掌握了遭盜掘遺址的數據,他們就可以列出可能遭劫掠的物品的清單,而這樣的清單將有助於斬斷從盜墓賊到市場的整個非法鏈條。
但更關鍵的是,要了解整個黑市交易背後的機制。貨幣貶值、失業、遊客數量的減少和物價的上漲,都會引發遺址遭盜掘事件。目前來看,大型考古遺址的安保措施已經大大提升,但就一些偏遠地區的遺址而言,盜掘活動可能會愈演愈烈,因而這些遺址亟須加強保護。面對21世紀最嚴重的“隱患”之一,我們有必要採取創新的解決方案。隱患,異常危險的隱患。
部分專家表示,在利比亞、伊拉克和敍利亞等地,盜掘活動與恐怖主義有着根深蒂固的聯繫。在其他一些地方,盜掘活動跟毒品交易和人口販賣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這些犯罪網絡還有待進一步調查研究,但它們之間很可能是聯通的。
據傳,販賣古物的利潤非常可觀,傳言中的金額從一年數百萬美元到數十億美元不等。同其他任何黑市交易一樣,具體的利潤規模無從得知。目前來看,我們需要採取更多的措施,斬斷非法鏈條,同時弄清楚古物是如何從埃及等地流入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各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的憤慨聲明很容易被忽視。問題的解決需要全球行動,而唯有如此,才能粉碎古物的非法交易網絡。
我們不能説所有的盜墓賊都是恐怖分子。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們需要弄清楚的是,哪個階層的人會從盜掘活動中獲利,以及一般的盜墓賊處於何種生活狀態。這些都有助於我們釐清危機的真正本質。
在埃及的盜墓圈子,據説村民會集體瓜分盜掘古物所得的小額收益。當地的盜墓賊多半是孩子,獲取酬勞的方式有二:一是按照盜掘的文物計費,二是按照夜間工時計費,風險當然自擔。隧道坍塌。在黑夜中,開放式墓井無異於陷阱。有時候,在墓井深處作業的盜墓賊會被安保人員抓個正着,即便這些安保人員沒有配備武器,但身邊有的是大石頭。一名安保人員曾經跟我説:“盜墓賊是給自己挖墓。我輕輕鬆鬆就送他們一程。”這種憎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遺址的安保人員一般都是成年男子或家中的父親,經常遭到有組織的盜墓團伙的槍擊,甚至被射殺。
盜墓是一種完全不要命的犯罪活動。當地人可能會把盜掘的古物賣給犯罪分子,但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養家餬口。據我聽到的描述,即便是那些把盜墓當成副業的人,往往也是為了能讓一大家子人吃上飯、過上更好的生活,或者是為手術籌集資金。雖然談不上完全絕望,但這也絕不是那種所謂的第一世界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抱持同理心去看待這場危機,那麼我們還是有機會拿出有效的解決方案的。
富人也會參與盜掘活動或充當古物的掮客,而這才是真正能發大財的環節。職業犯罪分子也會參與盜掘活動,但這並不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古物非法交易、軍火走私和強迫賣淫等地下網絡,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即通過買賣來獲取利潤。
賺大錢的是最後的賣家,交易可能通過大型拍賣機構或私人掮客,儘管我們無從得知在這個轉手過程中古物的價格被抬高了多少。讓泥鏟鏟入沙土的真正的背後力量,是西方和遠東的買家——從在網絡上競拍標價100美元的聖甲蟲雕飾的小買家,到斥資數百萬美元在高端拍賣會上競拍雕塑的大買家,無一不是幕後推手。沒錯,推動市場的就是他們。
如果沒有需求,那麼盜掘活動就不會出現今天這種情況。這才是我們首先需要對抗的。同理,對瀕危動物的身體部位以及對外來寵物的文化需求,也必須通過全面的再教育和嚴厲的懲戒措施來應對和解決,否則無數的物種就會永遠消失。無論是野生動物的交易還是古物的交易,都不能把責任轉嫁到鏈條的下游,鏈條頂端的消費者才是罪魁禍首。即便這意味着要審視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們也不應退縮。
解決方案……或許吧
就遺址保護而言,衞星影像只是起了輔助地面行動的作用。在當地推動培訓和教育計劃至關重要,而且這些計劃在遺址保護方面已經產生了巨大影響。目前,全球範圍內正在開展的培訓和教育計劃有數百項之多。它們已經跳出了很多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兜售的所謂窮情影像的窠臼,成為真正幫助當地人從他們的文化遺產中尋找合法的可持續的有經濟價值的計劃。
與考古遺址周邊社區的關鍵利益相關方建立合作關係,進而瞭解他們的需求和技能,是開展遺址保護的強有力的方式之一。當那些城鎮和村莊的居民看到自己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時,他們就會知道他們的未來是與過去關聯的。此外,與年輕人保持接觸也非常重要。我們可以向他們展示,他們是當地文化寶藏的真正守護者,而且發展旅遊業,可以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機會。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在約旦,考古學家莫拉格·克塞爾與佩特拉國家信託基金合作,攜手開展佩特拉少年遊騎兵和佩特拉青年參與計劃等項目。她幫助創建了一個教育模塊,為100多名年齡為12~17歲的女孩提供培訓,着重講述考古、博物館和保護遺址的重要性。之後,參加者又被要求去採訪佩特拉的遊客以及當地的攤主,問一些與古物銷售相關的問題。這類工作坊為年輕人賦能,讓她們成為保護當地歷史的利益相關方。克塞爾還率先使用無人機對約旦境內遺址遭盜掘的情況進行測繪,並將其作為她的“跟着陶罐走”計劃的一部分。
在我心目中,她是當今在中東工作的最酷的女性之一。只要當地人參與進來,那麼全世界的情況都會大有改善。以盧克索為例。相比埃及其他地區,從衞星影像上看,這個地區可以説基本沒有發生盜掘遺址活動。零星的盜掘活動當然還是存在的,但要知道,盧克索有數百處遺址,鑑於如此規模的考古景觀,這已經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了。在盧克索的經濟活動中,近乎百分之百都與前來參觀古代奇蹟的遊客有關。
由於2011年埃及政局出現動盪,很多遊客放棄了出行計劃,進而導致盧克索地區的人陷入困頓之中。這不僅包括導遊和酒店員工,還包括那些為在酒店廚房工作的表親供應西紅柿等食材的人。即便如此,當地依然高度重視古埃及文化遺產的價值。請親自來盧克索走一趟:酒店便宜,食物美味,人們熱情好客,更重要的是,你將為打擊盜掘遺址活動貢獻自己的力量。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遺址都能變成旅遊景點。發展觀光旅遊業不僅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和時間,還需要有足夠的遊客。但是,這個世界上有待發掘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只有“死硬派”遊客才會去參觀那些小型遺址或偏僻冷門的遺址。
儘管如此,解決方案還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為考古遺址周邊的人提供新的經濟發展和教育機會。通過舉辦技能培訓活動,鼓勵當地人製作仿古代風格的手工藝品,然後通過大城市的合作社或在線平台銷售,當然也可以拿到當地集市上售賣。從事遺址考察工作的考古學家也可以參與當地的社區活動。在考古發掘季,我的很多同行都會邀請當地學校師生和社區居民參觀遺址,併為他們提供相關解説。
有時候我們的工作會在無意間產生積極效果。在特比拉台形遺址,附近村莊一個名叫阿比拉的少女用籃子幫我們運送發掘出來的碎石。她對考古工作非常感興趣,而且她的英語水平遠勝我們的阿拉伯語水平。在她的高中考試成績出來的時候,她的叔叔買了一整箱汽水請我們團隊喝:她考了全班第一名。我們所有人都為她感到驕傲。阿比拉後來考取了開羅大學,專業是考古學。她後來告訴我,之所以選擇考古學,就是因為受到了我們這些女考古學家的啓發和激勵。
就遺址保護而言,如果有一個全球性的可以實時追蹤的遺址數據庫,任何遺址只要受到盜掘、土地開發或氣候變化的威脅,就會成為全球熱點,那會怎麼樣?在影片《盟軍奪寶隊》中,那些勇敢的男男女女在二戰期間的歐洲,從納粹手中奪回了眾多無價之寶。想象一下21世紀也存在這樣的奪寶隊。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奪寶隊成員:一支覆蓋全球、涵蓋不同年齡段的數百萬人的隊伍,羣策羣力,分析高分辨率衞星影像,尋找遺址,識別盜掘活動,並同政府和考古學家分享相關數據。這樣的成效將是何等驚人。
那麼,現在我們怎樣才能動員如此龐大的力量呢?
(本文節選自薩拉·帕卡克所著《我從太空考古》,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