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凱、格雷厄姆·艾利森、李世默:中美“大碰撞”如何化危為機
guancha
編者按:
近些年來,“修昔底德陷阱”成為探討中美關係時的一個常見術語,其對應的現實是中美雙邊關係複雜多變,尤其是美方,在競爭的同時期待兩國“負責任地管控競爭”,既要築起“小院高牆”,又不得不與中國在眾多領域依存合作,體現在行為上,如一邊擴大制裁名單,一邊安排高級官員訪華。
中美互動如何擺脱一些思維困境?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又將給中美關係增添哪些不確定性?近日,中國前駐美大使崔天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北京對話”聯合創始人李世默,在北京進行了一場有關中美關係的深度對話。

李世默:中美兩國正在進行非常激烈且全方位的競爭。格雷厄姆,你創造了一個人人都在使用的術語——“修昔底德陷阱”,習近平主席在10月會見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也用了這個詞。我們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嗎?還是在擺脱“修昔底德陷阱”?
格雷厄姆·艾利森:謝謝你。我於2012年在《金融時報》上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後,很多人引用,但習近平是第一個引用這一概念的大國領導人。他認為中美之間爆發戰爭並非必然,我非常同意。實際上,我們有必要擺脱“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一名中方官員向我解釋的,習近平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因為中國知道,舊的大國關係模式經常演變為我所描述的競爭關係。
在過去500年間,我們看到了16次“修昔底德陷阱”,其中12次以戰爭告終,4次沒有爆發戰爭。因此,戰爭是可避免的,但總體風險也很高。我們現在重視中美關係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風險,是因為歷史提醒我們,這種挑戰有嚴峻性。因此,如果一切照舊,外交照舊,就會導致歷史重現;如果中美真的發生戰爭,對兩國來説都將是災難性的。我們必須做得更多且更好。
李世默:如果修昔底德看到中美關係現狀,且願意幫助我們避免戰爭,他會給美國和中國分別提出什麼建議?
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會認為,現在發生的一切都符合劇本,中國的表現符合傳統新興大國的樣子,美國的表現符合傳統守成強國的樣子,雙方正在加速朝着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衝突的方向發展。我曾於2017年在《註定一戰》這本書中寫道,中美關係可能“沒有最糟只有更糟”;當然,這是假設雙邊關係按照當前軌跡繼續發展。
有趣的是,修昔底德提到,他曾試圖分析雅典和斯巴達競爭的過程,以便了解雙方所犯的錯誤,能夠讓未來的政治家做得更好。
面對中美矛盾,我認為習近平和拜登都一直在努力解決問題,但這充滿複雜性。中美一方面經歷着歷史上最激烈的競爭,但同時又在很多方面存在利益關係,需要互相合作才能確保自己的生存。這兩個方面將中美關係朝着相反的方向拉拽。因此,對於具有戰略想象力的領導人來説,如何為這一矛盾關係制定管理框架是具有挑戰性的。這正是習近平和拜登在舊金山試圖做的事情,我認為他們的第一步做得很好。
崔天凱:如果修昔底德今天還活着,他應該不希望看到人類沒有吸取歷史教訓,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樣的錯誤。不過,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例如,兩國元首在巴厘島和舊金山舉行了建設性的會晤,他們彼此保持着密切的溝通。此外,高級官員們也在相互溝通。也許我們仍然沒有達成很多共識,但雙方都越來越願意更多瞭解對方,試圖更好地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希望我們能繼續向前推進。我始終認為,擺脱或避開“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辦法就是走出一條新路。
李世默:多年來,我一直往返於中美兩國之間。前幾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在國會上説,美國與中國正在進行全社會的競爭,我當時感到震驚。但經過最近幾年,我認為他説的對,事實就是如此,這一思維也蔓延到了中國。
當下,即使是過去只追求利潤而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現在也無時無刻不在考慮中美競爭。我們如何擺脱這一狀況?光是通過兩國領導人對話,是無法解決困境的。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再次強調中美關係存在無法迴避的複雜性。兩國為了各自的生存都必須避免一場可能演變成核戰爭的大戰。我們能否生存下去,取決於雙方的合作,這應該是非常強大的合作推動力。當然,還有氣候問題,我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生物圈中,任何一個國家的温室氣體排放都可能使彼此無法居住。我們的金融體系、經濟體系關係很緊密,民間來往也很多。因此,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第26屆氣候大會上,年輕的氣候活動家參加示威遊行。(圖/聯合國新聞)
接下來的問題是,兩國政府能否找到一種可以將合作具體化的戰略思維:一方面,中美之間存在高度的不信任和甚至敵對性認知;另一方面,中國的貢獻也很突出,如去年太陽能電池板裝機量超過美國25年來的裝機總量,從而大幅減少温室氣體排放,這創造了更適合生存的氣候環境,我認為這是件好事。因此,我們需要妥善處理這一複雜性。
李世默:不幸的是,最壞的結局有時會發生,雙方同歸於盡。你提出的氣候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生產最便宜的太陽能設備和電動汽車,然而歐美的態度似乎是“我們寧可不解決氣候問題,也不買中國產品”。
格雷厄姆·艾利森:(前)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會優先考慮氣候問題,但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會優先考慮美國生產商的利益,因為他們的成員可能面臨失業。美國政治如何平衡這兩方面的考慮,取決於這一行業的政治重要性,以及工會的相對重要性。
過去30年間,兩國產業對比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前中國製造業微乎其微,現在變成了所有大規模製造產品的第一生產國。美國正在經歷較為痛苦的調整,尤其是這一調整對鄉鎮造成巨大影響。
崔天凱:我看到,美國政府嘴上説的跟實際行動之間存在很大矛盾。有時我真的很困惑,不知道哪一邊才是真實的。
例如,我們都同意應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展合作,因為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但與此同時,這麼多家中國公司受到美國製裁,大概有1500家左右,其中很多是從事綠色經濟的公司。美方這樣做,導致新技術、新產品很可能被放到所謂的“小院高牆”裏。但是,應對氣候變化,僅靠發表政策聲明是不夠的,必須讓整個社會攜起手來,要有企業界的參與。然而,中國許多大公司都受到制裁,它們怎麼可能參與到這一合作中來呢?
格雷厄姆·艾利森:目前在美國安裝的太陽能電池板,有75%是中國製造的。這是因為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質量更好,成本也更低。然而,我認為新能源車的問題尤為複雜,因為汽車行業是美國人較為看重的,並且,這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利益相關,而它是民主黨政治支柱之一。
崔天凱:我認為你説的沒錯,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另一層面。雖然應對氣候變化、產業升級,推動綠色經濟是為了全球所有人的整體利益,但是,一些人、一些羣體所付出的代價很可能相對更高。我們必須更公平地分擔成本和分享收益。

2023年,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罷工(圖/美國白宮)
格雷厄姆·艾利森:有一次,我和你談到這個問題,你指出,在自由貿易體系下,各方都能買到更廉價、優質的產品,這對任何消費者都是好的。但對某些製造羣體而言,不是這樣。比如俄亥俄州的鋼鐵工人,他們在國際鋼鐵市場落伍了,只能以不可持續的低價生產鋼鐵,可能無法參與競爭。
我認為,貿易在全球範圍內如此迅速和廣泛地拓展是一件好事。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該預料到,利益受損的羣體會產生更大的反彈。因此,在如何對他們進行補償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想象力。
崔天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總是強調,我們不應該把一切都寄託於市場。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之一就是共同富裕、共享繁榮。我們密切關注所有潛在負面影響。但是,我們仍然不應該被“中國恐懼症”所誤導。當美國的一些高級官員説,不應該讓中國的電動汽車出現在美國街道上時,令我很震驚。她還聲稱中國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把全部300萬輛電動汽車同時熄火,好像“瞬息全宇宙”。
我沒想到高級別官員會説出這樣的蠢話。希望他們不要變得更荒唐。我有點擔心,有一天他們會警告人們不要去美國的中餐館,聲稱每個餃子裏都可能有芯片,它們會監視每個美國人。
格雷厄姆·艾利森:中餐是我的最愛,那我全身都有芯片咯。
崔天凱:希望人們不會如此瘋狂。
李世默:如果我們能做出這麼高級的芯片就好了。
崔天凱:如果中國真能做出這麼高級的芯片,倒是可以有更好的用途,而不會用來去監控誰。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們之前討論過封禁Tiktok。
李世默:這次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的優勢通過了相關法案,參議院中只需要60票通過後,美國總統就會簽署。這對美國意味着什麼?
格雷厄姆·艾利森:毫無疑問,修昔底德式競爭會顯著影響人們的心理。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並不少見:我曾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名,現在你卻能跟我平視,這讓我很不舒服,我會認為你可能是通過不公平地利用我才實現成功的,然後我就變得更加多疑、更加敵對,甚至妄想。因此,我認為這是雙邊關係的一大風險,尤其是在美方。
我認為,Tiktok被禁的可能性大約為60%,但還不能確定,因為法案在參議院進展緩慢,而且涉及很多利益衝突。Tiktok的美國用户已達1.7億人,包括拜登競選團隊。
李世默:去年底以來,雙邊關係似乎出現了一些穩定的跡象,但拜登幾個月後可能就會下台。我們該如何繼續推進雙邊關係呢?
格雷厄姆·艾利森:從商業視角來看,民主選舉制度的一個缺陷是,每四年就會安排一次惡意收購。當某一企業面臨惡意收購時,顯然會佔據該公司的大部分注意力,並導致相當大的混亂;當然,這也是政治更新過程的一部分。
當人們與拜登政府打交道時,不得不考慮:這個政府明年1月份還會在嗎?人們會對美方提出的任何交易條件打折扣,他們會考慮潛在的“第二選擇”。以烏克蘭戰爭為例,對普京來説,如果特朗普有50%的勝選機會,普京此刻為什麼要接受妥協條件呢?特朗普可是聲稱將在一天內解決戰爭,拋棄烏克蘭的。所以我認為這是美國的一個弱點,卻無法避免。
李世默:在美國政治更加兩極分化的當下,惡意收購可是真的“惡意十足”。根據目前的數據,特朗普獲勝的幾率高於50%,如果今天舉行大選,他必勝無疑。那麼中國應如何應對?我們要像普京一樣等嗎?

特朗普(資料圖/新華網)
崔天凱:我認為試圖預測美國大選結果是有很大風險的。平心而論,我認為如果拜登再次當選,美方政策的可預測性會更高一些。如果特朗普歸來,可預測性就會降低。但我不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會有根本性、實質性的改變。無論誰當選,美國或許都會維持當前的方向,或許直到撞到南牆,他們才會改變自己的想法。
我告訴我的一些美國朋友,我們已經準備好繼續“與狼共舞”,但不會按別人的節奏起舞。
李世默:如果特朗普當選為總統,我認為我們在歐洲的外交空間會大一些,因為歐洲會對美國失去希望,將不得不尋找其他的合作和貿易伙伴。
格雷厄姆·艾利森:從歷史上看,無論美國局勢看起來多麼混亂,它都有自我復原和革新的的能力,美國有這樣的基因。我認為特朗普的一個優點是,不會輕易發動戰爭,他行為上比喊出的口號要謹慎得多。
李世默:他應該是多年來第一位從未發動戰爭的美國總統。
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對此感到非常自豪,競選期間經常強調此事。
李世默:我認為,如果拜登連任,對中國的一個好處是,拜登試圖維持美國霸權,需要同時關注多處發生的事情,無法集中精力對付我們。美國正參與兩場代理戰爭,一場是與俄羅斯的戰爭,另一場是在中東的戰爭,還有可能在某處爆發另一場戰爭。特朗普不會關心這些,特朗普只會關注中國。美國是否捉襟見肘?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們之前談到,仍然有一些美國人存有幻想,認為世界是單極的。這完全不符合事實,當今世界是多極的。世界上有很多力量中心,美國、中國、歐洲、俄羅斯、伊朗等等。這些國家可以獨立行動,無需徵求第三方許可,也不用擔心遭到懲罰。如果土耳其想在戰爭期間與俄羅斯做生意,它就能這麼做。
美國人的習慣認知是,我們統治世界。現在他們感到沮喪。他們要適應這種情形,看清世界實際的格局。顯然,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利益,對世界多國都做出了承諾。如果把烏克蘭當作主要關注點,那麼美國就很難同時關注中東。因此,我認為美國必須調整其在不同地區的利益優先級。
李世默:崔大使,中國在這些衝突中的戰略考慮是什麼?
崔天凱:中國的外交政策確實長期恪守一定的原則。我們總是強調要尊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句話的含義其實很清楚,不論出於什麼目的,我們都不贊成使用武力。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認為這是一場正在上演的悲劇,而且情況只會變得更糟。大家可以看到,拜登總統對這種情況越來越憤怒。參議員舒默評論説,只要內塔尼亞胡還在,這個問題就無解。我希望他能下台,只有這樣,以色列政府才能代表以色列的中間派,以色列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是理智的。
現場提問: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否會發生轉變,允許中國對國際衝突保持中立態度,以實現大部分美國人民通過兩國合作獲取利益的目標?
格雷厄姆·艾利森:中美關係一方面是激烈競爭,另一方面是密切合作,目前沒有非常清晰的框架,需要根據細節進行各種調試。
在俄烏衝突問題上,如果中美能合作,能找到一種結束戰爭的方法。自2022年11月以來,烏克蘭戰局基本上陷入僵局,沿着實際控制線,雙方的推進都不超過50英里。這一情形很像一戰期間的西線戰況,來來回回打,卻無濟於事。這一情形也像是朝鮮半島當年的戰爭,交戰雙方几年間被困在三八線附近,直到人們決定這是一個合適的停戰邊界。
崔天凱:關於烏克蘭戰爭,老實説,如果交戰各方不想止戰,中國也無法阻止他們。如果交戰各方不想打仗,中國也無法觸發戰爭。中國能做的是有限的。當然,我們會盡力做到最好,我們的李輝特使前不久赴歐洲斡旋,剛剛回國。
有人説,也許俄烏之間也可以建立類似朝鮮半島的軍事緩衝區。我曾告訴我的一些歐洲朋友,也許你認為北約的擴張消除了所謂的俄羅斯戰略空間,但實際上,你們是在消除自己的緩衝地帶,你們在邊界上直面的就是俄羅斯核武庫。這讓歐洲更安全還是更不安全?很難説。也許我們可以在俄烏之間設立非軍事區,在那裏部署聯合國維和部隊,也可以由中國將領擔任指揮官。
李世默:對,我們應該努力這麼做。現在我看到很多分析説,俄烏衝突將不再是一個僵局,俄羅斯越來越靠近勝利。分析預測,如果繼續按照這個趨勢下去,將會有40%的烏克蘭人變成俄羅斯人。
格雷厄姆·艾利森:這是有可能的,勢頭有所改變。哈佛有一個叫做“俄羅斯問題(Russia Matters)”的項目網站,我們每週都會發布一份報告,記錄戰局變化情況。上週,俄羅斯控制的領土增加了兩平方英里。變化並不大,速度也不快,但俄羅斯有可能取得重大進展。如今,俄羅斯控制着烏克蘭20%的領土,我認為,如果兩國能達成類似於朝鮮半島的長期停戰協議,會拯救很多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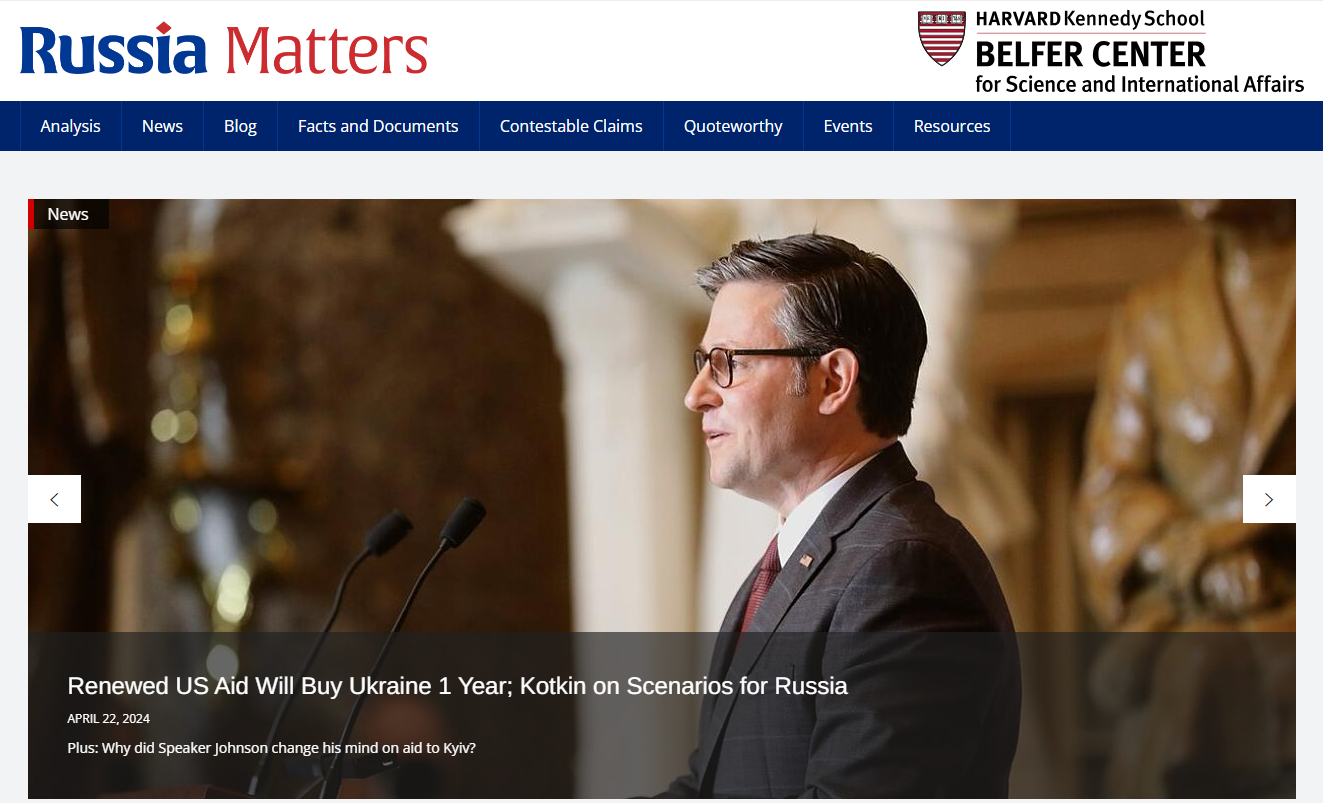
“俄羅斯問題(Russia Matters)”網站首頁截圖
現場提問:中美新冷戰是否已經打響?特朗普若當選是否會導致衝突升級?中國與美國打交道過程中,如何面對美國的種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問題?
崔天凱: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你經常能感覺到美國政策中潛在的種族主義因素,但又不是明目張膽的,至少一部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甚至知識分子有這樣的偏見,但不是大多數人。有很多美國人也反對這種做法。我們必須公平客觀。與此同時,也必須認識到,考慮到不同的國家利益,每個人都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偏見。
中華文化不贊成偏見。不僅對美國、中國,對整個世界都應如此。歐洲人明面上提倡文化多樣性,但實際上他們的偏見更為悠久。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明必須學會如何真正和平共處、共同繁榮,如何共同應對全球問題,如何為人類的生存共同努力,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格雷厄姆·艾利森:近代,亞洲移民對美國做出巨大貢獻;然而,隨着美國人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敵意,一些醜陋的種族主義浮現出來了。特朗普總統甚至羞辱過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的妻子趙小蘭,她是一位華裔美國人。與此同時,英偉達、微軟等美國科技公司的領導者幾乎都來自亞洲。我認為,種族主義是個問題,但是在可控範圍內。
中美之間是一場新冷戰嗎?不是。中國並不尋求將其政黨政治模式輸出到其他國家。基辛格對此有一句名言,他説,中美都有自我優越感,兩國人民都認為各自文明高人一等。美國人對美國文化、政府和社會有着巨大的優越感,認為只要把人們從舊環境中解放出來,他們就會變得和美國人一樣。就歷史和觀念而言,中國不會派兵佔領其他國,中國不會試圖將自己的政治模式強加給其他國家。
不過,現在的形勢與冷戰有一些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冷戰期間,大家認識到美國和蘇聯都有強大的核武庫,任何攻擊都會成為自殺式行為。這是一種醍醐灌頂的認知。羅納德·里根曾説過,核戰爭是打不贏的,因此永遠不要開打。我認為,中美的核問題、氣候問題,還有兩國緊密聯繫的金融系統也是可以相互毀滅的。因此,我們必須通過合作維護生存空間,這種觀點也能夠緩和競爭性。
崔天凱:我曾提醒過許多美國朋友,在舊冷戰時期,兩場最大的熱戰發生在亞洲,在中美之間展開,分別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所以我們不要輕易談論新冷戰。我們準備好再次面對冷戰這樣的後果了嗎? 一戰後出現了與歐洲原有政體截然不同的蘇聯,中國則誕生了共產黨,中國的歷史從此改寫;二戰之後,世界上出現了聯合國這樣的新的多邊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那時成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發展中國家獲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致力於經濟發展。這些都是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
冷戰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認為中國重返全球舞台是幫助結束冷戰的一個重要因素。1971年10月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是世界走向多極化的轉折點。現在我們處於一個更加多極的世界,如果有人試圖開始一場新的冷戰甚至熱戰,我很確定在這場冷戰或熱戰結束時,很有可能會出現一種全新的全球結構。恕我直言,也許所謂的西方將失去更多的權力,全球南方會進一步崛起,國際舞台上會有更多的聲音,世界結構會更平衡、更理性,也有可能朝着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所以人們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動不動就想搞新冷戰,甚至是新熱戰。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非常同意。去年10月,亨利·基辛格發表了最後一篇文章,我是文章的共同作者,篇名是《人工智能軍備控制之路》,回顧了核時代的歷史。我們能否將核時代的經驗用於分析新科技時代的潛在災難?

亨利·基辛格與格雷厄姆·艾利森合寫的《人工智能軍備控制之路》,《外交事務》2023年10月13日發表
我們認為,如果你能將以下數字與其代表的含義相對應,你就能大致瞭解過去80年間國際安全的全貌。這三個數字分別是78、78和9。
第一個78是指,有多少年沒有發生過大國戰爭?自1945年以來,已過了78年。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長的和平。未來是否不會再有大國戰爭?並非如此。實際上,和平正面臨更大的壓力,這是由於中美之間存在“修昔底德式”競爭等原因。但這一持久的和平時期之長仍是驚人的。
第二個78是指,如果你在1945年或1950年,給出未來戰爭中不再使用核武器的幾率有多大?你的答案或許是1000:1,甚至是10000:1。自核彈用於廣島和長崎以來,78年過去了。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但這一和平也很脆弱。
我認為,9這個數字相關的問題最不可思議。當下有多少個國家擁有核武器?只有9個,但有90個國家可以造出核武器;高超的治理能力、合作機制阻止了核擴散,尤其是中美之間的合作。
20世紀發生了兩場巨大的戰爭,一戰後僅間隔20年就爆發了二戰。所以,1945年的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得益於國際秩序架構的建立,得益於戰略構想,得益於善意和好運,沒有爆發新的大戰。但絕非“一勞永逸”,和平是相當脆弱的。
崔天凱:我同意艾利森教授所言,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我們能享受全球和平是非常幸運的。問題在於,有些人可能已經忘記了人類當時贏得和平的代價。
格雷厄姆·艾利森:《人工智能軍備控制之路》這篇文章主要是寫給美國人看的。在美國,大多數人認為大國戰爭不會再發生,因此不用擔心,也認為各國不可能使用核武器,甚至認為核武器也已經消失了。我們稱這種現象為美國的歷史健忘症。美國所有上星的軍官中,沒有人見證過大國戰爭。
崔天凱:亨利·基辛格博士一次又一次地告誡我們,100年前沒有人策劃過世界大戰,這是一步一步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