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軍:誰來為“白左”的偽善買單?
guancha
【文/吳軍】
有能力去設計並實現一個社會的是少數人,但並不意味着其他人不想管理他人的生活。很多人自己的事情沒有管好,卻熱衷於規劃別人的生活。他們規劃和干涉他人生活的藉口是所謂“很多人很可憐,我們要幫助他們”,這些人的典型代表就是今天西方的“白左”。
“白左”是《牛津詞典》中為數不多的由當代中國人發明的新詞。根據英語詞典的定義,“白左”通常是指極端自由派(或者進步主義者),他們有三個特徵:居高臨下、虛偽和天真。“白左”不一定都是白人,也包括美國的很多亞裔。“白左”強調政治正確性,只關心大而空、無法落實的事,而不是以現實的方式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白左”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中帶有一定的貶義,但是在西方,“白左”並不覺得這個稱呼是做錯了什麼情,相反,他們認為自己在動物保護、環境保護、平權、膚色平等、LGBT、女權主義、素食主義和對待非法移民等方面的態度是完全正確的。他們批評中國的民族主義和西方的保守主義。

極端“環保組織”成員為了宣傳其主張向梵高名畫《向日葵》潑番茄罐頭
在中國,“白左”一詞的含義略有不同。它帶有貶義,令人反感,最令人反感的地方是他們氾濫的同情心、虛偽的人道和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優越感。
照理説,有同情心是件好事,那麼什麼是同情心氾濫呢?它又是如何侵害社會的呢?我們不妨來看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美國左派對罪犯濫用同情心的例子。
美國很多左派認為,罪犯犯罪是因為對他們不夠好所導致的,因此要對他們格外照顧,要寬容他們的罪行,要善待他們的生活。左派的候選人和他們的支持者主張取消最低刑期,大量釋放罪犯;監獄罪犯種族比例要協調,非洲裔和拉美裔比例不能過高,因此要更多地釋放黑人和拉美裔罪犯;徹底廢除死刑,消滅死刑對犯罪的威懾力;取消罪犯的保釋金,罪犯可以在出庭之前擁有自由。
此外,他們還有一項主張是動搖文明社會根基的,那就是削減警察經費。拜登親口承認,他支持把警察經費“分流”到其他機構。這些左派人士主張,對於輕罪就不要處罰了,比如在加州950美元以下的搶劫不入罪;對於重罪,比如強姦罪,也要從輕發落,比如在美國強姦罪通常量刑不超過三年。等到那些被定了重罪的犯人開始服刑後,這些左派人士又主張要改善監獄環境,讓罪犯更舒適;罪犯出獄後沒有住處,政府還要提供免費住房。
由於左派人士濫用同情心,導致給一個嫌疑人定罪成本變得極高,比如要對一樁謀殺案定罪,特別是定死罪,沒有上百萬美元的訴訟成本是下不來的。即便定了罪,處置一個罪犯的成本也是極高的。比如,2017年3月加州立法分析師辦公室公佈了上一年(2016年)看押刑事犯人費用的報告,這份報告經媒體報道後引起公眾譁然,因為每年看押一個犯人的費用居然高達70812美元,而當年上哈佛大學一年的學雜費加上食宿費也就是63025美元。
因此,媒體嘲笑道,還不如讓那些罪犯去上哈佛,反而更省錢。為什麼美國看押犯人的成本如此之高呢?其實監獄設施費用、伙食費和改造費(讓他們學點技能)很低,高就高在看守人的工資和醫療費用上,每人每年的醫療費用高達21582美元,是當年美國人均醫療費用(10241美元)的兩倍。
不難想象,這樣的司法制度破壞了社會的法律和秩序,讓法律對犯罪沒有太大的威懾,從而導致美國的犯罪率極高。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給出的數據,美國的重罪(謀殺、入室搶劫和強姦等)犯罪率大約是日本的20倍,是韓國的3倍。
上述現象不僅出現在美國,在歐盟大部分國家也是如此。比如,歐盟中最大的兩個國家——德國和法國,前者重罪率接近美國,後者甚至超過美國。如果把聯合國給出的各國犯罪率和各國人均GDP做對比,全世界總體趨勢是人均GDP越高,犯罪率越低。但是深受“左傾”思想影響的美、德、法等國是例外,它們的人均GDP明顯高於其他大部分國家,整體社會發展水平應該更高才對,但是犯罪率卻相對高很多。
第二個是歐洲非法移民的例子。歐洲舊大陸的國家,在歷史上就不是移民國家,這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新大陸的國家不同。可以講,前者毫無處理移民問題的經驗可言。在這種情況下,它們通過開放邊界,大量引入非法移民和難民,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移民不是以個體的身份進入歐盟國家的,他們是成批到達的,因此完全沒有意願融入當地社會。對此,歐洲的左翼人士以支持多元文化的名義縱容一些極端宗教的傳播。
相比英語國家,歐洲大陸的國家左翼勢力更為龐大,他們控制着媒體,使得大家幾乎聽不到中間派和右翼的聲音。由於歐洲大陸國家並沒有應對移民問題的經驗,它們對移民問題缺乏深度思考,導致它們的很多做法非常幼稚。由於當地人濫用同情心,新來的移民開始以多元文化的名義摧毀當地原有的宗教和文化。在治安方面,大量非法移民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在經濟方面,他們的福利開支也大大增加了納税人的負擔。

露宿街頭的非法移民羣體(圖片來源:ICphoto)
同情心氾濫的另一個問題是慷他人之慨,剝奪他人的勞動成果。做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使用同情心幫助罪犯或者非法移民,即便是在做好事,也是有成本的。對於任何一個經濟體,這個成本通常都被分攤到所有人的身上。也就是説,張三想做一件事,卻要李四和他共同承擔費用,如果李四不願意,張三就對李四進行道德綁架。有人覺得幫助罪犯或者非法移民,從長遠來看或許對社會有好處,這種想法要麼是天真,要麼是虛偽,當然也可能是一種自欺欺人。歐美國家越來越高的犯罪率説明寬容罪犯並沒有帶來什麼好處,即便是100年後可能有好處,那也是不確定的事情,而當下大家的損失是確定的。在歷史上,所有的邪教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許願遙遠未來虛幻的利益,而讓大家損失當下的利益。
歐美社會濫用同情心的結果,一方面是讓警察對一些移民聚居區或者犯罪率高的地區乾脆撒手不管,從而導致其治安極度惡化,因為管就有種族歧視的風險,於是各類“禁入區”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遍佈歐洲和美國大地。在歐洲很多地區,外來的宗教通過歐洲各國言論自由的便利,反過來要求更多福利,從而壓迫其他族羣,甚至壓制其他族裔的言論。在美國一些地區,比如芝加哥的某些地區,乾脆黑幫化了,也就是説,警察懶得管,黑幫替代了警察,當然,外人也就懶得去了。另一方面,這也導致歐美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加劇了不同族裔之間的對立,甚至國家之間的對立。
接下來再説説虛偽的人道。在經濟領域,“白左”信仰的福利國家,主張讓搭便車的懶人受益,是慷他人之慨,讓他人為此買單。在安置非法移民方面,“白左”一方面表示歡迎為他們建造安置房,另一方面又將這些安置房建在別人的社區。當有人把非法移民送到他們家時,他們卻經常把那些移民趕走。正是覺得自己有同情心和人道主義,很多左派人士自我感覺良好,對不同意他們的政治主張和想法的人口誅筆伐。殊不知,對於弱勢方溺愛式的照顧,有可能最終害了弱勢方。溺愛得越過分,弱勢方越會認為這種溺愛式的照顧是理所應當,然後索要更多的利益。今天,民粹主義之所以能夠形成氣候,和左派長期實行的“逆向壓迫”和“逆向歧視”有很大關係。
在很多中國人看來,西方的“白左”把自己裝扮成聖母,然後毀掉自己的文化,簡直就是又蠢又壞。中國人的這種看法是否有道理,抑或過於偏激呢?如果有道理,那麼為什麼那麼多被他們稱為“白左”的西方人會那麼傻呢?其實這反映出奮鬥的第一代對於富二代想法的不理解,以及富二代自身的傲慢。這裏我們説的富二代不是那些含着金湯匙出生的經濟上的富二代,而是那些被稱為“民主富二代”的人。
什麼是民主富二代呢?任何一個國家,經歷了工業化和現代化,實現了基本自由和經濟上獨立的幾代人,相當於創業奮鬥的一代。他們的後代,可能是子孫輩,也可能是後幾輩,生來就在一個富裕自由的環境中,就是民主富二代。他們完全不瞭解當初他們的祖輩為了爭取個人權利和經濟上的地位所付出的艱辛努力,不懂得珍惜自由,不尊重他人的權利,自我感覺良好,居高臨下地對待他人,濫用他們的同情心。
生活在當下中國社會中的這幾代人,都屬於現代社會的創業者,而與他們生活在同時代的歐美國家的大部分人,都是民主社會或者現代社會的富二代。我們都知道兩代人之間會有代溝,相互難以理解;奮鬥的創業一代和享福的富二代之間自然也有代溝,也難以相互理解。在前者看來,後者愚不可及,自己這一代人吃了多少苦,才有今天安穩的日子,可是下一代放着好日子不過,卻要折騰;而在後者看來,前者不文明,同時,後者還有點少爺脾氣,動不動就用政治正確的大道理教訓人。

當下中國社會的幾代人,都屬於現代社會的創業者
現實情況是,世界上沒有那麼多的可憐人需要大家同情,有些時候對人過分的同情反而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是把自己放在了高高在上的位置去俯視他人。每個人都不是神,不需要濫用同情心。如果一個人真的富有同情心,覺得自己該幫助這個世界,用自己的力氣去做就好,比如安置幾個非法移民在家裏,不用要求社區去給後者什麼幫助。
我在“硅谷來信·第三季”中講,我非常欽佩中世紀的聖徒聖方濟各。今天舊金山(聖弗朗西斯科)這座城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聖方濟各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是用自己的錢財和生命幫助他人。在方濟各生活的年代,人們不關心窮人,方濟各先是把自家的布賣了錢去救助窮人,後來他的父親知道此事之後震怒,把他怒打了一頓後,和他斷絕了關係,當然他也就失去了財產的繼承權。此後,方濟各就開始用行動幫助窮人。他先到修道院做工,修復破舊不堪的小教堂,讓當地人有祈禱的地方。在隨後的20多年裏,他自己過着赤貧的生活,同時盡心盡力幫助窮人和病人,特別是當時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麻風病人。後來他的行為感動了他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他的宗教團體。今天,如果有人真的想當聖徒,就不妨學學聖方濟各,先把自己的財產和一輩子的時間拿出來做善事,不用綁架他人。
當然,有人可能會覺得,我説的“白左”都在西方,在中國沒有這樣的人,但是今天沒有不等於明天沒有。正如我之前所説,今天的中國人還都屬於創業的第一代,但接下來的幾代人就不好説了。事實上,今天很多亞洲移民在美國的第二代,就成為被他們父母稱為“黃白左”的人。根據我的觀察,今天很多在中國的中國人,雖然不同意“白左”的主張,卻採用了與他們相同的做法對待社會問題、對待他人。比如在對待社會問題上,你會發現很多人在談論遙不可及的中東時頭頭是道,卻從來不會把自家門前的水坑填上;他們對國家的宏觀決策有很多看法,對政府的做法指手畫腳,卻不去思考一下如何改進自己單位的產品和服務質量,或者提高銷售業績;在對待他人上,他們常常喜歡代替公權力去伸張正義,甚至一大羣人試圖通過網絡輿情左右司法、左右公共政策,甚至左右選舉。大家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表達意見原本是件好事,但是給予他人、政府機構和司法部門壓力,這就干擾了別人的生活。
上面講的這些人往好裏説,叫作心懷天下,但是對社會發展不會產生什麼好的作用;往壞裏講,就是把自己當成了上帝,對他人、對社會指手畫腳,濫施同情心,破壞社會原本的運行法則。社會自有其發展和運行規律,不需要誰把自己當成上帝去改變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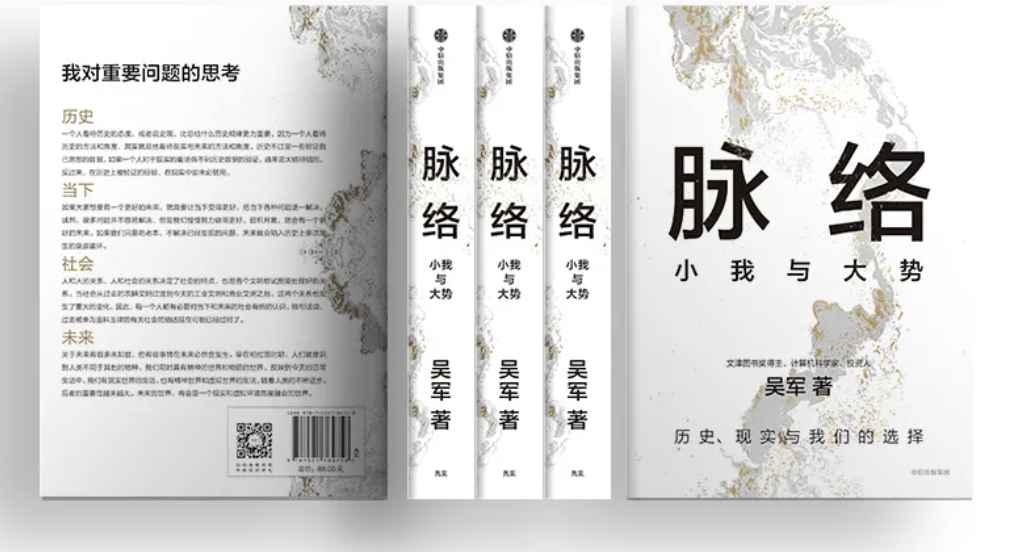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