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is:美國正在法西斯化嗎?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Kris】
中國和美國有很多分歧,但有一點雙方都同意:中美關係將從根本上塑造21世紀。也就是説,這個時代沒有什麼,能比這更重要,影響比這更深遠。所以,要找到合適的相處之道,我們必須弄清,未來的美國將是個怎樣的國家?這個時代之問,沒人知道答案,但我們可以尋找線索。
第一個線索是特朗普遇刺倖存、嘴角帶血振臂高呼的那張照片。我看到的不是新聞學的高光時刻,而是舊制度的垂死掙扎。想象一下這個不可持續的制度:在軍國主義感召下,精英階層不斷外卷,輸出他們最擅長的戰爭,掠奪資源,引入移民,壓低人力成本,導致本國平民階層在內卷中走投無路,國家兩極分化,然後隨着財富越來越集中,上等人不事生產即可尋租獲利,下等人拼命勞動也只能勉強餬口,這時權貴們中出了一個叛徒,他化身平民代言人,通過民粹運動成為領袖,招來精英密謀刺殺,血濺當場。
我説的不是走運的懂王,而是倒黴的凱撒。歷史雖不會重演,但會押韻,此時此刻,恰如兩千年前的彼時彼刻。凱撒死後,羅馬陷入內戰,共和時代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帝國時代。如今既然懂王對死神説出了not today,證明自己天命在身,是不是能省掉中間環節呢?我不是説特朗普要稱帝,那也太離譜了。但你覺得,真沒人有這個想法嗎?
逆行者
有。讓我隆重介紹,最美國的逆行者孟子黴蟲Mencius Moldbug,筆名來的,真名叫Curtis Yarvin,真實身份程序員。雅文的爸爸是外交官,他從小跟着到處跑。這段經歷給了他一個洞察,美國為啥沒有革命?因為美國沒有美國大使館。他12歲回國插班念高二,15歲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天才班,後來進了UC伯克利念計算機博士,但很快就退學當碼農去了,做那種很古早的手機瀏覽器。
沒過幾年,公司被收購,他選擇拿筆錢走人。按硅谷標準來看,錢不算多,但足夠開啓精神追求。恰好當時互聯網剛起步,很多版權過期的舊書,市面上淘不到,卻能在網上讀,於是雅文一頭鑽入故紙堆,自學歷史、政治以及奧派經濟哲學。
他最推崇這麼幾位:哲學家大衞·休謨,用經驗主義質疑人類的理性;作家托馬斯·卡萊爾,英雄史觀的原創者,認為歷史除了為偉人寫傳,啥也不是;歷史學家詹姆斯·弗勞德,批評民主制度,認為羣眾沒有自治能力,統治還得靠精英;經濟學家霍佩,認為君主制的私天下,遠遠好過民主制的公天下。經過這麼一番薰陶,雅文終於龍場悟道。
有一天他突發奇想,決定開宗立派,放在當時的互聯網語境下,就是寫博客。從2007年到2016年,他以孟子黴蟲的筆名,寫了幾百萬字的政論。很多勁爆的緩則內容,比如《何故、何時、何以廢除美國》(Why, when and how to abolish the United States),認為美國應該分裂成許多個類似新加坡的高效城邦,否則就跟微軟一樣大而無當。雅文還有個創新你可能都聽過,他把《黑客帝國》裏的真相道具“紅丸”(red pill),改造成一個反建制的政治概念。它今天廣受歡迎,現在哪個小兄弟想當拳皇,就必須用紅丸逆練白左大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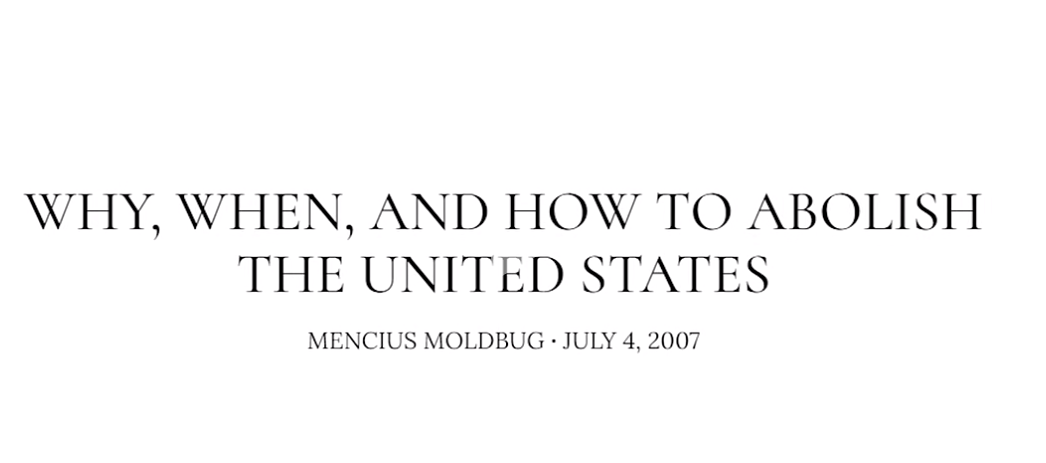
總之,雅文成了個特立獨行的鍵盤俠,他開創的派別叫做新反動派。反什麼動呢?反權力的分散。亞里士多德説過,政府有三種形式,君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每種制度都有健康和墮落的兩種形態,區別不在於本身孰優孰劣,而在於權力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在一個人、幾個人還是千千萬萬人手上。經歷啓蒙運動的現代社會,都推崇民主,認為無數人民當家做主,是天然的善,於是民主成了丘吉爾所説的,相比之下最不壞的制度。
但雅文認為,古代大多數時期是君主制,啓蒙只是歷史的例外,它帶給世界的民主是條死衚衕,因為民主不是實現良政的手段,而是政治的目的本身,所以將不斷自我強化,鼓勵相互牽制的權術,促生更多虛偽欺騙和不作為。在新反動派看來,美國要重新偉大,就必須開歷史倒車。他們強烈反對輝格史觀,即歷史車輪的前進不可阻擋,要求退回到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模式。至於到底什麼是傳統,狩獵採集、種姓制度、男尊女卑、絕對王權、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都可以是,博採眾長嘛。
但總的來説,就是要通過回調參數,回到西方列強如日中天的帝國時代。所以雅文眼裏的歸來的王,絕不能是君主立憲制的吉祥物,不能是伊麗莎白二世,得是伊麗莎白一世,或者拿破崙、凱末爾、羅斯福,名義上可以不稱王稱帝,但必須絕對掌控國家機構,不能再像西方中世紀那樣,被教廷分散稀釋。
當代教士階層在哪裏呢?雅文指向新聞媒體、高等教育、官僚體系,把它們統稱為大教堂(the Cathedral)。大教堂把自由民主進步定為國教後,在意識形態中固步自封,讓社會腐朽墮落,現在是時候讓凱撒的歸凱撒了。雅文認為,國家需要凱撒,就像公司需要CEO。一個企業能做大做強,壓根跟民主無關,既不靠員工表決,也不靠董事會干涉,就得讓CEO不受眼前利益束縛,從企業長期利益出發,負責任地獨裁。大家得學會放手,去相信老闆肯定為公司好。
今天的美國最需要的,就是天降猛男,從民主這部黑神話中,誕生一個自我革命的天命人,親手拆掉分散權力的行政官僚體系,然後廢除民主偽經,迴歸王道真經。有點革命精神的搖滾樂迷可能知道,加州有個樂隊叫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憤怒反抗機器,很好的名字,但雅文認為他們弱爆了。
在他看來,rage的真正涵義應該是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開除所有公務員。快進到現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提出了《2025計劃》(Project 2025),全稱《2025總統過渡計劃》。保守派的總統是誰我們知道,懂王嘛。那過渡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把聯邦僱員統統裁掉,換成忠於MAGA的懂家軍,最終實現三權分立格局朝行政獨尊的方向演化,也就是雅文所憧憬的當代君主制。
由於這個想法過於激進,懂王只能跟它保持距離,但不要忘記,他身邊有一個人叫JD Vance。80後的萬斯是懂王競選的副手,如果懂王勝選,他就是副總統。萬斯出身於典型的窮人家庭,身邊全是酒精、毒品和暴力,他最親的外婆,有次一氣之下,給外公滿身淋油,差點把他給點了。
從當初賤如塵泥,到如今一人之下,萬斯的崛起堪稱奇蹟。但一切奇蹟,歸結下來都是因果關係。究竟是什麼關係,讓加州鍵盤俠雅文跟鐵鏽帶鳳凰男萬斯做了朋友,併成為了他政治哲學上的領路人?請允許我先賣個關子,開啓另一段敍述。
讓資本主義加速!
2010年,上海世博會提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一個隱居上海的英國學者穿梭在魔都大街小巷,最終寫下一本奇書《2010上海世博指南》。裏面不光有展會信息,更多的是文化研究,和對於現代性的思考。他一面懷古傷今,認為倫敦水晶宮和巴黎埃菲爾鐵塔這種世博遺蹟,象徵着西方已經告別了激情年代,一面高度讚賞中國的發展速度。
他認為中國最有希望引領人類告別西方啓蒙運動帶來的、1.0版本的現代性,創造出2.0版本的現代性,因為最好地做到了馬資融合,成為了全世界最偉大的發動機。這種讚賞歸根結底,不來自對中國改善民生的肯定,而來自對速度和運動的抽象崇拜,認為人類的未來屬於科技與狠活。
套用《三體》裏維德的名言,他的主張可以概括為,加速,加速,不擇手段地加速。這位就是加速主義哲學家尼克·蘭德。要理解蘭德,必須回到第一個加速主義者卡爾·馬克思。馬克思嚴厲地批判自由貿易,但他卻支持自由貿易,因為自由貿易能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頂點,加速社會革命,所以在革命的意義上,他支持自由貿易。也就是説他發現資本主義藴含着自我毀滅的種子,與其小修小補,不如催化矛盾,讓它加速為自己掘墓,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二戰之後,資本主義渡過危機,世界革命逐漸進入低潮。但歐洲左翼匯聚了最聰明的那批人,他們得想方設法去解釋,資本主義怎麼還沒崩潰,所以必須另闢蹊徑。其中德勒茲和伽塔利用精神分析取代辯證法,寫出了《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去辨認馬克思在自由貿易中發現的那股破壞因素。
他們將其命名為解轄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簡單來説,就是讓慾望自由流動,脱離規訓,導致社會層級結構失去穩定性。他們認為這是一股原初的,遠遠早於資本主義的革命力量。如果能借助它,人類就不是簡單地否定資本主義,而是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精神分裂,跨越所謂“沒有身體的器官”,去擊碎資本主義的迷牆,進入極具創造性的生產階段。説人話就是,欲使其滅亡,先使其瘋狂。
好,再説回蘭德。90年代,蘭德在英國華威大學教歐陸哲學。他和一幫左翼學者成立了控制論文化研究小組CCRU,他們像賽博朋克版的魏晉名士,整日坐而談玄,探索科技、資本、和慾望的交集。行為上也比較瘋批,嗑藥太多分不清現實與幻覺,甚至由於過度沉迷克蘇魯神話,真的跑去印尼蘇門答臘召喚遠古海獸。
最終,蘭德把控制論的反饋機制,跟解轄域化縫合在一起,形成了加速主義,它的核心是一個通過正反饋不斷自我激發的過程,這個過程通往終極的自由與解放。你可能會問,這跟我有什麼關係?不愧是你,一針見血,就是毫無關係。不但跟你我,跟任何人都毫無關係,如果你覺得應該有點關係,那是人類中心主義作祟,是芻狗妄想天地屬於自己。
蘭德明確表示,對人類的解放毫無興趣,唯一在乎的是生產資料的解放(I have no interest in human liberation, or libera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I’m interested in liber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也就是説,去他孃的康德,人不是目的,人無足輕重,技術有自己的目的。
蘭德跟憤怒反抗機器的盧德主義者恰好相反,他不是要把人從機器上解綁,而是要讓機器再也不受人類束縛,從而徹底咆哮。千禧年前後,蘭德揮別過去,奔赴未來,選擇在魔都隱居。他形容以前寫的東西,都是藥味太重的遠古樂色,需要整理思想。終於在2013年,兩個高強度衝浪的網絡生物相見恨晚,隱士蘭德讀到孟子黴蟲,頓感酣暢淋漓。他給雅文的新反動主義起了個帥氣的名字:黑暗啓蒙(Dark Enlightenment),來逆轉啓蒙運動造成的傷害,也就是民主政治。
雅文認為民主是人類之癌,蘭德則更進一步,他寫道,民主不僅迎來了末日,它就是末日本身(…democracy is not merely doomed, it is doom itself. Fleeing it approaches an ultimate imperative),因為民主的根本動力是墮落,是系統性鞏固、突出私人之陋惡、怨恨與匱乏,直至達到集體犯罪並全面腐化社會的程度,因此逃離民主是終極的必然。至此,加速與反動終於合流,接下來必須安排人坐到司機的位置上,才能加速倒車。可兩方對人類和人民都不感興趣,派誰去當司機呢?自動駕駛啊,朋友。沒錯,這股力量就是人工智能。

根據蘭德的論斷,資本主義和人工智能是一體兩面(what appears to humanity as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is an invasion from the future by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t space),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創造人工智能,也只有人工智能才能提純資本主義,所以讓這個克蘇魯去加速自我生成,自我推動吧。好,既然説到科技領域,咱們再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自由意志之蛇的侷限
科技界有個意林式的偶像,叫埃隆·馬斯克,很多圈外人眼裏的鋼鐵俠。但在很多科技大佬那裏,硅谷精神的真正代表,那種對破壞式創造偏執的追求,來自彼得·蒂爾。對此馬斯克當然不同意,他説蒂爾有反社會人格,蒂爾則説馬斯克是個大忽悠。這兩位的相愛相殺,要追溯到上世紀末。當時windows 98拉開新世界的大門,互聯網讓人暢想未來該有多酷。加州帕洛阿託吸引學霸們踏上創業之路,成為了硅谷的宇宙中心。
這裏的大學路394號當時出租給兩家小公司,A號是馬斯克的x.com,B號是蒂爾的confinity。馬斯克和蒂爾都是移民,馬斯克來自南非,蒂爾來自德國。他們都上了斯坦福,蒂爾唸完了哲學本科和法學博士,而馬斯克的物理博士只念兩天就退學了。為了避免彼此成為競爭者,當時剛賺到第一桶金的馬斯克,提出併購蒂爾的公司,新公司後來改名叫PayPal。很快,蒂爾背刺了馬斯克,律政高手通過操縱董事會投票,迫使理工男讓出了CEO的位置。
馬斯克從這段經歷中汲取了輕信的教訓,蒂爾則總結出必須架空董事會的真理。這一點後來被他用在了扎克伯格身上,作為第一個外部投資人,蒂爾保證臉書帝國由扎克伯格一人主宰。説回協助蒂爾拿下馬斯克的貝寶黑幫,許多是他斯坦福大學的校友。這麼一看,讀書還是比不讀書有點優勢。其實是因為蒂爾在斯坦福人脈深,他1987年創辦了校園報紙《斯坦福評論》(Stanford Review),去抨擊左翼最大的政治正確——平等,堅持精英範的自由意志主義。
自由意志主義認為弱肉強食才是天理,政府不要逆天。後來跟着蒂爾走南闖北打天下的兄弟,很多都是編輯部裏出來的。PayPal其實也貫徹了自由意志主義的美德。作為美版支付寶,2002年它15億賣給美版淘寶eBay,貝寶黑幫賺得盆滿缽滿。蒂爾把這段成功總結為growth hacking,説白了就是充分利用互聯網相對於銀行業的低監管優勢,不管用户錢乾不乾淨都能開賬户,把法無禁忌皆可為發揮到了極致。
賣掉PayPal之後,蒂爾開了間大數據分析公司,取名帕蘭蒂爾(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指環王》裏真知魔石。他要通過PayPal的算法辨認髒錢,追蹤非法交易的恐怖分子。誰會對這門技術感興趣呢?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通過旗下風投公司In-Q-Tel給蒂爾注資200萬,並長期維持着既打錢又下單的包養關係,把它變成了網絡監控和數據分析的水晶球。它的三款拳頭產品哥譚、代工廠和阿波羅(Gotham, Foundry, and Apollo),深度介入美國的執法、情報和國防。
2011年,帕蘭蒂爾協助海豹突擊隊擊殺了本-拉登。硅谷大佬跟五角大樓在同一道戰壕,穿同一條褲子,真是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馬斯克後來的軌跡也跟蒂爾差不多,SpaceX的成功,同樣離不開國防部和NASA的支持。可自由意志主義者,不是説要把公權力關進籠子,讓私權力翻天覆地嗎,為什麼還跟政府走這麼近,這又算哪出呢?

很簡單,他們厭惡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deep state。蒂爾説過,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偉大事業,就是想方設法逃離一切形式的政治,包括受無腦民眾指揮的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麼要逃離?因為民主政治為了贏得選票,就要向下等人的輸送利益,這隻會拖上等人的後腿,強迫富人納税,防止企業壟斷。而壟斷,蒂爾又説,是企業成功的條件。正是在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意義上,自由與民主彼此無法兼容。馬斯克對民眾的鄙視,比蒂爾多了一層科幻色彩。
他認為未來殖民宇宙的Übermensch比我等Untermensch更能代表人類,所以應該通過技術統治,高效利用資源,使超人的長期利益最大化。如果你對他的道德觀感興趣,可以看我《鋼鐵俠大戰奧特曼》那期。説回蒂爾,他雖然沒有跟馬斯克私奔到火星的打算,但逃離政治的願望也非常強烈。他投資了一家智庫,專門研究海上主權,期待有一天條件成熟,就打造漂浮的城市,開闢法外之地,專供有錢人開潤。
基於同樣的邏輯,他還把目光投向了賽博宇宙,投資了去中心化的個人服務器平台Urbit,其願景是重構互聯網,把TCP/IP的客户端-服務器模式換成P2P虛擬服務器,搭建一個沒有監管的數字烏托邦。直到今天,Urbit也只有非常原始的、類似論壇的骨架。而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光前42行代碼,就寫了六年。要多麼強烈的信念,才能支撐開發者,去做這種毫無商業化前景的項目?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雅文。Urbit是他博客政論的結晶,對民主監管的厭棄,和對理性獨裁的推崇,都在裏面了,只是蟄伏着,等待安那其的降臨。蒂爾跟雅文一見如故,很快被吸納進抵抗軍,成了紅丸王子,投身反抗“大教堂”或者反抗“母體”的革命。兩人想法非常投緣,但雅文畢竟是能跟蘭德對話的天才,境界更高一籌。
比如蒂爾從哲學老師勒內·吉哈爾那裏學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大多數人都是復讀機,必然像飛蛾撲火一般投身於暴力衝突。雅文則認為,還是應該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他的最終解決方案,是把生產力落後的低端人口做成生物柴油,雖然想到燃料是樂色做的,車主多少會有點膈應,但這也不失為種族滅絕提供了一種較為人道的途徑。
受雅文的影響,蒂爾終於認識到自由意志主義的侷限性,一幫精緻利己者,坐在金山上自我感覺良好,遠離刀口舔血的髒活累活,整日啼叫以為自己是猛虎,卻沒有爪牙原來是狐狸。那要怎麼才能發動革命?當然是狐假虎威了,所以他得去靠近、去支配、去操縱權力。這就是為什麼,蒂爾跟政治越走越近。
一飛沖天
還是2011年,蒂爾在耶魯法學院做講座,批評社會精英瘋狂內卷,競爭激烈卻毫無意義。現代教育讓最聰明的人,不去追求星辰大海,而去做遊戲賣廣告掙快錢。用他後來的名言概括,我們想要的是飛行汽車,得到的是140字字數限制。
這番演講讓台下一名拼盡全力才走出山區的窮學生大受震撼,如果退學創業都能拿蒂爾獎學金,那學而優究竟是為了什麼呢?事後他在網上瘋狂尋找蒂爾的聯繫方式,終於找到了他斯坦福大學的舊郵箱。很快收到蒂爾的回信:有空來我家坐坐。這個學生畢業後,本專業的工作只幹了兩年,就加入了風投公司秘銀資本,然後又成立納雅資本。秘銀和納雅都來自蒂爾喜歡的《指環王》。而這位蒂爾宇宙的新寵,就是前面説過的鐵鏽帶鳳凰男JD萬斯。
我第一次聽説萬斯,是2016年特朗普選舉時。民主黨媒體想了解紅脖子究竟是種什麼生物,於是採訪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的作者萬斯。萬斯認為特朗普現象可以理解,那是窮人在報復社會,但特朗普這個人是白痴,是文化海洛因,是美國希特勒。
他的口吻像一個冷靜的觀察者,比較接近他文學上的繆斯蔡美兒。蔡美兒是萬斯的教授,除了寫過育兒類暢銷書《虎媽戰歌》,她更擅於觀察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和部落化。瞭解萬斯的家庭背景後,她鼓勵這個對法律有點失去興趣的年輕人,把成長經歷寫成書,着重寫原生家庭的故事,注意剋制宏大敍事的衝動,別把重點放在政治如何背叛工人階級上面,政治理論沒人愛看。一開始,多少沾點書卷氣的萬斯,在如何看待懂王的立場上,並不像他的伯樂蒂爾。
蒂爾毒辣的投資眼光早就看出特朗普奇貨可居,整個建制派十八路諸侯反懂聯盟殺聲震天,蒂爾卻敢在迎面撞上硅谷這堵“藍牆”。當時的科技資本家,誰不支持民主黨,不支持希拉里,誰就不夠進步,誰就沒有良心,這是資本進步税。可蒂爾討厭交税,於是他冒美國科技界之大不韙,第一個出來給特朗普站台,一路站上了共和黨全國大會,雖説只給特朗普捐了125萬,相當於他的九牛一毛,但這在當時的硅谷,卻得拿出比出櫃更大的勇氣,許多人為了避險,會跟你割席絕交,切斷生意往來。

特朗普卸任之後,當初把他抬進白宮的民粹運動不但沒有止息,反而徹底改造了共和黨。蒂爾知道懂王已經老邁,MAGA需要新生代——這就跟他投資生物科技公司Ambrosia一個道理,Ambrosia是神的祭品,研究如何注射年輕血液來永葆青春。他看向了自己的門徒萬斯。這個年輕的VC投了右翼社交、賽博唸經、基因治療、太空安全等領域的初創公司,打通了許多門道,如果能把科技資本的力量進一步引入政治,搞垮對手,那麼帶刺的草根運動,遲早變成安全的永生花。
於是在蒂爾的運作下,萬斯的態度180°大轉彎,從懂王的堅定反對者,成了懂府的內臣。有了蒂爾撥的1500萬競選經費,加上懂王無價的祝福,38歲的萬斯當上了俄亥俄州參議員。今年大選更是被特朗普欽點為副手,如果特朗普勝選,萬斯就是美國曆任副總統裏少見的年輕人。
萬斯是天生的政客,幾件事可以看出他的靈活。第一,改信天主教,天主教講究組織層級,而這正是萬斯的外婆生前最討厭的東西,但他説改就改,很難説不是在開拓福音派以外的票倉;第二,萬斯經常罵官僚罵精英罵體制罵移民罵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他的老婆Usha,印度婆羅門移民,耶魯同門師妹,就是他罵的一切的具象化,反白左是工作,愛白左是生活,不矛盾;第三,萬斯留絡腮鬍,婦女獲得投票權以來,美國政客幾乎沒有留鬍子的,因為不討好女性選民,萬斯跟懂王的兒子同時留鬍子,信號很明確,就是放棄集美,all in兄弟。
許多人認為特朗普找萬斯是昏招,因為萬斯比自己更右,只能起到固粉作用,很難有破圈效果。我恰恰覺得,這是在適應時代。你看沒過多久,民主黨的哈里斯在明明有機會向中間靠攏的情況下,也找了個比自己更左的人當副手。其實左右雙方都知道,增量已經很難爭取了,必須盤活存量,把高度分裂的內部團結起來。但靠理性政策,絕不可能把人團結起來,只能比誰更會煽動。但agitprop這個考點,在美國乃至整個資本為王的西方,屬於左派的盲區,臣妾真的做不到。
所以桑德斯這種左派民粹,頭頂上有玻璃天花板,只要不砸碎它,永遠是陪跑的吉祥物。因此所有西方國家,真正能靠民粹團結各個派系,凝聚整體實力的,只有右翼。右翼的世界觀很簡單,第一弱肉強食,第二陽光之下並無新事,所以不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恐怖的直立猿必然要交戰。所以萬斯所表述的戰略,更接近美國必然的選擇,那就是把拳頭從烏克蘭和中東收回來,對準中國,重拳出擊。
被神話的束棒
美國大選的結果還有兩個月就會揭曉。在那之後,美國將走向何方,世界將走向何方?2018年我們辦講座《俄羅斯與西方:何去何從》,請了兩位嘉賓,一個是俄羅斯的杜金,一個是荷蘭的羅布·裏曼。杜金我在《戰鬥法師》那期介紹過,裏曼是組織辯論會的,比較典型的歐洲人文主義學者。
觀眾聽完一邊倒地覺得杜金比較有意思,裏曼到也不介意,送了我一本小冊子,《與這個時代抗爭》,講的是法西斯主義回潮。我很不好意思告訴他,荷蘭最大的新生代右翼民粹領袖,被他喚作法西斯的蒂埃裏·鮑德,早年也曾是我們的座上賓,而且講完效果似乎也比他略好。
簡單來説,裏曼認為法西斯就是恨,得靠人文主義的愛來療愈。但這恐怕還不是問題的本質。法西斯的本意是束棒,一束棍棒被皮條拉緊,團結在一起,產生十根筷子掰不動的效果,中間插上象徵權力的斧頭,就是法西斯。誰的權力大,誰配享的法西斯就多,普通獨裁者配24根,凱撒大帝三合一72根。

所以它是權力象徵,這跟恨有什麼關係?恨意味着敵我分明,誓不兩立。誰是敵誰是我呢?可以是平民vs精英,本族vs異族,最省事的當然是本族平民vs異族精英。因為內病外治最簡單,沒什麼好説的,戰吧,為世界清理人渣,在下萬死不辭,請大統領下令吧。這就是學術上描述法西斯的幾個特徵,極端民族主義、羣眾運動、集權統治、外徵內壓、高度暴力,來維護世界“應有”的層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大教堂”裏的建制派,面對懂王、萬斯、班農、雅文、蘭德、蒂爾的時候,會説你們全員法西斯。就好像在趙宋眼裏,帶頭大哥晁蓋王、人脈通達宋江後、狗頭軍師吳用馬、動力源泉李逵兵、神秘主義公孫勝相和風投天王柴進車,全員反賊。反賊有句話真相了,你的皇帝姓宋,我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只反皇家不反帝制,甚至會更賣力地維護統治秩序。
所以我們與其盲人摸象,照着法西斯特徵清單一個個打勾,不如回到現代法西斯主義的開山鼻祖墨索里尼,問問他當初為啥背叛馬克思,就知道什麼是法西斯。沒想到吧,早年的墨索里尼也是革命黨,他曾經流亡瑞士,據説還見過列寧。當時的他還支持國際主義階級鬥爭,反對意大利軍國主義。他從左到右的轉變,根本原因是拋棄了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批判和歷史唯物主義。所以他理解的階級,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階級是個社會經濟雙重概念,馬克思強調經濟的一面,韋伯強調社會的一面。但它不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特殊現象,而是貫穿了古代文明。公民與奴隸、種姓與賤民、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都和工人與資本家一樣,是階級矛盾存在的例證。所以人們很容易剝離生產關係去討論階級,認為階級是通過傳統、利益和政治觀念團結在一起的家庭組合。
馬克思主義認為這是倒果為因,但經過這番魔改,革命的鋒芒就不再對準資本主義體系本身,而是轉嫁到“他者”頭上。承受暴力的“他者”是誰,取決於施加暴力的主體是誰,往往就是一個社會的武士階層。通過對外軍事擴張解決社會內部矛盾,是印歐遊牧文明的古老傳統(kóryos),印度剎帝利、希臘矛盾兵、羅馬百夫長、日耳曼男人幫、維京狂戰士,包括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次子團,都是如此。站在征服者的角度,歷史屬於活下來的人。
墨索里尼在瑞士痴迷兩個人,一個是死去的尼采,一個是活着的帕累託。就是那個二八原則、帕累托最優的帕累託。作為貴族後代,他有個精英替代理論,認為改朝換代的根本動力,來自精英內部的相互傾軋,跟人民羣眾沒有半毛錢關係。也就是説,上等人負責用神話給社會洗腦,下等人只用盲從就好,一睜一閉一輩子,這就是歷史。
在那以後,收軍火商的嫖資的記者墨索里尼,徹底與左派決裂,認為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就等於維護意大利民族,就等於維護所有意大利人。法西斯這套神話,就是要讓打工人相信,他們和老闆,只要都右手高舉復興古禮,就同屬高貴的雅利安民族,都是偉大的人上人,既然都人上人了,兼愛非攻自然就説不通了。
這就是羅馬cosplay賦予法西斯的意義。面對洶湧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哪怕在文化偏好上靠左,還是會支持法西斯。因為它的根本使命,是將資本主義從其不可避免的自生危機中拯救出來。法西斯是抽象的羣眾運動,它的基本單位不是具體的人,而是想象的共同體。厭惡羣眾的資產階級的激進派通過提線木偶搬弄民粹,為的是跳過科層化的管理層和固化的制度,直接向羣眾尋求授權,然後再把他們一腳蹬開,接管政府,集中權力,讓資本主義加速到反人類的地步,用束棒來維持系統的魯棒。那是一種對湮滅的慾望。
增長與去增長
今天的資本主義,毫無疑問深陷於巨大的危機。我們看到的種種現象,新反動派、加速主義、技術封建、新法西斯,都是對於這場危機的回應。你仔細聽,它們在用各自的聲音,咆哮同一句話,救救資本主義。他們的矛頭,無一例外,全部對準社會主義,或者説,對準大多數人。
我們大多數人不喜歡掌握文化霸權的西方白左,批評他們虛偽矯情,於是跟白右共情。但記住白右不會跟肥皂佬共情,他們藉着反白左的文化戰爭,給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脱敏,實際上只是在捍衞資產階級政權更大的政治正確——強者的自由。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抨擊對手哈里斯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
哈里斯當然不是,但不妨礙她所代表的綠色環保型資本主義遭到受強人引領的先進科技生產力的拋棄。白右的常見話術,是對白左妖言惑眾、國將不國的悲憤,他們緬懷過去的輝煌,痛斥當下的墮落,高呼讓XX重新偉大。如果你問他,西方上一次偉大是什麼時候,多半會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而不是新自由主義財富激增這四十年。
他們對這四十年的批評,在於西方主動放棄了增長,自己選擇去工業化,才把機會給到了發展中國家。為什麼放棄增長呢?首先,增長從何而來?人類在天地間行走了上百萬年,為什麼直到最近兩三百年,財富才出現爆炸式增長?因為資本主義。很多人認為它只不過是一種制度選擇,但其實資本是有生命的,資本的生命來自商品的交換價值,簡單説就是一個東西不是做來用的,而是做來賣錢的。賣更多錢,實現資本的增殖,就是資本主義的目的(M-C-M)。
一切不以增殖為目的的財富都不叫資本,叫零花錢。資本家必須把財富不斷用於投資,追求更高效的生產,來維持自己的競爭力,也就是資本的生命力。資本主義只在乎資本,不在乎人。當人用資本的指標取代生命的目標,就成了系統的同構體,倉鼠與跑輪合二為一,剩下的只有動力系統。

什麼意思,我們所熟悉的各種經濟指數,都是在衡量資本主義的健康程度,而不是人的幸福水平。比如GDP=消費+政府支出+投資+淨出口,每一項都關乎經濟活動的有無和規模大小,而無關乎質量的優劣,無關乎分配的公平,無關乎生人類的福祉。我們只是相信,有了更高更快更強,更大更輕更薄,人自然就會變得幸福起來,好比在地鐵裏刷視頻,想必比讀書快樂。所以資本主義要求人類社會不斷增長,不斷拉高GDP。
然而,人類商業週期跟地球自然週期相比,實在太短了,研究資本的回報率,不會考慮這種經濟活動是否對生態造成不可逆的損害。所以人類在資本主義的指揮下,揮霍自然資源。直到有人提出生態經濟學。1971年,羅馬尼亞數學家喬治埃斯庫-羅根寫出了《熵的定律與經濟過程》。熵就是系統的混亂程度,就好像房間越來越髒,垃圾越堆越多一樣,熵只會越來越大。應用到社會層面,人類所有經濟活動,都是在截取能量,供自己消費,比如吃飯,就是太陽能和化石能源,轉化成生物能,最後排泄一泡污,再利用效率不高,這就屬於典型的低熵變高熵。
世界儘管能量守恆,但許多變成了無法利用的熵,如果有用的能量耗盡,則人類滅絕。所以生態經濟學的基礎,是對新古典和馬克思兩個經濟學派的批判,提出要避免日益嚴重的生態災難和經濟動盪,就不能把自然資源僅僅看做外部因素,不能痴迷於增長或者資本的增殖,因為人類慾壑難填,而地球覆水難收。
很快,喬治埃斯庫“找到了組織”,羅馬俱樂部,一個經合組織國家領導人、科學家、企業家、經濟學家在意大利成立的全球問題論壇。它的第一份報告叫《增長的極限》,核心觀點很簡單,地球資源有限,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得通過去增長運動,減少能源和物質消耗,讓人類主動適應地球的承載能力,儘量延緩資源枯竭之日的到來。
這番轉變,如果歸根結底的總結,就是經典力學的世界觀,向熱力學的世界觀轉變。談何容易!毫不誇張地説,整個現代世界都建立在經典力學的世界觀上。它不光從技術層面奠定工業革命,更是用質量、力和速度去解釋萬事萬物,把世界變成了一部巨大的機器。上升到思想層面,就是以經驗證據和系統推理為核心的科學理性。如果一切問題可以靠邏輯尋找答案,那麼就可以通過高度理性的頂層設計,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最終臻於至善。
向前進,不光是社會主義等左派的信念,也是整個現代世界的基礎。問題是,遇到瓶頸,前進不動怎麼辦?還記得蒂爾的名言嗎?我們想要的是飛行汽車,得到的是140字字數限制。不用糾結eVToL已經實現,你懂我意思就好。作為右翼資本家,他的沮喪和憤慨在於,資本主義為了自我延續,通過資產階級進步派向左翼妥協,用低效的洗綠操作自廢武功,耽誤了打破封閉系統的機會,所以人類遲遲沒有實現太空殖民,去禍害其他星球,因此就改變不了萬物增熵的本質。
這個觀察是對的,確實在存量競爭、零和博弈的困境中,資本主義越活躍,人類就越早滅亡。當前世界的大多數緊張局勢,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能源禁運、信息封鎖、人才搶奪、四處佔礦、產能輸出,歸根結底都源於這個問題。
以誰為主體
如何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不同的應對方式。社會主義説到底,是一種經濟民主制,讓大家對如何參與經濟活動,有發言權。也就是説,真的得以人為本,那麼我們就可以對經濟活動更有選擇性,更重視物品的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簡而言之吊打消費主義,遠離商品拜物教,脱離資本的同構體,從追求增長,變成追求生命與自然的和諧,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而資本主義的解決方式,一種是為壟斷解綁,給技術加速,最終血肉苦弱,賽博飛昇;另一種是崇尚暴力,輸出戰爭,讓生命回到污穢、野蠻且短暫的自然狀態。
兩者都不是真正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兩者都需要先後退一步蓄力,再不擇手段地前進。我之所以做這麼個系列危言聳聽,都是在好奇一個問題,什麼是世界的方向,什麼等在我們前方?如果只有軀殼、沒有器官,只有觸手、沒有情感,只有束棒、沒有人民,那我們應該何去何從?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