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麥葉的熏籠精:中國一直是這羣西方人眼中的“天命人”,但可怕的是……
guancha
【文/伍麥葉的熏籠精】
《黑神話·悟空》爆火,引出了“天命人”一詞。這是新生成的詞稱,在該遊戲推出之前,我國文化裏並無“天命人”這樣一個詞彙。不過,該詞與一個極為古老的概念相連——天命,於是也就激發了大家對“天命”那一概念的興趣。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在西方“中國學”裏,天命是極其重要的內容,在“中國通”們的帶領下,很多西方人都相信天命,即,他們相信,“中國自有天命”——本文且稱為“西式天命觀”。
那麼,西方精英是怎樣理解天命呢?
天命等於上帝與中國皇帝立約?
讓我們先從阿拉伯語媒體上的一篇文章談起 。

該文章截圖
2022年,阿語《中東報》上,沙特專欄作家沙吉朗在《〈論中國〉與關於“後美國時代之世界”的爭論》一文中,摘錄了基辛格《論中國》第一章的阿拉伯語版的片段,包括:
“對於中國人來説,在與其共存的那片地理區域內,中國始終高於其他所有羣體,那是不言而喻的和自然的,那根本就是世界的自然狀態,並且它還體現了一項諾約,即天委託(ahidat)皇帝的諾約(ahd)。對於皇帝來説,這一由天賜送的諾約倒是並不希望中國與鄰國人民持敵對狀態,而是相反。”(據文章中的阿語行文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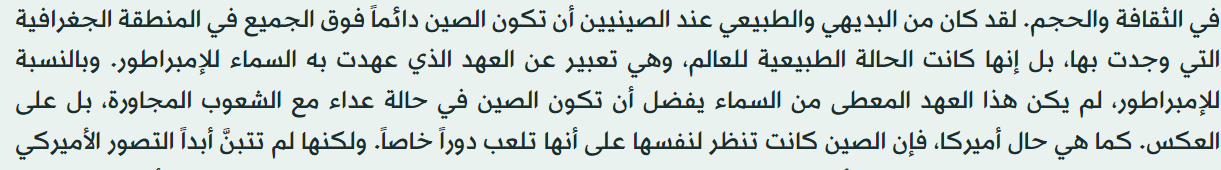
這部分內容的原文截圖
上述阿語譯文,在《論中國》的英文原文是什麼呢?是:
“ That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tower over its geographical sphere was taken virtually as a law of nature, an expression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For Chinese Emperors, the mandate did not necessarily imply an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peoples; preferably it did not.”
“天委託皇帝的諾約”,是對應“Mandate of Heaven”,而後者正是天命一詞的英文固定譯法!
在這裏必須介紹一下ahd與ahidat的詞義:
ahd是動詞ahdan的詞根,也是其名詞形式。該詞的詞義非常豐富,包括:
囑咐;委託;瞭解;諾言;守信用,踐約;擔保;憲章,盟約,公約;誓言;委任狀;契約,合同……
這個詞意義莊重,往往用在非常重要的地方,例如,阿語裏,《新約》是alahd(約) jadiid(新),《舊約》是alahd(約) ghadiim(舊)。再如王儲、皇儲,是valii(隨後的) alahd(委任)。
該詞的動詞形式還包括“暗示”“照顧”“重申諾言、承諾”“締約”等意思,而ahidat正是動詞的第三人稱單數陰性形式,意謂天委託中國皇帝、天給中國皇帝暗示、天向皇帝承諾、天與皇帝立約等意思。

聖經故事中的“上帝立約”
這就意味着,馬舒赫教授把天命理解為“天與中國皇帝單獨立約”,而該種“理論”在阿拉伯世界蔓延開來。
前一陣,隨着巴以衝突加劇,中國民眾注意到,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曾經手持聖經宣稱,上帝與以色列人立了約,把巴勒斯坦許給了他們。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頭一次聽説那樣的説法,覺得匪夷所思,捉摸不透以色列人的底層邏輯。沒想到,阿語世界的嚴肅學者用“立約”來解釋天命,而其他阿拉伯人也覺得順理成章。譯者馬舒赫教授還認真地告訴同胞,相信天與中國皇帝立了約,包含在“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思考和看法”裏。
馬舒赫是從英語世界接觸中國天命的相關觀念,該情況無疑是一種提示,讓我們想到去檢視一下西方文化裏又是怎樣的理解。
天命是上帝頒發的信託令?
美國通俗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以下簡稱“史迪威”)裏如此簡介:
“中國縱貫其歷史,都相信她自己是文明的中心,由野蠻人們包圍着。她是中央王國,宇宙的中心,其皇帝為天子(Son of Heaven),由天命(Mandate of Heaven)所統治。”
從塔奇曼真誠的文字可以看出來,在西方,天命的對譯詞組Mandate of Heaven,是嵌合在一套完整的中國史觀裏。因此,不能孤立地討論西方文化裏天命一詞的含義,而要將其置於西方的中國史觀內觀察。
在英語世界,中國文化裏的特定詞彙“天命”,統一翻譯成Mandate of Heaven。然而,實際上,Mandate of Heaven所藴含的理論內容與中國文化裏的天命基本沒有相合的成分。經由中國通們的演繹,這一詞組變成了“中國皇帝”與“中華帝國”的專屬品。
heaven本意為“天、天空”,但一旦首字母大寫,便成了“上天、上帝”以及“天堂、天國”。mandate的意思則包括:
(書面)命令;委任統治權;授權,委任;受命進行的工作;指令;(羅馬教皇發佈的)聖職授任令;(羅馬法中的)委任契約;代理契約,(英國法律中的)私人財產委託。(陸谷孫主編《英漢大詞典》)
如果把Mandate of Heaven直譯,那就是“上帝對神聖統治的委任”“上帝的授權”“上帝授命代治的契約”之類的意思。在西方現代文明裏,該詞組也確實就是那一類含義。
從明代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一代又一代的西方漢學家大多深受基督教神學的影響,像費孝通那一批美國漢學家都是來華傳教士的兒子。基督教的思想世界籠罩着他們,讓他們身不由己地利用原生文化去理解和解釋中國——除此之外,他們也沒有別的思想工具。

近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
於是,有人出於自覺,有人出於無意,漢學家們分工合作,“團伙作案”,遵循一神教的神學觀念建立了一套關於中國歷史的基本模型,也可以稱為“原則性歷史”“元敍事”“底層敍事”。
漢學家們都是優秀和嚴肅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文章精湛嚴謹,結果就把那套神學敍事藏在了現代學術的下面,讓人們——包括他們自己——都察覺不到。其他領域的學者生活在同樣的文化環境裏,就很容易地接受了他們提供的中國史觀,不具備免疫力。
在西方中國史觀的神學模型裏,一部分構件是這樣的:
上帝手搓出來“中華帝國”那麼一個神奇玩意,讓它早早就出現,還決意讓它就此長存。萬能的主大概對它搓出來的帝國很得意,給它又搓出來全套的配置,諸如勤勞的中國人、從冰淇淋到足球的發明等等。眾所周知,上帝是統治制度的創造者,所以他自然地要想到怎樣統治那個塵世裏的帝國,於是他按需設崗,設立了“中國皇帝”的崗位,讓中國皇帝代替上帝統治人間。
按照上帝的旨意,中華帝國是綿延不盡的,但人的壽命卻有限,怎麼解決這個矛盾呢?上帝想出了一招兒,專門為皇帝設置了天命——上帝的委任狀。它規定,只有拿到那件委任狀的人才能成為中國皇帝。
一旦哪個幸運兒得到了上帝的委任,就會處身於人類社會的封建等級制度的金字塔尖,享受無限的權力與財富。不過,如果中國皇帝做得不好,那麼上帝就會收回委任狀,皇帝就會跌下寶座,他所屬的王朝也會崩潰。然後,上帝會再發一張委任狀,於是新的皇帝、新的王朝上台,如此不斷循環。所以,Mandate of Heaven,既是上帝給中國皇帝的授命,也是上帝與中國皇帝立的約。
咱就説,馬舒赫教授並沒有譯錯,人家是抓住了西方中國學的精髓。
讀到這裏,很多人會説,噢,懂了,西方人的意思是“君權神授”。然而這麼説就草率了。
一代代西方學者打造中國學時,遵循的原則不僅有神學,還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思想,幾項元素交織在一起,決定了他們如何虛構中國史的內容。西式天命觀即是如此,包含着多層的內容,其中一層為:
上帝信託給中國皇帝的統治對象,並非僅僅是中華帝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後者所獲得的神權,是以上帝的代理人的身份,代表上帝,對整座世界進行統治。所以,中國皇帝是“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Gods representative on earth)(保羅·斯特拉森《引領世界的十座城市》)、“上帝的信託人,受命統治大地”(the heavenly trustees of the mandate to rule the earth)”(霍斯特·J.赫勒《中國:應許還是威脅?——一場文化的比較研究》)
很明顯,上述這種奇怪念頭既是一神教思想的投射,也是帝國主義思想的投射。所以,西式天命觀,完全是近代西方文化精英們的產品,徹底偏離了中國文化的原義。可是,西方人卻堅信,該套天命觀是中國人自己的思想。他們更堅信,中國人擁有那樣的思想,乃是上帝意志的表現。
天命是真實存在的?
讓我們問這樣一個問題:
就算把天命理解成“上帝給中國皇帝的委任”,那麼,如此的一條設定,只是人們心裏的觀念,還是真正存在的?
對讀者諸君來説,這是一個很好笑的荒唐問題,根本就不值得提出來。那種設定當然只是人們心裏的想法,而且那想法不科學!
然而,以漢學家為首,在相當一部分西方精英的心目中,天命是真實存在的,有最充足的證據為其存在做了證明。《論中國》有一條表達顯露了真諦:
基辛格告訴世人,在“中國”的意識裏,“中華帝國應該如同高塔,俯臨在它的地理領域之內,這一條,實際上是被當作”“上帝的委任(天命)的一種顯相(expression,也可翻譯成表現、表達方式)”。
這種闡述反映了西方人藏在史學裏的一條神學觀點:
中國文明的成就本身,就是上帝的委任真實存在的顯相。固然神意是無形的,沒有詔書一類的物質載體,但幾千年綿延不絕而輝煌的中國文明始終都在體現上帝的委任。
在西式天命觀裏,上帝一方面狠抓觀念,一方面狠抓實跡,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從實跡方面來説,上帝創造了一套“中國的世界秩序”,作為其意志的顯相,而所謂“中國的世界秩序”也有具體的顯相,那就是朝貢體系。

清代宮廷畫師筆下的“萬國來朝”
美國作家霍華德·W.佛蘭奇(Howard W. French)於2017年出版的《諸天堂之下的一切事務(歪譯“普天之下”):往昔如何幫助中國形成其對全球性強權的追求》(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Global Power)是宣揚中國威脅論的標準作品,竟有個童話式的開頭:
從前有一個國家就在世界的中央,而其地位得到無論遠近的各國人民的承認。今天,我們把那個國家喚作中國。
對鄰國的統治者們來説,從中央王國(Central Kingdom)的承認中獲益固然重要,但,對一連串中國皇帝來説,讓外國人象徵性地成為屬臣,一次次地來向他們的道德優勢與權力鞠躬致敬,於他們的權威也同樣重要。換句話説,其他人心甘情願地卑躬屈膝,拜倒在皇帝面前,這是對內證明了他無懈可擊的道德權威,按老話講,是證明了他擁有上帝的委任(天命)。
這一套説辭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們的標準答案,一次次在他們的筆下反覆出現。
據西式天命觀,上帝一面讓實跡綿延不絕,縱貫古今,一面給中國人灌輸了與實跡配套的全套觀念,中國文化裏的一些獨有的奇妙概念——天命、天子(上帝的兒子)、天朝、中國(中央王國),都是在表達上帝的意旨,是上帝故意讓中國人知道了部分真相,是上帝藉助中國人泄露了部分天機。
有趣的是,西方人發明了上述神學模式的歷史敍事,結果給自己製造了一種精神上的窘境。
在一神教的世界裏,不存在“西方的神管不了中國的閒事兒”“中國的神管不着西方人”一類的道理。相反,按照一神教的信仰,只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它籠罩世界,管定世界,嚴格來講,它無形無象,但它的意志決定一切,構成了萬物的命運(fate、destiny)。而如此的信仰導向一項結論:
在中國那裏,自古至今,一直有着種種的顯相,明白無誤地證明着上帝的委任確實存在,那麼,降下那項委任的神絕不是中國的地方神,而是那唯一的至高神本身。也就是説,把世界信託給中國皇帝讓他代治的神,就是那“萬能的主,唯一的上帝”——所有人共同的神,在不同的文化系統裏可能有不同的稱呼,但神本身是唯一的。
中國通們研究來研究去,成功地研究出一項疑問:神意究竟要幹什麼呢?這就成功地讓西方人兩眼一黑,覺得他們的文明在處境上變得微妙、艱險和困難。

馬嘎尼使團隨行畫師筆下的乾隆皇帝和清朝官員
具體來説,那項總的疑問包括但不限於下列疑問:
上帝設置中華帝國、中國皇帝、信託委任令,目的到底是什麼?中華帝國,究竟該有多大,其範圍和邊界最終該在哪裏?上帝授命她統治的世界,包括哪些地方?那委託令,最終的信託對象包括誰,指向誰?上帝意欲置西方人於何地呢?
這些我們壓根想不到的疑問,在一些保守思想的西方人那裏卻是活生生的問題,構成了他們的焦慮甚至歇斯底里。
中國威脅論裏藏着神學迷信
我們不容易注意到的是,很多西方學者的中西關係、中美關係研究裏就嵌着上述疑問,他們以西式天命觀為前提,絲毫不懷疑那則神話。例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藏在理性言論之下的,是他對天命的執着:
“在今天……中國相信,終於,它正迴歸其在世界上應有的位置。
‘這個帝國自視為文明宇宙的中心, ’學者哈利·蓋爾伯解釋,‘中國的學者和官員根本不是按照現代意義思考“中國”或“中國文明”。’
(儘管美國自視‘我最偉大’)但中國的觀念是把自己當成人類與天堂之間唯一的聯繫,大概更欠謙虛……讓中國人理性地接受一種‘天有二日’的宇宙觀,或讓美國人同意與另一家很可能地位更優越的超級大國共存,哪一種會更困難呢?”
如果不瞭解西式天命觀,就體會不出艾利森的微妙語意,他的意思是:
中國人腦子裏的思想也是神意的一種顯相,就如同上帝植入的軟件,只能按照既定程序運行,那程序裏只有“天無二日”的指令,所以讓中國人改變觀念那是不可能的。
艾利森如基辛格等學者一樣,把迷信表達得含蓄,而通俗讀物就把同款神學性敍事説得直白了,如《龍之寶座》在終篇説:
“1912年帝國的倒台,並不意味着那些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的傳統就此終結……(中國人依然在)試圖推進它(中國),以成就其命運(destiny),那是早先的皇帝們為中央王國所展望(envisioned)的命運。”
至於那些公然鼓吹“中國威脅論”的作品,論調極為狂熱和誇張。哈爾·布蘭德斯(Hal Brands)與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hley)合著的《危險地帶——對華衝突正來臨》(Danger Zone——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便歇斯底里:
“然而,中國並不僅受地緣政治的冷酷邏輯驅動。它還出於歷史性的命運(historical destiny)而追求榮耀……在有記錄的歷史中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都是超級大國。一系列的中華帝國都宣佈‘普天之下’皆在它們的委任統治權(mandate)範圍之內;他們命令帝國周邊的各小國給以尊重。
資深亞洲觀察家邁克爾·舒曼寫道:‘關於中國人和他們的國家在今天的世界該扮演什麼角色,那段歷史在他們心中培養了一種牢固的信念,他們也堅信,那種角色將是長久無絕的。’”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蒂莫西·布魯克(Timothy Brook)的《巨型大國——中國與世界》(Great State——China and the World)污衊中國搞“新型霸權”,其中的囈語裏最清楚地曝光了西方研究涉及中國時的神學基調:
“一些(中國人)建議……遵循一種中國獨有的世界觀,他們稱之為天下的視角。天下——天堂之下的一切——原本為周朝的一種觀念,意謂皇帝應該在上帝的委任之下統治他的所有領土。他是上帝的代理人(proxy),凡是仰望天堂尋求指引的事物(everything that looked up to Heaven for guidance),他都加以管理。有一些國度落在他的統治之外,不過蒙上帝下顧的事物不包括它們,它們遠遠夠不到上帝的目光的邊緣,所以,任它們留在文明的光暈以外的昏蒙裏,也根本沒啥損失。
隨着中國成為巨型國家,潛在而言,已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那統治者無動於衷,也沒有人不會被納入華和夷的種族分隔之內。他的統治是普世的,所有人都只能服從。不過,在那樣的情況下,相關的這一切(即華夷之間的政治差異)都得到了解決,巨型國家就不再需要利用華和夷之間的區別。那會只是一種文化差異,而不是像從前周朝時那樣的政治差異。
(一些中國的評論家認為)由於皇帝曾經是上帝的兒子(天子),所以現在的中國是上帝所指定者(designate),負責監督一個國際等級體系,那一體系就從它面前向下鋪展開去,而它自己最低也是該體系中最為強大的國家。這樣的模式抵消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關於國家間關係的理想化設想,後者認為所有國家都是自主的實體,彼此平等以待。”
布魯克是一個典型例子,他那類西方精英發表涉華言論時,在我們看來像精神病人。只有看清神學觀念對他們的支配,才能明白究竟是什麼原因刺激他們那樣語無倫次。
上述三位作者都採取了同一個前提:
其一,上帝曾經賦予中國皇帝一種權力,就是在世界相當遼闊的一部分地區替上帝行使代治;
其二,上帝把關於代治的一整套觀念植入中國人的心靈裏,於是中國人就擁有那樣一套不滅的念想,無論如何也要承擔人間與上帝之間的唯一媒介,要做上帝的世界代治者,所以,到了現代,中國還是非要實現那個目標。隨着全球化時代到來,中國要代治的範圍也擴張到整個世界;
其三,也是讓西方人最鬧心的是,中國的全部歷史都表明,很可能上帝確實打算讓中國代理統治整個世界。
國際關係如何發展,關乎世界是走向和平還是紛爭,因此相關研究需要理性精神與人文立場,然而,在這一領域,西方學者一旦涉及中國的時候,總是以神學模型作為基礎,在他們自己造的迷魂陣裏打轉,這是目前無解的僵局,不僅荒謬,也很危險。
每個人都擁有天命
話説回來,在中國文化裏,天命的原義又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概念,在漫長時光中,其含義也有變化的過程。
早在《尚書》中,《盤庚》一篇就提到了天命,當時的語境是,盤庚率領臣民遷居新都,臣民們非常牴觸,盤庚便向他們發表講話,其中提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先王定下了制度,敬謹地奉行天的命令)在此,天命乃上天所降與的命令之意。
及至周代,出現了“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的正統觀念。即,上帝本來是把統治的命令授予殷商,而周人因為美德昭著,所以從上帝那裏接受了本來屬於商朝的命令,此後一直擁有這種“天命”。該觀念也一直流傳下來,如屈原《天問》談到自幽王以後的春秋亂局,便質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天發出的命令顛倒無常,究竟哪些是懲罰,哪些是保佑?)

屈原《天問》
不過,從春秋時起,以子夏鏗鏘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為標誌,對於“天”與“命”的新定義出現了。那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定義,閃爍着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光彩。最突出的乃是《荀子》中的《天論》一篇,振聾發聵地指出,天地只是按照自然規律運行,不會為人事動情,也不會干預人事,所以“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個人的命運是受外界擺佈的,但國家的命運卻是靠人類所創建的文明決定興衰。
在此,“命”變為命運的意思,而“天命”則指任何人的命運。同篇中又有“從天而頌之,孰若制天命而用之”(與其服從並崇拜天,何不掌握天命、利用天命呢),則是將天命徹底地定義為自然規律了。
此後,天命一直存在於歷代人的思想中,而“命”不再是上帝的命令,改指命運,乃至指運勢。
東漢史學家班彪《王命論》分析“帝王受命”的道理所在,其中提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認為一個人一生窮苦還是顯貴,那是由命運決定的,但運勢向好轉變還是向壞轉變,卻是事在人為。顯然,班彪至少有一點與荀子接近,那就是認為人人都有“命”即自身無法控制的命運(“貧窮亦有命也”)。
不過,在班彪的理論裏,帝王的“王命”特殊一點,涉及“天之歷數”,即上天神秘的規律。一方面,“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江山社稷是有天命的,不是純靠人力就能攫取的;另一方面,就算是天意明顯屬意的人,也要各方面做到極其優秀,“應天順人”,才能“成帝業”。
同為東漢思想家的王充在《論衡》《命祿》篇中認為:“自王公至庶人、聖賢及下愚……莫不有命。”與班彪看法一致。看來,認為人人都有難以改變的命運,是東漢時代的主流觀念。
《劍橋中國秦漢史》“班彪關於天命的論文”一節痴痴纏纏地堅持:
“從上下文看,王充所指的是‘命’(destiny);他似乎沒有用‘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字樣。”
這本秦漢史的作者如他的西方同仁們一樣,死抱着“天命(Mandate of Heaven)專指上帝給中國皇帝的委任”的念頭,所以非説王充只談到“命”,未涉及“天命”。
然而,恰恰是《論衡》的《吉驗》一篇給出了天命的明確定義:
“凡人秉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
又在《命祿》篇引述了漢高祖自信的話語:
“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王充的理論為,凡人都有命,但天命侷限於帝王公侯的羣體,包括烏孫王、竇太后的弟弟竇建國等人都有天命,而所謂天命就是富貴的命運,那是上天所決定的。很顯然,王充思想中的天命是指人的命運,即天意賦予的貴命。
該書《恢國》篇如此議論:
“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同儒者所説的那樣,漢朝之前的五代都有一次“受命於天”,唯獨漢朝有兩次,可見天命特別厚待漢朝。)
這裏所説的天命,同樣是指天所賜的貴命。因此,《論衡》中運用了天命的字樣,而其意旨頗接近destiny——命運;與“上帝的委任”沒有任何關係。

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護臂
在後世,天命往往用於指所有人的命運。最有趣的是南宋文人羅大經《鶴林玉露》裏質疑對墳地風水的迷信:
“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説,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
他説,不管是誰,其人生都是由上天設定好的,就叫天命。所以,遷墳改葬怎麼可能改變子孫的命運呢?難道上帝的意志反而打不過一堆泥土嗎?
再如清代文人文康的小説《兒女英雄傳》裏描繪安二老爺的心理活動:
“自己一想,可見宦海無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裏了,倒不如聽命由天的闖着作去,或者就這條路上立起一番事業,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也不見得。”
由此可見,在清代,相信每個人都有天命,是一種很平常的共識。另外,安二老爺的思路也很典型,反映了傳統上人們的生活態度:一方面相信天命,覺得窮富、貴賤、賢愚等等,都是由無形的上天設定的;一方面,又覺得人應該在順應天意的前提下努力有所作為,那樣就有可能借助天命的運勢,讓一切都向好的方面轉化。
實際上,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一方面承認天命,一方面又強調事在人為,是最為普遍的觀念。今天,我們偶爾會用天命作為比喻,大家是默契地用唯物主義賦予天命一詞以新的含義。
在當代的文化氛圍裏,天命往往指世界上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形成某種必然性,構成某種巨大的外在力量,有時甚至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某個人或者某個羣體的條件或者行為如果恰好與那種外在力量的導向相契合,就有可能達成某種善與好的目的,完成某種重大任務,甚至創造歷史。
在今天,天命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指某種重大使命,在某種具體的歷史境遇中,該種使命出現,並且降臨在某個或某些因緣際會最適合完成那項使命的人身上。當天命意指使命的時候,一定是指善良與美好的使命,能夠造福於人,將一個民族乃至多個民族上升到新的境遇中。
並且,我們使用天命的比喻時,繼承着古人的辯證傳統,一方面以天命比喻外在的客觀形勢,認為人要順勢而為,認清大勢,順應大勢;一方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深知人的行為與外在客觀形勢的互動是複雜的,彼此反覆影響,會不斷激發出新的動態。
當然,本文這裏只是做了最淺顯的介紹。“天”以及“天命”的觀念,反映着中國人幾千年從鬥爭與進取中獲得的感受與積累的智慧,值得我們好好去研究。
遺憾的是,西方的天命觀把天命侷限為“上帝單設給中國皇帝的委任”,然後又按照一神教的邏輯將之染上“立約”的色彩,繼而填入帝國主義思想的內容。他們拿到一個“天命”的對譯詞,就用它做支點撐起了整個地球,硬是替地球想象出了一種“世界秩序”的幻影,然後再把那種幻影作為對手,上演堂吉訶德大戰風車。這,屬於人類文明交流史上最意想不到的一樁奇事。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