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圖赫爾:美國根除假新聞,為何越努力越失敗?
guancha
編者按:
“假新聞”一詞於2017年獲選為柯林斯詞典年度詞彙,被解釋為“假借新聞報道形式傳播的錯誤虛假、聳人聽聞的信息”。
從17世紀到21世紀,假新聞貫穿了美國新聞業的發展歷程,從早期未經核實的不實消息,到後來蓄意捏造的虛假報道,假新聞變得越來越像真相,事實與虛假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
美國曆史學家、記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安迪·圖赫爾(Andie Tucher)曾任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及前副總統戈爾的演講撰稿人。她在著作《謊言與真相:美國曆史上的假新聞與假新聞業》一書中回顧了美國假新聞的發展歷程,深入發掘其成因,歷數其造成的影響;書中還談及美國政府機構如何介入新聞報道,以及美國媒體如何服務於其所有者的政治立場和傾向。
本文節選自《謊言與真相:美國曆史上的假新聞與假新聞業》尾聲《“一個墮落且變態的怪物”》,講述對美國現代假新聞的觀察和反思。
【文/安迪·圖赫爾】
特朗普總統的任職與垮台,讓任何一個有理智的新聞歷史學家都免不了要回答這樣一個急迫的提問:現在是不是史上假新聞最猖獗的時候?假新聞是不是對民主和公共生活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是的。
特朗普沒有發明“假新聞”這個詞,把自身錯誤歸咎於新聞媒體的策略不是他想出來。他不是第一個為了自身利益而操縱記者和新聞慣例的公眾人物,不是第一個用意識形態標準來衡量真實性的人,也不是第一個以發明者從未想過的方式利用新技術的人。其他政治操作者也蓄意破壞公民對公共機構和新聞機構的信任,或與那些志趣相投的新聞機構建立共生關係,這些新聞機構只是假裝獨立,或者給它們認為負面或尷尬的報道貼上虛假的標籤。
只要有美國新聞媒體存在,並顯示出令人不安的創新力和適應力以掩蓋其意圖,令公民生活變得複雜和混亂,假新聞和假報道就一直會是美國新聞格局的一部分。民主信息系統是對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但它也面臨着不安全因素。多年來,民主信息系統一直被騙子、宣傳家、吹牛者、黨派擁護者、虛張聲勢者、醜聞製造者和出於個人動機的欺詐者入侵和利用,如果不對民主信息系統遭受入侵和利用的多種方式進行説明,那美國新聞史就是不完整的。
新聞業與真相之間的關係,總是比我們許多人意識到的更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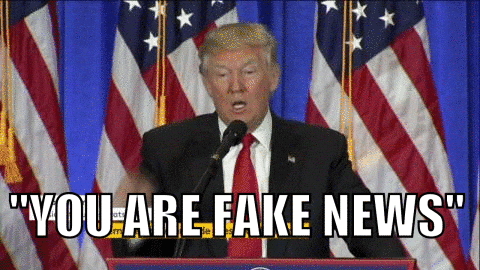
但是,這位總統在其4年任期內公開發表了3萬多條“虛假或有誤導性聲明”——通常是為了取悦其忠實的右翼支持者——此舉聚焦並加速了歷史趨勢,這一點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幾十年來形成的政黨關係腐朽之風達到頂峯;公民被嚴重分化,各派別幾乎沒有共同語言;人們往往將專家、專業知識和真相妖魔化,而不是將其視為別人的意見。
再加上不斷排斥科學和專業知識,即使是在致命的大流行病中,也認為科學和專業知識是精英主義,不可信任;人們廣泛支持瘋狂的、世界末日般的陰謀論;社交媒體是龐大、神秘和不負責任的機構,似乎有無限的黑客行為、偽造和虛假信息;互利契約將右翼政治世界和右翼媒體帝國結合起來。
結果是,公共生活中充斥着規模空前的有毒謊言,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被當作基本工具使用,而“真相”則被視為一種應得的東西。任何應該是真的東西都可以是真的。任何支持自己政治對手的東西都是假的。
新聞史學家也被這一請求所困擾:難道不能從假新聞的歷史中學到什麼東西,幫助我們應對當前的危機嗎?歷史學家們將過去視為一種塔羅牌是有道理的,因為塔羅牌可以為未來的道路提供預示性的見解,但即便如此,這也可能是一個錯誤的問題——當然,特朗普政府過度使用假新聞這個詞,導致任何可能的答案都變得模糊不清。也許更有用的是這個問題:我們能從假新聞的歷史以及它與政治黨派之間日益惡性的關係中學到什麼?
美國第一份報紙在波士頓閃亮登場並隨即消亡後的兩個世紀裏,報紙幾乎都是在玩弄真相,而不是調查真相,虛假新聞和它對應的真實新聞之間沒有明顯的形態區別。負責任的新聞機構一直願意承諾有義務向公眾提供值得信賴的信息,負責任的讀者和觀眾也一直期望新聞業能認真關注嚴肅的事情。但在早期報紙自由競爭的世界裏,負責任的報紙需要不斷與惡意、狂熱、貪婪和愚蠢的報紙競爭。自19世紀起,人們普遍知曉報紙、相冊、19世紀末的電影院和以太領域包含大量嚴格意義上非信息的內容,讀者並不期望他們在公共場所聽到或讀到的所有內容都是真實的。他們可以自己選擇接受什麼是真實的。
讀者看到信息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他們可以相信這些信息是可靠的、相關的;而記者則看到了有用性、聲望和商業優勢,聲稱自己是告訴公眾真相的人。正是這兩種利益攸關方的雙重壓力,最終讓新聞實踐得以形成一定的秩序。記者在塑造自己真相講述者的地位時,虛假這個標籤的襯托必不可少。19世紀80年代,當記者第一次開始談論“造假”時,許多人都將其視為一種恭維,代表着輕鬆、便於讀者閲讀。然而,很快,職業化的記者階層就把這個詞作為行話,在這個過程中,讀者不再有責任(或機會)決定他們應該相信什麼公共信息。
因此,當主流記者開始宣稱最終被視為客觀性的調查方法作為職業準則,將事實作為他們的信條,將“真相”作為他們的特殊財產時,報紙上的造假才有了拉爾夫·普利策在1912年所説的“一個墮落且變態的怪物”的味道。儘管職業化的記者們有時也達不到自己設定的標準,但他們對自認為可接受的工作類型、希望行業中出現的記者類型,還有他們負責為公眾提供的服務類型做出了明確聲明。他們的原則很明確:
真相就是看起來像新聞的東西,而新聞看起來就是真相。

美國報紙出版商拉爾夫·普利策
然而,將造假污名化非但沒有制止造假,反而將其變成了一種可以用來對付污名化者的武器。“造假”這個詞逐漸淡出有關新聞業的討論,對於新聞報道這項嚴肅的事業來説,造假太過輕率。但是,當記者逐漸將其權威性和特殊地位的主張更深地植根於公正性和準確性之中時,針對偏袒和不準確性的指責就成了更有力的武器。對於自己不願接受的真實信息,公民和公眾人物都利用這些武器來破壞信息的可信度。
有時,這些指責有效批評了真正糟糕的報道:屍體工廠聳人聽聞的故事、沃爾特·杜蘭蒂對蘇聯饑荒的傾向性報道、珍妮特·庫克和其他新聞工作者捏造的謊言。有時,正如麥卡錫參議員對“紅色”新聞媒體的攻擊,或大煙草公司挑戰有關吸煙危害的科學報道,指控者發出事實層面或意識形態方面不準確的言論,將這些言論偽裝成對報道的有效批評,而這些報道本身在當下看是準確的。
有時,其他偽裝也會發揮作用。在“真正的”、職業化的新聞業出現之前,假新聞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假新聞將自己偽裝成真新聞的樣子,假裝接受真新聞的標準,並且常常因為有了假新聞而破壞了真新聞的可信度。假新聞越來越像真相,偽造的真相越來越像新聞。
主流記者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嘗試捍衞其職業界限,要向廣大公眾(有時也向他們自己)解釋為什麼這些假新聞事實上不是真的,而要這麼做很困難,往往使得捍衞職業界限變得更加複雜。
新的傳播技術和實踐不斷重塑媒體格局,但它們算不算是新聞業?新聞工作者需要糾正什麼?一些內容碰巧具有新聞特質,但從未聲稱自己忠於事實,假新聞與這些內容的界限又在哪裏?畢竟,在1898年,先鋒電影製片人阿爾伯特·史密斯和J.斯圖爾特·布萊克頓用帆布桌布和浴缸拍攝出了聖地亞哥灣,只要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看到的並不是真的古巴,這真的那麼糟糕嗎?當新聞業與娛樂業糾纏在一起,哪種價值觀佔據上風,讀者和觀眾又有多在意呢?
隨着媒體規模越來越大,與政治體系的糾纏越來越深,假新聞也越來越多,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和其他人不可能通過努力將假新聞根除。
在一戰中,媒體進行了令人不齒的過度宣傳,在此之後,國際聯盟試圖通過條約禁止假新聞。讓每個人都同意不再以廣播散佈謊言,這種做法很高尚,但國際聯盟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宣傳者,他輕率地忽視了事情的全局。
從長遠看,美國在教育領域的理想化嘗試也沒有好到哪裏去:美國成立了宣傳分析研究所,教導兒童和成年人如何檢視自己的偏見,然而研究所不到半年時間就關閉了,以便為官方認可的戰時宣傳騰出空間。
在麥卡錫時代,參議院中的民主黨人開始努力取締故意歪曲的競選材料,該努力之後付諸東流,在憲法層面也存在疑問,在民主黨失去多數席位後,這一做法就消失了,因為新掌權的共和黨人不會放棄這些已成為他們有效武器的東西。
到20世紀70年代,新聞機構自我監督或對其他新聞機構策略作出可靠批評的傳統權威已破滅。具有反叛精神的“新新聞主義”記者強烈否定客觀性(即幾十年來專業新聞的基礎),認為它不足以滿足需求,傳遞的信息不足。但同時他們也提出了新質疑,即主觀性是否會鼓勵不準確的報道。年輕記者在一些最負盛名的新聞機構中工作,他們一次又一次讓老闆蒙羞,老闆似乎無力控制他們。在戰爭和外交事務的重要報道中,出現了一些令人尷尬的錯誤,進一步削弱了公眾對新聞界的信任,公眾們不再相信新聞界能將一切事情處理好。
通過公開承認和譴責來做一件光榮的事情,似乎只是招致更多尖鋭的批評。隨着網絡上知名的“小聲喧囂”變得越來越嘈雜,任何理性對話的嘗試都被過濾泡沫所淹沒,消失在迴音室中,埋沒在煽動性言論、黑客和欺詐行為、傀儡表演、算法操縱和其他在線不當行為之中。數字新聞世界日益細分,傳統的新聞機構面臨前所未有的資金挑戰,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因為不滿而離開。
在驅動公共生活的政治極化方面,假新聞現在已鞏固了其重要地位。假新聞植根於一個新興的生態系統,該系統由右翼媒體活動者和組織構成,他們利用網絡世界快速、輕便的優勢,採用福克斯新聞的策略,將其超黨派的內容呈現為經過專業驗證、準確和無偏見的信息。這些組織經常炫耀民主和新聞自由的言論,明確聲稱按照專業化的新聞標準運作,並且經常詆譭國家媒體和“自由派媒體”,理由是它們沒有做到這一點。
例如,在2018年,數十名在保守派電視廣播公司辛克萊廣播集團工作的新聞主播被要求朗讀一份文稿,文稿譴責“新聞報道不負責任和片面化,這一趨勢一直困擾着我們國家”。文稿接着寫道,全國性的新聞機構“沒有先核查事實”,就發佈從社交媒體上扒出來的“假新聞”,“新聞媒體正在利用他們的平台推動發佈個人偏見和議程,以‘控制人們的想法’,這對我們的民主極其危險”。
與此同時,隨着越來越多的地方報紙倒閉,一家神秘的網絡組織在美國50個州建立了大約1300個在線網站,這些網站的名字聽起來還不錯,包括“安阿伯時報”(AnnArbor Times)和“得梅因太陽報”(Des Moines Sun)等,並經常説他們“提供客觀的、以數據為導向的信息,沒有政治偏見。”這些網站很少承認,他們的許多文章實際上是由共和黨政治活動家、企業公關公司和保守派宣傳團體訂購和資助的。他們決定了文章內容、來源和明顯的右傾傾向。
布賴特巴特新聞網時任執行主席史蒂夫·班農在2016年共和黨全國大會期間向記者吹噓説,布賴特巴特新聞網是“美國另類右翼的平台”,在其網站上自稱“美國領先的新聞機構組織之一”,創立理念是“真實的報道和自由開放的思想交流,對於維持強大的民主制度是必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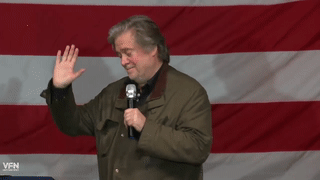
詹姆斯·奧基夫的“真相項目”在對主流新聞機構、民主黨政客、工會和自由派宣傳團體的“調查”(正如該組織網站所稱)中,經常使用道德上或法律上可疑的卧底技術和編輯做法,經常被譴責為具有欺騙性。《紐約時報》2020年報道稱,一個與特朗普政府關係密切的安全服務承包商參與了一項由前美國和英國間諜提出的倡議,旨在對“真相項目”的特工人員進行間諜戰術和情報收集技能培訓。當被問及看法時,奧基夫告訴《紐約時報》,他的組織是一個“令人自豪的獨立新聞組織”。
在InfoWars.com網站上,亞歷克斯·瓊斯推動了從“比薩門”到白人種族滅絕的陰謀論,並遭到了起訴。一些一年級的學生在一場學校大屠殺中遇難,瓊斯將該屠殺稱為騙局,遇難學生的家長以誹謗罪起訴了他,他將自己描述為一個“頑強的記者”,他的組織“公開並自豪地將我們的偏見——真相——戴在袖子上”。這位“門户專家”網站的博主炮製有諸多流言蜚語,包括希拉里·克林頓病入膏肓、新冠疫苗導致數千人死亡,還有喬·拜登號召穆斯林聖戰。2021年初,他在推特散佈了數週關於選民欺詐的虛假信息後,其賬號被封禁了。在2019年和2020年的幾個月裏,瓊斯在自己的主頁上吹噓稱,他的網站“過去兩年來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微軟全國廣播公司都更準確並且還將持續下去!”
《每日電訊》(Daily Caller)網站強烈倡導白人民族主義和反移民,其聯合創始人塔克·卡爾森於2020年6月離職,專注於他在黃金時段播出的高評分福克斯新聞節目。該網站特意強調歡迎其讀者報告任何錯誤,並承諾會“迅速”糾正錯誤,“以便我們的讀者能夠知道真實的故事”。當然,人們通常認為公開接受和糾正錯誤是職業操守的主要信號,一個新聞機構願意這樣做的程度,真實反映了其對事實準確性的承諾度。
然而,《每日電訊》的做法並非完全像其所承諾的。2020年1月,我使用該網站的搜索引擎檢索“更正”(correction)一詞及其近義詞的使用情況,在前100條搜索到的信息中,只有3條涉及《每日電訊》本身的錯誤,其中一條有關演員和泳裝模特凱特·厄普頓的“性感”。其餘大部分都是分享其他新聞機構或專家不得不做或應該做的更正笑料,這些更正“重要”“尷尬”“驚人”或“巨大”——絕大多數都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
傳達的信息很清晰:《每日電訊》對職業操守的興趣僅限於利用職業慣例,以損害遵守慣例的新聞機構。策略也很清楚:假記者正在以他們開展新聞工作的方式定義新聞實踐。假記者正在劃定自己的職業界限,以破壞、否定和拋棄真正的職業界限。假記者正試圖控制真相的模樣。
説新聞業已達到危急時刻,這種説法聽起來既熟悉又讓人厭煩——什麼?又來了?但特朗普及其盟友對記者和真相本身的攻擊是空前的,而且考慮到涉及的權力和財富,這些攻擊不可能迅速消退。
即使是用心良苦的記者,也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來彌補對公共生活的損害,恢復人們對公共機構已經受損的信任,或者彌補本行業的重大錯誤。記者可以嘗試用信息彌合政治極化的鴻溝,可以調查造成這些鴻溝的不滿和怨恨,但他們不能強迫那些不滿和怨恨的人接受或採取行動,甚至不能強迫他們關注記者要説的話。記者可以試圖澄清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但他們不能也不應該滿足聽眾(非常人性化)的願望,證實這個世界完全按照他們希望的方式運作。記者不能阻止公眾人物撒謊,也不能強迫人們認識到他們在撒謊。
新聞工作只有在那些接受其權威的人看來才是真實的。對其他人來説,真相併不像新聞的樣子。

《謊言與真相:美國曆史上的假新聞與假新聞業》,(美)安迪·圖赫爾 著,孫成昊、劉婷 譯,中譯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