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勁 | “情”與製造“日常生活”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44分钟前
範勁|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2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範勁
**人的愛憎、品味和行為方式來自情感結構。**看起來,每個民族或地域的人們都有自己特殊的情感,構成一個民族或地域的特有氣質,這就是通常所説的,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情感(樂天知命、崇尚自然、追求和諧,等等)。但情感結構説到底是“世界”的結構,中國人的情感來自中國人的世界。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情感結構和世界結構都是在社會系統和歷史演化中構成的,是世界的產物而非本體論屬性,是規定行為的先驗模式而非對現實的“客觀”描述。**當代理論界如此重視情感,旨在揚棄傳統的主客二元論框架,走向一種人和世界的新關係,用一個哲學術語來概括:走向“生活世界”。胡塞爾後期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流行至今,乃因為它象徵着哲學開始走出意識世界的靜思,面向社會和實踐。人們領悟到,自然科學所預設的客觀世界只是抽象化的結果,生活世界才是一切理論和實踐活動的共同根基。
社會學家盧曼卻不同意這一看法,他重視的不是先驗的生活世界,而是社會系統的運作。他不僅把胡塞爾的現象學歸入傳統的主體哲學,還在《生活世界——徵詢現象學家之後》一文中對“生活世界”概念進行了批判性的解剖。不過,他真正的針對目標不是胡塞爾,而是哈貝馬斯。後者明確反對盧曼的系統理論,認為生活世界才是社會和歷史的基礎:要生活世界還是系統,成了一道意識形態的選擇題:要系統,就是拒絕解放,服從資本和權力的統治。然而,人們逐漸認識到,盧曼的觀點自有其合理之處。
哈貝馬斯忽略了,盧曼的系統其實不是實體,而是系統/環境的差異形式。既然如此,系統概念就可作為觀察世界的方法,賦予世界以形式。以系統為方法,必然引出一個問題:是生活世界產生系統,還是系統產生生活世界?**盧曼將生活世界概念置回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製造生活世界。**他的系統概念代表了一種後形而上學的立場。首先,本體論視角下的系統由要素組合而成,用之生活世界問題那就是生活世界有其本真的要素,人是本體論的個體,生活世界意味着“返本”。但盧曼以系統/環境的區分作為系統成立的前提,照此思路,先有系統的框架,再有生活世界的要素和體現生活世界的“人”。其次,系統的構成要素不是實體而是操作,對於社會系統來説就是交流,而生活世界代表一種以生活世界為形式的交流。

尼克拉斯 · 盧曼(Niklas Luhmann)
人們普遍同意,生活世界涉及一個主體視角,它作為主觀實在區別於自然科學構造的客觀實在。主體關聯保證了世界的確定性,但也保留了和形而上學傳統的聯繫。如果放棄這一主體性興趣又會怎樣,盧曼不禁要問。依他看來,主體指涉雖説讓現代人獲得家園感和安全感,終究是一個空洞安慰。盧曼注意到“生活世界”概念的語義分裂,生活代表熟悉者和確定性,世界代表不熟悉者和可能性,胡塞爾試圖將二者統一。按照現象學的觀點,世界不是實體對象或實體物的集合。為了理解何為世界,胡塞爾提出了視域和基底這兩個隱喻,世界既是“每種個別對象經驗的普遍信仰基底”,也是“所有可能的判斷基質的視域”。**胡塞爾一方面把世界界定為視域,另一方面把生活世界描述為基底。**如盧曼所指出,兩個隱喻在功能上有別。基底供人站立,供人在上面運動,但人不能在視域上站立和運動,只能朝向視域運動,而視域迴避所有抵達它的嘗試。基底給出安全感,視域代表無限,盧曼認為,這就將生活世界變成了悖論:生活世界如果是基底,那就不是生活世界(因為世界是視域);生活世界如果是視域,那就不是熟知的生活世界(因為生活乃是基底)。
胡塞爾融合這兩個隱喻的根據在於“原初被給予”,此即他的明證性原則:“每一原初給予的直觀都是認識的法律淵源,所有在‘直覺’中原初地(即在其身體性實在性中)提供給我們的,都只能如其所給出自身地(als was es sich gibt)單純接受,不過也只是在其給出自身於此的界限中(nur in den Schranken, in denen es sich da gibt)。”作為絕對的確定性,原初被給予就是認識根據,但它的視域(世界)也必須一同被給予,“界限”即視域,在其中,事物“給出自身於此”。如果這種被給予的原初方式通過還原回溯到原初的意義締造成就,生活世界就呈現了。而現象學還原意味着,放棄近代科學所依賴的“技術理想化”。按胡塞爾的想法,這一程序不會取消主客體差異,不會因為一個完整的客體描述而放棄主體,反之,它使得在原初被給予者中同時描述確定性基底和視域成為可能。但盧曼稱之為基底和視域的“混淆”,因為一旦放棄原初被給予這一前提,或反思其可能性條件,統一體就瓦解了。
基底/視域代表可能性/潛在性、熟悉/不熟悉、已有者/未來者的區分,盧曼認為這一矛盾無法在主體範圍內得到解決。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構想沒有解決主客觀統一的問題,因為先驗主體無法進入客觀世界,先驗自我範圍內不可能出現“不熟悉者”。生活世界概念的內在矛盾源於胡塞爾的先驗哲學立場,他一方面希望通過回溯到生活世界這個原初自明的經驗領域,來使一切科學、邏輯和文化構成物獲得真正的根;但另一方面,他又以超越自然態度的最“科學”的方式,還原到先驗性的生活世界的普遍關聯。考慮到理性和先驗也是社會產品,哲學工作也是生活方式,這裏就出現一個明顯的套套邏輯:尋求生活世界的先天結構這一理論行動,本身出自生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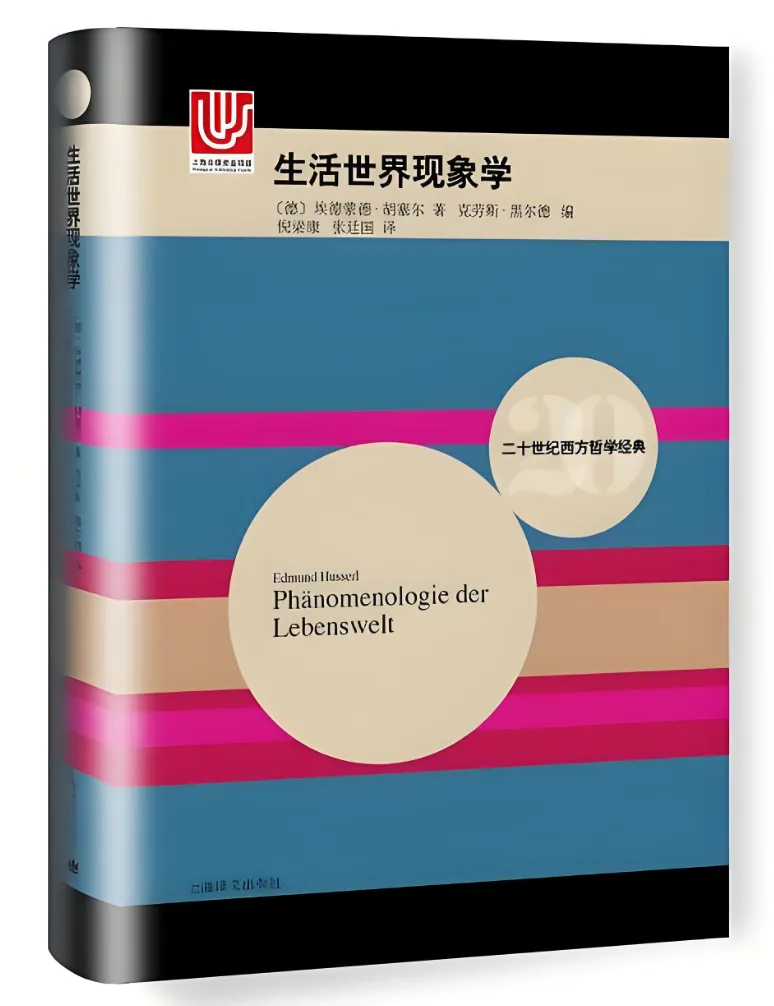
盧曼則認為,早在伽利略式物理學出現之前,本體論形而上學已脱離了生活世界,而按照存在/非存在的編碼自我運作。胡塞爾倡導回返生活世界,動機源於歷史情境——他試圖在非理性主義的納粹時代為理性正名,維護歐洲的精神正統。盧曼説,細察之下會發現,基底本身並不具備所希求的確定性,因為它是一個完全的行動關聯項——“改換了頭面的行動本身的自我指涉”。盧曼打了一個比方:“如果你往上望,它(基底)在下方;如果你向下望,則它在上方。”日常生活中的我總是屬於一個具體的生平情境,它決定了我把什麼視為基礎,什麼視為目的。座標原點轉移,相當於換了一個世界,原來世界中的先驗就可能變成新世界中的經驗。
在盧曼之前,舒茨(Alfred Schütz)已看出胡塞爾的自相矛盾。**舒茨認為,先驗自我是一個無法變成複數的概念,他人的存在從根本上説也並非先驗領域的問題。**交互主體性雖然是最重要的社會現實,但它屬於日常領域。我們關注的焦點應該是世俗的交互主體性,因為恰恰是他人和社會決定了何為先驗自我。舒茨揶揄説,進行還原的胡塞爾不是先驗自我,而是遵從哲學的思考和言説方式的哲學家。作為解悖論的辦法,他主張以“日常生活世界”取代“先驗的生活世界”。世界是我們通過行動與之實際打交道的東西,而非先驗主體的構造。**日常生活世界不僅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場所,而且其根本特徵是交互主體性,交互主體性使交流成為可能,讓個體在交流中變得精明成熟。**雖然日常生活之外還有藝術世界、宗教世界、夢的世界和科學理論的世界等多重實在,但日常生活構成所有實在的經驗原型,其他意義域都可以看成它的變體。經過舒茨及其弟子們的闡發和推廣,“日常生活”成為20世紀後半期的重要文化概念,在哲學、社會學、美學領域都發生了重要影響。我們今天談論“情”與“日常生活”這個話題,也離不開這個思想史的背景。
經由舒茨的中介,“生活世界”概念才進入了哈貝馬斯的理論框架。盧曼發現,哈貝馬斯保留了基底和視域的隱喻融合。一方面,生活世界作為交流行動的總語境即視域而在場;另一方面它又是具體實在,既構成系統的基礎,又和系統相對立。哈貝馬斯綜合了胡塞爾和舒茨的觀點,既接受社會性優先的現實,又試圖維持理性的整合功能,他的辦法是以理據話語代替先驗主體,在交流者的共識追求中實現統一。生活世界的核心仍然是交互主體性,但其根據不是先驗自我而是交流合理性。為了抵抗經濟、政治這兩個功能系統的過度擴張,必須將生活世界建設為主體性的最後據點。
**盧曼卻在生活世界這一開端背後又找到了一個開端,即熟悉/不熟悉的區分,正是這一區分製造出了代表熟悉者的生活世界。**他採用英國數學家斯賓塞-布朗(Spencer-Brown)的區分理論來説明生活世界的成因。後者提出,觀察即區分:看什麼和不看什麼,標記和不標記。任何一個區分總是在分出兩邊的同時對某一邊進行標記,如果重複標記,即標記總是落在同一邊(斯賓塞-布朗稱之為“壓縮的形式”),就會造成熟悉性。生活世界代表了“熟悉性的壓縮”。可以想象,不斷使用華/夷區分來標記“華”,或不斷使用科學/迷信的區分來標記“科學”,也會製造一個熟悉的生活世界。盧曼説:“當世界以語境專屬的方式由熟悉/不熟悉區分所表徵時,世界就顯現為生活世界,但這並不排除,可以再次以多元語境的方式去闡釋熟悉者。”這裏有兩層意思,首先,只要社會在運作,觀察者在觀察,就要進行區分操作,而生活世界就不會消逝,因為“壓縮的形式”會將它再生產出來;其次,生活世界(熟悉者)的表現形式隨語境不同而改變。然而,基底和視域絕不能混淆,因為只有在區分的情況下,對立的意義領域才各自成立。區分意味着,生活世界是差異形式而非實體,而維持這個區分的,只能是系統運作造成的交互觀察:人人都能使用區分進行觀察,而拒絕某一區分獨佔鰲頭,成為獨斷標準。
**交互觀察取代了交互主體性,日常生活的結構不再是主體間關係,而是所有觀察者——不一定是人,也可以是機構——的交互關係。**無形中,日常生活成為對全社會的描述,又因為這一描述出自社會本身,故而是全社會的自我描述。雖然是全社會在自我描述,但允許每個觀察者從自身角度提出自我描述。現在,真正能夠模擬不同觀察者和不同系統的全社會自我描述的,也只有大眾媒體了。因為,雖然哲學和藝術也渴望承擔這一社會反思的功能,但哲學和藝術有自身嚴格的專業要求,如果過分遷就讀者而放棄專業編碼,就成為大眾媒體的一部分了。
盧曼認為生活世界是系統運作而非主體共同行動的結果,他拒絕先驗分析,但也反對舒茨的自然態度。自然態度把日常生活世界看成理所當然:我與他人的交流可能,社會組織和文化的歷史給定性是不言自明的,正像你我的身體和意識生活是既成事實一樣。這些“理所當然”基於一個前提,即社會由自由個體組成,人們行動和互動,共同塑造一個有意義的社會世界。舒茨和胡塞爾都從主體角度來看待生活世界,只不過舒茨的立足點是經驗主體,面對面的我們關係決定了所有社會集體和制度化的關係。他們都認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的實在,由交互主體性的基礎結構產生了社會生活。説到底,自然態度也是一種抽象。舒茨心目中平等的面對面的我們關係,本身是一種理想化的主體間關係,正如哈貝馬斯的“共識”實際上源於無數其他社會關係的複雜作用。而盧曼把一切“自然”都看成不可思議,而社會的作用就在於把不可思議變成日常。主體和交互主體性並非自然的、給予的、奠基性的,是社會系統提供的交流網絡才將“人”變成了交流行動主體。對盧曼來説,生活世界無論作為基底還是視域,先驗領域還是自然態度下的日常生活,都是社會的產物,無須藉助主體這一虛構形象。

回到我們今天的問題,如果日常生活只是觀察和區分的伴隨效應,是一種寄居在社會運作中的最原初、最古老差異,熟悉/不熟悉就不可能專門化為某種特定區分,而如同德里達的“原文字”一樣可望而不可即。通向它的路徑就不應是現象學或社會學還原,而是對觀察和區分的“排演”。**今天的大眾媒體承擔了排演“日常生活”,創造“熟悉者”的任務。**媒體為社會供應其自我描述,這個描述有可能被政治系統採納而轉化為集體行動,但更多場合下,會作為一個商業化的傳媒產品加入各種社會描述的遊戲。日常生活也可能成為傳媒產品,根據不同語境,還衍生出情感、氛圍、格調、身體等更細分產品。盧曼的生活世界批判恰好能給所謂“情感轉向”提供一個社會學解釋:情感不屬於意識主體,但也不是實在客體,而是社會的新治理技術和社會創造的新媒介。同理,我們此處的“日常生活”討論可能也不觸及實體,更不影響時代走向,而恰恰是媒體掌握我們的方式,即也是社會技術。
**日常生活形式的運作本質上意味着諸多日常生活,因為只有日常生活對日常生活的更替和抵抗,才能製造日常生活的實在感。**而引入對日常生活的討論也是製造日常生活性實在的重要路徑,媒體以此方式為自己補充新鮮血液,通過加速更替的節奏留住讀者的注意目光。信息/非信息的交替取代了認知性的知識/客體區分,成為大眾媒體的系統符碼,而這就意味着,媒體隨時將信息變為非信息,為新的信息騰出空間。同時,媒體維持一個幻象,人人都可以加入二階觀察的遊戲,而不需要以哲學家或聖賢為準繩。如果二階觀察成為制度化網絡,就在媒體範圍內製造了日常生活。雖然無法達及實在的“先天本質”,但大眾媒體的優勢在於它從不要求共識。要得到日常生活,人們不用回到本真性,只需要都參與本真性的建構,而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以我的方式去設想日常生活,同時也知道他人有自己的設想日常生活的方式。
**大眾媒體制造“日常生活”,是為了激擾日常的日常生活,激活被工具理性壓制的意義流通,因為功能導向的現代社會最缺乏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不是讓社會返璞歸真,恰恰相反,它要打破人們的規定性預期,提高社會的複雜性和可激擾性。大眾媒體的日常生活排演不只提供美好的現代童話,以基底和視域的統一來安慰大眾,還要引入意外和偶然,製造聳人聽聞的預言如環境和倫理災難。由此,熟悉/不熟悉的生動區分才能恢復,躲在固定範疇之內的社會才能重新直面當代的不熟悉者,那就是無處不在的未來風險:理性決策和技術進步本身帶來的不確定性、偶然性。一句話,生活世界即風險世界。反之,先驗理性力圖消除世界的不確定性,讓所有不熟悉者合併入熟悉領域,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本身就是風險之源。
確認日常生活的建構特性,對今天的中國人有什麼用處呢?須知,**日常生活的改變就是社會整體的改變。**20世紀末已有學者提出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課題,試圖通過生活方式的改變實現人自身的現代化,建構現代化的“日常生活”,實現“以‘天人合一’為基本精神的中國傳統的自然主義宗法文化向以科學理性和人本精神為主要內涵的現代文化轉型”。然而,盧曼“犬儒主義”式的概念重釋恰恰讓我們警惕“批判”這一啓蒙理念。日常生活批判本身是個悖論:脱離了日常生活的先驗主體才能批判日常生活。“批判重建”的主體哲學思維內,隱藏着一個真假日常生活的本體論區分,真的日常生活代表理性的普遍性去糾正日常的日常生活。如果“日常生活”是作為系統的大眾媒體的發明,那麼,這一區分就失效了,因為它無關於理性,而只是媒體特有的工作方式。盧曼意義上的“日常生活”是社會運作的一個必然環節,沒有主體,也沒有先驗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