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輝 | 情感的三重隱喻:流、機器與儀式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1分钟前
姜宇輝|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12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姜宇輝
**思考情感,固然可以且理應從概念或歷史來入手,但也不妨以隱喻作為引線。**隱喻,或許不如概念那般嚴謹而準確,亦不如歷史那般往往有着清晰可辨的脈絡,但就情感研究而言,它至少具有三個優勢。其一,它可以如萊可夫與約翰遜所謂的那般指向我們“賴以生存”的在世根基,進而更為貼近日常的生活,也更能反映時代的脈搏。其二,它更可以被視作一種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中所闡釋的“思想-形象”,進而揭示諸多代表性的學者及流派所默認但卻未嘗明示和明辨的前提。其三,隱喻還存在着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優點,就是具有發散性和拓展性,由此常常能夠為思考與研究打開豐富而未知的方向。而流、機器與儀式就是這樣三個我們賴以思考情感的關鍵而基礎的隱喻,它們形態各異,但又密切相關。流與機器形成明顯的對照乃至對峙,而儀式又在二者之間中介與斡旋,進而或許敞開了第三條不同的路徑。
那就先從情感之“流”來説。**這不僅從學理上指涉目前最為主流的“情動轉向”,而且其實也頗為符合我們對於情感的最為通常的理解與暗示。如果被問起“情感是什麼”這個話題,相信很多人都會用“流”這個形象來比擬。這個流不一定是迅疾的(如憤怒),也可以是安靜的(比如愜意);不一定是膚淺的(比如快感),也可以深不可測(比如冥想)。但無論怎樣,它總是連續的,充滿強度的,而且帶着生生不息的創造性變化。若再簡單一點來概括,可以説情感之流總是一個過程,體現出不可計算的力量,而且每每能推陳出新,甚至打開生命的未知方向與格局。**我們在生活裏經常用來表達和描繪情感的話語莫不如此。比如,因為情感是一個流動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所以人們會説被某種情感“裹挾着”“推着走”“捲入情感的漩渦”等。又比如,因為情感具有起伏不定、來去莫測的特徵,所以我們經常會説一種情感“驟然間降臨”“像被閃電擊中”“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等。此種形態的情感不僅難以被計算,更是幾乎不可被掌控。深陷情感之流中的人,總是有強烈的“忘我”甚至“無我”的體驗。再比如,因為情感是一個“創造進化”的運動,它總是能夠在我們的心靈之中留下至為深刻、難以磨滅的痕跡。每有一次重大的人生轉折,似乎都有某種鮮明而刻骨銘心的“情感記憶”作為背景和基調。喜怒哀樂,就像是生命之流這部交響曲中隱藏但卻根本的節奏。
當然,德勒茲所謂的“情動”帶有明顯的逾越人類中心(impersonal)甚至超越生命範域(inorganic)的特徵,這似乎與平常人用情感來體驗生命、確證自我的基本樣態有些對立。但其實遠非如此。德勒茲與斯賓諾莎的“情動”,絕對不是對人的削弱甚至貶低,反倒是試圖給人的生存和生命提供一個更強的本體論前提。生命何以生生不息,不斷創造?生命何以能夠推動自我邁向更大更高的境界?情感/情動顯然是一個關鍵的動力。一句話,情動是對人的提升、擴展和增強,而絕非否定、還原與削弱。匯入情動之流、融入Conatus(努力)之運動的人類個體,最終才能在斯賓諾莎的意義上實現從束縛(bondage)向自由的躍變。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體會也並無二致。固然,情感也經常具有內向的特徵,我們也有時喜歡一個人默默地品味內心的情感之流。但實際上,在更為通常的狀態下,一旦將情感從隱喻的角度描繪為流,那麼,它註定就將在不斷的生成和流變的過程中突破既定的邊界,實現人與人,個體與個體,乃至自我與宇宙的密切交融。情感是紐帶,是動力,是場域,似乎只有經由情感才能真正凝聚起各種形態的人類共同體。正是因為情感首先是流,甚至本質上是流,它的流動,帶動着自我,也突破着自我,讓每個“我”融入“我們”。

電影《我,機器人》
但社會場域本是多元的聚合體,日常生活也是各種異質性要素和力量的不斷交織。即便人們通常傾向於在日常生活中將情感描繪為、體驗作“流”,但仍存在着各種別樣的情感隱喻與之對峙,形成抗衡和紛爭。科學往往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反常識的力量或體制。**如果説情感的常識性隱喻是“流”,那麼,當代在科學界盛行的主流情感隱喻恰恰是“機器”。**各種情感模擬、情感計算,甚至情感設計、情感工程(emotioneering)等主流的情感科學的默認前提似乎都可以追溯至馬文·明斯基那部開創性、奠基性的名作《情感機器》。那麼,流與機器真的有那麼大的差異嗎?德勒茲自己不是也以“慾望機器”這個原創的概念將生命之流變與機器之操作(operation)結合在一起?況且,從隱喻形象上來看,今天的機器早已與蒸汽機時代大相徑庭,不再笨重和龐大,而變得愈發的輕盈、光滑,甚至微觀而匿形。明斯基在這本書裏開篇談論的機器似乎也正是這樣一個形象。當他用“手提箱”這個關鍵詞來拓展和修正人們日常對於情感的狹隘理解時,由此得出的關於情感機器的界定更為接近今天的人工智能與數字網絡:“每一種主要的‘情感狀態’都是因為激活了一些資源,同時關閉了另外一些資源 —— 大腦的運行方式由此改變了。”
然而,這只是相當表面的印象。在這背後,是情感機器與情感之流的諸多根本差異。首先,科學工作的旨歸顯然與德勒茲式的生命主義存在不小的差距。科學追求的是真理,描繪的是客觀世界的根本規律,並由此通過測量和計算的方式去不斷積累、掌握對生活與生產有所助益的知識。在科學家們看來,本不必、似乎也不可能將情感和情動視作生命的根本動力,萬物的創造本源。情感對於科學研究來説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是人們用以增強智能的思維方式”。大腦從根本上來説是一部思維的機器,而思維的根本目的是掌握知識,思維的根本方式是合乎法則的推理與計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情感僅是組裝大腦這部思維機器的重要紐帶、關鍵黏合劑,卻遠非根本,更談不上歸宿。**也正是因此,當有人質問明斯基,為何他一定堅持要引入那麼多的層次,而不能索性就將大腦視作一個網絡,他的回答也很明確:網絡太過動態發散,缺乏穩定性,也很難形成明確的方向與秩序,由此就會導致各種難以根除的偶發狀況乃至錯誤、失調,而這些恰恰是科學研究的大敵。
一個很有説服力的例證正是明斯基談到了“苦痛”這種典型的負面的否定性(negative)情感。如果説快感在生命進化中往往起到推動的作用,因為它是生物對於自身的積極肯定,那麼,苦痛所起到的作用亦同樣根本。正是經由痛苦,我們才能清醒、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困境和癥結,以及外部環境對我們自身所施加的各種影響與限制。當然,從《尼采與哲學》的角度來看,苦痛作為生命對於自身的否定,總會導致削弱、貶低生命力的惡果,因而很大程度上僅能被視作生命創造與生成中的過渡性、轉換性環節。而到了列維納斯和米歇爾·亨利這樣的哲學家那裏,情感體驗的否定性維度轉而被突出強調,進而打開了另外一條不同的路徑。但我們不難發現,至少就對待苦痛的態度而言,德勒茲的“流”與明斯基的“機器”達成了相當的默契。雖然“流”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擴展的網絡,而機器則是一個相對層次鮮明的系統,勢必層層修正,處處設防,但對這兩個典型的情感隱喻來説,否定性都是一個必須直面、全力抵禦的頑疾。對於德勒茲,苦痛削弱了生命力,而對於明斯基,苦痛影響了思維繫統的正常運作。而且,他們最終的解決方式也極為近似:對於德勒茲,苦痛只是暫時狀態,因為生生不息的創造進化必然會超越克服每一個障礙,每一次低谷;對於明斯基,苦痛也只是局部的失調,因為自我監控、自我調節和組裝的智能機器必然會一次次地復歸和諧和正常,維繫穩定,在進化的途程上堅定前行。也正因此,契克森米哈賴(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宇宙自我,最終會將快樂與幸福作為根本的訴求;明斯基也同樣如此,因為他在全書的最後也同樣將“為什麼我們喜歡快樂”視作根本的問題。
**生命之流與智能之機器,固然有着鮮明的差異,但對於肯定性的高揚,對於否定性的拒斥,最終將看似對峙的這兩極匯聚在一起。**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所提出的可塑性(plasticity)這個大腦模型堪稱是從否定性的角度發出的最摧枯拉朽的呼聲。生命為何一定要肯定自身,而不是以自我否定作為根本的存在與運動的方式?大腦為何一定要自我組裝,而不能以一次次徹底的自我破壞、自身解體作為新生動力?這些看起來離經叛道的論調,卻是馬拉布多年以來從黑格爾和海德格爾那裏悟出的根本真諦。她由此揭示出可塑性的兩個不同面向。一方面,它更傾向於肯定性,指向大腦機器在不斷生長的過程之中所展現出的強大適應力和自我調控的能力,無論面臨怎樣的外來內在的影響乃至破壞,都能一次次復歸和諧與穩定。但另一方面,它更是對黑格爾的辯證法中的否定性這個關鍵環節的極端化推進,進而將連續性的中斷、結構的瓦解、機器的碎裂視作所謂“爆裂式可塑性”(explosive plasticity)的根本特徵。
而“儀式”正是這樣一個為人忽視但卻很值得深思的隱喻。談到情感儀式,首先必須提及的當然是蘭德爾·柯林斯的那本影響甚大的名著《互動儀式鏈》。但其實,僅就柯林斯在其中的相關論述而言,似乎並沒有多少我們意在彰顯的否定性意味。比如,他的這個總結性論斷就很能説明問題:“我們可以利用貫穿情境的情感流作為微觀之間聯繫的關鍵因素,這使微觀關聯又進一步與宏觀模型聯結起來。”顯然,“情感流”“情感能量”這樣的語彙與第一種隱喻極為切近,但反過來説,全書隨處可見的層級結構和模型又展現出與第二種隱喻的密切關係。因此,説柯林斯的儀式意在流和機器,網絡與樹形之間尋找一條折中乃至綜合的路線,這即便並非其本意,卻也頗契合本文給出的三重隱喻的基本框架。然而,即便《互動儀式鏈》的基本傾向還是肯定性的,但其中着重援引的最為關鍵的一個思想資源多少透露出一絲否定性的意味。那正是戈夫曼及其表演理論。情感是一種儀式,而儀式的重要特徵正是參與者皆為戴着面具的表演者。本色出演,往往會破壞儀式的氛圍,只有每個人讓渡但又同時隱藏一部分自我,才能讓整個儀式順暢運轉。固然,戈夫曼在諸多論著中也每每談到各種有意無意破壞表演儀式的舉止,比如欺騙、背叛甚至誤估等,但前台與後台,面具與真身之間的不可還原、縮減的差異,始終是情感表演和儀式的重要前提。而否定性也正是發生在這個根本的差異和間距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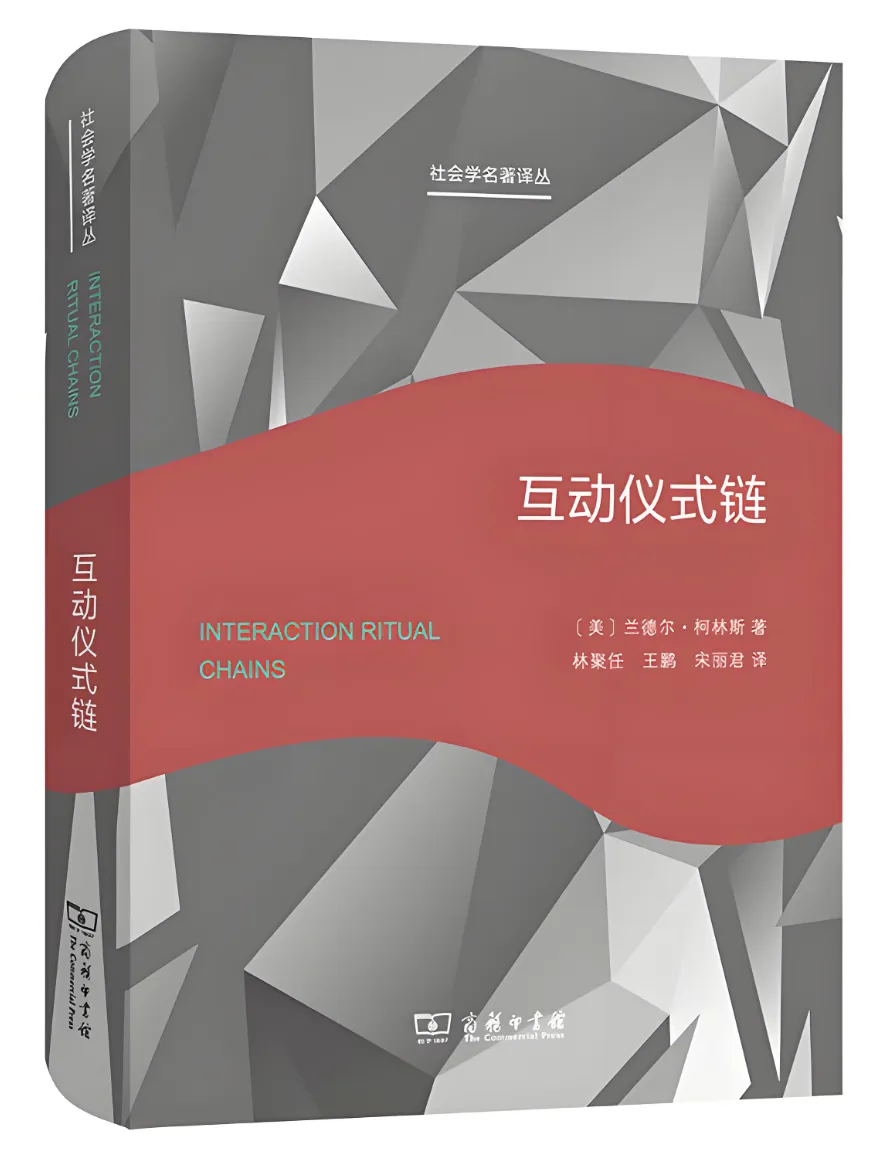
結合前文的論述,固然不妨將情感視作生命之流、思維之機器,但這兩種基本隱喻都忽略了“情境”這個重要的因素。“情境而不是個人作為出發點”,戈夫曼的這個原初洞見在今天仍然具有啓示作用和指導意義。當生命流、情感流在不同的情境之間流轉之時,當情感機器帶着自己的層化結構進入充滿偶發與未知的情境之際,單純的哲學之思辨和科學之計算都不再充分,而顯然需要引入社會學乃至人類學的介入性的立場、實地考察的方法和自我反思的態度。情感作為隱喻,並非僅是一個哲學的框架、認知的模式,而更是人與人之間日常交互的根本紐帶,我們帶着情感去對面他人,也同樣帶着情感去展開研究和思考。情感這個“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在這裏展現出更為切實的行動乃至互動的意味。這一番理論的思考也必然會與中國人當下的情感生活與情感狀態發生密切關聯,不妨仍從這三個隱喻着手來進行反思,並着眼於否定性這個關鍵環節。
**首先,情感作為流,不僅是中國人的日常所感,更是有着遠比西方文化更為清晰而源遠流長的歷史脈絡。**將“情”置於基礎乃至本源,對於古代的中國文人,似乎向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並不需要大費周章地去進行何種“轉向”。從“氣韻生動”的美學精神,到近現代美學家們(尤以宗白華、方東美為代表)對西洋哲學中的生命概念的持續熱情,都是此種情感之流的承續。尼采和柏格森在中國的思想與文化領域所掀起的一陣陣熱潮,亦為明證。但在這個肯定性的主流之外,也總有否定性的潛流在積蓄,在湧動。伴隨着鴉片戰爭以來的東西方文明衝突之加劇,在這個充滿血淚和創傷的歷史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文人開始將否定性的情感體驗作為反思自身、重思文化的根本契機。王國維對叔本華的酷愛,以及他那句刻骨銘心的箴言“以生活為爐,以苦痛為碳,而鑄其解脱之鼎”,或許並非只是私情流露,而更是透露出時代的悸動。然而,關注這個否定性線索,由此用別樣的眼光反觀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這個頗有價值和意義的研究工作迄今還鮮有人真正開始進行。這也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伴隨着數字時代的全面降臨,人類世的極限界檻不斷迫近,或許會再度激發中國文化內在的此種苦痛之情和否定性之思。
**其次,就情感儀式而言,這本也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甚至不妨説,戈夫曼的諸多看似離經叛道的闡釋,若放在中國社會的語境之下,反倒顯得更為順理成章。然而,伴隨着整個世界從實在向虛擬的轉化,人類的情感儀式也越來越頻繁地開始轉入數字空間繼續上演,而在這個過程中,註定會發生很多陣痛乃至危機。著名數字人類學家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所深入剖析的“數字自戀”正是數字化情感交際中註定會面臨的一個頑疾。雖然,特克爾對美國幾代兒童的情感生活之轉變的實地考察不宜被原封不動地照搬進中國的語境,不過,在數字浪潮的席捲之下,東西方人類情感所面臨的難題或許確實存在明顯的共通。數字自戀是一種惡性循環,它源自內在自我的空洞、主體性的崩塌,因此就需要由外部的虛擬的數據和信息來“填補”內心的無底深淵。越交際反而越迷失,越連接反而越孤獨,正是數字自戀的鮮明症狀。而日漸全面轉入互聯網和數字生活的中國的年輕世代,也註定要直面這個根本的難題。如何在數字情感之中探尋自我,如何在數字親密中保持本真,這些都是數字自戀在主體與面具之間撕裂開的難以癒合的否定性傷口。
**再次,儘管在中國傳統的情感文化中似乎少見“機器”這樣的隱喻,但伴隨着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不斷取得突破性成果,情感的機器化、智能化、計算化似乎愈發成為當下中國人情感生活的基調。**聊天機器人、虛擬偶像、戀愛遊戲等,早已成為中國年輕人生活中相當重要的情感體驗。由此也就自然會引發此種並非杞人憂天的焦慮:也許無需多少時日,年輕人會更喜歡跟機器人而非真人談情説愛,吐露衷腸。這其中除了涉及數字自戀等精神政治的話題之外,也同樣需要從AI技術自身的角度來進行一番重思。人工智能的目的、使命和未來到底何在?它固然已經不侷限於對人類智能進行單純的附隨性的模擬,然而,在新一代的生成式AI的飛速發展過程之中,對人類生命的關切也同樣理應是一個根本旨歸。這已經不只關涉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生活,而更是對整個人類都具有普遍意義的一個難題。在一個人造生命(artificial life)的時代,在一個生命進入3.0版本的時代,重審AI與人類的死亡與重生的密切關係,這正是情感之思的另一重迫切的否定性意味。

那麼,為何情感的隱喻只有、只能有三種呢?也許我們更應該積極介入到情感的儀式和遊戲之中,傾情表演,盡情創造,去探尋情感的更多隱喻的面向。這,或許才是未來人類的情感生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