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汀陽 | 想象一種新啓蒙:動詞思維與無限圖書館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1小时前
趙汀陽|國家文科一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5年第1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趙汀陽教授
失去未來的現代性
董仲舒提出過一種歷史哲學,聲稱“天不變,道亦不變”。變天難得一見,不過當代人就在目睹難以置信的變天事件,即由技術發展所引發的存在論級別的革命。人工智能、生物技術、量子計算等高科技將改變人類的存在方式乃至存在本身。技術正以唯物主義的力量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人類對此的唯心主義回應卻顯得頗為乏力,主要症狀表現為對未來的厭惡或試圖規避未來,既無法拒絕“變天”,又不願意“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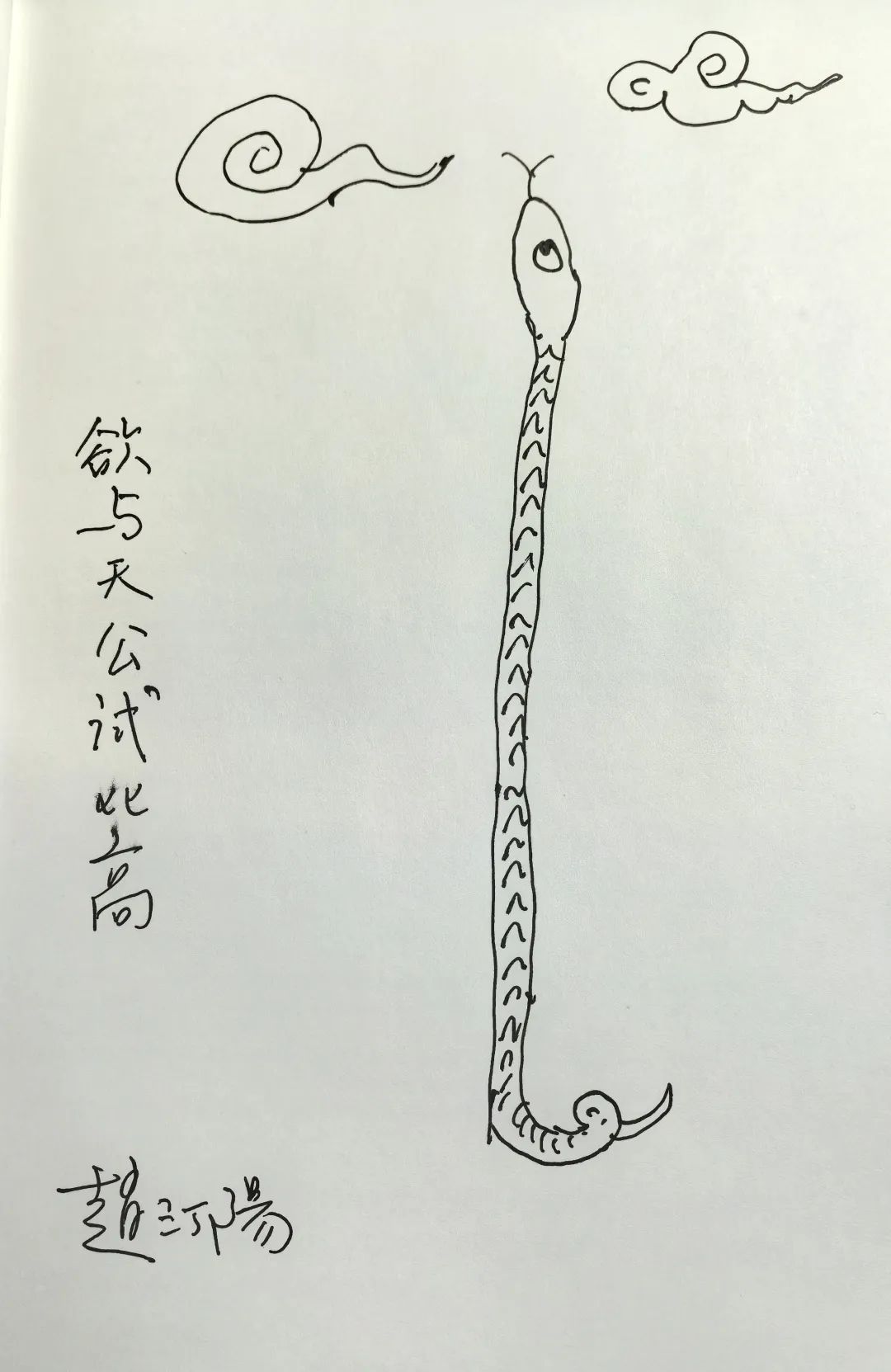
圖:欲與天公試比高
by趙汀陽
神學化的古代“變天”概念可重新定義為能夠科學分析的“存在論事件”(ontological event),或可近似地理解為歷史奇點(singularity)。奇點是科學概念,這裏比喻地用於人文世界,但不完全等同。變天之説可能是關於歷史奇點的最早直觀説法。**具有“變天”效果的存在論事件會改變文明的性質,不僅會連鎖地改變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事物的存在關係,甚至可能改變意識和人性乃至生命本身。**一旦發生導致歷史奇點的存在論事件,就意味着文明進入一種新的歷史性階段。
只要開啓某種新的歷史性,就會許諾某種未來。這説明未來正是歷史意義之所在。**歷史性是關於時間的建構,即以某種演化方式或模式去定義歷史時間,簡而言之,是“化時間為歷史”的創作。**Francois Hartog的理解最為切中要害:歷史性是時間觀的體制(régime)。正如Hartog所發現的,古代人的歷史性體制以“過去”為本,現代人的歷史性體制以“未來”為準,當代人的歷史性體制則只見“當下”。一旦時間概念收縮為當下,就必定失去過去和未來,歷史性萎縮為瞬間,也就容不下歷史了。因此,當代的歷史性體制在實質上是反歷史的。在一次討論中,我問Hartog:如果失去過去和未來概念,又如何能夠書寫歷史?他給出了意味深長的回答:現在就已經不知道如何書寫歷史了,只好談論歷史的概念。
歷史否定自身的一個重要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包括本雅明和茨威格在內的一些思想家(估計還有不少,只是我沒有讀到)不約而同地敏感地指出,一戰是歐洲歷史時間的一個轉折點,其嚴重性就在於現代歷史性對自身的否定,現代理想和價值變得可疑,於是歐洲陷入了難以恢復的精神迷茫,以至於再也沒有“給人教益的故事”可講了,現代性失語了。接下來的歐洲時間不僅失去故事,而且失去了未來感。一旦思想倒映為事實,就真的失去未來。歐洲的歷史時間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歐洲發明的現代性尤其是啓蒙思想在很長時間裏決定了全世界的歷史時間,而且現代性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世界歷史性體制。因此,歐洲不僅是一個地方,同時是一個普遍歷史概念。也有人認為二戰才是歷史轉折點,也有道理,但對於歐洲,二戰只是對一戰危機的再確認。對於美國,二戰確實是轉折點,開啓了光榮偉大的歷史時間,同時,世界許多“其他地方”也進入了獨立發展的歷史時間。可見,各地的歷史時間既不同步也不一致。美國的榮耀歷史時間在冷戰後達到頂點,以至於福山過於急切地宣稱“歷史的終結”。在歐洲因精神迷茫而失去未來感的時代,美國卻獲得了趾高氣揚的未來感。不過,美國想象的未來概念並不是一個普遍歷史概念,而是屬於美國自己的未來。這個未來概念意味着美國成為世界的主人但不與別的地方分享未來,這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最多是其他地方的歷史終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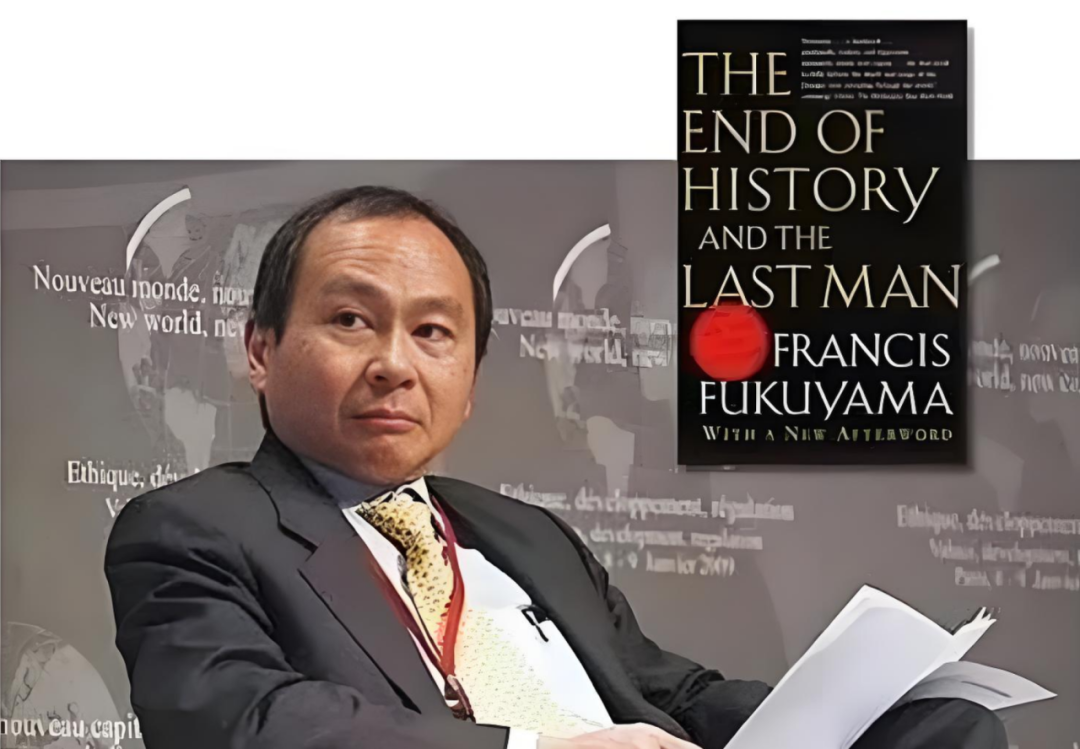
弗朗西斯•福山及其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往事是歷史的對象,未來才是歷史的意義所在。**如果失去未來,歷史就失去全部意義,包括確鑿無疑的過去也變成無意義的記錄,只是科學研究的對象,類似恐龍。可見,歷史的第一關鍵詞是未來。一旦歷史性失去未來性,就只剩下無意義的複製。本來各地都有自己的歷史性和未來概念,但現代性、全球化尤其是數字技術強行實現了歷史時間的大一統。簡而言之,普遍化和系統化的技術統一了時間。各地的歷史時間雖仍然參差不齊,但通過與技術“對錶”而似乎在當代匯合對齊了,形成世界“同此涼熱”的普遍歷史時間。正如Hartog所發現的,收縮為當下瞬間的當下主義(presentism)已不可阻擋地成為當代世界的普遍時間體制。這個事實的嚴重性在於世界在當代一起失去了未來概念而陷入精神迷茫——未來總要來到,但並非人們想去的時空。物理存在不需要未來性,重複或循環或偶然演化就是存在。然而,**文明的存在卻在於非重複的未來,必須通過創造未來去生成存在的意義。**因此,失去未來概念是文明的深度危機。
悖謬的是,失去未來的危機卻是渴望未來的現代性藴含的結果。在現代性開啓了似乎前途無量的未來之時,就悖論性地悄悄藴含了未來概念的終結。那不是從此處於穩定均衡的歷史終結,而是人類的自我否定。現代性藴含着一個內在秘密:主體性能夠創造強於主體性的事物。不過,在現代早期,人的主體性強於制度和技術,自由強於約束,未來呈現無限分叉的可能路徑。一旦人類創造了強於主體性的制度和技術,未來就變成不斷收斂的扇面,自由就受制於制度和技術所指定的、用來實現制度和技術自身功能的有限可能性。於是,不可測的未來湧現就被制度和技術強制地收斂為可控的因果關係。**當因果性取代了不確定的未來性,未來就不再是未來,而是按時到達的現在。**就觀察效果而言,相當於重複或循環。
如此抽象分析也許不夠“驚悚”。通常説到制度就容易想到政治體制或法律之類,這些規則性的制度可以修改,可以革命,還可以在靈活的制度實踐中去解構或逃避制度(如鑽制度空子之類)。這樣想來,問題的嚴重性就減弱了。但需要提醒的是,技術也是制度,而且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那麼,問題就變得更加嚴重了,乃至於觸及存在本身。技術就是革命,技術革命的結果還是技術統治,卻不是可以被推翻的制度。因此,**技術是規定了生活方式而無法規避的秩序,甚至是人類在主觀上也不願意拒絕的秩序(技術提供了人們想要的一切服務)。**於是,技術的力量超越了社會批判(批判是白費力)而構成人類的一種存在論條件。技術與存在疊加合一的事實使得對技術的海德格爾式批判是無效的,就像人不能舉起自身。技術與存在的合一意味着人類必須出賣自由去兑換生存可能性的最大化,直白地説,以自由換福利。儘管個別人願意以“詩意的棲居”去拒絕技術,但這種個人行為沒有改變人類的命運。人類作為種羣一定會選擇技術化的生存。
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湧現之前,人類的技術化生存尚未真正形成挑戰性的問題,至少尚未危及存在本身。即使有了恐怖的核武器,其在原則上仍然是可控的。確切地説,在人工智能突破奇點之前,人類仍然保有作為自由選項的可能未來,也就保有最後的自由。人工智能奇點的呼聲有些近似“狼來了”——人工智能確實還有一時難以突破的侷限性,如概念理解、邏輯推理、因果推論、創造性和自反性(reflexivity,自我意識的機制),但奇點突破恐怕是遲早的事情。即使無法達到奇點,人工智能也永遠不會超越人類而成為最高統治者,在“安全的”人工智能率領下的大規模技術系統將支配整個生活,形成存在與技術全面合一的生活形式。那將開啓一個比“人類世”更新的新紀元,比如“AI世”。由人工智能替人選擇的未來將否定未來的概念:預定的未來不再是未來。失去未來的概念肯定是文明將遇到的最深刻危機。失去自由的未來意味着未來的概念變性為“沒有未來性的未來”(future without futurity)。
自然意義上的未來,即作為自然流程而源源不斷到達的“下一步”,就是一種沒有未來性的未來。此種未來沒有意向性,沒有承載任何意義或願景,這一步與下一步並無實質差異。雖然物是人非足以引起文學感慨,但連續的下一步所表示的時間本身無變化(不變的時間其實是一種形而上學假設)。因此,“自然連續統”(似可映射為數學的連續統)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只是重複的流逝,沒有歷史刻度。與此不同,文明是不自然的。文明的本質在於化時間為歷史,文明創造了不同於自然時間的歷史時間。於是,未來有了未來性,意味着未來的自由度,意味着對未來的創造性想象,未必能夠實現,但為未來賦予意義。因此,未來性也可理解為未來的意義附加值。此種屬於文明的“具有未來性的未來”起源於農耕。農耕最早創造了可預期的未來。甲骨文的“來”字原型是麥子,麥子預期了未來的收穫,麥子就是具有未來性的未來。可以説,未來性是人類主體性的初始作品,自由的未來是文明的本源。失去未來就是失去本源。

**當代世界的文明危機就是由於失去了未來,並非歷史的終結(因為並沒有達到什麼最終目的),只是未來的概念退化為沒有未來性的未來,這是一種重新蠻荒化。**自然時間繼續,但接下來的事情恐怕不再是人類主體性的故事,不是人類創造的歷史時間。在未來,人類恐怕不再是歷史主體,實際上現在人類就只剩下半個主體性了。人類創造的技術系統已經成為異化系統,意味着人類作繭自縛地創造了規定自身生活的外在系統。但人類卻沒有理由反對技術,因為正是技術使人類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技術化的生活卻悖論性地否定了人類。目前的技術系統只是異化,尚未形成異己的主體性。這是需要反思的時刻。然而,情況似乎相反。在這個可能發生文明奇點的時代,世界卻失去了與之同步的思想。更多的人希望新現實能夠裝進舊觀念的瓶子裏。可問題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變了,路徑依賴的思想沒有用,舊觀念失效了。無論人們多麼愛惜啓蒙建立的人類中心觀念而依依不捨,比人的主體性更強大的系統化現實以事實證明,啓蒙以來的現代觀念和價值已經文不對題了。
一個例子是,人們未雨綢繆地討論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對齊問題,大都要求人工智能向人看齊,學會人的價值觀,而且是人類中心價值觀。“向人看齊”的想法顯然一廂情願且不得要領。假如人工智能獲得完全自主的主體性以及比人類更強更高的心靈,那憑什麼向人看齊?外星人至今只是個假設(估計外星人沒有能力來到地球,即使能夠到達,來的也是掌握了宇宙量子聯絡的外星人工智能)。但可以類比:代表了更高心靈的外星智能會向人看齊嗎?所以,假如需要看齊,恐怕也是人反過來向人工智能看齊。
人類不願思考的時候,未來的人工智能就要代替人類去思考了。這會出現存在論換位(onto logical transposition):人工智能將代替人類成為思想主體,而人類變成人工智能的忠實用户。人類一直為主體性而自豪,其實人尚未形成完全自主的主體性,比如與康德想象的“啓蒙了的”主體性就有着很大差距。然而,人工智能卻可能要超車成為新主體了,這種可能性有着不小的成功概率。未來世界很可能形成跨物種的“雙主體”格局,而且人工智能將強過人而成為超越的主體,不需要人類假惺惺地為動物頒發的那種“動物權利”。
現代之前只有一個純屬想象的絕對主體——上帝或神。現代性是個偉大的計劃,試圖使人變成主體。**主體性計劃的主導思想是啓蒙觀念,確定了以個人作為思想、權利和價值的主體單位,結果是產生了人類內部的複數主體,即物種內的多個主體。**複數主體之間互相沖突的利益、價值和知識使每個人互相構成負面外部性(霍布斯狀態),產生了人類獨有的主體間性及其永遠的難題,可以概括為“他人不同意”。這個難題不奇怪,奇怪的是,被假定為普遍有效的主體性原則卻居然並不必然藴含解決主體間分歧和衝突的方法,或者説,主體性原則推不出主體間的合作方法,更簡化地説,理性推不出合作原則,這就很反諷了,具體情況更加反諷,比如理性博弈推出非合作結果(納什理論),或個人理性的加總不能推出集體理性(更多的情況是產生集體非理性)。許多偉大哲學家的努力都失敗了,包括著名的康德倫理方案(絕對命令)和政治方案(永久和平),試圖為康德補漏的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方案,試圖藉助博弈論算法來建構公正的羅爾斯方案,以及其他種種修補性的方案。所有這些方案的共同弱點是:由啓蒙思想奠定的主體性概念無法推出一種理性必然的方法,使得某種合理的主體間關係成為每個主體的最優選擇,除非設定每個主體都是全等的抽象人(但這種不真實的設定實際上沒有意義,如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這個不合理的事實提示了現代的主體性概念有着根本缺陷。事實也表明,啓蒙以來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沒有能力解決人們在利益、價值和知識上的衝突和分裂。
啓蒙運動的理想是崇高的,但其能量已近乎枯竭,猶如衰老的恆星。老問題依舊存在,新問題不斷升級,而思想卻久未革新。據説,物理學自二戰以來未有根本性突破,哲學亦是如此。未來的世界很可能需要在跨物種的多主體條件下,建立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共主體性(con-subjectivity),以及多種文明之間的跨主體性(trans-subjectivity,這一概念源自人類學家Alain Le Pichon)。這是無法迴避的新問題。古代人生活在各自的羣體中,羣體內部有着共同的價值觀,即所謂的共識。甚至可以説,古代世界裏幾乎所有羣體都擁有通用的價值觀,至少有着高度相似的道德第一原則(Hans Kung的調查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在古代,尚未出現需要建立共主體性或跨主體性的情況,因此,這一問題具有歷史性。如前所述,當代世界的未來概念已退化為坐等事情發生的“沒有未來性的未來”。原本充滿未來感的啓蒙思想,已無法詮釋未來,因此,我們需要能夠重構未來概念的新啓蒙。
另一種哲學視域
如果能夠有新啓蒙,它應當是從思想到制度的系統化革命。我無力構想一個全面的革命圖景,只能想象以另一種哲學去反思一切問題,這甚至比尼采提出的“重估一切價值”更為激進,但思想形勢如此,我們不得不激進。
新啓蒙需要的反思線索很長,可能需要追根溯源地延伸到文明早期對思想的基本設置。需要反思的層次也很深,可能需要對思想的元語言進行反思。啓蒙運動專注於建立替代神學的另一種“神學性的”人類主體性,即試圖以新神學取代舊神學。這一過於專注的目標限制了對思想本身的深入反思與重構,它急於運用傳統的理性概念(基本上未超出亞里士多德的視野)去證明理性能夠詮釋一切思想,這顯然低估了思想的複雜性;同時,它又急於以人為本去界定所有價值,從而低估了人的侷限性。以事後之見來看,休謨的懷疑論、萊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論、維科的歷史循環論以及中世紀的存在論,或許比啓蒙的主體論和理性主義觸及了更為深刻的哲學議題。
當代社會似乎已遠離了啓蒙思想,卻又缺乏新哲學。這或許是因為當代人對信息的興趣遠勝於對思想的興趣,試圖以數據化的知識來替代哲學。據説,破碎的現實導致了人們對“宏大敍事”的不信任。然而,以知識替代哲學卻是一個知識論謬誤(epistemological fallacy),它如同迴旋鏢般擊中了知識自身。因為所有知識(不僅限於經驗知識,甚至包括數學和邏輯)都基於某些形而上學的概念,而這些概念純屬假設,如無窮性、因果性、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整體性、連續性、斷裂、實體、存在、事物、本質、真理等形而上學概念。甚至,分類學和邏輯學的所有概念都是人類強加於事物的形而上假設。嚴格來説,除了專名,所有的名詞都是形而上學。即使有經驗外延,名詞本身所表達的共相也屬於超驗的形而上學。事實上,整個語言就是形而上學,語言本身就是最大的宏大敍事。在這個意義上,先驗論是正確的,所有知識和思想都需要先驗秩序的支撐。如果不使用形而上學的概念,就無法進行思維活動。
不過,大模型人工智能似乎對此提出了挑戰。ChatGPT等大模型採用的是貝葉斯經驗主義方法論,幾乎不需要先驗概念,僅需依賴經驗數據的相關性。儘管大模型人工智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更清晰地暴露了人工智能當前的侷限性,即缺乏概念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因果理解能力、創造性和思維的自反性。這同樣是一個迴旋鏢式的例證,説明了一種具備全功能的思維必須依賴形而上學的支持——至少人類思維是如此。至於外星人的思維是否需要哲學,這是個哲學懸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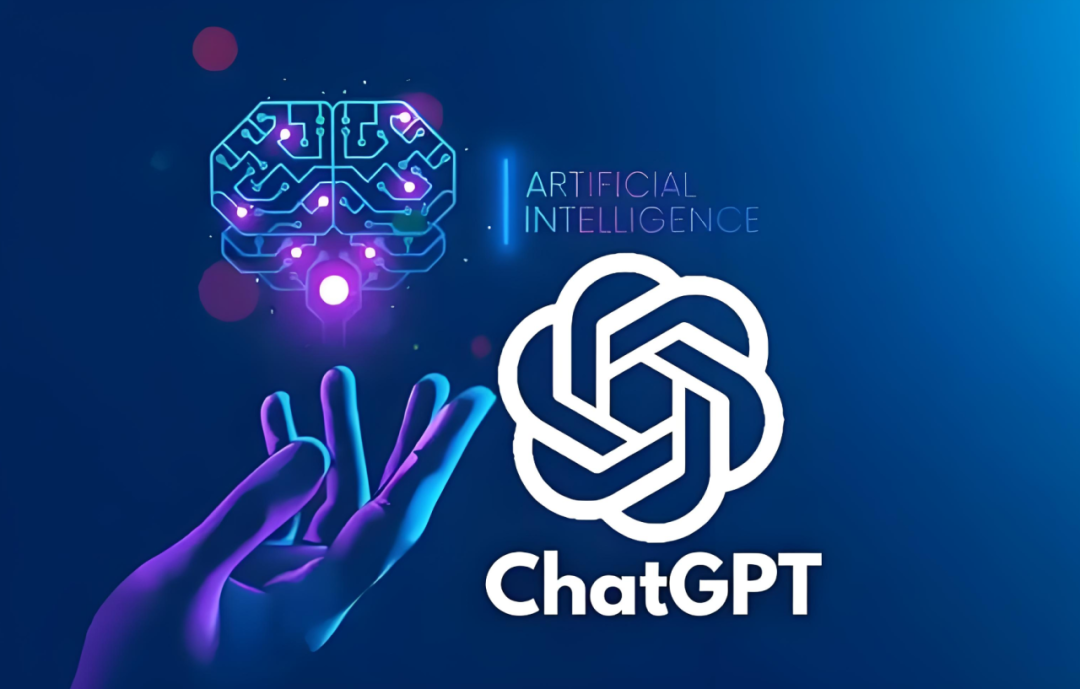
至少有一部分形而上學概念,即使不具備真值,也是思想不可或缺的“先驗軟件”。思想可以自反地(reflexively)證明某些形而上的概念確實是思維無法減省的條件和結構,康德的先驗論證便是一種自反證明。然而,思想的“先驗軟件”在應用於經驗數據時是否能必然產生普遍為真的結果,卻令人懷疑。一個例證是,看似無懈可擊的邏輯規律也並非普遍有效。例如,在潛無窮狀態下,排中律便失效了;在量子世界中,矛盾律以及排中律都不可信;假如存在多維時間世界(尚未證實),或在複數主體自由選擇的狀態下(這是現實情況),甚至連看似絕對可靠的同一律也會失去確定性。這意味着,最堅實的邏輯規律也並非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對於任何可能世界都是先驗為真的,它們僅僅是“我們的”思維規律,且只對某些可能世界為真。這説明了:(1)思想必定需要形而上學,放棄或反對形而上學是哲學自我貶低的錯誤;(2)形而上學的傳統設想,包括從亞里士多德直至當代的現象學形而上學或分析形而上學的傳統,僅是思想所需的一個形而上學維度,對於解釋更復雜或動態存在的問題就不夠用了。因此,思想需要增加新的形而上學維度來構建新視野,以便洞察在傳統哲學光譜之外被遺漏的事情。
傳統形而上學的侷限性直接體現為知識論的侷限性,僅進行修補無濟於事。問題在於形而上學和知識論需要維度升級,需要新座標、新視域和新方法。傳統形而上學及其知識論最突出的侷限性在於無力解釋存在的動態性、複雜性或湧現性,即當代複雜科學在思考的問題。複雜科學始於1984年成立的聖塔菲研究所,那裏的前沿科學家試圖開創科學的新概念,即“複雜科學”(complexity science),其研究對象是還原論無法解釋且概率論無法預測的所有事物,如意識、生命、大腦、智能、氣象、地震、城市、公司、國家等,其核心概念包括湧現、規模、系統、互動、突變等。複雜科學的方法論屬於理科範疇,於是它試圖將社會和文明事物也視為科學對象,這一點存在疑問。老實説,這仍然帶有科學主義的習慣,以為人文事物能夠還原為物理事實,比如試圖將意識和智能分析為大腦神經機制,雖有進展但顯然遺漏了某些重要方面。考慮到文明覆雜性具有不同於自然複雜性的存在條件,關於複雜性的研究就不能僅限於複雜科學,而應擴展到包括複雜科學和人文思想的“複雜知識”。
複雜知識的問題意識在於:(1)事物的整體效果無法由各部分之和來解釋,這意味着還原論的侷限性。然而,作為替代方案的整體論至今僅是一種洞見,尚未形成有效的操作方法,即缺乏與還原論同等技術水平的方法論。(2)不確定的動態會在無法預測的時間點上形成突變性的湧現,這意味着基於確定條件的邏輯推理或經驗相關性的建模都不足以解釋演化過程,對此也缺乏形成普遍有效解釋的方法論。(3)更復雜的問題來自意識和所有屬於文明範疇的事物。人類世界具有雙重不可測因素:不僅有着自然的複雜性,而且疊加了複數主體的自由意志、創造性以及不可測的選擇造成的複雜性。這意味着文明事實不可能還原為物理、化學或生物規律(儘管自然規律是其約束條件),甚至不可能完全還原為人類理性原理。人類知識中缺乏解釋非理性事實的方法論。顯然,複雜知識仍處於初步探索階段。甚至可以説,人類文明仍處於初級階段,還需要經歷多次啓蒙。
事實上,在啓蒙運動之前就已經發生過若干次更為深刻的啓蒙,如語言的發明、農耕的發明、文字的發明、政治制度的建立、邏輯和數學的建立、科學的建立等。作為專有名詞的“啓蒙運動”是歷次啓蒙中最為傲慢的一次。這種傲慢並不在於試圖解釋萬物,而在於構建了人類神聖化的主體性概念,使人類產生了遠超自身實際知識和道德水平的傲慢心態。
然而,恐怕還不能指望它能夠立即解決問題。具體而言,如果建立了另一種形而上學和多維知識論,就能夠獲得另一個思想維度去重估一切問題。當代思想之所以缺乏創造性的一個表現就是,當代思想運動對於重新評估價值的興趣遠大於重新評估問題。自現代以來,價值觀已被顛覆過多次(出現了太多的“主義”),卻並未解決或減少人類生活的任何難題。如果説有所增加的話,那反而是更多難題的出現。正如邏輯規律基本上都已被發現,人類價值也基本上被窮盡了。自從現代定義了以個體為終端單位的現代價值之後,就再也沒有發現新的價值了,只剩下價值排序的爭議。這意味着以價值定義的思想空間裏已經沒有多少餘地了。因此,新啓蒙只能是形而上學維度的革命。於是,新啓蒙的基礎工作是建立一種重新理解存在的形而上學。既然本源意味着開始,那麼思想要重新出發就必須為自身重建一個本源。
要建立另一種形而上學,我們需要考慮以下三個事實。**(1)萬物本身並不是按照分類學、概念系統和邏輯關係而存在的。也就是説,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分類學、概念系統和邏輯關係所設想的事物秩序並不存在,它們僅僅是思想的秩序。或者説,分類學、概念和邏輯並沒有言説存在,而是對思想內在關係的建構。因此,傳統形而上學只是思想的自白,從來不是揭示存在的存在論。這裏並不是要否定亞里士多德的絕世成就(邏輯學和分類學),而是要指出傳統形而上學無法表達存在。世界不是人類創造的(維科有定理:誰創造,誰知道),所以人類無法知曉世界本身。只有存在的跡象——即時間中的動態或動態顯示的時間——才是理解存在的路徑。動態存在(becoming)是存在(being)的唯一跡象,也是形而上學的唯一可信資源。(2)人類不僅是觀察者,也是創造者,是以創造為存在方式的存在。人類擁有自己創造的非自然世界,通常稱之為文明。文明的存在方式有別於自然世界。在其中,時間被轉換為歷史,或者説,時間性(temporality)轉換為歷史性(historicity),從而定義了不同於物理時間的歷史時間。能夠定義時間意味着能夠創造存在的另一種本源。人類創造的制度和技術定義了歷史時間,就意味着為存在開創了另一個本源,也意味着與上帝無關的另一種存在論和創世論。任何一種有意義的存在論與創世論必須是同一的。如果不能解釋創世性,就不能解釋本源性。傳統形而上學尋找關於存在本身的絕對概念,這是找錯了方向。因為關於存在的絕對概念對於創世毫無解釋力,也就對存在本身沒有説明。因此,存在論必須是“創世存在論”(creationology,區別於關於上帝的創世論creationism)。(3)人類世界具有獨立意識的複數主體,因此產生了自然界所沒有的主體間性。**這是人類世界獨特的存在狀態。主體間性首先是人類的一個存在論問題,然後才是知識論問題。
這三個出發點意味着,未來的形而上學不再去徒勞地研究絕對不變的存在本身(being),也不再妄圖成為萬物理論(這一點要聽從霍金的忠告),只能去研究動態的存在,去研究在人類的創世行為中反覆造成的本源狀態。或者説,傳統形而上學已經充分研究了名詞,現在需要另一種形而上學去研究動詞。
動詞要“奪權”
在量子力學興起之前的主流知識(涵蓋哲學與邏輯)所追求的理想,是發現必然性與確定性。這是一個名詞性的理想,它基本上依據亞里士多德式的“種加屬差”分類學或現代集合論來定位事物,並且以柏拉圖式的理念模式去形成關於事物的“理想化”封閉定義,同時它主要以還原論為分析方法去拆解和化簡對象,尤其是化經驗為數據以便進行概率分析。此外,它還運用形式化邏輯(包括亞里士多德邏輯與現代數理邏輯)作為構建手段,以形成命題關係及理論架構。假如具備更理想的系統封閉條件,就進而形成歐幾里得式的公理化系統。
這個經久不衰的偉大知識計劃的形而上學基石是名詞系統。語言就是最基本的形而上學,人類的主要語言都是以名詞為核心的表述系統,因此,**迄今為止的知識基本上都屬於“名詞的知識”,都趨向於名詞能夠達到的理想。**名詞的理想狀態是封閉性定義,其自動藴含了一種超時間的形而上學,承諾了事物的恆定本質,進而建立了名詞知識的元定理,主要包括:(1)部分相加等於整體(估計與分類學的金字塔模式有關);(2)複雜效果可還原為簡單因素(不清楚還原論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最早或可能與四則運算建立的思維模式有關);(3)邏輯規律對於一切存在普遍有效(這個假設可能來自對理性的信念,希臘人相信理性觀念與存在是一致的,但理性信念其實也是未被證實的假設)。這三個元定理在事物的穩定或確定狀態下是正確的,但其普遍性卻已被新科學嚴重質疑。即使其中最可靠的邏輯,至今只是按照名詞理想而形成的名詞邏輯,如前所論,只是推理的規律,並不是存在的規律,甚至不是意識規律(胡塞爾早已發現了這一點,因而決心建立據説能夠真正解釋意識的現象學)。名詞知識不能解釋存在的生成動態(the becoming of being)、萬物的不確定動態湧現和系統的不可分解的複雜性,更不能解釋人類歷史的存在論事件的本源性或創世性。這些問題或者落在名詞之外,或者發生在名詞之前。
名詞知識以及名詞邏輯所以不足以理解動態和本源,原因在於名詞設定了封閉的對象,而且是死的對象(超時間而不變的存在雖然是永在,但也是死的)。因此,名詞所指涉的對象事實上並不真正存在,而只是思維的一種形式或裝置。但不要誤會,這裏不是在拒絕名詞知識。名詞對於語言和思維是絕對必需的,且名詞知識已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就。然而,問題在於,名詞知識的能量已經幾乎達到最大值,進一步的思想生產力已經明顯減弱。通過名詞系統,我們似乎看不到更多的新問題了,實際上思想也因此少有新發現了。於是,哲學家們不得不編造或借用一些似乎有新鮮感的文學名詞(如星叢、延異、幽靈、遊牧、皺褶、千高原之類),雖然這些名詞對名詞思維或許有些許助益,但缺乏突破名詞空間的方法論似乎難以形成新空間。這種能量耗盡的情況類似於牛頓時空內的知識幾近飽和而需要愛因斯坦的突破,而愛因斯坦時空也被發現與量子力學的微觀世界不一致。因此有理由推想,思想也需要在名詞空間之外去拓展另一個思想空間。名詞只是思想的一個維度,如果能夠增加另一個思想維度,就能夠建立一個非單調的思想座標系而擴展新空間。
與存在的足跡更為步調一致的思想形式是動詞(名詞只是思想的內在對象)。推舉動詞並不要求把語法改造為以動詞為核心,這既無必要也無可能,語法自有歷史原因也有語言學的理由,**推舉動詞應當是去發現一種與名詞思維形成座標式配合的動詞思維,或者更準確地説,建立雙層思維,以動詞思維作為反思名詞思維的元語言。**因為在並非名詞設定的“如此之存在”(being as such),而是動詞提示的動態生成(being-in-becoming)。存在的唯一可循跡象就是動態,或從本源性去看,存在即所成(to be is being made to be)。鑑於動詞呼應了存在的實況,而名詞只是虛構的分類,所以哲學需要從名詞思維轉向動詞思維,從“是什麼”(what it is)的定義轉向“如何做”(how it does)的問題。動詞哲學,或許還需要動詞邏輯,以及相關的動詞知識,正是尚未被充分開發的思想維度。
如果承認存在即動態,那麼概念似乎就應該重新理解為一組動詞所產生的湧現效果,而不應該是表達某種給定不變的本質。關於事物的知識,最終就是名詞和動詞座標的交點。動詞創造了時間的歷史性,因此,人所主謀的行為都有創世性——沒有創造世界,但創造了歷史和未來、文明與秩序、制度和價值。所以,哲學的第一命題不是作為世界觀察者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而是身為事物作者的“我作故我在”(facio ergo sum,更精確地説是creo ergosum)。Facio或creo意味着“主動創作”(I make/I create)。人類為存在創造了本來所沒有的價值,為時間創造了本來所沒有的歷史,因此,理解人類自身的哲學同時也是一種神學——但不是宗教,不是關於外在超越者的神學,而是解釋人類如何創造歷史的“神學性”存在論。通常關於神學的想象總是關於神如何創造世界的“榮耀神學”,而關於人類如何創造歷史也是一種神學,但由於人自身不完美,不是全知全能,而且作惡多端,因此,關於人類的神學就是一種“罪惡神學”。從超越人的普遍視域來看,人類的胡作非為對於萬物眾生就是罪惡,甚至對人類自身也是罪惡。啓蒙運動試圖為人類主體性編造一種仿神的榮耀神學,此種傲慢的態度不利於人類的自我反思。

以動詞為本的存在論,或創世存在論,其追問的是,動詞如何湧現為名詞?事件如何湧現為事物?過程如何湧現為秩序?可能性如何湧現為現實性?未來如何湧現為歷史?還有一個連帶的倫理問題:人類是否能夠使人類的動詞達到罪惡最小化?簡化地説,人類如何創作歷史?又如何才能使罪惡最小化?倫理學是人類專用於自身的一種思想,用來反思罪惡。人類世界有着複數主體,產生了上帝從未遇到過的主體間問題。主體間性意味着來自四面八方的多方動詞形成匯合和衝突而導致了比自然運動更加不可測的湧現。按照萊布尼茲的有趣想象,上帝是唯一創造者,只需設計萬物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 of beings)。複數主體的人類卻產生了主體間的互相不同意,於是,“同意”就不僅是知識論問題,同時也成為人類世界的存在論問題。將來很可能還會形成人與人工智能的主體間性,甚至人與外星人的主體間問題。如果求解多主體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 of subjectivities)難題,就需要建立自然裏不存在的跨主體性或更強的共主體性。這是文明世界的一個存在論條件。
**動詞發動一切事情,因此,動詞才是存在論的實質主語。**動詞是實在,而名詞是虛在。因此,對於存在論的主語,動詞要奪權。名詞只是語法主語,而語法主語不等於存在論的主語。在存在論裏,所有事物包括人都退居賓語,動詞才是主語,即如此結構:動詞v造成了如此狀態的事物t以及如此狀態的人h。存在論本身並不涉及應然判斷,即不涉及價值、權利、責任之類的判斷,在天地不仁的存在論裏,“發生什麼事情”比“誰幹的”要重要得多。因此,動詞即問題,動詞才是思想的出發點。名詞思維試圖從虛構的普遍概念出發去尋找恆定答案,但始終徒勞,因為名詞是否能夠説明事物,最終取決於動詞是否支持,就是説,名詞有何種實質意義,最終要由動詞來落實,動詞是名詞的充實形式(fulfilment)。這説明,動詞不僅是思想的出發點,也是思想的最後證詞。孔子可能最早意識到了名詞不可信。由此有了動名同源的映射公式:Xn≡Xv,即任何名詞Xn的意義必須由足以落實其意義的同性質動詞Xv去證明(如“父父”“子子”)。
名詞思維藉助名詞在語法上的主語地位,幾乎造成一種誤導思想的隱性思想專制,一個表現就是以名詞的分類學層級去虛構知識的等級制,比如以為“存在”是最大概念所以意味着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存在”並不存在),或“道”一定比“器”更重要(其實不盡然);另一個表現是名詞崇拜,以為名詞藴含答案,例如制度決定論,事實上制度實踐才真正解釋了一個制度的真實存在(比如以權謀私或以私廢公的司法實踐可以解構哪怕最好的法律制度)。如果在人工智能時代繼續堅持名詞主義,名詞專制將通過人工智能的力量而全面控制人的思想。而名詞專制最終會發生自我解構,啓蒙思想建構的主體性概念就是一個例子,由於未能解決連帶產生的主體間難題,即“他人不同意”這個最基本的問題,失敗的主體間性就釜底抽薪地消解了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上,啓蒙思想從來沒有完成主體性的建構。
不會被他人消解的“真正的”主體性意味着每個人都擁有一個世界,這是在名詞思維裏無法完成的建構任務,不能成為動詞的主體性只是一個幻覺。如果把思路切換到動詞思維,自主活躍的主體性卻是可能的,因此,**未來需要動詞思維來保持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讓每個人成為動詞,讓每個人像初民那樣重新成為符合本義的“哲學家”。**主體性必須是一種動詞狀態,必須是名詞無法限制的狀態。實事求是地説,人不可能成為為萬物立法的絕對主體,只能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動詞。成為動詞也就成為時間的作者,成為時間的主人,這就是真實的主體性。啓蒙思想受限於名詞思維,不可能確立具有創世性或本源性的主體性,反而導致了後現代反轉。所以,新啓蒙需要從“名詞哲學”(philosophy of nouns)轉向“動詞哲學”(philosophy of verbs),這才是主體性的可信立足之地。
知識間性與每個人的無限圖書館
無論是否願意,在未來都很難避免人工智能成為主體性的競爭者。人工智能將掌握名詞思維及其知識系統,其學習速度遠超過人,何止萬倍。在以名詞為本的知識上,人類不可能成為人工智能的競爭者,只能退化為用户。相對而言,創造性是人工智能的弱項,即便未來人工智能具備某種創造性,這仍將是其弱項,這是由人工智能的機器工作方式決定的。因此,人類只能在創造性上保持主體性,所以必須發展動詞思維,讓每個人擁有動詞性的主體性。
與職業化的知識訓練不同,動詞思維促使人與他人、事物或觀念自由相遇,從而激發思想的創造性湧現。這種相遇可以產生“緣分”,意味着某種偶然性中藴含的必然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緣分,因此應有一個與之相匹配的無限圖書館——網絡上的非實體圖書館。無限圖書館的潛在信息量相當於一個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可以“真正”擁有一個世界(2001年我使用的是“新百科全書”概念,但考慮到百科全書概念不能充分體現知識的動態性,因此參考博爾赫斯和瓦爾堡,改為“無限圖書館”概念)。然而,在目前的條件下建立無限圖書館仍不現實(能源供給和運算速度都遠遠不足),因此,無限圖書館仍是一個理想。就潛力而言,在互聯網平台上,每個人的無限圖書館都可以鏈接到任何人的無限圖書館,實現圖書資源的自由“借閲”。於是,存在於網絡空間的無限圖書館同時也是一個萬向鏈接的圖書館,最終可以形成所有人共享的跨主體圖書館系統。這是新啓蒙運動的一個知識基礎設施計劃,它將有助於每個人的思想既保持主體性又具有跨主體性。
**跨主體的萬向無限圖書館意味着可以容納所有文明、所有知識體系的“知識天下”,它與“政治天下”是協調的,都以“無外”作為建構原則。**這意味着所有或任何知識體系都具有平等的在場資格,成為思想資源。所有知識平等在場的理由是,每種知識體系都藴含了不同的可能世界以及可能的生活方式,都承載了不可替代的意義和想象,都可以成為其他知識體系的參照系。互為參照系的跨主體萬向無限圖書館將為任何一種知識體系提供最大化的思想想象力資源。
名詞思維已經很好地建構了關於必然性的知識(knowledge of necessity),但考慮到未來是無限開放且不確定的,就必須處理博爾赫斯式的“時間分叉”(forking times)條件下的複數未來問題。這就需要動詞思維去展開可能性的知識(knowledge of possibilities),以便理解存在的動態性,從而建構具有未來性的未來概念。這個問題的迫切性在於,如前所述,文明的深層危機在於正在失去“未來”的概念。不確定性、未來性和複雜性疊合成為存在論的新問題,顯然不能以本質不變的名詞概念或普遍必然的規律去解釋,而需要關於可能性的動態知識。這意味着,“什麼知識是普遍必然的”這種康德式的啓蒙理性問題已經不能充分表達知識論了,而需要考慮“何種觀念可以創造未來”以及“不同知識體系如何合作建構未來”的動詞理性問題。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能夠容納所有知識體系以及所有想象力的跨主體萬向無限圖書館。
啓蒙理性設想的知識主體是單數的人類通用心靈,知識對象被假定為客觀事物,目標是追求普遍必然真理。與此不同,動詞理性設想的知識主體是複數的具體心靈,知識對象是一切可能性。與必然性不同,任何可能性都可以被質疑或重構。只要把任何被假定為必然的觀念或命題映射為某種可能性,就變成了可以反思的對象。在此,動詞思維就成為知識的元語言,並使理性具有全方位的自反性,即一切知識或觀念同時也成為被反思的知識對象。因此,**新啓蒙的知識論在實質上就是建立能夠反思一切知識的元語言,而且是互動反思的元語言。**在其中,不同的知識系統互相成為反思對象,在互相反思中形成知識間性,而知識間性同時也是知識互相證明或互相驗證的條件。
傳統知識的建構基於名詞分類學和形式化邏輯,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層層分科知識,相對忽視甚至切斷了不同知識之間的互相反思關係。事實上,沒有一種知識能夠自證其真理性,世界上也不存在哪個問題或事實是獨立的,所以知識需要互證。當代人意識到了這個缺陷,因此試圖建立跨學科的研究,但成效並不明顯。原因在於,跨學科只是知識的簡單組合,並沒有“跨”,至多隻有知識量的增長,並沒有互相成為元語言,也就沒有實現互相反思,所以難以發生實質性的突破。未來的知識需要形成不同知識間的互相反思,讓不同的知識互相成為反思的元語言,在互相反思中發現不同知識的底牌和侷限性,在互相反思中建立有利於每種知識發展的知識間性。可以説,知識間性就是不同知識的互相反思,互相成為元語言。

美籍奧地利數學家、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庫爾特·哥德爾
建立元語言去反思知識系統而發現知識系統的元性質和元定理,哥德爾是典範,但哥德爾迫使數學系統發生魔術般的自指反思的條件是有着內在嚴格邏輯關係的數學系統。然而,大多數知識系統,尤其是人文知識體系,並沒有也不可能建立具有內在嚴格邏輯關係或公理化的系統。它們只有邊界開放的基本假設和鬆散的結構關係,因此也就不可能建立哥德爾式的自指性反思。考慮到非嚴格知識沒有能力反思自身,對非嚴格知識的反思就只能通過建立不同知識系統之間的互相反思來實現,即以“他者”的外部眼光去代替鏡像式的自指反思。具體地説,就是不同知識系統可以“互為元語言”而形成互相反思。例如,把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問題映射到經濟學和心理學裏,同時,把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問題映射到政治學和社會學裏,就可以發現這些問題在另一個系統裏是否有着不同的表現,甚至可能發現,在一個知識系統裏無法解釋的問題在另一個知識系統裏可以找到更好的解釋。事物本為整體,被拆分的知識只能通過互為元語言的互相反思來複原事物與問題的整體性。
除了復原事物的整體性,知識互相反思產生的另一個結果是發現同時有效的複數知識,這意味着關於同一個對象的不同知識不可能僅僅產生唯一真理,而非常可能產生多種不同而同樣有效的真理——但不是相對主義。關於同一個對象的不同真理並非基於各自的主觀理解,而是基於不同的事實關係。這個問題已多次論證過,在此重提,細節從略。簡單地説,設A和B為不同知識主體,知識對象為O,那麼,事實關係AO和BO不同,但都真實發生,相當於不同的函數關係。不同的事實關係必定產生不同的真理,即相對於特殊事實關係而為真的特殊真理。因此,並非所有真理都是普遍的。考慮一個普通到有些庸俗的例子:C對A很好,因此,對於A而言,“C是好人”是真理;而C對B不好,因此,對於B而言,“C是壞人”也是真理。這兩個互相矛盾的特殊真理可以同時為真,因為兩種函數關係同時真實存在。因此,確實存在着互相矛盾而同時為真的一些“特殊必然真理”。事實上,普遍必然的真理並沒有那麼多。複數真理解釋的是同一個事實的不同函數關係,而不同的函數關係意味着互相不可替代也不可還原的特殊事實。基於特殊事實產生的特殊知識雖然缺乏普遍性,但卻是客觀可證的,因此是“特殊必然真理”。複數真理是互相增益的知識,而不是爭權的知識。
**如果容納所有知識的無限圖書館概念是可能的,就必須容納互相矛盾而同時特殊為真的複數真理。**假設無限圖書館等價於複數主體共享的知識-精神世界,在互相參照和互相反思中不斷生長,那麼必定有某種跨主體的知識演化方式。可以將其想象為一種“綜合文本”(syntext)的方法,儘管這是一個虛構的概念。綜合文本被設想為一種建構知識動態關係的方法論,其基本假設是:(1)每個事實都等價於一組關係函數;(2)所有關係都是由動詞造成的,理解事實就是去理解動詞的創造性、複雜性和連續性;(3)每個事物在特殊關係裏會產生特殊知識或特殊真理,但任何特殊真理都不可能成為普遍真理;(4)所有問題最終都必須由動詞去解釋;(5)由一個問題出發可以鏈接到所有問題。因此,如果一種知識是有效的,就必定與其他知識存在着合作關係。
於是,綜合文本的預期是:(1)所有知識系統都互為參照系,知識的互相參照可以生成關於事物的綜合文本。(2)從問題出發,思想就恢復到思想的初始經驗(Ur-experience),而初始經驗裏大概率包含生活的普遍問題,因此最有希望成為所有人的思想聚點(focal points,借用Thomas Schelling表達不約而同的意向“聚點”概念)。人們對同樣問題有不同看法,而問題本身卻是不同看法得以相聚的交叉路口,因此是聚點。可見,問題就是思想的本源,既是思想的出發點,也是連接點或匯合點。(3)以問題去引導知識,相當於以問題作為關鍵詞來重新編排知識,這樣可以超越名詞分類學和學科分類,而將所有知識聯動起來成為網絡式的無限綜合文本。以問題為交通樞紐而展開的無限知識世界,其無限性並非線性無窮,而是萬向無窮,是藴含着無窮可能世界的博爾赫斯式分叉。同時,以問題為核心去展開思想和知識的無窮鏈接,就相當於建構了無限的瓦爾堡圖書館。

瓦爾堡圖書館
如果每個人都根據自己與問題的“緣分”,並以綜合文本的方法去建立思想和知識的無限鏈接,在理論上説,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問題鏈接去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瓦爾堡式圖書館”(即以問題鏈接為準而不是以學科分類為準的圖書館)。這將有助於每個人的思想湧現。這個理想化的知識建構工程顯然需要網絡數字化平台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支持才能夠實現。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每個人的無限圖書館的鏈接方式和知識結構可以即時即興地形成或改變,即始終是動態的。並且,每個人都可以參考或借閲別人的無限圖書館。甚至,將來人工智能也可能成為世界中的新主體,並建立自己的無限圖書館。無數主體的無限圖書館將共同產生一個包含複數真理、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且不斷演化的精神世界。在其中,**每個人都有最大機會建立自己的思想主體性,也有最大可能性去形成跨主體性。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同時擁有主體性和跨主體性的思想家,結果可能形成一個“知識天下”。**這是可以想象的新啓蒙的第一步,僅限於精神世界的建構,尚未涉及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