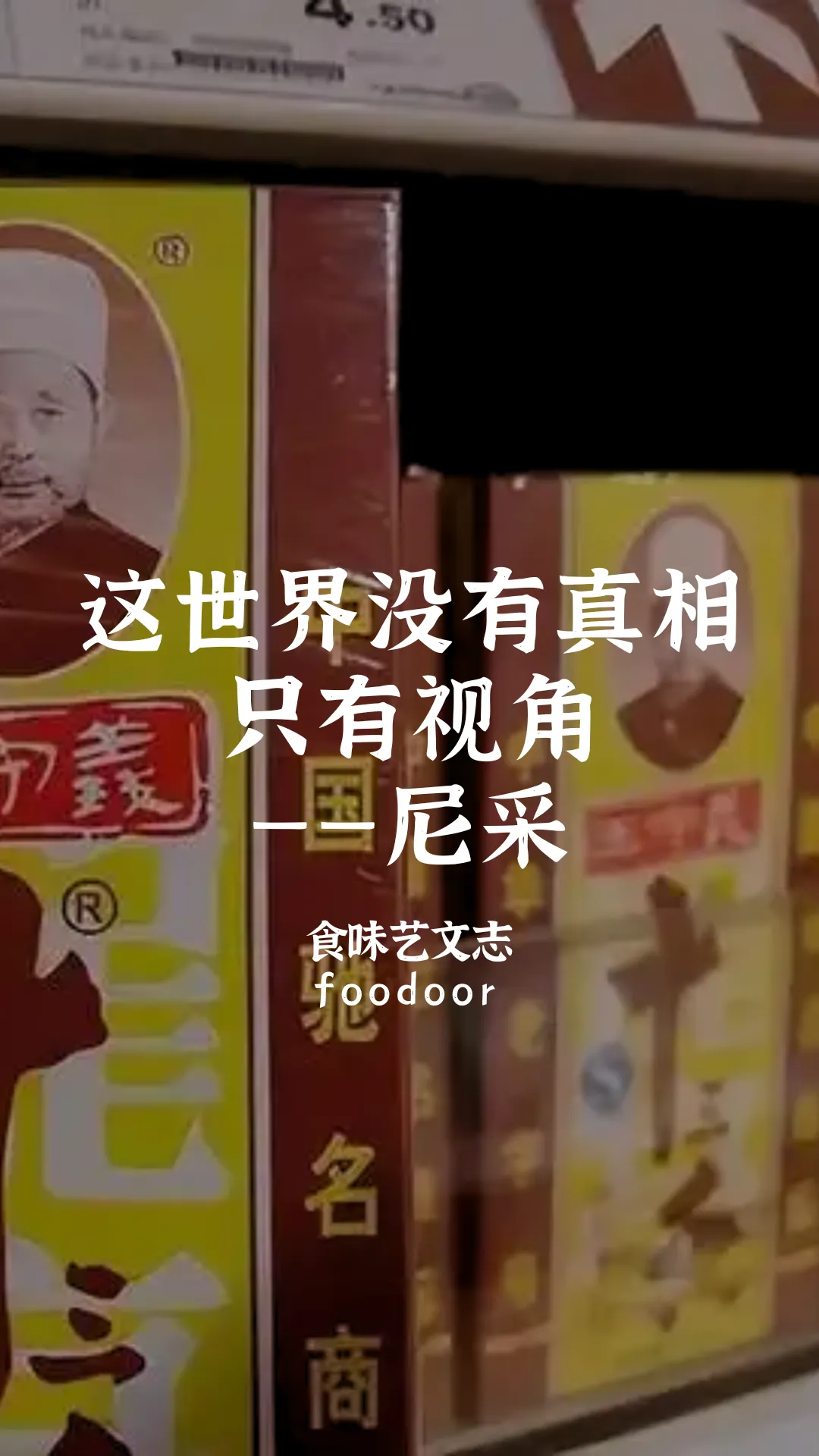恕我直言,對原汁原味的執念,是禁錮中國菜的最大枷鎖_風聞
食味艺文志-食味艺文志官方账号-人间至味,莫过碳水。公众号foodoor12小时前

撰文 | 魏水華
頭圖 | canva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簡單的烹飪。
刀工見真章,本味自流香。
吊湯不用味精,全憑火腿乾貝高湯提鮮
雞有雞味,魚有魚味,絕不能用香料蓋過食材本味。
……
這些話術,常常見諸於描述中餐技藝的菜譜裏,描述中國美食的文章裏。總而言之一句話**,高端的烹飪必須原汁原味,多用香料就是低級的。**
但這種飲食邏輯本身,有一個巨大的漏洞:
這是雲南人以薄荷作為煮火鍋的蔬菜。

這是廣東人的陳皮豆沙,陳皮不是單純的香料,而是紅豆沙裏的一部分食材。

這是湖南人的紫蘇螺螄,紫蘇葉入味了比螺螄還好吃。

香料和調味品之間是有區別的。香料可以用於調味,但很多時候,它們也可以是食材——當香料作為食材出現的時候,所謂的原汁原味少用香料,就是一個無法自圓其説的悖論。

中國人對於香料的偏見,始於地理。
在東亞這片被青藏高原、戈壁沙漠與太平洋切割成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裏,千萬年來受到西伯利亞高壓冷空氣的影響,氣温明顯低於同緯度地區。除了少數耐寒的香料之外,大部分香料作物都無法在中華文明起源的華北華中地區種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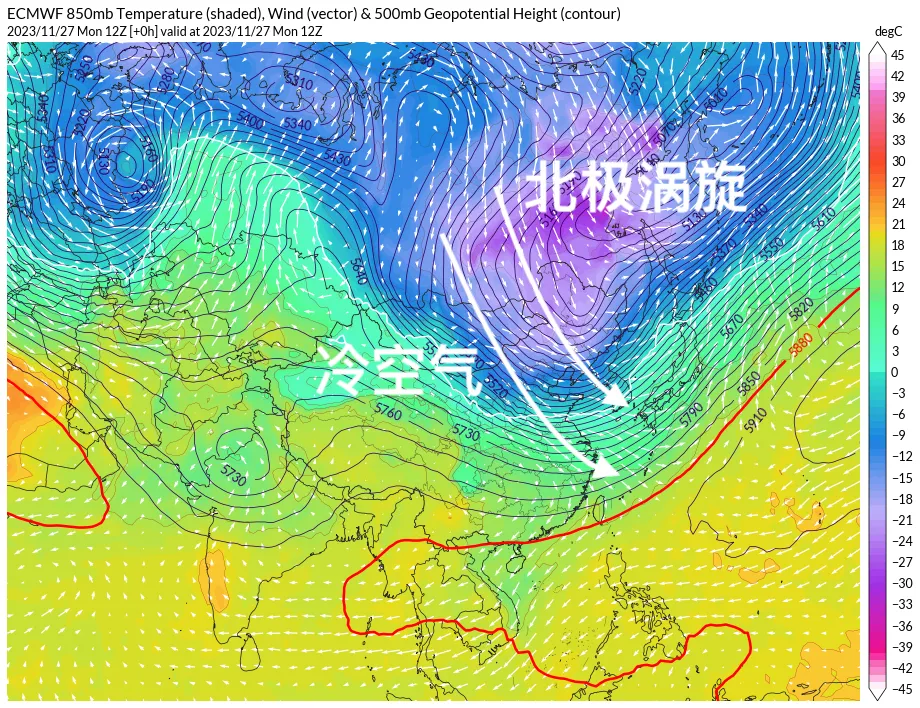
當印度次大陸的咖喱葉在潮濕空氣中肆意生長時,中國本土香料植物如花椒、八角等卻演化出適應氣候的生存智慧——果實更小、精油含量更低。
這是中國家常廚房香料通常只有葱薑蒜辣椒“四大件”的直接原因;也是不從事專業烹飪的多數中國人無法準確描述丁香、豆蔻、草果、牛至、砂仁、山奈、木姜子等熱帶香料的風味的文化基因來源。
對我們來説,這些香料都是滷味料包裏那一堆分不清楚誰是誰的兄弟姐妹,或是中藥房里君臣佐使陰陽配伍的神秘素材。
與寒冷氣候相對,奔流而下的長江黃河又帶來了豐饒的腐殖質,季風氣候為農田勞作提供了準確的週期,使得這片土地的農耕文明很早就開始萌芽。人們擺脱遊獵捕撈的生活,以農田裏的產出作為主食,去腥、除羶變得沒有那麼重要。
當美索不達米亞人在泥板上記錄百里香栽培技術時,中國甲骨文正在歌頌粟米豐收;當波斯商隊在絲綢之路上運輸藏紅花時,中國農民正在培育抗旱的稻米品種,這種文明重心的差異,註定了香料在中國農業體系中的邊緣地位。過早成熟的農業思維,也將香料植物貶為"奇技淫巧"。
《齊民要術》記載的37種烹飪技法中,涉及香料創新的不足十分之一,暴露了農耕文明對味覺探索的消極態度。
大量的農田物產,還讓先民們產生"靠山吃山"的自足幻覺。當絲綢之路帶來胡椒、孜然時,士大夫階層將其鎖進藥櫃,用"蠻夷之物"的偏見閹割了香料的烹飪價值。這種地理決定論導致的認知侷限,使中國錯失了構建香料文明的黃金時期——下南洋的華人們帶回的肉豆蔻最終淪為驅蟲藥,而同期歐洲正用這些香料重塑飲食文明。
歷史和地理的共同醖釀下,中國日益成為一個書同文、車同軌的大一統帝國。但對味覺的認知割裂,也讓那些本應盛產香料的邊疆地區,處於尷尬的境地:
在花椒的原產地四川盆地,川廚將花椒的麻感奉為圭臬,卻拒絕探究其與黑胡椒的協同效應;在盛產柑橘植物和樟科植物的嶺南,粵菜師傅深諳陳皮妙用,但對錫蘭肉桂的認知仍停留在"桂皮替代品"層面。


地理的特徵,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信仰,而信仰之下,香料在中國的道路又被拴上了重重枷鎖。
儒家"克己復禮"的倫理觀是最早被異化到餐桌上的:《禮記·內則》規定**“不食雛鱉,不食犬肝”,這種對飲食的過度規範延伸到香料領域,形成“重調和、輕個性”的保守傳統。當意大利廚師大膽嘗試藏紅花燴飯時,中國文人卻在《隨園食單》中寫下“多用香料便是市井氣”**的訓誡,用士大夫審美窒息了味覺創新的可能。
道家的"道法自然"則在魏晉之後,淪為拒絕進化的遮羞布。過分強調"食材本味",實質是對烹飪主體性的自我閹割。清代《養小錄》記載的"十香糕",本可發展出複雜香料體系,卻因"恐奪米香"的迂腐觀念,最終淪為單調的糖油混合物。這種對"自然"的片面理解,恰是反自然的:人類烹飪文明的本質就是改造自然。
佛教素食主義製造了香料替代的幻覺。豆腐用石膏點制本就是化學反應的產物,卻要標榜"天然本味";素齋用菌菇仿製葷腥,本質上是對香料的變相渴求。這種既要又要的虛偽,導致中國素食陷入"拒絕香料卻渴望肉味"的精神分裂。
諷刺的是,在佛教的誕生地印度,人們倚靠阿育吠陀體系,在素食文化裏坦率運用數十種香料構建出獨立的美學體系。

這種重重枷鎖之下,最悲哀的案例要屬川菜——作為中國四大菜系之一,川菜本以“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特徵聞名於世,它的背後,就是對香料協調搭配的嫺熟應用,構建出複雜的味型譜系。
但在“原汁原味”的底層要求下,川菜廚師們常常在官府菜、商人菜、市井菜的邏輯自洽裏陷入迷茫:所有的川菜大廚都會告訴食客,川菜裏也有很多不辣的、少用香料的、服務官紳階層的“高級”菜餚,但如果你反問“這些菜餚和淮揚菜、粵菜有什麼區別?”大廚們多半會陷入無法自圓其説的尷尬。
説到底,這種尷尬並不源自大廚們的見識和技術,而是源自中國文化裏預設的,不用香料的菜餚才高級的成見。


發酵的美學,是中國香料文化薄弱的又一大原因。
黃河流域的粟作文明孕育出最早的麴櫱技術;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甑,殘留着4300年前的酒麴痕跡;《周禮》記載的"五齊"實為不同發酵階段的酒漿,這些早期發酵產物很快被納入烹飪體系。當羅馬貴族為胡椒瘋狂時,漢代庖廚正用酒醴醃製"腶修"(肉脯),以替代昂貴香料的防腐功能。
到今天,四川郫縣豆瓣經歷三年日曬夜露,蠶豆與辣椒完成從辛辣到醇厚的蜕變;鎮江香醋在江霧繚繞中發酵,醋酸菌將糯米轉化為琥珀色的液態哲學;浙江紹興的腐乳,在黃酒裏沉澱出妖嬈的鮮味;山東博山醬油在凜冽北風中濃縮出醬香;山西老陳醋在黃土窯洞裏沉澱出礦物風味……

本質上,這些調味品的原材料高度近似,無非是小麥、大米、大豆、蠶豆這些農田裏大量產出、司空見慣的穀物。但在地方各異的風物、水土滋養下,在不同發酵工藝和發酵週期的促動下,形成了複雜而輝煌的發酵譜系。
從某種程度上説,這些發酵類的調味品,取代了香料在餐桌上的生態位。
18世紀,當登陸馬來羣島的英國殖民者們品嚐了下南洋的華人們製作的魚露後,以番茄作為基底,加入多香果、肉桂、丁香、洋葱、芹菜等複雜的香料,並以閩南話魚露(膎汁)的發音,命名了這種複合調味品ketchup——是的,就是後來的調味番茄醬。
這一案例,充分證明了發酵技術和香料複合技術可以相互替代的烹飪慣性,和中國人遠離香料的底氣。


宋代開始,以范仲淹為首的文人士大夫們提出了“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口號,掀起了文人從醫的浪潮。中國的醫學,開始與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綁定起來。

把理科當文科玩,出現了一個災難性後果: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沒有介入式治療的能力,漢《五十二病方》以來的中醫外科就此停滯;各種草藥的熬煮配伍在此後成了中醫正統。而由此派生出來的藥食同源的理論,則異化為餐桌上自我設限的牢籠:將八角定義為温腎藥材,肉桂歸類為活血通經之品。
這種巫醫視角的介入,阻斷了香料在烹飪領域的自由發展:明代《食物本草》規定"丁香日不過三粒",讓廚師永遠無法探索丁香在慢燉中的潛力。
與此同時,朝貢貿易的畸形發展掐滅了香料革命的火種。鄭和船隊七下西洋帶回47種香料植物,卻被鎖進皇家園林供貴族賞玩。當葡萄牙人為胡椒發動戰爭時,明朝正將香料作為官員俸祿折算。這種將香料貨幣化的短視行為,使中國失去了建立香料美學的歷史機遇。

一個反例是日本,同樣氣候寒冷的東亞地區、同樣天然缺乏香料植物、同樣處於大航海時代的世界邊緣,但日本卻發展出了"柚子胡椒"“山椒芽"等極具創意的本土香料文化;風靡全球的日式咖喱,則更具代表性——缺乏薑黃,就增加南瓜和胡蘿蔔着色;缺乏椰奶,就用麪粉調出濃稠的質地;吃不了太辣,就用蘋果泥、醬油、味醂或味噌配置出平衡微甜的風味;甚至考慮到普通家庭長時間熬煮咖喱會影響鄰居生活,違背了東方文化裏的謙退禮儀,還發明瞭方便運輸保存的咖喱塊……
反觀中國烹飪,對"老滷"“陳醋"的路徑依賴,本質上是將氣候制約、地理制約,轉化為文化上不思進取的託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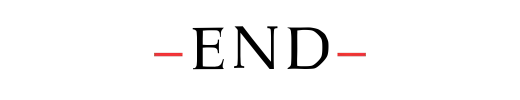
這是上海某米其林三星中餐館用松露醬搭配的小籠包。

小籠包是地道的滬上口味,薄皮、鹹鮮、微甜、爆汁;松露醬是南法地區黑松露和橄欖油的經典組合,香氣濃郁、油潤化渣。
但二者結合起來,就變得古怪難吃:松露醬不僅沒有化解小籠包的油膩,反倒為豬肉餡增加了可疑的腥羶味。除了價格翻十倍之外,完全無法與小籠包和鎮江陳醋的經典搭配相提並論。
顯然,主廚既不懂松露的香氣特性,也不解中式麪點的味覺結構。這種粗暴嫁接,正是香料文化缺失導致的創新窘境。

在今天的烹飪江湖裏,意大利主廚能用郫縣豆瓣創新披薩醬,中國廚師面對藏紅花仍只會做西班牙海鮮飯仿品;印度通過輸出咖喱文化年創匯300億美元,而出口的中國醋99%只能銷往海外中餐館和華僑社區。
這種單向度的文化輸入,折射出香料世界裏中餐可悲的話語權,和味覺軟實力競爭中的全面落後。
另一方面,美團數據顯示,18-25歲消費者在川渝火鍋店額外加購香料的比率達63%,遠高於父輩的12%。這種"香料飢渴症"暴露出傳統烹飪哲學與當代需求的巨大鴻溝。
當西班牙分子料理用液氮鎖住羅勒香氣,當秘魯菜系創造出亞馬遜雨林香料矩陣,中國菜依然困守"大道至簡”“原汁原味”的古老訓誡。這種對香料文明的系統性輕視,不僅造成了味覺創新的停滯,更折射出一個古老文明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深層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