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京飛,偷出了半部好戲_風聞
Sir电影-Sir电影官方账号-16分钟前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
一部國產劇,後台不停有人在問。
Sir也去看了,幾分鐘便來了精神——
火車上,猥瑣男摸上了熟睡女乘客的腿。
突然,女乘客驚醒,大罵抓流氓。

女乘客拽着流氓在車廂裏讓眾人評理。
唉?
但,不對啊。
這怎麼他倆的手往乘客的兜裏伸呢?
小偷!

這場偷包戲,讓人想起了《天下無賊》裏那些“橋來橋上走”的手上功夫。

很難想象,這居然是一部電視劇的質感。
沒錯,你們一直催更的——
黃雀

雖然在電視劇裏,發生地為“荔城”。
但,畫面裏,火車站的佈局,茶樓的燒麥,以及, 廣場上人們張口就來的粵語,IP屬性簡直不要太明顯。
這裏是,21世紀初的廣州。



在這個時候,廣州火車站,必定是每一代人的陰影。
割包、搶劫,還有砍手飛車黨。
70後的人,這是南下掘金的大門;80後的人,是青春求學之路;90後的人,定會來這裏經歷南國的悶熱暑假。
廣州火車站也還是魚龍混雜之地。
騙子、小偷、“道友(有毒癮者)”、無家可歸之人,更聚集在此。
被偷、被搶、被騙的事情,在2000年左右的廣州,已經“氾濫成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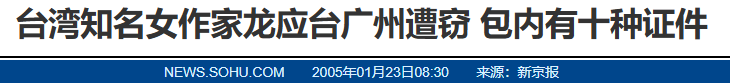
編劇王小槍(《功勳》《對手》的編劇)將故事放在時代下廣州火車站,又特地按照郭京飛的“窩囊樣”,寫出了這部電視劇的男主角——一名毫不“熱血”的反扒警察,郭鵬飛(郭京飛 飾)。
但為什麼老感覺他出門會被扒?

他一邊費勁巴拉地在荔城火車站刑警隊裏“反扒”,一邊,又大海撈針地找自己從老家出走,來到荔城經商的未婚妻。
他能否“得償所願”?
Sir在這篇文章裏,絕不劇透。
——就聊幾個彩蛋。

01
角色連接《黃雀》裏的角色都很有意思。
主角郭京飛,典型窩囊廢,話癆,倒黴蛋,誇張的表演撐起《黃雀》裏的喜劇部分;

反派祖峯,代號“佛爺”,出道多年的賊王,冷靜、縝密、負責團隊內的調控,撐起劇裏的暗黑、陰謀部分。平時,慈眉善目,但你卻看不透他眼鏡下深藏的殺意。
他也是郭鵬飛的主要對手。

將二者聯繫在一起的,則是一個醫生。
TVB新晉小生,王浩信,在《黃雀》裏飾演往返於香港、內地的眼科醫生薑吉峯。
故事的“線頭”,也是他身上攜帶的一雙眼角膜被偷而起。

一副眼角膜只能放7~10天,超過這個時間了,眼角膜也就廢了。
這個色令智昏的醫生為了迅速找回眼角膜並保守自己的秘密,在表面上與警察合作,背地裏又跟賊做起了交易。
一次,逃離警察監視,你看,他連腳指頭都有戲。
下車之後,先轉轉腳指頭。

接着,如踩了電門一般,手舞足蹈地扭着就衝過了人行橫道。
(論演戲還是香港藝人放得開。)

不過,Sir之所以覺得這些角色有意思,倒不在於他們的演技。
而在於他們的角色,與飾演者本身的關聯。
比如,姜大衞。
在《黑社會》裏,他是許警司,主持着黑道的“秩序”。


在《黃雀》裏,他飾演的廣叔,主持的是火車站附近“小偷”的規矩——
只要能從他的理髮店裏偷走一樣東西出去,就可以劃片自立。

是不是覺得,有某種程度的相似?
另一個,尤勇智。
在《天下無賊》裏還是黎叔的手下。

如今,時過境遷,入了警校,當了警察,成為郭鵬飛的“反扒”師父。
但,手上功夫依舊靈活,説偷你鑰匙就絕不偷你褲衩。

看來,即便轉了正派,“本事”卻沒減。
最值得一提的,則《黃雀》裏郭柯宇飾演的荔城警局反扒組的花姐。
絕對的大姐大。
給屬下拍煙的時候,動作老練。

Sir在查反扒警資料時候,找到了一部拍閔行公安分局刑偵支隊反扒隊在抓小偷的紀錄片。
這裏的隊長几乎與花姐一模一樣,她也讓下屬喊自己叫“阿姐”。

在同事跟丟了小偷時,阿姐也照樣發他們脾氣,一邊罵人,一邊順手接來了旁邊同事遞來的煙。
老練的氣勢不輸鬚眉。

所以這劇本假麼?
太真了。
02
老廣風味《黃雀》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質,廣式風味明顯。
為了保證“廣式”風味獨到。
《黃雀》裏不單是找來了“廣式雙馬尾”的特邀演出。

或是,讓腸粉、蝦餃每集客串,讓《外來媳婦本地郎》成為下飯神劇。

還加入了許多“老廣”意味的俚語與風俗——比如,在四川幫的大哥何小竹(王錚 飾)找到廣叔,想讓他能給自己也分片地時。
他來廣叔的髮廊,要求“洗個頭發”。
在粵語裏有這樣的一句俚語——“洗濕個頭”的意思就是,形容事情已經開始,無法回頭,不得不繼續下去。
通常形容無奈何或身不由己的情感,尤其是事情本身存在風險或是不利因素時。
而,此時的何小竹為了讓自己能在荔城立足,而不得不一步步走向更不可控的境地中,他最後的結局,也正是印證了,他這一天“洗濕了頭”也再無回頭的可能了。

還有,反扣的茶杯。
佛爺為了偷獎盃,收留了一名渾身都反骨,時時刻刻想從佛爺的保險箱裏偷錢的四眼(周政傑 飾),作為自己組內成員。

在他們準備最後一次的合作時,四眼已經擺明了要想要“反水”,在吃完早茶後,四眼將杯子倒扣在了桌子上。
而“倒扣”,是指在對“主人”表示不滿與抱怨,也表示會客結束。四眼的這一行為也就是在向佛爺抱怨——他的分贓不勻,四眼想另起爐灶單幹。

還有,在廣叔退休在即,去茶餐廳吃飯的時候,牆上貼的標語——得閒飲茶,夠鍾食飯。
其實也是暗指他“得閒”了也退休了,但,“吃飯”是吃的哪門子的飯,是最後一票的分贓?還是等待他的“牢飯”。(還得聽第二季的“下回分解”)
《黃雀》絲毫不掩飾對“港片”元素的偏愛。
比如,在四川小偷的家裏,DVD機放的港片一直不斷,演員有李小龍也有鄭秀文;

在一場“告別戲”裏,燒着的《猛龍過江》海報成了一份送別的禮物。
電影裏的李小龍似乎靠一身武藝就能闖遍世界,但,在《黃雀》裏,那些底層的人連混口飯吃也難。

但顯然,《黃雀》並不想把港片元素做成簡單的符號致敬。
它還成了佛爺犯罪行為的“靈感”。
佛爺的小偷組織,擅長設計圈套,製造意外,做到讓受害人在不知不覺中,就將鉅額財物就“送”到了他的手裏。

想起了什麼?《意外》。
在那部電影裏,一幫殺手通過製造“意外”殺害目標人物,並輕鬆脱罪,可謂是港片中難得一見的“高智商”犯罪。

這個團隊裏有4個人,女人負責做誘餌,大腦負責設計“意外“,其他兩個幫手為機關的實操人。
但,最後也是因為內訌,團隊走向分裂。而“佛爺”的小團體裏,也是如此。
前面所説的那起眼角膜的案件,就是團隊裏的阿蘭與男友財神因為分贓不均要單飛,但由於計劃不完善,將“佛爺”團隊徹底暴露在警察的面前。

這也是《黃雀》的來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小團體裏,黑吃黑,是“黃雀在後”;而在黑白勢力對抗時,也是“黃雀在後”。
03
“小偷”術語如果沒有經歷過這個年代的人,很難能感同身受這“防不勝防”的盜竊與詐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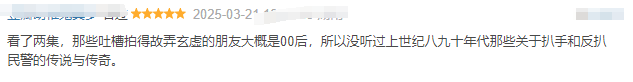
與Sir同個年紀的人,必定聽過要把書包背在前面,不然就會被人扒錢包的勸告。
這並非故弄玄虛,而是那個年代的小偷、騙子,太猖狂了。
而《黃雀》裏,融入太多在只有那個年代才有過的“犯罪”。
比如,你突然發現有人的錢包掉了,過了一會,有人特地在你面前撿起錢包,並打開錢包讓你看見鉅款,為了不被失主發現,他提議與你分贓。

在Sir那個年代,這種騙局隨處可見,併成為那時候最“出名”的騙局。

與此同時,“失主”回來找錢包,並告知你,這錢包裏還有鉅額支票,讓你貪小便宜準備分錢時,實施詐騙。

還有,2004年,廣州“飛車黨”搶包的屢禁不止,騎着摩托車在路上搶包的比比皆是。
就連鍾南山院士的手提電腦,也曾在街上被搶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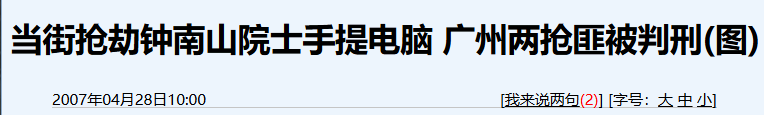
喏,在這裏也有。

也因為“飛車黨”搶包太嚴重,最後,廣州宣佈全面禁摩。

還有,在地下通道里追着你算命的,張口就算準了你有“血光之災”。

這種騙局在2006年也還是有人信,只要廣撒網,就會有人碰上。

編劇王小槍是下了功夫的。
包括郭鵬飛在飯桌上想廣叔透露些“賊王”的線索,所用的黑話——
肯定不是鬥蟑螂
不是擠車門
扣死倒也不太可能
肯定不是隨機的
也不是摘掛
會不會是趕場子的
萬一是老外竄了呢
水上漂
醒了有沒有可能

以代客買票、帶客進站為名,騙取旅客錢財,後立即消失叫“鬥蟑螂”;
偷夜間坐車睡覺的旅客叫“扣死倒”,偷行李物品的叫“滾大個”;小偷將自己的衣服掛在乘客的衣服上,假借拿衣服,趁機將旅客衣服內財物偷走,叫“摘掛”。
有趣的是。
“佛爺”這個代號,看上去像端莊肅穆。
但,實質上在行業黑話裏,佛爺,就是指有着多次、相當程度的盜竊犯,區別與普通的小偷小摸。
這些黑話,將《黃雀》裏的小偷行當上升為“幫派”行為。
他們有自己的黑話,也有着自己規則與等級秩序,如同江湖上的其他各行各業。
他們需要“老人”考核、批准,才可以入行,“新成員”還要定期向老人進貢,要維持這樣的秩序,才能保證這項行業“長治久安”。

既然有幫派,就會有等級。
在《黃雀》裏,將小偷分為三六九等,玩鑷子的、玩刀片的,各路手活不同,風格也就不一樣。
以廣叔為代表的,象徵的是一種“體制內”,他們是小偷等級裏的“體面人”,屬於練就手上絕技,並有自己在冊的花名單;
也有像是“佛爺”這樣,單拎出去的“小團體”,而,佛爺的劃片自立,也是經歷了廣叔的考驗,是通過“上級”允許的,他們主攻用“計謀”賺大錢。

最次的,是從四川來荔城的外地人,他們沒有在編,手藝也就一般,在不同街區流竄搶飯吃,屬於下手狠,只要能賺錢都幹。

這絕對是《黃雀》這部電視劇大膽的地方。
它深入塑造這些不同層級的“小偷”,他們各自為政,自有其生存法則。
拍出了一個“弱肉強食”的都市叢林。
04
全員有病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黃雀》裏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設定:“全員有病”。
警察這邊——
郭鵬飛,肝移植,隨時隨地在吃抗器官排斥的藥物。

這顆肝臟的主人,曾經是一個得了絕症的出車禍的詐騙犯。
生前簽了器官捐獻,也算了是救了他一命。

這顆肝臟是他“猶豫不決”的根源。
他放大了人性中的“善意”,正如,他無法認定捐肝給他的詐騙犯是罪無可恕的惡人一樣。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庇護一名年邁的小偷慣犯,最後,小偷釀成大禍,付出極高的代價。
李紅旗(趙濱 飾),郭鵬飛的小組成員。
舊疾腰傷,低血糖。
他的腰傷是一種長期無法解決的身體痛苦,他一直隱忍着生活給他帶來的創傷。

妻子炒股,欠下大筆高利貸,債主天天堵門要賬,回家也不敢開燈。
活得偷偷摸摸。
那句“為人民服務”就如突出的頸椎間盤,時不時刺痛着他。

花姐,她的第一場戲,就是在醫院看病。
什麼病,沒細説。
但她的病也是心病,未婚的她收養了自己抓的賊的女兒,“女兒”的叛逆與捂不熱的心,讓她一直痛苦。


“佛爺”這邊呢——
火車站站內醫生,黎小蓮(秦嵐 飾)有着嚴重的潔癖,被別人碰過的東西,她都要用酒精消毒。
她怕髒。

但,這個毛病並不是之前就有。
當初她跨越大江南北,找到了自己被父母遺棄的腦癱弟弟時,她一點沒有嫌髒,甚至與人販子在地上打架。
此時的她還是正常的。

直到她加入了“佛爺”的組織後,成為部門裏設定計劃的頭腦時,她的潔癖也就越來越嚴重。

阿蘭,佛爺組織里成員,所有東西都要擺放整齊,包括吃完的雞骨頭。
她有強迫症。

在她牀頭,一本《霧都孤兒》貫穿了她的少女時期與成年。
也由此可以猜出她的身世,無父無母,迫於生活,誤入賊窩。

在電視劇裏,插入了一段阿蘭的回憶,被室友霸凌,喜愛的裙子被剪破,身上被剪刀劃傷流血。
她儘可能地想掌握自己的命運,但,可惜的是她“控制”不了任何事。

“佛爺”,常年手腕有問題。
説是修手錶,其實應該是為了練就“手活”而落下了病根。

年輕時,也因為不守規矩而被砍斷了一根手指。
所以,佛爺為什麼那麼強調“規矩”,最後又因為有人壞了規矩而“斬草除根”,也都是因為,他當年就為了學習“規矩”而付出了許多代價。

還有,那幫從四川來的三兄弟,小春與大春都是屬於聽力障礙人士。
小春聽不見也張不開口,大春弱聽,表哥的何小竹是唯一一個正常人,作為他們的大哥,帶弟弟們一起來廣州混飯吃。
但,手上的活入不了廣叔的眼。
他們的委屈是無法訴説的,他們被暗算、被排擠,最後被逼無奈,也走上了復仇的絕路,卻還找錯了對象……
他們説不出,道不明,也聽不見。

他們的病,何處而來?
是來自經濟大變革下迅速轉型的社會,那些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江湖,那些灰白不明,善惡兼容的人性。
而這些角色身上的沉痾頑疾,是他們的“人味兒”,也是這個時代的痛症所在。

05
時間”在《黃雀》裏,表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道具。
不論是佛爺作為真實身份的掩護,而經營的修表生意;

還是在作案之前,團隊裏的成員要提前對錶,將時間要精準到分;

又或是,郭鵬飛手上一直戴着從師父手裏“偷來”的手錶。

表,那個時代最常見的,也最有代表性的東西,它象徵着財富、地位;象徵着主人的性格與不同的時代屬性。


△ 年輕一代的人,更喜歡戴電子錶
在最後佛爺所説的,“修表生意不好做,戴錶的人越來越少,用手機看時間的人越來越多。”
也正是電子產品的全面鋪開,讓手錶的作用愈發單一,最後,也慢慢走出了這個時代的必備品舞台。
手錶的消失,也是“時間”的消失。
也是一個年代的消失。
一如李宗盛的那首歌“當你發現時間是賊,早已偷光你的所有選擇”,其實,時間才是最大的“小偷”。
在《黃雀》的每一集開頭,都通過倒敍,去聊一聊這些人之前發生的故事:有的,是如何上了賊船,有的,是如何懲惡揚善;有的,又是如何在感情裏不告而別;有些,又是如何將惡一步步積累,走到了現在……

《黃雀》新穎之處在於,它敢拍灰色地帶的故事,它也敢將我們帶回到那個混沌的時代中。
在90年代末社會經濟改革之下,它呈現出了一種荒蠻的、瘋狂的社會狀態,那個時代並不完美,但,確實是一段獨有的集體的共同記憶。
誠然,《黃雀》的問題也有,線索冗長,節奏稍慢,結尾的頭重腳輕,破壞了前面費盡心機所鋪墊的懸念。
這也是它開分只有7.2的原因。
但,好就好在,它着實切中了這個時代的脈搏。
從綠皮火車,到空調特快,再到幾個小時就能橫貫中國的高鐵,火車在變,火車站在變,人也在變。
不變的是,那些從火車站裏出走又投入更大的命運洪流中去的人。
一波又一波,如浪花般。
湧起後,又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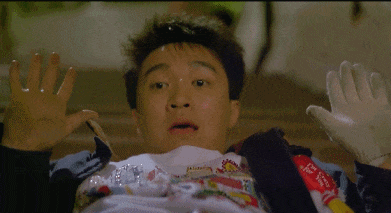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點擊閲讀往期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