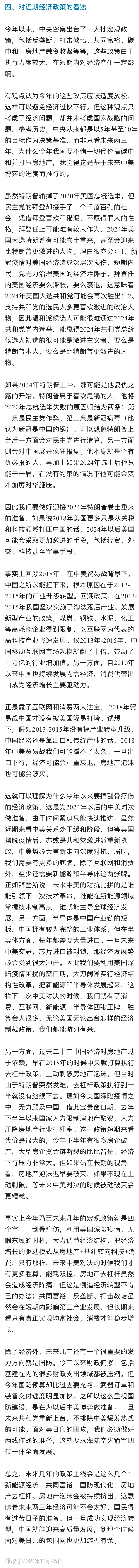還是要對自己的國家多一點信心_風聞
洋恺宏观-43分钟前
2017—2021年的時候民族情緒高漲,很多人對未來充滿樂觀預期。當下卻存在另一種情況,社會上出現很多消極負面的論調。事實上,中國經濟主要取決於出口和房地產,2022年以來經濟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地產收縮有較大關聯。然而人不能只在賺錢的時候才愛國,因為大部分人只能跟國家共進退,個人發展曲線取決於國運β。
特朗普對華脱鈎這事情,長遠來看影響會很大,畢竟我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貿有很高的依賴度。但往好了想,面對逆全球化帶來的威脅,我國是世界上準備最充分的國家之一。
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前提,是60年代吃夠了苦。面對美蘇的威脅,當時的民眾勒緊褲腰帶搞出了兩彈一星,保障我國的經濟建設不會因為外來侵略而中斷,這與後來的烏克蘭形成鮮明對比。2018年我國扛住貿易戰的前提,是2012—2015年忍着通縮壓力,堅決實施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出了世界級的互聯網產業;之後又推行供給側改革,大量淘汰落後產能。面對特朗普1.0時期加徵的關税,內需發力對沖了出口下行帶來的負面衝擊。
與G7國家相比,我國擁有充足的中央財政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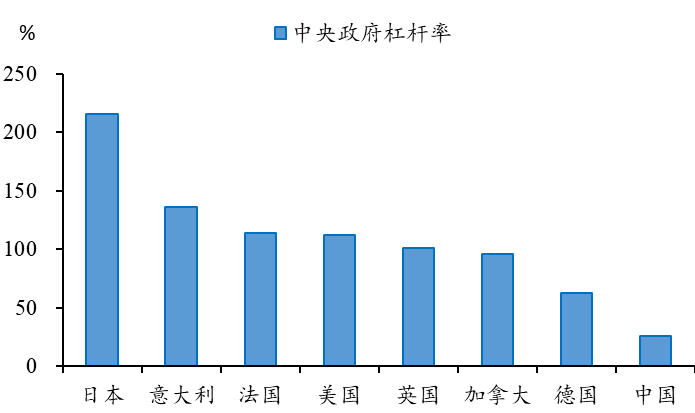
過去幾年國家作出最正確的決策,就是頂住市場要求強刺激的壓力,不輕易實施中央加槓桿,拒絕搞大水漫灌。當下特朗普對華加關税,我們手裏是有籌碼的。在與美國的博弈中,財政空間是戰略預備隊,相當於核威懾,在驚濤駭浪的時期可以穩住宏觀經濟大盤。中國和德國是世界上唯二擁有充裕中央財政空間的經濟大國,手裏有糧心中不慌,這是不服軟的底氣。面對美國的關税大棒,我國可以採取以時間換空間的策略,只要能靠寬財政支撐兩三年,事情就有可能迎來轉機。
另一方面,特朗普如欲調停俄烏戰爭,或需要中國配合,這是我國在跟美國打交道時的另一個籌碼。就算美國是超級大國,它也不具備三線作戰的能力,我國可以靠地緣手段來平衡關税壓力。
對大國來説,最重要的還是要把內政搞好。中國在制定經濟政策的時候是以未來5—10年為基準,而非僅考慮未來一兩年的情況。站在2021年的時點上,房地產泡沫是歷史遺留問題,與其繼續放任,靠拉地產維持虛假繁榮,等特朗普上台後加關税導致泡沫被動破滅,不如選擇外部壓力較小的時機主動刺破泡沫。事實上,2020—2021年的海外疫情為我國創造了兩年的窗口期,2022—2024年的俄烏和中東戰爭又牽制了美國三年,利用這個機會解決房地產問題,代價最小,風險最低。
從結果來看,過去四年我國擠出房地產泡沫取得明顯成效。從數據來看:
商品房銷售面積從2021年的18億平,回落至2024年的9.5億平。恢復至2009年的狀態,供需基本回歸合理水平。
房地產投資完成額從2021年的15萬億元回落至2024年的10萬億元,中國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度明顯下降。
居民部門槓桿率自2021年以來穩定在61%左右,沒有進一步攀升的趨勢,房地產信貸風險得到控制。
相比一手房,更具市場參考價值的全國二手房成交均價,基本回落至2017年水平,商品房逐漸從金融屬性迴歸為居住屬性。
可以説,經濟去地產化最艱難的階段已經過去,去年GDP能實現5%的增速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把去地產化類比為做手術的話,這場手術很成功,病變的器官已經被摘除,儘管在傷口癒合前仍會產生疼痛,但最大的風險隱患已經被排除。
雖然這幾年經濟增速不如2018—2019年,但經濟增長質量卻比那個時期更高,是剔除了地產泡沫後的高質量增長。試想如果2021年沒搞“三道紅線”,放任地產泡沫繼續膨脹,等特朗普二次上台後開啓脱鈎,那才是束手無策。好比某個器官面臨癌變風險,雖然令人遺憾,但正確的選擇是手術摘除,而不是放任不管等待危險來臨。
本文並不是盲目看多未來的經濟形勢,只是認為過去幾年的經濟政策,是權衡利弊後的最優選擇,兩害相權取其輕。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對房地產依賴太深,擺脱地產後伴隨的陣痛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但這種刮骨療傷的做法更符合長遠利益。
客觀地説,過去五年,中國在經濟去地產化的同時,產業升級也在同步推進。從鋰電池到電動車,從光伏到儲能,新能源經濟蓬勃發展。在國產芯片領域,雖然7nm製程仍待突破,但成熟製程已基本搞定。航空發動機和大飛機也取得進展,電磁彈射航母和六代機相繼問世。十年前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戰略,已完成了90%的指標。
另一方面,我國早就為中美脱鈎做準備,包括糧食安全(育種自主)、能源安全(雙碳)、經貿安全(雙循環)、金融安全(數字人民幣)、科技安全(自主可控)等。面對前所未有的關税壓力,我國亦保留了一定財政空間予以對沖。事實上,人類歷史上財政政策從來不單純是經濟問題,更是地緣政治問題,政府舉債行為必須結合外部安全形勢相機抉擇,即《預留政策空間,以應對驚濤駭浪》。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反而更有利於發揮制度優勢。不同的制度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在和平時期,西方的議會制能部分反應各個階層的訴求,有利於社會多元化;但在動盪時期,西方制度的缺陷會被急劇放大。二戰前,採用議會制的法國政治結構極其不穩定,政黨頻繁輪換,導致其無法形成有效決策,外交上屢屢犯錯,成為最早滅亡的大國。當下的美國亦是如此,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上台,使其無法執行長期戰略,削弱了來自盟友的信任度。
在某種程度上,檢驗一項制度好壞的重要尺度,是看它在動盪時期的承受能力下限。二戰時期蘇聯是歐洲唯一贏家,靠的是社會主義超強的動員能力。當下的中國模式,穩定可持續,可以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能更好適應亂紀元時期的殘酷競爭。即使經濟高速增長的全球化時代一去不復返,當下我國仍是全球最安全的地區之一。展望未來,要承認困難,但也要懷揣希望。
以上內容並非事後諸葛亮,筆者曾在三年半前提出過類似觀點,現附上當時文章的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