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玩遊戲會上癮、感動、憤怒?這些書嘗試寫下答案_風聞
游戏研究社-游戏研究社官方账号-1小时前

在人文學術語境裏,“遊戲”一直是很難馴服的野獸。作為相關領域的學生,閲讀數字人文論著時,我常常感覺自己在巨獸的脊背上顛簸,稍一不慎,龍一甩尾,我就飛出去了。
電子遊戲研究天生的硬核技術性和物質屬性,註定了它被“研究”時會受到阻礙——從知識儲備門檻、概念界定到大眾輿論,都是一條讓人有些望而生疑的路。它比以往的任何媒介都更加複雜,更加綜合,在大眾數字文化世界誕生,自下而上入侵學術領域,氣勢洶洶,非常迅速。
故正如本社的箴言:研究遊戲,也研究一切。遊戲研究的拓路者們,選擇的主題像他們的學術出身一樣,五花八門,幾乎沒有邊界。
而不管學者們落腳何處,整理遊戲以及它的歷史,都是進入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環。前些時間,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翻譯引進了一套#遊戲文化經典譯叢#叢書,首次面世於遊戲研究方興未艾的2006-2015年。

它們的作者,就在數字人文的語境裏,將“檔案整理與闡釋”做到了極致的奠基人。
遊戲檔案研究已有十數年曆史。從2000年後期的民間收藏夾和愛好者,到2019年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LGIRA等國際檔案數字化項目,再到2024年北京大學舉辦的首屆國際電子遊戲研究年會,遊戲檔案越發頻繁廣泛地被納入學術討論,電子遊戲也已經進入全球GLAM機構的研究與策展視野,被作為文化遺產進行保存和闡釋。
十數年來,賽博考古從未停止,甚至曾有人拿着“洛陽鏟”進行物理發掘——2014年,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雅達利大挖掘,是很讓人震撼的場面。1300多份遊戲卡帶,從垃圾填埋場的水泥沙土中被剝離,帶出遊戲史一大謎團的最終答案。

紀錄片《雅達利:遊戲結束》
從這次大挖掘開始往前回溯,卡利·克庫裏克通過《投幣機裏的美國》講述了一個充滿夢核色彩的故事。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的青年,只要他們經歷過上個世紀70、80年代,就一定會有深刻的共鳴。
一張遊戲精英玩家的合照,一款以暴力聞名的《死亡飛車》的誕生,一羣逃學遁入街機廳的少年少女,一場充滿輿論焦慮的訴訟……書中回溯了遊戲行業的形象在幾十年內發生的變遷,小到街機廳作為“公共空間”,其環境維護、門面裝點、氣味音樂甚至光線佈置;大到“允許”和“禁止”在遊戲合法性政策上從未停止的權力博弈,其間穿插着高分玩家的競贏傳統,競技體育的綁定對遊戲口碑的挽救,以及遊戲記錄系統的誕生與留存。遊戲行業的形象在不同人羣的抨擊和辯護中不斷變化,各方勢力此消彼長,塑造着遊戲,也塑造着遊戲玩家的身份。
很多議題我們至今依然關心。我們回顧那個懵懂年代,會看見自己手裏拿着遊戲機,在外界和內心各種聲音的質問中,試圖搞清楚我們是誰,以及“遊戲對我們來説意味着什麼”。
來自馬耳他的戈登·卡列哈在《宅茲遊戲:從沉浸到歸化》中也做出了他的解答。從一個更加微觀又更加抽象的層面,從《魔獸世界》和《星際Online(行星邊緣)》開始,他邀請我們一起觀察自己的遊戲體驗,同時觀察遊戲世界的其他玩家,並思考:沉浸於虛擬是一種自我欺騙嗎?嫺熟的技術能否超越精良的裝備,成為戰鬥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為什麼存在“迷路”的可能時,旅程會更有獲得感?
我們在遊戲中經歷的挫折,能不能對抗在現代世界中漸漸彌散的、巨大的無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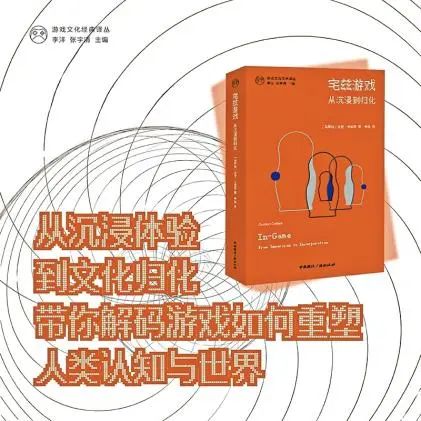
“我們應該避免認為沉浸體驗是由技術決定的。”
“遊戲涉入不僅僅體現為玩家的直接操作和屏幕上的呈現,還體現為玩家的認知努力,而這種努力不一定以某種輸入形式被記錄。”
學者們對遊戲的探討不僅限於玩家和遊戲體驗本身。如果説卡利和戈登在微觀層面探討玩遊戲,那麼下面兩本,則試圖告訴我們,遊戲能做的,或許要比我們想象中更多。
在《遊戲中的算法文化》的作者亞歷山大·R·加洛韋看來,電腦遊戲教給我們的,是一種與算法先關的思維結構,我們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將程序的邏輯內化。為了贏得遊戲,我們不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將自己限定在遊戲規則範圍之內,學會推斷、預測、計算反饋,最終,“我們的決策會絲滑得近乎直覺,迅速得就像決策是由計算機自身做出的一樣。”於是遊戲中的靈活性,看似具有烏托邦的色彩,賦予我們自由,但——
“千萬別被騙了;靈活性是全球信息控制的基本原則,是控制社會的工具,其功能與規訓無二。”
在博雅學術年會上,來自中國社科大的李苒舉出相似的例子:“反烏托邦職業模擬器”類型遊戲,通常會將職業簡化成“按鍵操作+進度條”,暗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實際上掩蓋了現實中的階級、運氣、剝削等問題。再比如,《請出示證件》讓玩家反抗極權政府,但反抗的方式依然是服從遊戲規則(按系統要求蓋章/放行) ,這讓人想到現實中抗議996的方式是“更高效地完成KPI”。
還有類似“做個好人就能贏”的“道德淨化”或“選擇自由”的幻覺——這類遊戲被看作“糖衣藥片”,我們也能夠察覺到其機制與現實之間的裂隙:外面是“批判社會”的苦味,裏面是“服從系統”的甜芯。
它們用遊戲的形式證明新自由主義連“反抗”都能做成商品進行售賣。像這樣,遊戲不易被察覺的“算法”底色——通過規則和代碼建構並規訓玩家行為——一方面為我們理解算法文化提供切口,另一方面,也提醒着我們對代碼控制及其內生的意識形態邏輯保持警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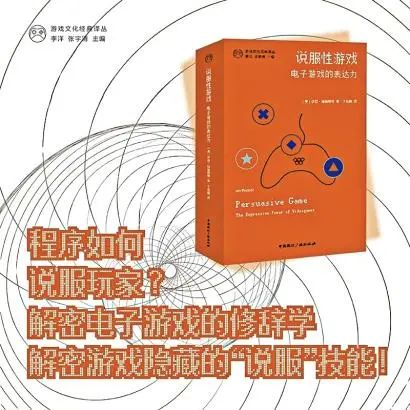
因此,從特定的視角來看,遊戲可以是具有修辭力量的系統,獨立於其他所有的藝術形式。正如伊恩·博格斯特在《説服性遊戲:電子遊戲的表達力》一書中所説,電子遊戲用“過程”作為論據,具有獨特的説服力,能夠成為實現制度目標的工具,也能在政治、廣告和教育三個方面,改變人們對世界的根本態度和信念,甚至引發社會變革。
“電子遊戲絕非機器的表達式。它們,是人之為人的表達。而驅動遊戲的邏輯則宣示着我們是誰、我們的世界如何運作,以及,我們希望它成為怎樣的世界。”
其他藝術都在呈現結果,但計算機藝術,或者説電子遊戲,是在描述過程。通過規則、交互和系統設計,而非語言或圖像來傳遞觀點、塑造認知並影響行為。
**遊戲能利用技術的黑箱,幫玩家打碎社會的黑箱。**這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已經並非新鮮事,因為我們已經見識過遊戲從小眾到主流的生長過程,也知道我們在玩《文明》或《模擬人生》時,會體會一些我們通過單純的“閲讀”或“觀看”或許很難理解的事物,比如種族與民族身份的建構,作為數據類型的身份,以及當代生活的匱乏和生存焦慮,等等。
在讀這套叢書的過程中,我能夠從理論性較強的句子中分辨出熟悉的味道來——這些感觸和觀點,我們似乎在很多地方看過——在Steam的評論區、貼吧的吐槽樓、微博熱搜、或者某個深夜玩遊戲輸到紅温的隊友的朋友圈。因為這些作者和我們一樣,擁有多重的身份:是玩家,是讀者,也許同時也是創作者。我們不僅在旁觀,也在切身經歷着遊戲為我們展現的社會和文化變革。
他們的工作難就難在,他們嘗試了統籌地研究整個遊戲圈,並將許多我們其實並不陌生的東西,提煉成一種比較抽象但極具結構力的哲學認識。
數字世界日新月異,這套書籍現在讀來或許不乏陳舊之處,但這些提煉允許辯駁和反對,也允許我們通過不同花紋和顏色的放大鏡,重新觀察我們所熟悉的電子遊戲。新的視角重組新的認知,我們就或許能夠帶着更清晰的視野,看見“遊戲對我們來説意味着什麼”,也看見我們自身的記憶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