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罪案劇,先要年輕人的“命”_風聞
肉叔电影-肉叔电影官方账号-1小时前
前幾天,有朋友在戛納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陸川。
他帶着《西野》來戛納放映。
這是聯想集團和陸川一起打造的,關於動物保護的短片,它講述的是一個關於“命”的故事,是犛牛的命,也是與動物打交道的人的信仰,也關乎於他們的“命”。
而主辦方Screen Daily在眾多影片中關注《西野》,也是這個原因。
不過,在戛納的圓桌會議上,我最感興趣的其實還不是這部影片拍攝有多曲折,而是陸川回應了他面臨的一些爭議——
製作、影評、公眾的反應,組成了一個完整的作品
我也希望人們給我掌聲,為我叫好
但更重要的其實是真實
不管是他們給你麪包,還是石頭
這都沒問題

爭議,這幾乎是陸川這幾年逃不脱的話題。
就像之前的《借命而生》,作為陸川這幾年來口碑最好的作品,其實也面臨着不少爭議,就像我之前説的,這部劇在技術層面堪稱優秀,內核抓得也非常精準,但陸川對於這個故事的把控力,顯然有所欠缺。
這也是看完整部劇後,我們覺得可惜的原因。
沒錯,我後來還是追完了《借命而生》。
不過今天,我並不打算再重複去聊它的優劣與得失,該説的話早已説完了,既有的觀點也依然保持不變。
我想從另一個角度聊一下它,以及它的“同類”們。
原因就在於,回過頭來再看,《借命而生》裏提出的這個“借命”的概念實在是太有意思了,你甚至可以從中窺見這些年國產年代犯罪劇,最隱秘的內核。
話不多説,先從劇集説起。
01
“借命”
沒錯,《借命而生》的內核其實並不是懸疑,也不是犯罪。
而是“借命”二字。
什麼是“借命”?
簡單來説,就是在時代浪潮衝擊下,小人物被摧折後失去反抗命運的力量,與活着的信念、動力後,將自己可以依附、寄生、“還魂”到另一個人身上。
他們以取代、繼承等方式。
在坎坷的生活中,擁有了一個微乎其微的,能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這樣的話聽起來似乎很玄。
我們不妨來看劇——
在《借命而生》裏,兩個犯罪嫌疑人徐文國、姚斌彬因為一場“不明不白”的兇殺案,而進了看守所。
而看管他們的獄警杜湘東並不認為這徐、姚兩兄弟是殺人犯。
可是,就在杜湘東在監獄外為他們二人找案件證據時,命運就在中途開了個玩笑。
一場車禍,讓徐、姚二人越獄。
被抓回來的姚斌彬,在還沒有找到確鑿的殺人證據的情況下,直接被判了死刑。
這場案子,就以一個槍斃,一個越獄的方式,結束了。

可是啊,姚斌彬的死,才是這個故事開始的第一步。
他被各種人,以被借命的方式“活”着。
首先是徐文國。
他之後逃亡、復仇的理由,實際上都是來自於姚斌彬。
正如他自己所説,“我欠了斌彬一條命”。

如果,沒有姚斌彬的奪槍,杜湘東的注意力就不會放在姚斌彬身上,那麼,徐文國就沒有藉機逃跑;
如果,不是姚斌彬要徐文國越獄,逃跑,也許他們二人都要走上刑場,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
徐文國,是“借”了弟弟的命。
這也是《借命而生》裏,最為直觀的“借”。
而杜湘東呢?
其實,他也是借了姚斌彬的命。
他覺得不只是徐文國
就連自己的這條命也是借來的
向姚斌彬借
向徐文國借
向劉芬芳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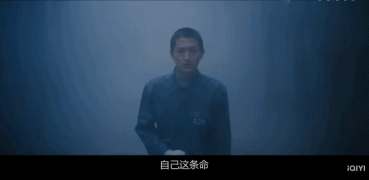
怎麼説?
實際上在姚斌彬死後,杜湘東活着的意義已經不再是為自己了。
而是為了姚斌彬。
他想弄清楚姚斌彬究竟是不是真的殺人了,想弄清楚有沒有冤枉好人。
更想彌補自己職業上的污點,捉拿徐文國。
他活在過去的時代裏。
也正是因此,哪怕是有了調回刑警隊的機會,他也沒有接受。
因為離開,似乎就意味着背叛。
而杜湘東所借的命,也遠不止姚斌彬一條。
還有妻子劉芬芳。
長時間追捕徐文國的杜湘東,常年不在家,妻子孕期急性大出血時,無人發現,死在了家中。
之後,他就一直活在劉芬芳死後,給他帶來的幻想裏。
幻想着他們一起過日子,一起聊天……

他一直愧疚地揹負着兩條人命,為了延續他們的期望而活。
他不得不活着,才能去做那些未盡之事,才能繼續在幻想中活着,用自己的命,換來救贖。
所謂“借命而生”。
實際上就是因他人而活,也為那個時代而活。
02
“借命”的共鳴
説起來,這種“借命”的概念,也並非是陸川,或者原著作者石一楓的首創。
他們只是把這概念明確的提了出來。
如果我們仔細去想,便會意識到,這幾年的年代犯罪劇,普遍地擁有和《借命而生》一樣的內核。
它們都強調“借命”這一個動作。
比如,在《漫長的季節》裏,沈默通過殺人“借命”,借殷紅的身份,繼續活着;
而她又借了王陽的命,在沈默自殺的時候,王陽因為救她,自己溺水身亡。
甚至,她也借了弟弟傅衞軍的命,是他的“自投羅網”,讓沈默跑了。

而,王響則借了王北的命。
在他想卧軌自殺時,卻被棄嬰的啼哭“叫”了回來。
他也借了沈默的命,只是一個背影,他就記下近20年。
他只想抓到兇手,還兒子一個清白。


今年上半年的8分懸疑、犯罪劇《沙塵暴》,也是如此。
段奕宏飾演的警察陳江河,為了追師父的車,而陷入了流沙裏,師父為了救他而出了車禍成為植物人。

《沙塵暴》裏,那件撲朔迷離的案子,也同樣是“借命”。
弟弟“借”了姐姐的命,師父“借”了徒弟的人生,妻子又“借”了丈夫的命。
他們相互寄生,又相互廝殺,直到在“掙命”時,又害死了自己。


在《三大隊》裏,張譯飾演的刑警程兵,為一樁懸案追兇20年。
當罹患胃癌的兄弟,目送程兵越走越遠時,他明白程兵的這條命,早就不屬於他自己了。
程兵揹負了受害人的命之外,搭上了自己的“命”,也借了自己兄弟的“命”。
他如果回頭,就是辜負了借來的“命”。

為何“借命”就成了犯罪片的共同特徵?
重大的變故下,人們才會開始正視自己的命運,像是沈默,她難逃被自己姨夫猥褻、掌控的命運,她想盡一切辦法,儘可能地找到救命稻草活下去。沈默是借,但,她的借,更像是一種破罐子破摔的“奪”。
她如果不去搶自己的命,下一次,在砧板上的就會是她自己了。
所以,“借命”的通常都是那些陷入困境的小人物,不論是通過什麼樣的手段去“借命”,是他們為了活下去理由也是不得已的選擇。
放在沈默身上,是一種不得已的自私;
放在程兵身上,又是一種幾近癲狂的無私。
但,目標都是殊途同歸,就是小人物要選擇一個活下去的方式,它伴隨着一種恥感、愧疚感,但也是活下去的執念。
而反之。
那些被“借命”的人,總是最為大公無私的,勇於分享的英雄。
王陽是,傅衞軍是,那些犧牲的、死去的、離開的人都是,就連彪子最後的信仰一躍,都成了給老幾位的安慰與開導——要樂樂呵呵的。
如此對比,你就會發現。
在借與被借中,死亡,都被富有了不同的意義。

03
被淘汰的小人物
這似乎是個巨大的巧合,不是嗎?
所有的年代犯罪劇導演,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同一種思路,他們塑造了一個個年輕的,早逝的生命,並相信,這世上,總有人記得他們,因他們而活。
這也讓這些犯罪劇們,呈現出一種漫長的憂傷,與哀悼的氣質。
但這世上哪有那麼多的巧合。
就像唐諾説魯迅,“一直用一種借來的聲音在説話”,這些年代犯罪劇裏一直重複這樣“借命”的母題,其實也是當代的創作者們,表達自己,用來“説話”的集體傾向。
它的重點從來都是被借的那條命,而不是借命的人。
《借命而生》裏有這麼一個情節——
許多年後,杜湘東發現了徐文國的蹤跡,他興沖沖地跑到刑警隊,試圖説服他全力圍捕。
可老同學潑了他一盆冷水:
過去有當年的重中之重
現在有現在的當務之急
明白嗎,兄弟

在大多數人眼裏,那些已經被定性的歷史,也就只能塵封下去了,那些歷史裏不清不楚的人,也就只能讓他們繼續面目模糊下去了,那些時代浪潮下,被淘汰的,不知名的小人物們,何必花費那麼大周折,去看清他們的面貌?
我們都是活在“當下”,也只能“向前看”。
可是啊,我們今天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過往一次次“失敗”的基礎上的,我們今天能夠自信地站着,往往也是因為有很多無名無姓的人,不得已地倒下,我們回望歷史,不是為了緬懷,更是為了更準確地和當下對話,去反思,去自省,去找尋未來的路。
所以專注當下當然沒錯。
回到歷史的情境中,去看着那一雙雙具體的眼睛,也同樣重要。
也正是如此。
當下的歷史研究者早已不再侷限大人物的故事了,他們關注的更細節——
可以是一段吆喝,“磨剪子嘞戧菜刀”。
也可以是一種氣味,夏天的柏油路上,蒸騰的柏油味兒。
甚至可以是一種姿勢,《翦商》裏記錄了商周時代墓葬裏各種各樣的姿勢,通過這些姿勢,還原了一段歷史……
總之,歷史是該有温度的,它是一個個個體的總和。
更因為如此。
當下的年代罪案劇創作者們,也不再像以往一樣,着重於描摹一個大時代大事件,也不再着重於描述案子裏的奇情,而是試圖塑造出一個個被歷史“淘汰”的小人物,並讓後人,藉由他們的“命”而繼續存在下去。
這是對具體的生命的銘記,也是對遠去的生命的憐憫。
更是對還願意回望過去的肯定。
就像《借命而生》裏。
導演讓杜湘東一直保有他的善良、愧疚,一直讓他“困”在那一年的夏天。
這在旁人看來是一種執念。
但對於杜湘東來説,那些過往的生命,那些無法付諸實現的情感,才是他活下去的最大動力。
這是一種對過去的銘記。

或是《漫長的季節》裏。
導演讓範偉最後説了那句很著名的台詞,“往前看,別回頭”。

這是一種積極的態度。
可同時,我們也知道,這樣的“當下”,其實是建立在對過去的全面釐清基礎上的。
沒有身後身,也就沒有眼前路可言。
所以説。
儘管當下的這些年代犯罪劇的質量有高有低,儘管抓住了內核並不代表就擁有了致勝的武器。
但我對國產年代罪案劇這樣的趨勢,還是會繼續期待。
它是一種理想主義。
也是一種勇氣。
而縱觀整個國產劇的環境,有這樣的創作意圖,本身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畢竟被即時滿足的當下。
誰還會關心,那些遠去的,一個個被時代淘汰的小人物呢?
本文由公眾號「肉叔電影」(ID:dusheyingdan)原創,點擊閲讀肉叔更多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