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臟病發作時,專家都出差了,這竟然是好事?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6分钟前
 醫生和患者常常認為醫療決策是基於科學研究的深思熟慮,但現實經常不是這樣,事實上醫學中存在的大量隨機行為。比如一些非常反直覺的研究表明,當高級別的醫學專家集體缺席時(因出席學術會議或醫生罷工),患者的死亡率反而降低了。如何解釋這些現象呢?
醫生和患者常常認為醫療決策是基於科學研究的深思熟慮,但現實經常不是這樣,事實上醫學中存在的大量隨機行為。比如一些非常反直覺的研究表明,當高級別的醫學專家集體缺席時(因出席學術會議或醫生罷工),患者的死亡率反而降低了。如何解釋這些現象呢?
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Anupam Jena與美國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重症監護科醫生Christopher Worsham在《醫學的隨機行為》一書中給出了答案,並充分展示出,醫療從來不是流水線上的精密零件,而是人性、系統與隨機事件的角力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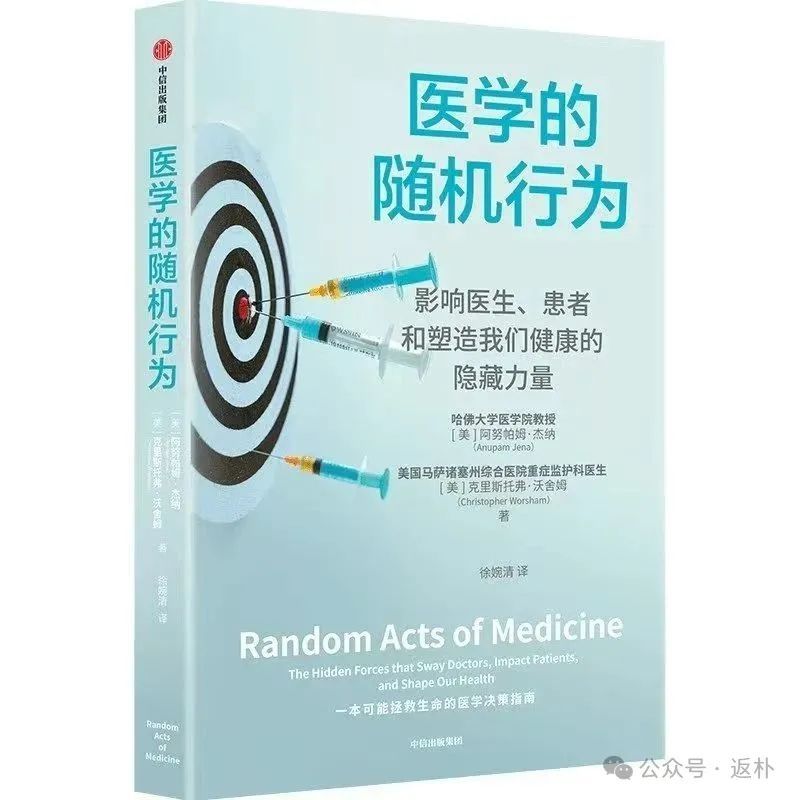 《醫學的隨機行為》,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4月
《醫學的隨機行為》,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4月
撰文 | 阿努帕姆·傑納(Anupam Jena)、克里斯托弗·沃舍姆(Christopher Worsham)
翻譯 | 徐婉清
美國有兩個大型心臟病學會,即美國心臟協會和美國心臟病學會,每年都會舉行大型會議。參加這些會議的醫務人員多達 2 萬人,其中許多人是執業心內科醫生。其他醫學專科的情況也是如此,這些專科每年在全球範圍舉辦數百次大型會議,每次會議通常會吸引數千名醫生參加。
這樣高密度的學術會議導致我們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試圖聯繫一位同事,因為他的病人需要治療,卻發現他恰好在拉斯維加斯、新奧爾良、芝加哥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參加學術會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通常會有其他醫生來替代這位同事完成工作。他們可能是經驗豐富的醫生,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參加此次學術會議,也可能是某些資歷較淺的醫生,由於沒有研究成果或發言任務而選擇不去參會。不管是什麼樣的醫生暫時頂替了這位同事的工作,都意味着該科室的實際工作人數減少了。
但是,患者的心臟病不會因為日程表上有全美心臟病學會議就不發作。正如我們之前描述的流程,無論是否有學術會議,當患者突發心臟病並撥打 911 時,急救團隊都會將患者送往附近具備救治能力的醫院。在大城市中,這類具備專業能力的醫院通常都是大型學術醫療中心。
這些機構之所以被稱為“學術”醫療中心,是因為它們隸屬於醫學院。這些大型“教學醫院”(有時人們會這樣稱呼它們)的醫生不僅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還從事大量醫學研究工作。這樣的醫院往往也是最先推出最新療法的地方。雖然我們兩位作者的研究可能並未涉及開發最新的外科技術或新型癌症療法,但我們與許多在學術中心工作的人一樣,都享受着這些工作環境所提供的科研氛圍。在這裏,下一個重大的醫學突破可能就隱藏在任何一扇門之後。
在心臟病學領域,學術醫療中心發揮着引領者的作用,致力於不斷提供並改進針對心臟問題的先進治療方法。這些醫療中心通常都配備了先進的“心導管室”。這是一類特殊的手術室,在這裏,受過高級培訓的心內科醫生可以對心臟病發作的患者迅速實施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也就是在冠狀動脈上安裝支架,以緩解導致心臟病發作的堵塞。一些學術醫療中心不僅能為患者提供專門的手術,還擁有具備處理複雜心臟問題能力的專業醫生團隊,比如泵血功能不足(心力衰竭)或心臟電活動紊亂(心律失常)。這些醫療中心是心臟病學研究和治療的匯聚點,能為患者提供最全面、最高水平的醫療服務。
與任何工作場所一樣,如果有同事缺席,無論是因為參加會議、休育兒假、擔任陪審員還是因病請假等,都可能會導致溝通不暢、錯誤和疏忽。在醫學領域,這種影響可能更為嚴重,因為每一個決定都可能直接影響到患者的生命健康。
常識普遍認為,醫院的醫生數量變少是不利的。比如,當醫院在週末人手不足時,心臟病發作等急診患者可能無法得到及時且有效的治療,從而影響治療效果。然而,醫生數量變少是否就一定會對醫療質量和患者安全產生負面影響?心臟病學會議或許能為我們揭示這一問題的答案。
不過先讓我們回到 40 多年前。在 1983 年,耶路撒冷的醫生們開始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在大約 4 個月的時間裏,醫生們決定停止提供除重要醫療服務(緊急狀況的處理、重症患者的救治以及生命維持系統的運作等)之外的所有服務,以此為手段與政府就工資問題進行談判。因此,許多選擇性手術被推遲,僅有幾個臨時救助站分佈在城市周圍,為患者提供門診治療。
耶路撒冷醫院的醫生數量大幅減少,由於此次罷工與病人的健康狀況無直接關聯,並非因人口健康狀況的突變而發生,這就為自然實驗提供了絕佳機會。在罷工前或罷工結束後生病的病人被歸為對照組,他們在正常時間接受了治療。而那些在罷工期間生病的患者則被視為干預組。對後一組人來説,醫生數量的減少是否意味着醫療水平的下降呢?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對罷工前後的死亡記錄進行了分析。令人驚訝的是,結果顯示,罷工期間的死亡人數與罷工前、罷工結束後,以及前一年同期相比,並沒有出現顯著增加。這表明,除重要醫療服務外,醫生的缺席並沒有導致死亡率明顯上升。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患者沒有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醫療延誤可能還是產生了其他並不明顯的影響。
自 1983 年以色列的那次醫生罷工以來,針對世界各地其他醫生罷工 a 的研究也顯示,在罷工期間,死亡率要麼保持穩定,要麼甚至有所降低。這使得許多人得出結論:醫生數量越多並不一定意味着診療狀況就越好(在基本服務仍然可用的情況下)。
那麼當有病人在全美心臟病學會議召開期間,因心臟病發作被送進醫院,她是否應該感到鬆一口氣呢?
心臟病學會議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我們能夠深入研究醫生人數減少對患者治療效果的影響。首先,我們先驗證了一個假設是可以成立的:即心臟病學會議召開期間,無論心內科醫生是否外出參加會議,患者的心臟病都有可能發作,那麼我們就可以着手尋找數據進行研究。讓我們看看一段 10 年時間的數據。在這段時間裏,美國心臟協會和美國心臟病學會共舉辦了 20 次大型年度心臟病學會議,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切入點。為了更好地瞭解急性心臟病患者的狀況,我們使用了醫療保險數據,詳細調查了在 2002—2011 年間全美各地因心臟病發作、心臟停搏或心力衰竭而住院的患者信息,包括每次住院患者的入院日期、是否進行了專業的心臟手術(如心臟支架植入或搭橋術),以及是否在出院後 30 天內死亡。
我們進一步研究了這些住院事件與美國心臟協會和美國心臟病學會年度會議的關係。在年會期間接受治療的患者被劃入治療組,而在年會之前或之後接受治療的患者則歸入對照組。為了確保對照組與治療組在各方面儘可能相似,我們只考慮了每次會議前後三週內因心臟問題住院的患者。最終,我們收集並分析了超過 20 萬名患者的數據。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確保治療組和對照組的住院病人在除患病之外的其他方面也相似。結果顯示,兩組患者在男女比例、平均年齡(79 歲)、種族分佈,以及患有心臟病、糖尿病、腎病、高血壓和高膽固醇等既存病症的比例方面基本沒有區別。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他們出現急性心臟問題的風險。
我們預計,根據患者患病風險的高低(即他們死於心臟問題的可能性有多大),死亡率可能會有所不同。由於風險較高的患者(通常是指原有基礎病較多的患者)更有可能需要複雜的介入治療,所以心內科醫生的缺席對他們的影響可能更大。所以,根據患者的基礎情況,我們將患者進一步分為“低風險”和“高風險”兩組以進行深入研究。
初步分析支持了我們的假設,即無論是否正在召開心臟病學會議,兩組患者出現急性心臟問題的風險相同。這意味着自然實驗的前提條件已經滿足。我們現在可以合理地推斷,兩組之間死亡率的任何差異都可以歸因於他們所接受的治療的不同。
那麼,我們具體發現了什麼呢?讓我們從“高風險”患者講起。
我們發現,在 6000 多名出現了心力衰竭或心臟停搏的高危人羣中,在全美心臟病學會議期間住院的患者死亡率明顯低於非會議期間。也就是説,在醫生人數較少的時候就診的高危患者,比在醫生正常工作的時候就診的患者,更有可能在治療中存活下來。這種差異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高危心力衰竭患者在非會議期間的 30 天死亡率約為 25%。而在學術會議期間,30 天死亡率則降至17%。換言之,這一研究結果表明,每 100 名在非會議期間入院的高危心衰患者中,就會有 25 名在 30 天內死亡,而如果這 25 名患者在會議期間入院,就能有 8 人倖存下來。同樣,在心臟停搏患者中,我們也觀察到了類似的情況:在非會議期間入院的高危心臟停搏患者死亡率為 69%,而在會議期間入院的患者死亡率為 59%。
與此同時,心臟病發作的死亡率似乎並未發生顯著變化。接下來的問題是:患者接受的護理是否存在差異?事實證明,確實存在差異。我們發現,在非會議期間,心臟支架植入(一種改善心臟病患者心臟血流的侵入性手術)在高危患者中的使用率為 28.2%,而在會議期間這一比例降至 20.8%。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這些發現只代表在學術醫療中心展開的治療。對於大約 5 萬名不在學術醫療中心接受治療的高危患者(一般在社區醫院接受治療),治療組和對照組的死亡率沒有差異。我們從一開始就假設,教學醫院的心內科醫生最有可能參加會議,他們是努力站在自己領域最前沿的醫生,也是會議的目標人羣。教學醫院和社區醫院之間的結果差異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教學醫院的心臟病治療在會議期間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工作人員的差異是最有可能的原因。
目前的結果顯示,在研究人員聚集的學術醫療中心,當心內科醫生不在時,風險較高的患者的治療效果似乎更好。雖然這一初步發現很有趣,但要讓這一結論更可信,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工作。
為了驗證我們的研究結果是否確實由心臟病學會議引起,我們進行了一系列進一步的分析。首先,我們考察了心臟病患者的治療結果是否只受心臟病學會議的影響,而不受一般醫生會議的影響。結果證實,當整形外科醫生、癌症醫生和腸胃科醫生外出開會時,心臟病死亡率並未發生改變。由此可見,心臟病學會議是造成這些變化的根源。
其次,我們需要確認上述結果是否反映了全院範圍內的死亡率變化,即心臟病學會議期間會不會恰好是全院死亡率降低的時間。由於心內科醫生主要負責心臟病患者的治療,並不參與醫院大多數其他類型患者的治療,所以我們認為心臟科學術會議不太可能對其他類型患者的治療產生干擾。然而,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我們對非心臟疾病的死亡率進行了分析,如髖骨骨折、胃出血等。我們採用了原來的心臟病學會議日期,以瞭解這些疾病在心臟病學會議期間是否存在治療效果方面的差異。結果不出所料,心臟病學會議只對心臟病患者產生了影響。
經過上述排查工作,我們最大的疑問依然存在:為什麼會這樣?究竟為什麼在全美心臟病學會議召開期間,學術醫療中心的高危心臟病患者死亡率較低?
我們越來越確信,答案就在醫生自己身上。要了解更多信息,我們需要深入瞭解心內科醫生及其診療習慣。
在另一項研究中,我們(巴普、安德魯·奧倫斯基、達納·戈德曼、約翰·羅姆利、哈佛大學心內科醫生兼衞生政策研究員丹尼爾·布盧門撒爾和羅伯特·葉)再次利用了醫療保險數據,但這次我們將研究範圍縮小到了學術醫療中心的心臟病發作患者。我們還專注於研究一種特殊類型的心內科醫生,即介入心內科醫生。他們主要負責對心臟病發作患者的心臟進行專門的介入治療,例如冠狀動脈支架植入(普通心內科醫生通常不進行此類手術)。我們希望通過關注介入心臟病學會議期間心臟病發作住院患者的情況,來準確地瞭解當這些醫生不在場時醫療服務所發生的變化。
因此,我們研究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心臟病發作:一種是通常需要特殊手術的嚴重心臟病發作(稱為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或STEMI),另一種則是不太嚴重的心臟病發作(稱為非 STEMI),有時需要進行特殊手術。需要明確的是,非 STEMI 雖然相對較輕,但仍然是一個嚴重的醫療急症,需要及時治療,否則可能會給患者帶來生命威脅。心內科醫生將兩者區分開來的原因是,非 STEMI 中發生的冠脈堵塞往往不如 STEMI 中的堵塞那麼完全,因此對不完全的堵塞進行危險的手術可能並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介入心臟病學會議期間,非STEMI 患者(是否實施手術的決定更為主觀)接受心臟支架植入的可能性較低,死亡率較低。
所以,當一名老年心臟病患者在學術醫療中心因非 STEMI接受治療時,他接受手術的概率會降低,但30 天后存活的可能性卻升高了。然而,當穿着嶄新白大褂的年輕心內科醫生與羅伯塔交流時,她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
我們描述的影響有多顯著呢?從表面上看,這些影響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對於病情較輕的心臟病患者,學術會議期間的死亡率從 15.9% 降至 13.9%,下降了 2 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率的降低完全歸因於未接受手術的患者,在心臟病學會議期間,他們的死亡率從 19.5% 降至 16.9%,而接受手術的患者的死亡率則保持不變。
換句話説,問題的核心在於,一些本不需要做手術的患者在非會議期間接受了手術治療。
死亡率上升兩個百分點意味着什麼?每 50 名因非 STEMI 而到教學醫院就診的醫保患者中,就有 1 人如果在學術會議期間就診將得以倖存,而在非學術會議期間就診就會死亡。如果這個差異還不夠明顯,我們可以再通過一個對比來理解:死亡率降低兩個百分點大約相當於我們採用了現有的一些治療心臟病發作的最佳療法所取得的效果。例如,對因 STEMI 住院的各年齡段患者進行的臨牀試驗表明,與改善心臟血流的靜脈注射藥物(稱為溶血栓藥)相比,心臟支架植入可將死亡率平均降低兩個百分點。
這些侵入性手術的成本和風險都相當高,但其改善死亡率的效果卻與會議期間自動發生的變化不相上下。
我們希望進一步瞭解所研究的介入心內科醫生,包括參加會議和未參加會議的兩組醫生。從初步觀察來看,兩組醫生存在一些相似特徵。首先,介入心內科醫生幾乎都是男性,在參加會議的醫生中,男性佔 95.4%,未參加會議的醫生中男性比例也高達96.0%。其次,兩組醫生的平均年齡均為 51 歲,並且他們的行醫時間也大致相當。
然而,兩組醫生之間也存在一些顯著的差異。相較於未參加學術會議並留守醫院的醫生,參加會議的醫生更有可能在排名較高的醫學院就讀(二者分別佔比 15% 和 23%)。此外,他們也更有可能領導過臨牀研究試驗(分別佔比 3.9% 和 10.3%)、獲得過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的研究基金(分別佔比 0.4% 和 5.3%),以及在醫學期刊上發表過論文(分別平均發表 6 篇和 19 篇)。
參加會議的介入心內科醫生與留守醫院的介入內科醫生之間的另一個主要區別在於他們每年做的心臟手術數量。與參加會議的專家相比,留守醫院的醫生不僅在會議期間進行的心臟手術較少,而且全年進行的心臟支架植入手術也較少,平均每年為醫保患者做的心臟手術數量比參加會議的醫生做的少 39%。
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當你的心臟出現問題時,你會選擇哪位醫生來進行治療?是那些擁有頂尖醫學院學位、發表過大量論文、擁有熟練手術技能的醫生,還是他們那些看起來資質平平的同行?在研究之前,我們可能被令人印象深刻的資質所影響。然而,現在我們發現,對於某些患者,那些傾向於採用更具侵入性的心臟治療方法的醫生,可能不僅提供了不必要的治療,還會對患者造成傷害。
這些研究結果存在爭議。許多心內科醫生認為它們令人難以置信,他們甚至直言不諱:這些研究結果是要醫生全年召開學術會議嗎?有人認為它們僅僅是雞尾酒會上的談資,並不具備實際操作性。在最初的研究報告發布後不久,美國心臟協會主席也表達了他們的疑慮:“歸根結底,對我們美國心臟協會來説,在這項研究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可以讓我們改進臨牀實踐的建議。”
儘管受到批評者的質疑,這些研究結果仍然揭示了一些重要信息。它們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某些形式的侵入性心臟治療手段在臨牀上可能被過度使用了,這主要是因為心內科醫生缺乏精確的指導方針來判斷哪些病人能從這樣的治療中受益,哪些病人不能。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心內科醫生麗塔·雷德貝格博士在隨研究發表的評論中寫道:“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些發現?一種可能是,對心力衰竭和心臟停搏的高危患者進行更多幹預會導致死亡率升高。而在現實醫療環境中,一些高風險干預措施,如球囊泵或心室輔助裝置,也可能被用在那些沒有證據顯示可以從治療中獲益的人羣身上。”
所有醫療服務,尤其是心臟支架植入等侵入性手術,都存在風險和益處。隨機對照試驗可以幫助醫生了解哪些類型的患者接受醫療服務的平均益處會大於風險。然而,對坐在醫生面前的患者來説,通常情況下未必如此。這就是醫生在決定提供何種治療時都要進行臨牀判斷的原因。他們需要綜合考慮患者的具體情況、病史、身體狀況等多個因素,以確定最適合的治療方案。
有些臨牀決定是明確且直接的,比如,對一個沒有其他重大疾病的中年人來説,如果他患有某種類型的嚴重心臟病,那麼選擇心臟支架植入通常是正確。但其他一些決定則更為複雜:對患有多種疾病的老年婦女來説,即使她的心臟病類型與前述中年人完全相同,心臟支架植入的風險也可能會大於益處。如果一些醫生傾向於為這類患者實施支架植入手術,那麼總體而言,這些患者很可能會因為這種手術而受到傷害。因此,對於這類患者,少做一些醫療干預或許會更好。
這是醫學實踐中最為關鍵的問題,也是我們經常捫心自問的問題:這種手術、藥物或檢查對病人的益處是否大於潛在風險?由於患者的情況千差萬別,所以在臨牀評估時,即使有高質量的隨機試驗可以作為參考(現實中往往缺乏這樣的研究),不同的醫生也可能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這也正是醫學的複雜性和獨特性。
現在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假設一位心內科醫生同時接診了 200 名心臟病患者,並被告知只能為其中的 50 名患者實施心臟支架植入手術。雖然不同的醫生在確定優先考慮哪些患者時可能會有所差異,但心內科醫生應該能夠相對容易地從 200 名患者中篩選出那些能從心臟支架植入中獲得更多益處而不是風險的50 名患者。
當然,病人並不會以這種方式出現,而且對我們的目的來説,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心內科醫生不會面臨這種限制。他們通常會利用全部所學來幫助患者減輕痛苦和疾病。這種心理會促使心內科醫生自覺或不自覺地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
傾向於“過度治療”的醫生可能會為那些會從手術中面臨更多風險而不是益處的患者實施手術,從而導致部分患者的治療效果更差。相反,傾向於“保守治療”的心內科醫生也可能會使那些本可以從手術中獲益的患者錯過手術。作為一名醫生,你可能時刻受到“反事實”的困擾:如果我採取了行動,患者是否會獲得更好的療效?如果我沒有采取行動,又會怎樣呢?
我們在這裏討論的是一種採取行動的傾向。通常,醫生會有更強烈的傾向提供更多的治療措施,而不是減少治療干預。不過,這種想法並不僅限於醫生,實際上,這是人類的普遍心理。
想象一下,在足球比賽中,當球員獲得點球機會時,他們有機會在 11 米外將球踢進球門,此時守門員需要面對的是除球員本人之外沒有其他對手的局面。一旦球員踢出球,守門員的任務就是阻擋球進入球門。在這種情況下,守門員面臨三種選擇:向左側躍起、向右側躍起或留在球門中央。由於點球的速度非常快,球員會小心翼翼地避免通過肢體語言暴露自己的真實意圖。因此,守門員實際上沒有時間在採取行動之前看清球的走向,向兩側躍起只是由於猜測球員可能會將球踢向某處。
研究人員對頂級職業聯賽中的 286 個點球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防止進球的最佳策略是守門員原地不動並站在球門正中間。但實際情況中,守門員有 94% 的時間會選擇向一側跳起。顯然,守門員選擇跳起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傾向於採取行動來阻擋足球。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德博拉·格雷迪博士和麗塔·雷德貝格博士對醫生的這種傾向進行了研究。2010 年,她們在發表於《內科學文獻》雜誌上的文章中寫道:“美國臨牀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有時可能是過度的,這背後有多種原因。比如,支付系統對於診療程序的激勵遠大於對與患者溝通的激勵;患者往往將更多的檢查和干預等同於更好的治療護理;新技術的吸引力;開具檢查單或處方可能比向患者解釋他們沒有得到治療的原因更方便快捷。當然,防禦性醫療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技術蔓延’:當一種療法被批准用於高風險人羣並證明對其有益後,其使用範圍往往會擴大到低風險人羣,然而在這些人羣中,這種療法帶來的風險可能會大於益處。”
讓我們再次回到羅伯塔和心臟病學會議的問題上。參加學術會議的心內科醫生是否更有可能在弊大於利的情況下采用特定的治療手段?這些醫生是否受到“當你只有一把錘子時,一切看起來都像釘子”這句諺語所描述的偏見的影響,無意中對某些患者提供了過度的醫療服務?而那些在會議期間留守醫院的心內科醫生是否不容易出現這些傾向呢?
雖然數據無法明確回答上述問題,但將責任全部歸咎於參加會議的醫生並不公平。在會議進行期間,心內科醫生的人員配備和覆蓋範圍可能會有所減少,導致某些特殊手術的實施數量減少。這些研究揭示了一種特殊類型的過度醫療傾向,這種傾向在我們中間無聲無息地發生着,這是隨機試驗無法觀察到的。
阿希什·傑哈博士,現任布朗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及喬·拜登總統的新冠疫情應對協調員,在 20 世紀 90 年代作為一名醫學生時,就開始關注醫療質量問題。他回憶道:“在醫院病房照顧病人的過程中,我意識到可能存在過度醫療的問題。”他通過觀察和研究發現,儘管醫生和護士都非常努力,但病人往往無法得到恰當的護理,甚至會在治療過程中受到傷害。
“減少醫療干預”並不是新近提出的觀點,但這與人們的直觀感受相悖。比如,人們可能會認為,如果心臟病是由冠狀動脈堵塞引發的,那麼打通堵塞的動脈應該是對治療有利的吧?同理,乳房 X 光檢查和宮頸塗片檢查對於及早發現乳腺癌和宮頸癌是有效的,那麼為何不能頻繁檢查?但在醫學領域,我們有時會發現減少檢查、治療流程以及給患者的信息量反而能帶來更好的效果。不過,這一概念對醫生和患者來説,都是難以理解和接受的。
例如,轉移性肺癌是指已經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的嚴重肺癌。由於癌症擴散後治癒難度大,治療方法有限,所以這種晚期癌症患者在確診後的期望壽命非常有限。儘管許多患者尋求治療以延長生命(最近開發的新療法也的確延長了患者的期望壽命),但轉移性肺癌患者的生活可能會充滿困難和痛苦。
姑息性治療是醫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其核心目標是緩解不舒服的症狀。對轉移性肺癌患者來説,姑息性治療主要關注如何減輕導致患者生活質量嚴重下降的症狀,如呼吸困難、疼痛和焦慮等。同時,姑息性治療也會結合化療和其他癌症靶向治療,以儘可能地延長患者的生命。
在 2010 年,哈佛大學的腫瘤科醫生兼姑息性治療研究員詹妮弗·特梅爾及其團隊招募了 151 名剛被診斷為轉移性肺癌的患者,並進行了一項研究,旨在探究姑息性治療服務是否能延長患者的生命。在確診後,這些患者被隨機分配接受以下兩種治療:(1)標準的癌症治療,同時允許他們在需要時選擇接受姑息性治療;(2)在接受標準癌症治療的同時,立即獲得姑息性治療服務,以確保患者不僅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而且在整個癌症治療過程中都能得到這些服務。
在對這些患者的癌症治療過程進行全程跟蹤後,研究發現,接受早期姑息性治療的患者比未接受早期姑息性治療的患者平均多活了 2.7 個月(11.6 個月對比 8.9 個月),並且接受早期姑息性治療的患者的生活質量和情緒也有所改善。這項研究的關鍵發現,也正是我們現在提出的問題:接受早期姑息性治療組的患者在接受姑息性治療後,不僅平均多活了 2.7 個月,而且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接受的癌症治療更為温和,側重於更簡單的、基於症狀的治療。通過姑息性治療緩解症狀,病人更加舒適,壽命也更長,同時令人不適、風險高、成本高的化療也因此而減少了。
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和《消費者報告》認識到了推廣“減少過度醫療”這一概念的困難性,於是在 2012 年發起了“明智選擇”運動。該活動為醫生和患者提供了有關“可能不必要”或“有害”的醫療服務的科普信息,旨在“促進臨牀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交流,幫助患者選擇有證據支持的、不重複的、無傷害的和真正必要的醫療服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明智選擇”發佈了數十個清單,列出了許多不同醫學領域中“少即是多”的情況。例如,他們建議“不要對肺癌低風險患者進行肺癌 CT 篩查”。
如果在錯誤的患者身上進行,這些篩查掃描往往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會檢測出假陽性結果或不需要治療的小問題,造成過度醫療的情況。這種趨勢也同樣適用於重症病人,他們可能會在某些方面受到過度的治療,而在另一些方面,如預防或心理保健上,受到過少的照顧。
如果仔細回想自身經歷,大多數醫生會承認他們傾向於提供更多的醫療服務。我們兩人也不能免俗。有時,即使非常確定是病毒感染、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我們仍會選擇預防性地讓患者使用抗生素;有時,即使知道患者患罕見外來疾病的概率極低,我們仍會讓其做大量相關的檢查(這種策略被稱為“霰彈槍”式診斷方法);有時,即使根本不指望通過影像掃描發現什麼陽性結果,我們仍會為了“以防萬一”而為患者進行全身各處的 CT 檢查。然而,每隔一段時間,這些原本“不必要”的檢查結果就可能會挽救一個人的生命,這進一步強化了做更多檢查的趨勢。
我們該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呢?正如哈佛大學心內科醫生、作家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國家通訊員麗莎·羅森鮑姆博士所説:“也許最準確的結論是,有時少即是多,有時多即是少,而我們往往就是搞不清楚。”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觀點,但作為執業醫生,我們不能否認它的真實性。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通過不斷的學習和研究,努力去照亮那些模糊的灰色地帶,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它們能夠變得更加清晰。
説到這裏,我不由想起曾在醫學院遇到的一位經驗豐富的外科醫生,他在評估一名情況不穩定的患者時,曾提出過這樣的建議:“什麼都別做,待着就行。”這句話最初出自20世紀40年代,是一位因演員表演過火而憤怒的戲劇製作人説的,它也是“做點兒什麼,別待在那裏”的反語。實際上,儘管很難接受,大多數醫生都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為當你站在病牀前,面對一位處在生死關頭的患者時,有人問你:“醫生,我們該怎麼辦?”你往往很難回答:“什麼也不做,我們先繼續觀察。”
作者簡介
阿努帕姆· 耶納( Anupam Jena),哈佛大學醫學院約瑟夫· P.紐豪斯教授、 醫學博士、 經濟學家, 《貝克爾醫院評論》 評選的“ 100 位健康護理領域的偉大領導者” 之一, 他還主持了一檔名為“魔鬼經濟學” ( Freakonomics) 播客, 幫助患者和聽眾瞭解健康護理的隱藏面, 做出最佳的醫療決策。
克里斯托弗· 沃舍姆( Christopher Worsham),哈佛大學研究員、 醫學博士、 馬薩諸塞州總醫院肺科醫生和重症監護醫師。 他的研究成果經常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美國醫學會雜誌》 《英國醫學雜誌》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華盛頓郵報》 等學術期刊和大眾媒體上。
本文經授權摘編自《醫學的隨機行為:影響醫生、患者和塑造我們健康的隱藏力量》(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4月)。
 特 別 提 示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