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巴黎街頭的學生夢到東方紅太陽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6分钟前
文 | 北方朔風
説到貝託魯奇這名導演,他在國內最為知名的作品應該是《末代皇帝》,讚許的人會稱讚他的電影美學,批評的人會認為他還是有着濃厚的東方主義情調。今天想要和大家聊聊他的另一部電影,一部很適合當下去討論的作品,《戲夢巴黎》。(本文含有劇透)

貝託魯奇
近代以來,巴黎是浪漫的代名詞,不同時代的巴黎,有着不一樣的風情。不過《戲夢巴黎》劇情的時間點,巴黎的風格毫無疑問最為與眾不同,因為劇情發生的時間是1968年。
相信對於歐洲歷史有基本瞭解的讀者都知道,這年五月,歐洲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那就是五月風暴。由於貝託魯奇作為左翼導演的背景,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是一場關於革命與社會運動的電影。
大體如此,但是在整部電影中,那場浩浩蕩蕩的社會運動只是作為某種背景。至於“戲夢”二字,指的則是電影。電影中主角三人,法國的孿生姐弟和美國交換生,都是電影愛好者,他們之間的很多交流都與電影相關。
五月風暴的發生雖然有多種原因的綜合,但直接起因也與電影有關。1968年,法國文化部試圖解僱當時的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亨利·朗格盧瓦,導致文化界大範圍的不滿,也助推了五月風暴的發生。當時法國的新浪潮電影在全球電影行業都有巨大的影響力,那大概是法國電影最為輝煌的時代。那個時代,確實有很多藝術工作者與愛好者真實的相信,電影是與資本主義鬥爭的一種新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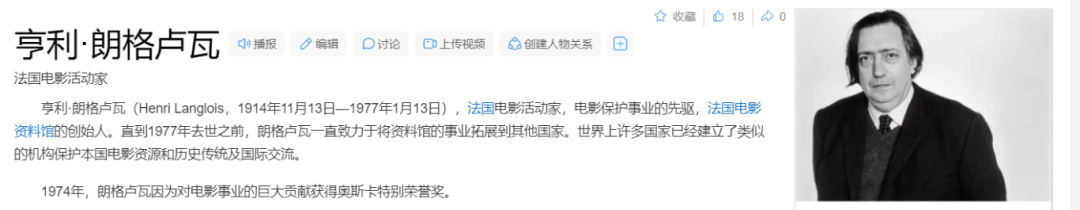
當時歐洲電影評論的核心,也在法國,當時樹立出來的電影評論範式,至今仍然有巨大的影響力,像齊澤克的很多電影評論也可以説是對於那個時代的模仿。《戲夢巴黎》中三位主角跑過盧浮宮走廊的畫面,也是對法國新浪潮核心人物讓.呂克.戈達爾的電影《法外之徒》的致敬。戈達爾的電影風格,對貝託魯奇產生了很大影響。
《戲夢巴黎》中,無論是法國的兄妹里奧與伊莎貝拉,還是來自美國的交換生馬修,在電影大部分情節中,對於五月風暴這場浩浩蕩蕩的運動其實都不是很積極。雖然三個人經常討論各種社會問題,但馬修對於革命遠沒有里奧那麼積極,他認為里奧並不真的懂什麼是革命。**連接這三人的,是三個人扭曲的肉體關係與情感。**最終,因為三個人關係的破裂,里奧和伊莎貝拉加入了遊行隊伍,而馬修只是在看着。

看起來貝託魯奇似乎在解構這場運動,把五月風暴這場運動降格為青春的迷茫。觀眾應該怎麼理解呢?或許從貝託魯奇的另一位老師出發可以看出端倪。。除了戈達爾,對貝託魯奇的電影和思想有重大影響的另一位導演是帕索里尼。這個名字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但是如果説到一部電影,大家應該都聽過,那就是《索多瑪120天》。
久聞《索多瑪120天》大名的人可能會以為帕索里尼是一個拍重口味電影博出位的導演。實際上帕索里尼是當時意大利最著名的左翼文藝工作者之一,他拍攝那麼重口味的電影,一大原因是出於對原作者薩德侯爵的研究,**意識到性與暴力和政治的關係。**後來大量從精神分析角度研究政治的歐洲哲學家,都借鑑了帕索里尼的理論,貝託魯奇在《戲夢巴黎》中的各種限制鏡頭,很大程度上也是對帕索里尼哲學的模仿,通過身體來展示觀點。
一次意大利學生和軍警發生衝突時,帕索里尼寫了一首詩,大概意思是“那些學生也只是小資產階級,只不過是對於自己的父母的叛逆,才選擇投身這些事情,而那些軍警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也不會幹這樣的苦差事。”《戲夢巴黎》的基調和這個十分類似。

帕索里尼
里奧的革命熱情很大程度來自於出自對自己父母的叛逆,而來自於美國的馬修,風格更接近美國式的“要愛,不要戰爭”。在里奧的父母離開的時候,三人的小窩是如此的脆弱,以至於三人要結伴自殺的時候,屋子被路人的一塊磚頭破壞。夢就是夢,夢就是這麼脆弱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説,貝託魯奇也算是重複了帕索里尼的觀點。
站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該怎樣理解這種觀點?《戲夢巴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是否對當時的社會運動進行了徹底解構?或者説,我們該怎麼理解五月風暴和它之後的影響呢?這場運動即使過去了半個世紀,對於思想界的影響依然沒有一個絕對的定論。但不論是左右翼,有太多思想的派別都是在這場風暴中誕生的。有的東西,我們確實應該回頭看一看。
60年代歐美的社會運動,是否有太多浪漫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因素?答案是肯定的,**不論是搖滾樂,迷幻劑還是靈脩,當時都被賦予了對抗資本主義的意義。**毫不意外,這些東西后來都被資本主義體制化了,從邊緣行為收編進主流文化了,甚至成為資本主義個人自由的牌坊,電影也是如此。
今天再回頭看,這些東西真的可以對抗資本主義嗎?的確,當年的年輕人用這些事物寄託對現狀的不滿,無論口號如何,終歸是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只要把時間尺度稍微拉長一些,寄託在這類事物上的“革命性”往往馬上就會褪去。

我們也要承認,翻看我國革命先烈們的歷史,很多人最初參加革命的理由是非常個人化的,並沒有明確的理想。我們也確實不能指望,參與社會變革的每個人都有統一的理想,這本來就不現實。但過度強調個人主義的“革命”從來不會真正成功,這就是歷史反覆告訴我們的。
對新自由主義相當有研究的大衞哈維曾經寫過,一切過度強調個人自由的運動,最終都有可能被新自由主義收編。雖然説大衞哈維一向是比較悲觀的,**但是這種悲觀,一大原因不就來自於六八年之後的迷茫嗎?**這半個多世紀裏,推崇個人自由的左翼思想家,在後來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簇擁的情況不也出現了不少嗎?如果福柯再活個十年,成為某種新自由主義全肯定專家,那場面一定會很有趣。
那麼,五月風暴算是勝利還是失敗呢?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場社會運動的目標是什麼,只有明確了這個問題才能進行討論。應該説,雖然戴高樂政府再次當選,但是戴高樂政府依然被迫做出了讓步。一些左翼史學研究者認為,當時法國學生的鬥爭方法與路線如果繼續優化,是有可能把戴高樂趕走的。
這種歷史假設的可能性我們不作評價,但就算是能把戴高樂趕走,就足夠了嗎?當時歐洲的左翼知識分子對這場運動抱有太大的期望,認為這是終結或是改變資本主義的一場序曲,假如以這個作為目標,只趕走一個戴高樂,是遠遠不足的。
軍事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制定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戰略目標,會導致軍事上的失敗。對五月風暴寄予了巨大期望的知識分子們也是如此,他們本來想看到巨大的改變,但是實際上只改變了一點點。**這種失望的情緒至今影響甚深。**所謂的政治正確思想與當年運動的失敗也有關係;筆者之前也寫過,尼克蘭德那種加速主義毀滅一切的理論,也帶着五月風暴失敗之後的迴響。
但話説回來,那種嚴格制定的計劃什麼的,是很不受年輕知識分子待見的,當年歐洲知識分子不喜歡蘇聯,一定程度也和這個有關。而他們對毛主席的推崇,一個原因是主席體現的浪漫主義氣質。雖然如此,《戲夢巴黎》中牆上貼着的主席海報,和主角三人複雜關係的畫面放在一起,實在是太有種荒誕的東方主義質感。

主席毫無疑問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這樣的氣質對於歐洲從古典時代以來的哲人王崇拜文化來説,無疑是極富魅力的。可是説到底,哲人王只是古典時代的哲學家基於當時的生產力的一種想象,遠遠不能用來形容當下的社會。而毛主席之所以偉大,在於他領導黨和人民,把中國從混亂中帶出來。這個驚天偉地的歷程,顯然只靠浪漫主義與哲學是做不到的。
近代以來,好像還沒有什麼重大社會進程是隻靠哲學與浪漫就實現的。這並非單純是知識分子和學生們脱離羣眾,而是當代社會的特點導致的。社會分工極度複雜化,個人對於社會的理解會顯得十分有限。這也是帕索里尼詩歌中提到的問題,資產階級學生和無產階級軍警,誰更加進步?五月風暴中,學生與其他各方的訴求,又是否一致呢?誰又是值得團結的力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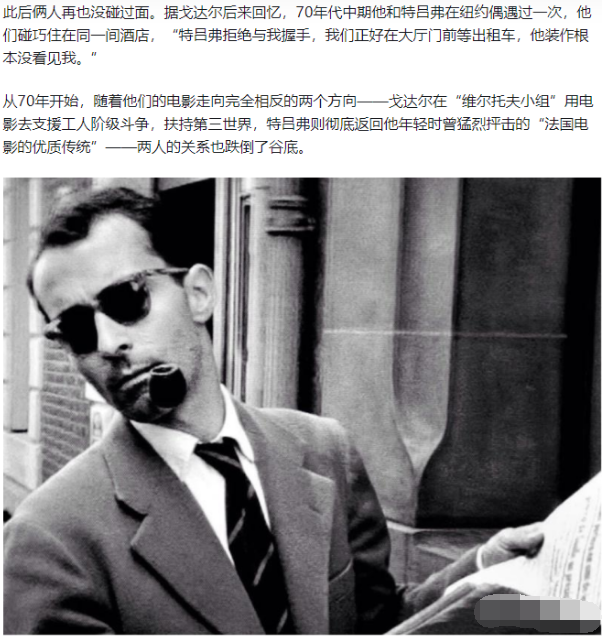
也就不奇怪,後來部分左翼知識分子開始選擇搞什麼性別多樣性,多元化的“進步主義”,並將激進政治運動的希望寄託在邊緣羣體身上。他們覺得其他的力量太容易被資本主義體制同化,所以還是和這些邊緣人合作才能有勝利的機會。他們相信這些被隔絕在社會主流之外的邊緣人,會帶來真正的變革力量。終究,他們極大低估了新自由主義下,以個人自由作為核心理念的制度同化能力。
在如今的短視頻與算法時代,一切都更加碎片化。各種多元化的,極化的情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被製造出來。你的思想未必是你所想的,你愛的與恨的,可能也是別人賦予你的。新時代民粹主義也由此而誕生。相信經常看我們文章的讀者對於歐美各路抽象右翼,已經有了些認識了。我國互聯網上的各種“抽象壬”,也有類似的性質。
值得高興的是,我國的互聯網討論場有那麼多正常的泛左翼,有那麼多質疑資本主義的人,説明主席那一代人的革命文化已經深刻融入了我國傳統之中,這比西方某些閒着沒事就懷念納粹主義的“傳統”可好太多了,就算某些自稱傳統文化研究者再怎麼胡説八道,否認1921以來形成的新傳統,也改變不了這樣的事實。
複雜的地方在於,一些羣體對於左翼的推崇同當年一樣,也開始呈現一種浪漫主義化,有的甚至走入刻奇的模式。通過消費各種文化消費品中似是而非的左翼符號,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把左翼文化想象成為某種只要念念經,就可以解決當下所有問題的神啓。這樣的文化現象,就很難説成是全是好事了。
68年的某些情況,似乎此時又在上演,承載左翼文化符號的可以是當年的電影,也可以是當下的手遊短視頻,或是翻譯來自於某位西馬精神分析大牛的博客文章。而夢也並非一定要是幾人之間的禁忌關係,完全可以是在小羣體中的優越感。當下的問題,可能比68年更加複雜。《戲夢巴黎》並非單純是對當年的諷刺,但是無疑是恰逢其會的比喻,比起思考社會的未來,是否情緒價值很多時候才是真正的的主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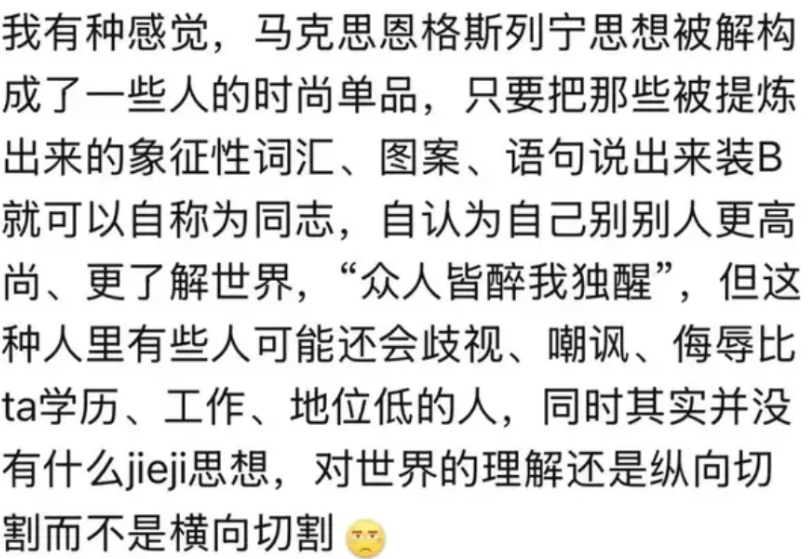
説到底,我們不該把左翼思想想象成是某種神啓的,超驗的經書,也不應該把任何一種左翼理想想象成是地上天國,**因為這樣的浪漫主義想法最終只會倒向失望,而這種失望往往孕育着某種自我毀滅。**尼克蘭德是如此,那些68之後,覺得人類破壞環境,所以人類會和資本主義一同被毀滅的人也是如此。
而在當下,被算法馴化的更加失去延遲滿足能力的人們,如果不擺脱這樣的觀念,新一波的左翼文化符號恐怕難以孕育出什麼碩果,我們不能指望自我毀滅的想法,引導人類走向更好的未來。
**社會進步的理想,更像是一條曲折,但是可以一直前進,又沒人能保證一定達到終點的路。**從這個角度來看,浪漫主義也是必要的,因為一旦失去革命的浪漫主義與想象力,面對如此直接的現實,就會很容易陷入要麼對資本主義全肯定的狀態,要麼陷入“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資本主義終結更加容易”的虛無之中。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確實需要有能力去想象新的東西,這也很重要。
但不管怎麼説,夢終究是夢,人應該有時間做一做夢,無論是美夢還是噩夢,這都是需要的,從夢境之中尋找啓發與動力。但想把夢中的東西變成現實,這終究是需要在現實中去完成的,我們在夢裏面走的路,還是需要在現實中邁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