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中諜 8》都有哪些槽點?_風聞
segelas-自由撰稿人-电影学硕士已毕业,但仍旧略懂皮毛11分钟前
從類型化的角度出發,以具體的特工行動作為表達主體,與商業元素的動作場面作為輔助,麥奎利交出了很不錯的答卷。但在戲劇層面,本作終究沒法深入到最直接的世界格局部分,以各國政府作為主角,完整呈現他們的“當下狀態”,以及更可信的“轉變”,一切的“世界視野,宏大格局,文明去向,政治議題”,都停留在了非常單薄的呈現,得到了極度輕易的化解。
最典型的是第二階段。美國政府與俄羅斯政府的整體存在基本缺席了這個部分的敍事,只以一線的軍人的形式出現,可以直接轉入動作場面。並且,由於政府整體組織的缺失,他們與伊森的互動也就無法深入,對伊森的打壓、其管理邏輯與手段所表現的“當下風氣”也就無從表現,甚至沒有到第一部或第四部的水平,彼時尚有着“舊組織/IMF拋棄伊森等人”的宏觀設定,不需要太多的鋪陳,只要讓伊森直面舊同事與上司的反水即可。
本作試圖擴大“整體組織”的範疇,從特工組織IMF上升到各國政府主導的世界環境,又要呈現1996-2025的大跨度時代。如果展開落實,必然會讓本片變成一部以“特工與政府,多時代中的對抗與共融”為主要內容的作品,探討個人與集體的關係,集體在不同時代中的表現,應對各種現實中大事件與政治局面之時的反應,其內始終不變的“犧牲個體”與“互相懷疑”,反映出內裏的權力貪慾。這會讓本片變成非類型片,不再是《碟中諜》。

因此,麥奎利必須用非常濃縮的形式來表現上述主題,AI是政府黑暗本質的極端結果,也具體化了伊森與“當下政府”的對抗,再加上其“理性與貪慾”之黑暗面承載的人類加布裏埃爾,以及美國一方的吉姆之子,作為現實“後冷戰時代”的承載,讓二者牽起首尾的時代,並帶來直觀的動作對抗形式,分別被擊敗與扭轉。此外,他通過核潛艇與海洋等空間,象徵世界環境,並給出系列裏的“極限求生”動作元素。
但是,這種模式之下的各國政府會淪為背景,其對於當下狀態的表現、轉變的達成契機與驅動力,自然也就無從談起。這也連帶到了伊森的塑造,如果當下環境沒有無法改變到極限,也就不會逼迫他到極致程度,無法帶來他之於環境的絕望感,甚至無法達到第一部中吉姆“被政府所拋棄”的心境程度。美國總統出現在IMF的錄音帶之中,由此完成了IMF到政府的升級,伊森被IMF拘捕,也被政府抵制、不信任。但是,政府與IMF對他的態度變化顯然過於輕易了,讓整體環境的質變也非常隨意,其在當下的深重度也隨之淡化。作為當下籠罩、壓迫的對象,伊森的絕望感也就顯得力度不夠,甚至被導演“放棄”,只在剛接觸AI預言的時候有所出現,“它是對的”,一旦行動真的開始,就直接變回了堅定不移的強大特工,此後的受壓更多來自外部環境,內心中始終堅信着“一切可擊敗與扭轉”的意志。在他完成第二階段“對外環境的勝利”之時,回答格蕾絲“只有你可以掌握AI力量”的時候,説出了“我不能,任何人都不能”的回答,其抹除AI、不同於加布裏埃爾的意志力,個人內心的動搖到堅定,直接得以完成,它事實上也沒有過程可言。
並且,作為極端形式的AI,其絕對理性的計劃正是“當下世界”對伊森的壓迫與掌控的表現途徑,伊森帶有希望的感性意志想要對抗它,卻在其絕對正確性之中找不到出路,因為其預判的政府、官員、乃至於所有人的行為都逐一應驗,讓伊森的“不可能任務“超出了生理與應付自然的範疇,而是對”AI判斷之當下世界與人類“的艱難衝擊。如果這個部分能夠做實,其中各方勢力與人物的當下狀態同樣能夠得以展露,作為整體世界格局的代表。特別是加布裏埃爾的存在,看似反抗它、實則被其掌控、同樣具有當下之人的貪慾,既是其意志的被動執行與代表者,也是當下人類的極端代言人,連接了AI與其象徵的“人類統治之世”,作為具體的壓軸反派而出現,更是對本片主題的確立,並非探討人類與AI的科幻母題,而是人類政府主導的當下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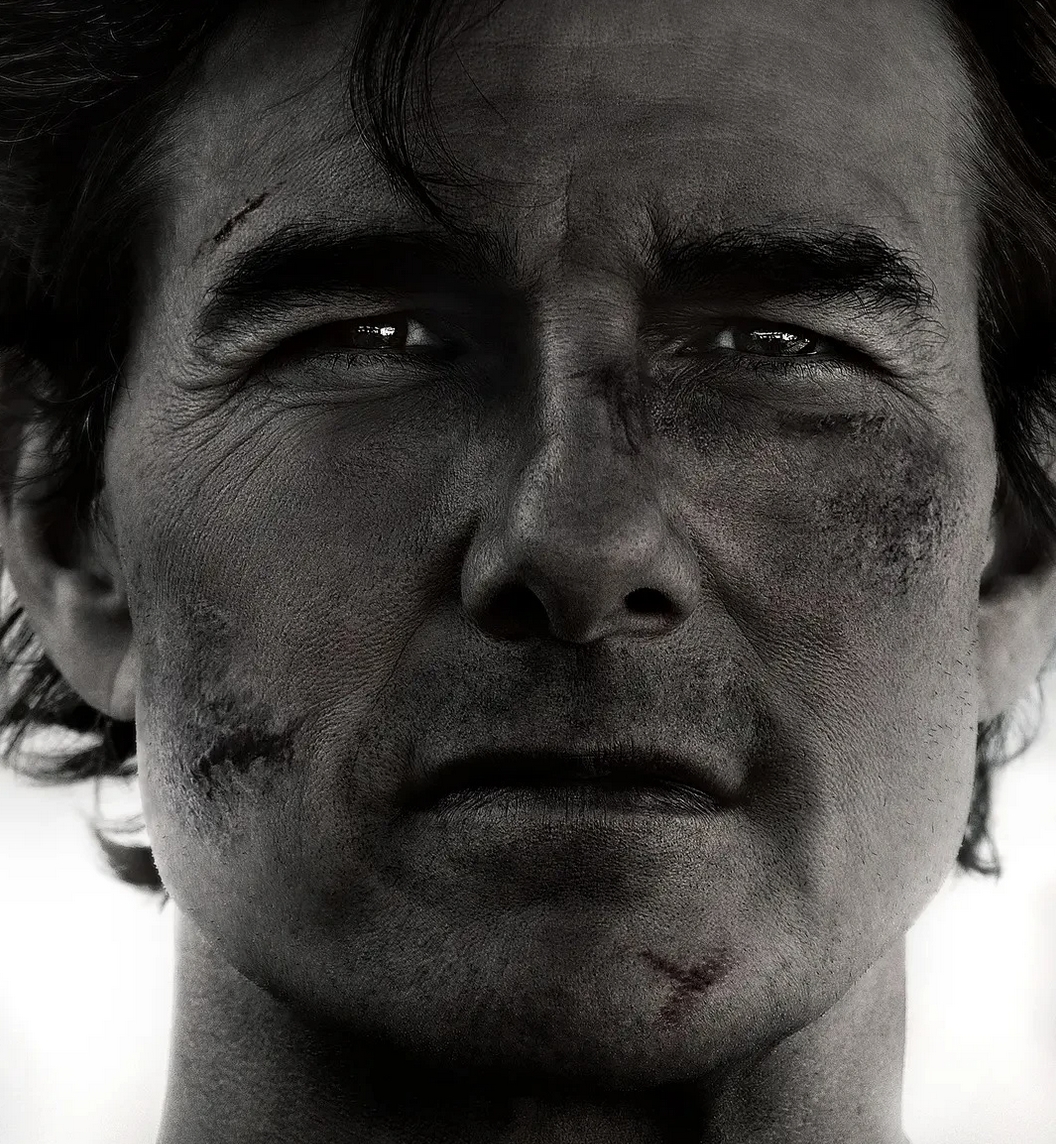
但是,如何設計出一個理性邏輯上確鑿無比、完全説服觀眾、紮根於當代現實情境與思維方式的AI計劃,再套入一個同樣具有看似反抗、實則被掌控、行為邏輯符合貪慾之人的合理性的加布裏埃爾計劃,又能讓伊森基於感性“相信、希望”的計劃能夠合理地衝破它,同樣是非常艱鉅的工作。因此,麥奎利放棄了這個嘗試,讓AI直接隱去,加布裏埃爾也缺席了整個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的1小時中,伊森等於只是在面對着美俄的軍方與潛艇,直接進入了現實維度的世界格局之環境,併成功地扭轉完畢。美國政府、軍方的人物,輕易地被改變,俄羅斯軍人也輕易地被戰勝,他們之於當下的“負面合理性”完全沒有得到展現,伊森與格蕾絲對他們的説服與扭轉也非常簡單,展現了口頭的意志與精神,釋放了極其“家人俠”-----對妻子的尊重----善意,僅此而已。
作為結果,真正足以承載世界格局之語境的高層政府、國別對決,從未出現在敍事一線,只有畫面上的“核彈威脅(AI點亮了一個個的國家標識)”,而美國政府也只能在幾場戲中快速質變,作為濃縮代表的具體人物的深陷當下狀態也非常輕度,被改變的過程只是最標準的好萊塢類型片水平,並未顯著高於《速度與激情》中“你我都是家人”的打動力。第二階段的動作戲非常出色,文戲部分有着麥奎利的細節植入,完成度卻非常平庸,對人物與政府的扭轉不足以説服任何人。我們看不到“當下”的深重,也沒有“突破沉重阻礙而扭轉成功”的艱難感與合理性。同時,作為“當下狀態之難以撼動”的濃縮形式,AI的計劃也就此變得非常潦草、粗放,政府與人物都被輕易地爭取到了伊森一邊,AI對他們的分析、預判、局勢的把握,也就變得兒戲一般了,完全失去了應有的強大之感。
這可能也是麥奎利安排AI與加布裏埃爾缺席第二階段敍事的又一個原因。他既要騰出戲份去強調主題對現實世界的指向性,淡化AI本身的“人類對機器”調性,也就此規避了對AI計劃的具體展開,將之放置在現實世界中“伊森對抗政府與俄國”內容的後面,作為“AI預判了美俄政府與軍方行為”的大背景而存在,再讓伊森扭轉美國、對抗俄國、達成核潛艇計劃,從而象徵性地取得“對抗AI”的進展,逐步扭轉被其極端化的“核戰爭陰雲”之當下世界。而在第三階段中,麥奎利也必須用加布裏埃爾與伊森的動作對抗,作為最終打敗AI代表的“人類世界之黑暗面現狀”的具體表現,而非讓伊森真正直面、對抗AI的龐大計劃,因為AI計劃實在過於簡單,不足以支撐起影片需要的絕對高潮,不如轉而在動作維度中追求高潮。
作為本片的高潮,第三階段仍然有着其能觸及內容程度、許可表意範疇之下的高完成度。在第三階段的起點,伊森的計劃變為對抗加布裏埃爾,作品用閃前的技巧交代了他的計劃。這與此前的閃前用法一樣,卻首次與隨後的實際情況有所不同。這意味着他對ai主導、判斷的既定計劃的衝破,這種對人類意志力與可能性的信任正是打破理性分析情況的關鍵,也是他與ai的區別。他的計劃試圖控制利用加布裏埃爾的行為,與ai控制他一樣,但加布裏埃爾超出了他的控制,意味着他不是神,對應此前的“任何人都不能掌握ai的力量”,也是隨後他從高空降落的所指。
在這個階段中,作品也展示了倒計時、時間概念的全貌。它在片中一層層地嵌套,帶來每個階段與局部段落的緊張感與小高潮,在整體層面則從100毫秒到10秒再到72小時,再到最宏觀的1996至今的時代層面,集中在高潮的三線聚合之上。它也收束了一些貫穿全片的細節,如格蕾絲與伊森再次的“神偷與扒手之區別”的解釦(從面對兩個特工,到解決世界核彈危機),格蕾絲與女總統對伊森的“你在哪裏”的呼喚,以及配角的關係,法國女殺手一直在喝酒,最後給班吉喝,救了他一命,前者象徵着二人扭轉生命危機的紐帶,由此推升了人物之間始終存在的信任與情感。
但是,綜合上述的種種原因,當麥奎利推進到本作的第三階段與高潮段落之時,明顯地出現了一些力有不逮的現象,只能非常生硬且倉促地安排着主題層面的內容,將之強行收束完成,再與動作戲的部分結合起來。在動作戲穿插的縫隙之間,人類政府完成了潦草的轉變結果。總統下令關閉核武器發射的聯網系統,放棄了用核武器蕩平AI所在地的計劃。美國與AI形成了個核武器的對壘,AI又控制了英、法、中、朝等國家的核武器,讓這種對抗成為了人類政府之間的關係,AI也非常具體地成為了“當下政府”的總括。擁有核武器的美國也是AI的對等者,由總統的善意激發、放棄對戰,率先擺脱了“當下”的狀態,蜕變到了新時代的面貌。這源於總統此前看到的母子照片,兒子不僅是她的士兵,也是她的親人,讓她放棄了將其拋入死亡的核戰爭,總統與軍人的純粹政治、軍事、上下級關係變成了人情層面的母子關係,作為新時代政府的根基。

此前用上下級關係的強制命令拿走了守衞槍支的將軍,擁有了剪輯賦予的懸念,似乎時刻要反水總統,成為當下政府的權力象徵。但這個定位落在了一個路人保鏢的頭上,而將軍反而是挽救者,拯救了總統,隨後放下了象徵自身暴力權柄的手槍。顯然,麥奎利知道自己的資源非常有限,已經無暇再去細化呈現將軍的轉變過程,只能生硬地將他與保鏢做成臨時的對比組,都象徵着當代政府中擁有“暴力武器”(核武器)手槍的權力者,他殺死對方,完成自己的轉變。
同樣的處理也發生在了吉姆之子與IMF領導的身上,二人缺席了最終的決戰部分,甚至沒有將軍程度的戲份,只是在一切結束之後,與伊森象徵性地達成了和解。IMF到白宮的升級,是本片應有的工作,本部與1996年第一部的呼應,更是系列在戲劇與主題完整性、升級需要之上的必然。但是,麥奎利沒能處理好特工組織與吉姆之子,讓他們更具體地化為白宮意志的具體執行者,從而廣泛地加入到故事之中,也在互動中完成人物的塑造與轉變,由此浪費了他們,而這本應是系列貫穿、或極具塑造潛力、表達主題性很強的兩個元素。
對於當下人類政府極端形式的加布裏埃爾與AI,麥奎利突出了二者在主題層面的現實指向性,卻也沒有細緻地安排好劇情。AI幾乎離開了高潮部分,在整個作品裏也出場不多,伊森在高潮裏對抗的始終是加布裏埃爾。這突出了後者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態”的屬性,也明確了主題的定位,同樣以AI一樣的理性分析掌控伊森的行為,並試圖掌握AI,表現着人類政府為了權力而發展AI的動機。伊森與他一起在高空搏鬥的動作戲,除了系列標配的刺激感之外,也帶有主題層面的暗喻意味,是雙方面對AI、與其同化或反抗之狀態的對抗。二人承載了人類政府的兩種走向,也具備了統治現實世界的“上帝”資質,在高空中決鬥,爭奪着上帝位置的最終所有權。伊森獲勝,標誌了世界的未來發展方向。
但是,加布裏埃爾的計劃非常潦草,對於突然出現的IMF勢力完全失察,對伊森的掌控也被對方輕易化解,給到的最大程度壓制甚至是動作部分。同時,AI的缺席讓它作為“終極BOSS”的整個計劃變得虎頭蛇尾,甚至沒有掌控加布裏埃爾----它得到情報最多,可拿捏把握最大---的心理,如預判其反水而轉化成自己計劃的一部分。加布裏埃爾的背叛超出了它的預料,它也對此毫無反應,全部計劃只是針對各國政府的核武器系統的,掌握其他國家的核武器,並判斷美國政府必然會與自己互相攻擊,然後又被同樣輕易轉變的美國總統與將軍等人瓦解,潦草之上更添粗糙,讓當下政府本身、象徵物“AI”的絕對存在顯得非常小兒科,基於理性判斷的絕對正確性完全沒有説服力,前者過於草率地轉變完畢,無轉變的後者則沒有得到真正強大計劃的支撐。
即使有着如此能力與自主權的麥奎利,終究也難以改變本作的商業片、類型化、動作主打元素的客觀定位,哪怕給出了幾乎完美的設計思路,也無法真的將之落到實處。他只能在第一階段的“鋪墊”之中,儘量呈現完畢自己的思路,隨後就要在雙方戰鬥開始的正片之中,回到名為諜戰、實則動作的傳統打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