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華文學看馬來西亞華人的百年身份求索_風聞
爽爽的南洋-马来亚大学 文化研究博士在读-香港、新马研究学者|关注:历史、冷战与华人文化。4小时前
儘管馬來西亞華人的祖輩已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超過一個世紀,儘管他們手持馬來西亞護照,國籍一欄清清楚楚地寫着馬來西亞,但在一些本地政治論述中,他們依然被視為不忠誠的“外來者”、“寄居者”。這不禁讓人好奇:在遙遠的南洋,這些與我們同文同種的華裔同胞,他們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他們是中國人,還是馬來西亞人?答案遠比一個簡單的標籤要複雜得多。我們從馬華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1:我們終將歸去
故事的起點要從英國殖民時代説起。當時大批國人下南洋,來到馬來半島謀生。英國殖民者為了便於統治,實行了族羣分治政策。讓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不同族羣生活在相對隔絕的社羣裏,從事不同的行業。這種人為的隔離為日後的族羣矛盾埋下了伏筆。
對於第一代華人移民而言,故土是心中永遠的牽掛。他們自視為僑民,暫居南洋,終有一日要“落葉歸根”。這種濃厚的僑民意識,深刻地烙印在當時的馬華文學中。翻開1919年檳城的報紙社論,你會看到這樣的文字:
“我們雖則僑居在這南洋地方,但我們的根本,究竟還在中國……”
據統計,1919年至1924年間,《檳城新報》的社論中,關於中國的篇數有954篇,遠超關於新馬本地的370篇。當時的馬華文學,無論是題材還是情感都被視為中國文學的海外支流,是華僑文學。作家們筆下描繪的是在南洋的刻苦生活,以及對遙遠中國的思念與愛國情懷。
 《檳城新報》報頭然而到了1920年代末,文學界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聲音。有人呼籲:“我們應當醒悟了,華僑以南洋為家鄉”。1940年代末,一場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大辯論更是標誌性的事件。
《檳城新報》報頭然而到了1920年代末,文學界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聲音。有人呼籲:“我們應當醒悟了,華僑以南洋為家鄉”。1940年代末,一場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大辯論更是標誌性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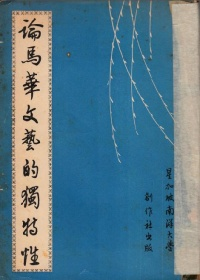 《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新加坡 南洋大學創作社 1960年作家們疾呼馬華文藝不能是翻版的中國文藝,也不能是僑民文藝,它應該是馬來亞文藝的主要成分。這顆本土意識的種子雖然微弱,卻預示着一場深刻變革的開始,華人開始在原鄉與新家之間搖擺。
《論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新加坡 南洋大學創作社 1960年作家們疾呼馬華文藝不能是翻版的中國文藝,也不能是僑民文藝,它應該是馬來亞文藝的主要成分。這顆本土意識的種子雖然微弱,卻預示着一場深刻變革的開始,華人開始在原鄉與新家之間搖擺。
2:我們不是候鳥
1957年,馬來亞(馬來西亞前身)獨立建國。新國家的誕生並未立即消弭族羣間的隔閡。相反,關於這個新國家應該以誰的文化為核心的問題爆發了激烈的爭奪。從馬來主政者的角度看,馬來族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理應享有特殊地位。而華人儘管在經濟上貢獻巨大,卻被視為非原住民,其忠誠度備受質疑。語言、教育、文化政策上的種種衝突,讓族羣關係日益緊張。
1969年5月13日,一場因選舉引發的嚴重族羣衝突——“五一三事件”爆發,成為馬來西亞歷史上最沉痛的一道傷疤。這起事件讓華人社會充滿了恐懼與不安,許多人選擇移民,回鄉的渴望和文化上的鄉愁一度飆升到頂點。事件之後,政府推出了以扶持馬來族羣為目的的新經濟政策,和以馬來文化、伊教為核心的國家文化政策。
面對被邊緣化的壓力,華人羣體如何自處?文學再次成為他們表達心聲的出口。一種回應是打造“原鄉神話”。 許多作家,特別是遠赴台灣發展的作家如李永平、温瑞安等,在他們的作品中構建了一個古典、純粹、充滿文化想象的中國。比如李永平的《吉陵春秋》,通篇是中國小鎮的風味,彷彿作者從未離開過那片土地。這並非簡單的懷舊,而是一種在現實中受挫後,於精神世界裏進行的文化抵抗和自我鞏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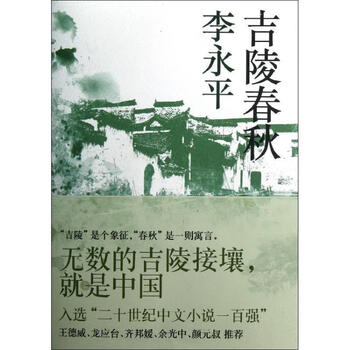 《吉陵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但另一種更深刻的轉變也在悄然發生。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正式建交。華人被迫正視自己的身份,他們是生活在馬來西亞的公民。“落地生根”逐漸取代了“落葉歸根”。著名作家方北方(原名方作斌)的創作軌跡就是最佳見證。他早期的“風雲三部曲”以中國抗戰和內戰為背景。而到了1980年代,他的新作《樹大根深》、《頭家門下》等,則將目光完全投向了馬來西亞的土地。他自己坦言:“想起自己在這裏已生活了五十多年,由僑民化為公民,對這裏的鄉土已產生了感情。”
《吉陵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但另一種更深刻的轉變也在悄然發生。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正式建交。華人被迫正視自己的身份,他們是生活在馬來西亞的公民。“落地生根”逐漸取代了“落葉歸根”。著名作家方北方(原名方作斌)的創作軌跡就是最佳見證。他早期的“風雲三部曲”以中國抗戰和內戰為背景。而到了1980年代,他的新作《樹大根深》、《頭家門下》等,則將目光完全投向了馬來西亞的土地。他自己坦言:“想起自己在這裏已生活了五十多年,由僑民化為公民,對這裏的鄉土已產生了感情。”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方北方介紹頁當有心之人再次拋出“華人是移民”的論調時,詩人方昂在詩歌《給HCK》中發出了強烈的質問: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方北方介紹頁當有心之人再次拋出“華人是移民”的論調時,詩人方昂在詩歌《給HCK》中發出了強烈的質問:
“究竟我們愛不愛這塊土地 / 還是我們去問問他們 / 如果土地不承認她的兒女,如何傾注心中的愛?”
而砂拉越詩人田思那首廣為流傳的《我們不是候鳥》,更是喊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聲:
“我們不是候鳥 / 我們是大地的兒女 / 誰生養我們 / 誰就是我們的母親 / 我們不是候鳥 / 我們永不離開 / 最最親愛的土地”
從僑民到公民,從歸去到紮根,這是一個充滿痛苦卻無比堅定的過程。華人的身份認同,開始真正植根於腳下的這片熱土。
3:我是誰?
進入1990年代,隨着馬來西亞經濟的騰飛和時任首相馬哈迪提出旨在團結各族的“馬來西亞國族”(Bangsa Malaysia)的宏願,族羣關係進入了相對緩和的時期。
此時馬來西亞華人,特別是新生代,開始了一場更深層次的自我審視。他們不再滿足於紮根,而是要追問:“我是誰?我的中國性(Chineseness)從何而來?我與中國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這場深刻的內省,在文學界掀起了一場名為“斷奶論”的大辯論。 以黃錦樹、林建國等旅台作家為代表的一方認為,馬華文學必須切斷與中國文學的“奶水”關係,擺脱支流地位,才能真正獨立,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另一方則認為,這種文化上的血脈聯繫無法也不必切斷。這場辯論的背後,是華人羣體對自身文化身份的集體焦慮與探索。
新一代作家開始解構自己的中國情結。他們發現,自己對中國的情感,大多來自祖輩的口耳相傳、來自書本的閲讀,以及自我的浪漫想象,而非真實的生命體驗。作家鍾怡雯寫道,他們對中國的感情,是通過長城、黃河這些文化符號召喚出來的鄉愁。黃錦樹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中國性的體現,如舞龍舞獅、過傳統節慶,其實是一種在公共領域受挫後,轉而在私領域進行的表演性文化實踐。最能體現這種複雜身份的,莫過於那些有過再離散經歷的作家。
 新聞:20萬人次逛廟會 檳城人過年好熱鬧 來源:馬來西亞 光明日報 日期:2025年2月1日作家林幸謙,在馬來西亞、港台多地生活後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新聞:20萬人次逛廟會 檳城人過年好熱鬧 來源:馬來西亞 光明日報 日期:2025年2月1日作家林幸謙,在馬來西亞、港台多地生活後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我回中國人組成的社會,彷彿前世曾經來過,卻又極其生疏,赫然發現自己竟是一個身在故國的他者……我所信仰的中國屬性,原來僅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當這些作家身處異鄉,味蕾的記憶最是誠實。他們心心念唸的不是燒餅油條,而是馬來西亞街頭那剛炸好的、帶着濃郁香料味的咖喱角,是那碗香氣撲鼻的咖喱雞飯。
更有趣的是,連過去被華人社會普遍排斥、甚至妖魔化的伊教的文化符號也悄然融入了他們的鄉愁。作家辛金順寫道,當他身在異鄉,記憶中:
”那常在黃昏裏穿過重重雲氣和雨霧的清真寺的祈禱聲,幽幽渺渺地突然在記憶中明亮了起來。”
他們既認同自己的中華文化之根,又深愛着馬來西亞這片生長於斯的土地。他們的身份,不再是中國人或馬來西亞人的單項選擇。而是一種既是,也是。
回看馬來西亞華人的百年身份求索,其實為我們理解“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生動的現實案例。他們的故事證明,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構應是超越國籍,以中華文化為紐帶的文明共同體。我們應在尊重他們作為住在國公民身份與情感的基礎上,以平等包容的文化交流為橋樑,並將他們融合當地特色的在地化身份,視為中華文明在全球化時代開枝散葉的寶貴財富與豐富延伸。這才是新時代中華民族最宏大、也最自信的敍事方式。
參考文獻
[1] 田思. 我們不是候鳥[M]//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 我們不是候鳥. 古晉: 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 1989: 29-32.
[2] 黃錦樹. 中國性與表演性: 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緊張[M]//張永修, 張光達, 林春美. 辣味馬華文學: 90年代馬華文學辯論性課題文選. 雪蘭莪: 中華大會堂, 2002: 319-322.
[3] 鍾怡雯. 從追尋到偽裝: 馬華散文的中國圖像[M]//陳大為, 鍾怡雯, 胡金倫. 赤道回聲: 馬華文學讀本Ⅱ. 台北: 萬卷樓, 2004: 262-291.
[4] 林幸謙. 盛年慶典[M]//林幸謙. 狂歡與破碎: 邊陲人生與創新創意. 台北: 三民書局, 1995: 3-13.
[5] 辛金順. 九月授衣[M]//鍾怡雯. 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6: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