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杭州上海,哪裏是你心中的那碗麪?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32分钟前

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江南 麪條
經常在蘇州、杭州、上海三地生活,我發現三座城市有一項共同的美食——“麪條”。雖然味道形色各異,但一碗碗熱氣騰騰的麪條裏,似乎還藏着挺大學問。
當我像偵探一樣對蘇式面、杭州面進行溯源後發現兩個疑問:
疑問1:三座江南中心的城市都吃麪條,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為什麼?因為我們江南地區多產水稻,但麪條卻是小麥軋成麪粉製成。照理説“南稻北麥”,那麼江南地區不是更應該吃米線、米粉嗎?
疑問2:都是麪條,但蘇式面、杭州面、上海面有很大不同。上海的面是“海派特色”,包羅萬象,很難説出是什麼地方風味。但蘇杭都屬江南,地理、氣候、人文相近,但蘇式面卻和杭州面迥異,麪條之間的差異遠大於蘇幫菜和杭幫菜的差異。這又是為什麼呢?
考證(多吃)下來,一碗普通的麪條裏還隱含着經濟、歷史的變遷密碼。我不是專家學者,只是愛吃愛琢磨,和大家説道一二。

杭州麪館——浙江面面觀
作為一個蘇州人,十五年前我剛到杭州,非常不習慣杭州面。彼時,我工作附近有一家杭州當地赫赫有名的麪館——松木場面館。這家招牌面是各色拌川,以現炒澆頭和筋道麪條相拌。
一開始我覺得這面又粗又硬,不好吃。和我們“蘇式的‘龍鬚麪’”很不一樣。也不止我,蘇州朋友到杭州旅遊,都説杭州什麼都好,就是面不好吃,不能和蘇式面比。
但在杭州生活久了,我越來越喜歡杭州的麪館,它們不是單一的“杭州面”,而是豐富的“浙江面”。浙北有桐鄉羊肉面、杭州拌川片兒川、浙東有寧波黃魚面、舟山海鮮麪、浙南有温州米粉面、浙中有金華手擀麪、諸暨次塢打面,幾乎每座地方城市都有代表的麪條,並且風味各異,橫亙山海。

以杭州為例,杭州麪食的特色是拌川和片兒川,前者講幹拌入味,後者講究湯頭鮮美。其中,我偏愛拌川。拌川用鹼水面,十分筋道,強調現點現炒的“鍋氣”——麪條與高温快炒的澆頭充分拌勻,澆頭非常豐富,有豬肝、腰花、蝦爆鱔、牛蛙等,分量也紮實。蘇州人喜歡早上一碗麪,但在杭州,很少早上吃麪,因為料太足,早上根本吃不下。
為什麼蘇州人不喜歡杭州面呢?我後來研究了一下,發現杭州很多面館擅用“鹼水面”——麪條偏粗且硬,和細軟的蘇式水面不一樣。
我也是很長時間才喜歡上“鹼水面”,其中個人最喜歡蘭谿手擀麪和諸暨次塢打面。這都是曾在浙江金華、紹興出差途中偶遇的當地小麪館,一般是夫妻老婆店,現場手工打製麪條,麪條韌性十足,湯頭雖然簡單多是雪菜、筍片、肉絲,配以骨頭高湯,一種質樸的滿足感充盈口腔,確實非機軋的麪條所能比。
很喜歡杭州的麪館,在杭州這座崇尚華麗的城市裏,麪條有難能可貴的質樸,從寧波舟山的海鮮麪到金華山頭的手工打面,在那些路邊街巷不起眼的小店裏,最自然、原始的山海風味向人襲來。天目山的鮮筍、舟山寧波的東海小鮮、金華火腿、紹興醬貨臘腸肉,一碗麪可以藏着一座微型浙江,各地的底料單看都很平常普通,但一組合就鮮美無比。


蘇州麪館——精緻的士紳文化
和杭州的華麗相比,蘇州城市倒是典雅樸素。但蘇州總是不聲不響,在精微之處,流露驚豔。蘇式面是蘇州人最日常的早餐。吃“早面”是因為蘇式面“重湯輕面”,和夯實的杭州面很不同。
杭州的朋友也説不喜歡蘇式面,説口感偏甜、麪條吃不飽。一個是當早飯點心,一個是作中晚正餐,兩個城市對面條有不一樣的態度,倒也很有趣。
陸文夫筆下的蘇州“美食家”朱自冶每天早起只為一份頭湯麪——“千碗麪,一鍋湯。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話,那麪湯就糊了,下出來的面就不那麼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麪湯氣”。書裏的朱自冶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湯氣的面,他會整天精神不振,總覺得有點什麼事兒不如意,所以他必須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趕上吃頭湯麪。
現在很多外地朋友都趕着來蘇州吃麪,還問我懂不懂什麼叫“鯉魚背”,他們點面也很專業,要“寬湯,重青,重澆,過橋”。説來慚愧,這些術語我並不懂,也吃不出很大區別。
蘇式面的湯底要比浙江豐富不少。有豬骨、鱔骨、雞架、魚肉,甚至會輔以螺螄長時間熬製。蘇式面最有名的是 “紅湯”,帶有甜鮮味。

在杭州,可以説“一地一面”,但每一地只有一兩種品類。但蘇式面卻品類豐富,變化多元,且非常講究時令性,麪條和節氣都相應匹配。
蘇州人的立夏從一碗 “楓鎮大肉面”開始,到了端午,太湖的湖蝦開始抱卵,這是三蝦面上市的季節。而秋季有蟹黃的 “禿黃油麪”,冬天則是熱氣騰騰的羊肉面。“不時不食”的蘇幫菜精髓,也同樣在蘇式面中。人們對四季的感知,就是從早餐的麪條開始。
但“三蝦面”這種昂貴隆重食材的面,不太是蘇州本地人的選擇。蘇州人飲食很簡樸。我個人更喜歡 “素澆面”,能把素菜澆頭,用香菇、筍片、麪筋做成好吃、乾乾淨淨的一碗麪,在全國也不多。
浙江一碗麪是全省食材的組合。但蘇州的面都是就地取材,太湖的蝦、陽澄湖的蟹,自給自足,據説明代的麪館流行各色鮮魚面,春刀魚、夏鱔絲、秋蟹糊、冬爆魚,四季有別,且充滿吳地風味。
因為絲綢製造業的興起,蘇州成為江南中心,各地客商也匯聚蘇州,麪條、澆頭都有了進一步發展,到清代更是創立了不少老字號,松鶴樓創立於乾隆年間,以夏季供應滷鴨面聞名。
時至今日,蘇州麪館也不斷精緻化,不僅吃麪,還有高級裝修和蘇州評彈。這種麪館和茶館的組合,也成為蘇州麪館的一大特色。很多上海朋友都因“一碗麪”特地來蘇州度週末,蘇州的麪館就像“廣東早茶”,已經成為日常的社交場景,再現了江南舊時生活的鬆弛感。


上海面館——五湖四海拿來主義
回到上海後,一人就餐也多是去麪館。上海面館除了蘇式面、浙江面外,還有五湖四海各地的面。武漢熱乾麪、重慶小面、四川擔擔麪,統統在這裏落地生根、改良變種,也説不清楚哪碗才是“上海面”。
上海有一項本領,就是什麼地方美食到上海後,都會有本地化改良,味道似乎也更好了。我2007-2009年在上海長寧區工作,每天必吃一碗桂林米粉,最吸引我的是店中的酸筍,此店家的酸筍與豆豉、辣椒爆香,有一股 “鑊氣”,口感酸甜且一點也不臭。
為了這碗酸筍米粉,我還特地去廣西旅遊,但嚐遍街頭巷尾,卻遠不如上海這家好吃。因為廣西本地米粉大多細軟,當地的酸筍也很難聞,口感很怪,難以下嚥。想必這家小店來上海後做了改良,讓米粉有了麪條的勁道和韌性,讓酸筍去掉了臭味。
但近些年在上海吃麪卻有了不一樣的心境。選擇吃麪僅僅是因為速度、效率和經濟。那種在蘇州慢悠悠早起吃一碗麪,在杭州街巷中無意行走,發現一家麪館嚐鮮,心情完全不一樣了。
在上海已經失去了發現美食的能力和感受美食的心情,往往手機搜索,直奔主題,團購下單。上海從不缺美食,只是我等牛馬,行色匆匆,食而不知其味。
我越來越理解為什麼上海的朋友,喜歡來蘇州度週末。我自己也是帶着孩子週五衝刺一樣逃離上海回蘇州,週日晚上再回來,再期待下一次回蘇州家裏。城市越大、越高效,人們生活也會越發同質化、標準化。令人日漸失去生命的“感知力”。這種能力沒什麼用,不過能提升幸福感,提高心情免疫力,抵抗抑鬱、焦慮等“心理疾病”。
感知力需要在西湖的山水、蘇州古城的巷肆中再度恢復,在自然鬆弛的慢時光裏,讓生命重回飽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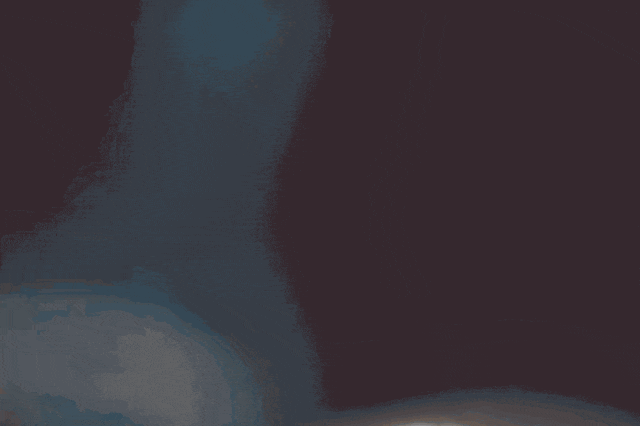

一碗麪裏的“江南城市化”
最後回到我開頭提到的兩點“小疑問”,我查了一些書籍資料對江南面條的歷史淵源,發現了一些脈絡(僅限個人觀點):
自古中國糧食的格局是——“南稻北麥”。“自南宋定都杭州臨安,小麥在江南開始廣泛種植。初夏的田野中,山坡丘陵上的冬小麥已經金黃,山下窪地裏的水稻綠油油一片。聰明的農民用苗牀育秧技術延遲了水稻的農田插秧期,正好滿足了小麥的後期生長。冬種小麥、夏種水稻,稻麥兩熟制就這樣在長江流域出現了。”(崔凱《穀物的故事:讀解大國文明的生存密碼》)而南宋時期的杭州,麪條已經很豐富了。《夢粱錄》中記載:“亦有專賣菜面、熟齏筍肉淘面,此不堪尊重,非君子待客之道也。”意思是麪館裏油膩嘈雜,不宜款待貴賓。
到了明清。由於對絲綢、棉布需求的激增,江南地區刺激了棉花、桑樹種植擴張,從而壓縮了糧食生產空間。再加上江南地區賦税重,糧食自給率開始下降, 蘇州、松江地區甚至要去湖南、江西等異地買糧。而在運河節點的城市,商品貿易往來如織,人們對稻麥之間差別的關注也越來越小。這些繁華的運河之城,在街坊之間,一座座麪館湯鍋中蒸騰的水汽翻湧彌散。
到了近代,1902年無錫榮氏兄弟更是創辦了無錫保興麪粉廠,隨後又在上海、武漢等地投資建設麪粉廠,在一戰期間出口海外。五四運動後,全國抵制洋貨,榮家的國產麪粉,巔峯時期佔到全國麪粉總量的1/3。麪粉的工業化生產降低了成本,使麪條成為城市平民的便捷選擇,麪條從家庭餐桌走向街頭巷尾的麪館。《小麥戰爭》一書中分析歐美工業革命的成功——“廉價的麪包將工人吸引到了消費積累型城市,城市居民積累資本並將積蓄存入銀行,進一步推動了帝國中心的繁榮。這也是1860—1890年的‘黃金時代’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可以這樣認為,因為美國的低價穀物進口,工人階級生活成本降低,且跨越了所謂的‘李嘉圖悖論’,歐洲工業革命獲得最終成功。”
按照這個理論,麪條也像歐美麪包一樣,成為平價的全民美食,也推動着人們越來越向工廠、城市聚集。
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與經濟上的工業化,共同推動了麪條在江南的“城市化進程”。
從南宋、明清再到近代的麪粉工業化,江南的一碗麪裏,藏着江南城市化的深刻變遷。南宋的杭州,明清的蘇州,近代的上海,可以説是一千年裏三個大歷史時期的中心大轉移。麪條也成為連接政治、歷史與生活的紐帶。

作者崔凱在書裏寫道:“‘上車餃子下車面’,有着豐富的寓意。一個人遠行前,家人或朋友請他吃餃子,希望他能平安回來。當遠行者歸來後,親友再請他吃麪,一根根麪條寓意着一種掛念,表示牽掛的心終於放下了。”
這段話寫得真好。我看現在蘇州網紅麪館生意興隆、價格昂貴,大家還在等位排隊。也搞不清楚這到底算消費升級還是消費降級。只是吃一碗麪容易,收拾一份心情卻難得。
城市化不只是高樓廣廈,更藏在一碗碗熱湯麪裏。有人在面裏品出鄉愁,有人在面裏遇見過往,有人走得再遠,也終究會回到家門口的麪館,用一碗麪,留住時間、留住味道、留住人心。
就像我每次端起一碗麪,總覺得,不僅是在吃,更像是慶祝與這三座偉大城市的相逢,共同回味一段走過的路。
——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