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徐坤《Deadman》,好到逆轉口碑?_風聞
音乐先声-音乐先声官方账号-解读音乐产业,见证黄金年代。1小时前
頂流偶像怎麼做出“細糠”?
蔡徐坤,被內娛“排擠”到格萊美去了?
近期,蔡徐坤的《Deadman》在社交媒體引發了眾多關注,關於他和他的音樂的討論也正在發生微妙的轉向。討論不再侷限於粉絲打Call或黑粉吐槽,而是吸引了大量業內音樂行業從業者的好評。

數據顯示,歌曲上線15分鐘內,QQ音樂在線聽歌人數突破16萬,創工作日凌晨時段紀錄。首日登頂QQ音樂新歌榜、熱歌榜等七項榜單,網易雲暢銷指數榜第一,僅用13天收藏量突破150萬。單平台單曲銷量突破50萬張,海外iTunes登頂15國榜單。
目前,《Deadman》在QQ音樂仍霸榜熱歌榜、新歌榜、流行指數榜、由你音樂榜、飆升榜、內地榜6個榜單Top1,抖音話題播放超過8億次。
那麼,一首《Deadman》究竟成色如何,可以讓蔡徐坤的口碑逆轉?在娛樂工業和固有印象的雙重裹挾下,頂流偶像還能做出“細糠”嗎?
“若命運由我執筆”“If it was up to me, I’d give you my soul.”
旋律推進之間,《Deadman》已然完成了某種轉向,無疑是蔡徐坤迄今為止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拋開音樂本身,這首作品在當下華語流行的語境中之所以格外顯眼,不在於它多麼先鋒,恰恰相反,它復古、剋制,審美上回避了一切流行公式化包裝的誘惑。
從編曲、配器細節上來看,吉他Tremolo顫音構成的切分音,以及音色上微量的法茲效果,都明確指向20世紀中葉美國靈魂樂的質感,而不是數字時代流行樂的快餐邏輯,做到了實實在在的復古。

從製作陣容看,除蔡徐坤外,全外籍陣容的製作班底,也讓整首作品具備了西方作品的完整度。
同時,視覺風格也是《Deadman》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荒原、牛仔、凝視、火焰、槍響,明顯借用了美國西部片和新浪潮電影中的敍事意象,北美與冰島的景別調度、色彩處理乃至鏡頭剪輯節奏,特別是抽煙、吻戲元素的大膽嘗試,都讓這部MV跳出了所謂的“偶像審美”。

長期以來,蔡徐坤所承載的偶像身份,是在高度商業化與道德化的雙重機制中建構出來的。他的形象被系統性地置於年輕、可控、非攻擊性的話語中,迎合了粉絲經濟中的“親密錯覺”邏輯。可以看出,這是蔡徐坤近年來在“偶像向創作者”的身份過渡中非常清晰的策略,挑戰的不僅是傳統偶像的角色設定,更是他原有受眾的心理舒適區。
當國內普遍聽眾耳機裏還在“別墅裏面唱K”,《Deadman》中吟唱的那句“If it was up to me, I’d give you my soul”,像是一記柔而有力的鞭響,抽在了華語聽眾長久以來的麻木感官上,也抓住了那些在無數爛梗中一笑置之的看客。這個被誤讀了太久的名字,交出一張如此温柔而鋭利、值得聆聽的答卷。

一時間,蔡徐坤的風評也來了個360度大反轉。
有網友指出,幾乎半個朋友圈的男性都對他改觀了。還有人稱,蔡徐坤此番操作像極了番茄小説裏的爽文劇情,屬於是“閉關100年發現全世界音樂水平下降100倍”、“發現國內跳樓機霸榜,這一次我決定不再隱忍”、“重生之華語樂壇倒退30年而我進步兩年半”。
但也有部分樂評人指出,這首作品,只是音色和節奏是復古的,沒有必要上升到神話的地步。

確實,《Deadman》從完成度上講,是蔡徐坤近年來最成熟、最有審美意識的一首作品。尤其對比其他頂流藝人更工業化的作品,這首歌呈現出更細膩的動態、更剋制的情緒表達、更成熟的樂句處理。
但聽感愉悦不等於音樂深度,復古風味也未必會復刻傳奇。客觀地説,如果將《Deadman》放在全球音樂的環境下,它的“好聽”更多來自安全、低風險的經典風格的復刻、借鑑。
從國內聽眾的視角來看,大家普遍仍處於旋律氛圍優先+歌詞情緒優先+歌手角色化+風格標籤式消費的階段,缺乏對音樂結構、節奏美學、和聲複雜性、編曲互動等更深入層面的欣賞能力。

而它的“新”,只是相對於過去國產流行歌曲“風格貧乏+旋律俗套+編曲工具化”的水平而言。
但回過頭,站在創作者的視角上看,《Deadman》仍是一個在中國流行音樂語境中非常值得鼓勵的作品。模仿經典不是原罪,而是創作者向成熟過渡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修行。
蔡徐坤選擇做復古,肯定是個比快餐曲風更值得肯定的方向,不過未來的難點在於,如何從模仿、深挖中“內化”出自己的音樂語言系統。
“若命運由我執筆”,欣慰的是,蔡徐坤已然提筆了。
蔡徐坤的口碑,為什麼逆轉了?蔡徐坤的口碑逆轉,並非常規偶然的偶像“洗白”,更像是長線籌謀後,終於等來的輿論撥正。可以確定的是,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要什麼,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他的音樂審美不斷進化、日趨成熟。
從唱腔而言,蔡徐坤的技術進步幾乎是“可量化”的。《Deadman》主歌開始,蔡徐坤就一改《情人》時期的發聲方式,刻意壓低喉頭,用接近哽咽的狀態去做主歌部分的處理,聽者可以迅速進入到歌曲氛圍。

在歌曲的中後段,蔡徐坤運用了大量細緻的滑音、波音處理,以及尾音處不規則的喉頭顫音等技巧性裝飾。而在高音部分,他的音域一度攀升至 G#5,已逼近男性聲部的極限。這不僅要求聲帶具備極高的延展性,還需在極窄的發聲點上,以極弱氣息精準控制音準與音色的穩定,難度極大,確實有點東西。
當然,在現場演出中,他的表現並不算完美。比如HITC音樂節真實舞台下的聲線穩定性、共鳴位置、混聲密度、輕微擠卡,都暴露出他與一線vocal技術細節上的距離。但這種破綻並不足以讓人失望。
對一個正從偶像身份脱殼的歌手而言,這樣的修正能力,本身就具有含金量。
自參加《偶像練習生》起,蔡徐坤便表現出一種少見的路徑清晰感。他似乎並非在成名後才思考“該做什麼”,而是從一開始就表露了野心,並精準識別了自己的受眾羣體、市場定位以及未來作品的發展方向。

比如2018年,蔡徐坤帶着第一首自己創作的單曲《I Wanna Get Love》登上節目,便已初步勾勒出其未來想要構建的表達核心“性感”,儘管作品內容略顯稚嫩,英文歌詞也多為可以堆砌性感的表達,未見特別深意。
當時身為評委的歐陽靖就指出,這首歌整體來説沒有特別的意思,大部分英文都很普通,更多的是蔡徐坤過硬的舞台表現力來做支撐的。

接下來幾年,從《Wait Wait Wait》到《情人》,蔡徐坤逐步確立了屬於自己的“性感敍事美學”。歌詞中對情慾、拉扯、渴望的描寫也更偏隱喻化,不再是初期《I Wanna Get Love》那種直白、小詞的堆砌表達。

自《情人》出圈後,蔡徐坤的音樂審美、意識也在不斷提升。近兩年,他相繼推出了《Spotlight》《RIDE OR DIE》《Afterglow》《Remedy》幾首編曲剋制,立意不侷限於微小情慾敍事的作品,唱腔開始更歐美,整體風格逐步向國際化靠攏。
詞曲方面,蔡徐坤也逐漸開始做減法,從早期傾向於使用細節堆疊,轉向更具象徵意義的留白式創作,用少量高度抽象的意象激發聽眾的聯想力,放棄“解釋”,強調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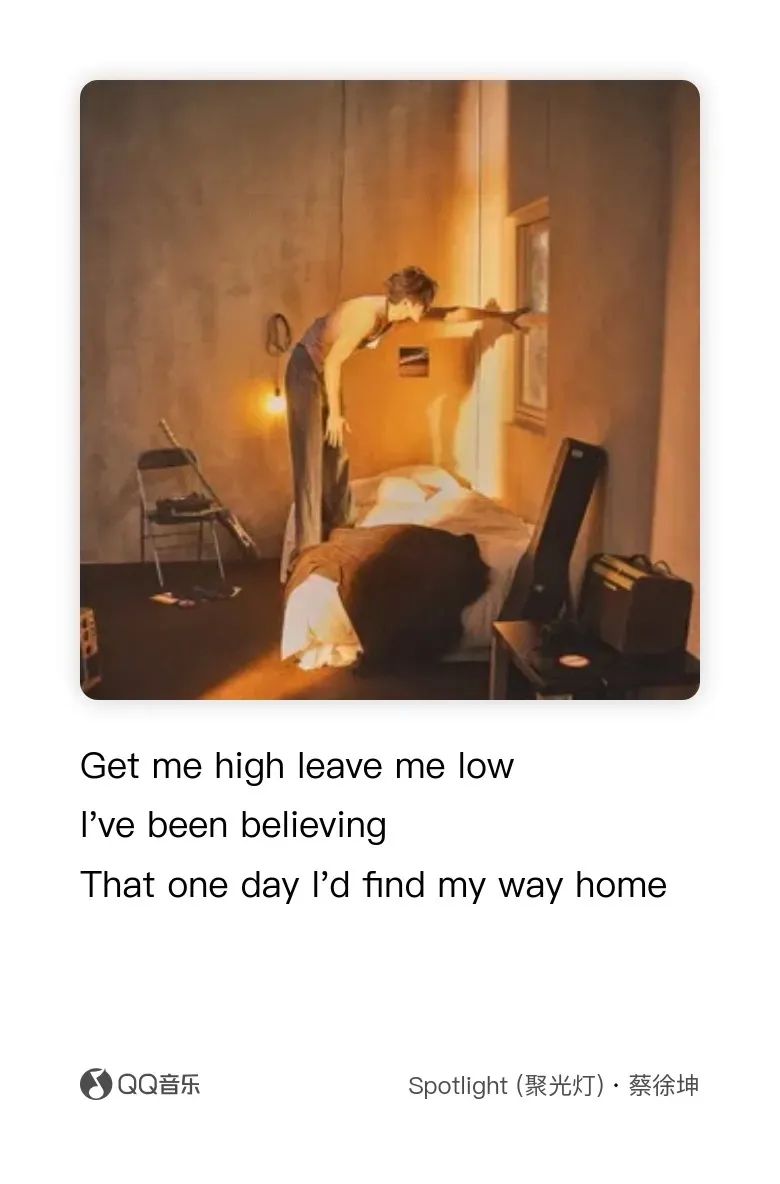
如網友指出的,儘管《Deadman》這首歌類似高中生滿分作文,和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還是有差距。但蔡徐坤做到了頂流偶像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寫出了一首工整的、致敬了不少前輩的靈魂樂,沒有迎合下沉市場,而是用自己的影響力引導了大眾的審美。
當一個曾長期被羣體妖魔化的公眾人物,開始展現出與既有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一面時,公眾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讚賞,而是認知震盪。這首《Deadman》正是如此,不僅刷新了聽眾對作品的感知,更激發了更深層次的心理機制,對偏見的自我修正所帶來的衝擊和心理鬆動。

事已至此,人們並非單純在評價一首歌的好壞,而是在重塑自己對“蔡徐坤是誰”的認識過程中獲得心理滿足。一方面,從貶低對象到承認對方的價值,這種認知反轉伴隨着強烈的情緒釋放,帶來一種“被打臉卻意外舒服”的心理體驗。
另一方面,這種反差還滿足了“深度樂迷”人羣在文化消費中的自我定位需求。他們樂於強調“逆風識珠”式的審美自豪感,通過與主流刻板印象的區隔,彰顯自己的品味、敏鋭度和話語權。
這也解釋了為何《Deadman》在非粉圈中能獲得廣泛轉發和討論。這不僅是一首好歌,更是一個足以讓人彰顯自我審美能力的文化事件。

因此,蔡徐坤的口碑逆轉除了他本身積少成多、逐步精進組成的良好口碑外,最關鍵的核心要素,並不是蔡徐坤是強是弱,是偶像還是藝術家。
而是因為蔡徐坤這次幹出了一件在大眾看來,不像蔡徐坤的事。
頂流偶像為什麼難做“細糠”?頂流偶像語境中,“細糠”或許不是一個被高頻提及的詞,卻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這需要時間的打磨、對審美的堅持,也需要藝人本身對自我表達的清醒認知。
但對偶像而言,邁向“細糠”的道路,往往是最遙遠的。
時間回撥至2014年,歸國四子的陸續迴歸,開啓了中國娛樂工業流量化運作的元年。那是一個關於“完美偶像”的虛構年代,國際資源、重金加持,品牌聯名,審美模式趨同卻包裝精緻,將偶像牢牢鎖進了一個工業模板。

但流量的邏輯,從一開始就與藝術的耐心背道而馳。在製作方與資本眼中,頂流、偶像,不過是更高維度的“快消品”,是以粉絲經濟為受眾的投餵機制。這種背景下,“發歌”不等於“做音樂”,就像是一次社交媒體熱度操作,也可以是品牌續約的配套交差。
《壞蛋調頻》主理人王碩就指出,目前大部分偶像的音樂作品都是對K-Pop、美國公告牌前十的淺層模仿。
但製作細糠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它不以取悦為前提,不迎合最大公約數的審美期待,而是逆勢、向內而生。這要求創作者剝去工業濾鏡,正視內心的質地,去做那些不一定討喜,甚至可能“反流量”的作品,既需要一種清醒的表達意識,也需要願意沉下心來對抗流量邏輯的勇氣。

對於頂流偶像而言,這無疑是一場高風險的豪賭。在一個以流量兑換資源的體系中,任何“自我表達”的嘗試,都可能成為打破人設、削弱商業價值的“危險舉動”。
更現實的問題是,他們是否都擁有獨立表達、獨立創作的能力或者天賦?
當產能過剩、審美滯後成為常態,所謂“創作”在多數情況下不過是流水線中一次被預設的包裝流程。於是我們會看到,有的作品雖然製作班底精良、編曲華麗,但用詞稚嫩,立意空洞,一切形式感大於內容深度,聽完即棄,徒留聲浪。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黃子韜,回看此前他擔任詞曲的作品在旋律、歌詞以及內核深度上,都存在明顯的短板。今年的説唱節目中,他作為Rapper導師參與的主題曲cypher,目前看來,在腔調、flow等方面也沒能展現出足夠的技術水準。
反觀他今年4月翻唱的改編版王力宏的《愛錯》,反而獲得相對的正面反饋。某種程度上,説明他在脱離“全權創作”後反而表現更穩妥,也暴露出部分偶像並不具備音樂創作天賦。在這種情況下,更務實的做法是依靠成熟團隊,慢慢沉澱審美與技術,而非倉促自我表達。

這也揭示了當下部分流量藝人的誤區,將“自我表達”誤讀為“創作全能”。在尚未具備成熟的審美判斷與創作技巧的情況下急於出手,反而導致輸出內容結構鬆散、表達乏力,最終落入尷尬輸出的循環。
不過,新的裂縫正在出現。當下觀眾的審美已不再是被動接受,他們開始主動辨別、主動迴歸內容。曾經“流量即正義”的市場信條,正在被“作品驅動”的新敍事所逐步取代。

無論是蔡徐坤在《Deadman》中展現的美學張力,還是張藝興主演的音樂話劇《受到召喚·敦煌》所引發的跨圈層好評,均表明不少偶像已經在從流量劇本中抽身,“內容即價值”已在新一代受眾中取得初步共識。
這些轉向説明,觀眾願意為真正有質感的內容放下成見,但前提是內容值得。
真正有思想密度與藝術野心的作品,或許無法制造“爆款”,但它們能留下回聲。這種口碑沉澱,正是頂流最容易忽視,也最難獲得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