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棄的詹周氏的一生_風聞
四味毒叔-四味毒叔官方账号-47分钟前


魯迅説“要麼墮落,要麼回來”。
電影則告訴你:
為自己而活的女性,有無數種可能。
作者|王重陽lp
編輯|小白
排版 | 板牙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這女人殺了自己當家的男人,還把他分屍了。”
一樁案子,一句話,一座城沸騰了。
對於1945年的上海灘來説,縱使身處風雲聚變的當口,也絲毫澆不滅人們對“殺夫案”的獵奇熱情。小劇場裏,演員們依據臆想編排劇情,肆意揶揄着所有可供嘲諷的對象,從兇手到警察。台下的觀眾醉生夢死,也僅僅是醉生夢死。
他們,終究阻擋不了時代碾壓而過的車輪——
看台下的薛至武(雷佳音 飾)起初並不在意人們如何咀嚼這樁“殺夫案”。至少在詹周氏(章子怡 飾)翻供前,他依然氣定神閒,篤信縱使風雲變幻,自己仍能掌控一方乾坤。
然後……
長官告訴他:“我們站錯隊了。”
1945年的上海灘,薛至武未曾料想之事何其多。傀儡們的大勢已去自不必説,連他經手的一樁“小案子”,竟也從“男歡女愛”的香豔談資,急轉直下成了“男默女淚”的時代悲鳴。
“殺夫案”猶如一道劃破時代的刀鋒,驚慌失措的何止薛至武?那些看客們,在喧囂中不知不覺,被一個女人沉靜如深淵的訴説擊中了心臟,旋即捂住胸口,彷彿窒息。
多年後觀看此故事的觀眾,亦復如是。
以至於影片落幕,唯餘一片沉重的靜默。
這便是《醬園弄》第一部《醬園弄•懸案》。
它穿透時光之壁,照進現實,開啓一段柔弱軀體裏迸發出的、驚心動魄的生命獨白。

01
被嫌棄的詹周氏的一生
詹周氏未曾想過,自己卑微如塵的一生,竟會成為“民國四大奇案”之一,更不曾預料,這具飽受摧殘的軀體,有朝一日會承載起某種沉重如山的時代精神。
她天生面有瑕疵,自卑深入骨髓,身份低賤如泥。若要倒溯她的人生,鏡頭需將她從法庭的被告席,一路拖拽回黯淡無光的少女時代。影片無聲地向觀眾昭示:

你們看,這個女子是微不足道的。她的愛情、婚姻、家庭,乃至她整個生命的存在,在世人眼中皆是如此。
放至今日,亦然。
一個弱女子,因幾句温言軟語的哄騙,便歡天喜地嫁了人。丈夫詹雲影(王傳君 飾),人稱“大塊頭”,蝸居於醬園弄二樓那間逼仄的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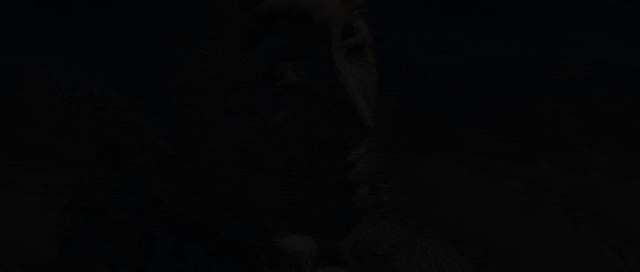
詹雲影並非生來便是“白相人”(上海方言:指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之徒)。他初時也有正經活計,而後卻沉淪賭窟,萬劫不復,日子過得一片狼藉。
房東太太(梅婷 飾)向薛至武描述時,言語間滿是鄙夷與嘆息:
“連窗户上的銅拴都拿去當了!作孽哦!”
詹周氏的日子,也活成了街坊鄰里眼中一個笑話。
無論她被“大塊頭”毆打得如何悽慘,嘶喊得如何絕望,她始終是那個被圍觀、被咀嚼的笑話。

縱然她曾竭力反抗,甚至不惜忍受債主張寶福(李現 飾)的輕薄與折辱,只想憑一己之力做工替夫還債。
她天真地相信,只要足夠拼命,這個風雨飄搖的家就還能維繫。
接着,她被“大塊頭”拖到賭場門外毒打。
她又一次成了路邊攤食客和冷漠路人眼中,一出鮮活的悲喜劇。
然後,我們回到影片那充滿隱喻的開場:
瞎子跌倒,掙扎爬起,滿臉鮮血,路人圍觀、驚呼。

薛至武氣定神閒地宣告:
“這女人殺了自己當家的男人,還把他分屍了。”

當薛至武終於驚覺眼前這個看似不堪一擊的女人,竟將成為他“一生之敵”時,事態早已滑向他無法掌控的深淵——
上海小劇場的看客們,興趣點悄然從香豔的姦情八卦,轉向了“被嫌棄的詹周氏的一生”。人們追問的不再是“她如何殺人”,而是“她為何殺人”?抑或“是怎樣的絕望與怒火,驅使這弱女子揮刀斬向一個壯碩的男人”?
引導這股輿論洪流的,是劇作家、社交名流西林(趙麗穎 飾)。她一篇《為殺夫女辯》(原文章為《為殺夫者辯》)震動上海灘。“西林”一角,原型正是彼時滬上著名女作家蘇青。當年,蘇青在其主持的《雜誌》上特闢《殺夫案筆談》專欄,振聾發聵地寫道:
“唯有常受委屈和難堪的人,才是永遠心懷毒狠的,久而久之,化為厲氣,才必須做出驚天動地的事來。做出來的結果,使萬人流血,便是英雄;使一人流血,便是犯罪。”

牢獄中的詹周氏,尚不知曉這來自外界的聲浪。她與西林之間,橫亙着身份、階層與教育的巨大鴻溝。此時的她,已被薛至武毒打數頓,更被其以“將‘大塊頭’頭顱縫回屍體,令其夫婦‘再續前緣’”的謊言恐嚇至幾近崩潰。
她心中的恨意,根植於無邊的恐懼——她不知世間女子竟可提出離婚,她所受的規訓告訴她:此乃宿命。
她想掙扎着呼吸,卻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
02
故紙堆裏的女性悲鳴
當王許梅(楊冪 飾)為她唸誦西林的《為殺夫女辯》時,一絲“這女人竟懂我”的念頭鑽進了詹周氏的心。在旁人看來,西林是詹周氏“這世上另一個我”,亦是一個女子在時代夾縫中掙扎出的、截然不同的人生選項。
當然,以現代視角審視,詹周氏、西林乃至王許梅,這三個身份迥異的女性之間,竟激盪出另一種靈魂共振。畢竟在那個年代,於大多數男女眼中,諸多桎梏皆是天經地義、不可逾越的鐵律。例如:
殺夫。
影片中反覆閃現魯迅《娜拉走後怎樣》的警句:一個離家出走的女性,“要麼墮落,要麼回來”。這命運的二選一,同樣懸於詹周氏、西林和王許梅頭頂,只是她們各自的掙扎形態各異。

她們的人生軌跡南轅北轍,社會地位雲泥之別。西林長袖善舞於名流之間,王許梅為求生不擇手段,詹周氏則渾渾噩噩於絕望的泥沼。
而她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那無聲或激烈的“抗爭”。
誠如魯迅所言,“要麼墮落,要麼回來”。
王許梅可視作詹周氏的“加強版”。她宣稱女子安身立命有三寶:“腦子、奶 子和肚子”。她以為憑藉與獄卒的苟且即可逃過死劫,卻不料亂世之中,她終究成了被輕易“銷燬”的物件。臨死前她慌亂中徒勞拍打那曾寄予希望的肚腹——她的死,陰差陽錯地鋪就了詹周氏的生路——

命運交錯間,西林買下了一個女子的奢望,給予另一個女子希望。
薛至武惱怒了。他自詡為執掌生殺予奪的判官,卻在輿論場上被西林壓制,在精神對峙中被詹周氏那沉默的堅韌所“霸凌”——
是的,當他仍居高臨下,以為還能掌控這小女子命運時,詹周氏卻在他眼前決絕地鬆開手,任由自己被黑豬啃噬。
那一刻,他自以為是的權力堡壘轟然坍塌。他徹底輸了。
薛至武不解,為何施加於他人身上屢試不爽的暴力,在詹周氏這裏竟如泥牛入海,毫無效力?
而在詹周氏的瞳孔深處,當薛至武第一次粗暴拽起她的頭髮逼其仰視時,那猙獰的面孔瞬間與“大塊頭”每次施暴後如惡魔般的嘴臉重疊:
暴力、漠視、不以為然。
這是詹周氏人生前半場的主題。

於是,死去的王許梅與被逐出法庭的西林,其精魂彷彿“附體”於詹周氏。那篇《為殺夫女辯》,字字句句化為她泣血的控訴。她終於將他人悲憫的側寫,變成了自己撕心裂肺的獨白:
“我終日與貧窮、暴力、飢餓為伴……”
字字如血淚,句句似刀鋒。
不僅震撼了法庭內的眾人,更穿透銀幕,直抵觀眾。
影片尾聲,詹周氏剪去長髮,坦然展露曾被她刻意遮掩的面部瑕疵。神情從最初的驚惶怯懦,蜕變為一種令人心碎的平靜。
而“殺夫案”本身,隨着政權更迭的浪潮,即將進入下一個故事。
熟知這段往事的觀眾,早已知曉“詹周氏”的最終結局。
然而,超脱於案件本身的深遠意義,卻綿延至今。
那個“終日與貧窮、暴力、飢餓為伴”的女性剪影,並未湮滅於歷史的塵埃。關於她,以及千千萬萬個“她”的爭議與思考,伴隨着輿論的激盪與文明的跬步前行,從未停息。
03
“詹周氏”們的悲喜與延續
1945年的人們或許會詰問:
“證據不足便判其死罪,豈非草菅人命?”
而“究竟是何等絕境,逼得一個弱女子不惜同歸於盡也要揮刀?”這才是影片拋給時代、值得大書特書的沉重叩問。
陳可辛素來擅長雕琢大時代洪流中的微小個體,並藉由這些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逆向燭照出整個時代的靈魂底色。
無論是《三更之回家》中滯留香港的中醫夫婦那至死不渝的繾綣,《甜蜜蜜》裏隨命運漂泊流轉的歌聲情緣,抑或《中國合夥人》中背水一戰的弄潮兒傳奇,無不是用他們的故事講述一個時代的悲喜。
《醬園弄•懸案》作為一部女性犯罪題材電影,以“殺夫案”折射出一羣女性在時代巨輪下的眾生相。她們在“為何殺夫”這一核心命題上,跨越森嚴的階層壁壘,達成一種令人動容的靈魂共鳴。
尤以詹周氏為甚。她的骨子裏交織着懦弱與孤勇。倘若環境能給予她一絲相對公平的喘息之機,她斷不會選擇以如此慘烈的方式與全世界為敵。
然而,命運最終將她推上風口浪尖,以跨越日佔、國府、新中國三朝的奇案女主身份,烙印於歷史長卷,如今復現於銀幕之上。公眾對其態度的戲劇性轉變,也映照出人性深處天然的正義與悲憫。
它昭示着,無論歲月如何流轉,回望這樁“殺夫案”,其核心的叩問始終振聾發聵:
“要麼墮落,要麼回來。”
面對這看似僅有的兩個選擇,我們的目光不妨暫時從詹周氏身上移開,溯流而上,跨越千百年的歷史長河,看到在特定階段內女性迫於各種原因產生的絕望與爆發。
因為在那個窒息的年代,女性不被允許擁有第三種選擇。
於是,“詹周氏”們只能在沉默中爆發,或在沉默中消亡。
鮮少能如西林(蘇青)所洞見的那般——“久而久之,化為厲氣,才必須做出驚天動地的事來。做出來的結果,使萬人流血,便是英雄;使一人流血,便是犯罪。”
影片中公眾對“殺夫案”態度的驚天逆轉,其根基便在於一種羣體意識的朦朧覺醒:
她本可以不與“貧窮、暴力、飢餓”終生為伍的,但,她有過選擇嗎?
因此,“很遺憾以這種方式認識你”,是影片表層的敍事嘆息;而“很高興以這種方式認識你”,則是影片穿透銀幕、指向當下的社會迴響——它讓被歷史塵封的“詹周氏”們,終於獲得了被看見、被理解的契機。
《醬園弄•懸案》不僅鐫刻了特定時代裏一羣女性的血淚勇氣,更讓這部電影埋藏的所有待引爆的線索,承載起超越影像的期待。
最重要的是,它絕非僅僅呈現“被嫌棄的詹周氏的一生”,而是藉由這樁塵封的舊案,向今人擲地有聲地詰問:文明前行的方向究竟何在? 並讓這些女性角色用生命和智慧喚醒的思想,得以閃耀。

魯迅説:“要麼墮落,要麼回來。”
電影則告訴你:
為自己而活的女性,有無數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