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評人,到底在寫什麼?_風聞
文娱先声-2分钟前
我們先不談“樂評”的定義是什麼,這樣做切分其實沒意義,我想給個具體場景,比如説一首歌擺在那,可以從哪幾個不同方向切進去:
我們可以問:“它本身用了哪些技巧?”
我們也可以説:“我聽得好爽/好emo,我聽到了像是春天般的感覺。”
我們還可以聊:“為什麼它會在這個時間點誕生於這個藝術家的筆下(文化背景?產業結構?藝術家個人經歷?)它後面又影響了哪些人的哪些作品呢?”
(當然,還有一種其他層面的價值判斷,已經脱離了值得嚴肅討論的範疇,我在此不做展開了。)

做個圖博君一笑,這兩撥人可以先自己打一架
我覺得再如何總結,其實都已經不外乎這三種路徑,幾乎都能被他們涵蓋,而我們不妨把它們概括性地稱之為:
(一)技術導向的本體論
(二)感受/個人審美導向的主觀美學主義
(三)脈絡/文化導向的元敍事
這幾種裏面,只要不極端傾向於只訴諸某一種,我覺得都不容易得出很偏激的結論,當然,偏激的結論可能也同樣有它的價值。
01 音樂本體論
本體派的音樂評論觀,即以音樂的內部結構和技術手段為核心評價對象。這一派,追求的是評論的“工匠性”,其實也可以説某種意義上容易唯技術論。
這套方法論在古典樂評論中自不用説,是主流,貝多芬的調性架構、馬勒的動機發展、德彪西的配器,都是可以分析、比較的。但在流行音樂評論裏,它的顯形是從爵士樂的黃金時代開始的。
藝術一定是有某種客觀高下之分的。這絕不是僅僅針對於“創作者”而言的,也是針對“欣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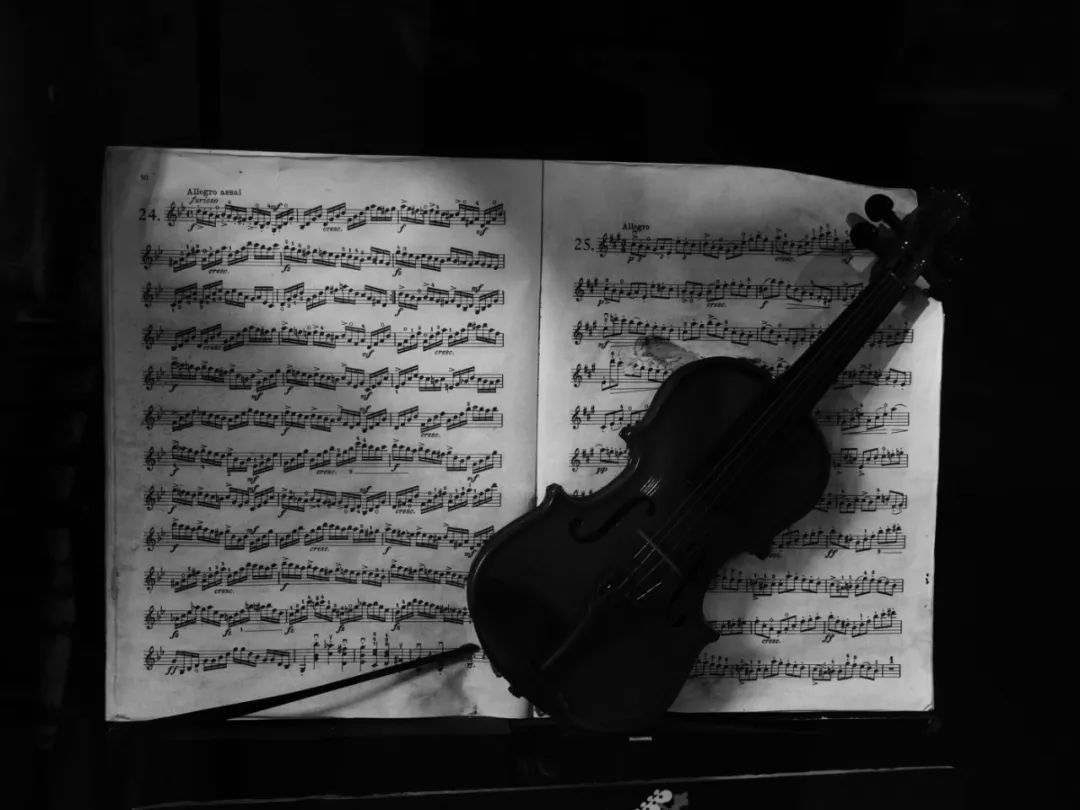
拿説唱舉例,“是不是接近美國原汁原味的匪幫説唱“這樣的説辭,即使在説唱圈子的審美體系裏也並不在乎,而真正有技術含量的flow、速度,文字層面如押韻、wordplay、內容表達,還有聲音、氣息控制、表現力等等,才是rapper和受眾們真正認可的技術含量的體現。
而貝多芬的音樂比網紅口水歌高級,高級在客觀層面,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和聲復調手法,多變節奏,動機發展的手段,精湛的結構安排,配器法的革新,這些都是網紅口水歌所不具備的。
這不是説所有人必須喜歡貝多芬,而是説從音樂技術的密度和結構的複雜度來看,他確實在某些層面上達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度。這本來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角度,但如果陷入過度依賴,就容易變成“做題家式”的技術至上主義,比如我們評價文學的時候絕對不會因為“修辭運用”來評價作品。
展開寫寫我能想到的幾個方向,以及每個單一方向走極端的不可取之處:
1. 聲樂技術
核心信念:一首歌好聽首先得唱得好聽,其他都是“伴奏”。這一派可能需要單獨從樂器技術拆出來,因為分析聲樂的人太多了,而且都有了派系之爭。
聲樂只是音樂呈現的無數方面之一。通常情況下,只有在評價live時,聲樂才會成為評論的主要對象。而對於已經有錄音室版本的歌曲,很多元素已經是既定事實,尤其是編曲也已經固定的時候,這時評論的焦點才會集中在聲樂的演繹上。而樂評應該包括對詞曲、編曲、演奏、演唱、錄音、混音、製作等多個環節的評價和分析,再推而廣之能有外延,談藝術影響前後,談社會價值等等。

我其實並不反對聲樂分析,但聲樂技術只能分析一部分音樂類型,比如用聲樂技術去分析Billie Eilish的音樂,完全就是雞同鴨講。如果一首歌不是追求聲樂至上,給你呈現最“美”的嗓音,而是人聲樂器化,或者本身追求的就是一種破壞性的美學呢?這套思路就非常有侷限性了。
2. 樂器技術
這個也是非常直觀的,常見於入門樂迷和樂手。典型的炫技崇拜,很多人認為"更高更快更強"就等於更好,那音樂都應該往極端金屬的方向發展,什麼高速雙踩、炫技solo速彈,但問題這些東西落在譜面上,很多就是簡單的五聲音階、32分音符密鋪而已。
我有的時候看着他們的手確實累,也確實能説一句牛逼,但很可能演奏有groove感、情緒留白、樂句流動設計的東西在我看來更有價值。很多演奏簡單的作品,恰恰比純技術炫耀的段落更讓人記住。
3. 作曲技術
或者也就是樂理派,這個裏面包含有和聲、結構、配器、織體編寫對位設計等等。樂理派走極端就是非常“做題家”的思路,這個“多即是好”的審美不管是門外漢(“和絃數量多所以它好!”)還是學院派,都有可能陷入(“轉調多、複雜所以它好!”)。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學院派,更是抱着“平五八是錯誤”這種教條主義試圖馴化不符合自己標準的音樂元素,大概率也是理解不了後電子流行樂普遍絃樂當pad用的手法。這不是在聽音樂,這是在改考卷。我不是説這樣有什麼錯,只是覺得這樣聽流行音樂只會處處受氣,畢竟流行歌裏不合你意的時候太多了,成功的反例也照樣能舉出一大堆古今中外的。最後,大概只能發出“xx獎是花果山在評哪個猴子叫的像人”這樣無能狂怒。
4. 製作技術
這個可以再細分一下,前期製作這派主要是在反向工程“我們怎樣得到這個聲音的”。對於不同流派的音樂來講,大如樂器、音色選擇、效果器、插件使用,小如麥克風型號、演奏廳的空氣濕度、樂器製作工藝,都可能涵蓋在內。比如説嘻哈、電子樂裏的“採樣技術”流,極端的技術崇拜的表現會對那些不依賴複雜製作技巧的音樂,比如説電子對用預製音色嗤之以鼻。
後期製作這派主要是混音、母帶,音樂工程方向的從業者和個別geek audiophile,比如説母帶黨會談論。其實能討論的範圍也比較窄,極端表現就是會説“椎名林檎的音樂水準不如K-pop,因為她的混音是災難”這種話。
5. 聲響、質感
這屬於一個很“雲”的技術主義派別,他們對好的取向比較不統一,也可以説主觀一點。古典樂説的“聲響”,搖滾樂説的“音牆”,現代電子樂可能説整體“氛圍感”這些名詞,都是大抵在形容這個東西。
所謂“發燒友”可能有自己的一套認為錄音應該還原現場,追求精緻通透的取向,有一派實驗噪音音樂樂迷也有自己一套對故意尋找髒、粗糙、奇怪、“難聽”的質感,離經叛道聲響的追求,但是他們二者極端化,也都容易本末倒置。
6. 精度偏執
這個我專門從製作拆出來,因為這已經不是音樂工業思維,而是理工思維。本身精度偏執沒什麼不好,促進音樂呈現更加完美,但有些人已經幾乎成為了音準、節拍機器。
這個極端的代表大多其實都不太懂音樂,但我也見過一個很罕見的,明明懂音樂卻鑽這種牛角尖的,會覺得某首其他層面都極其平庸的作品很好,但一首本身技術含量足夠高的歌,只要錄音室演奏有錯音錯拍的呈現,立刻就説“這是垃圾”,完全無視許多音樂,尤其是搖滾類的音樂中,有些人就是追求one take,追求jam這種粗糲感的事實。
説白了,就是喜歡用DAW一鍵quantize後的MIDI精準度去要求現場演奏。我覺得精度偏執派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在否定音樂的人性。音樂之所以動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那些不完美。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音樂素養應該包括知道什麼時候不用技術也是一種藝術家的選擇。**就像攝影師知道什麼時候不修圖,作家知道什麼時候不用華麗辭藻一樣,技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勝有技巧。
音樂藝術本來就存在着多種審美導向,粗分一下:一種是“為了表達而創作、演繹音樂”,另一種是“為了展示技巧而創作、演繹音樂”。

這兩種導向的出發點截然不同——追溯到原始人時期,音樂都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產生動力。一是為了表達內容、氛圍、情緒,內容就比如原始人妻子想讓丈夫知道“天黑了,回家吃飯吧”,她會以簡單的口頭旋律,和儘可能大的音量傳達這一信息,氛圍比如祭祀音樂,情緒比如干活時的號子,其他功能性很強的還有哄小孩的nursing rhyme等等,這種音樂注重傳達,而非技巧展示。
這種音樂的核心是表達,那麼技術只是服務於內容表達的手段。所以,這種音樂往往會選擇最能烘托內涵的技法,哪怕技術簡單。到今天,許多民間音樂依然簡單樸實,但傳神動人,這不就夠了嗎?
另一種動力則是對音樂形式的探索。比如説原始人發現敲擊不同的物體會產生不同音高、節奏,這引發了他們對音樂規律的好奇和探索。他們嘗試用各種方式組合節奏型,呈現音樂的多樣性。這種音樂在誕生之初,一開始就是更加重視技法體現。
這就對應着如今另外一種音樂,強調展示創作、演奏、演唱技巧。複雜的離調、多聲部對位等手法被運用得爐火純青,成為音樂的重心。樂器上各種花裏胡哨的技法、行雲流水的即興。人聲上各種炫技的鋭挫跳躍、難度極高的轉音等等。即使內容可能表達的就是非常簡單的情緒氛圍,但是卻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嚴密的賦格作品令人讚歎,感性的民歌同樣可貴。評價不同形式的作品,根本就不能用一個標準套。可以説,在這個背景下,不雙標才是一種雙標。(當然,要真能做到完全不雙標,堅持用同樣的標準審視,我也會敬你是條漢子。)
技術流派的樂評,我推崇什麼呢?我推薦所有人都去看Adam Neely對《The Girl From Ipanema》這首歌的“樂評”。這首歌可能是全球錄音室版本第二多的歌曲,理應證明它的火,但所有人都把它當成一首“很chill”的bossa nova標準曲那樣束之高閣,而Adam Neely做了什麼呢?

Adam Neely先介紹了bossa nova這個流派的起源與發展,將其定義為一種“看似輕鬆卻極其複雜”的音樂風格,需要澄清所謂“電梯音樂”的誤解。而這其中被誤解最深的《The Girl From Ipanema》就曾經被認為是歷史上錄製次數第二多的流行歌曲,自然引出了這首歌的各種問題。
然後他又説了調號問題,伯克利學生所作的Real Book把這首曲或許是按照Frank Sinatra等美國通行的版本,也或許是出於演繹的簡便性,把它按照F調進行記譜,也主導了美國乃至世界對這首歌的錯誤印象。而調號甚至都可以成為一個政治符號。他挖掘到了最早商業錄音是在1962年由Pery Ribeiro演唱的版本,調號為G,但是沒有流傳開,而後Getz/Gilberto的經典1963年錄音版本採用了D♭,併成為了對於巴西來説代表這首歌的調號,這背後有文化認同感的差異。
緊接着,他衍生地談到了《The Girl From Ipanema》的A段,基本上使用了與“Take the A Train”A段相同的和聲進行:I–V/V–II–V–I,再加上bII的三全音代替進行和絃,但這首歌加入了更多的bossa nova特有的和聲模糊性。當然,Jobim這種和絃設計不僅見於《The Girl From Ipanema》,在Jobim中後期的其他一些bossa nova作品中也常見。
然後他分析了旋律序列的使用技巧。在他分析之前,我幾乎沒有意識到,這首歌的前半部分可以拆解成三個音的切分+模進,並且分析了Real Book上不存在的布魯斯味道的副旋律解釋了美國黑人音樂在巴西的影響,且bossa nova本身在巴西就帶有一種“漂白”黑人音樂的文化政治意味。
而他着重強調的B段部分,Adam Neely用“ambiguity”,模糊性來形容其調性走向。他分析了橋段中如何通過不同的調式轉換技巧製造情緒起伏,例如從G♭maj7 → B7 → F♯m7 → D7 → Gm7 → E♭7,並且先給大家演示了Tin Pan Alley老式美國流行和聲體系會怎麼配這首歌的和聲,而經典的jazz harmony又會怎麼配這首歌的和聲。最後,他才進入Jobim的巧妙設計,他大概分析了Jobim的配法,核心就一句話,這是一種去tonic的減法思維。
當然,我不是説他的理解就一定是最正確的,因為複雜的歌曲,調式分析本無對錯,這首歌的理解分析版本已經多如牛毛,堪比國內紅學級別。

所以説了這麼多,我們一般説一個人能分析,可能就是他和聲學得好、節奏厲害、能聽出轉調的原理,這些當然在技術分析裏很重要。但Adam Neely是那種,你以為他是技術宅,其實他在同時做的也是關於音樂的地緣政治研究。
你聽他講Ipanema,不是“這首歌用了哪些和絃”這麼簡單。他會告訴你Real Book是怎麼“帶跑偏”了幾代爵士學生,為什麼你以為這首歌是“電梯音樂”,其實背後牽扯的是整個西方對拉丁文化的淺表化處理。這是什麼?這就是他不僅有深度,還有能meta-analysis(元分析)的廣度。
Meta-analysis是什麼呢?其實就是不光分析一個作品本身,而是試着去看它被怎麼看、被誰在看、怎麼看法,又怎麼塑造了我們的聽感。這個部分其實某種意義上就已經屬於後面我想講的元敍事了。
02 主觀美學主義
接下來講第二種,講“我感受如何”。這個其實跟後結構主義有點像,不是作品本身有什麼,而是聽者賦予它什麼,音樂是“體驗”。
在樂評領域,有人把它往美學上升,從個人出發來拍板好壞,很多人自然是最容易嗤之以鼻的。但其實我是來給這種寫作平反的,因為哪怕從技術出發,不管再怎麼説價值層面的東西也好,本質上也只是作者覺得好,歸根到底,一切價值判斷都來自人的判斷。
我曾經就看到過某知乎大v,在分析某個“華語樂壇yyds”的作品的時候先把他的簡譜扒出來,然後逐句羅列一遍,字裏行間不乏溢美之辭,最後不可避免地總是殊途同歸能推導出這麼創作、這麼改編如何如何好的結論。
我想説:so what?同樣的一個樂句,我可以説它以級進為主的作曲是樸實、接地氣的表現,也可以説它是很無聊的鋪陳;我可以説一個七度大跳感覺非常驚喜,讓人耳目一新,也同樣可以説它聽感很突兀割裂。如果你的樂理知識不是為了輸出一個客觀理性的分析而服務,而是用來做這種似乎是恰了飯的通告一樣,帶着結論找佐證,那這一通分析又有什麼價值?
**主觀式的音樂評論如果寫得好,對我來説,就接近王爾德的名言:批評本身就是一種創作。**這些人評價它的方式,也在創造新的意義,可能有它們自己的文學價值,美學價值,或者情緒價值,總之,這方面的價值是其他兩派都不可替代的。
比如説,我在學pop music這類課程的時候,基本上會要我去要看大量的music journalism(音樂報道)。這批journalists不關心“鼓點是不是緊湊”,而是寫聽這首歌時自己正在和某個音樂人在什麼lounge裏吹牛逼、夜晚的天氣如何,然後回憶到自己在倫敦某個地鐵站哭到不能自已的anecdotes(軼事),而且第二天的group discussions(小組討論)要建立在看類似這種東西80頁的reading的基礎上,並且作者的觀點很可能隨機出現在中間某一頁的某一自然段。
我一開始完全無法接受,覺得這不是評論“歌做得怎麼樣”,而是評論“這首歌在我身上做了什麼”。但慢慢理解到,他們真正重視的,是聽者的情境、記憶與感知是如何與這首歌編織在一起的。而且,第二天的小組討論還真的會以這些看似“遊離正題”的主觀文字為基礎來進行。
據我個人觀察,嚴格遵循這種文風的“媒體”倒是不多,但媒體人不少,Lester Bangs算一個,他寫搖滾的東西就經常使用意識流式的長篇大論。可能在如今更類似豆瓣短評,網易雲評論區級別的熱評。而一般我所理解這種樂評的最高境界是對於作家而言,比如説村上春樹寫爵士樂的東西,你説它是“樂評”嗎?好像也不盡然,叫聽後感或許更合適。但是他寫這種聽後感時,無需直接告訴你他用了哪些技術,但是用的遣詞造句,極具感染力。
比如這篇:
Chet Baker的音樂裏,有一種絕不含糊的青春氣息……他在單簧管四重奏中的演奏初聽之下熱情奔放,實則有一種深沉的孤獨況味。無顫音的號聲平地拔起,直衝雲霄,而又奇異地全然不留餘音,在歌聲尚未充分成聲的時間裏便被包圍我們的牆壁吞噬一盡。
並不是技術上有多麼老到,藝術上亦非爐火純青,演奏驚人地隨心所欲。我們甚至為之感到不安:這麼演奏,不會在哪裏摔跟頭?不會“喀吧”一聲摔斷?號聲是那樣高潔那樣幽怨。其中或許沒有劃時代的底藴,但底藴的闕如反而撞擊搖撼我們的心,它類似我們在哪裏體驗過的什麼,極為相似。

讓你相信,“這就是Chet Baker。”這種評論就像馬格里特的煙斗,評論者藉着作品,自畫像自己的感受世界。
我覺得寫得好的,可能比他們聽後感的對象本身還有意思。
03 元敍事
最後我們講元敍事,也就是將作品置入文化、政治、社會、產業脈絡,音樂人本身,音樂人圈子,音樂人-聽眾圈子……中進行前因後果的思考。
其實早在18世紀,Joseph Addison就提倡“輕批評且富見聞”;19世紀初,John Sullivan Dwight將音樂寫作大眾化;蕭伯納更將樂評與時評融為一體。
蕭伯納之流的批評之所以有所謂的文化威望,其實從來不是靠“噴人”或者“寫雜燴”本身,而是因為評論者在評論的同時引導了一個時代的品味結構、審美判斷、價值秩序。他的音樂批評與他的戲劇觀、政治觀、文化觀是聯動的。也正因如此,他的批評才跳脱出“誰用了什麼技術”這種層面,變成了“這個社會怎麼聽音樂”的思考。
聽起來,這單獨拎出來好像就已經是一個更高級的評判方式,對吧?但你會發現,即便從元敍事出發,人的判斷仍然分裂,甚至更分裂了。
為什麼?因為我們各自選擇的“元敍事”,本身就立場不同:你從“反抗消費主義”角度切入,會罵K-pop是造星流水線;我從“給邊緣羣體話語權”的角度切入,會説K-pop是亞洲聲音在世界的擴大,衝擊西方中心;他從“文化輸出”的角度切入,會説,K-pop簡直是韓國文化的軟實力奇蹟,本質上都沒説錯。
至於那些持一首歌,需要對其從怎麼樣創作的角度進行解構才是合格樂評的説法,縱然有一定可取之處,但是還是略微偏激。因為當你沒有辦法瞭解它放在音樂界的位置的時候,很容易下有失偏頗的結論。
就像那種以普通的大路芭樂見長的流行創作歌手,出了一首dancepop,就有可能因為耳目一新而備受讚譽,但是實際上這僅僅是因為這首歌的風格,對於他來説新穎,而對於歐美同期的主流樂壇來説,這就是最工業最口水的編制。再比如説像邁克爾傑克遜這樣的歌手,許多僅僅對他有所瞭解,而缺乏對於歐美同期的流行作品的工業水準知識的人可能就會對他的定位產生錯誤的判斷。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有的時候,擁有一個看宏觀的能力,能夠進行比較分析,對一首歌是否在它同時期有所突破,在一個流派中和跨流派的價值,帶給後期的風格影響,是需要實打實的有聆聽數量,並且有聆聽能力的人才能做到的。
我其實覺得大部分對於文本的分析也算在內,因為大部分人分析文本同樣不是在看它歌詞寫的技術含量高不高。
實際上,流行歌的審美取向根本就不止有一種。有些音樂存在本身就是為了文本服務,這就是它的音樂核心。在這種情況下,去着重筆墨分析它的作曲實際上並不能提供一篇非常有價值的樂評。用狹窄的知識面去單純分析它的作曲水準,反倒不如對於那些創作者的思想深度以及時代背景(甚至哪怕包括創作者在創作時的感情八卦之類的)研究要來的有價值。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比如説丁太升那種樂評姿態的根本邏輯,不是主觀愛罵,而是信奉了一套敍事。什麼敍事呢?我覺得他其實特別像當年rockism(搖滾主義)的思潮。他認為,真正的音樂應當有“表達”、“態度”。“唱得沒問題,但態度很差,”這句話在一個pop音樂世界是沒法解釋的,但在rockism裏,它是致命的。

Rockism指的是什麼?它的核心邏輯是:一定範圍的技術崇拜(崇拜solo,演奏技術,崇拜聽起來“高級”,不流俗的和聲調式設計,但不崇拜演唱技巧、製作水準);搖滾是藝術品,流行是工業品;樂隊音樂比製作人音樂真實,唱作人比歌手高貴;有髒兮兮的live錄音比拋光後期更keep it real。
這股風潮在1970年代形成,它來源於反商業,反文化的左翼敍事,到了80年代,NME和Rolling Stone上的大部分樂評,會默認這是一種“高文化的立場”。比如説Neil Young寫的是真話,Whitney Houston唱的是別人寫的垃圾,你有看過這人自己彈吉他嗎等等。
所以rockism的技術崇拜是選擇性的:不流行、不油、不刻意取悦聽眾、最好能難倒一批業餘樂手(參見第一點),這才叫real。
老一輩樂評人如李皖、郝舫等人,如今華語圈子很多小眾愛好者,以及國際上的RYM的審美主流趨向,其實本質上的審美就是這種rockism的延伸。他們會認為,好音樂=反流行、去工業、強調演奏或者作者性、調式高級、最好反映時代。當然這種取向的極端反面例子就是K-pop,所以這些人會默認一套“只有某些風格才值得認真聽”的品味偏見。
而到了2000年後,就又迎來了poptimism(流行樂樂觀主義)的風潮,Ann Powers、Carl Wilson,以及其實非常代表性的就是Pitchfork團隊了。他們會告訴你倒不是説所有商業流行都是好東西,而是説商業流行裏也有好東西,也有複雜度,只是你沒去看。所有被喜歡的都值得認真分析,這是一種去中心化的視角。
如今微博樂評人、聲樂系樂評人等等,其實很多就是poptimism的延申,對流行音樂表現形式價值的重新肯定。這些人掌控了流量,掌控了“樂評人”的話語權。
所以,即使我們都同意“要從意義出發”來討論音樂,我們理解“意義”可能本身就完全不一樣。不是説哪一個“更對”,而是看你想要從音樂中獲得什麼。這時候,所謂“好壞”就根本不是音樂層面的事了,而是誰更會講故事,哪一派更能控制話語權。
而我們現在呢?我們已經活在一個後poptimism時代了,不再能靠“擁抱流行”顯得進步,但也不能回去説“技法/搖滾才是好的”,那樣你會被罵“老白男”。於是就出現一種話語困境:每個作品都可以被賦義,每種音樂都可以拆解;你能寫,但你寫的意義並不比AI瞎編的多多少。
Poptimism時期那種強行“賦予流行深度”的寫作,如今變成了一種拼湊式的修辭手法,我們甚至會讀到很多樂評像模板寫作:“這首歌輕盈的表象下,反映了當代青年對X的焦慮”——一讀完就知道下一句要講什麼了。這其實讓評論寫作者、普通聽眾,甚至音樂人自己都陷入一種迷茫狀態。

後poptimism時代,真正的難題不是“流行歌是不是好”,而是“你還能不能説點別人沒説過的話”,這更多的是傳播學、流量思維層面的東西。
話又説回來了,審美和認識論這個東西,不管是從業者還是愛好者,人人都能建立。但是為什麼你的審美一定是代表着審美的正確方向?或者換句話説,我們自己也有耳朵能聽,有大腦能思考,為什麼要聽你的判斷呢?其實説穿了,大眾還是需要這些人在音樂評論的某個層面建立能體現自己真正的專業性的東西。如果長期都是情緒輸出,難免會被反噬。
像丁太升就常常給音樂人做出純抨擊乃至“罵街式”的評價,並沒有舉出橫向比較的上位替代例子,卻拿自己明顯不擅長的東西比如《黑刀Style》《慾望和情感之間》這種讓人一言難盡的作品下場參與,正中了抱着“你行你上”情緒觀眾的下懷。這就會很明顯難以服眾,甚至會讓自己的資格受到質疑。
所以,我認為,“樂評人”其實本質上應該幹好一件事,就是講好自己知識場域內的東西——當然,絕不僅僅是樂理,擅長講和聲、曲式、旋法、配器就去講這些,擅長樂器技術的就去分析樂器技術,擅長音樂製作的電子層面的就去分析製作層面的東西,擅長聲樂的就去分析演唱,擅長文本的就去分析歌詞,擅長講音樂史的就去講音樂史,擅長講文化的就去講文化,擅長講產業和商業趨勢的就去講產業,擅長當偵探的就去分析歌手創作動機趣聞八卦……
引領審美的責任使命,可以肩負,**但請儘可能壓縮空洞的言辭,多提供實質性的內容。**恰恰是過多的毒舌+説教,過少的乾貨輸出,才是現如今有一些樂評人在大眾裏喪失公信力,乃至提出這個“樂評人還有存在的必要麼”這個問題的原因。